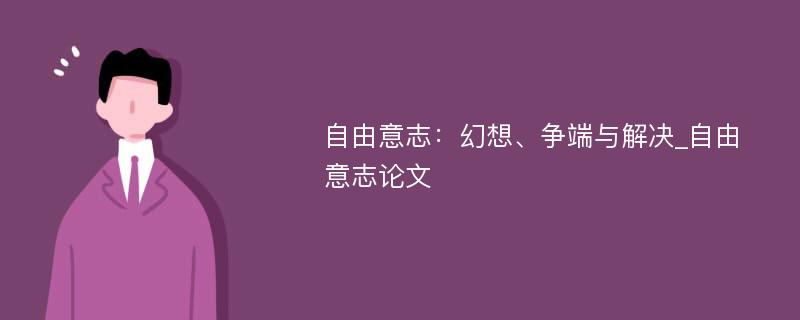
自由意志:幻象、纷争与解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幻象论文,纷争论文,意志论文,自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志码:A
在所有文化中,人们都相信存在某种程度的意志自由。能够选择自己的行为,是人之为人的特征之一。在哲学领域,这个概念意味着心灵控制身体的部分动作;在科学领域,自由意志意味着,身体的动作包括大脑在内,不全由物理因果关系所决定。然而,今天的神经生物学正在冲击着支撑人类社会的这根支柱。
自由意志是一种无意识?
人类是否能够以及怎样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行为?这一难题困扰了人们几个世纪。美国心理学家李贝特(Benjamin Libet)1982年得出的研究结果曾经震撼了整个科学界和哲学界。实验是这样的:李贝特找来一些志愿者,用脑电记录装置监测他们的脑电活动,然后给他们下达指令:无论何时,只要起念头,就动动手指。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理解,“动动手指”都是一种自由意志的产物:你决定动了,这个意识产生,于是运动皮层发出指令,通过神经—肌肉接头调动相关肌肉群,接着手指就动了,其次序是“意识决定要动”,然后“相关脑区活动,运动皮层发出指令”,最后是“手指动”。
但是脑电记录装置显示,当志愿者“意识到自己要动手指”时,大脑早已发出动手指的指令。也就是说,先出现“相关脑区活动,运动皮层发出指令”事件,过了大约300毫秒以后,才出现“意识决定要动”,接着又过了200毫秒左右,“手指动”了。大脑中引导身体动作的电信号(大脑准备电位,preparatory brain activity)的产生,比人们意识到并开始做出动作要早出几百毫秒。也就是说,在我们意识到之前,大脑已经做出决定。李贝特实验无疑展现了惊人的内涵:自由意志可能并不存在,至少在动手指这个简单任务上,是我们的大脑决定了行动,而意识,只是紧随其后。
二十几年过去了,为了弄清其中的机制,海嘉德(Patrick Haggard)等人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他们所设计的实验是,让志愿者坐在桌子旁,桌上有一个按钮,他们每隔10秒钟按一次按钮。然而,有些时候,他要求某些志愿者做出按下按钮的决定,却要在最后时刻阻止自己做出这一动作。整个过程用脑成像仪来检测志愿者的脑部活动。海嘉德发现,当志愿者阻止了行动时,涌向背侧额叶皮层和另外两个脑部区域的血流量就会增加,表明这些区域被激活了;当受试者按下按钮时,这些区域就是静止的。海嘉德说,这些区域与人类自我控制的能力有关。脑部的这些区域可能就是阻止我们做出某些事情的能力的来源。这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一些注意力方面的问题,比如冲动、缺乏自制力等。
很多批评者质疑道,在李贝特的实验中,大脑准备电位出现的提前时间非常短,这也许只是由于人们对有意识的运动或决策报告不准确造成的。鉴于这种怀疑,德国神经学科学家海恩斯(John Dylan Haynes)及其同事使用了现代成像手段,重复并扩展了李贝特的经典脑波实验,他们以功能核磁共振成像仪作为大脑扫描器对实验者进行了测试分析,进一步证明,自由意志的感觉其实只是一种幻象。实验参与者的任务是,自由地决定用左手还是右手食指进行按键反应,同时他的大脑被进行扫描。参与者通过指出屏幕上一串连续变化的字母,来报告他做出有意识反应的时间。李贝特的实验证明,通过大脑活动可以辨别一个人将在两个选项中选择哪一个,而且辨别的时间早于这个人自己意识到他将进行哪种选择。而海恩斯的最新研究支持了李贝特的理论,并进一步拉大了时间间隔[1]。海恩斯认为,在人们作出某个决定前,大脑会在无意识中自发性地兴奋,这是大脑为随后作决定而准备的过程,并非人们通常认为的思考过程。
如此说来,自由意志仅仅是个错觉?支持者解释,人们自认为是独立而自由地做出各种决定,而事实上,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没有一个负责全面指挥的司令官。大脑完成的所有工作,是大脑本身生理过程的产物,做决定的结果取决于大脑如何构成以及如何处理信息。自由意志只是事后的产物,如同一个傀儡。不过,在众多崇尚自由意志的人们看来,如果人类的行为和见解与自我意识无关的话,那么再冷酷的杀手也可以用这个观点为自己解脱,这无疑太荒谬。
假如意识不能控制我们的行为,那么它进化的意义何在?李贝特等人表示,意识的作用可能在于它具有否决能力,即停止去做那些大脑已发出信号要我们做的事情。这些科学家并不打算完全否定自由意志的作用,他们认为,自由意志虽然无法控制动作的发生,但是却可以投否决票,最终叫停这个动作。意识中枢并非仅仅听取汇报后就默不作声,若它觉得这个行为不合适,就会发出紧急命令,将已经下达的行动指令扼杀在摇篮里。因为,在“意识知道”和“手指动”之间有200毫秒的间隔,这是“意识”判断并作出是否要叫停的时间,一旦有必要,它就会快速制止这个行为。“制止”才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存在意义,也是海嘉德在脑中找到的那些区域的任务。在他看来,人类无法决定“自由做”什么,只能决定“自由不做”什么。
尽管如此,李贝特等人的发现备受争议。在李贝特的实验中,参与者被要求当他们决定移动一只手指时就说出时间,事实上,这一操作没有听起来那样直接。视觉活动是缓慢的,而参与者很有可能在他们作出意识决定移动后很快就有所反应。这将导致他们说出的时间过早(比如,当他们作出决定,他们的大脑已经在腾出时间处理时钟上更早的时间了)。李贝特的研究小组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在一个分开控制的条件下,要求参与者提供施放在他们手上的电击时间,而这个时间估计的误差被用于纠正参与者们作出动作决定的估计。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邓奎及他的同事指出,人们的触觉机制的不同会导致其功能运转速度的不同。他们按照李贝特实验的设置复制了控制情境,但是他们不仅要求参与者提供轻微的电击时间,还要求被试提供瞥向时钟以及听见时钟的滴答声的时间(该声音通过耳机传输)。研究者们发现参与者们对于视觉和听觉的估计并不比对电击感知的估计精确(比如:他们估计得过早了)。换言之,李贝特会在估计参与者们作出决定的时间方面因采用视觉或听觉控制任务而得出不同的结论。邓奎等人说,模式和研究中的主观偏差而造成的变动程度,使得他们在选用何种纠正标准来估算人们意识到危险发生的时间方面变得困难——李贝特的研究小组低估了大脑准备活动控制人的动作的动机程度![2]
然而,该研究对于大脑的自由意识仍有待于深入分析:第一、在准备电位的起始与行为决定之间仅仅存在几百毫秒的时间延迟,因此有可能存在一种潜在的不准确性,也就是说,在这么短暂的间隔中,通过主观报告的方式测量行为决定时间,也许会错误地将脑活动的开始与意图的形成这两者在时间关系上发生错误地分离。第二、准备电位产生于辅助运动区,它只提供了运动计划相对晚期阶段的信息,因此,并不能确定辅助运动区是运动行为决策的起源。
此外,该实验只是简单地去选择用左手还是右手去按钮,不能映射精神活动性或更复杂的思想决定。海恩斯说,在现实生活中所做出的一些决定,是很难由大脑扫描器进行判断确定的,比如:我现在要买这套房子还是另一套,接受这项工作还是另一项,等等。同时,大脑扫描器的预言也并不是完全准确,或许自由意志会进入做出决定的最后一刻,使人们改变令人不快的下意识决定。海恩斯就认为,我们的研究并不能最终否定自由意志的存在,虽然实验结果显示,无意识的决定远早于有意识的意图,但是我们还不知道最终的决定在哪里形成,因此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这些无意识的脑区所做出的决定是否仍然可以被改变。
主观的自由与客观的随机性
自由意识是否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存在?20世纪之前,随着牛顿物理学获得巨大成功,机械论的观点支配着科学界。按照牛顿经典理论,宇宙是一个巨大的时钟机构,依据定律机械地运转。这个封闭的系统根本容不下非物质的灵魂,因为根据粒子物理以及神经生理学的基础,如果我们的思考、行为、感受、意志等等的表现,是基于脑这个器官,而脑的运作是基于神经电冲动,电冲动是基于生理的电化学变化,电化学变化又是基于基本粒子之间的关系,而基本粒子之间的关系还受制于物理定律,那么我们的一切活动无可避免地是锁在因果链之中,包括意志。
量子力学迫使我们不再以确定性而改用或然率的方式来解释自然界的某些现象,而且,某些随机因素可能改变整个系统的结果,它们看来似乎都是不可预测的。于是,有人以量子力学中粒子的随机现象来作为自由意志的理论基础。然而,即使在实际操作上真的无法预测,在本质上,它们的运作也还是依据自然法则的,换句话说,它们的运作仍旧是被预先决定的。[3]
看来,即使是现代物理学也无法容许自由意志的存在。因此,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意志的基础是神经电冲动,还是独立于物质世界而存在的另一种实体?如果是前者,我们拥有自由意志的体验只是一种错觉。从而问题就变成,脑中如何及为什么创造这种错觉;如果是后者,我们就必须寻找意志这个非物质的存在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神经电冲动的。
按照神经科学的解释,“自由意志”问题内生于“神经元运动”中。这不啻于说,所谓的“先验理论”毫无价值。康德强调不能放弃我们的自由意志,尽管这是针对“惟有拒绝才彰显自由意志”而言的,但其“先验”色彩浓厚的论述及其影响,都在昭示一个问题:为什么让我们放弃自由意志这么困难?而与此同时,我们对因果论也坚信不疑。常言道,万事皆有因,我们预设了在我们与自然的关系中,一切事件的发生都是先前充足因果条件的结果。
由此,自由意志会成为一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决定论:如果凡事必有因,理论上我们可以追溯到第一因,并且按照因果关系来描述这个世界。按照决定论(determinism)的概念框架,当起始条件被确定后,自然界依照不变的物理法则来运作,未来的一切都早已被决定。根据这样的假设,意志就必须独立于因果关系存在,不然就会受限于因果关系的锁链之中,也就没有自由可言。因为,如果自由意志存在,则未来是开放的、不确定的。[4]此外,决定论认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无一例外地由该事物或事件存在或发生之前的先决条件以及自然规律唯一地确定,果真如此,人类所需要承担道德责任的行为则成为一个问题,因为该行为如果已经由各种自然条件所唯一地确定,人们似乎就没有选择和行动的自由,那么人们还需要为自身的行为承担责任吗?
康德在他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表达了一个有趣的思想,他相信,自然界的必然性和人的自由意志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真正的冲突。[5]然而自由意志问题在当代已被自由意志论者转换成这样一个问题:我(body-brain)是如何不受物理条件的控制作出决策。如此,人们自然可以合法地运用当代神经科学、量子力学等大量模型和证据。于是,关于自由意志究竟是什么东西(问题1)成为自由意志是如何产生的以及是否和决定论相容的问题(问题2)
关于意志自由是否与决定论相容,如果神经科学表明决定论真实,那么人们会放弃对自由意志的信念。自由论者从这一立场得出了推论:自由意志与决定论不相容,而且决定论是错误的,因为决定论暗示着自由意志不可能。与自由论立场相反,承认相容性似乎能为自由意志辩护。相容论假设存在常识性的自由意志的概念,认为自由意志与决定论是相容的。按照这个相容论的描述,我的行为表述了我的价值。相容论(compatibilism)意味着,自由论和决定论分别描述着现实的不同层面——纯粹主观vs.纯粹客观,或者,本体(noumenality)vs.现象(phenomenality)。如果相容论能够为源于一个人价值的行为的方式找到原因,那么这种因果联系效力为所有自由意志与道德称赞或谴责所需要。
近年来,兼容论者和自由论者从各自立场出发,对自由意志问题的阐释与解答作出新的尝试,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进展;还有一些哲学家则另辟蹊径,探索不同于传统的兼容论和自由论的新思路。[6]例如,慎思自由意志论认为,非决定论因素发生在人们进行慎思的过程中,而早于做出抉择的那一刻,类似的抉择自由意志论认为非决定因素发生在进行抉择的那一刻,所以人还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丹尼特(Daniel Dennett)认为,决定论并不威胁自由意志,我们拥有一种与决定论不相容的自由意志。与丹尼特不同,霍布斯认为,自由意志与决定论是相容的,我们所说的表面自由其实就是真正的自由,它与自由意志相容。丹尼特和霍布斯都承诺了自由意志,但是出于不同的理论立场。
这里,我们就自由意志的问题梳理一下几种观念:决定论/非决定论和相容论/不相容论。
1)自由意志与决定论不相容,根本不存在自由意志——这是强决定论观点;
2)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相容——这是霍布斯的观点;
3)自由意志与决定论不相容,但仍然存在自由意志—丹尼特的观点。
实际上霍布斯给出了对自由意志的消除式解决方案,现代的相容论者和消除论者受到了霍布斯的启发,提出了四个重要的问题,在Robert Kane看来,以下四个问题处于自由意志问题争论的核心:
A、相容性问题: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相容吗?
B、意义问题:我们为什么需要一种与决定论不相容的自由意志?这种自由意志就是我们想要的吗?如果是,为什么?
C、可理解性问题:这样一种与决定论不相容的自由意志是可理解的吗?或者如批评者所言是神秘晦涩的吗?
D、存在问题:这样的自由意志存在于自然的秩序中吗?如果存在,在哪里?
这四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对其中一个问题的回答依赖于我们对其他三个问题的回答。大致来说这四个问题分为两对:相容性问题和意义问题;可理解性问题和存在问题。要论证确实有一种有意义的与决定论不相容的自由意志,就必须展示这样一种与决定论不相容的自由意志是可理解的,而且在自然世界能够找到。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处理可理解问题和存在问题。
这里,我们给出一个关于自由意志的常识定义:如果决定体可以做与此不同的决定,那么这个决定是自由的。为理解这个定义,需要把世界(universe)划分为两部分——决定体(agent)和外部世界(external world)。无论这种划分如何实现,以上定义都隐含以下三种可能:
a)在不同外部环境下,如果同一决定体可以做与此不同的决定,那么,这个决定是自由的——显然,这并不意味着自由意志。因为,即使一个无生命体(如一台自动调温器)也可以有这样的表现;
b)在相同外部环境下,如果不同决定体可以做与此不同的决定,那么,这个决定是自由的——显然,这也不意味着自由意志。同样因为,即使无生命体(如不同的几台自动调温器)也可以有这样的表现;
c)在相同外部环境下,如果同一决定体可以做与此不同的决定,那么,这个决定是自由的——这也不意味着自由意志。因为这只是一种随机选择,任何非确定性(nondeterministic)决定体(如一个随机对象或量子力学对象)都可以有这样的表现。总结以上三种可能如下:
决定体 环境 决定 自动调温器能否这样表现
相同 不同 不同 能
不同 相同 不同 能
相同 相同 不同 随机决定
虽然,以上三种可能并没有穷尽所有可能性,但是,关于这三种可能的讨论已经揭示:任何基于围绕一个决定的客观环境的定义都无法成功定义自由意志。其中,如果决定体的思想、感知、情绪和行为等也算在决定体之外的话,那么客观环境也应该包括这些思想、感知、情绪和行为等。因此,如果从围绕一个决定的客观环境的观点来定义自由意志,那么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这样定义的自由意志并不存在。可见,只有当存在着一个从其客观环境中分离出来的决定体时,才有自由意志的概念。这种分离正是二元性(duality)的本质。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二元性,则既没有决定体,也没有决定体作用的对象,那么,自由意志也就没有意义了。[7]
不管是哪种观点,真正的自由选择看起来难以琢磨。在确定性的世界里,也许的确不存在客观的选择自由。但是,客观自由的不存在并不能排除自由的主观性。客观世界中的“随机”和主观世界中的“自由”是不同的概念。真正的自由,要求我们的意志决定我们的行为,无论现象世界是否完全确定。
重新统合心灵与物理的因果法则
神经科学在揭开大脑神秘感的同时,必然会影响到与自我概念紧密相关的人类理性与自主性等概念。亚里士多德说过,人是理性的动物。人与其它动物不同,能用理性指导自己的行为,我们的理性不仅仅决定了自己的本质,也决定了自己的需求。理性为人类提供了一种人生追求——对我们生活的反思是人类的高尚追求。无论科学如何进步,人们从未怀疑理性是人类与动物一个本质区别。但是脑科学威胁了我们作为理性动物的化身,因为,神经科学决定论意味着,我们的行为比我们所认为的更少受到理性的指导。而作为理性动物,我们能感觉自身的存在是与我们作为自主选择者密切联系的。
值得一提的是,神经科学的另一些研究结果似乎在向我们表明,不必放弃自由意志或自我的信仰。认知神经科学家加扎尼加(Michael Gazzaniga)认为,我们的脑按照我们的指令工作,而不是其它方式,并且脑能对造成的“错误的自我”负责。他的著名的裂脑研究告诉我们,存在于左半球的一个心理“模块”总是试图去解释那些以非语言和非意识的形式工作的脑区所产生的行为和情绪。
大脑右半球与左半球呈镜像对比,即右半球接收来自人体左侧的信息,并控制左边身体的动作。左右大脑各司其职,分工处理外部信息。左半球专司语言处理及分析,同时善于观察细微之处;右半球则比较善于处理立体图形。加扎尼加利用大脑的分工来观察信息如何分别流向大脑左右半球。他要求病人注视屏幕上的某个点,然后,让某个词或某物体的图片快速出现在这个点的右边或左边,闪现的速度快到病人连移动视线的时间都来不及。如果这个点的右边闪过一张帽子的图片,这个影像就会落在视网膜的左半边上,之后视网膜会将这个神经信息送回到左半球的视觉处理区。加扎尼加接着会问病人:“你看到了什么?”因为左半球拥有完整的语言能力,所以这位病人会立即轻松地答道:“一顶帽子。”如果帽子的影像是闪在这个点的左边,那么这个信息只会被送回到非掌管语言的右大脑半球。所以,加扎尼加这时问病人:“你看到了什么?”病人则回答:“什么都没看到。”但是,当加扎尼加要病人用左手从一张有好几个图像的卡片中指出正确的图像时,病人却会指这顶帽子。虽然大脑右半球确实看到这顶帽子,但它却无法用语言回答,这是因为它没有拿到进入左半球语言中枢的通行证。
当加扎尼加对左右半球闪现不同图片后,情况变得更为诡异。加扎尼加对右半球闪现一张鸡爪图片,对左半球则闪示一张一个屋子和一辆车子埋在雪堆中的图片。接着他拿出一堆图片摆在这名病人面前,要后者指出哪一张图片和他之前看到的图片配得起来。病人的右手指着一张鸡的图片(这张和左半球之前看到的鸡爪有关),但他的左手却指着一张铲子的图片(这张图片和右半球所看到的雪景有关联)。当加扎尼加要病人解释他自己的反应时,他不是回答:“我不清楚为什么我的左手会指铲子。”而是立即编出一个很精彩的故事,毫不犹豫地说:“啊!简单。鸡脚配鸡,所以你需要一把铲子来清理鸡舍。”左半球看到了左手的反应,但由于不了解那幅雪景,所以它只能用已有信息来解释其所作出的那个反应。[8]
这种杜撰各种理由来解释自己行为的病症称为“虚构症”(confabulation)。接受过裂脑手术的病人以及其他脑部受伤的病人都常有“虚构症”表现,加扎尼加称左脑的语言中枢为大脑的诠释模块,其作用是针对自我所做的一切立即做出评论,即使它根本无从得知“自我行为”的真正原因或动机,也还是会做出反应。举例来说,如果对右半球闪现“走”这个字卡,病人可能就会站起来走掉。但问他为何站起来,他也许会回答:“我要去拿可乐。”左脑的语言中枢非常擅长编出各种解释,但却不知道行为背后真正的原因。[9]
不仅如此,德国科学家最近研究发现,在没有任何外界刺激的情况下,果蝇能自发地改变飞行方向。研究者表示,这一发现表明自由意志不仅可能存在,而且可能是大脑的一项基本功能。李贝特在上个世纪80年代所做的实验使得神经科学家们认为,这种所谓的“潜意识准备”(readiness potential)只是大脑简单地对外部刺激作出的反应,其功能仅仅在于将传入信号转换成输出信号,而意识只是大脑用来合理调控它已经作出的行动的方式。
那么,没有传入信号会是什么情形呢?Brembs和他的同事设计了一个果蝇实验。之所以选用果蝇,是因为动物特别是昆虫很机械,通常被认为只会对外部刺激作出反应。他们将单独的一只果蝇固定在一个纯白色(为避免视觉刺激)的小室里,并记录下它转向的意图。用多个果蝇多次重复之后,他们对得到的数据进行分析。
Brembs本以为结果将是毫无规律的运动和声音模式,就如收音机调台时两个频道之间的那种嘈杂声。事实却十分令人意外,果蝇的飞行模式有章可循。Brembs说,果蝇变幻不定的左飞或右飞是由大脑决定的。这一发现揭示了一种可能会形成自由意志的生物基础的机制,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已经从果蝇身上发现了意识。
果蝇选择的变化模式显示出很多生物学过程都具有的一种典型的非线性特征。研究结果排除了另外两种对于这种自发转向行为的解释,即随机论和纯粹决定论,从而在简单的决定论(把大脑当成简单的输入输出设备)和完全的随机行为之间开拓了新的中间地带。研究人员推测,如果自由意志存在的话,它应该就存在于这个中间地带。[10]
如果我们根据直观相信自由意志存在,那么,目前尚无任何科学理论可以用来解释自由意志的法则,否则,我们就必须同意,需要一种完全不同于现在物理规律的新概念框架来统合心灵现象的因果关系。而假如否定自由意志存在,由于自由意志在心灵概念的框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那么,我们便需要一个与现在心灵法则不同的新概念框架来重新理解心灵现象的因果关系。看来,无论结果是哪一个,我们都必须拥有一个新的概念框架。另一种可能性是,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既不同于现在的物理概念框架,也不同于现在的心灵概念框架,来重新统合心灵与物理的因果法则。质言之,在概念框架的结构上,心灵与物理概念至少有一个存在问题,而更可能的是,二者都需要改变。[11]
收稿日期:2010—06—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