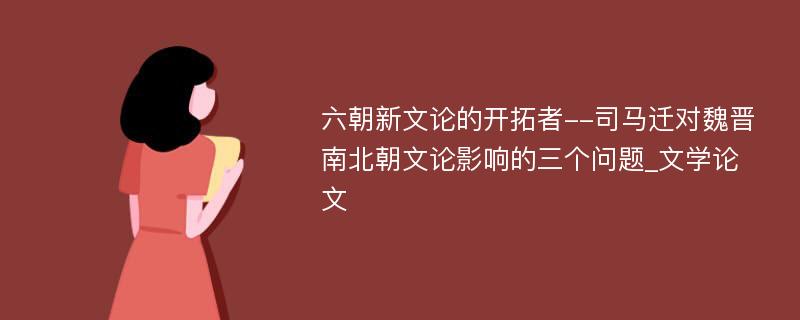
六朝新文学理论的先声——司马迁对魏晋南北朝文论影响三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声论文,文论论文,司马迁论文,学理论论文,魏晋南北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司马迁开六朝新文学理论的先声。他对学术性的“文学”与文学性的“文章”的区分和对文学家、文学作品的重视影响了六朝人对文学不朽价值的认识和对文学规律的探讨;他提出的“发愤著书”理论影响到六朝文论中的“蓄愤说”和“怨愤说”;他的“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影响了六朝文论中的“通变”思想。
关键词 司马迁 六朝文论 文学价值 文学规律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社会的急剧变化,出现了强大的思想解放潮流,迎来了文学的自觉时代,文学理论思想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新的文学理论思想的诞生,是由诸多因素促成的。笔者认为,汉代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的影响是其中的因素之一。关于司马迁的文学思想,拙著《史记与中国文学》已有论述。这里就司马迁对魏晋南北朝文论的影响提出三题,求正于方家。
一、司马迁对文学的重视与六朝时对文学的认识
魏晋以后,思想的解放、个体意识的觉醒,使人们对文学价值的认识有了新突破,把文学创作看成人生价值的追求,看成不朽的事业,而不只是政治道德的附庸,这是六朝新文艺思想的突出特点之一。最为我们注意的是曹丕《典论·论文》中的一段话: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身名自传于后。
曹丕对文学的认识,是六朝文论的第一声“春雷”,文学乃是永垂不朽的“盛事”,是比个人的生死、荣乐具有更长远意义的事情。文学的独立价值在这里得到确认。曹丕自己在《与吴质书》中,就曾说明他之所以撰写《典论》,就是为了“立德扬名”,死后“可以不朽”。这与前期儒家把文学作为教化工具迥然不同。这是一种全新的角度,是从个体人生出发来认识文学的价值,正因此,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指出:“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曹丕对文学价值的认识,奠定了六朝文论的基础。此后,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进一步说:
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文心雕龙·序志》)
人的形体生命如同草木之脆,容易腐烂。立言则同金石之坚,永远不朽。这也是从个人生命的价值出发,认识文学作用的。刘勰在《诸子篇》中出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群居,苦纷杂而莫显;君子之处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达,则炳曜垂文,腾其姓氏,悬诸日月焉。”曹丕、刘勰对文学不朽价值的认识,可以说是当时的一种普遍认识。[①a]
由于对文学价值有一定的认识,因此,魏晋以后,人们对文学自身规律的探讨也就前进了一大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注意作家个性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的观点,他所说的“气”就是作者的气质和才性。曹丕以此对建安时代的作家进行评论:
伟长独怀文抱质,恬寡淡欲……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德琏斐然有述作之意……孔璋章表殊建,微为繁富,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与吴质书》)
尽管曹丕受了当时社会品评人物风气的影响,但他能从作家个人的气质与才能方面去分析创作的得失,反映了建安文学向个性化发展的新趋势,同时也开辟了文学评论的一个新天地。此后,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进一步把作家的性情与作品的风格联系起来,总结了汉魏以来重要作家的创作特征,其结论就是“吐纳英华,莫非性情”。这种认识,实际上是人的个体意识觉醒以后的产物,如果没有思想的解放,没有人的觉醒,就不会看到,在社会角色之外,人还有自己的情趣、性情。
其二,注意到文学的想象构思特点。陆机《文赋》云:“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鹜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于是沈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堕曾云之峻……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陆机对艺术想象问题的论述,是十分精辟的,在文学创作理论的研究和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陆机之后,刘勰在《文心雕龙》创作论的首篇《神思篇》中专门谈论构思问题。“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物沿耳目。”刘勰还进一步论证说:“夫神思方运,万涂竟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这种对文学自身规律的探讨,比起魏晋以前,显然是一个长足的进步。
其三,注意对“情”、“采”、“味”的认识。文学创作的发展,使文论家对于文学本身的特点有了更多的认识,曹丕提出“诗赋欲丽”就已注意到了文学在形式上不同于其他著作。沿着先秦“诗言志”的线索,陆机在《文赋》中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强调感情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这在文论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朱自清在《诗言志辨》中说:诗言志,指的“表见德性”,“可是‘缘情’的五言诗发达了,……于是陆机《文赋》第一次铸成‘诗缘情而绮靡’这个新语。”“缘情”说比起“言志”说,更符合艺术的特点,这正是人的个体意识觉醒之后,文学由社会的人向着个体的人回归的一种表现。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把创作论部分总称为“割情析采”,专设《情采》一篇,详细论述“情”与“采”的关系,强调文采要本于情性,情采两方面要以情为本。在其他篇目中,也多言及“情”“采”。(见《原道》、《征圣》、《体性》、《熔裁》等篇。)由于对“情”“采”关系有一定的认识,因此,刘勰在《情采》篇中对齐梁文坛的形式主义倾向进行了批判:“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性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钟嵘在前人论述基础上,提出了“滋味说”:
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诗品·序》)
“滋味”说强调文学作品既要有“情”,亦要有“采”。“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作品才能有滋味,才能感动人。
其四,对不同体裁不同风格有一定的认识。曹丕《典论·论文》中认为“文本同而末异”,于是提出:“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陆机《文赋》则作了更进一步的论述:“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诗缠绵而凄怆。铭博物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狂。”刘勰《文心雕龙》从第五篇《辨骚》起,到第二十五篇《书记》止,属文体论,研究各种文体的源流、特点,无疑是前期理论的一大总结。萧统《文选序》也对各种文体的特征进行了论述。
六朝人对文学价值的认识,对文学规律的探讨,确实令人耳目一新。他们为什么那么懂文艺?为什么那么重文艺?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话,司马迁的影响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说起文学的“不朽”,我们自然想起这种思想的来源。《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叔孙豹谈人生的“三不朽”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把“立言”作为“不朽”之一,但“德”是首要的。到汉代司马迁,进一步继承发展了这种思想,他在《与挚伯陵书》中劝友人挚峻不要放弃人生价值的追求:“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伏惟伯陵材能绝人,高尚其志,以善厥声,冰清玉洁,不以细行,荷累其名,固已贵矣。然未尽太上之所繇也,愿先生少致意焉。”(《全汉文》卷26)就司马迁本人而言,他最初也是要建功立业、效力于朝廷的,但“李陵之祸”使自己遭受宫刑,“立德”、“立功”的路被堵塞。奇耻大辱,使他痛不欲生,他想一死了之,但一想到《史记》未完成,自己即使死了,与蝼蚁无异。“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报任安书》)于是,他把所有的希望、追求都放到写作《史记》上来,“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报任安书》)。“文采”要流传后世,这已经见出司马迁对于文学独立价值的初步认识。可以说,由于自己的不幸遭遇,司马迁把“立言”——写作《史记》作为自己的崇高事业,以顽强的毅力去完成这个不朽的工程。两汉时期,真正对“立言”有明确认识、而且以毕生心血去实践“立言”、要“成一家之言”的人,司马迁当是第一位。曹丕《典论·论文》:“唯干著论,成一家言”,《与吴质书》:“伟长……成一家之言。”曹植《与杨德祖书》:“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他们立意创新,反对空洞说教,反对形式主义,强调作品要有“情”,要有“味”,实质上也是提倡文学作品“成一家之言”的。
《史记》中已开始把学术性的“文学”与文学性的“文章”有意区分,注意到文学的独特性。[①b]对文学家及其作品特别关注,给屈原、司马相如等文学家专门立传,甚至非常动情地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史记·屈原列传》)。《司马相如列传》收入了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哀二世赋》、《上疏谏猎》、《谕巴蜀檄》、《难蜀父老》、《封禅文》,是《史记》中收文章最多的篇章。《李斯列传》收《谏逐客书》等,《乐毅列传》收《报燕惠王书》,《贾谊列传》中收《吊屈原赋》、《鵩鸟赋》,《邹阳列传》收《狱中上梁王书》,如此等等。足见司马迁重视有文采的艺术作品。这种做法,直接影响到班固的《汉书》,并影响到魏晋南北朝。
司马迁在评价作家作品时,也注意到了将个人品性与作品风格联系在一起。他在评价屈原时说:“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史记·屈原列传》)。正是由于屈原“志洁”“行廉”的伟大人格,才有光耀千秋之《离骚》。后来的曹丕、刘勰等注重作家个性与文学创作之间的联系,不能说与司马迁评论作家的做法毫无关系。
总之,两汉时期,有意识地注意文学的特点,重视文学家的社会地位,重视文学作品,司马迁当是第一位。他在许多方面直接影响到六朝人对文学价值及文学特征的认识。
二、司马迁的“发愤”说与六朝时的“蓄愤”“怨愤”说
司马迁在文学思想方面的一大贡献,就是提出了“发愤著书”理论。他在《报任安书》中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这是司马迁对前代文学创作的一个总结,也是他自己写作实践的理论概括,在实质上阐明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以及个人的身世遭遇对文学创作的巨大影响。这一理论,突破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揭示了文学创作中一条普遍规律,因而受到历代文论家的重视。魏晋南北朝时期,从理论上继承并发展“发愤著书”说的是两位文论大家刘勰和钟嵘。
刘勰对“发愤著书”说的发展最主要地表现在他对《诗经》和《楚辞》的评价上,提出了“蓄愤”说。《情采》篇云:
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乘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
刘勰把《风》《雅》之“志思蓄愤”与诸子之徒辞赋的“心非郁陶”作了对比,认为《风》《雅》之作乃是因愤而作,且是发自内心的“真”性情,这样的作品才具有力量,才能达到“讽其上”的效果。相反,辞赋家及南朝诗人抛弃了“志思蓄愤”、“为情造文”的现实主义传统,胸无怒愤而勉强编造其“愤”,即“为文而造情”,目的在于沽名钓誉,所以他们的作品不能感发人心,也就难以产生社会效果。在这里,刘勰从“真”的角度来论述“愤”。提倡“真愤”,即真情之文;反对无病呻吟,为文造情。这是刘勰对“发愤”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也是他的贡献所在。而“愤”的产生乃是由于现实的作用,所以,《时序》篇说:“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指出《诗经》中的“怒”、“哀”之音都是由于社会动荡而产生的。作家因现实而“蓄愤”,那么“愤”又如何发泄出来呢,刘勰认为是“比兴”。《比兴》篇说:“比则蓄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记讽”。比兴都是用来表达“愤”的手法。而在汉代,“辞人夸毗,《诗》刺道丧,故兴又销亡。”由于辞赋家背离了发愤、讽谕的传统,没有怒愤可泄,因而比兴手法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也体现了刘勰的“蓄愤”说。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对屈原“发愤以抒情”的特征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刘勰在司马迁及汉代其他批评家的理论基础上,注意到了屈原作品的不同风格,尤其注意到其中的怨情。尽管刘勰认为屈原作品有不符合儒家经典之处,但他对屈作的“哀志”、“情怨”的认识,还是继承了司马迁的思想,突破“以经立说”的传统做法,表现出一个文论家的独到见解。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思精的著作,在许多地方继承了司马迁的“发愤著书”理论。如在《哀吊》篇中称赞“贾谊浮湘,发愤吊屈”,说明贾谊的《吊屈原赋》是发愤之作。在《才略》篇中评道:“敬通雅好辞说,而坎壈盛世,《显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蚌病成珠”的比喻,说明人生因坎坷而产生愤怒,而愤怒之作易有审美价值。在《杂文》篇中,刘勰评“对问”一类作品时也说:“原夫兹文之设,乃发愤以表志。”可见刘勰对“蓄愤”的重视。钟嵘《诗品》论诗突出了《风》、《雅》、《骚》的怨恨传统,与刘勰以“真”论“愤”不同,他着重从“怨”的角度来阐发“愤”,提出“怨愤说”。他在《诗品序》中说:
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
钟嵘在这里所列的例子皆属命运不佳者,正是由于残酷的现实、痛苦的人生使他们产生怨愤之情,“心灵”受到“感荡”,只有通过诗歌,才能“展其义”、“骋其情”,把自己的“怨愤”之情发泄出来。钟嵘所总结的诗歌创作规律,一方面立足于儒家“诗可以怨”的传统理论,另一方面又继承和发展了司马迁“发愤著书”思想。钟嵘还把“怨愤”之说运用到品评诗歌上来,如评古诗“多哀怨”,评李陵“文多凄怆,怨者之流”,班婕妤“怨深文绮”,曹植“情兼雅怨”,王粲“发愀怆之词”,阮籍“颇多感慨之词”,左思“文典以怨”,刘琨“多感恨之词”,等等,这些“怨愤”之词,或反映社会动乱,或揭露统治阶级罪恶,或表达爱国悲愤,或抒发贫贱孤愤,或讽刺虚伪礼法,或抨击门阀制度。钟嵘从理论上对这种文学创作加以总结,在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在钟嵘的“怨愤”说中,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强调“文典以怨”,抒发怨愤必须合乎礼义典则,“得讽谕之致”,不能像《离骚》那样怨愤横生、有失典雅,也不能像嵇康那样“过为峻切,许直露才”,因此,这又回到了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中和之美”的理论上来,这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形成鲜明的区别。司马迁“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①c],冲破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樊篱,表现出强烈的“非中和”思想,其进步意义是很明显的。另外,司马迁提倡“发愤”,决不是一己之愤,不是为了个人的利害得失而呐喊,而是对黑暗社会的一种有力指斥,它是建立在进步的政治主张,积极的政治热情的基础上,像屈原那样“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抒发出来的是强烈的忧国忧民之情,而非个人的私怨。钟嵘把屈原与一些个人之怨的人放在一起,也是由于对“怨”缺乏仔细分析所致。
除刘勰、钟嵘的“蓄愤”、“怨愤”说之外,其他文论家对于“怨”“悲”也有所涉及。如萧绎说:“捣衣清而彻,有悲人者,此是秋士悲于心,捣衣感于外,内外相感,愁情结悲,然后哀怨生焉。苟无感,何嗟何怨也?”(《金楼子·立言》)这些都有助于我们认识“发愤著书”说的影响。
三、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与刘勰的“通变”观
“通变”一词源于《易传·系辞》。变是变化,通是通畅不阻塞。《系辞下》云:“变通者,趋时者也。”由自然界的变化论及社会的变化,指出人们必须随着时势发展而有所变化。
司马迁将《周易》的通变思想运用到人类社会历史领域,提出了在旧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保持社会制度的活力问题。他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己任,探究中华民族发展史,探究古今变化的规律。这里的“通”即司马迁所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之意。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谈作八书的目的:“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平准书》云:“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这些论述,尽管还没有完全跳出循环论的窠臼,但包含着一定的辩证思想。“今天”从“昨天”发展而来,要把握“今天”的社会,就必须了解“昨天”的历史。司马迁的《史记》,处处体现出“通变”思想。如从秦楚之际的战争风云,到刘邦建国,社会急剧变化。司马迁从“通变”思想出发,对这段历史作了高度概括:“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率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陈涉、项羽、刘邦三人就代表了这个时期的三个阶段。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中又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何必旧闻?”“今”以“古”为鉴,可以明得失,可以知教训,这即是“通”;但“今”与“古”又不相同,一切都处在变化之中,这即是“变”。所以,司马迁对古今关系的认识,也包含着深刻的“通变”思想。整部《史记》,上下3000年,司马迁注意到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如“十表”,把几千年的历史划为三个段落(上古、近古、今世),五个时期(古朴时代、春秋时代、战国时代、秦亡至西汉统一时代、今世时代),“司马迁是我国古代第一个具体划分历史发展阶段的历史家,用以表现历史之‘变’,具有作规律性探讨的卓识远见”。[①d]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都注意到了总结前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宋书·谢灵运传论》、《南齐书·文学传论》、挚虞《文章流别论》、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都不同程度地对文学发展史进行总结。刘勰尤其如此,一般认为,刘勰写作《通变》篇是受《易传》思想的影响,这是不错的。但如果我们再结合刘勰对文学发展历史的总结与探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不仅受《易传》影响,而且受到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思想的影响。
其一,能够从总体上把握文学发展的历史。《文心雕龙》不仅提出了深刻而系统的文学理论,还提出了比较明确的文学史观,并能联系社会背景,分析各个时代文学的发展变化情况,对各时期的代表作家作品,也作了简要的评述,勾画出从先秦、两汉、魏、晋以至齐历代文学发展的大致轮廓。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文学史大纲”[①e]。这个纲,明显体现了“通”的特点,犹如司马迁的《史记》是“通史”一样。如《明诗》篇,叙述了从唐尧、虞舜、夏、商直到周、秦、两汉、魏、晋、宋、齐历代诗歌发展情况;《诠赋》篇从赋的渊源谈起,逐次论述了战国、秦、汉、魏、晋时代赋的发展概况。关于文学发展的原因,刘勰在《时序》篇中提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文学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物色》篇中又提出:“古来辞人,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文学是在不断的继承与革新中发展的。《通变》篇则对此作了更系统的论述。刘勰“原始以要终”,以历史家的眼光认识文学发展的历史,具有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那种气魄。
其二,对各时代文学的不同特征,及各时代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有一定认识。这也是“通变”的表现之一。“通变”就是要探讨规律性问题。刘勰在《时序》篇中把宋、齐以前的文学发展史,概括为“蔚映十代,辞采九变”。根据各个时代的社会状况和文风,划出发展变化的阶段,然后加以评价。唐尧虞舜之世:“心乐而声泰”;夏商周三代:诗歌由歌颂发展到怨刺;战国时期:“百家飙骇”,开创“炜烨”之局面;两汉时期:“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建安、正始时期:由“梗概多气”发展到“篇体轻淡”;两晋时期:由“结藻清英,流韵绮靡”发展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的玄谈之风;宋齐两代:“英采云构”“才英秀发”。在《通变》篇中,刘勰把“辞采九变”又归纳为六个阶段: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尽管刘勰的概括不很确切,但他在“通”的过程中看到各代文学的不同特征,如同司马迁“通”3000年历史,但又注意不同时代的阶段性那样,是很有价值的。
其三,注意总结教训,为当代服务。要对历代文学进行“通”观,没有批判精神是不行的。刘勰在自己的著作中,由“原道”、“征圣”、“尊经”的原则出发,对文学史上一些现象进行批判。这种批判,是为了更好地总结文学发展的规律、为当代文学服务。当然,他的一些批判是以儒家眼光进行的,因而结论也有错误之处。但总的来说,在批判中总结,在批判中前进,促进当代文学发展,这也是“通变”的一种表现。司马迁写《史记》时,也曾“考信于六艺”,“折中于夫子”,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进行分析评价,如他所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是为今天提供借鉴。刘勰的目的也在于通过对文学史的总结,为今天的文学服务。从这一点来说,刘勰与司马迁也有相似之处。
总之,我们认为,刘勰的“通变”思想,是继承了司马迁“原始以察终”的“通古今之变”的思想,在论述文学发展、探讨文学规律时,表现出“通”的思想,把握不同时期的文学特征,以“通”观“变”,以“变”观“通”,在文论史上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以上列三题论述司马迁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思想的影响,从中可以看出,六朝新文论的出现,决非偶然,继承和发展前代文学思想是一个重要方面。司马迁是一位历史学家,也是一位文学家,他对历史的许多真知灼见,同样也适用于文学。《史记》本身就是历史与文学的融合。司马迁在文学上的贡献主要是在他的写作实践上,即以生花之笔描绘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他的文学理论思想是与历史学思想密切相联的。我们说司马迁开六朝新文学理论思想的先声,并不是有意抬高司马迁,而是一种实际的存在。
注释:
①a 关于文学的价值,曹植认为是小道,对此,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据我的意见,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意,遂说文章无用了。”
①b 详见拙著《史记与中国文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3页。
①c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①d 张大可:《史记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7页。
①e 张文勋:《刘勰的文学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
标签:文学论文; 司马迁论文; 文心雕龙论文; 典论·论文; 南北朝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魏晋南北朝论文; 六朝论文; 历史规律论文; 屈原论文; 汉朝论文; 史记论文; 读书论文; 离骚论文; 报任安书论文; 情采论文; 二十四史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