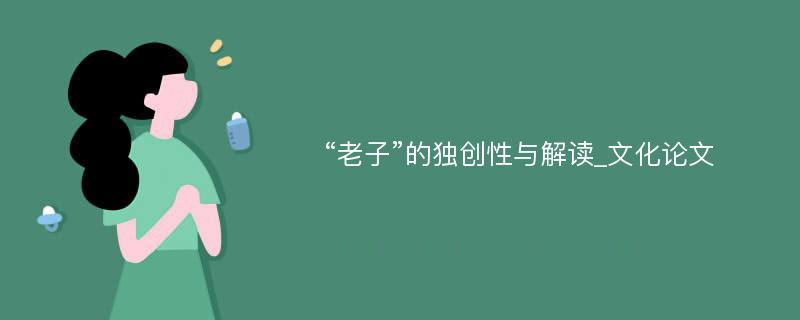
《老子》的原创与诠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老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道-自然”:《老子》① 的文化原创
以“道”为核心的意义系统的开创是老子的贡献。虽然“道”这个字在殷周以来就广为使用,不仅《六经》中有,甚至甲骨文和金文中也出现了,但其大都是在具体的意义上使用的。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有试图在超越的意义上使用“道”的趋向,如说“吾道一以贯之”(《论语·卫灵公》,下引只注篇名)、“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人能弘道”(《卫灵公》)等等,但却始终未能脱离社会治道、人生正道而形成超越的意义系统。老子则不然,他要在终极的形上层面超拔天、地、人,并探寻能将其贯通起来,从而既是宇宙的本根、又是人生存乃至生命的内在根据的东西,于是“道”作为合一“天人”的纽结而被“创生”出来。
“道”的原创性首先在于老子将“道”与宇宙万物生成、根据以及人的生命存在联系起来。老子所做的是对宇宙万物的终极性思考:道不仅是万物的总根源,而且是宇宙的终极性存在,万物由之以生,由之以成,并最终复归于“道”,所谓“夫物芸芸,各归其根”(《老子》十六章,下引只注章次),可见老子首先给“道”赋予了宇宙本原论和生成论的意义。同时,作为万物存在的内在根据,“道”又有本体论的意义。老子说:“道者,万物之奥”(六十二章),“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三十四章)即道是万物存在的根据,万物不过是“道”展开和显现的状态。道无所不在,无所不成。这个道也称为“大”,称为“一”,故道又是一本性自足的整体,是无限和普遍,它与万物同一。
与本体的、实存的“道”相关,老子还创设了一个重要的概念,这就是“德”。“德”是老子从形上过渡到形下的一个重要概念。按照陆德明的解释,“德者,得也。”得之于道而内在于物自身的属性就是“德”。“德”亦与“性”相关,是表示事物属性的概念。但老子更多地讲“玄德”,亦即“道”之“德”,其内涵就是“自然”。在老子那里,“自然”已脱离了实体的意义,成为彰显“道”的属性、功能的范畴。“道”的原创性集中体现在“自然”概念的提出和运用上。“道-自然”的原创性主要在于:
首先,它表征着宇宙万物的本然状态及其过程。在老子看来,宇宙根本的、与其本性同一的存在状态是自然。“自然”是指事物的“本然状态”。道对于万物来说其根本的德性(玄德、自然)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五十一章),它依遵万物的本性自生、自长、自成,也就是说,“道”“认同”存在者“自己成为自己那样”,并按照“自己那样”存在和发展着、变化着,如同王弼所说,“在方法方,在圆法圆”。
其次,“自然”也是人生命的本真状态,是人“自在”“自得”的精神境界和生活智慧。当世人以种种“有为”和智巧,既冲击着自己的生存环境,也异化着人自身的质朴本性时,老子则进行着反向思考,即对宇宙、人生的负价值作探寻。这种自然主义的价值取向开出了一条与当时几乎所有的价值体系迥然有异的思想进路。老子认为,人合理的生存状态应该是“自然”的状态,即本真的、自主的生活状态,它体现了人生境界与自然宇宙的合一,也体现了一种个体的精神独立和意志自由。这里,老子把宇宙本体与人的生命意义统一起来,开创了异于儒家的道德价值追求、而以自然为本的“天人合一”体系。由此,“无为”就成为处理天与人、人与人关系的根本态度和方法。“无为”之“无”,蕴涵了一种对人的某一类行为的否定,即对依待、虚伪、巧智、造作、刻意雕琢等背离人性本真的行为或外在的、形式化的东西的否定。
再次,“自然”作为人面对宇宙万物应持的根本心态,就是守“静”、“无常心”。“道”从根本上说是“静”的,而“动”(躁)不过是它的暂时的、显现的状态。“莫之命而常自然”,“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十六章)。静是宇宙的本体,也是人生本真的常态。懂得这一点就是“明”,相反,“不知常”而“妄作”,就会带来很不好的结果(“凶”)。这样,“静”不仅是宇宙的第一原理,同时也是人格的本体,“守道”者就要保持平静和谐、恬淡无欲的淡泊心境。“静”作为一种境界,并非是独立于万物之外的空灵,而是即物而自静的状态。从人的生存本体论(自然)意义上说,“道”是境界的形上学。
最后,“自然”在社会生活中表现为“无为而治”的“治道”。尽管无为的治道在先前的政治生活中已有人提出,如所谓“垂衣裳而天下治”(《周易·系辞下》)、“垂拱而天下治”(《尚书·武成》),然而那主要还是作为一种策略而尚未成为根本的治道理念。老子的无为而治则是宇宙本体论落实到现实社会生活的“自然之治”,它是老子“以道观物”从而对社会文化所带来的种种异化现象做了反思之后的理性选择。“无为而治”既是一种统治术(“道治”),即顺任自然、无所妄为、杜绝干预的治术,也是一种社会理想,即无制度安排、无等级差别的自然状态。所谓“治大国若烹小鲜”(六十章)、“以无事取天下”(五十七章),此即基于“道”的统治术;主张统治者要“以道佐人主”(三十章),过一种“小国寡民”、“使民复结绳而用之”(八十章)的生活,此即合于自然的理想社会状态。显然,这种理想社会与自然质朴的人性追求以及自由自得、恬淡无欲的人生境界相联系,“道”的本体论与“自然”的价值论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统一。
二、《老子》的诠释系统
原创文化一般是具有持久影响力的整体系统,它开创了一个以往没有的精神世界,因而可以开悟当世、启迪后人,并不断地被诠释且在诠释中获得生命力。原创的东西虽“前无古人”,但“后有来者”。在中国哲学史上,《老子》即是这样的一种原创性文化典籍。
1.庄、玄哲理系统:本体论的彰显
现有资料表明,《庄子》是对《老子》进行解释发挥的最早文献。《史记》称“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老子·韩非列传》卷六十三)唐陆德明《经典释文》说:“庄生独高尚其事,优游自得,依老氏之旨,著书十余万言,以逍遥、自然、无为、齐物而已。”可见《庄子》与《老子》有着明显的学术渊源关系。
庄子承继了老子的宇宙论,而更多地发挥了其本体论思想。从《庄子·大宗师》所说“道”具“有情有信”、“无为无形”、“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生天生地”等特征以及关于道“无所不在”、“物物者与物无际”等说法来看,庄子明确认为“道”虽实存但不是实体,它是无限的、普遍的、与万物同一的,万物因得“道”而自然生灭。“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庄子·天下》,下引只注篇名)“皆原于一”,成玄英疏:“原,本也。一,道。”即万物“皆本于道”,这些都透露出庄子确是以道作为万物存在的最后根据的。
庄子对于“自然”,除承继老子“天道自然”、“因任物性”、顺从规律、无为无造等意义之外,更多的是将其作为“至人”“真人”的心灵境界来加以发挥。其发挥有三:一是“顺物自然”、“安之若命”。所谓“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圹埌之野”,“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应帝王》)。二是任性逍遥,无为自得。庄子说:“逍遥,无为也。”(《天运》)又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知北游》)如成玄英疏所说:“无心因任”,才能逍遥自得,心旷神怡。三是虚静恬淡,寂寞无为,所谓“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天道》)四是“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渔父》)法天之自然,贵道之本真,不为俗累,不为物役,心灵才能超越是非、功利、毁誉,达到“与天地为一”的境界。显然,“自然”有人格本体的意义。
到了魏晋时期,崇尚老庄成为风气。“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以迄晋代,注老谈玄者,多有数家。魏晋玄谈,以《老》、《庄》、《周易》为主,在思想上开启以儒解道、儒道合一的新思路。何、王注《老》,倡“贵无”之论;向、郭注《庄》,立“崇有”、“独化”之说,并开出“庄子注郭象”的义理新风。《老子》的“道论”与“自然”的根本旨趣,被作了玄学式的解读和发挥。
何、王力图放弃《老子》“有生于无”的生成论,而立足于从万物存在本质的层面探讨物之为物的内在根据,从而提升了老子的本体论思维。何晏《道论》说“有之为有,恃无以生,事而为事,由无以成。”(《列子·天瑞》注引)王弼进一步指出,“道”本是“未尽其极”的,即它并不是最高的抽象,只有“无”才是最高的抽象,说:“穷极虚无,得道之常,则乃至于不穷极也”(《老子注》十六章)。他从《老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观点出发,通过“损之又损”即损象近道的方法,提出“无”才是世界的本体。在这里,“无”因为没有任何规定,反而能规定一切、成就一切。于是老子的“以道为本”遂转化为“以无为本”,《老子》被纳入了玄学理路。张湛的《列子注》则把佛教哲理引入道的解释中,把道释为“至虚”。
同时,“自然”命题也在玄学中得到了新的解释。如果说老子的“自然”对应的是人离开自然之道的“妄为”和巧智,那么王弼的“自然”则对应的是虚伪的“名教”。他说:“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同上,二十九章),又说“仁义发乎内,为之犹伪”(同上,三十八章),即认为仁义等道德应是发之于内的自然真情的流露,而不应是刻意的造作,故主张“崇本息末”。此论遂成为社会批判思想的理论根据,如在嵇康、阮籍等的论说中。其后郭象在本体论和人生论两个层面又做了发挥。从本体论上说,万有都是“自生”、“独化”的,即“不为而自然”的,它不依赖任何外在的“造物主”而独立生化;从人生论上说,“自然”即“无心以顺有”,由此而提出“自足其性”的“顺性”论和“足性逍遥”的解脱论。
2.黄老系统:经验与致用
黄老之学不大关注《老子》的形上学,而把《老子》及其道论引向形而下的经验和实用方面。由于它以道家为主,兼融儒、法,并特别关注道与礼、道与法、道与气等关系以及社会治道、经验认识等等,因而表现出鲜明的经验论和实用化色彩。陈鼓应说:“‘道’的向社会性倾斜,是黄老学派对老子思想的一种发展,也是黄老道家的一大特点。”(陈鼓应,1995年,第25页)
在被视为黄老学的一些著作中,“道”常被明确释为构成万物本源的“精气”,如说:“凡物之精,比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又说:“精也者,气之精者也。”(《管子·内业》,以下只注篇名)“道”在这里同于无形而实有的“精气”,并以此说明宇宙万物的本源。还说:“虚无无形谓之道”,“道在天地之间,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心术上》)。在这里,《老子》“道”的无形、无名、隐晦等特征,黄老之学把它们解释得既隐微又显明,既高远又切近、既虚无又实有,从而使抽象玄远的“道”更具具体性和可操持性。这为它在体系上趋向社会化做了思想上的铺垫。
“道”与“礼”、“法”等相结合,是黄老道论的又一特点。黄老之学遵循“以无为之谓道,舍之之谓德,故道之与德无间”(《心术上》)的方法论原则,使得通行本《老子》中“道”与“礼”、“法”的对立,在这里被调和了。《黄帝四经·经法》肯定了“法”的作用,即“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同时赋予“法”以本体论的根据,说:“道生法”。《管子·心术》也说:“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乎道”,“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在“道”的基础上,黄老之学建立起不同于儒家的新的社会秩序,即既合乎礼法又合于自然的新秩序,秩序与自由被统一起来。这种观念在《文子》等黄老著述中也多有体现。
把道家的政治智慧通过“无为”和“自然”进一步推展,更突出“自然”的规律义,也是黄老释《老》的一个重要特点。黄老吸收了《老子》“静观”思想,强调“道贵因”,但排遣了无为的消极性,主张“缘理而动”,即要认识和遵循事物的规律而为,反对主观妄为。《心术上》说:“无为之道因也,因也者,无益无损也”。放弃庄子无所事事的消极态度,主张顺应事物规律的积极作为,几成为黄老学派的一致主张。将老子的“无为”引向具体的政治实践,讲“君无为而臣有为”,这在《慎子》、《管子》四篇、《文子》等书中都有明确的表述,从而使老子的“无为”更具实际的操作性。黄老派有时也与养生相联系,如《老子河上公章句》,然此注后又被道教养生家所汲取。
3.道教诠释:神道、仙道与养生修炼
魏晋南北朝时,《老子》对道教的理论化、哲理化起了重要的作用。道教在发展中渐尊老子为教祖,《道德经》也被当作道教的最高经典加以崇奉。许多道士都曾为《老子》作注,《老子》义疏之学到隋唐进一步升温,仅道士注疏解释《老子》者就有三十余家。宋明时北方全真派、南方正一派仍有关于《老子》的新解,从而形成了连绵不断、别有特色的《老子》道教诠释系统。
道教不同时期及各派对“道-自然”的界说虽然有同有异,但大体上说有以下几种共通之处:
一是“道”被解释为独立的超自然的神灵。在《老子》那里,“道”本来是排斥鬼神的:“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六十章),道在“象帝之先”(四章)。但《老子》关于“道”的无形无象、玄虚以及生万物的特征,为道教将“道”释解为超自然的神灵留下了充分的思维空间。桓帝时有《老子圣母碑》称:“老子者,道也,乃生于无形之先,起于太初之前,行于太素之元。”(《太平御览》卷一)此已将老子与道合而为一。此后,道教改变了《老子》的思维路向,对“道”作了宗教性和神学化的解释和阐发,而且这种解释和阐发与对老子本人的神化亦步亦趋。例如,陶弘景的《真灵位业图》将上清派所奉神灵安排位次,所列最高次位者即居于玉清境上的“上合皇道君应号元始天尊”。此神亦与道(老子)合一,其后各阶次诸神亦皆体现了道、神(仙)合一的特征。楼观道充分利用历史上所谓老子过函谷关为尹喜说《道德经》的传说,将老君视为“道”的化身。唐代更推尊道教,有关“太上老君”、“元始天尊”的称谓和神异故事在道书中屡见不鲜。
二是“道”又被解释为“仙道”。魏晋神仙道传人葛洪把“道”释为“玄道”、“仙道”。他利用《老子》所说“谷神不死”、“长生久视”等说法,建立起一套旨在宣扬长生不死、肉体成仙的仙道学说。其“仙道”也称“玄一之道”或“玄道”,以此作为其养生和成仙的根据。其仙道包括还丹金液为核心的“仙术”和“思神守一”为中心的“道术”。仙道学说的出现标志着道教丹鼎派的成熟,也说明《老子》的“道”已被方术化。受佛教影响,也有把“道”释为“觉”的,如《太清金液神丹经并序》:“道之为言觉,觉犹悟也。”(《云笈七签》卷六十五)
三是“重玄”说对“道”作了颇有深度的理论开启。所谓“重玄”,即吸收《庄子》的“心斋”、“坐忘”和佛教破除妄执的思想,对《老子》中“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一句所做的一种新解。成玄英以佛教的遣除“滞着”(即“能所双忘”)解释“玄”,认为老子的前一“玄”,是要遣有、无之“滞着”,后一“玄”则是要遣“不滞之滞”,这种所谓的双重遣滞即为“重玄。”按《老子》本意,“道”是宇宙幽深玄远的本根,而重玄家则以既不执有、也不执无,甚至连有、无之念头也不执着来释“玄之又玄”,将其释之为“澄心遣欲”、双遣真妄、物我双忘而“与道冥合”的神秘境界。其他重玄家说法虽有异,但也大体不离此旨。
道教对“自然”的解释,既不同于老子的“自然无为”,也不同于玄学家主要作为生活态度的“无心以顺有”、“无心因任”,更不同于黄老之学的“舍己而因物为法”即对规律的强调,其特点在于突出长生久视的理念和“修真”、“养生”之术对人自然生命过程的作用,并将其纳入生命哲学的范围。道教尝把自然说成是“道之真”即道之“真性”,如《太上玄妙经》说:“道曰自然者,道之真也;无为者,道之极也;虚无者,德之尊也。”《混元皇帝圣纪》说:“老君者,乃元气道真,造化自然者也。强为之容,则老子也。”事实上,道教讲的“守静”、“行气”、“导引”等种种修真之术,都始终贯穿着避免主观强制的自然主义。
4.佛教诠释:“道”即涅槃,即觉,即佛;自然即因缘
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时候,曾不可避免地发生过与中国传统道家、道教的冲突与交融,魏晋时期名僧广为研习道家典籍、在其论著中引证并解释《老子》的情况经常出现,于是形成佛教对《老》《庄》的独特诠释系统。
对《老子》的“道”作佛学式解释或道佛互释,最平常不过的是将“道”或释为“涅槃”,或释为“空”,或释为“觉”。较早将老、佛互释的,是“尝读老子”的佛教高僧僧肇,其所著《肇论》,既以老庄释佛,也以佛释老庄。元康《肇论疏下》说:“老子云:‘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借语以明涅槃也。”显然,“道”的无所不在被释为涅槃佛性的恒久永住,《肇论疏》引《老子》“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何患也。”并解释说此为“超度四流”,“亦可直谓诸法体性毕竟本空”,“言此涅槃,毕竟性空。”此又将“道”释为佛教的“空”;又有释为“菩提”或“觉”的,如《金师子章云间类解》说:“菩提,此云道也,觉也。”佛教尝释“佛”为“觉”,故“道”有时与“佛”、“心”相通。《宗镜录》卷二十六谓:“佛是自心义,亦名为道,亦云觉义。觉是灵觉之性,……亦是心。心即道,道即佛,佛即是禅。”以道佛为不二之法门。《楞伽师资记》卷一释《老子》“窈兮冥兮,其中有精”为“外虽亡相,内尚存心。”佛教有时也释“道”为“灵知”的,如释法琳说:“道是智慧灵知之号”(法琳《辩正论》卷六)。或释“道”为“导”的,如说:“道之言导,导人致于无为。”(见《弘明集》卷一)“夫佛也者,体道者也。道也者,导物者也。”(《弘明集》卷三)在《老子》中,“道”也称为“一”,释氏湛然则以“一”释佛之“四谛”,说“若集得一谓灭谛,因缘得一谓无明……六蔽得一谓至彼岸。”(《止观辅行传·弘决卷》第五之四)此将“道”视为“四谛”的根据,道显然与佛相通。
把《老子》的“自然”与“因缘”相贯通,是佛教释老的又一特点。佛教认为,“菩提自然生,则一切果报不由修得。”(延寿《宗镜录》卷四十六),故佛教尝以“因缘”释“自然”,认为一切事物的流转,皆为因果缘起所造。故在修佛之时就要随缘而解,缘来不挡,缘去不留,一切随缘。由此,佛教尝将“因缘”与老庄之“自然”对应,如说“佛者以因缘为宗,道者以自然为义。自然者无为而成,因缘者积行乃证。”(《佛祖历代通载》卷十)虽然佛宗因缘,道宗自然,但因缘即有自然之义,故延寿释《老子》“道法自然”一句时说,此“谓虚通曰道,即自然而然,是虽有因缘,亦成自然之义耳。”(《宗镜录》卷七十二)在这里,道、自然、因缘是通一不二,缘起缘散,皆为自然。佛教还尝将《老子》“清静无为”释为“寂灭”。朱熹认为“清静无为”是“佛家偷得老子好处”,然释为“寂灭”,此又“不足以垂世立教,于是缘业之说、因果之说、六根六尘四大十二缘生之说,层见叠出,宏远微妙。然推其所自,实本老子高虚元妙之旨。”(《文献通考·经籍考》五十二)佛僧注《老》《庄》,以支道林注《逍遥游》最为有名,其以佛释道曾被视为“标新理”。通过对“道”和“自然”的诠释,佛教也受到道家那种高远玄妙之旨的启示,从而在本体论上有了大的升华。
5.儒学(理学)系统:本体的阐释,经世的取向
传世的《老子》文本将“道”与儒家的“礼”、“仁”置于对立的地位,但道、儒的相互吸收早就开始了。儒对道的吸收尤其体现在对《老子》“道”、“自然”的诠释过程中。《中庸》有“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说法,“道”被改造为儒家伦理的准则。迄唐代韩愈写《原道》,认为老子是“去仁与义”而言道,他则主张“合仁与义言之也”,解释“道”为“由是(按:即仁义)而之焉之谓道”,道即为“仁义之道”,韩愈由是而提出所谓“道统”说。宋儒后来接着孟子后中绝了的“道统”,将此道与道家、道教、易学、佛教等思想结合起来,作了充分的发挥和创造,提出了一个贯通天、人,融通本体与工夫、知识与价值的庞大的理学体系。宋初“合老庄于儒”的周敦颐,把《老子》的“无极”(道)与《易》的“太极”结合起来,提出“无极而太极”的命题,又吸收道教的相关图式,创造了一幅《太极图》,还著有《太极图说》,不仅用以揭示宇宙万物生成的过程,更重要的是为其所尊奉的儒家经世济民的社会政治理想和“中正仁义而主静”的道德修养方式提供一个本体论的根据。二程和朱熹的“理”固然也有其他的渊源,如佛教的“真如佛性”和华严宗的“理”,但是“道”也被轻而易举地改造为宇宙万物形而上的最后根据“理”亦是不争的事实。原在老庄那里“无所不在”的“道”,在这里变成了“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的“无所适而不在”的“理”。(《晦庵集》卷七十)道即理,故理学亦称道学。朱熹有时也将二者略作区分,说“道是统名,理是细目”,“道字宏大,理字精密。”(《朱子语类》卷六)不过道与理在程朱看来都是形而上者,“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朱文公集》卷五十八)。总之,老子的“道”经过宋儒所做的一番融通,成为理学家阐述本体、用以经世的核心概念。
6.近现代及当代“新道家”的《老子》诠释:中西会通
随着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和现代变革,《老子》也被一些学者做了新的富于时代精神的诠解,这些学者被称为“新道家”。陈鼓应把近现代新道家分为三个时期:其一,以魏源等为代表,寻求老学经世致用的努力。魏源著有《老子本义》,称《老子》为“救世之书”,力图发挥老子革新救弊的作用。其二,西学东渐后,严复、章太炎等人在自由、民主思潮激荡下,以道家文化为中介,力图沟通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的努力。严复称“《老子》者,民主之治之所用也”,努力使道家传统适应现代社会之要求。其三,“五四”以后,有学者如胡适将《老子》释为“革命的政治哲学”,并特意推崇老子的“无为”理念,以为无为合于现代民治主义思想。(参见陈鼓应,2003年)
被称为“当代新道家”的一批学者,则“发现了道家思想的现代性和世界意义,并发展出它的现代形式”(董光璧语,转引自陈鼓应,2003年)。在“96北京道家文化国际研讨会”上,有学者首次提出“当代新道家”的称号。一些青年学者的学术论文称严复、章太炎、金岳霖、方东美等人为“当代新道家”。严复是在中国最早引进西方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论的学者,他在诠释道家思想时,尽可能将《老子》的思想与传统儒、释及西方的民主自由等观念相沟通。如他对道的解释是:“老谓之道,《周易》谓之太极,佛谓之自在,西哲谓之第一因,佛又谓之不二法门。”(《严复集》第4册,第1084页)他把《老子》的“自然”释为“无待而然”即自由,将老子的“安”、“平”、“太”释为颇具现代意味的自由、平等、合群。显然,在严复那里,对《老子》的解释处处渗透着现代自由民主的精神。对《老子》和道家作了独特的开创性工作的也许更推金岳霖,他在《论道》中说“道是式-能”,以“式”、“能”解“道”,从而对在《老子》那里本只可直觉的“道”,作了清晰的逻辑解析,还将无极、太极、动静、无有等范畴组成了一个严密的逻辑系统。至于方东美,更以“道”统贯儒、释,将老子的道与孔子“吾道一以贯之”之道、佛教华严宗的“一真法界”统汇贯通,并最终落脚到大乘佛教。此外,熊十力、冯友兰等学者也对道家作了富于时代性的新解。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对《老子》的思想阐释不只这六大系统,还有一些影响不大但也有特点的诠释,如唐代王真的兵家系统,以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清世祖为代表的皇帝对《老子》的政治诠释系统等。此外,还有清代学者多立足于考据和训诂的《老子》注解,此不赘。
《老子》在中国思想史上被多向诠释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了它在中国哲学史、文化史上作为源头活水的原创地位;也正是这种多向度诠释,形成了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但也必须看到,这种种诠释的系统在发展原创的同时,也在客观上起着如海德格尔所说的“遮蔽真理”的作用,甚至“使原创的精神智能受到遮蔽或异化”(杨适,第6页)。因此,本文的目的不仅仅是揭示《老子》被多向开启的事实,还在于进一步通过“去蔽”而返回原创,以澄明真理。当然,从诠释学的观点看,这似乎是一个永远难以完成的任务。
注释:
①当我们从诠释的角度来讨论《老子》时,所说的《老子》是指通行诸本。虽然有学者认为郭店楚简《老子》是“优于今本”且合乎老子原来思想的版本,但我以为,即使如此,对中国两千多年的哲学与文化发生实质性影响的,不是竹简本,甚至也不是那个《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的马王堆帛书本,而是通行诸本,如河上本、王弼本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