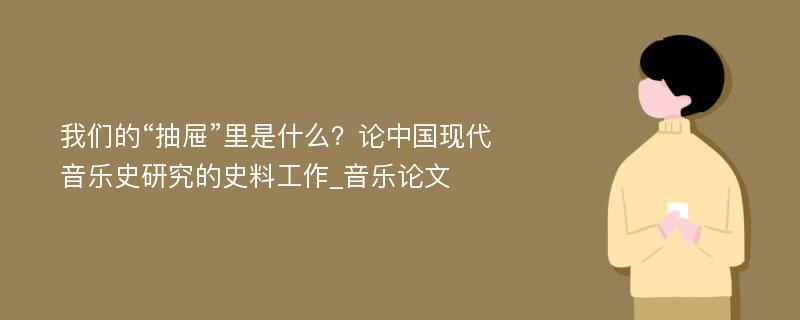
我们的“抽屉”里有些什么?——谈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史料工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料论文,中国论文,抽屉论文,近现代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近读陈思和教授《我们的抽屉——当代文学史(1949~1976)的“潜在写作”》(注:见《中国大学学术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2002年6月6次印刷)第86~100页。)一文,陈文中提出了应当重视和发掘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由于种种原因而被忽视乃至埋没的各种“潜在写作”的文学作品,以开拓文学史研究的新视野。文章说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史,却触动我想到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更为严重的史料工作问题。借用上引文章的标题,也就是想请大家看一看,我们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抽屉”里有些什么,还没有被有关的研究者所关注的东西,或者明知“抽屉”里藏有“宝物”,却始终未能或不能去“取出来”加以研讨论评,以充实和丰富我们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
文、谱、音、象、图、物齐全方能构成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完备史料
先要说一说文学史与音乐史研究的史料之异同,进而略谈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在史料构成方面的特定要求。
文学史的基本史料,当然是作家的创作之本及其相应的各种出版物;而为了全面深入地探究作家及其创作的时代,社会与个人的成因,当然也要广泛地收集这些方面的文字的口头的图象的乃至实物的史料—这些都已成为常识,在此不赘。
音乐史研究的重心与文学史研究相同,也应当是作(曲)家及其创作,因此,也必然要求将作(曲)家及其创作之本,作为史料构成的基本要件加以关照—这也是常识,不必赘述。
但音乐史研究的是乐音通过创作和唱奏、表演、传播而成为时代与社会文化的历史,这就对研究史料的构成提出了特定要求;尤其是对于近现代音乐的研究,如中国的近现代音乐史;更由于众所周知的传媒载体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日益近现代化,因此对于相关史料的采集累积提出了更为多方面的要求,简而言之,即要求从文、谱、音、象、图、物等方面开拓和积累相关史料,方能构成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完备的史料体系。
“文”,即关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各种文字著述史料,包括相关的文字手稿,专著书籍和文论杂纂的报刊载本等等。
“谱”,即关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各种民间的传统的与新的专业创作的音乐作品的乐谱史料,包括相关的各种体式的传统乐谱与简谱、线谱史料;同样,也包括着从手稿到专书与报刊载本等各种载体的乐谱史料。
“音”,即关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各种音响史料,包括从最早的纸带录音到蜡盘唱片,以及更为现代化录音手段的各种音响史料;它可以是中国近现代录制的各种民间的传统的与新的专业创作的音乐作品及其演唱演奏的音响史料—这应当是这方面史料的主体;也可以是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相关的各种口头讲述和现场活动的音响史料—这也是构成中国近现代音乐史音响史料的重要方面。
“像”,即关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各种活动的成像史料,包括以电影与录像等手段所拍摄记录的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有关的各种活动成像史料。
“图”,即关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各种图片史料,包括各种相关的照片、书刊报章画报上的摄影载照以及相关的绘画美术图片等等。
“物”,即关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各种实物史料,如相关的乐器与音乐活动设施实物,以及音乐家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各种实物等等。
还可能会有一些没有设想到的方面,也有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有关的史料;而如果我们能从上述文、谱、音、象、图、物等方面来收集和累积相关史料,必能够成全面有序的史料体系,从而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打好坚实可靠的基础。
看一看我们的“抽屉”
“抽屉”当然是一种比喻的说法,是指我们的史料宝库。治史者都知道论从史出,有几分史料说几分话,而决不能作无米之炊。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作为一门后起的至今尤不成熟的音乐史学科,即使是在1958年风行“以论带史”(实际成为了“以论代史”)的年代里起步的时候,也还是进行过初步的史料工作;由当时的中国音乐研究所(今中
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汇编油印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参考资料》,就是那时工作的成果,它不仅为当时呱呱落地的学科铺下了一方赖以安生立命的基土,而且至今犹为后来的研究者所珍视,作为研究工作的重要依据。自1958年至今,经过“十年文革”的浩劫和进入新时期以来朝着纵深方向的开拓,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走过了40多年曲折坎坷的路程,“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学科,即使是在史料工作方面也已有了不小的进展和建树,其略况可见于笔者《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在20世纪》(《音乐艺术》1999年第3期)一文概述。
但如果我们从学科建设的全局和可以期望能够得到更大发展的前景来说,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史料工作却是难以令有关的研究者和有志于此学的后来者满意释怀的:未能形成学术力量足够的专门的史料工作队伍,以开展足够规模的持续性的史料工作,因此至今犹未建立起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全面、完备、有序的史料体系,便是大家都看得到的严峻的现实。
有一种说法以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是离我们最近的音乐史事,大部分史料已为我们了然于胸,或都在身边唾手可得,大可不必象挖掘千年万年前的出土文物那样迫不及待和兴师动众;而且,历史材料的把握并无一个确定的底线,收集到何时何种程度才是一个尽头呢?基于这样一些并非全无道理得想法,有关的研究者并没有把史料工作放到应有的位置上,便是必然的了。
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史料和已被掌握的状况果真是如此吗?!这就要请大家看一看我们的“抽屉”了。以下略择数端简言之以见一斑—为了免得引起误会,以为笔者藏有什么“家传秘本”塞满了“抽屉”,因此才在这里吆喝卖乖,我只举人所共知却又未曾进行过认真的查访、编集、研讨得史料为线索为便,如:
既有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著作都侧重于论述创作方面的历史成就,并约略述及表演方面的历史建树,这当然无可厚非;“但是对于理论方面(的)历史性成就的反映则相对薄弱”——这是冯文慈先生《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学:两个传统并存与古今衔接问题》(注:见载于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一文指出来的一个涉及到本学科概括历史内容尚不完全的问题。冯先生认为在20世纪,特别在其下半叶(即1949年以来),中国音 乐学的各学科都出现了重要学者和学术成果,完全可以和应当与作曲家、表演艺术家及其成就一样受到关注,纳入到近现代与当代音乐史的研究范畴。而从我们“抽屉”里的史料来看,即使是对于20世纪上半叶音乐理论方面历史成就的反映,我们的有关著作也是难说充分的。最近十数年来,虽然有张静蔚教授查访汇编成《中国近代音乐史料》那样的重要成果;在对王光祈、萧友梅等的音乐著述史料发掘、汇集、编注和研究方面也有不小的进展;但如果我们稍稍看一下同一时期音乐理论著述的部分书目(姑且不计发表在同一时期报刊上的音乐文论篇目),就会发现还有数量不小的重要著述并没有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以与本学科关联最为直接的关于中国古代音乐史的著作来说,从20世纪20年代初到40年代末,就有7至8部带有通史性质的著作和5至6部专史性质的著作(注:7至8部通史性质的著作是:《中国音乐史》(叶伯和著,1922年)、《中国音乐史》(四册,郑觐文著,1928年大同乐会)、《中国音乐小史》(许之衡著,1931年8月商务印书馆初版)、《中国音乐史话》(缪天瑞著,1932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中国音乐史》(上、下册,王光祈编,1931年中华书局初版)、《中国音乐史》([日],田边尚雄著,陈清泉译,1937年5月,商务引书馆)、《旧乐沿革》(萧友梅编,1938年9月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所编教材)、《中国音乐史纲》(杨荫浏著,1944年1月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油印本);5至6部专史性质的著作是:《17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的研究》(萧友梅1916年向德国莱比锡大学哲学系提出的博士论文)、《音乐的文学小史》(朱谦之著,1925年8月,上海泰东图书馆)、《外族音乐流传中国史》(孔德著,1926年商务印书馆)、《中国音乐文学史》(朱谦之著,1935年10月,商务印书馆)、《隋唐燕乐调研究》([日]林谦三著,郭沫若译,1936年11月商务印书馆)、《唐宋大曲之来源及其组织》(阴法鲁作,1945年8月油印)。)问世,如果再加上在传统音乐理论研究方面“指南”、“寻源”一类谱集与专著(注:如:《中国音乐指南》(沈寄人著,1924年5月再版,世界书局)、《中国丝竹指南》(祝湘石编,1924年6月石印,上海大东书店)、《雅音集》(第一、二集杨荫浏、陈鼎钧合编,第一集1923年6月,第二集1929年7月,无锡乐群公司)和《中乐寻源》(童斐编著,1926年2月,商务印书馆)等。)中,也都有颇具新意的关于中国古代音乐史的发展的了论述,就可看到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步入其发祥阶段的洋洋大观;毋庸讳言,对此我们现有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著作关注与反映是很不充分的,这同我们对“抽屉”里的这方面的珍贵史料“熟视无睹”直接有关。其实,20世纪的20~40年代,除了中国古代音乐史学之外,也是具有近现代学科意义的中国的音乐美学、西方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音乐教育学以及相关的音乐考古学、传统乐律学、戏曲音乐史学和音乐评等步上创始之途的重要时期,都或多或少地有略具学科雏形的著述问世,在此都暂不涉及。
前文已述,既有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著作都以作曲家及其创作为论述重心,但却不能说我们对这方面的历史材料都已尽数在握。例如:最近十数年来关于中国近现代的艺术歌曲创作的论说文章不在少见;但我们的“抽屉”里所藏有的这方面的乐谱史料,却还有相当数量并未真正进入有关研究者的视野。如以20世纪20~40年代间问世的带有钢琴伴奏的独唱曲集(含有其他载体歌曲的集子在内)为限,除了青主、萧友梅、赵元任、黄自及其弟子,以及周叔安、应尚能、李惟宁、张啸虎、马思聪、陆华柏、江文也等人的这方面曲集谱本和代表作,已深度不同的为人所论及外,至少还有如:《新声乐》、《摘花》、《金梦》、《夜曲》、《爱的系念》、《别离》、《回家以后》、《树伐歌曲集》、《感旧》、《易水别》、《宋词新歌集》、《江南谣》、《骸骨舞曲—独唱歌集》、《春潮曲》、《寄影集》(注:所列曲集据《中国音乐书谱志》(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年3月,增订本);《新声乐》(冯亚雄编著,1924年11月北京求知学社)、《摘花》(钱君匋、陈啸空等著,1928年3月,上海开明书店)、《金梦》(邱望湖、钱君匋合编,1930年7月,上海开明书店)、《夜曲》(钱君匋等著,编成交商务印书馆出版,毁于“一·二八”日寇侵略淞沪战事中,现见《恋歌三十七曲》,钱君匋编,1992年1月,上海音乐出版社)、《爱的系念》(索非歌、邱望湘曲,1928年8月,春蜂乐会)、《别离》(郭沫若词,王沛纶曲,1929年9月小说书林社)、《回家以后》(采石词,王宪伦曲,1929年9月,小说林书社)、《树伐歌曲集》(李树伐撰,1930年上海三民公司,内含歌曲10首和钢琴曲2首)、(感归)(李树伐曲,1932年作,出版年月及出处待查)、《易水别》(林文铮词,李树伐曲,石印)、《宋词新歌集》(陈厚庵著,1934年9月,商务印书馆)、《江南谣》(姚牧著,1941年中国乐谱供应社)、《骸骨舞曲—独唱歌集》(龙七词,钱仁康曲,上海音乐公司)、《寄影集》(邱望湘曲,乐艺出版社石印)。)等等,尚无人进行过认真的史料考释与研究;如果再加上同一时期的音乐刊物上刊登的同类作品曲谱,数量当更多。虽然我们尚不能说,这些还藏在“抽屉”里的艺术歌曲集子,其作品的艺术质量和历史代表性,与那些已被程度不同地进行过研讨论述的众所周知的歌集与作品相比,会更胜一筹;但在这些已知存世的歌集与作品没有被认真地考释和研究之前,总难求得对于中国艺术歌曲创作在20世纪上半叶创始时期的全面认识。
音乐作为必须通过唱奏表演才会发生实际效用的艺术,其演唱演奏的实际音响史料,必然为有关的研究者所倚重;而这正是我们这个学科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之所在,因为在近现代已有了唱片、录音等手段,可以将有关作品及其唱奏音响留存下来,供我们进行更具直观性的研究(既研究作品的创作,也研究唱奏者的表演艺术)。例如:在一份1964年编印的《中国唱片厂库存旧唱片模板目录》中,列有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开始灌制唱片以来,只到1949年全国解放,由以“百代”、“丽歌”、“胜利”、“高亭”、“蓓开”、“和声”、“长城”等唱片公司牌号灌制的旧唱片模板34,300面中的11,752面的目录,其内容包括“戏曲”、“曲艺”、“乐曲”、“歌曲”与“其他”五个部分。虽然据这本目录的“编印说明”称,这还只是中国旧唱片模板“遭受帝国主义分子窃盗与毁弃”之后的一部分剩余旧唱片模板的资料极不完全的一个编目,而我们从这本280多页的编目所列旧唱片模板各自已可知道,这是20世纪上半叶我国戏曲、曲艺、音乐—传统音乐与新音乐的门类齐全、曲目丰富、唱奏名家荟萃的一个历史音响宝藏,其中的历史珍品胜不胜数,尤其对于我们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试问:我们对这样的“抽屉”里—不!“金库”里所藏的“宝物”,到何年何月才能取出来用之于我们的科学研究何教学与传播呢?!
从唱片想到电影,这又是一个与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关系密切的艺术门类。从1959年8月编印的一份《中国电影音乐资料选编》(注:见《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参考资料》(第二辑,中国音乐研究所1959年9乐油印本)。)可知,在1930~1937、1938~1945、1946~1949三个时段中问世,插有电影歌曲或既有歌曲又有配乐的各类影片(故事片、记录片和卡通片等),共228部,涉及的电影歌曲与配乐的作者与编者约近60位(不计歌曲的词作者;同一音乐作者用不同的笔名计为1人);而这如与《中国电影发展史》上下两巨册所附中国各类影片的历史总目相对照,还只是一个极不完全的统计。不用说,如果我们不能把这方面的活动成象并带唱奏音响的史料,切实地看到听到和尽数把握,就难以对中国近现代的电影歌曲与电影音乐的发展有切实的了解,更谈不上作出切实的历史论述与评价了。
与唱片和影片相比,对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相关的图片史料的收集、汇编和运用于研究、教学、传播,应当是比较容易着手的。众所周知,这样的图片史料,无论是在私人手中,还是在有关的研究机构与图书馆、博物馆的馆藏中,以及近现代的书刊、报章、画报等等出版物上,都是极为多见和丰富多彩的。近些年来,“老照片”之类的编集出版已成为时尚,其中也不时见到一些与音乐有关的“老照片”。但我们却至今还没有为例如“中国近现代图片音乐史”那样的必可构成洋洋大观的课题立项,试问:我们的“抽屉”里—不!这又是一个“金库”里的“宝藏”,到何年何月才能示人以历史真相呢!?
对于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有关的实物史料的收集和收藏,似乎应当是相关的历史文物研究机构的事;而如果我们想到近现代也是中国的民族乐器改革得到发展的时期,在这方面留存有不少可作为历史研究之用的实物史料;如:1936年由前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仪器工厂印行的《琴管萧说明书》和《新笛说明书》,就是由当时主持该所的物理学家丁西林设计的两种改革而成的新的民族乐器的制作与推销说明书;其所说的“琴管箫”和“新笛”还有实物存世吗?或者可以按说明书所示制作出这样的乐器,以使历史实物按原样“克隆”存世。类似这样的事物史料,不是可以开拓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尚未涉及的研究领域吗!
以上所举只是涉及到了文、谱、音、像、图、物等方面有待我们去“拿出来”进行研究的史料有限的一角,更没有涉及到如陈思和教授的文章所说,那些作(曲)家未曾或无 从发表的“潜在写作”的作品—这样的“潜在写作”和被压在“抽屉”里的作品,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也时有所闻;而且由于音乐出版比之文学出版更有特殊的难度,所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还有不少虽然已经以实际传播的方式发表了,却又始终未能正式出版而被压在作曲家的“抽屉”里的作品(如:数量颇多的为电影音乐而写的器乐曲等),可以说,我们要开掘这方面的史料,更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着眼于未来,从基础工作做起——重提《关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学科建设的若干建议》
请大家看一看我们的“抽屉”里有些什么未被关注和研讨的历史材料,是为了对本学科的实际状况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作为历史研究之基础的史料工作还存在着严重缺陷,因此还远没有为学科发展构筑起扎实的根基,这就是经过了这番审视和反思之后得到的结论。这使我想起了1991年时,向中国音协在重庆召开的“中国现代音乐史研讨会”提出的《关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学科建设的若干建议》(注:载于吉林艺术学院学报《艺圃》1992年第1、2期合刊。)。在这篇文章中,我以多年从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和教学所强烈感受到的,本学科存在着基础薄弱、研究工作难以纵深发展和不能适应教学要求等严重状况为依据,向会议提出了加强学科建设的8点具体建议,即要求组织起全国协作的力量来:(一)编纂刊印《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料大系》;(二)重印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出版的重要的书、刊、文、谱;(三)编纂出版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代表性音乐家的史料与研究专集;(四)组录“中国近现代音乐作品音响大全”;(五)编纂出版《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图集》;(六)组录“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资料与作品演出录象系列”;(七)编刊《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期刊;(八)建立中国近现代音乐资料馆。这些建议在当时曾经得到与会音乐界领导与前辈首肯和出席者的积极响应。但一眨眼间十多年过去了,已经进入了新的世纪,这些曾使自己鼓起勇气并得到所期望反响的建议,至今仍只是纸上梦想的记录。而正在这时,却又再度听到了“重写音乐史”的声音,我的直感就是:“重写”必须面向未来,从学科建设的基础工作做起,其具体的做法,也许仍不出1991年时的那8项建议。
在结束这篇“老生常谈”的文章的时候,我也仍想抄录当年文章的结论,以表述自己在历史研究与教学上的完整观点和所追求的目标:
“历史研究应当首先致力于弄清历史真相,接着就应当对历史真相作正确的和准确真实的叙述;在以上两点都充分地做到的基础上,才谈得上从大量准确无误的历史事实中抽取出反复出现的因此可能是带普遍性的东西,并由此归纳出历史经验与规律,以供今后的实践作参考。而作为历史教学,还应当从上述研究成果中提取最典型精当,同时又是丰富充实的材料,以最有效的手段,帮助学生主动地吸收掌握这些材料,从而心悦诚服地接受已被历史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观点。……结合本学科研究与教学所面对的实际状况,为了实现上述基本任务,当务之急还是要从基础工作做起,也就是应当抓紧做好基本史料的开掘、收集、整理、研究和汇编,尽可能建立起一套文、谱、音、象、图、物俱全的“立体化”的史料体系和教材,只有做到了这一工作,才谈得上把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建设成一门成熟的学科。‘重写’出科学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注:1990年北京:中国音乐史学会发言(发表于此会议简报))
收稿时间:2002-07-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