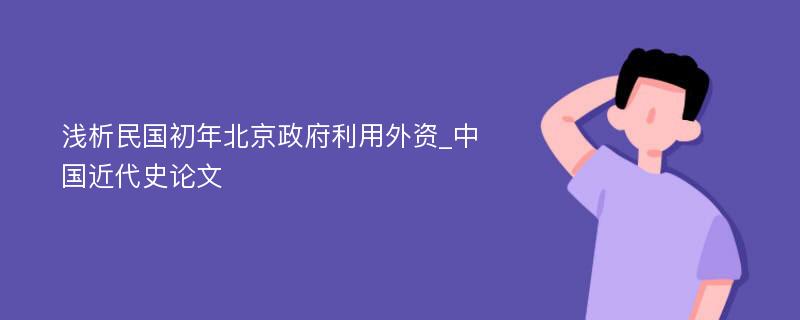
民国初年北京政府利用外资简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国初年论文,利用外资论文,北京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资本的国际流动是不可遏止的经济潮流,而利用外资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点在20世纪初就已为世人认知。结束了封建帝制的中国也适时地走上了利用外资以谋求国内实业发展的道路。民初北京政府时期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尝试阶段,而利用外资则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试就民初北京政府利用外资情况作一简要分析,以助于对近代中国利用外资历史的全面深入的研究。
一
历史进入20世纪后,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迅速。随着殖民侵略的全球性蔓延,资本被输送到世界各地,于是资本主义各国与世界上落后弱小的国家和地区便发生了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经济联系。然而,综合而论,借助于资本的这种国际性流动,经济发达国家不仅得以从落后国家和地区获取生产所需的原料,而且落后国家也得以利用发达国家资金,从而为本国资金的匮乏问题找到一条解决途径。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对外经济掠夺的主要手段由商品输出转为资本输出。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而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生产技术落后,自然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倾销的市场和资本输出的场所。从历史上看,自《马关条约》与《辛丑条约》签订以后,中国开始大量地、被动地接受外来资本的输入,并由此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境地。
在爱国热情的激励下,先进的中国人为了使中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进行了艰苦的努力。他们要求改革落后的社会体制,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以此寻求中国的强大富足。清朝末年,清政府迫于内外交困的局势,采取了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然而清政府的腐朽已经无法使这些措施有效地实行,于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一场革命运动便势不可免。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废除了帝制,建立起中华民国,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民国初立,社会上到处洋溢着实业救国的思想,各实业界人士纷纷组织起实业性团体,如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西北实业协会,安徽、苏州等地实业协会等。南京临时政府也大力提倡兴办实业,并积极规划实业发展蓝图。于是伴随着实业救国热潮,利用外资的呼声亦日益高涨。
发展实业离不开资金,而中国资金极度短缺的现况,则使有识之士将目光转向外资。早在辛亥革命发生之前,资产阶级人士就曾提出“实行开放”、“利用外资”的设想。如康有为即主张“借外债以办国家银行”,梁启超亦提出“借重外资”兴办实业的计划,孙中山更是主张“共和国成立之后,当使中国内地全行开放,对于外人不加限制,任其到中国兴办实业”(注:《孙中山全集》,第560页。)。辛亥革命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则将引进和利用外资作为执政之要务。“今欲求发达,则不得不持开放主义。利用外资,利用外人,皆急求发达我国家之故,不得不然者”(注:《孙中山全集》,第480—481页。)朱执信还从维护主权的角度提出广泛利用外资的共同借款论,指出,“自理论上言,以一国之投资,独占一世界要津之权利,必至引起国家间之嫉妒,而受其害者即为独占之人,与以其利益供人独占之人”,因而他提出中国应在共同借款基础上,“排去一切损及中国主权之条件,使其借款纯然为经济的,不生势力范围之问题”,并表示“若是之外国资本,吾非惟不反对之,且欢迎之”(注:《朱执信集》下,第713 页。)在这样一种指导思想之下,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了诸多利用外资振兴实业的规划。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些计划虽多数未能付诸实施,但却为随后建立的北京政府的利用外资活动奠定了基础。
民国初年,社会广泛流行的振兴实业、利用外资的思想更为具体和深入。当时,中国资产阶级政治地位已有明显提高,这使其振兴实业、发展经济的愿望更为强烈,于是纷纷为政府出谋划策,提出各种建设性意见,其核心即为振兴实业,认为:“我国险象环生,虽由武备之不振,内治之不修,外交之失败,然其原因,则由于实业之不发达”,而“欲求挽救,则富而强,实业为救贫唯一之道”(注:《中华实业界》第1号,1914年1月1日,载《民国经世文编》实业(三)第3页。)。对此,北京政府颇为重视。农商总长张謇明确表示,“巩固民国,非振兴农商各项实业不可”。工商总长刘揆一也表示振兴工商之目的有两方面,一在使国民之生计充裕,一为经济对外竞争”。(注:《民立报》,1912年9月27 日。)甚至认为,“商务为富强要政”、“农工尤为商务之根本”(注:《大公报》,1903年10月4日。) 显然北京政府已将发展实业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政策。
然而,发展实业首先需要大量资本。当时“资本缺乏,实为吾国企业家最痛苦之事”(注:曹均伟:《近代中国与利用外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10月,第213、230、240、379、381、402页。)。社会普遍认为,要使实业振兴,“与其坐视外资投入,毋宁即以外债为抵制外资之方”,“与其坐视事业落于外人,不如以借债自为经营,宁负多量之外债,决不欢迎外资也”(注:《民立报》,1912年10月28日。)。张謇首先明确提出利用外资发展棉铁工业的主张,认为“以振兴实业为挽救贫弱之方,以开放门户利用外资为振兴实业之计”(注:《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7 。)。各实业界人士也都认为,“实业以资本为前提,中国民穷财尽已非一日”,要发展实业,“非是借外债不可”(注:《民国经世文编》实业(一),第40页。《政府大政方针宣言》,载《熊希龄集》上册。)。有鉴于此,政府制定相应的大政方针,将利用外资作为发展实业的前提和抵制外国经济侵略的手段,并表示,外资投资于我境内所生之利,使得其三四,而我恒得其六七,故政府愿与国民共欢迎之”
与此呼应,一些政府要员出于牟利的目的纷纷投资于工商业,并在经营中参与利用外资活动,由此也客观地促成了政府的利用外资政策,如周学熙在唐山、天津、青岛等地创办华新纱厂,还在唐山设立启新洋灰公司、耀华玻璃厂等。(注:曹均伟:《近代中国与利用外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10月,第213、230、240、379、381、402页。)另外,梁士诒先后投资于通惠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证券交易所龙烟铁矿等。(注:曹均伟:《近代中国与利用外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10月,第213、230、240、379、381、402页。)他们二人曾多次出面承借铁路等实业借款,并与外商合办实业。与此类似,许多官僚经手外资的利用,并试图以此牟取回佣,积累私产,扩大自己经营的实业。
二
民初北京政府利用外资的活动主要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制定有关利用外资的法令法规,以为约束利用外资活动的总原则。
张謇出任农商总长时,看到社会“经济潮流,横溢大地,中外合资营业之事必日益增多”的形势,认识到利用外资,若“无法律之防”,“其危险将视无可得资的为尤甚”(注:《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7。)因而指出中外合组公司,“宜有公司条例为之准则”, 同时以“矿业条例”、“实业公司条例相辅而行”,如此才可“巩固华洋合办之基础”。(注:《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7。) 这一主张得到北京政府的认同,于是在张謇主持下,农商部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利用外资的法规和条例,以助于民族资本企业的创设、发展以及对外资的引进和利用。
熊希龄组阁时,以政府名义颂布了许多涉外法规,如“公司条例”、“矿业条例”、“垦荒条例”,要求“凡办矿必照矿业条例,办垦必照垦荒条例,并各应守其他办法之法律”(注:《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7。)。这些法规、条例,允许外国商人与中国商人合组公司, 并规定了有关保障中国利权的具体内容。此外,政府还特别重视侨资的引进和利用,专门颂布了“保护华侨条例”,对华侨回国投资予以法律保护和相应奖励,以此刺激华侨回国投资的积极性。
法规的制定不仅有利于加强外资利用的管理,也有利于民族资本企业的自身发展,同时又可有效地把握利用外资的进展和程序。利用外资是一种跨越国界的经济现象,涉及到海外投资者和当地外资利用者的不同目的、利益以及不同的经营思维,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尺度使两者在统一认识和统一行为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因而一个较为完备的利用外资的法规是其达成共识的标准和依据,也是双方合作的基础。而且,以法治理利用外资的活动;既适应海外投资者的习惯作法,也使利用外资的系统管理具有法定性,从而对利用外资的活动起到强制和约束作用。另外,通过利用外资法规的建立,还可以使利用外资的投资经营活动具有一个法律环境,并使之纳于法律规范,从而有利于外资活动的有效开展。但是,在北京政府时期,中国特殊的社会性质及其屈辱的国际地位,注定其法律手段的软弱和空虚,再加之当时利用外资的法令法规更未健全,缺乏配套的、成系统的法规体系,这使得各种有关利用外资的法规、条例在实施中经常受到人为的干扰,根本无法达到应有效果,而且有些法规形同虚设,仅一纸空文而已。
第二、开展利用外资的实践活动。
首先是大举借用外资。当时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般都主张通过举借外债或商借外资的办法利用外资。梁启超尤为称道以政府名义向外国个人借贷,他曾说:“与其商借而散漫无经验,毋宁官借而统一有责成也”(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6册,第64页。)。1912 年到1916年,北京政府共借外债68笔,其中政治、军事性借款为48笔,实业性借款为20笔。在这20笔中,除去以用实业建设名义转作军政开支的2 笔外,真正意义上的实业性外债只有18笔,共计1.3亿多银两。 其中铁路借款11笔,电信借款2笔,矿务借款2笔,其他实业借款3 笔。(注: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第114—128页。)
一般而言,外债与外资是有差异的,只有实业性外债才可算作外资的一种,是只以资金形态表现出来的一种外资。从上述实业性外债的项目分布上可见,此时以用于铁路、电信、工矿业等营利事业为主,因而是一种营利性外债,即能够通过项目所具有的投资回收能力和对外债务偿还能力,在生产经营中产生大于债务数值的经济效益,即能偿还本息,又能发展实业。从当时情况看,北京政府利用这些实业性外债,弥补了国内实业建设资金的不足,增强了自我发展的能力,还得以购置先进技术工艺和设备,开发国内资源,发展交通通信事业,加快经济建设步伐,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其中成效最明显的当为铁路借款。
出于发展事业、交通为先的考虑,政府将利用外资的主要投向定位于铁路建设。从1912年底到1916年初,北京政府以“国体变更”为由,实行“铁路国有”政策,并将这些收归国有的铁路作抵押,与外国签订铁路借款合同,换取借款。如:1913年与比、法签订的同成铁路借款合同,1913年与英国签订的浦信铁路借款合同,1914年与英国签订的宁湘铁路借款合同、沙兴铁路借款合同,1914年与法国签订的钦渝铁路借款合同,1915年与日本签订的四郑铁路借款合同、 四兆铁路借款合同,1916年与俄国签订的滨里铁路借款合同等。除此之外,政府还以原有铁路材料,机车的购置或路权的出让为条件换取垫款,如1912年津浦铁路德华银行垫款,1913年来自中英公司的沪宁铁路借款以及1941年来自中英公司的沪枫铁路借款等。
上述借款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自身的作用,有助于中国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一些新路因此得以开筑,清末未完成的旧路得以延展,机车也多有购置添设,直接扩大了铁路营运量,并促进了铁路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不过这些借款多未全数落实,也未全数用于铁路修筑。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欧战爆发使资金紧张所致。1912年至1914年所有与西方国家签订的铁路借款合同,均因战事而未履行,如沙兴铁路举借1000万英镑,到1915年底止仅得到5万英镑,同成铁路举借1000 万英镑,到1916年8月底止也仅得到100万英镑。(注:曹均伟:《近代中国与利用外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10月,第213、230、 240、379、 381、402页。)另一方面是由于各国银行团在为中国招募债款时,从中盘剥,使中国实得债款不到债票面额的九成左右。此外,北京政府常将借款挪为他用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如1912年9月, 政府以建筑汴洛路名义向比公司举借陇海铁路借款,计400万英镑, 其中至少一半挪作政府行政费用。(注:张嘉敖《中国铁道建设》第111 页。)缘于此,计划中的许多项铁路建设无法进行。从实际情况来看,当时铁路修筑较好地区只是东北,其他地区成效不大。其他实业借款结果也大多如此。
其次,以中外合资的形式兴办实业。张謇就任农商总长后提出了多种方式同时并举来引进和利用外资的方案。在1913年提交给袁世凯的《筹划利用外资振兴实业呈》中,他提出“合资”、“借债”、“代办”三种办法,认为“合资”是利用外资的“最普遍方法”,因而大力提倡兴办合资企业,同时还论证了“中国各矿最宜令中外商人集资合办”(注:《实业丛报》第16期。)。熊希龄内阁采纳了张謇的提议,也认为中国普通矿业“最宜开放”,主张在矿业上应以中外合资方式开采,并制定“矿业条例”加以约束。(注:《东方杂志》第10卷第8号。) 于是袁世凯批准开平、滦州两个煤矿合并,成立开滦矿务局,由中英合办,并以长子袁克定为局督办。此后便出现一、二十家中外合资企业,如1914年成立的中日实业公司,即由日本财阀涩泽、三井、大仓等投资,中方股东有杨士琦、孙多森等,新交通系官僚张弧、李士伟等出任历届理事长。另如1915年中日合资兴办华宁公司,中方股东有梁士诒、朱启铃等。
当时在中外合资企业中,中方股本基本有三种形式:政府出资、私人出资、政府与私人同时出资。至于私人出资者多为军阀与官僚,他们以各种方式与外国资本家合办近代企业,利用自己的权势,牟取私利,又反过来通过中外合资经营为自己壮大实力。但其中也不乏通过利用外资兴办企业而逐步转变为民族资产阶级之人,如财政总长周学熙1913年1月与法方签订合同,设立中法合办的实业银行, 并由该行与北京政府签订1亿5千万法郎的中法实业借款合同,他本人在利用外资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并逐步转变为民族资本家。
就投资方向看,当时合资企业多出现在矿业中,银行、航运、机器制造等行业也有所见。合资伙伴多为英、美、法、日等国。这些国家的投资者与中方股东将资本更多地投向矿业,尤以煤矿为多,仅开滦一家,1913年资本额就达1400多万元,前者超出后者近3倍。(注: 曹均伟:《近代中国与利用外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10月,第213、230、240、379、381、402页。)
“共同出资,共同经营”是近代中外合资企业区别于其他企业的标志。按常理来说,这种合资企业当为一种正常的国际间经济合作的形式。然而,却处处表现出一种不平等的国际合作的经济关系。外国投资者以其强权政治和经济优势,“得到非中国人不得开办实业的地方,开办非中国人不能开办的企业”(注:曹均伟:《近代中国与利用外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10月,第213、230、240、379、381、402页。)。由此可见,中外合资企业在某种上说成为外国资本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和掠夺的手段。不过,从另一角度看,我们又不能否定它对中国旧有经济体系的孤立和闭关自守状态的确起到了瓦解作用,而且,对于弥补国内资金不足,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培养新一代技术人才,发展实业亦有着积极的客观效果。
再次,鼓励华侨投资祖国。袁世凯曾以大总统名义发布《令保惠侨民》的通令,着内务,农商两部通令各省军民长官“于该省之侨商,均应设法招徕,随时拊喻。并晓喻海外各中华商会,切实劝导各商,集资回国,兴办企业。其已经归国者,尤必悉心保护。务使安居乐业,各泯猜虞”(注:《农商公报》第56期。)。奖励华侨回国投资的政策有利于对侨资的利用。当时侨资的主要输通渠道是捐款、侨汇和投资,而尤以侨商投资为要途。政府允许侨商以独资形式经办企业,投资地区主要在沪、闽、粤沿海地区,投资行业多为房地产、商业和工业。据不完全统计,自1912年至1919年,侨资企业多达1042家,投资额达7100万元。(注:曹均伟:《近代中国与利用外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10月,第213、230、240、379、381、402页。)侨资的利用加速了沿海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值得肯定。
三
综上所述,民国初年北京政府利用外资,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值得总结与淘沥,以作为后人利用外资时的一个借鉴。
北京政府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为举借外债与中外合资经营两大类型。前者为间接投资,后者为直接投资。以借债为形式的间接投资有利于“由我自主”地应用所借外资,也可免受外人直接干涉,但这种形式的外资若使用失当或借款过度,则会因无力偿还而陷入债务的泥坑。以中外合资为形式的直接投资有利于中国全面引进外资、先进生产技术和设备以及管理经验,并可在经济上对外资比例加以限制。不过,这种形式也易于导致外来投资者利用其优势直接干涉和控制企业的经营管理。
选用何种方式引进外资,引进的外资发展何种实业,并非盲目之举。北京政府考虑到铁路与制造业方面资本需求量大,技术要求高,对外资控制较难,故采用“借洋债”的方式利用外资。至于煤矿开采业,其生产对象和利润来源为特定区域的煤炭资源,对技术和资本要求不高,政府可根据矿业法限制矿区的范围及外资比例,故采用“招洋股”的方式利用外资。这种根据实业项目的不同情况和不同要求,结合利用外资具体方式的特点进行比较权衡,以选择尽可能合适的利用外资方式的做法,对于实业项目的开发、建设是有利的。
民初北京政府将利用外资的重点定在交通运输业和能源采掘业等基础经济部门,是出于务实的考虑。因为中国当时经济相当落后,而交通、能源等基础部门又是薄弱环节。要发展实业,交通、能源部门必须先行。尽管在这两大部门中利用外资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毕竟改善了中国的交通运输状况和能源采掘面貌,为日后外资的广泛利用提供了一个相对有利的国内环境,也为中国走向近现代化打下基础。将外资投向国家急需发展的建设项目,仍是今天利用外资的一项原则。
一般来说,利用外资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外资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加快对现有行业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从而迅速改变社会生产力落后状况。北京政府以中外合资方式利用外资的同时,全面引进机器设备、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从而使近代中国有了一批在不同行业中掌握新型操作技术的工人和掌握先进管理方法的管理人才,这对中国落后的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大有助益。特别是侨资的利用尤其为中国近代工业提供了技术和动力来源,使生产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从而推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以上所述,可以看作是北京政府利用外资的成功经验。但从总体来看,当时利用外资活动是失败的。其原因除了中国特殊的社会性质和国际地位所造成的外国资本侵略、殖民地性外债、不平等债约以及外国资本的绝对控制力之外,国内投资环境的制约也是一个重要方面。民初政局混乱,政治民主毫无保证,法治建设刚刚起步,涉外法规极不严密、更不成体系,文化教育落后,官僚作风败坏,军阀割据、战乱不断等等,这一切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利用外资发展实业的规模、数量和效益。当时在不少中外合资企业中,北京政府许多要员都是中方股东,那些企业成为他们与外国资本势力密切结合的通道与牟取私利的工具。“袁之左右,更利用借款有大宗回扣,足饱私囊”(注:谢彬:《中国铁道史》,中华书局,1929年。)的情况更是见怪不怪的现象。
此外,相应而来的企业滥借外债和盲目投资现象则是失败的另一重要原因。不考虑偿还能力的滥借外债结果是主权的不断丧失,而不作周密计划的盲目投资的结果则是企业被债务所窒息。有例为证,1913年借款合同规定汉冶萍公司在40年内供应日本矿石3千万吨, 以偿还所欠债务。但据翁文灏先生估计,大冶铁矿蕴藏量总共不过2千万吨, 那么即使将汉冶萍公司卖掉,也还倒欠日本1千万吨。(注: 《中国近代史丛刊》第2册,第194页。)可见在这种情况下,汉冶萍公司不垮是不可能的。
以上种种,足资为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