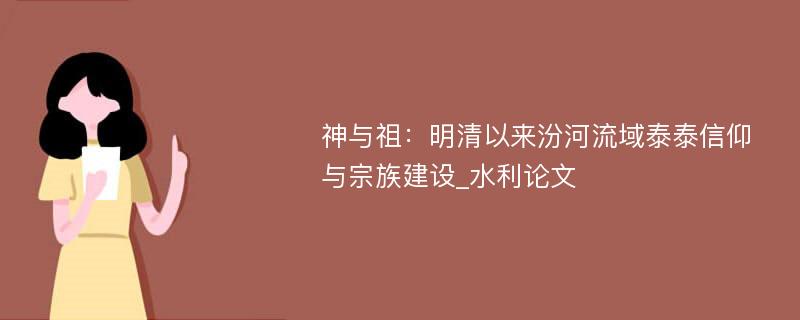
神明与祖先:台骀信仰与明清以来汾河流域的宗族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宗族论文,神明论文,流域论文,明清论文,祖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15)01-0132-(11) DOI:10.13852/J.CNKI.JSHNU.2015.01.015 一、研究的问题 本研究涉及“水利”与“宗族”两大领域两个关键词。其中,“宗族”是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历来就备受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学术积淀深厚。近年来随着宗族研究的深入发展,在地理空间上出现了由南向北转移的趋势,研究者开始将目光投向广大北方地区,力图纠正以往宗族研究观念上的某些“偏见”。伴随观念的革新,国内外学界越来越期待中国北方宗族研究诞生更多更新的成果,以此来检验并对话江南、华南的宗族研究范式。①水利则是区域社会史研究尤其是北方研究中一个新热点。在水利社会史领域十余年工作积累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当前水利社会史研究欲向纵深发展,取得更大的理论创获,同样需要改变以往那种就水言水,只见表象不见本相的研究局限,进一步就水利与宗族、姻亲、市场、祭祀等所谓“中层理论”的核心要素之相互关系开展更为深入系统的研究,实现从“乡土中国”向“水利中国”的视角转换。②在此,我们认为在当前的区域水利社会史研究中,研究者需优先探讨水利与宗族的关系问题。 1.弗里德曼的“水利与宗族”关系论断及其争议 就以往的学术史来看,在宗族与水利关系研究方面,较多呈现为宗族与水利各说各话“两张皮”的特点,能够将两者结合在一起进行综合考量的成果并不多见。较早涉及这一问题的应该是英国人类学家莫里斯·弗里德曼。他在闽粤宗族研究中曾对宗族与水利的关系做过思考,最先提出在稻米种植这种生产条件下,水利灌溉促进宗族团结,宗族反过来适应水利系统需要的问题,从而为此后的水利社会史和宗族史研究埋下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命题。 1980年代,黄宗智在讨论华北乡村研究中水利与政治经济结构的关系时,曾借弗里德曼的观点去解释华北宗族组织不发达的原因。然而,黄宗智对华北水利的认识存在着一个明显的误区,即将华北水利简单地划分为由国家建造和维修的大型防洪工程和由个别农户挖掘和拥有的小型灌溉井两类,忽视了华北水利的多样性,因而使弗氏的“水利与宗族相互适应性”观点遭遇了解释困境。 对弗氏学说最具挑战性的研究是其弟子巴博德(Burton Pasternak)来自中国台湾的人类学观察。1964至1969年间,巴博德在中国台湾屏东和台南的研究证明:弗里德曼的证据大多来自小型的、宗族所有的水利系统;而在考察大型的、跨村庄的水利系统时,便可发现其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不同姓氏的宗族的合作。屏东的社区水利事业相当发达,可是并不存在像弗里德曼所说的那种地域化宗族,反而存在跨宗族的社区联合体;台南的社区水利事业很不发达,宗族势力却十分强大,从而用中国台湾的事例否定了弗里德曼的论断。 与此相关联的是1972-1976年由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主持,王崧兴、庄英章、陈其南等中国台湾人类学者参加的“台湾省浊水溪与大肚溪流域自然史与文化史科际研究计划”(简称“浊大计划”)。该计划中研究者继续对弗里德曼的宗族研究范式进行反思,认为超宗族的祭祀圈与信仰圈才是中国台湾社会构成的特点,进而运用祭祀圈和信仰圈理论解释中国台湾区域社会的历史,反映了中国学者对弗里德曼有关论断的积极回应。 就中国的学术实践而言,在“水利与宗族”关系问题上则遵循一条以宗族研究为主兼及水利的学术路径。其中,郑振满和钱杭的研究就很有代表性。郑振满对福建莆田平原的长期观察表明,水利建设构成了莆田平原开发史的主线,莆田历史上的水利系统、聚落环境与宗族和宗教组织构成了地方社会的主要活动空间。唐以后莆田平原的礼仪变革与社会重组过程,就是在这一特定的社会生态环境中展开的。这种强调长时段的综合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已大大超越了弗里德曼的宗族研究范畴。同样,钱杭对萧山湘湖“库域型水利社会”的研究,则得益于他对江浙宗族历史的谙熟,因而能够游刃有余地由宗族而水利,概括提炼出中国水利社会的一种重要类型,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水利社会史的研究。此外,石峰还以“非宗族乡村”为题,以关中“水利社区”为观察点,力图揭示在宗族力量缺失的北方乡村社会,水利是如何发挥关键作用的。然而关中地区是否确实是非宗族乡村颇令人生疑。 概而言之,在宗族与水利的关系问题上,研究者绝不可陷入或“强调宗族为主”或“强调水利为主”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逻辑,尚需有意识地付诸大量实证性的经验研究来加以解答。以上研究构成了本论题的理论基础和学术脉络。 2.国内外学界对汾河流域“水利/宗族”问题的相关研究 具体到汾河流域的水利、宗族与乡村社会变迁这一主题上,尽管以往学界在该区域已开展了很多卓有成效的研究,如由中法学者完成的“山陕水资源与民间社会”国际合作项目,项目参加者董晓萍、张小军、邓小南、韩茂莉等都发表了有关汾河流域水利社会史的重要研究成果。山西大学以行龙为带头人的学术团队对山西不同类型水利社会的研究,赵世瑜对汾河流域分水传说及其水权争端的讨论,英国学者沈爱娣从道德经济的视角指出了晋水流域百姓和官方不同的水利观念,使汾河流域水利社会史研究达到一个极高的水准。然而,研究者多将重点置放于水利开发与地域社会发展联系性方面,强调了水利在区域社会发展变迁中的某种中心地位,而宗族充其量只是他们在探讨水利社会的构成、权力、秩序、变迁等具体问题时的一个普通变量而已。同样,明清以来汾河流域甚至山西区域的宗族研究中则呈现出以宗族问题为中心、水利为边缘,甚至极少涉及水利的特点,如常建华对洪洞韩氏、刘氏宗族的研究,赵世瑜对阳城陈氏宗族的研究,邓庆平对寿阳祁氏宗族的研究等。故此,汾河流域宗族与水利之间的关系及其乡村社会变迁的动力问题依然有待澄清。 本研究力图抓住水利与宗族这两大学术热点,把握两大趋势,即:宗族研究热点由南而北的转移,水利社会史由着重建立结构类型到探讨诸构成要素相互关系的转变两大趋势。在此基础上,努力克服以往宗族或水利研究中各说各话、两相分立的缺陷,通过实证性的个案研究,提供北方宗族与水利关系的典型例证,实现“通过水利看宗族,通过宗族看水利”的研究设想;进而理解北方宗族发生与生长的地方形态,厘清水利-村庄-宗族-国家之间的先后生成、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内在逻辑关系。 二、作为汾神的台骀:文本记载与民众记忆 台骀作为汾河水神这一身份之确立,最早出现于《左传·昭公元年》记载的“晋平公问疾”(公元前541年)一事。这一记载也是后世儒者考证台骀身份的唯一文献来源,对于确立台骀汾河水神的地位十分重要。兹摘录如下: 晋侯有疾,郑伯使公孙侨如晋聘,且问疾。叔向问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实沈、台骀为祟’,史莫之知。敢问此何神也?”子产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当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梦帝谓己:‘余命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属诸参,而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故参为晋星。由是观之,则实沈,参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沈、姒、蓐、黄实守其祀。今晋主汾而灭之矣。由是观之,则台骀,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禜之;若君身,则亦出入、饮食、哀乐之事也。”……晋侯闻子产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贿之。③ 晋平公是春秋时期晋国国君,晋悼公之子,公元前557年―公元前532年在位。从这条资料可以看出,当时晋国包括国君、大臣在内的人士均已不清楚台骀为何方神圣,以至于要求教于当时在郑国为相且学识渊博的子产(即公孙侨,?—公元前522年),从子产口中得知了台骀的身份和来历。在此,需要强调三个问题: 其一是台骀的身世。从“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中可以梳理出一条有关台骀身世的明确系谱,即金天氏—昧—允格、台骀。其中的金天氏是关键。历史上在金天氏为谁的问题上历来也充满争议,司马迁认为金天氏即上古五帝之一——帝喾高辛氏。④《史记》中有记载称: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高辛父曰蟜极,蟜极父曰玄嚣,玄嚣父曰黄帝。到战国时期,流行用五行说标五帝。⑤其中,以化生天下万物的五行之首“金”表示少昊的政德,再加上少昊传太昊诸法,观测太白金星,行金星历法,后世之人又对其追加封号为“金天氏”。这里金天氏就变成了五帝之一的少昊。因此,金天氏或为帝喾、或为少昊,两说并存。⑥此外,值得重视的一点是台骀的父亲昧为玄冥师这一记载。所谓玄冥,根据杨宽在《古史辨》中的考证,可能是一个人的名字,曾担任水正这一职务,后世便将玄冥师等同于水官。⑦因此,台骀的父亲昧极有可能是黄河流域某个部落负责治水事务的人。郑国子产说“台骀能业其官”,即可理解为台骀继承了父亲昧的事业,继续从事治水的工作,可谓是父子治水。⑧ 其二是台骀的事迹。“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是台骀担任玄冥师这一职务之后在治水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关于台骀治水的问题,学界已多有讨论,并形成了相对一致的看法。主流的说法认为,台骀治水的汾洮二河分别是位于山西南部运城盆地的汾河下游河段和涑水河;“大泽”则是包括河东盐池在内的古湖泊;“大原”就是汾洮二河所流经的区域,或为汾洮平原,即今之临汾、运城两大盆地。⑨鉴于台骀治水的功绩,“帝用嘉之,封诸汾川”,台骀及其所属部族遂成为历史上汾河下游地区最早的统治者和居住者。学者研究中存在分歧的是,台骀究竟是颛顼帝时代的人物还是唐尧时代的人物。早在西晋时代学者杜预就曾提出帝为颛顼。隋唐时代学者孔颖达提出质疑,认为帝非颛顼。今人李炳海延续并支持了孔颖达的研究,认为台骀是唐尧时代的人物。⑩如此看来,无论台骀治水于颛顼时代还是唐尧时代,均早于后世广为称颂的大禹治水。由此,台骀便有了“华夏治水第一人”的称号。加之其活动的区域主要是在春秋时期晋国的发祥地,后人也将其视为“三晋保护神”。 其三是台骀的祭祀。按照子产的说法,台骀受封之地“汾川”,即今汾河下游的临汾、运城地区,曾经被划分为沈、姒、蓐、黄四个小国,它们在台骀死后“实守其祀”,奉台骀为庇护者和祖先。因此,沈、姒、蓐、黄当是台骀之后晋南地区第二代统治者;延至春秋时期四国先后为晋国所灭,于是对台骀的祭祀便随之终止。或许是因为如此,才会有实沈、台骀作祟之怪事发生。不过,子产却明确指出晋平公之疾并非实沈、台骀所为,而是告诫他只要合理饮食、调节生活、克制情绪便可防止疾病侵袭。子产进而又指出,台骀作为晋国这片土地上的山川之神,关系到本地各种水旱疠疫的发生,是地方保护神,于是晋国便专门修建了祭祀台骀的庙宇。清代曲沃人裴志濂所撰《重修台骀庙碑记》中对此已有相似观点:“今由平公之卜、叔向之问、子产之对而观之,则庙之建为确始于吾邑,断创自平公时无疑也。”(11) 据1962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在晋都新田(即侯马)台神古城遗址之考古发掘报告显示:“台神古城西北三座夯土台基可能与祭祀汾神台骀有关,台基西北的今台神村北傍汾河耸立‘台骀庙’,庙址所在为‘古翠岭’,庙中台王殿梁上有大明崇祯八年即公元1653年题记。《重修台骀庙碑记》云:‘庙建于晋都绛时,即古之新田。’”(12)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相互印证,不难判断出侯马台骀庙或许是汾河流域年代最早的一座专门祭祀汾神的庙宇。 就台骀庙的数量和空间分布来看,至清光绪年间,山西全境范围内台骀庙总数已达11座。其中,汾河流域共9座,自南而北分别位于曲沃、临汾、汾阳、太原、阳曲、静乐、宁武(太原和宁武各两座,余皆为一座)。汾河流域之外的石楼县翠金山和五台县紫罗山各有一座。(13)现存庙宇中除曲沃、太原、宁武外,其余皆毁。依据各地台骀庙现存碑刻和有关方志记载,可以判断出各地台骀庙修建的年代和出现的先后顺序:曲沃台骀庙位于今侯马市西台神村,创修年代最早,约出现于晋平公执政时代,这一点前已述及,不再赘述。汾阳台骀庙有唐代集政治家、文学家和诗人身份于一体的著名人物令狐楚在贞元九年所撰《谢雨文》碑可兹佐证,表明此庙至少在唐代贞元九年之前即已存在。(14)太原王郭村的昌宁公庙相对略晚,然其创建年代不晚于五代时期,有后晋天福六年石敬瑭所赐“昌宁公”封号为证。(15)宁武定河村昌宁公冢庙则不晚于金明昌五年,有金泰和八年(1208)州同知张守愚所作《汾川昌宁公冢庙记》为证。太原晋祠的台骀庙则是嘉靖十二年由晋祠东庄人高汝行创建,有确切记载可查。位于阳曲县西门外演武堂东的“汾河神庙”,亦即台骀庙,创建于明万历年间,年代较晚。雍正《山西通志》有记载:“明万历中,巡抚李景元筑坝,得台骀像于晋祠前,因建庙奉台骀,三楹,左右钟楼、碑楼二楹。后奉尹、董二公,三楹,左右翼室六楹,门二重,缭以周垣,额曰万年保障。万自约撰碑。”是为明证。位于汾河源头管涔山雷鸣寺的台骀庙,尽管创建年代不详,但是据晚清五台知名学者徐继畲的《修建雷鸣寺记》所言,该处“旧有石洞以祀台骀之神。今于道光六年新建下殿三间,上有楼阁一间,俱奉台骀神像,鸠工□焕,斗然一新”,至少表明汾源台骀庙在清道光六年以前即已存在很久了。汾河流域所有台骀庙中,唯有位于临汾县的“汾水神祠”和静乐县城西郭的“汾水川祠”记载最为简略,(16)无法判明出现的准确年代。 综上所述,可以基本明确台骀庙在汾河流域的时空坐标:位于汾河流域下游的曲沃县台骀庙年代最早,创建于春秋时期;位于汾河中游的汾阳、太原在唐宋时代已建有台骀庙;位于汾河上游的宁武县至迟在金代即已建有台骀庙。根据这一总体特征,可以判断出台骀庙在汾河流域的出现大体上是按照自南而北的顺序不断扩展:从春秋时期开始出现台骀庙祭祀;到宋金时代汾河流域的台骀信仰已渐成气象,初具规模;延至明清时代,太原、阳曲等地不断有新的庙宇建立,使得汾河流域台骀庙达到历史上最为鼎盛的状态。 在众多台骀庙的文本记载和建筑遗存中,曲沃和太原王郭村的台骀庙规模较为宏大。其中,曲沃台骀庙被视为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祭祀台骀的庙宇,现存庙宇建筑系清乾隆年间由曲沃县令张坊重修,占地约10000平方米,建筑主要有台王宝殿、娘娘殿、献殿和春秋楼。据乾隆三十二年《重修台骀庙碑记》所载:“吾乡之庙,自汉唐以来,时为修葺。金元之际,奉敕兴修者不一。前明亦时有修举,然圮于火,毁于兵燹,宏规已失,断碣犹存。”另据当地一位自发保护台骀庙的老人贺际泰先生记述,20世纪30年代前后台骀庙献殿两旁单单碑刻就有40余个,1958年大跃进大搞水利建设,很多石碑被当成石料拉走,目前只剩下3个了。(17) 关于太原王郭村的台骀庙,宋代文献中已有记载说“凡作正殿并东西两庑,高扉前启,子亭中峙,复设厅事于后,为待宾之所,举其成屋八十有二楹”。(18)延至清代,该庙是以太原县公庙的地位出现的,(19)而且在每年端午节由当地官员出面祭祀。据王郭村已故晋源区政协委员王锡寿先生撰文介绍,该村台骀祠庙分前中后三个部分,南北长四华里,东西宽四十丈,占地面积近300亩,庙堂建筑200余间。主体建筑包括前部的台骀神殿,中部的昧公殿、挥公殿和后部的万花堡、藏经楼等。清代以来迭遭战火和洪水破坏。顺治六年,汾阳义军与清军战于晋祠一带,昌宁公祠遭兵灾,千年神庙大部被毁。嘉庆十七年,汾河水涨,祠院再次遭灾,劫余殿堂全部倒塌。道光十九年重修,但规模已远不如前,仅建成正殿三间,东西耳房、东西厢房各五间,前门和钟鼓楼及偏院一所。后因年久失修,殿宇倾圮,古树被伐,庙院荒芜,只余台骀神像被村民保护至今。(20)以上是我们从现存文本、庙宇遗迹和地方人士有关技术中提炼到的有关汾河流域台骀信仰的基本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继《左传》之后,后世文本对台骀的记载中多因袭了《左传》中子产的说法。其中,影响最大者莫过于汉代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如果将《史记·郑世家》的记载与《左传》相比较不难发现,司马迁对台骀身世、事迹的记述基本上是对《左传》的原文照搬,改动不大。于是,后世士人便依靠《左传》和《史记》这两部重要文献,将台骀作为汾河水神和三晋大地上最早的统治者、保护神的角色长期确立了下来。 单纯就文献本身来分析,自《左传》和《史记》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难以看到“台骀”的字眼;直至唐代才再次出现,共有两处记载:一是贞元九年(793)唐人令狐楚为汾阳台骀庙撰《谢雨文》碑;二是河东节度使卢钧将台骀庙改名“汾水川祠”。卢钧在大中六年至九年间(852-855)间在太原任河东节度使。唐代的这两处记载中,台骀的功能、身份与祈雨、汾河水神相关,与先秦时代的记述差别不大。 北宋宝元二年(1039),时任并州通判的掌禹锡主持重修太原王郭村昌宁公庙并撰写碑记。碑文中作者首先援引《左传》的记载,确信“昌宁公即金天氏之遐裔。世长水官,通汾洮、障大泽而能似续其业,以处太原。春秋左氏纪之详矣”。接着他描述了昌宁公庙的职能,“或水潦作沴,一时缺雨,府帅以牲币禜之,必如响应之验。及天有六气,晦明生疾,编氓以豚蹄祝之,多获勿药之喜”。可见其依然是作为水神形象出现的。紧接着他肯定了台骀庙的久远历史,“故晋阳境中,博询群祀,最越前古”。最后他又再次强调了台骀的职能和贡献,“公生则以劳定国,没则能御大灾”,如此等等。这与此前的记载相比,依然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在记述台骀的核心话语上呈现出高度一致的特征,甚至出现前代不清楚、怀疑,后代反而愈加清晰、笃信的状况。 金代的两处记载亦有此特点。金代汾河流域的台骀庙文本记载中均统一使用“昌宁公”这一名称。披览文献可知,昌宁公的称号最早始自后晋天福年间石敬瑭的封赐,上引掌禹锡所撰碑文中即有记载称台骀庙在“晋天福中始有封公之号,著于地志”。与此相应,汾河流域现存各有关地方志书中均承认这一点,有据可查,不赘述之。金代的两篇碑记均收录于地方志书中,且均为官员或士人所撰:一在汾阳,为金大定十三年汾州观察判官王遵古所作《昌宁宫记》;一在宁武,为金人张守愚所作《汾川昌宁公冢庙记》。王遵古文中再次继承并重复了前人的论调,对台骀的身世、台骀的封号、台骀的功用及祭祀台骀的原因做了阐述。同样,张守愚文中亦是如此。两人均认同台骀是金天氏的后裔,台骀之父为昧,昧是治水官即玄冥师;后晋受封昌宁公,宋代加封“宣济”庙额;由于祷雨灵应,屡获官方和各地民众的隆重祭祀。 颇有意味的是,乾隆《宁武府志》的作者魏元枢、周景桂却对宁武定河村的台骀庙和张守愚的这篇文章表示出一种不屑的态度,断言“台骀冢庙太原、汾州并有,其障汾洮初不在此,特里俗附会耳。守愚作碑殊失事实,文亦无可观。以其年岁颇古,故与元尚思明《魏知院碑》并存之”。后世修志者在面对前人记述时表现出的这种态度,表明时人已经在怀疑宋金以来汾河流域各地民众对台骀及其神迹表述和认知的客观真实性。张守愚的记述无意中揭示了一个知识分子人为建构台骀信仰的历史过程。他说定河村“村侧有小丘,左汾堧右谷口,高且寻仞,广殆亩余,上有丛祠,古往流言谓为台骀墓,主汾神。土俗虽承传之久,亦不知所以然。又不喻建祠之由,第以土地神视之”。说明当时人们并不清楚这里是否真的有台骀墓,在现实生活中只是把这里作为土地神来看待,没有人能搞清楚究竟是否如此。而人们的认知彻底发生改变,与来此做官的汾阳人任从仕有关。任从仕经过考证后告诉当地老百姓,说这个庙就是台骀庙,人们才将土地庙改为台骀庙,并将其视为非常灵验的汾河水神来看待。然而何以认定一座小土丘即是台骀墓呢?从张守愚的记述中我们并未看到任何直接的证据,如其所言“明昌五年州得汾阳人任从仕为判官,任讳知微,博闻之士也。因悼彼俗颛蒙,渎神之祀。乃追讨图志,以春秋传考证之核厥事迹,知其昭然不诬为神之墓、为神之庙也。乃与儒士史世雄、宋鈛,取旧图经,参校编次,增补其缺,具载兹事,以示郡人。由是民得晓然,知所敬在是”。(21)因此这段记述只是一个人云亦云的建构和附会。但是,历史往往就是这样延续、演进而来。宁武定河村台骀庙恰恰自任从仕考证之后,才正式以台骀冢庙的身份受到当地官民的信奉和祭祀,进而与汾阳王遵古的《昌宁宫记》一道成为台骀信仰记载谱系中的重要文本,成为汾河流域台骀信仰的重要话语支撑。 元代山西各地台骀庙的情形如何,因目前缺乏相应的文本记载,尚难以呈现。我们可以做到的是,通过明、清两代的文本记载来揭示宋金以来历经百余年战争和非汉族政权洗礼后,是否发生新的变化。明代的记载仅有太原东庄高姓人氏在晋祠名胜创修台骀庙的事例,高汝行是这次创修活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高汝行字修古,号东庄,太原晋祠人,曾官至浙江按察副使,并在明中叶东南沿海抗倭斗争中担任过浙江温、处二府的军政要职,显赫一时;其所在的村庄后来以他个人的号来命名,称为东庄,足见其在当地的影响力。高氏本人在致仕返乡后还亲自主持编修了嘉靖《太原县志》。关于高氏在晋祠修建台骀庙的原因,刘大鹏的《晋祠志》中有如下解释:“台骀神庙为东庄高氏之庙,故高氏修之。传言高东庄汝行号,仕江浙日渡江遇险,有人拯救得免。询姓名不答。再询,则曰台骀。飘然而去。东庄曰:‘救我者,台骀神也。’致仕,归乃立庙于晋祠。”这个故事讲述了汾神台骀显灵搭救水上遇险的高汝行的事情,令人半信半疑。尽管如此,嘉靖十二年晋祠台骀庙就这样建了起来,并为高氏族人所独享。此后晋祠台骀庙即由东庄高姓族人世代修缮,道光《太原县志》对此有明确记载:“台骀庙在晋祠,副使高汝行所建。雍正八年高□等重修。乾隆辛卯邑岁贡高碧等重修。嘉庆丁卯高氏合族重修。”(22)值得注意的是,雍正八年一位有贡生身份的高姓子弟高若岐在《重修台骀庙碑记》文中,有意对高姓族人所修台骀庙与王郭村台骀庙做了区分,说当地有两座台骀庙,“一在王郭村昌宁公庙。昌宁公者,石晋天福之封号也。此县中之公庙,每岁端午日有司祭之。一在晋祠,居于广惠祠难老泉之间,此则东庄高氏之所独建也。其不建于东庄而建于此地者,因台骀泽为水之东汇,故建于其源也。创始于嘉靖十二年,重修于雍正之八年。高氏始之,高氏继之,宜也”。(23)在高家人看来,汾神台骀不仅是汾河流域的保护神,更是高姓全族的保护神;汾神显灵搭救高姓祖先高汝行的故事遂成为晋祠东庄高姓族人展示话语,显示其在晋水流域存在和声音的一个象征资源,反复为历代高姓族人所强调,以至于道光八年高氏全族竟在台骀庙内立下“东庄高氏族规碑”。在这里,尽管台骀依然是作为地域保护神和汾河水神的形象出现的,但是对高姓族人而言具有更为特殊的意义,已经演变成为高氏家族私有的、类似香火庙性质的宗教建筑,其背后当与东庄高氏在晋水流域的较大势力和影响力有着莫大的关系。 相比之下,清代汾河流域各地文献和民众记忆中对台骀的记述更为丰富多彩,且遍布于汾河上中下游多个区域。其中,影响最大者当属清初知名学者朱彝尊游历山西时,为曲沃台骀庙写下的五言长诗《台骀庙怀古十韵》: 凤鸟书官后,鸿荒障泽年。 神功开白壤,帝系出金天。 分野扪参次,山川奠禹先。 按图移岸谷,纪远昧星躔。 乱水汾洮别,诸姬沈姒联。 唐风水始祀,鲁史至今传。 簘鼓横流散,风沙急溜穿。 势曾吞北汉,润亦被西边。 璧马黄河并,云旗玉井旋。 轩裳存想像,凭吊一茫然。 该诗作以考据学家的眼光、文学家的笔调,道出了台骀先于夏禹治水的首创之功和对山西开发的特殊贡献,再次确认并弘扬了台骀作为汾神和三晋保护神的角色定位。学者朱彝尊的这一观点,在其身后广为传颂,并与之前的各种文本一起形塑了台骀的形象,成为后世讲述台骀由来的重要依据。乾隆二十年(1755)春,曲沃县令张坊重修台骀庙,“适逢上清查古昔圣贤祠墓,遂稽古核实以报。且传集一乡父老,肃容而告之。教民塑沈姒蓐黄四侯,以配神享。刻朱竹垞先生诗章,以润泽古迹”。(24)至今,在曲沃台骀庙内仍完整保存着刻有朱彝尊诗词的碑刻。 另一位对确定台骀身份产生影响的是晚清著名学者山西五台人徐继畲的《修建雷鸣寺记》。徐氏在此文中直言“台骀于太原汾神,理地星宿,宜崇庙,貌水官,属有明禋闻之”。接着又说在宁武管涔山“旧有石洞以祀台骀之神,今于道光六年新建下殿三间,上有楼阁一间,俱奉台骀神像,鸠工口焕,斗然一新。又以石束汾源,使从龙口涌出,喷薄一溪,灌注千里,三晋第一胜境焉”。最后回溯了台骀的身世,“台骀汾神,为金天之裔,玄冥之子,封神于颛顼之世,守祀以沈姒之宗。其立庙血食于汾水之源,当必有昭显应而默佑,佑此一方者”。(25)显然,还是一以贯之地将台骀视作汾河水神和地方保护神来对待。 文本之外,是汾河上下游各地至今仍口耳相传的有关台骀治水的传说故事。这些传说故事与上述文本交相辉映,将台骀的角色和功能以更加生动的形式呈现出来,形成了汾河流域独特的民众记忆。位于汾河上游的宁武县定河村台骀庙周边,就有台骀治水并在当地娶妻的传说。相传上古台骀治水时,从天上摘来三颗星宿,垒成“品”字状,置于象顶之上作为镇压汾魔的镇魔石,并以此处作为点将台,调兵遣将。后世这里便成为宁武八景之一的“支锅奇石”。还有传说称台骀死后葬于定河村旁,与定河村隔河相望的是阳方村。因为台骀治水时娶了阳方村民女为妻,便留下“定河爷爷、阳方奶奶”这一乡谚。至今定河村台骀庙内仍供有台骀夫妇的塑像,定河、阳方二村因此而结为神亲,相互认同,关系亲密。 位于汾河中游的太原,则有彰显台骀治水功劳的“打开灵石口,空出晋阳湖”传说及端午节祭台骀的习俗。相传台骀为治洪水,南北奔波。他率领民众疏导汾水和洮水时,奋战在灵石山头,白天挖山一丈,夜间山石就又长高一丈,次日还得从头挖起。消息传到晋阳湖边,晋阳百姓为犒劳挖山民众,就用湖旁的苇叶包上糯米和红枣,放在湖中的竹筏上顺流而下送给乡亲们吃。挖山民众吃到远来的粽子,备受鼓舞,终于打开灵石口,将汾水导入黄河,空出了晋阳湖。此即是“打开灵石口,空出晋阳湖”这个在山西广泛流传的民间传说之由来。同时,这也是太原地区五月初五祭祀台骀神以及包粽子的由来。太原地区流传的这一说法,与以往人们将治理洪水功劳归于大禹,以及将五月初五包粽子作为祭祀爱国诗人屈原的说法是不同的,显示了区域社会独特的民众记忆。 不仅如此,太原还有湖泽因台骀而得名。嘉靖《太原县志》载:“台骀泽,一名晋泽,县南十里,晋水下流汇为泽,泽广二十里,今为汾水所没,尽为民田。其旁有昌宁公庙,即台骀神也。”从历史文献来看,太原的台骀泽在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中已有记载:“初,太祖皇帝命引汾水浸其城,水自城门入,而有积草自城中飘出塞之。是时,王师顿兵甘草地中,会岁暑雨,军士多疾,乃班师。王师已去,继元决城下水注之台骀泽,水已落而城多摧圮。”足见,至迟在宋太祖赵匡胤攻打晋阳城时,当地已有“台骀泽”这一名称。 位于汾河下游的侯马西台神村,民间流传有神仙台骀受命于玉帝,驱赶神牛,下凡治理汾河的传说。不过,其治水事迹与太原民间流传的“打开灵石口,空出晋阳湖”的说法有相似之处,只是改变了具体地点而已,故事主题仍是在强调台骀治理洪水的功绩。(26)与宁武定河村台骀娶当地女子为妻的传说类似,在侯马西台神村同样有台骀娶当地东台神村黄姓女子为妻的故事。每年农历十月十五,台骀庙周围的六个村庄还要共同举办盛大的台骀庙会,并建有台神村、褚村、北平望、南平望、下平望、东高村六村构成的村社祭祀组织。(27) 鉴于台骀在汾河流域的上述事迹和文化传统,历代朝廷对台骀多有加封褒奖。文献中最为常见的是:“唐有令狐楚《谢雨文》之碑。晋有昌宁公之封。宋有灵感玄应公之赠、宣济广惠之额。今则灵威素著定河之称。”(28)综上所述,无论是历代文本还是民间传说中,对于台骀的主流记载均是将其作为汾河水神乃至三晋地域保护神来加以奉祀和崇敬。这就构成了有关台骀形象的支配性话语和民众耳熟能详的口头记忆,在很长时间内流传并一直延续下来。台骀形象开始出现新的变化,发生在明代中晚期以来宗族庶民化过程的不断加剧中。 三、作为祖先的台骀:明代张姓宗族系谱的建构 在汾河流域,至今仍流传有台骀是张姓第三代祖先的说法,将台骀与张氏家族文化牵扯到一起。此种说法是否属实?如果确有其事,又是何时开始形成的,反映了怎样的现实需求和社会变化?这一问题耐人寻味。在此,我们不妨从文献记载、文化建构和区域实践三个维度,考察台骀与张姓宗族关系的历史建构过程。 第一个维度是比较文献记载。前节论述可以明确,明以前文献中所有关于台骀的记载均与张姓无关。台骀的身份是在《左传》中首次记载,后在《史记·郑世家》中延续传承,唐宋金以来代代延续的汾河水神与张姓无关。再来看明以前关于张姓起源的记载。东汉王符的《潜夫论·志氏姓》中“张氏”条目被视为汉代以前张氏源衍总结性论著,书中记载史上最早姓张的历史人物是西周宣王时的张仲,所谓“侯谁在矣,张仲孝友”。(29)此时并没有后世张氏宗族系谱中明确宣扬的张姓得姓先祖张挥,更没有三世祖台骀的身影。之后在姓氏史上产生较大影响的著作是唐林宝的《元和姓纂》和北宋欧阳修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林宝《元和姓纂》云:“黄帝第五子少昊青阳生挥,为弓正,观弧星,始制弓矢,主祀弧星,得姓张氏。”第一次明确提出张氏得姓始祖为张挥,且认为挥是黄帝第五子少昊青阳所生。与此略有差别的是,欧阳修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言:“张氏出自姬姓,黄帝子少昊青阳氏第五子挥为弓正,始制弓矢,子孙赐姓张氏。周宣王时有卿士张仲,其后裔事晋为大夫。”此记载认为张氏得姓始祖挥是黄帝子少昊青阳氏的第五子。两者孰是孰非,令人莫衷一是。不过,这两条记载相同之处却在于明确了挥为张姓得姓始祖,系黄帝之孙。而且可以明确,挥是因为发明了弓矢,身任弓正亦即弓长职务而得姓的。在欧阳修的张姓系谱中,挥以后第二个姓张的便是张仲,两者是何关联并未言明。上述记载层累地构成了后世张姓的氏族文化。挥为张氏始祖一说,自宋代起伴随私修族谱的兴起和盛行,广泛流传开来。 首次将台骀纳入张姓宗族系谱的是成书于明嘉靖十四年(1535),由徽州人张宪、张阳辉等人主修的《张氏会修统宗世谱》。该谱是现今所能见到的最早记述张氏起源地的张氏宗谱。由于其撰修者官职和文化层次高,因而在张氏宗谱中有一定的权威性;它又是排版印刷,印数多,故流传也较广;对之后的张氏宗谱,特别是对张氏起源地的认知有较大影响。此后的张氏宗谱及姓氏著作经常引述该谱为据。该宗谱在“得姓郡望”中记述:“吾张氏之得姓者,自轩辕黄帝第三妃彤鱼氏之子曰挥,观弧制矢,赐姓张氏;官封弓正,主祀弧星;居尹城,国于青阳,后改清河郡。此张氏得姓之由,而望清河郡者独最。”如果将其与此前的姓氏书、氏族志相比较,不难发现在唐宋时代并不清晰的世系关系,至此时反倒“考证”得相当清楚了,令人生疑。不仅如此,在宗谱的“本源记”中还进一步厘清了张氏得姓始祖与台骀的关系:“张氏出自姬姓,黄帝子少昊青阳氏第五子挥为弓正,始制弓矢,子孙赐姓张氏。尹城派始祖挥公,受封之国在山西太原府属之地。挥生昧,为玄冥师。昧生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太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掌水旱疠疫之职,即山川之神也;世飨其祀,今太原县有庙存焉。”以此为据,黄帝—少昊青阳氏—挥—昧—台骀的张氏祖先系谱便清晰地建构出来,作为汾河水神的台骀从此堂而皇之地以张氏第三代祖先的身份进入张氏尹城派世谱。正因为如此,太原王郭村台骀庙内才有了台骀庙在前、昧公庙在中、挥公庙在后的建筑空间布局。不难判断,这一布局出现的年代当不早于明代,甚至可以将其视为嘉靖统修张氏宗谱活动的直接产物。对于张姓宗族而言,神明与祖先便开始合二为一了。 第二个维度是汾河流域张姓宗族围绕祖先进行的宗族文化建构。众所周知,明代嘉靖大礼议对于宗族在地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这一大背景下,太原张氏也持续进行着宗族形象和象征资源的建构。仍以太原王郭村台骀庙为例,据该村已故离休教师王锡寿先生记述说,台骀神庙所在的王郭村古称尹城里,为张氏始祖挥公受封地。至今村中仍有一条街巷名叫张家巷,是历代张姓聚居之地。张姓曾经是该村所在尹城里的名门望族。王郭村村西还有青阳沟、青阳河、青阳庙等地名或遗迹。笔者于2014年6月在青阳河村访问时也了解到,这里过去曾经是张家坟,村里殷姓人家是张家看坟人的后代。该村过去还有一座规模很大的青阳庙,供奉张氏始祖挥公。传说此处还有春秋战国时期赵国谋臣张孟谈的墓地。附近一处名叫神仙峁的地方,据说是八仙中张果老与八仙聚会之地。神仙峁南麓的南峪山半山腰还有明代张三丰的墓地。这些与张氏有关的地名和传说,构成了尹城派张氏发源地的重要文化表征,有助于强化张氏族人的宗族认同意识,在区域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类似的事例在侯马西台神村也同样存在,今天人们在当地的台骀庙内仍能看到台骀与张姓祖先关系的各种文化表征物。在此意义上,太原尹城派张氏便与河北清河张、河南濮阳张共同构成天下张姓最主要的发源地之一。这种宗族文化认同,对于不同的区域社会具有各不相同的实践意义。 第三个维度是从区域实践的角度剖析将台骀建构进张姓宗族系谱的现实意义。受资料所限,我们仍以太原王郭村台骀庙为例加以讨论。王郭村所属的晋水流域,是山西一个重要的水利灌溉区,其水源是太原晋祠的难老泉。笔者在以往研究中,将其形象地称为“泉域社会”。研究中笔者发现,在晋祠泉域社会中存在着张姓世袭渠长职务的现象。晋水一源四河,分别是北河、南河、中河和陆堡河。其中,中河和陆堡河归属于南河水系。在这一水利系统中,南河与北河三七分水,北河七,南河三。当地将负责水利管理的职务称为渠长。根据规定,北河渠长历来由花塔村张姓世袭充任。同样,中河渠长也是由长巷村的张姓世袭担任。何以张姓在水利管理中具有如此大的优势?以往笔者只是简单地将其与晋祠泉域长期流传的花塔村张姓族人“跳油锅捞铜钱”的传说相联系,认为张姓族人舍弃一己性命捍卫北河水权的行为,是后世该村张姓族人世袭渠长职务的重要依据。但何以不属于北河的长巷村张姓也同样能够世袭中河渠长职位?显然,单纯强调油锅捞钱的义举是不够的。 通过进一步检索文献和实地调查,笔者发现位于晋水北河的花塔村张姓,乃是晋祠泉域内不少村庄张姓的一个重要迁出地。花塔村张姓并非当地土著居民,而是明洪武年间从南京花柳巷迁来的,分为前股、后股和东股三股。(30)之后以花塔村为中心,张姓族人不断迁徙至附近的长巷、赤桥、古城营、南城角、东蒲村、城东后街等地。(31)笔者在实地调查中得知,长巷村的张姓承认与花塔村的张姓是一家,并且是长巷村最早的住户。长巷村张姓过去每年都会派人去王郭村台骀庙参加祭祖活动。王郭村的张姓则是从古城营迁移过去的。古城营张姓包括多支,人数最多的一支是明洪武年间自河北宛平县迁来,另有从太谷县范村、清源县和花塔村迁来的张姓,不同的张姓之间存在联宗行为。由此可见,张姓遍布于晋祠泉域各主要村庄。明清以来,随着晋祠泉域水资源供需矛盾的不断加剧,张姓族人便利用其宗族共有的文化符号和象征资源,参与到争水、管水的事务中去。刘大鹏的《晋祠志》中还记载了明弘治年间北河渠长张宏秀献民间夜水给晋藩王府的事例,显示了张姓族人在晋祠水利中不可替代的支配地位,实现了宗族与水利的密切结合,呈现出祖先治水—祖先争水—后辈献水—后辈管水的特点,展示出晋祠泉域宗族在地方水利这一公共事务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尽管如此,在晋祠泉域并未形成张氏一族独揽水利大权的局面,而是有多姓宗族力量参与其间。如陆堡河北大寺村的武氏宗族,就专擅晋祠陆堡河水利大权,陆堡河因此被称为武氏“家族之河”。此外,晋祠东庄高氏一族也凭借其祖先的威名,以明代嘉靖年间担任浙江按察副使的高汝行为代表,通过建立高氏与晋祠台骀庙的联系,将晋祠台骀庙改造成为高氏家族的香火庙,从而与以台骀作为祖先的晋祠泉域张姓宗族争夺文化资源,分庭抗礼。这显示了张姓宗族并未获得晋祠泉域完全的支配性地位,而是不断面临其他姓氏和家族力量的挑战与威胁。在此形势下,张姓族人更需不断强化以台骀为象征符号的宗族认同,以便在激烈的竞争中能够处于不败之地。不同宗族势力在特定地域社会内的权力角逐,本身是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其中应当既有对抗也有合作。有趣的是,今天当我们在太原晋祠台骀庙前访问时,这个明清时代曾经与东庄高氏一族有密切关联的神庙早已失去了昔日的功能,台骀作为张姓祖先的观念已经深刻地嵌入到当地人的精神世界里,完全忽略了东庄高氏宗族明清时代对台骀庙的长期经营。那么,东庄高氏何以会丧失对晋祠台骀庙的控制,不再与张姓争夺台骀这个象征性文化资源,是未来研究中值得继续探讨的话题。 四、余论 台骀从一个三晋大地上最早的统治者、居住者,到春秋时期成为汾河流域的山川之神、地方保护神,再到明嘉靖以来合神明与祖先于一体,成为张姓宗族借以实现自身发展壮大的一个认同符号和象征资本,显示了神明与祖先对于明清以来北方地区宗族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推动作用。在这一点上,与学界在华南宗族“发达”地区所观察到的“祖先与神明”(32)的关系并无二致,反而具有高度一致性。如果继续用弗里德曼意义上的宗族概念来讨论北方宗族问题的话,人们会发现北方宗族“不发达”地区竟然和“发达”地区一样也存在着如此相似的历史过程。这就不得不让我们重新审视以往所谓北方地区宗族不发达、甚至是一些研究者所言之“残缺型宗族”是否真实可靠。或许这只是一种表象或假象。因此,以往人们所持有的宗族观念是存在偏见的,不能仅仅从外部形态上用华南宗族的标准来衡量北方地区,而必须对中国北方宗族的形成过程加以重新审视。 同时,台骀形象的改变还激发了我们对山西水利社会中宗族角色和作用问题的重新思考和定位。“亦神亦祖”的台骀揭示了北方水利社会中宗族势力借用象征符号在地方水资源争夺中表达宗族意志的一种重要手段,表明宗族与水利的结合在北方地区表现得也是非常明显的。其不同之处在于,受地理条件、经济水平和政治因素的作用及影响,在北方地区难以出现某一族姓长期、完全控制或垄断稀缺水资源的情形,反而会出现多个宗族瓜分挤占、相互妥协、相对均衡地分配有限水资源的局面。正是在此意义上,笔者以为将宗族研究引入山西水利社会史,有望突破以往各说各话的宗族史、水利史研究,从而为北方水利社会史研究增加一个新的视角。 注释: ①科大卫:《皇帝与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26-429页。 ②张俊峰:《明清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的理论视野》,《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2期。 ③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19页。 ④按照这种说法,五帝为:黄帝、颛顼(黄帝孙,即高阳氏)、帝喾(黄帝曾孙、颛顼堂侄,即高辛氏)、尧(黄帝玄孙)、舜。 ⑤按照这种说法,五帝为:白帝(西,金)、青帝(东,木)、黄帝(中,土)、炎帝(南,火)、黑帝(北,水)。按吕不韦“十二纪”的提法,五帝是主管四方、四时和五行之神。黄帝居中,具土德;大皞居东方,具木德,主春,亦称春帝;炎帝居南方,具火德,主夏,亦称炎帝;少皞居西方,具金德,主秋,亦称白帝;颛顼居北方,具水德,主冬,亦称黑帝。 ⑥另据马骕《绎史》中的观点,认为台骀属东夷族少昊世系,值得重视。其系谱顺序为:少昊—修—昧—台骀—沈、姒、蓐、黄。详见马骕:《绎史》第一册,王利器整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页。 ⑦杨宽:《鲧、共工与玄冥、冯夷》,载顾颉刚编:《古史辨》第七册第十二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36页。 ⑧比较有趣的是,这种父子治水的模式在中国古史和传说记载中屡见不鲜。比如尧舜时代的鲧、禹治水,后世留下了大量有关大禹治水的神迹和庙宇;秦代的李冰父子治水,至今在不少地方仍建有祭祀李冰父子治水的庙宇,其中尤以四川成都灌口二郎庙最为著名。 ⑨参见陈怀荃:《大夏与大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1期;李炳海:《汾神台骀与周族始祖传说》,《山西师大学报》1993年第1期。 ⑩李炳海:《汾神台骀考辨》,《山西师大学报》1990年第4期。 (11)《曲沃县志》卷38《艺文上》,第343页。 (12)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编:《晋都新田——纪念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建站40周年》,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3页。 (13)台骀作为汾神,何以在汾河流域之外的其他地方出现两座台骀庙,非常奇怪。山西大学民俗学者段友文教授认为五台县出现台骀庙,应该是晋国文化北上迁移和村落人口流动的结果,笔者对此持谨慎态度。详见段友文、王旭:《汾河之神台骀传说信仰的文化传承与村落记忆》,《民族文学研究》2013年第6期。 (14)另据金人王遵古《昌宁宫记》有“唐贞元九年,始庙于近郊”的记载,亦可为证,文见光绪《汾阳县志》卷十二《艺文》,第331页。另,光绪《汾阳县志》卷九《坛庙》中亦有“台骀庙,唐贞元九年建,有碑,令狐楚撰文”记载可互为印证。可惜的是,令狐楚的谢雨碑现已佚失,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宋金时代人们在有关台骀庙的记述中屡屡提及此事。清刑部员外、曲沃人裴志濂在《重修台骀庙碑记》也曾讲到“唐令狐楚有所撰碑文,在汾阳县台骀神庙”,足见令狐楚在台骀庙谢雨一事在汾河流域影响之大。 (15)《旧五代史》卷七十九《高祖纪五》;《新五代史》卷八《晋本纪第八》。 (16)雍正《山西通志》卷164《祠庙一》:“临汾县:汾水神祠,在西一里,土人名河神庙。”雍正《山西通志》卷166《祠庙三》之静乐县,在记述该县定河村昌宁公庙时,最后提及“又西郭外有汾水川祠”。无论是汾水神祠还是汾水川祠,均是指台骀庙而言,其名称始自唐太原节度使卢钧。 (17)贺际泰:《台骀庙今昔》,《侯马文史资料》第六辑,第48-56页。 (18)宋宝元二年(1039)掌禹锡撰《重修昌宁公庙碑记》,见道光《太原县志》卷之十二《艺文》,第627-628页。 (19)太原东庄人高若岐《重修台骀庙碑记》中有“昌宁公者,石晋天福之封号也。此县中之公庙,每岁端午日有司祭之”的记载。详见《太原县志》卷之十三《艺文》,第650页。 (20)王锡寿:《台骀庙的传说》,载郭永安主编:《太原张氏遍天下》,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页。 (21)(金)张守愚:《昌宁公冢庙记》,见乾隆《宁武府志》卷十二《艺文》,第165-166页。 (22)道光《太原县志》卷之三《祀典》。 (23)雍正八年《重修台骀庙碑记》,见刘大鹏:《晋祠志》卷第一《祠宇上》,第33页。 (24)裴志濂:《重修台骀庙碑记》,见《曲沃县志》卷38《艺文上》,第343页。 (25)徐继畲:《修建雷鸣寺记》,见《三晋石刻大全·宁武县卷》,三晋出版社2010年版。 (26)参见段友文、王旭:《汾河之神台骀传说信仰的文化传承与村落记忆》,《民族文学研究》2013年第6期。 (27)同上,第86、87页。 (28)雍正《山西通志》之静乐县。 (29)见《诗经·小雅·六月》,记述周宣王大臣尹吉甫自镐京返乡时,与亲友欢宴,其中出席的人员中就有以孝友著称的张仲。 (30)道光二十三年《先畴永赖碑》,碑现存太原市晋源区花塔村华塔寺正殿内。 (31)咸丰三年《东里解张氏家谱》。 (32)参见贺喜:《亦神亦祖:粤西南信仰构建的社会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