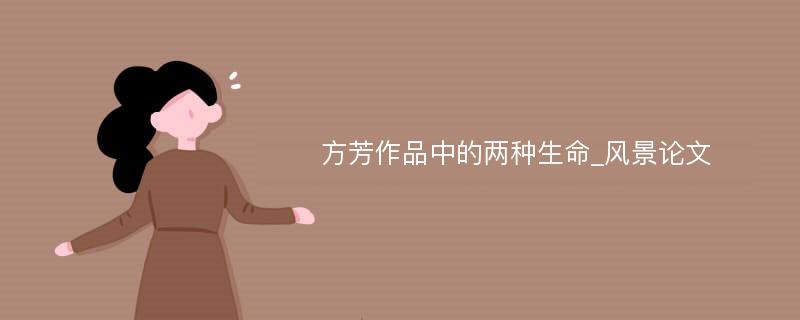
方方笔下的两种人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笔下论文,人生论文,方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方方在“新写实”的热潮中崛起于中国文坛。在“新写实”的喧嚣之后,在作者、读者及批评家的激动与亢奋过去之后,我们有必要再次梳理和审视方方笔下的人生。
纵观方方小说所反映的人生,我们可将其分为两种类型。
一、沉重而深邃的人生
人生之沉重,在于其丰富的生活蕴含及其触发的沉潜的人生思考;人生之深邃,在于作品深入而透彻的人生透视和对人的生存的哲理探寻。我们在方方的《风景》、《祖父在我心中》、《桃花灿灿》等小说中,不难看到这种人生。
《风景》以汉口著名的贫民区——“河南棚子”为背景,描绘了一个仅占有13平方米的11口之家的生存景况和生活状貌,展示了一种亦悲亦喜、令人深思的人生“风景”。小说以已经死去的“小八子”的眼睛来观察“父亲”一家的生活。粗略一看,小说似乎向读者展示了几种不同的人生:父亲贫穷而充实、麻木而自信的人生,大哥二哥开始认识自身但又中途迷失的人生,大香小香猥琐灰色的人生,五哥六哥在道德、伦理、正义与邪恶、犯罪之间摇摆的投机人生,七哥由被歧视被虐待而生出的逆反心理所致的不择手段向上爬、“换一种活法”的人生,等等。但实际上作者只描绘了一种人生: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和议论氛围中的中国平民的艰难、粗糙、困顿的人生——一种凡俗人生的生存史和生命史,《风景》主要以父亲的生活反映了这种人生,父亲的生活是这种艰难粗糙困顿的凡俗人生的主要内容。父亲勤劳、正直、刚毅、豪爽,但又浅陋、愚昧、自私、粗暴;母亲是父亲的补充或注脚,而九个儿女的生活则是父亲的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条件下可能发生或应该发生的变异与衍化。可以这样说:九个儿女的人生是在父亲的人生这块培养基地或菌块上长出的菇群或“子实体”。——大哥继承了父亲的正义感与好斗精神,二哥有着父亲的正直与良心,大香小香拓展了父亲的自私与猥琐,五哥六哥正运用着父亲的智慧与愚蠢在汉口与现代人斗智斗勇,就象父亲当年在汉口“打码头”一样;七哥似乎背叛了父亲的一切,然而,只有经历过父亲的人生的人才会对贫穷与低贱产生铭心刻骨的仇恨,并且如避瘟疫般地逃离父亲的人生和不择手段地追求与父亲完全两样的人生。
从父亲的人生中我们窥见了千万个父亲的人生乃至整个东方民族的生存史与生命史。这部生存史和生命史饱和着汗、泪、血和人生的酸甜苦辣,它带给人们的是深刻的反省和深沉的思考,——《风景》中的人生是一种沉重如枷锁、厚实如磐石、苦涩如青果的人生。
《祖父在父亲心中》抒写的是知识分子的人生,作者对祖父和父亲这两代知识分子的气节与人格进行了对比描写。尽管祖父的生活花去了更多的笔墨,但作者的重心乃是落在父亲的一生之上。祖父乃一介文弱书生,但他活得刚毅正直,大义凛然,死得勇武刚烈,惊天动地。他毕业于“京师大学”,但他放弃了大学教授头衔和优厚的待遇而选择了小县的基础教育,目的是“教育救国”。进步学生惨遭杀害时,他敢于申张正义;带领乡亲们逃难却不幸与敌遭遇,但他面不改色,怒斥倭寇的侵略行径;面对敌人的利诱劝降,他慷慨陈词乃至破口大骂,视死如归,——祖父“书生一般地活着,勇士一般地死去”。祖父活在父亲心中,但父亲表现出来的却是另一种气质另一种人格,父亲同祖父一样“满腹经纶”。在全国解放前的岁月里,父亲似乎象祖父一样生活过:有救国的壮志,在何去何从之际果敢地选择了大陆而放弃台湾。但解放后的父亲慢慢地蜕变。首先他委屈地放弃了自己的专业爱好,在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之后他变成了惶惶不可终日的漏网之鱼;接踵而来的文化大革命更使他心神不宁如坐针毡:勤勤恳恳地写了一摞又一摞的反省与检讨,剃光了头发准备接受揪斗,为了在揪斗中表现出色或者是为了少受皮肉之苦而反复练习“坐飞机”。父亲忧心忡忡忍辱含羞提心吊胆地活着。最后,在观看日本人残杀中国人的影片《军阀》时,父亲绷紧到极限的神经不堪重负,他在影幕的刀光剑影和扬声器的枪炮轰鸣中倒下了。两代知识分子,两种人生。为什么祖父活得头高颈昂、刚毅激越而父亲却活得缩头窝脖萎蘼孱弱呢?为什么祖父面对吃人肉喝人血的活生生的野兽而面不改色巍然屹立,而父亲却在野兽的影像之前软塌下去呢?——作者留下了一个沉重得令人透不气来的考题!
还值得一提的是,方方对父亲的人生思索还提供了另外的两个参照系。一个是作为同类同向参照的席先生。席先生也象父亲一样谨小慎微战战兢兢地生活,唯一不同的是他比父亲多活14年。然而,这14年是于人于已都无任何意义的十四年,因此早在席先生偶遇车祸离世之前他就“很随意地”写下了八个评价他人生的字:留他如梦,送他如客。显然,席先生的14年是父亲人生的假设性延伸。——为什么父亲们这代人会有如此人生呢?另一个参照系是五叔的人生。拿作者的话来说,他们是“一条血脉,两种人生”。五叔蹲了30多年监狱,在被特赦出狱后他仍然顽固地说:我八年抗战有功,三年反共无罪。在听“我”讲述了父亲的死之后,他“切齿地说了句:‘日本人!’”因此作者暗示:五叔更象祖父。显然,五叔是作为父亲的对比参照而出现的。为什么同是祖父的儿子而五叔的人生与父亲的人生会有天壤之别呢?难道仅仅因为父亲是“懦弱夫子”而五叔是“见惯鲜血且制造流血并能直面鲜血谈笑自若的武士”吗?——这两个参照系启发人们对父亲及父亲们这一代人的人生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他们悲剧的成因是在于时代还是在于他们自身呢?
如果说《风景》、《祖父在父亲心中》写作的有意展现了生存环境、生存条件等外界客观因素对人生的干扰与左右的话,那么在《桃花灿灿》中,方方则主要从人自身的弱点等主观因素出发对人的命运与人性进行了思考。粞与星子互相倾慕,但由于家庭出生而自卑,他不敢向星子表白心迹;而星子则恪守传统的贞洁观念,努力掩饰自己的情感,矜持地对待粞的种种暗示,因此二人错过了互诉衷肠的良机。接着,粞在自尊自贱自慰的复杂心境中与水香发生性关系。他的这一举动深深地伤害了星子,使星子的心头乌云层积(或者“桃花灿灿”)。粞为了摆脱爱情的痛苦,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他想以繁杂的事务来麻醉自己,同时也企图以事业之成功来填补心头的创伤。在星子苦恼、犹疑之际,粞又一次作出错误的决定:将爱情作为赌注压到事业上,他毅然与顶头上司那患有精神病的妹妹结了婚。在痛苦与失望中,星子茫然地将自己一直坚守的贞洁草草地送给了亦文。事与愿违,由于突然的人事变动,粞不仅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而且还成为官复原职的领导的眼中钉。在爱情与事业的双重失败的重击之下,他倒下了。在弥留之际,星子从蜜月旅行的中途折回,投入了他的怀抱。粞带着一点可怜的满足而疲惫地睡去,而星子则带着一枚爱情的苦果(后来的儿子“旸”)为一个悲剧画上句号后朝另一个悲剧走去,——她与亦文的婚姻悲剧早已张开血盆大口盘踞在她人生的要道上。
这是一个古老而平淡的爱情故事,但作者从这平凡的生活、平淡的悲剧中提炼出了人生的精义。作者在小说结尾处发问:是谁造成了粞与星子的人生悲剧?是“生活本身”还是他们自己?作者的答案是:是人类这一类生命未曾进化得完美而自携的弱点一直在细细地咀嚼着他和她,而且“这种咀嚼是从一生下来便开始了”。方方的目光是敏锐的。粞总是在自卑自尊的情感漩涡中挣扎,在人生的紧要处他总是优柔寡断,一再判断失误:而星子在某种正统观念的支配下,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她正确的人生决断总是被自己的优柔、矜持、狭窄所断送,而在执行自己荒唐、错误的选择时她又总是那样自信、果敢、刚毅。就是他们自己酿造了自己的人生苦酒,就是他们自己“一口一口地”吃掉了自己。作者从平凡寡淡的生活中淘洗出一种沉甸甸血斑斑的人生,铺展于读者面前,读者在这触目的人生中发现了自己的痼疾,看到了人性的弱点,也看到了人类的悲剧。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感觉到了《风景》等作品中人生的沉重与深邃。为什么在方方的这些小说中会有这样的人生呢?
首先,《风景》等小说中人生的厚实与深邃主要来自作者对生活的深刻认识及对人生的准确把握。方方能以联系的目光洞察人生:在琐碎的生活里找人生,从平凡的人生中看世界。她在芜杂粗糙的生活现象中提取人生的精义,将历史的人生、现实的人生、未来的人生连为一块,对其进行共时的历时的思考;她能使读者在特殊的个别的人生中看到普遍的人生、民族的人生;她能从具体形象的人生中抽象出具有标本性质的人性,艺术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父亲”的人生、粞与星子的人生已说明了这一切。方方还能敏锐地指出人生的种种矛盾。生活现象如群山一样不规则地散布存在,只有找准了视点且有相当眼力的人才能“横看成岭侧成峰”。方方以犀利的目光从最佳的视角看出人生矛盾的“岭”和“峰”:从合理中发现不合理,从“无事的悲哀”之中找出触目惊心的人生悲剧、人性悲剧。例如,正义与邪恶、美德与恶行、高尚与低劣等等许多对立的东西是那样和谐地存在于父亲的一生中,历史要求人类不断地共同进步,但它总是极少为社会的最普遍最基本的分子——下层平民提供一条较为平坦的人生道路以及供他们展示自己的善良、质朴与正义的人生舞台,历史总在不断地制作一副副以“河南棚子”为主景的人生风景;心中装着祖父的父亲追求理想追求光明,但他最终都在阳光下像冰一样消溶;粞和星子寻找爱情渴望幸福,但他们的一切努力都是南辕北辙,适得其反。这些,也许只有在方方小说中才能看到。方方还能以正确的价值观念衡量人生。《风景》等小说创作于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初。在这段时期内,传统的价值体系正在松动,原有的价值观念正在接受时代的淘洗,新的价值观念不断破土而出,在许多作家评论家今是昨非、无所适从之际,方方敏慧地择取合理的价值尺度用于《风景》等小说的人生评价。她评价人生的核心标准是:人生的存在发展要有利于人性的升华与历史的进步。从这一尺度出发,方方揭示了人生的悲剧,批判了人生的弱点,指出了历史的荒谬。
其次,《风景》等作品真实地反映了人生。方方在发表《风景》(1987年)之后,人们给她戴上了“新写实小说家”的桂冠,但她并没有完全接受这一称号。戴望舒在三十年代论现代派诗的时候说:诗人应该在表现自己与隐藏自己之间。我认为方方的创作风格介于传统的现实主义与新写实之间。在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品中作家很少隐藏自己,他们一般以两种方式显露自己的面目:对生活的选择、提炼、加工和直接间接的生活评价;而在具有反传统精神的新写实小说中,作家大多深深地隐藏自己,他们躲在所谓“原汁原味”“毛茸茸”的生活后面,把评价、判断的任务与权力交给读者。方方的《风景》等作品既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如茅盾的《子夜》,刘心武的《班主任》),也不同于时髦的新写实小说(如池莉的《烦恼人生》、刘震云的《一地鸡毛》),甚至与她自己早期的《“大蓬车”上》、后来的《一唱三叹》等作品也大不一样。在《风景》等小说中,方方是半隐半现的。“半隐”:不删削生活的灰面,不回避生活的矛盾,不剔除生活的琐碎,但这些生活并非完全“毛茸茸”,因为从中能窥见作者的选择与暗示,这是一些会“说话”的生活;“半现”:作者通过情感倾向、“旁白”和人物的思想、语言等间接地表达自己对人生的思索和见解。例如,作者对《风景》中的父亲的同情与厌恶比较明显地表达了作者的理性评价,在《祖父在父亲心中》,作者让母亲委婉地评价父亲的一生,在《桃花灿灿》中以“旁白”的形式评论粞的悲剧、让星子探寻她为爱而努力的实际意义,等等。“半隐”带来了作品的感性真实,因为作者尽可能地将原样的生活展现读者面前;半现使作品具有理性的真实,固然,作者的评价、见解与思索不一定全是生活真理或人生哲理,但适当的理性规范能防止生活的琐碎与粗糙淹没生活的本质,适当的理性提示能使读者更准确地把握作品所反映的人生现实。因此,方方的这种半隐半现的艺术表现使《风景》等小说既具有一种有别于传统现实主义的、新颖的美学风格,又使作品具有传统现实主义的真实性。
二、虚浮而困惑的人生
我们在方方的《白梦》、《白驹》、《无处逃遁》、《行云流水》、《一唱三叹》等小说中会找到另一种人生,一种虚浮困惑的人生。人生之虚浮、困惑在此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指人物形象的浮躁、焦虑及其在人生道路上的惶惑,其二是指人物形象的人生内涵单薄或混沌。
《白梦》与《白驹》都是具有浓郁荒诞色彩的戏谑小说。
《白梦》通过女主人公家伙的际遇与见闻反映社会生活。作者似乎无意塑造典型,也无意展示某种具体的人生,作者企图概括的是一种抽象的人生:一种空虚、无聊、荒诞的人生。家伙玩世不恭,她以戏谑的态度对待生活,以戏谑的眼光看待自己身边的一切。她在“洪洞县中无好人”的作家协会中随波逐流,逢场作戏,游戏人生;在她眼中,上至领导、前辈,下到同事、好友无不虚伪、庸俗、贪婪、愚蠢;在她眼中,人生如梦,世界“茫茫一片白色”、“除了那白,什么也没有”。《白驹》写了两类城市青年:以麦子为代表的青年知识分子和以小男为代表的青年工人。麦子靠着一张大学专科文凭和一块干部子弟招牌活得洒脱风光。他随心所欲漫不经心,但又总是频频得手左右逢源;他毫不经意地使两个濒临倒闭的企业起死回生,他在妻子与情人之间优游自如,中高层干部视他为贵宾,流氓青皮奉他为神灵。小男萎琐、自私、玩世不恭。他偷偷摸摸(尤其偏爱少女的三角短裤),赌博抹牌,酗酒斗殴,投机买卖,活得也算潇洒。他与麦子的共同之处是追求吃喝玩乐、享受人生。显然,这两种人生也是荒诞的,尽管作者在小说结尾处借人物的对话说明:“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要想改变这种“可怜”的境地,只有“进入生命的另一个层次”,但从作品的整体结构来看,作者并无展示某种人生或探索人生之意。
《白梦》与《白驹》的内涵有相同之处。它们共同的文本现实是:展示一定现实阶段的经济文化的变更与动荡,以及由此引发的人们灵魂的骚乱与躁动。在这两个中篇里,作品所有的表意符号(情节与事件)不是以人生为主轴而集结,而是以社会为中心而排列;作者追求的不是人生的深度,而是对生活现象或表象进行罗列与串连,以此来证明一种社会现实。固然,社会现实之中也有人生,但《白梦》与《白驹》中的人生只有共时的广度,而没有历时的深度及内涵。我们没有必要苛责方方这两个中篇只注重社会而忽略人生,然而,漫长的文学史已向我们昭示:绝大多数成功之作总是社会中见人生、人生中有社会,那么,《白梦》与《白驹》在社会本质把握或人生探寻方面有何偏颇呢?在《白梦》与《白驹》中,我们看到了作者对《第二十二条军规》、《出了毛病》等西方荒诞小说的艳羡,和对《你别无选择》(刘索拉)、《无主题变奏》(徐星)等小说的戏谑姿态的赞同。作者刻意追求荒诞美学风格,但恶谑的语态与游戏的笔墨干扰着作者对社会本质的把握或对人生内涵的发掘。此外,荒诞美学风格虽然给读者带来了奇特的艺术享受,但“荒诞”既是一种美学特色或美学范畴,又是一种哲学认识或哲学范畴,它是西方工业社会的产物:作为艺术表现手法的荒诞是不完全适合于相对落后的东方农业社会。这姑且不论。但如果作家以“荒诞”的哲学眼光看待我们当今的社会与人生,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哲学意义上的荒诞所包含的否定、虚无等质素会使作家心气虚浮和观点片面。这无疑会影响作家对社会或人生的正确把握。事实上,在《白梦》与《白驹》中,冷静的分析与谛视被浮躁的嘲讽所替代,细致而客观的描写没于芜杂的现象罗列之中,因此,我们认为《白梦》等作品中的人生之虚浮与混沌,一方面是作者的有意追求,一方面是来自作者把握偏颇。
如果说《白梦》等作品中的人生以虚浮为基调的话,那么《无处逃遁》、《行云流水》、《一唱三叹》等作品中的人生则偏向困惑。
《无处逃遁》与《行云流水》是姊妹篇,它们分别写了高校教师严航和高人云的惶惑人生。严航为了评上副教授和到美国攻博而拼命地写文章、考“托福”、跑签证。为了挤时间,他冷落了妻子,因拒绝教学工作之外的一切杂务而得罪了同行与领导;为了凑钱,他忍痛让妻子去歌舞厅卖唱,厚着脸皮向父母借贷和向妻子讨钱。但最终他一事无成:“副高”评定因同行排挤而落选,妻子因被台湾富商紧追不舍而与之发生情感纠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的签证也因担保人不可靠而泡汤。此时,严航陷入了困惑的深渊:“家园何在,路人遥指天边。此番怎行,依是长亭短亭”;“原来命属一根根小绳子就只能总是属它”,——无处逃遁。《行云流水》中的副教授高人云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但在新的时代与新的生活面前,他总觉得心境杂乱、无所适从。例如,在发廊受到理发小姐的嘲笑与捉弄,在饭馆吃面时受到吃肉的学生的奚落,家中没有一件像样的电器使他在来访者面前窘迫,他想认真工作、努力做学问又力不从心,等等。在变化的形势与现实面前,他竭力保持平稳,但生活的浪涛却接二连三地搅乱他的平和与宁静,于是,在胃出血愈后又因心脏病而住进了医院。《无处逃遁》、《行云流水》通过对知识分子的琐碎生活描写,触及了社会的一个症结。我们不能否认作品生活容量和作者的观察角度,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作者在描写知识分子的人人生时所流露出来的困惑以及由此而致的人生把握偏颇。
《无处逃遁》等作品中的人物所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是“义”与“利”的选择。对于严航来说,他是应该安贫乐道为国为民尽力,还是应该奋力一搏到美国去脱胎换骨定居“天堂”?对于高人云来说,他是应该淡泊明志、恪守教书育人的信条,还是应该随波逐流而把改善生存条件(如象小李小马到南方去弄钱)放在第一位?这里涉及到金钱与道德的选择和物质与精神的价值判断;在“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情况下,是取“义”还是“利”呢?作者没有作出道德选择与价值判断,她的态度是犹疑的。与“义”“利”相关的是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问题。正如社会是由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所构成一样,人生也是物质内容与精神内容的结合体。人的物质生活条件、物质生存环境是评价人生质量的重要依据与指标。对严航、高人云等知识分子来说,我们只有把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物质生存环境置于整个社会的物质生活与物质存在的坐标中并找准对比参照系,才能对他们的烦恼与困惑作出解释并进一步对他们的人生作出比较合理的评价,在作品中,方方为她的人物安排了两个参照系。一个是高收入阶层:腰包撑得鼓圆的歌舞厅老板、一掷千金的台湾商人,等等;一个是从事简单劳动但收入颇丰的个体劳动者,如理发师,与前者相比,严航高人云活得寒酸甚至痛苦,与后者相较,他们又活得拘谨、萎靡。就是在这种对比中,作者凸现了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高投入低收入,生活窘迫,在现实的物质环境中举措失当,无所适从。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展示他们的精神困惑:浮躁、焦虑,在人生道路上彷徨,在人生价值观上迷惘。然而,这两个参照系的确定合理、准确吗?在此笔者不想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而只列举几个简单的事实:在小说中,严航为何反对妻子与歌舞厅老板合作?高人云夫妇为何反对女儿高苑放弃“复读”而去当发廊小姐?在现实生活中,为何年复一年地出现“黑色七月”千军万马挤独木桥拼死进入知识阶层?许多个体户腰缠万贯之后替子女设计的前程为何不一定仍是“万元户”?此外,在中国“体脑倒佳”既是一个物质现实,但其中又不乏情感因素;例如,在少数非脑力劳动者对知识分子的浅薄的睥睨中,不乏成功之后与知识分子在经济上和人格上平起平坐的自豪与喜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知识分子进行心理或情感报复的快意;而知识分子对自身处境的自我揶揄自我慨叹之中又包含着因传统世袭的至尊地位或名利优势的动摇而产生的惆怅和心理失衡。在《无处逃遁》等作品中,作者只注意到了“体脑倒挂”的一面,而忽视了其社会意识的一面。显然,作者对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等问题的把握也出现了偏颇。
作者在人生价值选择上的优柔和生存环境之设置的偏颇,导致了作品中人物在生活上的浮躁、焦虑和他们在人生道路上的彷徨与困惑,同时也影响了作者在已掌握的生活内容中进行深层的人生探索和在已经触及的社会问题中挖掘深沉的人生内涵。当然,从“新写实”或者“后现代派”的艺术宗旨看,作家可以对某些问题“拒绝阐释”或“保持感情的零度”,但这些问题他可以不明于口,却一定要明于心,否则,就会影响到作品的人生展示和读者对作品的人生把握。
在《一唱三叹》中,作家显得更加困惑,作品的主要人物琀妈的前半生活得充实、荣光。她向社会奉献了她的四个儿女和丈夫,换来满墙的奖状和街邻的赞誉。然而,社会开始发生变化。在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由义务服务变为有酬工作后,琀妈被挤掉了;房子拆迁之后,其它街邻都搬进了新居,而房管干部却动员她再发扬一次雷锋精神,将新房让给他人;人们开始冷落琀妈,嘲笑琀妈。琀妈住在只有十二平方米的房间里,她孤独、后悔、惶惑,人们每天看到她穿着紫色的衣裤坐在门外紫色的晚霞中发呆。盈月老师是作为琀妈的陪衬而出现的。她是琀妈的大学同窗,尽管她的前半生平庸、猥琐,但她现在却春风得意:子女们各得其所,她儿孙绕膝,被尊为“老祖宗”,她的居室内琳琅满目,珠光宝气。显然,作者在作品中设置了两种相互对照的人生观和价值体系。琀妈追求精神充实与思想进步,盈月老师追求物质享受与实际利益。在思想意识决定一切的年代里,琀妈如鱼得水,而在务实不务虚的新形势下盈月老师却扬眉吐气一路顺风。两种人生观,两种价值体系,谁优谁劣谁是谁非?作者虽然批判了盈月老师的“精明”、自私、庸俗,但对她现在的生活并无贬意。作者虽然肯定了琀妈的奉献精神,但对她的一生基本上是否定的。琀妈动员儿女下乡,但最终女儿在新疆失踪,才华横溢的大儿子在大山里成为庸人;在获奖、动员二媳妇追随儿子去西南等问题上,作者无情地嘲笑了琀妈的浅陋与愚昧;琀妈晚年的困惑与孤寂更是对她一生所求的全部颠覆。以此,作家表现出她前所未有的犹疑。她无法对两种人生作出正确的评判,于是她同时使用了两种价值评判标准:在批判盈月老师自私自利的务实人生哲学时则以精神追求为尺度,而在揶揄琀妈的务虚人生悲剧时则又以盈月老师务实的成就为参照。同时,作者对传统的价值体系与现今的价值体系这二者又不置可否。这里我们完全不可以用隐藏自己或“感情的零度”来掩饰作者的困惑。作家的困惑带来了琀妈的人生困惑以及人生内涵的混沌。
作家在《风景》等作品中是处于半隐半现之间,而在《白梦》等作品中作家的面目则处于半隐与全隐之间,在某些局部或枝节问题上不时进行情感判断,而在作品的整体倾向性上则态度隐晦。这一方面是因为作家不愿对生活作出解释,另一方面则因为作家不能对生活作出解释。
以上,我们讨论了方方笔下的两种人生。第一种人生厚实、深邃,第二种人生虚浮、困惑;我们肯定了方方把握第一种人生的准确及其透视人生与历史的目光的锐利,也指出了作者在反映另一种人生时表现出来的困惑与偏颇。然而,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指责作者在展示第二种人生时显露出来的困惑与偏颇。这首先是因为,有时对某种人生价值或某种社会本质作出正确的评价,只有历史才能胜任、才能完成,——是与非只有在生活完全冷却并经历史沉淀之后才会水落石出。第二,因为这种困惑与偏颇也是时代的困惑与偏颇,作者写出了时代的浮躁,写出了历史的混沌,也写出了自己的困惑,这从侧面反映了人生与社会的真实。方方没有回避困惑,也没有以生活的“毛茸茸”“原汁原味”掩盖自己的困惑,因此,我们在第二种人生中既看到了作家的真诚,又看到了生活的“本真”,——一种有待历史去提炼去分析的现实生活。
笔者深知,将方方小说中的人生仅仅分为两种且仅就极少数作品来讨论,有失片面;不过这种划分与讨论只是一种尝试,对方方小说中人生全面细致的梳理有待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