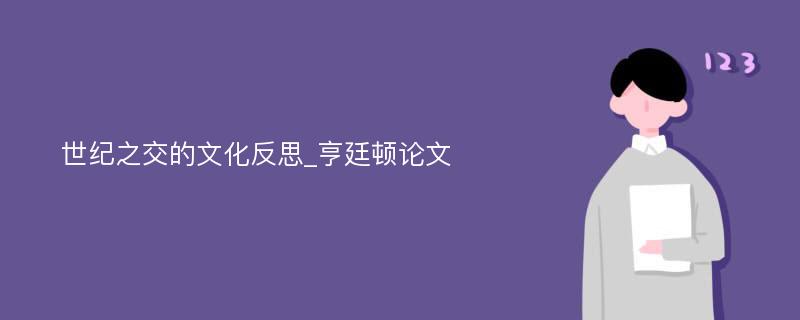
《世纪之交的文化反思》的思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思路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纪之交的文化反思》是东方文化研究所承担的一个科研课题。这里提出的,是一个“思路”。所谓“思路”者,就是对这个问题所思索的过程。这只是一条“小路”,一种“探路”,提出来和朋友们交流,目的是求得指路或引路。
一、把两个“世纪之交”联起来思索,会得到极其深刻的历史的启迪
我们面临的是20世纪到21世纪的“世纪之交”。即将过去的20世纪末,我们身在其中,已经看了许多,想了许多,还要继续看、继续想。即将到来的新世纪——21世纪会是怎样开头呢?我们只能想,还看不到,因为它虽然即将到来,毕竟还没有到来。但是,一百年前,也有一个“世纪之交”,这就是19世纪到20世纪即本世纪之交。这已经全部到来而且全部过去了。当然,对于全部到来和全部过去的“历史”,任何人都不可能全部看到和全部想到。因为历史太广大了,而个人(包括伟人)太狭小了。但是,过去的事情,终究是已经存在的了。从已有到未有,温故而知新。一般地讲,这是一种认识方法。特殊地讲,从已经过去的上一个“世纪之交”到尚未全部到来的这一个世纪之交,这个认识方法,具有极大的历史启迪意义。可以作为我们这个世纪之交的文化反思的先导。
上一个“世纪之交”的“新世纪”,就是20世纪。这个世纪开始的大事件在文化上就是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是怎样发生的?1919年之前,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21条不平等条约、巴黎凡尔赛和约……五·四运动的发生,直接的原因是民族压迫的刺激,中华民族想求得生存必须反对帝国主义;与此俱来的是帝国主义的奴仆、凶恶而无能的清王朝以及它统治下的黑暗的社会,人民想解放必须反对封建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这是不容否认的。
问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提出两大任务——反帝、反封建之后,历史的步伐来得太疾、太猛了。令当时的先进分子目不暇接,无法从容观察、从容认识、从容应付,不知不觉地就被卷入大潮,仓促地“跟着感觉走”了。当然,这是一种革命的感觉。
上一个世纪之交的新世纪初,即本纪的头一、二十年,历史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任务和问题:反帝、反封建,科学与民主,现代化与西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新国粹与新儒学……。除了社会主义在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毛泽东、邓小平的坚持和发展,历尽千辛万苦排除种种困境,终于取得了今天举世瞩目的成就以外,其它许多问题,都没有来得及从容思考认真解决。即令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其历史的因缘,也可以从上个世纪之交寻求到它先天不足的源头。
本世纪初,中国先进分子,高高举起反封建的旗帜,但是对于植根于宗法家庭制的封建主义意识并没有进行认真的清算,以致于半个世纪之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来了一个恶性的大发作。
本世纪初,中国的先进分子,高高举起反帝的旗帜,但是对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联系和区别,对于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历史作用还没有来得及认识和认真的评价,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浪潮就汹涌地到来了。
20世纪20年代末,世界的大势是:苏联的工业化迅速发展,而西方资本主义正遇到1929年以后的经济危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在许多先进分子的脑海中深深地扎了根。据本世纪的同龄人,亲身参加过五·四运动的中国先进文化人,有70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夏衍同志的回忆,这种历史条件对当年的先进青年,影响是很大的。最典型的是表现在“左联”的思想中。据夏衍同志的回忆,当时的左联有两种思想很突出,一是片面强调文化、文艺的宣传鼓动作用,提出“一切文艺都是宣传”的口号。这位几乎是领导了我国的文化工作一辈子的老党员很有感触地回忆说,从这种思想到文艺从属政治,到文艺为政治服务,到文艺为当前政治服务,到文艺为政策服务,到写中心、画中心、唱中心,到以阶级斗争为纲,从20年代到50年代,到文化大革命,都能寻找到它的脉络。当时左联的第二个突出的思想是关门主义。左联一成立,第一个纲领便是:“我们的文艺是反对封建阶级的,反对资产阶级的,又反对失掉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所谓“失掉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就是出身剥削家庭的知识分子,这是左的关门主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关门主义”呢?夏衍同志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左派青年的幼雅,二是受第三国际把各国社会民主党当作“最凶恶的敌人”的论点的影响。[1]
对照上一个世纪之交,联系起来反思我们的这个“世纪之交”,难道不是极具历史的启迪吗?
二、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破产和它的代表人物的心迹
和上一个“世纪之交”相比,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西方文化中心论”的衰弱以致于破产。表现这种变化的典型作品是发表在美国《外交》季刊1993年夏季号的哈佛大学教授塞缪斯·亨廷顿的文章:《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引起世界舆论的批评,亨氏又在《纽约时报》撰文回应,进一步表明了他的立场和心迹。
亨廷顿预言,冷战结束以后,代替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的,将是文化差异。他预言,未来的格局是西方与非西方的对立。亨廷顿说,“过去五年来世局不变,冷战模式已成为历史。我们无疑需要一套新模式,以便把世界政治整理出一个头绪,研判它的发展方向”。亨廷顿看到了“今天世界上充满各式各样的极权主义、民族主义、社团主义、市场共产主义,个个都生气蓬勃”,他看到了非西方国家的经济成就“助长文化自信”,“东亚和东南亚国家都对自己的文明愈来愈自觉,而且倾向于把经济成就归功于独特的传统和制度”。亨廷顿批评说,“冷战结束时,西方把事实过于简单化与自命不凡的表态,以及目前西文价值观耀武扬威的姿态,都令东亚和东南亚感到不平”。亨廷顿敏感地看到“中文已取代英文成为香港的地言语言”,等等。于是,亨廷顿警告西方政府,儒教和伊斯兰教将联手起来对抗西方世界,成为西方世界的极大的威胁。
亨廷顿的文章以及由此引出的全球性的关注,生动地说明了,西方中心论已经衰微,而他们的代表人士正在极力设法挽救已经失控的局势。
西风已经凋零,是不是东风已够强劲,必须压倒西风呢?这是一个需要反思问题。
三、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上一个“世纪之交”没有作完而留下来的课题
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是走向不是走到)和传统文化走出中世纪实质上是一个含义。这个起点,应该追溯到17世纪。发生于17世纪的反道学思潮,可以看到中国人文主义启蒙的表现。可惜,这个起步太艰难了,历史充满了曲折复杂。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这个早已起步的步履反而模糊起来。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化”和“西方”重叠了起来,而“传统文化”则被作为孔教的代表而与西化相对抗。胡适提出,只有一心一意的西化,才能打破文化折衷论。陈独秀也认为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的余地。倒是曾经是改良派的梁启超,他从欧洲回来以后,提高了认识,说出了比之陈、胡高明得多的见解来。
梁启超说:“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合起来成一种新的文明”。对于传统文化,他又说,要“语长道短”。“语其长则爱国之言也,道其短,则救时之言也”。(见梁启超:《欧洲心影录》)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今天还要讨论传统文化、现代化、西化的问题。这也是历史的曲折复杂所决定的。传统文化曾经被当作腐朽的封建主义文化而遭到惨烈的摧残,如今劫后余生,当然要加倍努力地抢救,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加上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哀弱,长期被压抑的对“国学”的热爱之情,高扬了起来,于是就有了对所谓“国学热”的批评。其尖锐程度提高到了“这是用‘国学’挤压马克思主义”的吓人的高度。马克思主义难道还怕“国学”的“挤压”吗?把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这本身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按照毛泽东的原则,马克思主义为了不变成教条,就要促进自身的“民族化”,这当然就包含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要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生长发展的土壤。
令人遗憾的是,和梁启超上述的论点相比,我们的长进似乎并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这也是很值得反思的。
四、传统文化·儒学·现代新儒学
传统文化是多元的。儒学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儒学、道学以及中国化了的佛学为主要思想资源,共同铸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丰富多姿,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她来自于中华民族又培育了中华民族。但是,历史的发展是曲折复杂的,传统文化离开不了历史的影响,包括经济的、政治的各个方面的影响,有的是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对于传统文化也要采取分析的态度。如梁启超说的,既要语其长,也要道其短。
什么是传统?传统就是传而统之。“传”谓纵向,它是从古至今一直传下来的,这是其历史性。“统”谓横向,它是现在还在起着作用的,它和各个时代的“当代”社会血肉相连,这是其现实性。否则传统就没有生命了。历史是不断变化的,传统文化也随之不断变化,有淘汰、有吸收、有改造,有发展,是之谓“变则通”也。
儒学的发展也是多元的。“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加上子夏、曾子,成了十家。后来的荀子,批评子张、子夏、子游为“贱儒”,对子思、孟子更是不客气。汉武帝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那个儒术,其实已混入了道家、法家和阴阳家的思想。就是汉宣帝所说的“王霸杂之”,那已经是一个政治文化的儒学了。
以孔子为代表的那一派儒家,是注重“人”的。特别讲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做人的道理。但这和从“神”那里解救出“人”来的“人文主义”不一样,他虽然实质上把“人”看得比“神”重要,但却把“人”编织在宗法社会的网上,每个人都成为这张“统一”的大网中的一个结子。每一个结子都有其固有的位置,不得越出,叫做“思不出其位”。“结子”与“结子”之间,有千丝万缕互相捆绑着,叫你不能动弹,叫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在这里,作为独立的个人,是没有的。只有关系中的人。这种关系是宗法社会的关系。讨论儒家,不管怎样分析,这一点本质属性,恐怕是难于否认的。
从儒家的这个本质属性来说,这个“传统”,确实是中华民族沉重的包袱。直到现在,我们仍然处处可以遇到它的幽灵。
但是,历史确实丰富而复杂,儒家在讲究人际关系和做人的道理的过程中,都确实提出了许许多多精彩的思想。特别是当西方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日益暴露出它的弊病来以后,儒学的思想和精神,就更加受到欢迎了。现代新儒学也因此而更加活跃。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讲座教授刘述先先生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说:“一百年前,韦伯想要解决的问题是,找出为何在儒家文化的笼罩之下,无法产生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的合理的解释。现在的问题完全倒转了过来,学者想要明白的是,亚洲究竟怎样走上它自己的现代化的道路,无须重蹈西方的覆辙”。这位教授说,“到目前为止,学者还未能建立儒家文化与当前亚洲国家经济发展之间的确定因果关系,但也很难否认二者之间有某种关系性”。
我们应该怎样来认识这些问题呢?除了有区域的差别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个“时间差”的问题呢?当西方资本主义受尽“现代化”的苦楚,要从“现代化的苦难”中解放出来的时候,我们正在为实现现代化而努力奋斗。我们当然没有错,也许西方的这些思想家也没有错。这也是需要反思的。
五、走向整合的世界
亨廷顿从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局势的变化,想到了文明的冲突。世界许多知名的学者,反对亨廷顿的理论,认为这种“冲突”不会成为主流。相反,世界的总趋势,将是文明的互补、世界的整合。科学技术的发展,确实使地球变得小了,文化的交流,资源的转输,人才的流动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世界的前景是乐观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促进了这种趋势更加明朗。邓小平提出,冷战结束以后,世界的主流是和平与发展,大大地加强了人们对世界前景的信心。当然,世界整合的必然趋势,并没有消除在这个过程中间充满着的矛盾和对立,包括某种条件下可能发生的严重的矛盾和对立。我们怎样来对待和处理这种世界局势呢?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面貌和心态加入这个世界的格局呢?总结两个“世纪之交”的经验,我们应该克服哪些短处,应该发扬哪些长处,应该改造哪些弊端,应该创造什么样的文化素质呢?这是最需要反思的。
注释:
[1]见夏衍《一个过来人的回忆与反思》载1989年第6期《新华文摘》。
标签:亨廷顿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世纪之交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国学论文; 梁启超论文; 现代化论文; 传统文化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