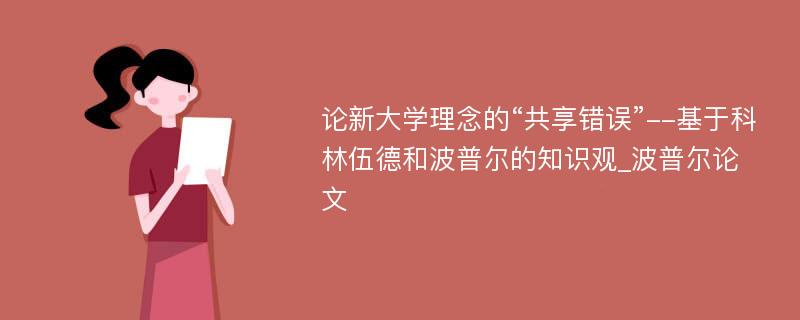
论新型大学理念“分享错误”——基于柯林伍德、波普尔的知识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伍德论文,理念论文,错误论文,知识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中国人的百年梦想。20世纪90年代出台的“211工程”、“985工程”,标志着我国揭开了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序幕。2006年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第四会议室面对6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说:“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①的确,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意味着大学不断涌现出大师级的人物。那么,大学究竟该如何培养大师级人才呢?其需要何种环境呢?“如果你想要知道你要去哪儿,历史帮助你了解你曾去过哪儿。”②本文沿着大学理念的历史发展脉络,阐述为什么德国大学在19世纪乃至20世纪前30年能保持世界领先地位,以及为何美国大学何以能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世界科学研究的中心。
虽然西方大学理念颇能解释其何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但本文认为,西方众多学者阐述的大学理念,并未基于柯林伍德(R.G.Collingwood)、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新型知识论阐述大学理念,因而其还不够完整。本文基于准波普尔知识概念,③结合大学物理学科发展的具体案例,提出新型大学理念“分享错误”,即在学科共同体内,学科领袖的权威不在于其是否犯错,而在于能否不断提出新颖的错误假设并与团队分享,从而激发团队的思考。大师意味其所提的“新颖的错误假设”是世界一流的,其也必然鼓励学生挑战权威,因其只是善于提出错误的假设而非必然是真理。
一、世界一流大学的创建首先是理念领先
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象征西方文明的科学中心像传递火炬一样在不同的国家交替出现。16世纪的意大利是世界的科学中心,至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科学中心遂迁至英伦三岛。法国在18世纪晚期以及19世纪早期引领世界科学的发展。随后一百年的时间里,即从1830年至1930年间,德国大学成为世界科学发展的王国。④20世纪30年代伊始,美国成为世界科学发展的中心。美国在某些应用科学领域的研究,早在1900年就与英国、法国和德国达到同等水平,但美国科学成就达到杰出的高度花费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大约在1815年到1930年之间。问题在于,德国大学为何能在19世纪一枝独秀,并引领20世纪前30年的发展?为何美国大学能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成为世界科学中心?原因众多,其中与大学理念的发展密切联系。
德国科学的兴起与威廉·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大学理念密切相关。洪堡在1809年至1810年任普鲁士内政部文化教育司司长期间组建柏林大学,一方面继承中世纪大学的教育理念,即大学是学者的社团,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和学术自由;⑤另一方面,他将科学研究职能引入大学,“立身的根本原则是,在最深入、最广泛的意义上培植科学,并使之服务于全民族的精神和道德教育。”⑥但洪堡所指的科学是纯科学,“高等教育学术机构倘要实现目标,其全体成员(只要可能的话)就必须服膺于纯科学的观念。”⑦须知,19世纪以前的大学被称为“教学型大学”(Teaching University),所以说洪堡在19世纪初期倡导教学、科研相统一的大学理念领先于世界各国。19世纪中叶,英国著名神学家、文学家、教育家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在《大学的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中甚至还坚持教学是大学的唯一职能,颇显得不合时宜。⑧
至于美国,殖民地时期至19世纪60年代,科学研究并未成为美国大学的基本职能。19世纪早期,美国高等教育界培养的主要是牧师,所以处于支配地位的是神学、古典文学和道德哲学等学科,许多未来的科学家最先从事医学方面的学习。美国内战之后十年间,包括业余爱好者在内的科学人员共约2000人。其中约500人是严谨的研究者。⑨时至19世纪60年代,私立院校才正式将植物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和物理学引入课程中来。⑩可以说,1876年美国创立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前,其大学基本属于教学型大学。整个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不是一个从事研究的地方,而是传授普通知识的场所。由此可见,美国大学在纯研究方面落后于德国大学,原因之一在于大学理念落后。
另一方面,美国公立大学将服务职能引入大学,从而拓展了大学的职能。美国于1862年制定的《莫里尔法案》(Morril's Act),改变了美国传统大学的职能,使得美国公立高等教育由单一教学向教学和公共服务转型。20世纪初,《莫里尔法案》所倡导的实用主义被威斯康星大学校长范·海斯(Charles Richard Van Hise)进行充分的实践。在他看来,“教学、科研和服务都是大学的主要职能。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所州立大学,它必须考虑每一项社会职能的实际价值,换句话说,它的教学、科研和服务都应当考虑州的实际需要。”(11)显然,《莫里尔法案》的出台是与美国传统实用主义哲学相联系的,它对美国大学物质科学学科的发展具有双重影响。从消极的意义上讲,实用主义哲学使得美国科学严重依赖于欧洲的理论成就;从积极的意义上讲,美国大学实验科学始终较为繁荣,而实用科学的繁荣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反之经济的发展为滋养教育和基础研究提供动力。一战结束之后,美国各个慈善基金会认识到纯研究对于美国军事、工业发展的重要性,开始为大学提供丰厚的科研经费和博士后奖学金。而德国研究型大学基础研究占绝对主导地位,以至于足以伤害实用的发展,从而陷入科研经费短缺的困境。及至20世纪30年代初期,美国大学在20年代弥补了纯研究方面的短板之后,结合传统实验科学的优势,创建了新型的“大科学”(Big Science)学科组织,从而一举成为世界科学的研究中心。(12)
20世纪各国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众多学者对大学理念做出了阐述,比如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的《大学之理念》(Idea of the University,1923)、奥尔特加(Ortega Y.Gasset)的《大学的使命》(Mission of the University,1930)、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的《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Universities:American,English,German,1930)、赫钦斯(Robert M.Hutchins)的《理想的大学》(The University of Utopia,1936)和科尔(Clark Kerr)的《大学的功用》(Uses of the University,1963)等,其哲学基础可归纳为“认识论”和“政治论”两种。(13)然而,上述论著未能回答,在遵从学术自由、学术自治的背景下,为什么有的学科带头人能带领学科团队一道开拓知识的疆土,而有的学科带头人却只是一枝独秀,后继乏人?本文认为,上述众多学者的大学理念主要是恪守传统知识概念的内涵,即知识是经过辩护的真信念(Justified True Belief),(14)而未能从新的知识论如柯林伍德、波普尔的知识论,丰富大学理念的内涵。
二、从柯林伍德、波普尔的知识观理解新型大学理念:“分享错误”
从柏拉图(Plato)开始,包括康德(Immanuel Kant)在内的西方传统知识论把知识界定为:知识是经过辩护的真信念,其特征是以命题的方式陈述的。西方哲学界最先对传统知识的“命题逻辑”(propositional logic)全面提出质疑的是英国学者柯林伍德。柯氏首次提出新的知识概念:“知识不仅包括‘命题’、‘陈述’、‘判断’,或逻辑学家用来指明有关思想陈述规则的任何名称,而且还包括陈述、命题等所意欲回答的问题。”(15)柯氏认为,只有当命题对问题做出回答时,命题才表现出矛盾或真假的特性,由此柯氏提出了“问答逻辑”(logic of question and answer):每一个命题都回答一个与自身严格相关的问题,即问题和答案之间是严格相关的。(16)柯林伍德的“问答逻辑”指出了知识概念本身包含问题,并非单纯由命题构成。“问答逻辑”虽然影响了一代大师迦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的诠释学,(17)但其对知识论方面的贡献迄今为止仍被冷落。
对传统知识论作出最深刻批判的代表人物要数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他从解决休谟的归纳法问题,提出了知识是一种猜想、假设,和传统的知识论“本质主义”倾向分道扬镳。他系统地论述了知识的一般理论,“知识的增长是借助于猜想与反驳,从老问题到新问题的发展:‘…P1——TT——EE——P2…’”。(18)问题(P1)引起人们试图用尝试性理论(TT)解决它,而且这尝试性的理论必须经过排除错误(EE)的批判过程。波普尔甚至认为,动物甚至植物也用竞争的尝试性解决和消除错误的方法来解决它们的问题。(19)基于上述柯林伍德对知识的理解,可以认为知识是由“P1——TT——EE——”构成的,意思是说“问答逻辑”由“问题以及提出解决该问题的经过辩护的假设”构成。但“问答逻辑”还不足以表达出波普尔对知识的全部理解,知识的增长显然还包括另外一部分“答问逻辑”即“…P1”,即“问题以及支持问题为真的理由”构成另一种类型的知识。于是,波普尔关于知识的一般理论可以解读为知识的进步是通过“答问逻辑”和“问答逻辑”交替作用,从而推动知识的发展。基于两类基本知识“问答逻辑”和“答问逻辑”,“准”波普尔知识概念可定义为:“知识是围绕问题提出的经过辩护的假设。”(20)
准波普尔知识概念不仅认同柯林伍德将问题纳入到知识概念之中,而且还认为提出问题并能论证其为真,本身就可能是一种知识。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认为,“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的或实验上的技巧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21)在准波普尔知识概念看来,爱因斯坦是在强调“答问逻辑”这类知识。而且,科学家在创造“答问逻辑”和“问答逻辑”之时,均是通过“试错法”。
作为促进人类进步的科学家,其实每天的研究工作就形式而言是非常之简单,即创造上述两类知识并加以检验,但其要以高深的学科知识为基础,并且往往每天都要制造出大量的错误假设。当然,科学家可以独自完成科学研究,无需他人参与;他也可以将其思考与人分享,任由同事、学生对之加以批评,发现错误,从而激发团队的思考。前者是“传道授业解惑型”教师,教给学生的都是真理——尽管也会犯错,通常能保证科学家个体自身的优秀;后者是“分享错误型”教师,(22)能带动整个团队的发展。在西方科学史上,就有两位风格迥异的天才式人物,分别是耶鲁大学的吉布斯(Josiah W.Gibbs),“传道授业解惑型”的典范,和哥本哈根学派的创始人尼耳斯·玻尔(Niels Bohr),“分享错误型”的典范。“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23)然而,大师的存在只是暂时保持了该学科的领先地位,不一定具有可持续性。因为作为美国大学19世纪末唯一的理论物理学大师吉布斯,其学生在理论物理方面毫无建树,而玻尔的学生却引领量子理论前沿的发展。
吉布斯是19世纪后半叶美国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他写的文章迄今为止尚未被发现有任何错误。他于1871年被任命为耶鲁大学无薪理论物理学教授,此后近十年做出了被大物理学家麦克斯韦(James C.Maxwel)认可的重要成就。但直到1879年,吉布斯收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吉尔曼(Daniel C.Gilman)的邀请后,耶鲁大学才认识到他的价值,开始给他发薪水。(24)更令人惊讶的是,吉布斯作为美国19世纪末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其学生均为实验物理学家。其原因,既有耶鲁大学校长及行政人员对其不够重视,也有吉布斯本身个性的缘故。
吉布斯拥有天才的思考力,但他性格孤僻,“他从来不愿花费一点力气宣传他自己的工作;他对于能够解决自己脑海中所存在的问题便感到满足,一个问题解决之后,接着他又着手思考另一个问题,而从来不愿想一想别人是否了解他究竟做了些什么。”兼之,“他的论文很难看懂,他很少接引范例帮助说明他的论证。他所导出的定律的含义时常留给读者自己推敲。”(25)在培养学生方面,过着离群索居生活的吉布斯只带了几位研究生,尽管当学生向他请教之时,他颇为热心地讲解他的观点,学生亦颇受启发。但吉布斯从来都不邀请学生参与其研究,他向学生展示的学术成果都是“成品”而不是半成品。(26)因而没有学生了解他的思考过程,无法了解他是如何试错的,以及从哪些错误的假设中得到启发。缺失了这笔财富,耶鲁大学即使拥有吉布斯这位物理学巨擘,仍旧无法培养出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更无法形成理论物理学的中心。吉布斯显然没有认识到,学生如何尽可能地掌握学科前沿存在的错误假设,是导师非常重要的责任。
吉布斯的不合群还体现在他不愿意与同行打交道。1899年5月20号,美国物理学会在纽约召开了第一届会议,习惯于同各个组织保持距离的吉布斯谢绝参与。(27)1903年吉布斯去世之后,美国大学理论物理学的发展更是雪上加霜,原因在于他并没有留下一个富有创造力的理论小组。然而偏偏在20世纪初,理论物理占据学科发展的中心地位。回顾19世纪美国物理学科的发展,以及20世纪初美国大学为缺乏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和物理学中心发愁,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如吉布斯更加合群一些,愿与学生、同行“分享错误”,理论物理学或许已经于19世纪末在美国大学扎下了根。
与吉布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哥本哈根精神领袖尼耳斯·玻尔。1921年玻尔在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创立理论物理研究所,很快成为量子理论研究的发源地。据统计,20世纪20年代到玻尔研究所工作一个月以上的学者共63人,来自17个国家,其中10位先后获得诺贝尔奖。(28)之所以有如此多的年轻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这与研究所独特的“哥本哈根精神”是密切联系的。物理学家雷昂·罗森菲尔德曾经作为玻尔的助手,将哥本哈根精神归纳为“一种在判断和讨论方面有着完全自由的最卓越的精神。”(29)
哥本哈根精神显然回答了这一问题:“怎样使一个集体在讨论问题中能相互启发、相互激励,从而使集体远胜于一个个不接触别人的简单总和。”(30)但如果将“哥本哈根精神”理解为“平等、自由地讨论和相互紧密合作的浓厚的学术气氛”;或者是,“高度的智力活动、大胆的涉险精神、深奥的研究内容与快活的乐天主义的混合物”,(31)本文认为,这种表达并没有发现哥本哈根精神的第一推动力,那就是作为学派领袖玻尔,除了具有卓越的高智商之外,更重要的是他愿意与同事、学生“分享错误”,或者说是他习惯于“出声地思考”。
就其研究风格而言,玻尔一生大部分时间内,都是通过和别人讨论来学习新科学的,阅读还在其次。(32)玻尔的学生内维尔·莫特受到了其研究风格的触动:“当(玻尔)有一个新想法时……他就到研究所中来,并把他的想法告诉他所能找到的第一个人……人们的一半工作就是讨论。”(33)有一个小故事很好地证明了玻尔善于“分享错误”,也善于承认错误。有一次玻尔试图说服两个青年人相信他的一种观点。在长时间的讨论以后他没有成功,然后他就分别和他们谈话。当这样还不行时,他就很失望地问他们道:“难道你们连一点儿也不同意我的话吗?”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又回来告诉他们说他错了。(34)相似的,在玻尔撰写学术论文之时,他通常会起草一份初稿,接着马上就对它进行批判,于是无数的修饰和改正就盖满了纸面。但是突然间,这篇好不容易搞出来的整篇文章又会被作废。等到第二份稿子被撰写出来了,又对其进行同样的批判。(35)与吉布斯掩盖了整个研究过程不同,玻尔的过程均与研究人员共享。事实上,坦诚自身的错误,已经成为玻尔个性中最自然的一部分,即使他已经取得大师级地位之时。
玻尔显然知道过多地敞开思维过程,同行会发现他提出的错误假设并不总是具有启发意义。1961年5月,玻尔最后一次访问前苏联,当他在一次讨论会上作报告后,有人问他,为什么你能在自己周围聚集那么多具有创造性才能的青年物理学家?玻尔回答说:“可能因为,我从来不感到羞耻地向我的学生承认——我是傻瓜。”(36)由此可见,“分享错误型”教师的确需要勇气。与玻尔相类似的有美国氢弹之父泰勒(Edward Teller)。他进实验室都要问问题,每天至少提十个问题。但是往往有八九个问题是错的,而他的伟大创造就是在那一两个问题上。(37)与此同时,学生也在反驳泰勒的错误假设过程中得到启发,受到教育。总的说来,在科学史上,大多科学大师都乐于承认错误,比如钱学森导师冯·卡门(Theodore von Kármán)曾经向钱学森认错过,(38)但能像玻尔、泰勒等热衷于敞开思维过程,从对方的反馈之中获得灵感的科学家并不多。
三、结语
从吉布斯、尼耳斯·玻尔较为经典的案例分析可知,现代大学除了继承中世纪学术自由、学术自治的传统之外,承担教学、科研和服务的职能,以及拥有大师、优秀的学生和充足的科研经费之时,只能保证该大学暂时处于世界一流大学。若要持久保持世界一流的地位,大学理念还要倡导学科带头人具备“分享错误”的精神。学科带头人所提出错误假设的质量和数量,决定学科当前发展的水平。而他是否有兴趣与学生、同事分享错误,决定着大学学科未来的发展前景。当学科带头人将自己的思维封闭起来,不愿在成果出来之前向同事、学生开放,他们将失去一次非常重要的学习机会,而学科领导人也失去被批判的机会。缺乏这样的沟通,学科团队的成长将非常之缓慢。
从方法论的意义上讲,“分享错误”的大学理念与科学的基本方法“试错法”是一致的;从评价体系上讲,有人因提出了错误但新颖的假设而获得教授职称,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量子理论的发展史。自1913年玻尔提出旧量子论至1925年底量子力学的建构,物理学家经过十多年的探索,走了不少弯路。但众多物理学家凭借错误的量子论文成为量子理论的重要人物,且均未因发表了被最终证明是错误的文章而被剥夺教授席位,因为科学本身就是看谁能提出更有新意但可能错误的假设,并不一定要求是终极真理。如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汤川秀树(Hideki Yukawa)所说:“当回顾理论物理学的历史时,我们说得过分一些几乎可以称之为错误史。在许多科学家想出的所有理论中,大多数是错误的,因而没有生存下来……但是,没有少数成功背后的许多失败,知识就几乎不可能有任何的进步。”(39)可见参与创造错误假设的能力并发表一系列相应的成果,是科学能力的体现,这就要求科学政策做出调整,即科研管理部门必须认识到科学研究是试错的过程,允许课题研究失败,但要求科研人员与同行分享错误,而不是因为害怕此次课题研究失败而影响到下一次申请,进而篡改数据,做出貌似成功的研究。就当前中国大中小学的教育实践而言,教师权威的建立是基于教师是真理的化身,而未认识到提出新颖而错误的假设本身就是一种创新。我国在21世纪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需要实践新型大学理念“分享错误”,即学科带头人得完成从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教师向“分享错误型”教师的转型。(40)
注释:
①http://news.sina.com.cn/o/2006-11-28/045110614012s.shtml,2006-11-28.
②〔美〕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9页。
③(20)周志发:《教学案例“新解”与“新课改”评估体系的改良——基于柯林武德、波普尔的知识论》,《教育科学》2007年第2期。
④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页。
⑤刘宝存:《大学理念的传统与变革》,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4页。
⑥⑦〔德〕威廉·冯·洪堡:《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和外部组织》,陈洪捷译,《高等教育论坛》1987年第1期。
⑧〔英〕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想》,徐辉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
⑨(24)Daniel J.Kevles,The Physicists:The History of a Scientific Community in Modern America,Vintage Books,New York,1978,p.3,pp.32-34.
⑩Alexandra Oleson and Sanborn C.Brown(ed.),The Pursuit of Knowledge in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American Learned and Scientific Societies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Civil War,Baltimore,1976,pp.38-39.
(11)康健:《“威斯康星思想”与当今高等教育改革》,《外国教育》1988年第4期。
(12)周志发、孔令帅:《美国大学从“地方性”走向“世界一流”的发展历程(1876-1950)——从物理学科发展的视角》,《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9年第1期。
(13)〔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3页。
(14)Edmund L.Gettier,Is Justified True Belief knowledge? Analysis,Vol.23,1963,pp.121-123.
(15)(16)〔英〕柯林武德:《柯林武德自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3、33-35页。
(17)〔德〕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薛华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39-42页。
(18)(19)〔英〕卡尔·波普尔:《客观的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舒炜光等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260、148页。
(21)〔美〕爱因斯坦、英费尔德:《物理学的进化》,周肇威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2年,第66页。
(22)(40)周志发、林斌:《重建教师概念:“分享错误型”教师》,《学术界》2010年第3期。
(23)黄延复、刘述理:《梅贻琦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0页。
(25)赵蕊愚、肖良质:《不求闻达、唯求真知的一生——美国物理学家吉布斯传略》,《自然杂志》1985年第6期。
(26)Lynde Phelps Wheeler,Josiah Willard Gibbs:The History of a Great Mind,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2,pp.46-106.
(27)Frederick Bedell,What Led to the Founding of the 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Phys.Rev.Vol.75,1949,pp.1601-1604.
(28)〔丹〕罗伯森:《玻尔研究所的早年岁月(1921-1930)》,杨福家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57-159页。
(29)(35)〔比〕罗森菲尔德:《量子革命——雷昂·罗森菲尔德文选》,戈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88-89、90页。
(30)龚放:《从思维发展视角求解“钱学森之问”》,《教育研究》2009年第12期。
(31)杨福家:《哥本哈根精神》,夏中义编:《大学人文读本:人与世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24-225页。
(32)(33)(34)〔美〕阿布拉罕·派斯:《尼尔斯·玻尔传》,戈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59、513、69页。
(36)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编:《成功与失败:科学人物评传》,北京: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1980年,第79-80页。
(37)杨福家:《大学的使命与文化内涵》,《现代教育论丛》2008年第2期。
(38)叶永烈:《走进钱学森》,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页。
(39)〔日〕汤川秀树:《创造力与直觉:一个物理学家对东西方的考察》,周林东译,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第54-55页。
标签:波普尔论文; 玻尔论文; 大学论文; 逻辑错误论文; 物理学家论文; 美利坚大学论文; 理论物理论文; 科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