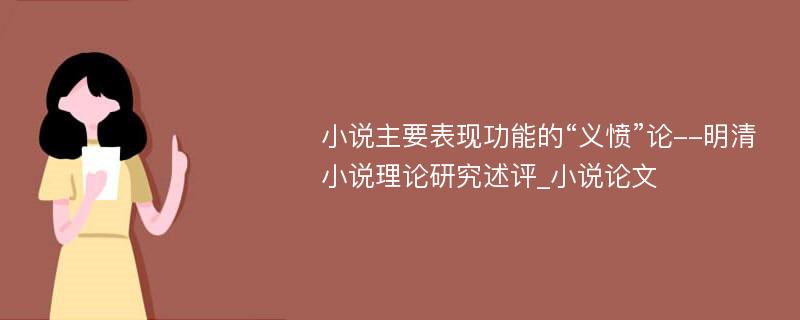
“发愤”说论小说的主体表现功能——明清小说理论研究札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愤论文,小说论文,札记论文,理论研究论文,明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一个美学命题,“发愤”说是明清小说作家和批评家对小说功能的一种美学认识和概括。“发愤”说揭示了古代小说作家对社会生活的共同感受,揭示了小说作家普遍的卑微不幸的命运,强调了小说的社会批判和政治批判意义,肯定了小说的巨大价值和功用,囿于篇幅,本文所讨论的仅限于其主体表现功能这一范围。
小说“发愤”的观念,在明初已用之于小说批评。瞿佑以小说“哀穷悼屈”[①],李昌祺也以小说“豁怀抱,宣郁闷”[②],刘敬肯定小说“特以泄暂尔之愤懑”[③]。而自从李贽全面阐发小说为“发愤之作”[④]以后,更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小说批评,如“酉阳野史”讲“泄万世苍生之大愤[⑤],“雉衡山人”讲小说“以抒其不平之鸣”[⑥],金圣叹讲“怨毒著书”[⑦],陈忱讲“泄愤之书”[⑧],张竹坡讲“悲愤鸣唈而作秽言,以泄其愤”[⑨],蒲松龄讲“孤愤之书”[⑩]等等。可以说,“发愤”精神一直是明清两代相当部分小说作家和批评家的准则,成为中国古代小说美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当晚清的批评家在总结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经验时,把“发愤”看成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特征。如王钟麟在《中国历代小说史论》中认为,象《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中国历代小说名著的创作,都是因为“士不得志于时,而能文章者,乃著小说,以抒其愤。”
小说创作作为一种人类至高心灵的活动,如果从创作发生学的角度回答“为什么创作”这一问题时,明清小说作家和批评家的回答并不一致。“补史”论者认为是为了羽翼正史、垂戒后世;“惩劝”论者认为是为了维持纲常名教、劝善惩恶;“游戏”论者认为是为了消闲遣兴、自娱娱人。而“发愤”论者则认为小说的创作是为了“发抒愤懑”,较之其他功能论,它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从创作主体的创作动机和创作目的两个方面肯定了小说的主体表现功能。
“发愤”说从创作发生学的角度阐示了小说创作主体的心理状态
“动机,这是与满足某种需要有关的活动动力。”[(11)]现代心理学有一个概念叫“缺乏性动机,”是指基于人在生存中的某种缺乏或痛苦而产生的动机,它以一种要求重新取得平衡的内驱力而起作用,以降低、缓解以至消除这种缺乏或痛苦。而在文学创作中,则更多地是基于精神上的失衡和追求,而并非生理上的缺乏或肉体上的欲求。当作家承受欲望与阻碍的冲突,心理处于噪动不宁的状态时,就会迫不得已通过创作达到一种平衡和宁静。所谓“郁结不通,而寄思于滑稽”。[(12)]这种创作主体内部的失衡状态还是创作活动的起点。
明清小说“发愤”论者一般把这种动因直接归结为外部环境作用于创作主体的心灵,而产生愤激。这个外部环境,可以是个体的“穷厄”的生活遭遇,就象周揖在《西湖二集·吴越王再出索江山》里所形容的瞿佑那样:“叵耐造化小儿,苍天眼瞎,偏锻炼得他一贫如洗、衣不成衣、食不成食,有一顿,没一顿。终日拿了这几本破书,‘诗云子曰,之乎者也’叫个不了,真个哭不得,笑不得,叫不得,跳不得”,因而只得写写小说,“把胸中欲哭、欲笑,欲叫,欲跳之意,尽数写将出来,满腹不平之气,郁郁无聊,借以消遣”;这个外部环境,也可以是李贽所说的“宋室不兢,冠屦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13)]的社会政治现实,由此而激起创作主体的愤懑,进而以创作《水浒传》泄其愤;这个外部环境更可以是陈忱所面临的王朝更迭,因而他借梁山泊起义英雄故事的“残局”,寄寓亡国之痛,写成泄愤之书《水浒后传》;这个外部环境还可以是张竹坡所断言的《金瓶梅》作者个人的重大冤仇,因而作者含酸忍辱,悲愤呜咽而作“秽言”以丑其仇,以泄其愤,等等。外部环境尽管不同,但都激起创作主体心理的激荡不平,导致创作主体心理的严重失衡,甚至激起巨大的痛苦。
李贽和张竹坡都描述过这种失衡、痛苦的心理状态:
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14)]
是吾既不能上告天子以申其隐,又不能下告士师以求其平,且不能得急切应手之荆、聂以济乃事,则吾将止于无可如何而己哉?……吐之不能,吞之不可,搔抓不得,悲号无益,……日酿一日,苍苍高天,茫茫碧海,吾何日而能忘也哉?……是愤己百二十分,酸又百二十分,不作《金瓶梅》,又何以消遣哉?[(15)]
这样一种伴随着生理反应的剧烈心理煎熬,强烈地激荡着、折磨着创作主体的心灵,促使着创作主体去寻找发泄这种痛苦的途径,而小说创作正是这种有效的途径。
要之,从创作冲动的发生性质来看,“发愤”说强调由外部环境的刺激而引发,这与作家的生活经历以及对社会人生的认识有很大关系;从创作冲动的形成来看,“发愤”说强调这种冲动是渐次形成的,它有一个情感的不断积累的过程,“日酿一日”、“蓄极积久”。长期的积蓄而渐至紧张状态,一旦趋于爆发的临界点,则“势不能遏”;从创作冲动的爆发方式来看,“发愤”说强调其触发机制,“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16)]于是创作就发生了,遂以旁托假借的方式,“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17)],借小说来诉说心中的不平,发泄一腔的悲愤。“发愤”说对创作发生的心理状态的描述,为文学创作心理学的研究提供了生动的素材。
“发愤”说从主体的创作目的出发,阐发了小说创作的泄导补偿作用
补偿原是心理分析学的一个概念。弗洛伊德认为,“本我”在“自我”的引导下,有可能找到既能补偿“本我”的欲望,又能突破“超我”压抑的道路,这就是补偿和升华。当人的欲望在现实生活中受到阻碍压抑之后,便郁积心中形成一种心理能量,要求寻找一个社会上可以接受的目标去替代一个不能直接满足的目标,寻找一个可以得到发泄的途径,从而减轻压力,消解痛苦,获得一种替代满足。而艺术创作恰好就是一种补偿升华的方式,恰好可以满足这种心理需求。“借着幻想来满足自己的希望、祈求,艺术即是一种典型的代表。”[(18)]如果剔除其中泛性论的成份,弗洛伊德的补偿升华说在相当程度上说明了文学创作的这种泄导补偿作用,不但早就有所认识,而且作了较充分的说明和强调。
陈忱在《水浒后传论略》中说:
《后传》为泄愤之书:愤宋江之忠义,而见鸩于奸党,故复聚余人,而救驾立功,开基创业;愤六贼之误国,而加之以流贬诛戮;愤诸贵幸之全身远害,而特表草野孤匠,重围冒险,愤官宦之嚼民饱壑,而故使其倾倒官囊,倍偿民利;愤释道之淫奢诳诞,而有万庆寺之烧,还道村之斩也。
作者对现实的政治、社会有太多太强烈的愤慨,而又无法去改变,于是借小说制造出一个丰富的幻想世界为来使自己得到心理的补偿。这里所指的是《水浒后传》的情节:李俊等重新聚义,称王暹罗;六贼流贬诛戮;燕青等冒险入重围朝见徽宗;众英雄散尽嚼民饱壑的官宦之钱财;李应火烧万庆寺,呼延灼斩杀妖道郭京等。这些情节正是针对作者心中之愤而有意为之的补偿性描写。
对于众多历阅坎坷,饱经忧患的小说作家来说,现实人生是如此无可奈何,迫不得已将自己原本准备用于治平大业的才志,移之于小说的创作,借以泄导幽愤和痛苦。李昌祺谈到自己的创作时说:
余两涉忧患,饱食之日少。且性不好博奕,非藉楮墨吟弄,则何以豁怀抱,宣郁闷乎?虽知其近于滑稽谐谑,而不遑卹者,亦犹疾痛之不免于呻吟耳,庸何讳哉?[(19)]
颇有殉此不悔之味道。李昌祺的话已说得再坦白不过了,他写小说的动机并不高尚,实际上也无须高尚,因为截至李昌祺为止小说的地位就未曾高尚过。因而在他看来,小说只不过与“博奕”之类的游戏近似,其目的是消闲自遣,泄导幽愤而已,就象“疾痛之不免于呻吟”一样,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治病疗疾,却可以缓解、减弱和转移一些痛苦。这个比喻很精彩,形象地说明了小说创作对于主体的泄导补偿作用。
命运偃蹇的小说作家,由于人生理想、人生追求与现实社会的剧烈冲突,而发生强烈的心理倾斜,“发愤”之作的小说,作为主体的情感的泄导,既是作家心理能量的释放,又是作家与读者进行情感交流的最有效渠道。通过小说“发愤”,一方面作为自我解脱的心理补偿,消解作家心头的郁积,另一方面则求得世人与后人的理解和同情。这是久历人世沧桑的作家获得心理平衡、心理补偿的两个不同的侧面。张竹坡在论述“泄愤”时,就突出地强调了“泄愤”和“后遇知心”这两方面的作用。他说:“盖作者必于世亦有大不得已之事,如史公之下蚕宝,孙子之刖双足,乃一腔愤懑,而作此书,言身已辱矣,惟存此牢骚不平之言于世,以为后有知心,当悲我之辱身屈志,而负才沦落于污泥也。”[(20)]在张竹坡看来,作者创作《金瓶梅》,除了发泄一腔愤懑外,另一个重要目的即是求取后世来者的理解和同情。这也是一种心理补偿形式。只不过是一种预约式的补偿、期待性的补偿罢了。
“发愤”说肯定小说创作对于实现创作主体的人生价值的意义
创作小说以发愤,还可以作为一种人生追求,以实现创作主体的人生价值。这当然也是一种心理平衡和调节和补偿方式,不过,不是李昌祺式的那种消极的释放,而是一种人生的积极追求。
明清小说“发愤”论者虽然并不很看重小说在人生追求中的位置,但是,毕竟还是把创作出成功的小说作品看成是实现人生价值的一条重要途径。现实人生是痛苦和不幸的,于是寄希望于通过小说的不朽来追求人生的不朽,用身后之名来证实人生存在的价值,也就成了这些在人生苦海中挣扎者的精神追求。“天花藏主人”在《天花藏合刻七才子书序》中分析了封建社会中有“才情”之士的出处臧否,其中大部分人“徒以贫而在下,无一人知己之怜,不幸憔悴以死,抱九原埋没之痛,岂不悲哉?”当其“欲人致其身,而既不能,欲自短其气,而又不忍”的时候,就“不得已而借乌有先生以发泄黄梁事业。”说是无可奈何也罢,是自我安慰也罢,当作家处于到处碰壁,走投无路的境地下,这种借小说发泄“黄梁事业”,不也是他们实现自己人生价值和人生理想的积极追求吗?因而,凡“胸中之欲歌欲哭”之苦痛,到了作品之中便成了“可喜可惊”[(21)]之欣愉。试以“天花藏主人”为例,仅就我们现在能见到的以“天花藏主人”署名编撰和作序的才子佳人小说就有十六部之多。他生于明清异代之际,怀才不遇,转而倾其全力从事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并从理论上对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实践加以总结。他的某种永恒的人生价值不正是凭藉着这些小说作品的流传而到了某种程度的实现了吗?蒲松龄写作《聊斋志异》,从素材的搜集到创作修改,前后数十年,数易其稿。徐珂说蒲松龄“因目击国初乱离时事,官玩民偷,风漓俗靡,思欲假借狐鬼,纂成一书,以抒孤愤而谂识者,则词章经济志节皆与之俱传矣。每当授徒乡间,长昼多暇,独舒蒲席于大树下,左茗右烟,手握葵扇,偃蹇终日。遇行客渔樵,必遮邀茗烟,谈谑间作,虽床第鄙亵之语,市井荒伧之言,亦倾听无倦容。……晚归篝灯,组织听闻,或合数人之话言为一事,或合数事之曲折为一传,但冀首尾完具,以悦观听。其文非一朝所猝办,其事亦非一日所网罗。历二十年,稿三数易,始得此高不盈寸之著作。”[(22)]的确,尤其是在经历了长期科举失意的痛楚之后,蒲松龄直面人生,借狐鬼以言志抒愤,把《聊斋志异》的创作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积极追求,凭着“遄飞逸兴,狂固难辞;永托旷怀,疾且不讳”的执着,置“少赢多病”、“长命不犹”而不顾,在“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如水”的艰难条件下,坚持创作,终于“集腋为裘”,“成孤愤之书”,并执着地认定“在青林墨塞间”,[(23)]自有其知己者,坚信自己的心血结晶,终将赢得社会认可,坚信自己的人生追求和人生价值终将得到应有的报偿。
这里需要指出两点。第一,同样把创作发愤之作的小说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追求,不同的作家存在境界之别。比如才子佳人小说作者往往寄情于红粉佳人,把理想的实现建立在科场高中,皇帝赐婚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上;而蒲松龄则求知已于“青林黑塞间”,把理想的实现寄托在鬼狐世界。前者是对现实的虚幻空想,后者则在冷峻的思索中表现出对现实的绝望。作品成就之高下,正见出各自的人生境界和思想境界之区别。第二,人生价值的追求在古人的价值取向中是有层次之分的。所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24)]立言的价值取向是低层次的。对于小说作家来说,虽可以获得某种人生价值的不朽,但对封建文人来,更是等而下之,迫不得已才干的事。所以方浚颐对蒲松龄竟以小说名而深感叹惋[(25)],就连吴敬梓的好友程晋芳也替小说家的吴敬梓悲哀。[(26)]相比之下,不能不使我们对明清小说“发愤”论者的这种人生价值的追求给予特别的关注和重视。
“发愤”说强调了小说的接受主体的心理泄导补偿作用
按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艺术本身就是一种补偿手段,作家的创作就是去寻找作满足他内在欲求的替代物。而艺术作品之所以有魅力,就在于接受者(包括读者和批评家)也有着和艺术家一样的苦闷,但他们不能制造出一个丰富的幻想世界使自己得到补偿。因此,文艺作品不但是对艺术家的补偿,同时又是一种社会性的治疗手段和一种使接受者摆脱苦闷的途径,接受者同样可以在阅读、欣赏和评论作品时象作者创作时那样,在作品中放纵自己,把他的幻想在小说世界的接受中去实现。“发愤”说在强调小说的补偿作用的同时,也注意到这一点。李贽讲“发愤”,在很大程度上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磊。怀林曾指出:“和尚一肚皮不合时宜,而独《水浒传》足以发抒其愤懑,故评之为尤详。”[(27)]李贽在阅读和批评《水浒传》时,与作品产生强烈共鸣,从而把自己的愤世骂世之情借评点时宣泄出来,得到精神上的快感,因而他自称:“《水浒传》批点得甚快活人”。张竹坡更是将他批书“发愤”,以消闷怀的动机说得十分明白:
迩来为穷愁所迫,炎凉所激,于难消遣时,恨不自撰一部世情书,以排遣闷怀,几欲下笔,而前后结构,甚费经营,乃搁笔曰:我且将他人炎凉之书,其所以经营者,细细算出,一者可以消我闷怀,二者算出古人之书,亦可算我今又经营一书,我虽未有所作,而我所以持往作书之法,不尽备于是乎?[(29)]
张竹坡借批书而发抒自己为穷愁所迫、炎凉所激的闷怀,并认为批书“可算我今又经营一书”,实际是对《金瓶梅》底蕴的一次再发现、再创造。现代阐释学认为,艺术解释活动就是主体参加的理解和体验活动,必然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是对艺术作品本文加以理解所不可缺少的“前结构”,正是由于有这个“前结构”听蕴含的主观性,作为解释活动的结果的“意义”,就不可能是纯然客观的,而一定会带有主体的“偏见”。因此,尽管我们可以肯定《金瓶梅》是一部具有强烈讽世骂世意义的现实主义杰作,但作者的创作目的是否就一定如张竹坡所说的那样是“发恨”,“泄愤”,甚至是作品中某个人物如孟玉楼来“自喻”,那就未必了。至于张竹坡这样认为,则是他借批书泄导幽愤、排遣郁怀而立说,因为在“发愤”论者看来,小说作品对接受者来说,本来就存在着这种泄导补偿作用。当然,象李汝珍所说的那样,阅读小说竟能产生“宿疾顿愈”[(30)]的神奇效用,则近乎神话了。
另外,一些“发愤”论者还将这种接受主体的泄导补偿作用扩大推演为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心理的补偿。如“酉阳野史”的“泄愤一时,取快千载”说,就是为了满足人们以蜀汉为正统的社会心理。其《续编三国志后传》可以是“百无一真”,可以是“诚所谓乌有先生之乌有者”,但却能收到“人悦而众艳”的艺术效果,因为其作品所泄之愤是“万世苍生之大愤”,符合并满足普遍感到缺憾的社会心理,是对人们对刘汉未能继大统而感到遗憾的一种社会心理的补偿,能“解颐世间一时之通畅,并豁人世之感怀君子”。所以,尽管作品是泄一时之愤,却可以“取快千载”。[(3①]
“发愤”说无视情感的理性原则强调情感的激烈和表现的充分
在“愤”的表现维度上,小说“发愤”论强调的是“势不能遏”的倾泄,很少有传统美学的那种吞吞吐吐式的“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也很少讲求“温柔敦厚、中正平和”,而是强调愤激的强度和表达的充分。儒家传统的美学原则,对于情感状态,首先提倡的是中正平和之情,但也为哀怨激愤留下了一点余地,这就是“变”。孔子讲“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在对诗的社会作用作了这一番内涵虽丰富但终不免简单模糊的界定以后,立刻以内涵和外延都十分明确的“迩之事父,远之事君”[(32)]对兴、观、群、怨加以概括和统摄。对于“怨愤”的这种质的规定性,一直为后世所遵从,即使是诗学领域里的“发愤著书”论也不例外。屈原讲“发愤以抒情”[(33)],司马迁则将其概括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34)]“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还是儒家诗教对感情表达上所要求的温柔敦厚,中庸平和的美学原则。过分为之淫,无度为之乱,这是儒家诗教原则所竭力排抵的。因此,虽然也给“怨愤”之类的变风变雅留下一点缝隙,但不能越出传统社会的理性轨道,长期以来,所谓“发愤著书”的诗学传统正是在这个缝隙中求生存的。
而小说“发愤”说,其总体精神是偏离政教的。尽管“发愤”说重视小说的社会功用和社会价值,而且不乏有人也讲“忠义”、“惩劝”,但更强调主体的表现,“忠义”等说法是一种保护性说法,为小说的合理生存提供“有力”的理论保护罢了。事实上没有人相信能寄希望于这些“专导人从恶”,专描写“奸邪淫盗之事”,“以杀人为好汉,以渔色为风流,丧心病狂”[(35)]的小说,以达到诗教目的。倒是“发愤”论者比较坦诚,前引瞿佑的“哀穷悼屈”,李昌祺的“豁怀抱,宣郁闷”,“雉衡山人”的“抒其不平”,均强调的是主体的幽愤的宣泄。“酉阳野史”将这种宣泄分为两个方面:从创作个体说,“无过消遣于长夜永昼,或解闷于烦剧忧愁,以豁一时之情怀”;从社会接受说,则“泄万世苍生之大愤”、“解颐世间一时之通畅,并豁人世之感怀君子”。张竹坡更是将《金瓶梅》纯看成是作者个人的“泄愤”、“发恨”、“复仇”。李贽稍有不同,他以“忠义”属之《水浒传》,而且极力肯定其巨大的社会政治作用,政治功利色彩较浓。但他将“啸聚水浒之强人”颂之以忠义,实为惊世骇俗之论,虽然他的“忠义”落脚点在于宋江的接受招安,但这较之小说中逼上梁山,揭杆造反的轰轰烈烈的生动逼真描写,显得极苍白,可谓讽百而劝一。故明清两代禁毁小说书目中,《水浒传》无不首当其冲。
正因为小说“发愤”说内在精神的这种反叛性,所以决定了它在对“愤”的情感表达上,强调“势不能遏”,强调愤激的强度,表现的充分。陈忱讲“愤”,列举“六愤”、“五愤”之多[(36)];张竹坡讲“愤已百二十分,酸又百二十分,……悲愤鸣浥而作秽言,以泄其愤”[(37)];金圣叹则讲“怨毒著书”,“冤苦设言”等等。既有单纯个人的“穷途有泪无可洒去”[(38)],更有对社会不平的激烈批判,就其激烈程度而言,是诗学领域的“怨愤”所不能比拟的。
李贽这样描述这种激情的酝酿、产生以致爆发的情形:
……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既已喷玉唾珠,昭回云汉,为章于天矣,遂亦自负,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39)]
这种长期积蓄的激情,在爆发时又加深固有的强烈维度,以致“发狂大叫,流涕痛哭,不能自止”,这是一种具有较强反叛性和艺术力度的激情,它可以使愤的对象“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这种激情难道还讲“怨而不怒”、“温柔敦厚”、“和平中正”吗?它无视传统社会理性的规范,也不讲动而中节,它强调的是反传统的愤激情绪的倾泄。相对于儒家美学的强调理性、强调中庸而言,它强调主体,呼唤“真我”、张扬个性,是一种“不必矫情,不必违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直心而动”[(40)]的率性真情,是主体意识觉醒的表现。这正是明中叶以后思想启蒙运动在小说批评领域的反映,它与小说戏曲领域里的以欲抗理、以情反理,诗文领域的“独抒性灵”等一起构成了明中叶以后的浪漫思潮。对于传统美学思想是反叛,也是挑战。
小说作为作家的主观创作,虽然从终极意义上讲是客观现实的产物,但它必然带有创作主体的主观情感色彩,带有一定的主体表现色彩。较之西方小说的以冷静的态度剖解人生,以精确的刻划再现生活的特点来说,中国小说更富于抒情写意的主体表现特色。但是中国古代小说批评对小说的这种主体表现功能长期缺乏应有的认识,大多将小说的功用仅限在其认识和教育功用方面。如史学本体论的“补史”、“史余”说,政教功利论的“惩恶劝善”、“裨益风教”说,狭隘认识论的“博闻多识”、“以资考证”说等等,莫不如此。“发愤”说的贡献就在于它在古代小说批评史上,第一次明确地肯定和强调了小说的主体表现性,这是小说功能的新发现,是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合逻辑的进步反映。
注释:
①瞿佑《剪灯新话自序》。
② (19)李昌祺《剪灯余话序》。
③刘敬《剪灯余话序》。
④ (13)李贽《忠义水浒传序》。
⑤ (31)酉阳野史《新刻续编三国志引》。
⑥雉衡山人《东西两晋演义序》。
⑦金圣叹《水浒传》十八回评。
⑧ (36)陈忱《水浒后传论略》。
⑨ (15) (29) (3⑦张竹坡《竹坡闲话》。
⑩ (23)蒲松龄《聊斋自志》。
(11)彼德罗夫斯基《普通心理学》。
(12)李维桢《广滑稽序》。
(14) (16) (17) (39)李贽《焚书·杂说》。
(18)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
(20)张竹坡《金瓶梅》第七回评。
(21)天花藏主人《天花藏合刻七才子书序》。
(22)徐珂《清稗类钞·著作类》“聊斋志异”条。
(24)《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25)方浚颐《梦园丛说·内篇》:“独怪留仙,有如许笔墨,乃不以诗古文辞传于世,仅托诸稗官小说家言,为鬼狐作南董,掩其沉博绝丽之才,而入于支离怪诞:此固大丈夫不得志于时者之所为也。吾为留仙痛己。”
(26)程晋芳《怀人诗》之十六:《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语传。”
(27)怀林《批评水浒传述语》。
(28)李势《续焚书·与焦弱侯》。
(30)李汝珍称友人“方抱幽忧之疾”,读《镜花缘》“而解颐,而喷饭,宿疾顿愈。”见《镜花缘》第一百回。
(32)《论语·阳货》。
(33)屈原《九章·惜诵》。
(34)《史记·屈原贾谊列传》。
(35)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载。
(38)张竹坡《金瓶梅寓意说》。
(40)李贽《焚书·为黄安二上人三首》“失言三首”。
标签:小说论文; 人生价值论文; 文学论文; 水浒传论文; 金瓶梅论文; 读书论文; 文化论文; 张竹坡论文; 李昌祺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