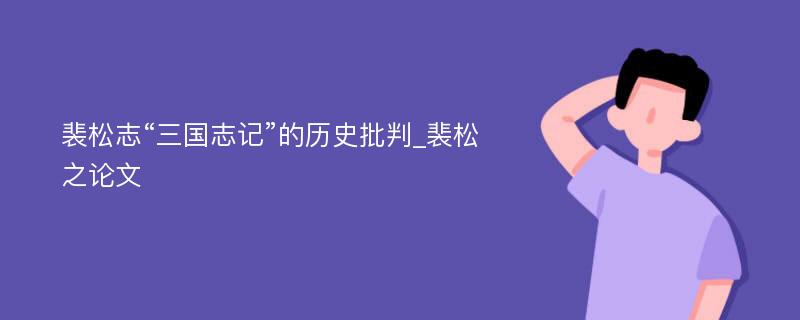
裴松之《三国志注》中的史学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批评论文,裴松论文,三国志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K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13)05-0054-08
裴松之在注《三国志》的过程中,善于利用各种方式来表现自己对史事、人物、历史现象等客观历史问题的见解与看法,这可以说是一种独特的历史评论①。这种寓评论于注释之中的方式,是裴松之史注的一个特色。但是他的贡献并不止于就客观历史进行评论,他还就史家、史书、史学现象等史学自身的问题进行批评。裴松之的史学批评在《三国志》的注文中多有表现。但是囿于注释之体,裴松之的史学批评显得较为零散,这就需要我们爬梳整理。笔者不揣谫陋,略陈一二,求教于方家。
一、关于史书叙事的批评
古希腊学者卢奇安说:“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1]真实,是史家叙事的“第一要义”[2],但一般史家往往很难做到。裴松之在《三国志注》中的史学批评,主要的部分就是对史家作史失实的原因进行分析:
——“假为”
裴松之在《三国志·魏书》卷5《后妃传》注释甄皇后因为失意而生怨言终为魏文帝赐死一事时,引用了王沈的《魏书》。但王沈《魏书》与陈寿所记完全相反,在王沈笔下,文帝对甄皇后宠爱有加,并且甄皇后是病死而非文帝赐死。两相对比,大相径庭。裴松之对此批评说:
《春秋》之义,内大恶讳,小恶不书。文帝之不立甄氏,及加杀害,事有明审。魏史若以为大恶邪,则宜隐而不言,若谓为小恶邪,则不应假为之辞,而崇饰虚文乃至于是,异乎所闻于旧史。推此而言,其称卞、甄诸后言行之善,皆难以实论,陈氏删落,良有以也[3]。魏文帝杀害甄皇后已经是“事有明审”,但王沈大概是出于“假回邪以窃位”[4]的目的,竟然不顾事实,凭空捏造历史。这种史家自身有意为之的“假为之辞”,是从史学主体的角度去掩盖历史的真相,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当是最为恶劣,甚至不仅仅是失实这么简单,已经关乎到史家的道德问题。所以裴松之对陈寿在记述此段史实不用王沈的史料给予肯定,这也反映了裴松之重视史书叙事的原则性。
同时,裴松之还批评有些史家通过移花接木的手法造成史实上的虚伪妄作。在《三国志·魏书》卷21《王卫二刘傅传》中,裴松之就王粲劝刘琮投降曹操一事,引用了张骘的《文士传》。《文士传》记载王粲言辞中有“(曹操)驱孙权于江外,逐刘备于陇右”之句,裴松之说:
孙权自此以前,尚与中国和同。未尝交兵,何云“驱权于江外”乎?魏武以十三年征荆州,刘备却后数年方入蜀,备身未尝涉于关、陇。而于征荆州之年,便云逐备于陇右,既已乖错。……以此知张骘假伪之辞。而不觉其虚之自露也。凡骘虚伪妄作,不可覆疏,如此类者,不可胜纪。”[5]张骘所记言辞,初看并无问题,但是细究起来,却会发现他是把后来发生的事情移接到此处,显然属于“虚伪妄作”。这与刘知幾所说的“或以前为后,或以有为无,泾渭一乱,莫之能辨”[6]的失实情况十分相似。至于他为何如此,我们限于史料尚无法得知,但是这种造假的手法却是相当肤浅,裴松之就多次指出张骘才学浅薄,在歪曲史实的时候往往“不觉其虚之自露也”。
——“专美”
因为政治因素,三国时代的各国史官在记载同一件事时,往往出现不同的说法:要么是记载的截然相反,要么是一味地粉饰己方,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史书叙事的失实。在《三国志·蜀书》卷32《先主传》中裴松之就赤壁之战引《江表传》为注释,但是《江表传》所引用的吴人的史料却是一味颂扬吴国,对于刘备方面则轻描淡写。对此,他借孙盛之口评论说:“刘备雄才,处必亡之地,告急于吴,而获奔助,无缘复顾望江渚而怀后计。《江表传》之言当是吴人欲专美之辞。”[7]如此事例尚可见《三国志·吴书》卷54《周瑜鲁肃吕蒙传》自注:
刘备与(孙)权并力共拒中国,皆肃之本谋。又语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则亮已亟闻肃言矣。而《蜀书·亮传》曰:“亮以连横之略说权,权乃大喜。”如似此计始出于亮。若二国史官,各记所闻,竞欲称扬本国容美。各取其功。……非载述之体也[8]。在裴松之看来,所谓“专美”就是各国史官“各记所闻,竞欲称扬本国容美,各取其功。”是出于政治目的而过度粉饰己方的行为。过度粉饰,必然会掩盖历史真相,导致失实,这正是刘知幾所说的“逮乎近古,无闻至公,国自称为我长,家相谓为彼短”[9]的作史弊病之一。
——“改易”
裴松之在注释《三国志》时,需要参考众多书籍,所以对诸家史书的材料来源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也因此得以察觉一些史家存有改易旧文的现象,他说:
孙盛改易(陈)泰言,虽为小胜。然检盛言诸所改易,皆非别有异闻,率更自以意制,多不如旧。凡记言之体,当使若出其口。辞胜而违实,固君子所不取,况复不胜而徒长虚妄哉?[10]
又说:
……松之以为史之记言,既多润色,故前载所述有非实者矣,后之作者又生意改之,于失实也,不亦弥远乎。凡孙盛制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后之学者将何取信哉?[11]
这种改易旧文的行为,刘知幾认为是史家为炫耀才学以“示其稽古”[12]。当然,“多用《左氏》以易旧文”,似乎还与当时追求“辞宗邱明”[13]的作史风气不无关系。但是无论怎样,这种行为所带来的危害却是很大的。一方面,改易之后的言语不与当时人物的语言特色相符合,以致“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纯”,所以反而“多不如旧”;另一方面则是直接导致了“失实”,使“真伪由其混乱”[14],令后之学者难以取信。所以裴松之感叹道:“辞胜而违实,固君子所不取,况复不胜而徒长虚妄哉?”极力反对史家这种出于炫耀为目的或盲目的简单模拟。
——“妄记”
裴松之还批评一些史家在具体的史实面前不能区分辨别,更未曾详究以理,便轻下笔墨,以致出现“妄记”失实的现象。他说:
……松之以为蔡邕虽为(董)卓所亲任,情必不党。宁不知卓之奸凶,为天下所毒,闻其死亡,理无叹惜。纵复令然,不应反言于王允之坐。斯殆谢承之妄记也[15]。
……松之以为(审)配一代之烈士,袁氏之死臣,岂当数穷之日,方逃身于井,此之难信,诚为易了。不知(乐)资、(袁)暐之徒竟为何人,未能识别然否,而轻弄翰墨,妄生异端,以行其书。如此之类,正足以诬罔视听,疑误后生矣。实史籍之罪人,达学之所不取者也[16]。
蔡邕有没有党附董卓,审配有没有逃身井中,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但裴松之要求史家在记述之前对史料先从“情”“理”的角度去“识别然否”,然后再慎下笔墨,这显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在他看来,史家作史未经判断便“轻弄翰墨”,只会“妄生异端”,是在“诬罔视听,疑误后生”,他甚至强烈批评这种轻下笔墨的“妄记”行为“实史籍之罪人”,这种强烈的愤慨,也正体现了一个历史学家严谨求实的作风。
——“因袭”
有些史家在引用前人史书时,对于其中错误,往往不予判别,便直接因袭,遂致再度失实。裴松之以鱼豢《魏略》为例说:
《魏略》既已难信,习氏又从而载之,窃谓斯人受诬不少[17]。
又举郭颁《魏晋世语》说:
颁撰《魏晋世语》,蹇乏全无宫商,最为鄙劣,以时有异事,故颇行于世。干宝、孙盛等多采其言以为《晋书》,其中虚错如此者,往往而有之[18]。
在引用前人史书时,刘知幾认为,后来学者应“识事详审”[19],清楚所引史实的始末原委,不能未经判别就直接使用。但是一些史家往往未必如此,习凿齿即不经辨别就引用“激抗难征”[20]的《魏略》;干宝、孙盛则直接因袭“蹇乏全无宫商”的《魏晋世语》。这种因袭不改所带来的影响是广泛和长远的,裴松之认为一方面它使得所记载的历史人物“受诬不少”,影响了史家的鉴识和判断;另一方面也使得其文多有“虚错”。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虚错”是对前人“虚错”的“从而载之”,是一种继承性的“虚错”,这种继承如果不加以辨别,往往使人产生错觉,误以为长期继承下来,一直未曾变化,自然就是“正确”的。所以“因袭”类失实可谓是继承性或积累性的失实。
——“妄说”
史家不记载诬妄之说是自孔子以来形成的优良传统,裴松之予以继承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在注文中多次强调史料采撰不能把出自“鄙俚”的“世俗妄说”等传言不实之词当作信史引用,他说:
《献帝春秋》云(荀)彧欲发伏后事而求使至邺,而方诬太祖云“昔已尝言”。言既无征,回托以官渡之虞,倪仰之间,辞情顿屈,虽在庸人,犹不至此,何以玷累贤哲哉。凡诸云云,皆出自鄙俚,可谓以吾侪之言而厚诬君子者矣。袁暐虚罔之类,此最为甚也[21]。
孙盛曰:此不然之言。(刘)备时羁旅,客主势殊,若有此变,岂敢晏然终表之世而无衅故乎?此皆世俗妄说,非事实也(22]。
裴松之很重视这种类似于现代所说的口述史料,他曾就蜀国庲降这一地名亲自“讯之蜀人,云庲降地名,去蜀二千余里”[23]。又“臣松之闻孙怡者,东州人,非(孙)权之宗也。”[24]皆表明他善于运用口述史料。但是对于不切实际的“世俗妄说”,他是坚决反对使用的,认为皆“非事实也”,这与刘知幾要求为史者当“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25]的作史原则是一致的。
——“爱憎”
史家作史的最高原则当是“尽其天不益以人”[26],即尽可能的客观记述,不要过多掺杂个人情感。若令史家“爱憎由已,高下在心,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欲求实录,不亦难乎?”[27]所以裴松之在注文中批评史家掺杂过多个人情感,他说:
《傅子》前云(傅)嘏了夏侯之必败,不与之交,而此云与钟会善。愚以为夏侯玄以名重致患,衅由外至。钟会以利动取败,祸自己出。然则夏侯之危兆难睹,而钟氏之败形易照也。嘏若了夏侯之必危,而不见钟会之将败,则为识有所蔽,难以言通。若皆知其不终,而情有彼此,是为厚薄由于爱憎,奚豫于成败哉?以爱憎为厚薄,又亏于雅体矣。《傅子》此论,非所以益嘏也[28]。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固然是“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29],但是若过多地掺杂个人情感,难免会有失实的情况出现,这就是裴松之所说的以“爱憎”为“厚薄”,则“亏于雅体矣”。所谓“亏于雅体”其实就是对史家叙事失实的婉转批评。
除上述事例外,高贵乡公为司马氏所弑之后裴松之引用的《汉晋春秋》亦是如此:
葬高贵乡公于洛阳西北三十里瀍涧之浜。下车数乘,不设旌旐,百姓相聚而观之,曰:“是前日所杀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悲不自胜。裴松之于其后说:“若但下车数乘,不设旌旐,何以为王礼葬乎?斯盖恶之过言,所谓不如是之甚者。”[30]所谓“恶之过言”就是说习凿齿过多掺杂了个人情感在内,以致所记不实。这种“以爱憎为厚薄”或“恶之过言”的态度作史虽“自诩客观忠实,而血气沸腾,情感激动,结果是不客观不真实”的[31]。裴松之的批评可谓的论。
——“疏谬”
裴松之在文中对一些史家因为自己的疏忽,导致叙述前后不一,以致失实的情况作了批评。他以干宝记载嵇康被杀时间前后错讹为例,认为这是“干宝疏谬”,遂致“自相违伐也。”[32]“自相违伐”就是指干宝叙事不够严密,从而失实。除此之外,裴松之还指出另一种“疏缪”,即某一史家就某一史事作了两种史书,但两书记载却彼此“殊异”,互相抵违,以致失实,如:
《魏氏春秋》曰:……初,(嵇)康采药于汲郡共北山中,见隐者孙登。康欲与之言,登默然不对。逾时将去,康曰:“先生竟无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又《晋阳秋》云:康见孙登,登对之长啸,逾时不言。康辞还,曰:“先生竟无言乎?”登曰:“惜哉。”此二书皆孙盛所述,而自为殊异如此[33]。
……松之案:《汉晋春秋》亦载此语,不云董恢所教,辞亦小异,此二书(《襄阳记》《汉晋春秋》)俱出习氏而不同若此[34]。这两种状况的出现,都是史家个人疏忽懈怠的原因所致,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这虽然与前文“假为”类失实一样,都是史家个人的主观因素所致,但细究之下仍能发觉不同:“假为”类失实是史家有意识造假,而“疏缪”类失实则是史家无意识所为。而且就危害程度而言,当仍以“假为”类为最。裴松之能分辨其中不同,辟为两类,可见其史学鉴识之深远。
——“好奇”
裴松之在注文中还批评一些史家以“好奇”心理作史,如官渡之战曹操以少胜多,本是事实,但有的史家在记述此事时,却故意夸大,以达到“以少见奇”的目的。裴松之分析说:
魏武初起兵,已有众五千,自后百战百胜,败者十二三而已矣。但一破黄巾,受降卒三十余万,余所吞并,不可悉纪。虽征战损伤,未应如此之少也。
然后又以逻辑推理的方法证明曹操兵力不可能过少,否则于理不合。最后他认为史家之所以如此是“将记述者欲以少见奇,非其实录也。”[35]
除此之外,裴松之还指出有些史家作史“盖由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伤理。”[36]也是对史家“好奇”心理的批评。这种“好奇”心理,刘勰分析说:“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这与裴松之所说“以少见奇”从本质上而言是一致的。而刘勰说“好奇”乃“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37],亦是裴松之所说的“非其实录”。
综上,经过笔者的爬梳整理,可知裴松之在注文中零散地列举出了多种导致史文失实的原因,有的是就史家个人因素的主观方面而言,如“假为”“专美”等类失实;有的是就史家个人因素的客观方面而言,如“疏谬”“因袭”“妄说”等类失实;有的是就史家史识而言,如“妄记”类失实;还有的则是就史家的个人情感而言,如“爱憎”类失实,等等。这些失实的原因包含了史家的主客观的方面,可谓详审,而且有的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二、关于史书体例的批评
唐代刘知幾说得好:“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38]史例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对于史书体例,裴松之的批评对象主要是纪传体史书中的类传与合传。裴松之在批评的过程中还就类传和合传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这可视为一家之言。
类传的特点,古代史家多认为是“事类相从”[39],或笼统为“以类相从”[40],裴松之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在注文中常引用鱼豢的《魏略》,并在引用之前会分析类传传主共卷的原因,如“《魏略·列传》以徐福、严干、李义、张既、游楚、梁习、赵俨、裴潜、韩宣、黄朗十人共卷”,他认为共卷的原因是“其器性皆重厚”[41],即认为这是从“器性”的角度予以共卷,不仅仅是传主之间的事迹相似。又“《魏略·勇侠传》载孙宾硕、祝公道、杨阿若、鲍出等四人”,其中宾硕是汉朝人,按理不当纳入此传,但裴松之分析后认为“宾硕虽汉人,而鱼豢编之魏书,盖以其人接魏,事义相类故也。论其行节,皆庞、阎之流。”[42]所谓“事义相类”,其中“事”就是事迹,“义”则是指以“义”为代表的“器性”。这也是指传主们不仅事迹相似,“器性”品质亦要相当。所以,“事义相类”四个字可以说是裴松之对类传特点的一个重要理论概括,可为一家之言。
类传体“事义相类”的特点也被裴松之要求运用到合传体中。自司马迁《史记》问世以来,列传中的合传大多以“时之先后”或“事类相从”为编排依据,如“服虔曰:‘传次其时之先后耳,不以贤智功之大小也。’师古曰:‘虽次时之先后,亦以事类相从。如江充、息夫躬与蒯通同传;贾山与路温舒同传;严助与贾捐之同传之类是也。’”[43]但裴松之在此基础上却有进一步的看法,即合传还要以传主的性格品质为共卷依据,他在《荀彧荀攸贾诩传》“评曰”后说:
列传之体,以事类相从。张子房青云之士,诚非陈平之伦。然汉之谋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则余无所附,故前史合之,盖其宜也。魏氏如(贾)诩之俦,其比幸多,诩不编程、郭之篇,而与二荀并列,失其类矣。且攸、诩之为人,其犹夜光之与蒸烛乎,其照虽均,质则异焉。今荀、贾之评,共同一称,尤失区别之宜也[44]。
裴松之首先强调司马迁首创了“以事类相从”的合传,然后指出张良、陈平在《史记》中本不应合为一传,因为二者虽然都是“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45]的谋略之士,但品质相差太大,张良乃“青云之士”,陈平则是“盗嫂受金”[46]之徒,难以并列共卷。只是汉初谋士列于传记中的仅此二家,所以“若不共列,则余无所附,故前史合之,盖其宜也。”这就是说将二人合传是没有办法的事,对于传主品质的考虑只能暂放一边。但曹魏之时,谋略之士尤多,如荀彧、荀攸、贾诩、程昱、郭嘉皆是。虽然皆为谋士,但是他们之间的品质却高低不同。荀彧、荀攸叔侄二人当时即被誉为有君子之风,其他几人则远非其伦,“程昱、郭嘉、董昭、刘晔、蒋济才策谋略,世之奇士,虽清治德业,殊于荀攸,而筹画所料,是其伦也。”[47]贾诩更是如此,他本为董卓谋士,董卓死后,西凉军群龙无首,多欲遁逃西北,贾诩却主张反攻长安,并屠城以立威,裴松之于此注释说:
《传》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然则不仁之言,理必反是。夫仁功难著,而乱源易成,是故有祸机一发而殃流百世者矣。当是时,元恶既枭,天地始开,致使厉阶重结,大梗殷流,邦国遘殄悴之哀,黎民婴周余之酷,岂不由贾诩片言乎?诩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乱,未有如此之甚。
可见贾诩确是毫无德行之徒,如此之人,焉能与百世楷模并列呢,所以裴松之说“攸、诩之为人,其犹夜光之与蒸烛乎。其照虽均,质则异焉。今荀、贾之评,共同一称,尤失区别之宜也。”就是要求在传主事迹相当的情况下,还应当考虑传主的品质是否相同,所谓“其照虽均,质则异焉”即不仅事类还要质同。从“时之先后”到“事类相从”再到“事义相类”,这是他对合传发展的更高要求。
三、关于史文表述的批评
裴松之在文中还对史文表述多有批评,所用笔墨较多,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史文繁简。史文的繁简问题,向来为史家所关注,刘知幾认为史家“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48]。裴松之在繁简问题上十分关注。《董卓传》后陈寿的评语说:董卓狼戾贼忍,暴虐不仁,自书契已来,殆未之有也。裴松之于其后论述道:“评既曰“贼忍”,又云“不仁”,贼忍,不仁,于辞为重。”[49]“贼忍”就是指董卓为人恶毒,这与后文“不仁”一词意思相同,既言“贼忍”又言“不仁”,故裴松之说陈寿用辞“为重”。
又《曹冲传》中裴松之引王沈《魏书》注释:
冲每见当刑者,辄探睹其冤枉之情而微理之。及勤劳之吏,以过误触罪,常为太祖陈说,宜宽宥之。辨察仁爱,与性俱生,容貌姿美,有殊于众,故特见宠异。
裴松之于其后批评说:“松之以‘容貌姿美’一类之言,而分以为三,亦叙属之一病也。”[50]“容貌姿美”是指曹冲的容颜、外貌、身姿都很美丽,都是形容人的外在之美。但是这三者都属一类言辞,稍嫌重复,所以裴松之批评说这是“一类之言,而分以为三”,为“叙属之一病也”。以上二则事例,裴松之都是要求文辞尽可能的简略,反对浮词过多。
第二,关于史文烦省。史文的烦省亦是史家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刘知幾认为“论史之烦省者,但当要其事有妄载,苦于榛芜;言有阙书,伤于简略,斯则可矣。”[51]裴松之认为史家在叙事的时候不可“妄载”,尤其是不应采撰琐屑之言,以求史文之省。在这方面,裴松之的看法甚至近于苛刻。如陈寿在《宗预传》中记载了邓芝与宗预二人就彼此年龄相互调侃一事,其文如下:
时车骑将军邓芝自江州还,来朝,谓(宗)预曰:“礼,六十不服戎,而卿甫受兵,何也?”预答曰:“卿七十不还兵,我六十何为不受邪?”
裴松之于其后说:
……松之以为芝以年啁预,是不自顾。然预之此答,触人所忌。载之记牒,近为烦文[52]。
邓芝与宗预彼此以年龄调侃,这当属琐屑无聊之事,不应当记载于正史之中,所以裴松之批评说这是“近为烦文”,这与刘知幾评论陈寿说他“颇从简约,犹时载浮讹,罔尽机要”[53]当属一致。但是也要看到,这样的史文表述却也有自己的优点,即比较形象。如果过于要求文字的简省,则史文不免显得干涩无味。所以裴松之有时候对于史文的要求已经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了。
第三,关于史文的文与质。裴松之极为重视史书文字的修饰,他强调“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54],此语虽是关于言语,但对于文字亦是如此。裴松之对于史书的评判往往是把文辞作为基本要素。如:
(张)璠撰《后汉纪》,虽似未成,辞藻可观。(虞)溥著《江表传》,亦粗有条贯。惟(郭)颁撰《魏晋世语》,蹇乏全无宫商,最为鄙劣,以时有异事,故颇行于世[s5]。
(傅)权作左思《吴都赋》叙及注,叙粗有文辞,至于为注,了无所发明,直为尘秽纸墨,不合传写也[56]。
“辞藻可观”“粗有文辞”都是就史书文字而言,即要求史书文字上能够做到文辞流畅,使人能读得下去,或者至少不是味同嚼蜡。对于那些文辞粗疏的史书,裴松之则直接痛责,如:
《魏末传》所言,率皆鄙陋[57]。
袁暐、乐资等诸所记载,秽杂虚谬,若此之类,殆不可胜言也[58]。
甚至认为史家文字若“言不经理,深可忿疾也”[59],足见他对史文言辞修饰的重视。但是他并不是一味强调修饰,更多的是希望史文能有质朴之美,这种质朴之美就是要求史家不可“怯书今语,勇效昔言”[60]。但是“怯书今语,勇效昔言”在当时却较为普遍,如孙盛《魏氏春秋》云:“(曹操)答诸将曰:‘刘备,人杰也,将生忧寡人。’”裴松之于其后批评道:“凡孙盛制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后之学者将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励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类。”[61]刘知幾对此论述说:“裴世期讥孙盛录曹公平素之语,而全作夫差亡灭之词。虽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62]可见这种“平素之语”,裴松之是希望尽可能保持原貌,从实记载,不必以旧文改易,否则容易不伦不类。又:
孙盛改易(陈)泰言,虽为小胜。然检盛言诸所改易,皆非别有异闻,率更自以意制,多不如旧。凡记言之体,当使若出其口。辞胜而违实,固君子所不取,况复不胜而徒长虚妄哉?[63]
这段话里包含了裴松之的两个认识,一是“凡记言之体,当使若出其口。”这与前文要求史家记言当保持历史人物的“平素之语”是一致的。二是对文辞和真实做了比较和权衡,认为史书的真实性应当是第一位的,即“辞胜而违实”,为“君子所不取”。
关于史文表述的批评除以上事例外,裴松之还指出一些史家的文辞有不够精审、不够恰当以及未能尽意等缺陷,这些问题在我们今天看来同样具有现实性的启发意义。
总的来说,裴松之的史学批评虽然零散细碎,但是若能钩玄提要,串联缨络,未尝不是吉光片羽。尤其是注文中关于史文失实的十数种原因的分析,应当是对刘知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至于《史通》中许多篇章都可以看到裴松之的影子②。因此裴松之的史学批评在中国史学批评发展史上应当占有重要一页,这对史学批评的总体研究来说也是有益的。
收稿日期:2013-05-26
注释:
①参见拙作《寓论断于注释——〈三国志〉裴注表微》,《史学汇刊》(台湾)2010年第2期。
②刘知幾受裴松之影响一事可参见逯耀东《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中华书局2006年版。或参见杨耀坤、伍野春《陈寿、裴松之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标签:裴松之论文; 三国论文; 三国志注论文; 历史书籍论文; 魏书论文; 魏略论文; 江表传论文; 汉晋春秋论文; 魏晋世语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