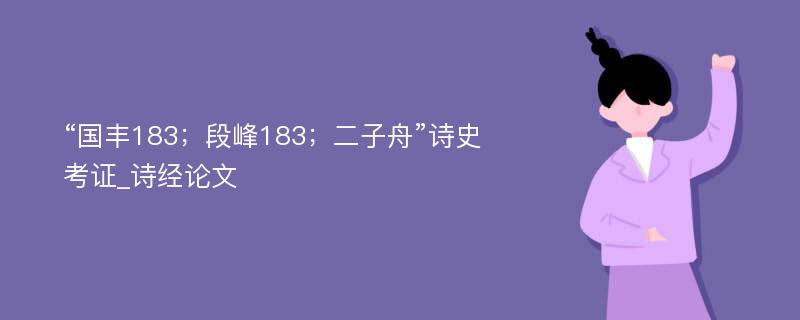
《国风#183;邶风#183;二子乘舟》诗史稽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史论文,国风论文,二子论文,邶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风·邶风·二子乘舟》:“二子乘舟,泛泛其景。愿言思子,中心养养!二子乘舟,泛泛其逝。愿言思子,不瑕有害?”①自清中期始,关于这首诗的内容与《史记·卫康叔世家》中宣公十八年的历史叙述是否有联系的问题,成为学界讨论《诗经》的一个议题。自汉代《毛序》和刘向《新序·节士》篇认定两者有联系以来,少有学者对《二子乘舟》中“二子”即为卫宣公二子伋、寿这一论断有所怀疑。清代的姚际恒、胡承珙率先对此提出疑问,认为《毛序》、《新序》是附会历史,没有确凿证据表明《二子乘舟》所叙述的便是卫宣公两个儿子之事。姚际恒《诗经通论》提到:“大抵《小序》说《诗》非真有所传授,不过影响猜度,故往往有合有不合。如邶、鄘及卫皆摭卫事以合于诗,《绿衣》、《新台》以言庄姜、卫宣,此合者也;《二子乘舟》以言伋、寿,此不合者也。正当分别求之,岂可漫无权衡,一例依从者哉!”②此后,质疑《二子乘舟》包蕴宣公二子史实的学者渐渐增多,随着20世纪初史学界疑古风气兴盛,不少学者提出回归《诗经》原貌、反对以经学的眼光附会历史的主张,对《毛序》可信度的怀疑也与日俱增。顾颉刚认为:“二千年来的《诗》学专家闹得太不成样子了,它的真相全给这一辈人弄糊涂了。”“很希望自己做一番斩除的工作,把战国以来对《诗经》的乱说都肃清了。”③傅斯年认为《二子乘舟》:“鲁说以为伋寿二子傅母作,毛以为国人伤伋、寿二子而作,然诗中无可证此义者。”④本文拟从文献入手,廓清有关史实,以求正于高明。
关于《二子乘舟》所指,汉初《毛序》认为:“二子乘舟,思伋、寿也,卫宣公之二子争相为死,国人伤而思之,作是诗也。”“二子,伋、寿也。宣公为伋取于齐女而美,公夺之,生寿及朔。朔与其母愬伋于公,公令伋之齐,使贼先待于隘而杀之。寿之知,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寿窃其节而先往,贼杀之。伋至曰:‘君命杀我,寿有何罪?’贼又杀之。国人伤其涉危遂往,如乘舟而无所薄,泛然迅疾而不碍也。愿,每也。养养然忧不知其所定。”⑤稍后的刘向同样认为《二子乘舟》与卫宣公二子之事有联系,但在二子“乘舟”的历史细节上,给出了不同的说法。《新序·节士》:“卫宣公之子,伋也,寿也,朔也。伋,前母子也。寿与朔,后母子也。寿之母与朔谋,欲杀太子伋而立寿也,使人与伋乘舟于河中,将沉而杀之。寿知不能止也,因与之同舟,舟人不得杀。伋方乘舟时,伋傅母恐其死也,闵而作诗,《二子乘舟》之诗是也。其诗曰‘二子乘舟’云云,‘养养’,于是寿闵其兄之将见害,作忧思之诗,《黍离》之诗是也……又使伋之齐,将使盗见载旌,要而杀之。寿止伋,伋曰:‘弃父之命,非子道也,不可。’寿又与之偕行。寿之母知不能止也,因戒之曰:‘寿无为前也。’寿又伪前,窃伋旌以先行。几及齐矣,盗见而杀之。伋至,见寿之死,痛其代己死,涕泣悲哀,遂载其尸还,至境而自杀,兄弟俱死。故君子义此二人,而伤宣公之听馋也。”⑥另者,今文三家诗对《二子乘舟》解释与《新序·节士》几乎一样⑦,不赘举。
以上构成汉儒释经一条基本线索,即从《毛序》到刘向《新序》、三家诗,皆以《二子乘舟》为记叙卫宣公十八年公室的事迹。但细读又可发现,上述文献对事迹的叙述有出入:《毛序》认为公子伋被贼人害于齐,《二子乘舟》乃“国人”作于二子死后;而《新序》认为公子伋载寿的尸体回到卫国后自杀,乘舟诗是“伋傅母”作于伋、寿乘舟之前。关于伋是自杀或是他杀、寿于其中起何作用等,《毛序》与《新序》的记叙不尽相同。
我们再来看看《史记·卫康叔世家》对卫宣公时期历史的记载。《史记》对伋死因的记述可能参考了《左传·桓公十六年》⑧的记载,与《毛序》说法相同,即认为伋不是返卫自杀,而是见杀于齐:
宣公得齐女,生子寿、子朔,令左公子传之。太子伋母死,宣公正夫人与朔共谗恶太子伋。宣公自以其夺太子妻也,心恶太子,欲废之。及闻其恶,大怒,乃使太子伋于齐而令盗遮界上杀之,与太子白旄,而告盗界见持白旄者杀之。且行,子朔之兄寿,太子异母弟也,知朔之恶太子而君欲杀之,乃谓太子曰:“界盗见太子白旄,即杀太子,太子可毋行。”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寿见太子不止,乃盗其白旄而先驰至界。界盗见其验,即杀之。寿已死,而太子伋又至,谓盗曰:“所当杀乃我也。”盗并杀太子伋,以报宣公。宣公乃以子朔为太子。⑨
《史记》这一记载与《左传·桓公十六年》相同。《毛序》显然采纳了《左传》、《史记》的说法,《新序》则不然。但就《二子乘舟》谈的是卫宣公家事这一点而言,《毛序》与《新序》、今文三家诗等是一致的。
汉之后各代的学者,对《二子乘舟》的解读,基本沿用《毛序》的说法。如朱熹在《诗集传》中对此诗的解释,亦引用《毛序》和《史记》的记载⑩。明代陈耀文的《经典释疑》也说:“《乘舟》之诗为伋、寿作也。”(11)从汉儒到宋、明儒,释读《二子乘舟》的途径没有大变化。直至清代,古文家沈镐,仍将此诗与伋、寿遇害相联系,认为是辞者“为君讳”,“不忍斥言其死”(12)。这种观点,到了清代至民国时期,才受到质疑。
清代学者首先针对诗与现实的矛盾之处,指出《二子乘舟》与春秋卫宣公之事无关。姚际恒认为《新序》中关于“二子乘舟”的部分内容是刘向编造的,卫宣公十八年之事应如《史记》、《左传》的记载,就史实上看应以《毛序》为准。但又据此认为二子并没有同时乘舟,不会发生“二子乘舟”的景象,因此《毛序》是以宣公十八年历史附会《二子乘舟》一诗,所述不合史实。他说:
小序谓思伋、寿,此有可疑。按《左传·桓公十六年》曰:“卫宣公烝于夷姜,生伋子,属诸右公子,为之娶于齐而美,公取之,是为宣姜。生寿与朔,属寿于左公子。夷姜缢,而宣姜与公子朔搆伋子,公使诸齐,使盗待诸莘,将杀之。寿子告之,使行不可,曰:弃父之命,恶用子矣?有无父之国则可也。’及行,饮以酒。寿子载其旌以先,盗杀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请杀我乎。’又杀之。”夫杀二子于莘,当乘车往不尚乘舟,且寿先行,伋后至,二子亦未尝并行,又卫未渡河,莘为卫地,渡河则齐地,皆不相合。《毛传》则谓“待于隘而杀之”,亦与乘舟不合,其解则为比,谓如乘舟,而无所“薄泛泛”。然迅疾而不碍也,甚牵强,不可从。《集传》则直载其事,而于乘舟以为赋漫不加考,尤疏。刘向《新序》曰:“使人与伋乘舟于河中,将沉而杀之。寿知不能止也,因与之同舟,舟人不得杀。伋方乘舟时,伋傅母恐其死也,闵而作诗”;其后又载杀伋寿之事,与《左传》同。何玄子引之,以为此诗之证。按向之前说,明是因与《左传》不合,故造前一事以合于诗,附会显然。(13)
疑古派崔述从诗作时间上考证,也认为《二子乘舟》与卫宣公之事无关:“邶卫二国风多似春秋以前所作。《淇澳》、《硕人》不待言矣,其余诸篇皆与春秋经传所载卫国之诗无关涉。”“故序虽以春秋中事附会之,而委曲牵强,卒不能合也。”(14)承珙亦怀疑《新序》的真实性:“传云:‘国人伤其涉危遂往,如乘舟而无所薄。’明是借喻之语。毛公岂不知二子皆殒于陆而非舟中?又后继往,亦非同舟而济邪。若《新序》谓:‘寿母谋沉伋于河。寿知而与之同舟,舟人不得杀。伋方乘舟时,伋傅母恐其死也,闵之而作是诗’,安知其不即因是诗而附会为此说邪?”(15)为了调和《毛序》与《新序》之间的矛盾,魏源通过解释另一首诗《鄘风·干旄》(16),来证明《新序》对《二子乘舟》解说的正确性。对此,黄节在《诗旨纂辞》中谈到:“节案:序传皆以此诗为国人作于二子既死之后,而《新序》则谓‘伋之傅母恐其死也,闵而作诗。’则是作于未死之前。魏源取《新序》,谓诗有‘乘舟’之文,则非待隘之役。曰‘泛泛其逝’、‘不瑕有害’,则非既死之词。诗作于事前。不能害诸水,而后改谋害诸陆,至伋载尸还,至境自杀。则当以《干旄》之诗证之。魏氏说良有见,得此则‘乘舟’之疑可释。姚际恒、胡承珙其疑《新序》附会,盖未审此也。”(17)在这里,黄节认同魏源对《鄘风·干旄》与《二子乘舟》关系的判断。魏源在《诗古微》中提出《干旄》叙述的是伋携被害的寿的尸体归国,在卫国的边邑浚自杀的故事,这是很有见地的观点:
曰:诗有乘舟之文,则非待隘之役。曰“泛泛其逝”,“不瑕有害”,则非既死之词。诗作于事前。不能害诸水而后害诸陆,新序胜矣。《水经注》云:“今阳平县北十里有故莘亭,道扼陈蹊要,自卫适齐之道也。望新台于河上,感二子之宿龄,诗人乘舟诚可悲矣。今县东有二子庙,犹谓之孝词矣,此用毛诗以乘舟为待隘,故词事不合。”至伋载尸还至境上自杀,则当以《干旄》之诗证之。史记:“姜予太子白旄,而告界盗见持白旄者杀之。”《列女传》:“宣姜阴使力士待界上,俟有四马白旄至者要杀之。”案:四马即诗(《干旄》)良马四之也。白旄易于识别,故诗言“孑孑干旄”,必三言“素丝组之”也。而左氏言盗待伋于莘,则在阳平。盖自卫过齐渡河在浚,由是东行至莘被杀,故伋载其尸,复于浚,由郊而都而城,遂不复北渡而自杀也,始四马而后五六者。寿先假车马以行,及伋追至,故并寿马为五六也。(18)
魏源经过翔实的地理考证,认为“诗(《二子乘舟》)作于事前”。对“莘亭”,《水经·河水注》五云:“漯水又北,绝莘道,城之西北有莘亭,《春秋》桓公十六年卫宣公使伋使诸齐,令盗待于莘,伋寿既陨于此亭。京相璠曰:‘今平原阳平县北十里有故莘亭,阨险蹊要,自卫适齐之道也。望新台于河上,感二子于凰岭,诗人乘舟,诚可悲也。’今县东有二子庙,犹谓之为孝祠。”(19)可见《左传·桓公十六年》记载“使盗待诸莘”的“莘”,确存在于卫、齐之间,且自古以来莘县便有“二子乘舟”的传说。黄节认为魏源对《干旄》的解释正好阐述了伋的确切死因:回国后在浚自杀而死。“干旄”、“四马”便是证据。《新序》说法是正确的,姚、胡没有认识到《干旄》这一点,才会因情节有矛盾,而认定《新序》之说为附会。黄节总结道:“盖《乘舟》之诗,欲杀之河而不遂;此诗(《干旄》)则杀寿于莘,而伋还复自杀于浚。《新序》与《左氏》、《史记》、《列女传》义互相备,而伋、寿二诗之情事,千载如见矣。节于《二子乘舟》之诗,即采魏氏说;则此诗亦自可从,故并录之。”(20)作为毛诗家的马瑞辰亦认同《新序》,认为《二子乘舟》作于未死之前:“首章‘中心养养’,二章‘不瑕有害’,皆二子未死以前恐其被害之词,非既死后追悼之词。且二子如未乘舟,不得直言乘舟也,新序说是。”(21)
伋的死因自古以来便没有确凿说法,经过清人的讨论,至今仍无确解。而寿死于莘基本上没有什么疑问。就诗与史之关系而言,魏源的说法给姚际恒、崔述、胡承珙的疑问提供了一种解释。姚际恒等提出二子并未乘舟,故与《二子乘舟》无关的观点,也不能成立。
那么,《二子乘舟》与卫宣公十八年的史事有没有联系呢?笔者认为二者间是有联系的。再就几个问题展开辨识:首先,有人认为《二子乘舟》来自《邶风》,并非《卫风》,故该诗情节不是来源于卫国。这种怀疑不能成立。今人冯浩菲对此的解释十分清楚:“由于卫诗39篇均作于卫并邶、鄘之后,当时的邶、鄘只属于卫国的两个地区,已不是昔日的邶国和鄘国了。也就是说,卫为卫土,人为卫人,诗为卫诗。”(22)他还认为作于邶、鄘、卫任何一个地方的诗,都可以以卫国的名义在其他地方流行。朱熹早就言及:“邶鄘地既入卫,其诗皆为卫事,而犹系其故国之名。”(23)傅斯年亦云:“邶鄘卫乃一体,不可分,误为人分为三。”“邶鄘卫篇章皆是卫诗。”(24)可见说《二子乘舟》描写的是卫国史事,是合情合理的。其次,《二子乘舟》作于伋遇害事前还是事后,现已不可考;但若认为此诗与卫宣公十八年二子之事毫无联系,也不妥。从《二子乘舟》成诗时间上看,戴震认为此诗作于东周桓王、卫宣公之时(25)。今人马银琴考证此诗作于卫宣公、卫惠公之时:“按照古籍记载,卫宣、惠时代卫公室极不安宁,卫宣公本是在州吁之乱后成为卫君的,为子伋娶妻而宣公自妻之一事,成为此后卫公室长期不宁的根本原因。此后卫宣公听谗杀子伋而子寿从死,二公子为乱而惠公被逐等事,皆由此而起。公室荒淫和国事日非是这一时期卫国的特点。”(26)从诗言志的角度看,构成上述诗与史的联系也不无可能。
《二子乘舟》列于《邶风》之末,与其相邻的若干邶诗,以及其后的鄘诗,大都是刺卫、刺淫诗。当时卫国动荡的现实撩动国人的情思,从《毛序》对下列《邶风》、《鄘风》诸诗内涵所作的诠释看,《二子乘舟》涉及卫宣公家事的写法,并不是孤例。《毛序》称:《邶风·匏有苦叶》:“刺卫宣公也。公与夫人并为淫乱。”《邶风·北门》:“刺士不得志也。言卫之忠臣不得其志尔。”《邶风·北风》:“刺虐也。卫国并为危虐,百姓不亲,莫不相携持而去焉。”《邶风·新台》:“刺卫宣公也。纳伋之妻,作新台于河上而要之,国人恶之而作是诗也。”《鄘风·墙有茨》:“卫人刺其上也。公子顽(卫宣公庶长子)通于君母(宣姜),国人疾之而不可道也。”《鄘风·君子偕老》:“刺卫夫人也。夫人淫乱,失事君子之道。”《鄘风·桑中》:“刺奔也。卫之公室淫乱,男女相奔。至于士族在位,相窃妻妾,期于幽远。政散民流而不可止。”(27)可见与《二子乘舟》同时而作、同时集结的几首邶诗、鄘诗较多反映了卫宣公、宣姜淫乱之事。可以说,无论《二子乘舟》表达的是什么思想内容,或是刺虐刺淫,或是思念二子、赞美孝道,它与卫宣公十八年事迹都有关联。与《二子乘舟》诗意关系尤其紧密的,位于它上首的《新台》。清周象明《韦庵经说》“新台乘舟论”条云:“《邶风·新台》、《乘舟》何为而作也哉?曰:《新台》,齐人所以刺宣公也。《二子乘舟》,国人所以哀二子也……读此二诗,则知卫之三纲沦、九法斁矣,不亡何待乎?卫宣公上烝夷姜,生伋,为娶于齐。宣公闻其美,欲纳之,恐其不从,因作新台于河上而要之,是为宣姜,生寿及朔……自宣公以后,父子兄弟君臣之间相残相贼,不惟毒流子孙,而且酿成王室之乱,袵席之祸,一至于此,可不惧哉!而职为万阶者,则皆为宣公之淫恶为之倡也。”(28)
由上可见,《二子乘舟》是基于时代的作品,与卫公室之事有关联,是“国人所以哀二子”而作。方玉润对《二子乘舟》的诗旨用意提出另一种观点,认为该诗是在讽刺二子违背天理人情、愚孝的行为:“不可泥诗求事,不可执事以言诗,当迂回以求其用心之所在,然后得其意旨之所存。诗非赋二子死事也,乃讽二子以行耳。意以为孝子事亲,尚先揆理,苟有当于理虽违亲命,亦于天理人情无伤?若沾沾固守小节,不达权变,非徒有害于身,亦且陷亲不义,其于理又何当哉?”(29)不论《二子乘舟》的诗旨如何,认为此诗与卫宣公十八年二子之间存在某种联系的观点,是能够成立的。我们可以将《毛序》建立起来的以“美刺”为核心的价值评判体系,视作使《诗经》成为文化经典的重要一环。用怨而不怒的“美刺”,用舒缓忧伤的文学笔法写一个凄美的故事,对当权者亦刺亦谏,是《国风》的一种基本手法,《二子乘舟》正是这方面的杰作。一方面,即便这首诗没有经过汉儒的政治性伦理性解读,它传达出当时卫国人的心理情绪也是真实而感人的。如明戴君恩所言:“明知遇害,但云‘不瑕’,悲伤之情更觉凄绝。”“不曰形,而曰影,已有顾影堪怜之意;不曰行,而曰逝,一去不返,影亦不复亲矣。真令人不堪卒读也!”(30)它渲染出苍凉、渺茫而无奈甚至绝望的情绪,与当时卫国人对二子的哀伤怀念、对国事衰微的无可奈何契合在一起,平添一种凄美的哀伤的神秘,赋予这首诗以无穷的魅力。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仅仅认其为‘文学’而否认其经学的研究意义,那么《诗经》的文化意义便会丧失殆尽。”“从文学转向经学,并非是《诗经》的‘厄运’,而是《诗经》的大幸。”(31)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
注释:
①(27)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2010年版,上册第120页,第86、99、110、112、117、124、126、131页。
②(13)姚际恒:《诗经通论》卷三,《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2册第55页,第55页。
③顾颉刚:《〈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古史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册第309、310页。
④(24)傅斯年:《诗经讲义稿》,中国人民大学2009年版,第61—62页,第61页。
⑤陈奂:《诗毛氏传疏·诗三》,《续修四库全书》本,第70册第60页。
⑥(28)刘毓庆等著《诗义稽考》,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2册第603页,第587页。
⑦(19)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续修四库全书》本,第77册第457页,第457页。
⑧《左传·桓公十六年》:“卫宣公烝于夷姜,生伋子,属诸右公子,为之娶于齐而美,公取之,是为宣姜。生寿与朔,属寿于左公子。夷姜缢,而宣姜与公子朔搆伋子,公使诸齐,使盗待诸莘,将杀之。寿子告之,使行不可,曰:‘弃父之命,恶用子矣?有无父之国则可也。’及行,饮以酒。寿子载其旌以先,盗杀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请杀我乎。’又杀之。”(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45页。)
⑨《史记》,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593页。
⑩(23)朱熹:《诗集传》,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5—36页,第21页。
(11)转引自刘毓庆等著《诗义稽考》,第2册第602页。
(12)“不瑕有害”条:此诗是害其身过为疑,辞者不忍斥言其死也。此明知其身已被祸而不敢言,非直为君讳也。(沈镐:《毛诗传笺异义解》卷二,《续修四库全书》本,第73册第323页。)
(14)崔述:《读风偶识》卷二,《续修四库全书》本,第64册第265页。
(15)胡承珙:《毛诗后笺》卷三,《续修四库全书》本,第67册第116页。
(16)《国风·鄘风·干旄》:“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丝纰之,良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丝组之,良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丝祝之,良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上册第145页。)
(17)(20)黄节:《诗旨纂辞》,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41—142页,第173页。
(18)魏源:《诗古微·卫风答问》,《续修四库全书》本,第77册第167页。
(21)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四,《续修四库全书》本,第68册第407页。
(22)冯浩菲:《历代诗经论说评述》,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66页。
(25)戴震:《毛郑诗考证》,《续修四库全书》本,第63册第553页。
(26)马银琴:《两周诗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38页。
(29)方玉润:《诗经原始》卷三,《续修四库全书》本,第73册第68页。
(30)戴君恩:《读风臆补》,《续修四库全书》本,第58册第182页。
(31)刘毓庆、郭万金:《从文学到经学——先秦两汉诗经学史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