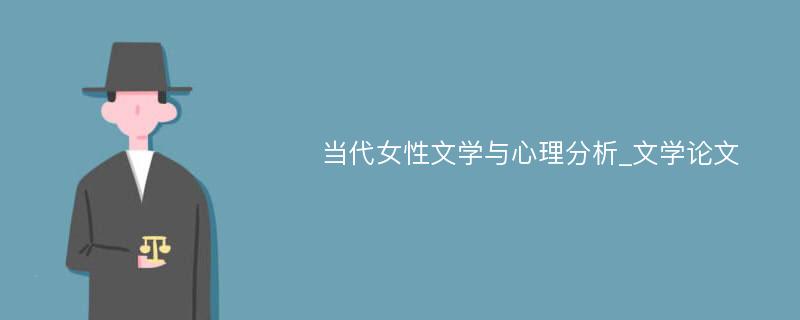
当代女性文学与精神分析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精神分析论文,女性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O-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3)03-0094-07
19世纪末由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在人类文化史上矗立起了一块划时代的丰碑,它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不仅仅是在心理学的领域,而且涉及到了人类文化的各个方面。尤其是文学,几乎在精神分析学刚刚问世之时,文学就成了精神分析这一心理科学的最好的盟友,文学既是精神分析学的主要对象,同时又是精神分析学的最为广阔的用武之地。自从精神分析学介入文学创作以后,文学对于人性以及人的本质的刻画已经获得空前未有的深度,而20世纪中像走马灯似的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的各种现代主义流派,几乎鲜有不以弗洛伊德主义为其理论基石的。中国文学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与西方文学接轨,弗洛伊德主义无疑是较早被介绍进来的一种文化思潮。在现代作家之中,能够比较地道、比较娴熟地运用精神分析学进行人物心理描写的,可谓大有人在。在过,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主流意识形态对西方文化采取严格的封闭政策,弗洛伊德主义在中国文学中销声匿迹竟达30年之久。而精神分析在中国文学中的全面回归,已经是在80年代中期了。
一、女性文学的理论资源
如果比较一下20年代弗洛伊德主义初入中国和80年代弗洛伊德主义大举回归这两个时期中国作家对弗洛伊德的接受情况,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味的现象。在20年代,最早接受精神分析学说并用之于文学创作的都是男性作家,鲁迅在1922年写作《补天》时,即是“取了弗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1](P341)。在稍后的《肥皂》一篇中,他用精神分析学说刻画假道学四铭的形象,写出他的潜意识中的流氓根性,颇受评论的赏识。郭沫若的《残春》等早期小说写梦、写变态心理与儿童性欲,也明显可见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许杰说他“一度注意过福鲁特的所谓新心理学,恰巧在那个时候,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也介绍到了中国来,于是乎文学是苦闷的象征,变态的被压抑的升华,下意识潜入意识的白日的梦,便传染上我的思想,那时的情形,差不多想以性的行动,为一切的中心行动,而去解决、观察一切的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的”[2]。这可以说是当时许多男性作家一种共同的倾向,但同时代的女性作家如冰心、庐隐、陈衡哲、苏雪林、凌叔华、冯沅君等,即使触及了男女爱情题材,也几乎没有谁显示出对弗洛伊德学说的特别兴趣。其中原因在于,一方面刚刚从封建礼教的束缚下解脱出来的新女性们还沉醉在情与爱的幸福之中,对于更深一个层次的性的问题还来不及作出思考和关注:另一方面,真正的职业性的女性书写是在20世纪20年代才开始的,在新文学的草创时期,女性书写的力量还相当地薄弱,经验亦相当地肤浅,女性的书写还没有成熟,因而也就缺乏一种为女性书写寻找理论资源的自觉性。
与20世纪初的情况大不一样的是,80年代以来弗洛伊德主义在中国文学中的复归并且取得辉煌的成绩,首先应该归功于女性作家。王安忆、残雪、陈染、海男、林白等在精神分析方法的使用上,其大胆、细腻、到位的程度远远超出于同时代的男性作家们,而其孜孜不倦的兴趣也不是那些善于追赶新潮的男性作家们所能比肩的。当然,在文学刚刚从“文革”的冰封中解冻时,也有一些较早接近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男性作家曾经试图越过这一被禁锢多年的“雷区”,如王蒙等人对意识流技法的运用,但真正引爆这一“雷区”,使人们对精神分析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刮目相看并且对文坛造成一股强烈的精神分析冲击波的,毋庸置疑乃是王安忆的“三恋”的相继问世。这三部中篇小说虽然还是像传统的小说描写男女之情那样用精神性的“恋”来命名,但其内容已经由写情转换为写欲,写人的本能欲望是怎样地不可遏止,怎样地驱使着人的情感活动与决定着人的行为方式。几乎与之同时的残雪的突如其来,则将精神分析由本能欲望的性驱力拓展到了更为宽广的领域中,她的小说以梦呓为主要方式,喋喋不休地探究非理性这一人类心灵深处的黑暗洞穴,在推崇理性、讲究功利、关注现实、忠于客观的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铁幕上撕开了一个裂口。在残雪的创作中,精神分析已经不止于对性驱力的揭示,而是涉及到了日常行为的各个方面,为中国文学与精神分析的关系开创了一个广阔的前景。就中国文学与精神分析的关系史而言,陈染的意义也许是最为引人瞩目,因为她不仅仅对自己与精神分析的联系津津乐道,不仅仅将性驱力的揭示由异性之恋开掘到了同性之恋与自恋的深度,而且在于她是首先自觉地以一个女性作家的身份与意识来领会、运用精神分析的,从而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第一次真正将精神分析与性别意识结合起来。
在此以一种性别比较的方式来描述20世纪中国文学与精神分析之间关系的发展,其用意就在说明中国的女性书写在曲曲弯弯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之后,终于在性别意识觉醒的同时也找到了自己最为契合的理论资源。首先,弗洛伊德主义是从文化压抑与力比多的转移与升华之一基本结构开始立论的,压抑与升华是弗洛伊德主义的中心词汇之一。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的精神结构分为本我、自我与超我三个层次。本我就是力比多,是人肉体里面总在冲动不安的本能欲望,自我是人的意识,超我则是被本人的意识所认同的一些社会原则、文化理念。本我作为一种肉体中与生俱来的本能欲望,它总在人体内奔突冲撞,具有强烈的毁灭性,而超我为了维护社会与文化的稳定,则不断地通过自我对力比多进行压抑,双方构成一种紧张的情势。力比多在被压抑之后,或者潜入意识的深层,或者升华为一种创造性的力量,而人类文明往往就在这种创造性力量的推动下向前发展。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宗法家族社会体制对妇女的压抑是极其严重的,这不仅是表现在儒家文化的礼教总是将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之类的观念与非礼勿视、非礼勿言之类的教条来压抑禁锢女性的性欲望,而且也表现在典型的父权文化体制用女子无才便是德之类的观念剥夺了中国女性的书写权利与表达欲望。在这双重的剥夺与压抑下,中国历史上的女性很少有人能够突破父权文化的重围,在民族文明的建树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女性书写已经发展到完全可以与男性书写分庭抗礼的时候,女性作家在欣喜于自己的才华展露、在快意于自己的表达欲望能够轻盈地腾升的时候,无疑对弗洛伊德主义的压抑学说会特别感到亲切。
其次,弗洛伊德主义的一个核心观点是潜意识,这一观点是由压抑学说推论而来的。正是由于超我(社会规则、文化理念、传统习惯等)对于本我的压抑,力比多被封闭而没有自己的宣泄渠道,于是固结在精神结构深处,日积月累,在人的精神结构深处就形成了一块黑暗的大陆。这块黑暗大陆有自己的活动形式与自己的活动规律,人的理性、意识都无法进入这块大陆,但它却常在意识放松了警惕的时候,或者人的理性处于暂时的迷惘的时候,突然浮出意识的地表,影响着、制约着人的言说与行为。这块黑暗大陆的发现与分析,是弗洛伊德在人类认知史上建立起来的又一块里程碑,它不仅极大地打击与摧毁了人类从工业革命以来就膨胀起来了的狂妄与傲慢,也极大地促进了人类对自我心理与精神活动的反思意识,从而改变了世界文学的历史进程。世界文学从19世纪末期的整体性的内转倾向,无疑是受到了弗洛伊德主义的牵引。而女性主义文学对潜意识理论的青睐,则是因为这一心理学理论表达了女性的一种文化痛苦。在女性主义看来,人类文明史上种种意识形态本质上都是父权文化的产物,理性是男性的理性,意识也是男性的意识,女性从来就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话语权利与言说方式。而且,女性自身一直是在被男性所言说,即使在偶然的机遇中某一个女性争得了自我表达的权利,也不过是用男性的语言、男性的眼光与男性赋予女性的传统格调来审视自我。因而,从性别差异来看,女性自我应该言说什么,怎样言说,始终是被男性文化所封闭的一块黑暗大陆,属于人类的潜意识领域。正是这一认识,使得“黑色”成了女性主义文学的流行色,而“黑暗大陆”、“黑夜意识”则成了女性主义文学自觉张扬起来的叛逆大旗。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是如此,深受西方女性主义文学影响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更不例外,就如翟永明所说:“黑夜的意识的确唤起了我内心秘藏的激情、异教徒式的叛逆心理、来自黑夜又昭示黑夜的基本本能。”[3](P229)
二、“黑暗大陆”的守梦者
梦是人类文化史上一个从古至今不可穷尽的永恒话题,在人类刚刚学会用文字记载自己的思想的时候,人类就开始了对于梦的探究。古人往往将梦视为神谕,是人之吉凶祸福的一种预兆,所以古代的方术之中也有释梦之说。1900年弗洛伊德出版了他的代表著作《梦的解析》,把释梦这一传统的方术纳入现代心理学的领域之中,赋予了梦以全新的心理学意义。弗洛伊德的贡献在于他首次提出了“梦是愿望的达成”的观点,并且围绕这一观点对梦的改装、梦的运作等作了深入的分析。这一理论对世界文学的影响是怎样估价也不过分的,因为不仅梦本身乃是人的一种生命显现形式,是人之生活一种重要而又神秘的内容,而且弗洛伊德以此对文学与梦的关系作了一个石破天惊的界定:文学是作家的白日梦。弗洛伊德在作这一界定时,将作家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作家像写英雄史诗和悲剧的古代作家一样,接收现成的材料,另一种作家似乎创造他们自己的材料。我们要分析的是后一种”[4](P140)。在中国,就其一般状况而言,女性作家多属于后一种“创造他们自己的材料”的作家,因为身体生理、文化环境与传统习俗等等都注定了女性的生活范围受到很大的限制。生活范围的限制导致女性文学题材兴趣天然地个人化与表达方式天然地私语化倾向,所以,当女性作家用书写的方式来幻想地实现她们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的愿望时,文学是作家的白日梦就成了她们将创作个人化与私语化的最有力的理论依据,而梦也就成了她们创作的主要灵感源泉与象征符码。
女性作家对梦的关注,从新时期一些女性作家所取的作品名字就可见一斑。在80年代初期,张辛欣有一篇著名的小说就题为《我们这个年纪的梦》。这是一个永恒的叙事模式,现实生活是枯燥乏味、呆板琐碎的,而女主人公却正是浪漫如花的年龄,她不甘心被日常生活的琐碎粗俗所淹没,却又不可能从生活的庸庸碌碌中自我超拔出来,于是便在一种虚幻的白日梦中沉迷不已。这个白日梦的起源是她童年时代与一个小男孩的邂逅相遇,朦胧的性意识的觉醒与童年时代的浪漫真纯使她把这个小男孩当作自己的理想偶像,一次又一次地在想象中继续与发展着那个浪漫的故事。可是真实中的故事却是,那个小男孩已经长大,而且恰恰就是自己的顶头上司,现在正在使用着卑劣的手段暗算着自己。白日梦的终于破灭尖锐地揭示了现实情境与心灵世界的南辕北辙。当然,这是一种典型的女性痛苦。男人的心中也许有一个同样浪漫的梦,也许同样有一个邂逅相遇却终生难忘的甜美的小女孩,但男性社会角色的自我定位将使他把这种浪漫的邂逅转化为一种奋发向上搏击人生的力量。而女性的社会角色的传统定位就在日常生活之中,所以她才会那样尖锐地感受到日常生活的琐碎庸碌与内心世界的浪漫幻想在情调品位上是如此地不谐。
如果说张辛欣的白日梦是那个年纪的女孩子们的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欲望表达,尽管最终的梦醒让人不免尴尬,但它毕竟带有一种女性的特有的绯色与温情,那么,宗璞笔下的梦却是漆黑一团。“大野迷茫,浓黑如墨。我在黑夜的原野上行走,再也找不到自己的家。”“我”梦里的人们“每人身后都背着一个圆形的壳,像是蜗牛的壳一样”。虽然在大家都变成蜗牛的时候,有一个秀气的年轻人悲壮地用自己的头颅点燃照亮黑暗的灯火,“但我竟动不了身。圆壳中的黏液粘住了我,我跺脚我挥着手臂,我拼命地挣,挣得精疲力尽,瘫软在地上”(《蜗居》)。这是一个恐怖的梦,荒诞的梦,是“文革”时代民族生存方式的一种变形的反映。它透露出一个有良知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对自我的反省与审思。“这一切都在黑夜里发生过了,既然天已黎明,又何必忌讳讲点儿古话呢?”小说的结尾也显现着解冻初期人们特有的一种乐观主义精神。当然,这是那个时代里一个公共的话题,但它的表现方式无疑是女性的,只有女性才会在那样一种理论资源十分贫乏的年代里,本能地将思想自由与回家的感觉联系起来,本能地去寻找一种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女性文学的性别意识日益明显,日益自觉,女性文学对于梦的描写也就更加弗洛伊德化。陈染无疑是将梦的描写弗洛伊德化最着力的一位。这位曾经以其出色的心理描写与精神分析而参加国际精神科学协会的作家,总是在她的作品中扮演着双重的角色,一个角色是弗洛伊德,一个角色是少女杜拉,她的理智的一半不停地对她的潜意识的一半作着自我剖析,所以,陈染的代表作几乎都是一种典型的精神分析叙事。梦魇(包括白日梦)在这类作品中是经常出现的意象,这里可以《角色累赘》作为范例来分析。这部中篇小说同陈染其他的小说一样,也是用青年女性第一人称叙事,不过,小说中还有一个虚拟的“梦幻人”,“我”虽然搞不懂梦幻人从哪里来,但“她像我的自然生命一样顽固不去,伴随我的生活”。应该说,这个梦幻人就是叙事者的第二自我,也就是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的潜意识。小说在心理发展的关键处安插了两段完整的梦境,一处是用蚕蛹吐茧将自己包裹起来的本事来暗示“我”的不可救药的自我幽闭,而那两个要破除“我”的自我幽闭的人乃是“我”的大学朋友,他们赤身裸体地站在“我”的面前,喻示着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需要赤诚相对,坦荡无私。当然,这个梦的发生也不是空穴来风,它说明“我”在潜意识中间是渴望与人交流与沟通的,只是因为幽闭时间已长,自己已经习惯了这种幽闭状态,所以自己才会对身上的“茧子”视若无睹。相形之下,另一处的梦境却要隐晦得多。“我”梦见一只母猿在树上叫唤,“我”把书扔过去,母猿把书吞吃了,说它已经懂得了人类,它要同人类交换,把一身棕色的皮毛披在“我”的身上,“我”感到非常的轻爽,母猿还说要送给“我”两只小猿,但到手后小猿却变成了两只靴子。在这里书的阅读乃是梦境产生的心理线索,母猿作为“我”的镜像,她对爱情本能的叫唤反衬“我”的性爱分离,而靴子显然对应着故事中“不穿鞋子的隐士”,“我”抱着靴子激动极了,则是“我”内心中对性与爱能够真正结合的一种愿望的达成。
讨论女性作家对梦的描写,人们绝不可能绕过残雪。因为,如果说在其他的女性作家那里,梦不过是一种材料,而在残雪那里,梦似乎已经成了生活的本质。无论小说的意境、氛围、语言、结构等等,一切都是梦一般的混乱无序,梦一般的恐怖狰狞,梦一般的找不到出口,梦一般的鬼鬼祟祟……在其他的女性作家笔下,梦与现实呈现出一种交叉结构,而在残雪那里,梦与现实已浑然一体。残雪的写作也许最能验证弗洛伊德的“文学是作家的白日梦”的理论,她写小说往往是由心灵的梦而进入现实的梦,在她的代表作《黄泥街》中,她曾用一种与她的一贯风格颇不一致的笔调叙说了她梦幻般纠缠的创作冲动。必须指出的是,残雪写梦虽然最能够验证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但残雪的梦魇世界其实已经超越了精神分析的性心理学的阈限,也超越了纯粹的性别界限,而触及了更为深刻也更为广泛的人类问题。正如邓晓芒所言:“残雪从《黄泥街》开始,走向了一个不断挖掘和寻找自己的自我的艰难历程。她有意识地从苦难中,从人心最隐蔽、最阴暗的角落中,从地狱中去发现她的真我。她看出这个真我不是一个可以抓得住的东西,而是一个矛盾,因而是一个在矛盾的推动下不断向内旋入的过程。这个矛盾就是自欺。在人心的最阴暗处,人类所曾经有过的或自以为有过的一切真诚、赤诚、纯真、纯情、童心、赤子之心全都破灭了,只剩下自欺。”知道这是自欺,并且力图发现自己的自欺,“这就是充满在残雪作品中的那种一般人无法看见的最高级、最深刻的幽默”[5](P210)。
三、创伤经验与童年固结
弗洛伊德研究人类的心理发展非常重视人的童年时代。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的心理发展在前20年中虽然是一个逐步的不断的过程,但也可以把它分为婴儿期、童年期与青春期、成年期,每一个时期都有自己的心理发育特征。一般情况下人是稳定地从一个阶段发展到下一个阶段,但如果那一个时期出了问题,发展也会停留,不能登上更高一个阶段。这种问题被弗洛伊德称之为固结,这种固结最容易在童年时代形成,它往往是由童年时代的某种创伤性经验所致,一旦形成,它就潜藏在人的人格发展动力结构之中。如果没有机会解开或宣泄这种固结,它就会对人的人格各个阶段的发展产生意识不到却又确实存在的影响,妨碍着人的心理潜力的充分释放。不过,由于各种固结对人格发展的制约,往往某种固结极有可能导致一种人格的偏至。对于作家而言,一种特殊的固结也许成就他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对于作品中的人物而言,一种独特的固结则有可能产生一种独特的艺术典型。所以,弗洛伊德对创伤经验与童年固结的重视,给世界文学的意义深度带来了极其伟大的理论启示。
童年的固结对每个人都是可能发生的,但比较而言,由于环境的制约与社会角色的传统定位,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怀旧,因而也就更容易意识到这种固结。事实上,许多当代的女性作家经常沉浸到自己的童年回忆中,不厌其烦地咀嚼着童年中的一些故事或印象,为她们现在的成就或个人风格作出浪漫性的解释。确实,当代风头正健的这些女性作家或者出生在50年代,或者出生在60年代,反右与“文革”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横亘在她们的童年生活中,许多不可理喻的荒诞行为使她们迷惑,许多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直接刺入她们的心灵,在她们童年的精神世界中抹上了一重重挥之难去的阴影。这些人格阴影曾是她们精神始终焦虑不安的原因,也很有可能就是促使她们用自我书写来宣泄、表达和确认自我的一种最深层的原因。正如翟永明在她的诗歌宣言《黑夜的意识》一文中所说的:“每个女人都面对自己的深渊”,这个深渊就是“不断泯灭和不断认可的私心痛楚与经验”。
对此,翟永明也曾有过典型的叙说:“七岁的那一年,我经历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死亡洗礼,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我高高地站在幼儿园的土坡上,山脚下就是我居住的家,一排人抬着黑色的灵柩从远处走来,我七岁的心里居然一下就有了不祥的预感,我从高高的山上一口气跑回了家,祖母躺在她的床上,惟一不同的是脸上平放着一张手帕,周围的人告诉我祖母回老家去了,那时的我尚不理解死亡的意义,我甚至没有哭泣,只是关心祖母以后是否还能带我去看戏。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消失,消失的人和消失的事物。”[3](P218)虽然作者说那时她还不懂死亡的意义,但这无疑是一种创伤性经验,因为在那个革命如火如荼的年代里,父母忙于自己的事业,照例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来陪伴自己的儿女,“我”的童年只能同祖母相依相伴。在一个本来就寂寞的童年心灵中,失去祖母就意味着失去了童年的梦,失去了童年可以享受的爱。所以,几十年后,作者还认为这“毕竟是她幼年时代最重要的事”,并且在长诗《称之为一切》中描写了这一场面。后来,翟永明的诗歌经常歌咏死亡的主题,在她的幻想中经常出现这一类的句子:“你是一个不被理解的季节/只有我在死亡的怀中发现隐秘。”“我生来是一只鸟/只死于天空。”这不能不说是因为她童年时代就过早地经受了死亡所带来的心灵创伤,而这一创伤一直固结在精神结构深处。
正是由于许多女性作家本身具有某种固结倾向,因而她们不仅在自己的创作自叙文字中喋喋不休地谈着她们童年时代一些隐秘的创伤性经验,而且对如何用创伤性经验与童年固结来塑造人物性格、剖析人物心理,也充满着浓厚的兴趣。王安忆在《纪实与虚构》中写到了“我”与“我家老房子弄底的一扇窗户”的关系:“那窗户在我幼年记忆里总是黑洞洞的,它长久以来成为我噩梦的根源,我到天黑时就不敢从它底下走过。我那时听来许多恐怖的故事,都提供我培养对这窗户的惧怕心理。我很模糊地认为那里面藏匿有鬼怪和罪人,它给这条狭窄的后弄增添了阴郁的气氛。这是一个相当晦暗的景象,可说是我童年的阴影之一。”至于这个窗户所固结的阴影在“我”性格中所产生的影响,王安忆自己在小说中作了分析:“现在看来,这里面好像有一种暗示。它首先暗示我是处在一个封闭的空间,犹如房间那样的,这是一个孤独的处境,一人面对四壁。其次它暗示这房间与外界有一个联系,这联系是局部的,带有观望性质,而不是那种自由的,可走出走进的联系,所以它决不以门的形式出现,而以窗的形式。窗户这东西看起来很优美,还有些感伤,带有闺阁气,许多评论家都被这迷住了,而无一注意到其间的暗示意味,这种暗示意味和闺阁毫无关系。关于窗户的故事都是发生于我的成长过程中,不只是童年往事,也包括少年往事。但我是一个晚熟的孩子,我身心的成长都要比普通人漫长而迟缓。”之所以“我”的身心成长比普通人漫长与迟缓,当然是因为“窗户”这一阴影在“我”人格中的固结。
陈染小说中的女叙事者“我”在不少的篇章中都表现出一种“恋父”倾向,在《与往事干杯》中,肖濛就是在与尼姑庵中一个邻居大男人的性爱中完成一个小女人的成长过程的,《私人生活》中的拗拗也与自己的老师有过一段虽然不是主动但却并不拒绝的私情,还有《角色累赘》中的黛二小姐,她之所以始终不能在自己甘愿投入的性中进入到爱的层次,就是因为她在少女时代曾经爱上了自己的文学老师——“不穿鞋子的隐士”。与这种情节构设相反的是,在陈染的小说中,女叙事者与父亲的关系往往是非常紧张的,要么父亲都是暴躁的、凶蛮的、孤傲而又自私的,要么就是无父文本,在故事里有一个巨大的父性空缺。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男孩子都有弑父情结,女孩子则有恋父情结。但是在陈染的小说中女叙事者无父可恋,但这样一种情结是必须要获得缓解与宣泄,人格才能获得正常发育,所以,小说中的邻居大男人与老师就都成了父亲的替代品。在一次与记者的对谈中,陈染曾说:“我热爱父亲般的拥有足够的思想和能力覆盖我的男人,这几乎是到目前为止我生命中的一个最为致命的残缺。我就是想要一个我爱恋的父亲!他拥有与我共通的关于人类普遍事物的思考,我只是他主体上的不同性别的延伸,我在他的性别停止的地方,开始继续思考。”[6](P258)将这一段告白同陈染小说中的情节构设联系来看,说恋父与弑父情节的反复出现与陈染潜意识中的童年阴影有关,应该不是无稽之谈。
四、变态心理的艺术聚集
由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理论结构是压抑与转化,其主要的研究对象是梦、潜意识、性本能、性倒错、固结、人格分裂、歇斯底里等问题,所以有的学者认为精神分析学说作为一门变态心理学,比其作为一门科学心理学更有价值。弗洛伊德自己在《梦的解析》一书的第一版序言中也说:“我尝试在本书中描述梦的解析,相信在这么做的时候,我并没有超越神经病理学的范围。因为心理学上的探讨显示梦是许多病态心理现象的第一种,它如歇斯底里性恐惧、强迫性思想、妄想亦是属于此现象。”[7](P1)将精神分析学主要作为一种变态心理学来看待,这是文学家所持的一种普遍态度,也是文学创作与精神分析学发生的一种基本联系。这是因为,一方面,精神分析学说诞生在西方由于大工业文明的高度发达使得社会日趋机械化、标准化,而个体在这种标准化社会自我失落、个性沦丧、精神畸变现象十分突出,因而精神分析学说引起了以研究人为己任的文学家的极大兴趣,另一方面,精神分析学说对变态心理的精微研究,也能够为文学家准确把握人物的变态心理提供理论依据。在中国,由于文学几千年的传统都是十分强调文以载道的巨大使命,而男性既是这种传统的创始者,也是这种传统的承袭者,在安邦立业、治国齐家的理想指引下的男性往往执著于用理性的精神与政治对话,与社会对话,而女性作家由于历史上就没有自由书写的权利,本身不在男性传统的言说与思想的模式之中,所以当她们用文学来反观自身时,她们更容易与研究变态心理的精神分析学发生联系,或者用变态心理的揭示,对压抑女性的男性中心话语方式予以反抗,或者在变态心理的揭示中体现出女性对人性理解的一种独特的角度。
残雪对变态心理的刻画在女性作家中应该说是最为深刻的一位,她的小说创作触及的变态心理类型很多,最突出的一种是窥视欲。《苍老的浮云》中,这种窥视欲就好像瘟疫一样传染了小说中的每一个人。虚汝华几乎是难以遏止地从窥视邻居的秘密中获得乐趣,她的邻居更善无无论做什么事情,总会看到“有一张吃惊的女人的瘦脸在他家隔壁的窗棂间晃了一晃”。“更善无的脑子里浮出一双女人的眼睛,象死水深潭的、阴绿的眼睛。一想到自己狭长的背脊被这双眼睛盯住就觉得受不了。”更善无的妻子慕兰则是一个不动声色、更加高明的窥视者。在这种欲望的刺激下,她甚至别出心裁地在后面的墙上挂了一面镜子,从镜子里可以很方便地侦察邻居的一举一动。在残雪的小说中,人们就是这样既被窥视,也窥视别人,人人在窥视别人的秘密中获得一点惊喜,一种刺激,以此来消磨无聊的时光。每个人都会有一些个人难以与外人道的秘密,守住这点秘密,这是人的基本权利。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家族群居的生活方式使这一基本权利往往被剥夺,人越是没有了保守自己秘密的权利,就越是企望窥视别人的秘密,越是焦虑于失去自己的秘密,就越是企望在窥视中获得一份窃喜。这就是中国家族宗法文化传统压抑下民族成员的一种心理变态,现代女作家张爱玲曾对此有过精彩的描写:“中国人在哪里也躲不了旁观者。上层阶级的女人,若是旧式的,住虽住在深闺里,早上一起身便没有关房门的权利。冬天,棉制的门帘挡住了风,但是门还是大开的,欢迎着阖家大小的调查。清天白日关着门,那是非常不名誉的事。即使在夜晚,门闩上了只消将窗纸一舐,屋里的情形也就一目了然。”[8](P26)残雪的关注点当然不只是传统文化的积淀,相对而言,她更感兴趣的是窥视欲所发生的现实情景。在“文革”那个特定的时代里,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是政治运动的主要方式,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是时代最流行的政治口头禅,灵魂深处闹革命,这是时代最流行的政治口号。在这样一个缺乏理性的时代里,甚至夫妻之间在床头上所发的人生感慨都有可能被当作检举揭发的犯罪材料,人们还有什么空间可以用来保存一点自己的秘密呢?残雪小说中的窥视欲望,就是这个时代的梦魇,是这个时代的政治话语的沉重压抑下所造成的国民心理的变态反应。
如果说残雪的小说在写变态心理方面更多地是显示出人类或民族的某些共同特性,那么,具有强烈的女性主义倾向的女性作家对于变态心理的描写则明确地表现出一种性别挑战的意味。因为在男性中心的社会文化模式中,女性一向被从两个方向进行定位,一个方向是她的顺从性,温良贤淑是她的美德,一个方向是她的“缺乏性”,因为根据弗洛伊德的阉割理论,女性相对于男性的本质是缺乏而不是他性,从小女性看到自己没有阴茎就生出自卑心理,认为自己不如男性,从而埋下顺从的根性。在漫长的父权制度的物质控制与精神浸润下,女性的这两种定位已经在人们的头脑中(也包括大多数的女性)根深蒂固,习以为常。所以,在西方女性主义作家那里,一种妖女写作方式应声而起。这种妖女写作的特征就是,在根深蒂固、习以为常的男性中心文化模式中,没有自己的言说方式的女性有意识地选择了与男性理想恰恰相反的角色定位来言说自己。男性要求女性温柔,她们就选择狂放,男性要求女性贞节,她们就选择纵欲,男性要求女性顺从,她们就选择逃逸。只有这样,女性主义文学才能以一种突出的反抗的语言形式,彻底地颠覆男性中心话语的叙事结构与思维模式。从文学本身所表现的内容来看,这种妖女写作方式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她们要颠覆弗洛伊德的阉割理论,一方面她们又充分地利用了弗洛伊德变态心理研究的理论资源,在作品中着力去描写种种在传统的眼光里被视为变态的心理与行为。
总体看来,中国当代女性主义作家对变态心理的描写主要是集中在性爱方面。这一方面是由于性是女性解构男性文化中心的一个最佳的突破点,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弗洛伊德关于性倒错的理论为这种描写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我们可以把当代女性主义作家对性心理变态的描写内容归纳为下述几个方面:一是施虐与受虐倾向。在施虐方面体现出的是女性对性爱暴力的崇拜,“用爱杀死你”(翟永明《女人·独白》)是这种暴力倾向的典型表达方式,体现出女性由被占有到主动占有的性爱抗争。受虐倾向则是将性爱暴力引向自己,“迎接你,即使遍体绿叶碎为尘泥。/与其枯萎时默默地飘零,/莫如青春时轰轰烈烈给你。”(伊蕾《绿树对暴风雨的迎接》)这种诗歌表达出的是女性对性爱暴力的一种渴望。二是女性的自慰。女性在性别意识觉醒之后,感觉到自己在传统的性爱方式上的屈辱地位,但又无力改变这样一种屈辱状况,更不愿意重复这样一种屈辱的状况,于是产生一种自恋情结,在自我的欣赏与抚摸中达到性爱的满足。林白曾把此种女性的自慰称之为《一个人的战争》,它体现了中国那些觉醒后却无伴侣可行的先锋女性的尴尬与绝望。三是女性的同性恋。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切丽·里吉斯特曾说:“为得到女性主义的认可,文学必须承担下述一种或多种功能:(1)为妇女提供一个论坛,(2)促进达到双性同体,(3)提供角色原型,(4)提倡姐妹情谊,并且在此基础上,(5)增进自觉意识。”[9](P277)这里所说的第4条“提倡姐妹情谊”无疑为女性主义文学描写女性之间的同性恋倾向准备了一个很充足的理由。无论是施虐受虐,还是自慰与同性恋,在弗洛伊德看来都属于性倒错的变态行为,是儿童时期性心理与性生理发育不健全的结果。由于已有专文论及女性主义文学的性爱主题及其描写,在此只是简略述及。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弗洛伊德主义本身是一种典型的男性中心话语,而女性主义作家却不仅对弗洛伊德主义兴趣浓厚,而且在自己的作品中不断地采用弗洛伊德式的语言与思维,这虽然是女性主义文学在颠覆男性中心话语方面所采取的一种不得已的策略,但确实也说明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在寻找与建构自我言说方式方式面的尴尬与困惑。
收稿日期:2003-01-28
标签:文学论文; 精神分析论文; 弗洛伊德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心理学论文; 女性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当代作家论文; 作家论文; 陈染论文; 残雪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