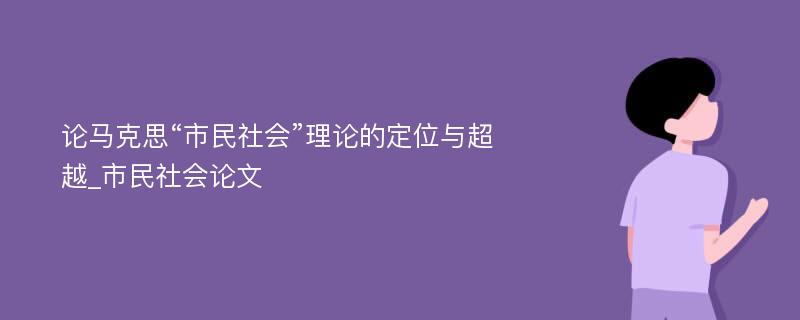
论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定位及超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市民论文,理论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1:C9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4)06-0100-0 5
“国家与社会”关系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学关注的一个主要视域,其中“市民社会”理 论又是该视域的主流话语。但是,“市民社会”概念本身又是歧义纷生的术语,不仅在 不同的学科之间所指的意蕴迥异,而且同一学科内部的不同发展时期其涵义也不一样。 在此情形之下,对涉及“市民社会”理论中的同一问题的探讨,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难 免缺乏共同语言,许多学术争论也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造成学术批评的无的放 矢现象,难以推动学术水平提高,甚至造成思想混乱、观点谬误。因此,对作为社会学 研究之主题的“市民社会”话语,首先必须厘清概念,辨析歧义。
其中,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诸多误读、误用、误判,是上述思想混乱和观点谬误 的一个基本原因。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文·古德纳就曾经批评说:“马克思越是忽略和贬 低市民社会,他就越是在描绘一个没有安全保障的社会主义,一个掌权后只能采取集权 模式的社会主义。”(注:Alvin W.Gouldner:The Two Marxisms—Contradictions and Anomal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y,http://www2.pfeiffer.edu/~lridener/ DSS/Marx/2marxtoc.htm.)古德纳认为马克思忽略和贬低市民社会,并导致后来社会主 义的专制集权。如果以当代社会学中的市民社会理念为参照,古德纳的批评似乎切中要 害。但是,正如我们下文分析将会看到的那样,这样的批评是不得要领的,它是对马克 思市民社会理论的误读和误判,实质是没有搞清楚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的概念及 其学术定位问题。这种情况在国内学术界中也比较普遍。因此,本文试图就市民社会理 论这一基础工作展开论述。文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从概念发展的逻辑着眼,深入 梳理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界定,认为市民社会理论只是马克思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 步,而马克思对市民社会解读的途径是政治经济学而不是社会学,“市民社会”被化约 为“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的其他层面及其独立性没有被纳入研究视野;第二部分从市 民社会历史演绎的视角出发,考察其内涵和外延的拓展过程,表明当代市民社会与马克 思的市民社会两者的规定性根本不同,并提出要在社会学领域获得市民社会理论的真知 灼见,必须从新的时代特点出发,超越马克思。
一
亚里斯多德在历史上最早使用市民社会的概念。但是,很显然,在城邦共同体的背景 之下,这个概念与政治社会、公民社会、文明社会等是同义词。14世纪,欧洲人开始采 用“市民社会”一词,但在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合而为一的背景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其 含义依旧与文明社会等同。公元17世纪至18世纪,在反对专制王权的斗争中,一些契约 论思想家(如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再度拾起市民社会的概念。他们一般都将社会 与市民社会作同义词使用,而且这个社会一般指社会的政治活动即政治社会,与此相对 应的则是自然状态或自然社会。虽然他们已经在理念上把国家与社会分离了,认为社会 先于国家,社会高于国家,但是,从概念上、理论上把二者区分开来,则是由黑格尔完 成的。
黑格尔在其《法哲学原理》(1821年)中全面论述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相互关系。 他认为“市民社会是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阶段”(注:[德]黑格尔:《法哲学 原理》,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97页。)。至此,他明确指出市民社会不同于政治国 家,是一中间地带。在黑格尔那里,市民社会是由私人生活领域及其外部保障(包括警 察、法院)构成的,它包括纯私域(个人)与特殊公域(黑格尔有时称之为特殊的公共利益 如同业公会等)。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作为私人利益而言,它是对家庭这种血缘关 系的否定,但是这种私人利益最终应该整合于国家之中。国家在伦理上包含了家庭和市 民社会,同时又高于它。市民社会是个多元性的载体,包括需求的体系(市场经济)、多 元的体系(自愿组织)、司法的体系(警察和司法机构)三个部分,更具体地说,经济、宗 教、文化、知识活动、政治活动等彼此部分自主的领域共同组成市民社会。萨拜因高度 评价了黑格尔对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区分和分析,他说,“在政治思想史、社会思想史上 ,黑格尔第一次把国家与市民社会作出明确区分,正是这一区分,黑格尔给了近代社会 政治理论以一个全新的转折。”(注:[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 ,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18页。)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继承和批判了 黑格尔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理论。首先,马克思肯定了黑格尔区分国家与市民社 会的研究思路,与此同时,他将黑格尔的国家与市民社会、家庭的关系颠倒了过来,迈 出了创立唯物史观的第一步。马克思说:“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 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即是说,“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 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可是在黑格尔看来却刚好相反,它们是由现实的理念 产生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1页。)对 此,恩格斯曾总结指出:“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出发,结果得出这样一种见解:要 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钥匙,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整个大厦的栋梁’的国 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轻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注:《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9页。)在这里,马克思是借用市民社会的 概念之壳,来表达自己的唯物史观的。这是马克思早期思想的起点:批判继承了黑格尔 的唯心辩证法思想,并开始探索唯物史观。
我们应该注意,马克思一经进入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领域里,就遵循自己的逻辑思 路展开了。他不仅扭转了黑格尔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颠倒的关系,而且把对市民社会的 关注重心从多元性的视域里抽回到经济领域、或者是物质的生活关系中来,这样,他的 任务是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来解剖市民社会并从而寻找全部历史的基础的,而不是从社会 学的视角来解剖市民社会并寻求对市民社会理论的系统理解的。我们且来看看,在历史 唯物主义的观念里,马克思是怎样理解市民社会范畴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提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并且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 是市民社会。”他还说:“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 交往。它包括该阶段上的整个工业生活和整个商业生活。……‘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 在十八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真正的资产阶 级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这一名称(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这个术语既有“资产阶级社会”的意思,也有“市民社会”的意思——引注。)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42页。)显然,市民社会这一概念首先意味着生产关系(即交往形式),但又不仅仅指生产关系,还包括“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以及其他构成上层建筑之基础的各种经济关系。其次,作为用语虽然只是从18世纪才开始使用,并内在含有资产阶级社会组织的含义,但是,正是由于“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发达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比先前的一切社会关系更切近于国家和社会的一般关系,才使得从这对特殊的范畴中抽象出一般范畴成为可能。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遵循从特殊到一般的逻辑思路,并由此通向历史唯物主义之路、“找到整个历史的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说:“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市民社会作了总结性的规定:“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页。)市民社会是“物质的生活关系总和”这一规定性,可以看作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内展开的逻辑思路的最终结论,再进一步,马克思就用更加规范、更具有一般抽象性的术语——社会经济形态——来替代它了。
综上,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研究,是他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起点,同时,他遵循 的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路径。从对市民社会的规定性上看,他认为市民社会乃是“私人 利益的体系”或特殊的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这包括了处在政治国家之外的社会生活一 切领域(实质上是一种“非政治性的社会”)。马克思的“私人利益体系”中包括了经济 关系的领域、社会关系的领域以及文化——意识形态关系的领域。由于在特殊的私人利 益关系的总和中,经济关系的领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所以善于抓住事物实质的马克思 就把它直接称为市民社会。把黑格尔多元化的市民社会界定化约为经济领域,这是马克 思为历史唯物主义打下的基础。市民社会被化约为经济,使之被人们从纯粹的经济层面 加以界定。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的理解就是直接从这里导出 的:一方面,认为市民社会就是指一种生产关系;另一方面,认为市民社会就是资产阶 级社会。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承继西方勃兴的市民社会理论,我国社会学界、政治学界 和法学界的很多研究者在借鉴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时,也是不加区分地直接拿来为自 己的论证服务。但是,物质交往形式毕竟只是市民社会中一个具有实质性意义的领域, 而并非唯一的领域,所以这一界定只是对市民社会实质的说明,而不应被看作是马克思 为“市民社会”所下的完整定义。马克思借助市民社会概念和理论,所要进入的是历史 唯物主义领域,目的是解剖人类发展的规律。因此,他的市民社会是属于历史哲学范畴 的。他对市民社会外延与内涵的化约,在一个高度抽象的研究领域内部是不得不付出的 代价。如果谁因此批评说这是马克思的错误,那么,这肯定是一种强求,毕竟,他要研 究的是历史哲学中的市民社会,而不是社会科学中的市民社会;他要寻求的是人类社会 历史发展规律,而不是资产阶级社会中或者所有历史上市民社会的具体规定性;他遵循 的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路径,而不是现代社会学的路径。市民社会之被化约为经济,是 因为唯有经济才是市民社会的实质,才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因此,马克思 说,他对市民社会的解剖,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来寻求的。在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中,市 民社会的其他层面自然不是马克思关注的重心。看来,错误不在于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 “简单理解”,错误在于后来的研究者对此“简单理解”的“错误运用”。
二
在欧洲历史上,市民社会的出现是与17世纪以后的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紧密联系在一 起的。其时,国家“从一个大社会离开并上升到它自己的层次,在那里,尤其是政治班 底和功能都集中化了。”(注:[美]贾恩弗兰科·波齐:《近代国家的发展》,沈汉译 ,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8页。)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不仅产生了非人格化的公共的国 家权威,而且产生了个人在其中以私人身份追求其各自利益(首先是经济利益)的作为“ 私域”的社会。现代市民社会概念正是对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分离的现实的反映。当 然,这个分离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在社会学、政治学的意义上,国家与市民社会这 一概念随着历史的发展,其含义经历了一个广义社会(市民社会等同于政治国家)、中义 社会(相对于政治社会,基于国家与社会两分法)和狭义社会(即市民社会,基于政府-市 场-市民社会三分法)三个不断演变的过程。(注:高峰:《市民社会:当代中国社会学 研究的主题》,《苏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国家与市民 社会的分离还没有到达十分明显的阶段,社会的分化还不是十分明显,市民社会、公共 领域还处于发生、发展的阶段,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的自主性上面。因此,国家与市民 社会的分化,主要体现在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的分化。出生年代略比马克思早一些的早 期社会学主要代表人物孔德所研究的社会是整体社会,也充分说明了当时的社会分化程 度,还未达到使社会领域引起足够重视乃至被作为独立于政治、经济的一个层面的程度 。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简单理解”,除了上述学科内部逻辑背景之 外,也有其社会历史背景。在马克思之后,随着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的进一步发展,市 民社会进一步从市场经济中分离出来。在当代,对市民社会概念的理解,主要是基于一 种政治-经济-社会三分法的观念。如果说古典市民社会理论一般将市民社会等同于政治 社会、现代市民社会理论,将市民社会看作是与政治社会相对应的一个概念,那么,当 代市民社会理论则主要通过社会和文化来界定市民社会。
这个“最新”界定跟葛兰西和帕森斯有关。“在与马克思主义的和自由主义的化约论 观点的论战中,葛兰西和帕森斯各自分别最早看到,当代社会不仅是通过经济与政治过 程、甚或经济与政治新的或重新的融合而再生的,而且它也是通过法律结构、社会交往 、沟通制度和种种文化形式(所有这些因素都具有相当高度的自主性)之间的互动而再生 的。”(注:简·科恩、安德鲁·阿雷托著:《社会理论与市民社会》,时和兴译,载 于邓正来、[英]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第179页。)安东尼奥·葛兰西,这位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在他的代表作《狱 中札记》中,也像马克思一样,将社会分为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两部分,前者指国家或 政府,后者指各种私人组织或民间社团。与马克思不同的是,他强调的不是市民社会的 经济意义,而是其文化意义。他主要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界定市民社会。认为市民社会是 制定和传播意识形态特别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各种私人的或民间的机构之总称,包括 教会、学校、新闻舆论机关、文化学术团体、工会、政党等。认为市民社会是统治阶级 实现“文化领导权”和革命阶级建立对立的“文化领导权”的主要领域。(注:俞可平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地位》,《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由此, 葛兰西开创了市民社会文化讨论的先河。帕森斯在其代表作《社会体系》一书中,则从 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探讨了社会结构。在他看来,社会结构是具有不同基本功能的、多 层面的次系统所形成的一种“总体社会系统”,包含执行“目的达成”、“适应”、“ 整合”和“模式维护”四项基本功能的完整体系。这个完整体系被划分为四个子系统, 分别对应四项基本功能:“经济系统”执行适应环境的功能;“政治系统”执行目标达 成功能;“社会系统”执行整合功能;“文化系统”执行模式维护功能。(注:[美]乔 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上),邱泽奇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32-3 8页。)葛兰西和帕森斯的学术努力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得当代市民社会理论正式 取得社会学研究的核心地位。
很显然,当代市民社会理念与马克思所说的市民社会有了根本的差别,前者是既区别 于政治系统也区别于经济系统的一个独立的领域,而后者则是指以经济为根本要素的一 个区别于政治系统的领域。这是两个质的规定性根本不同的概念。正如前文阐释所表明 的那样,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是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是一种整体的社会历史 观,其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构成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 原因和基本规律。而作为社会学基本范畴的市民社会概念,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 不是一般的,而是发展的。作为其发展的具体结果,市民社会在当代获得了相对于政治 、经济系统的独立的规定性。虽然,对什么是市民社会,国内外学术界并没有一个统一 的定义,但是,这并不排斥对市民社会的结构要素、特征及价值原则等的基本共识。一 般认为,“市民社会的结构要素和特征主要包括私人领域、志愿性社团、公共领域和社 会运动;其价值原则包括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公开性和开放性、参与性及法治原则。 ”(注:马长山:《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30页。)而在 前一部分的考察中,我们看到,“劳动的分工、交换、生产工具私人所有(这些在黑格 尔思想中已经至关重要)、以及社会划分为有产者与无产者……构成了马克思所想象的 市民社会的核心。”(注:查尔斯·泰勒:《市民社会的模式》,冯青虎译,载于邓正 来、[英]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35-3 6页。)的确,我们从中无法找到现代市民社会那么丰富的内涵。当代市民社会理论不论 从内涵上还是从外延上,都已经大大超越了马克思时代的界限,在这种背景之下,作为 一种社会科学概念的市民社会,必须超越马克思;如果固守,就难免会出现诸如我们在 本文开头所看到的误读、误用和误判现象。
标签:市民社会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国家与社会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社会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社会学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经济学论文; 政治学论文; 哲学家论文; 葛兰西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