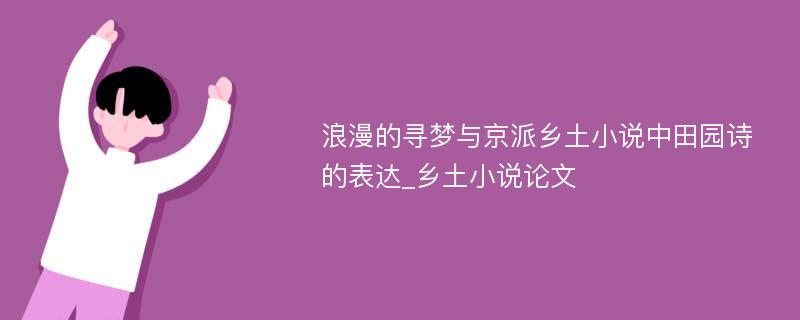
京派乡土小说的浪漫寻梦与田园诗抒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京派论文,田园诗论文,乡土论文,寻梦论文,浪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7)02-0132-06
京派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独特创作个性和美学风格的小说流派。20世纪20年代中期显露其风格雏形,30年代中期进入鼎盛时期,40年代因战乱而风流云散,但其影响至今绵延不绝。以废名、沈从文、凌叔华、萧乾、芦焚、林徽因、李健吾、何其芳、李广田等为代表的京派作家,是一个疏离政治的自由主义作家群体。他们站在中国古今文化与中外文化的交汇点上,以文化重造的保守主义姿态,规避激进的时代主流话语,高蹈于现实功利之上;以自身不同流俗的生命感悟与取向别致的现代意识,从容平和地融会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审美特质;以“和谐、圆融、静美的境地”为自己的美学理想,创造出具有写意特征的独具美感的抒情小说文体,在中国现代小说艺术中独树一帜。综观京派作家的全部小说创作中,虽然其都市小说的成就不容忽视,但乡土小说才是寄寓京派作家文化态度、生命理想与艺术追求的“神庙”。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作家大都以“乡下人”自居,他们虽然侨寓都市,但其小说主要是以自己的乡村经验积存为依托,以民间风土为灵地,在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的浪漫绘制中,构筑抵御现代工业文明进击的梦中桃源。他们偏于古典审美的“田园牧歌”风格的浪漫乡土小说艺术探索,其意义是在“启蒙的文学”之外,赓续虽不彰显却意义深远的“文学的启蒙”。
在中国现代诸多小说流派中,京派是最富有乡村情感的作家群体。他们侨寓于城市,却“在”而不属于其置身的都会,淡淡哀愁的心灵不无矛盾地漂泊在现代都市与古朴的乡村之间,大都毫不掩饰自己对城市文化的隔膜和厌恶,或如萧乾那样把城市体验为“狭窄”而“阴沉”的所在,或如芦焚那样把都市视作“毁人炉”。其中,沈从文对城市的解析与批判或许最有代表性,他认为:“城市中人生活太匆忙,太杂乱,耳朵眼睛接触声音光色过分疲劳,加之多睡眠不足,营养不足,虽俨然事事神经异常尖锐敏感,其实除了色欲意识和个人得失外,别的感觉官能都有点麻木了。这并非你们(城市人)的过失,只是你们的不幸,造成你们不幸的是这一个现代社会。”[1] (P230)都市空间的物质化与欲望化,使都市人难以达到“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 (P231)。因此,他们在批判现代城市文明的同时,将精神寻梦的目光转向他们曾遗落在身后的乡村。沈从文始终以“乡下人”自居,废名也一直以乡村生活为其精神归宿;萧乾则在《给自己的信》中说,“虽然你是地道的都市产物,我明白你的梦,你的想望却都寄在乡野”[2] (P274)。芦焚亦在自我解剖中辨识自己的文化身份与精神气质:“我是从乡下来的人,说来可怜,除却一点泥土气息,带到身上的亦真可谓空空如也。”[3] (P49)在这里,城市与乡村,已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地域概念或社区概念,而是文化概念;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分别是现代工业文明与传统农耕文明的代表。“城市人”与“乡下人”,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社会身份,更主要的是一种文化身份。他们对“乡下人”的自认,其实是他们对自我文化身份的选择与辨识,同时也标示了他们对宗法乡村所象征的传统文化的宽容和认同心态。正是出于这种内蕴复杂的文化认同与价值选择,他们在贬抑城市的同时,极力美化乡村,挖掘并张扬乡土中国的人性美和人情美。例如,在废名的《竹林的故事》、《菱荡》和《桥》等作品中,“充满了一切农村寂静的美。差不多每篇都可以看得到一个我们所熟悉的农民,在一个我们所生长的乡村,如我们同样生活过来那样活到那片土地上。不但那农村少女动人清朗的笑声,那聪明的姿态,小小的一条河,一株孤零零长在菜园一角的葵树,我们可以从作品中接近,就是那略带牛粪气味与略带稻草气味的乡村空气,也是仿佛把书拿来就可以嗅出的。”[4] (P97)在《边城》、《长河》和《萧萧》等作品中,沈从文构筑了一个化外的“湘西世界”。现实中的湘西,因为交通闭塞,远离沿海,直到清末民初还处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根本感受不到新世纪传入中国的现代文明气息。这与17、18世纪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所设想的“自然状态”有着相通之处。但是,沈从文始终把这种状态下的人性看作人类精神文明最完美的体现,是重造民族道德理想模式的最佳选择。在这块德性化和理想化的古老土地上,人们完全凭借他们的一套道德准则与他人、自然和社会和谐相处,没有现代社会中那种高度的紧张、自我的膨胀与心灵的焦虑,处处流淌的是人情、亲情和古朴淳厚的民风,人性在这里被充分浪漫化了。在这些与都市文明截然相反的乡村图景里,废名、沈从文、林徽因、芦焚等京派作家以自己的文化寻梦和生命信仰苦苦支撑起人性美与人性善的“神庙”。
京派乡土小说着力表现自然状态下人性庄严、优美的形式,这种生命形式虽然大都如废名、沈从文的乡土小说那样被安置在未被现代文明所侵蚀的偏远乡村,但在萧乾、凌叔华、汪曾祺等作家的部分乡土小说中,也有被安置在喧哗都市的。在高度物质化与欲望化的现代都市里,那些进了城的“乡下人”,依旧保持着在宗法乡村铸就的人性之“真”与“善”,成为与现代都市文明相碰撞的“城市异乡者”。正是这些“城市异乡者”的出现,使京派乡土小说有了“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另一种别样人生境界与叙事形态。
萧乾自称是一个“不带地图的旅人”,他以乡村人文精神的价值取向来反观都市生活与都市人生。萧乾自述说:“《篱下》企图以乡下人衬托出都市生活。虽然你是地道的都市产物,我明白你的梦,你的想望却都寄在乡野。”[2] (P274)在这种倾向支配下,他以自己早年的小说创作,加入到京派小说的文化形态之中。在萧乾大多数的都市题材小说中,《邓山东》、《雨夕》等作品与“乡下人”和“乡村”直接相关,可视作京派乡土小说的另一种形态。萧乾说:“我的小说是以北平为背影的,几乎都写北平城里的生活,只有一篇《雨夕》是写农村……比起他们来,我的创作似乎更注重表现人生,暴露社会黑暗。[5] 这是萧乾在“文化大革命”后说的话,他把《雨夕》放进了“为人生”的社会批判系列,虽然不无道理,但更多的是作者劫后余生的自我保护策略。小说中那个可怜的乡村女人,被丈夫遗弃后变疯,在外面又遭人强暴,如此不幸的女人连下雨天在磨棚中躲雨也遭人驱赶。这确有“暴露”的意味,却并不声嘶力竭,而是让城里来的孩子用与成人迥异而接近人类纯真本相、不带杂质的是非观,来判断和同情一个疯妇。在孩童天真的目光中折射出人生的忧患和世态的炎凉,在清澈中渗透着淡淡的苦涩。《邓山东》写的是“城市异乡者”的故事,小说中的邓山东是一个流散到都市的军人,以挑担贩卖杂货糖食谋生。他有着乡里汉子的粗犷,却出人意外地知道了孩子们的趣味,他的担子上也装满了孩子们喜欢的东西:“有五彩的印画,有水里点灯的戏法,有吓人一跳的摔炮,甚至还有往人背上拍王八用的装有白粉的手包……凡是足以使我们小小心脏蹦跳的,他几乎无一不有!”他更懂得孩子们对慈爱、尊重与信任的需要,他以自己诙谐、豪爽、体贴的性格,充当儿童世界的和事佬,甘愿代学生挨校方的无理罚打。他虽然经历过战争与流血,但不改耿直仗义的本色;虽然饱经沧桑,但依旧满是童心童趣。这其实就是人性的“真”与“善”,是对传统美德的皈依。简言之,萧乾书写乡村与“城市异乡者”的悲境,注重的主要不是对现实的社会关系与阶级关系的解剖,而是“世道人心”,是传统文化心理积淀的惰性,其作品因此表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和可贵的人性深度。
凌叔华的作品数量并不多,但她注意发掘自身的女性经验和文化优长,颇为专注地叙述女性故事,即使没有后来的那些作品,仅薄薄一册《花之寺》,即可奠定她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地位。凌叔华的小说在用温婉细密的笔调写“旧家庭中温顺的女性”[6] (P250)和新女性们的家庭生活的同时,也以充满人道主义悲悯情怀的目光,注视进城打工谋生的乡下女性,书写这些“城市异乡者”朴素的情感与良善的人性,《杨妈》、《奶妈》就是这样的作品。前者写穷苦佣人杨妈唯一的儿子在家不务正业,跑出去当兵又杳无音信,她每天晚上为儿子做棉衣,最后抱着棉衣踏上寻找儿子的渺茫之路。小说就这样在“劳动妇女的善良灵魂”的刻画中,“写出一种混合着愚昧与伟大的执著的母爱”[7] (P221)。后者写一位贫穷母亲为挣钱养家,无奈丢下自己三个月的婴孩去做富家少爷的奶妈,却因此而不幸夭折了自己的爱子。母爱,就这样因为贫穷而夹杂了愚昧,也因为自私地掠夺他人的母爱,而体现了残酷。凌叔华书写母爱的小说,显然与冰心、冯沅君、苏雪林等歌颂母爱的小说不同,她并非仅仅着眼于母爱的伟大和神圣,而是以女性的敏锐和体验写出了她眼中的母爱,使人性、女性与母性在社会、文化、贫富等的纠结中,显出全部的复杂,并带给读者沉重的思索。她的文字依旧温婉和美,却能在她所特有的清逸风格和细致的敏感中,同萧乾一样表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和可贵的人性深度。
汪曾祺被誉为“京派最后一个作家”[7] (P225)。《邂逅集》则可看作是其早期小说创作的主要成就。多年后,汪曾祺在其短篇小说选自序里说:“我以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我的小说里有些风俗画成分,是很自然的。但是不能为写风俗而写风俗。作为小说,写风俗是为了写人。”[8] (P219)在他早期的乡土小说中,这一创作原则已得到贯彻。《鸡鸭名家》以特有的“城乡结合”的方式,细致生动地描绘了故乡养鸡、养鸭的生产、生活场景和风俗民情,刻画了余老五、陆长庚两位有庄周“庖丁”神韵的风俗人物。余老五是城里孵小鸡的炕房师傅,小说把他照蛋、下炕、上床的孵鸡的繁复过程和技术,描写得出神入化。陆长庚诨号陆鸭,是乡里养鸭子的好把手,小说把陆鸭发出各种声音,呼唤逃散在芦苇丛中的三百余只鸭子集聚于岸边的情景,叙写得有声有色。这种风俗描写,即使小说充溢着微苦而又温馨的日常生活气息,又为塑造余、陆两位风俗人物营造出一种淡雅而朦胧的氛围,而作者在这两个“城乡巧人”身上,赋予了一种特别的生命“神性”,使作品在平静叙述中涌荡着魅人的浪漫情趣。
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社会是正在试图向“现代”迈进的乡土中国,但总体上还是前现代性的。正因如此,无论是从社会文明发展还是文学自身发展的角度,“反现代性”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奢侈。废名、沈从文、芦焚、萧乾、凌叔华、汪曾祺等京派小说作家对以城市为象征的现代工业文明和以乡村为象征的传统农耕文明的文化心态,显然是十分复杂的。在他们的乡土小说创作中,无论是写乡村还是写“城市异乡者”,都把原本并不美好的前现代农耕文明及“乡下人”理想化,挖掘乡土中国的人性美和人情美,试图以传统文化的伦理力量去对抗和融化西方文明及现代都市文明,但这并非表明他们就是彻底的“反现代性”。如果说鲁迅及其“人生派”和“乡土写实流派”的乡土小说面临着两种文化情感困惑的选择的话,那么,废名、沈从文等京派作家也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选择。他们一方面鄙视“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侵袭,另一方面又渴求现代文化,当他们拿起笔来写乡土小说时,其心境表现得异常复杂。
废名、沈从文等京派作家的乡土小说流露出的“乡恋”(而非“乡愁”)情感和怀乡情绪,显得“过分”浓郁。他们对“风俗画”、“风情画”和“风景画”如醉如痴的描绘,很容易使人感到作家对传统文化规范的认同和对一种静态文化失落的哀婉,而忽略了他们的乡土小说中隐含着的另一种情感,即对现代文化的某种无可奈何的认同。沈从文曾说过这样愤激的话:“这种时代风气,说来不应当使人如何惊奇。王羲之、索靖书翰的高雅,韩斡、张萱画幅的精妙,华丽的锦绣,名贵的瓷器,虽为这个民族由于一大堆日子所积累而产生的最难得的成绩,假若它并不适宜于作这个民族目前生存的工具,过分注意它反而有害,那么,丢掉它,也正是必需的事。实在说来,这个民族如今就正似乎由于过去文化所拘束,故弄得那么懦弱无力的。这个民族的恶德,如自大、骄矜,以及懒惰,私心,浅见,无能,就似乎莫不因为保有了过去文化遗产过多所致。这里是一堆古人吃饭游乐的用具,那里又是一堆古人思索辩难的工具,因此我们多数活人,把‘如何方可以活下去的方法’也就完全忘掉了。明白了那些古典的名贵的庄严,救不了目前四万万人的活命,为了生存,为了作者感到了自己与自己身后在这块地面还得继续活下去的人,如何方能够活下去那一些欲望,使文学贴近一般人生,在一个俨然‘俗气’的情形中发展;然而这俗气也就正是所谓生气,文学中有它,无论如何总比没有它好一些!”[9] (P330)因而,我们应当看到沈从文在文化选择上的两难情感,以及他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上的二律悖反现象。《边城》、《萧萧》、《丈夫》等乡土小说,表面上是对静态传统文化的讴歌和礼赞,甚至充满着古典浪漫的情感色彩,但却不能忽视其中所包孕的“反文化”倾向。沈从文正是通过对文化的消解来达到反封建的目的,甩掉文化造成的人的困顿,让人走向自然,这才是作者的本意。所以,我们绝不能将他对一种原始生命意识的认同和张扬与现代文化的渴求对立起来看待。恰恰相反,他正是想通过这种生命形式的肯定来达到对现代文化的某种认同,无论这种认同带有多少不由自主和多少无可奈何的情感。面对双重的文化负荷,沈从文及“京派”乡土小说显示出他们特别的文化意义:在反对封建文化上,它是与“五四”新文化站在同一战线上,以人道主义为武器与传统文化搏斗;在“文化制约人类”、扼杀人性和自然的前提下,它又是反一切文化的压迫,包括现代文化对于人与自然的物质和精神的虐杀。因此,他们所面临着的是对双重文化压迫的抗争。简言之,京派作家的乡土小说创作有“恋乡”和“恋旧”的倾向,但并未因此而迷失自己。在与“新”和“旧”的双重文化抗争中,虽然心态无比复杂,但却始终保持着较为清醒的状态,在审视的态度中含有批判的意识,写尽了人生之“常”与“变”。
沈从文曾怅然叹息:“我还得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赞颂。在充满古典庄严与雅致的诗歌失去光辉的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情诗。”[10] (P294、266)这其实是沈从文对自己的创作自律,也是京派小说作家共同的艺术追求。他们的乡土小说在这种美学风格的追求中就成了“充满古典庄严与雅致的诗歌”,也就是偏于古典审美趣味的“田园牧歌”。德国哲学家和美学家叔本华曾制订了一张诗歌体制级别表,将各种基本文体按等级分类,依次是:歌谣,田园诗,长篇小说,史诗和戏剧。叔本华这种分类的依据,是各种文体表现主观理想的程度。叔本华认为,戏剧最为客观,而田园诗则最接近纯诗,最为主观。但是,在中外诗歌理论中,田园诗最主要的特征,是因为不满现实而产生的对古代单纯简朴生活的幻想,是对现实的回避态度,并不是主观理想。在艺术上,田园牧歌则强调抒情性手法的运用,具有悠长、舒缓、优美的特点。偏于古典审美趣味的田园牧歌风格的京派乡土小说,在文体上的一个重要特征,正如沈从文所说的那样,把小说当诗来写,促进了小说与诗、小说与散文的融合与沟通,强化了作家的主观情绪,从而发展了“五四”以来的抒情小说体式。
京派乡土小说作为抒情小说的特征之一,就是淡化传统小说以情节为中心的结构模式。废名曾宣称:“无论是长篇或短篇我一律是没有多大的故事的,所以要读故事的人尽可以掉头而不顾。”[11] 沈从文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照一般说法,短篇小说的必要条件,所谓‘事物的中心’,‘人物的中心’,‘提高’或‘拉紧’我全没有顾全到。也像是有意这样做。”[12] (P90)汪曾祺则直言:“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8] (P462)他们淡化小说情节使其诗化和散文化的艺术途径是多样的,或侧重主观的意念、情感的把握,做做“情绪的体操”[13] (P40),把小说创作视为生命的追求和生命观的自然流露;或抛开小说情节的连续性,并置非连续性的叙事单元,而“对一个因果关系的线性结构的抛弃至少导向了一个有机的生活概念,在这种生活里,与其说事件是一条线上可辨明的点,倒不如说它们是一个经验的无缝网络中的任意的(而且常常是同时发生的)偶发事变”[14] (P166)。京派乡土小说所并置的非连续性叙事单元,有不同的形象系列、情节片断、场景和细节。而其中最突出的,是并置在京派乡土小说中的大量的自然风景和民俗风情。
民俗风情是京派乡土小说田园牧歌风格构成的基质。民俗风情所体现的相对独立的民间文化是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经过创造、继承、衍化后自然而然形成的,大都体现了民间对世界的理解,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现实的生存策略,传达了民间社会日常生活中的文化趣味,也就成了京派乡土小说作家用以传达文化理想与文学理想的叙事凭借。废名为了构筑他的“梦乡”,自述《桥》“全部的努力都放在当地的风土人物的描写上,对故事本身的展开是完全忽略的”[15]。《桥》里,有史家奶奶为小林与琴子两个未成年人的婚事奔走,还有“唱命画”、“送路灯”、“放猖”等乡村传统习俗;《竹林的故事》、《我的邻居》和《半年》等作品里,有端午节扎艾、吃粽子和鸡蛋,有大年三十夜围炉守岁、讲故事,有正月里游龙灯、赛龙灯;《鹤鸽》里,有出嫁的姑娘在枕头上绣上两个“柿子同如意”,表示“事事如意”;《阿妹》里,有“祠堂做雷公公,打鼓放炮”;《河上柳》里,有“清明时节,家家插柳”等。沈从文更是在其乡土小说中娓娓叙述龙舟竞渡、月夜渔猎、村寨聚会、山间野合、橹歌声声、情歌阵阵的湘西民间风习;还有乡间仁爱友善的淳朴民风,跋涉险滩激流、搏击虎豹豺狼的坚韧顽强的生命活力,甚至还有那大胆热烈、充满野趣的爱情生活方式。京派乡土小说中对民俗风情的描绘,提高了中国小说的造境功能,丰富了中国小说的文化蕴涵,同时也是中国小说人物性格的形成之文化背景或成因。
京派小说作家大都很注重绘制“风景画”,把自然背景与人物巧妙地融合为一,传达出抒情的格调。他们营造的亦是“世外桃源”的美境(除了田涛的乡土小说格调有所殊异外),有些大段的景物描写可谓精彩纷呈。例如“京派作家”中的凌叔华,她原是位画家,其乡土小说颇得风景画之神韵,虽然她并不在外在视觉上注重风景画描述,但其小说的“内心视觉”颇具元明山水画之神韵。尤为值得称道的是萧乾小说的写景更有诗一般的情韵,在他的小说《俘虏》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七月的黄昏。秋在孩子的心坎上点了一盏盏小莹灯,插上蝙蝠的翅膀,
配上金钟儿的音乐。蝉唱完了一天的歌,把静黑的天空交托给避了一天暑的
蝙蝠,游水似地,任它们在黑暗之流里起伏地飘泳。萤火虫点了那把钻向梦
境的火炬,不辞劳苦地拜访各角落的孩子们。把他们逗得抬起了头,拍起手,
舞蹈起来。
凌叔华和萧乾虽不是“京派小说”的中坚乡土小说作家,但这种把散文和诗的写法植入小说的做法,却成为其共同特征,写景成为他们美学思想的外在显露。最末一位“京派小说”作家,自诩为沈从文学生的汪曾祺在20世纪80年代仍坚持着小说这一做法:“散文诗和小说的分界处只有一道篱笆,并无墙壁(阿左林和废名的某些小说实际上是散文诗)。我一直以为短篇小说应该有一点散文诗的成分。”[8] (P324)废名和沈从文的乡土小说的鲜明特征就是将小说诗化及散文化,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注重风景画(景物描写)的象征性铺陈。
京派乡土小说还注意在风俗画与风景画的描绘中,采用象征暗示的方法,使风俗画与风景画转换为小说中深邃幽远的意象。原型批评家弗莱把原型定义为“典型的即反复出现的意象”,它“把一首诗同别的诗联系起来,从而有助于把我们的文学经验统一成一个整体”[16] (P62)。在废名的乡土小说中,“桃园”、“翠竹”、“桥”、“树阴”,沈从文乡土小说中的“菊花”、“橘园”、“水”、“碾房”,芦焚的乡土小说中的“果园城”、“古塔”等,既是风俗画与风景画,又是反复出现的意象。这些意象都具有很强的象征性,其象征意味又是多重的。一方面,这些意象中的大多数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相连,在它们所负载的文化意义里已经积淀了民族传统的文化价值体系和对之进行接受的文化心理。譬如,“翠竹”这一意象早已衍生出多层文化含义,它既可以象征一种清静淡和的人生态度,又可以喻示傲世独立的人格信仰,同时也预先规定了后来者读解这一意象时的审美体验和情感体验;另一方面,京派小说作家在营构这些意象时,赋予了自己的精神取向与价值选择。譬如,废名《竹林的故事》就把“竹林”这一意象同三姑娘联系起来,以竹的品性象征三姑娘纯真、善良的天性。而“树阴”这个意象则是废名对现实感到不满和失意,由现实退入内心,禅思生命的精神孤旅的象征。简言之,京派乡土小说中的风俗画与风景画,特别是那些反复出现的风俗画与风景画,大都被建构为有象征意味的抒情性意象,在与传统文化和作者自己的文化诉求建立关联的同时,拉开了与现实生活的距离,创造了一个朦胧美的艺术世界。
废名曾说:“对历史上屈原、杜甫的传统都是看不见了,我最后躲起来写小说乃很像古代陶潜、李商隐写诗。”[17] (P393)把小说当诗来写,差不多是京派小说家共同的艺术追求。中国的诗骚传统,不仅使京派小说家都讲求小说与诗歌的结合,注重对“情调”、“意境”、“象征”方式的把握,而且也为这种小说的诗性追求提供了资源。废名小说中的茅舍、桃园、竹子、庙塔等几种意象的设置,在陶潜、李商隐的诗文中,都可以寻找到源头。萧乾的篱下、矮檐意象,芦焚的废园、荒村意象,都可以在《诗经》、《楚辞》以及唐诗宋词中寻觅到它们的踪迹。在注意京派乡土小说借用中国传统诗文资源的同时,还应看到京派小说家对传统的改造与创新。实际上,不少评论家都注意到,沈从文的《边城》颇有唐诗的意境。1934年《太白》第1卷第7期对《边城》即有如下评价:“文章能融化唐诗意境而得到可喜成功。其中铺叙故事,刻镂人物,皆优美如诗,不愧为精心结构之作,亦今年出版界一重要收获也。”融化唐诗意境就是改造与创新,这使京派乡土小说在承续传统的同时,又具备鲜明的时代与地域特征。在京派乡土小说的文化源流中,显然还有外来文化资源,这里就不一一置论了。如废名所说:“在艺术上我吸收了外国文学的一些长处,又变化了中国古典文学的诗……我从外国文学学会了写小说,我爱好美丽的祖国语言,这算是我的经验。”[17] (P395)其实,这也可看作是京派乡土小说作家的共同经验。
金介甫曾言,沈从文和“京派”文人在现代文学中的悲剧性“命运”,也许正是其“价值”之所在。他指出:“他们在创作中崇奉的道德是,作品要出自个人心声。它不为‘关系’所左右,而要成为抒写自我完善的工具”,他们这是在“另走新路”,是通过“为自由歌唱,将自己的梦想与挫折作为‘原料’来建设新文学”[18] (P77、78)。此论说当是精辟的。京派乡土小说家寄希望于重振民族理想和人性信仰,要求在文化和道德的层面上进行变革,在当时中国社会风云激荡、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的时局下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也是行不通的。京派乡土小说家最高的精神指向就是充满爱、美和自由的理想人生状态,这也有着明显的偏颇和不足。前现代性的农业文明让位于现代工业文明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人性的变异在某种程度上讲,也许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一种现象,他们所向往的理想社会恰恰与人类社会进程的现代化、都市化相悖,这就是京派小说的孤独和悲剧所在。他们的文化理想与文学理想虽然注定是寂寞的,但是,如果不是怀抱过分偏激的历史进步意识论或激进的功利论,就可以认识到,他们的努力不是没有意义的。
标签:乡土小说论文; 沈从文论文; 小说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竹林的故事论文; 风俗文化论文; 象征手法论文; 读书论文; 萧乾论文; 边城论文; 人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