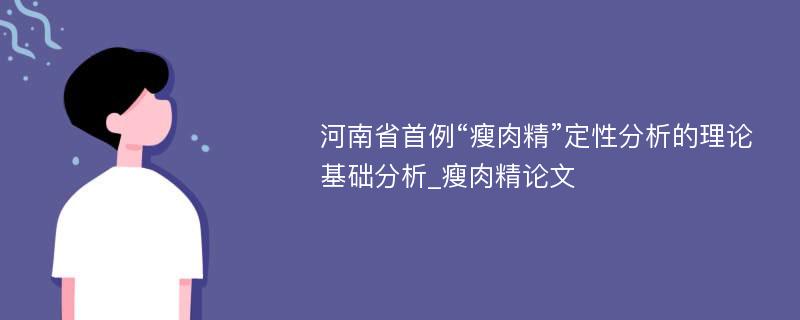
河南首起“瘦肉精”案件定性的理论根据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河南论文,案件论文,理论论文,瘦肉精论文,首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7年年初,曾在湖北某制药厂任职的刘襄与奚中杰约定共同投资,研制、生产、销售“瘦肉精”用于生猪饲养。随后,肖兵、陈玉伟也参与其中负责销售。刘襄之妻刘鸿林,从事过多年的制药厂化验员职业,其明知施用“瘦肉精”的危害性,仍协助刘襄进行了研制、生产、销售等活动。直至2011年3月,刘襄等5人共研制、生产、销售“瘦肉精”2700余公斤,非法获利250万余元。2011年7月25日,焦作中院一审认定刘襄等5人共同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主犯刘襄被判处死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而奚中杰等4人分别被判处9年有期徒刑至无期徒刑。8月10日,河南高院二审裁定维持原判。笔者认为,刘襄等人共同研制、生产、销售“瘦肉精”行为主要涉及非法经营罪,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四罪名,法院最终采纳“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性而排除其他三罪,这足以表明:刘襄等人研制、生产、销售“瘦肉精”并不符合其他三罪的构成要件,而只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才是最符合其行为的罪名。本篇主要探析对刘襄等人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性的理论根据。
一、刘襄案件能否定性为非法经营罪
刘襄“瘦肉精”案件犯罪成员共5人。在案件的侦查阶段,其中3人是以涉嫌“非法经营罪”而先被刑事拘留、后被逮捕的,另1人是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刑事拘留、逮捕,还有1人则是以涉嫌“非法经营罪”而先刑事拘留,后又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逮捕的。直至提起公诉与审判阶段后,整个案件才改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可见对刘襄“瘦肉精”案件的定性意见分歧很大。2011年7月25日,焦作中院在庭审中争议的焦点,就主要涉及是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还是定“非法经营罪”。一审判决后,5名被告人均不服判决而提起上诉,上诉理由主要还是定性问题,即认为不应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应定“非法经营罪”。①
刘襄案件最终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其理论根据主要在于:在犯罪构成的客观行为方式上,刘襄案件是研发、生产、销售“瘦肉精”行为,这既不符合《刑法》第225条非法经营罪的客观构成要件,也不符合原有司法解释中以非法经营罪定罪的有关规定。具体理由分述如下:
1.不符合非法经营罪的客观构成要件。根据《刑法修正案(七)》修正的《刑法》第225条规定,非法经营罪的客观行为方式主要包括四种:一是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二是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三是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或者保险业务的;四是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其中前三种是具体的“非法经营行为”,而后一种“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是抽象的、概括的“非法经营行为”,它带有内容不确定、范围较为广泛与数量可能更多等特性。这一概括性规定是为了弥补对非法经营行为的列举之疏漏而设的,又称之为“堵截条款”。对于“其他”不能作任意解释,防止出现“口袋罪”扩大化趋势。
非法经营罪在客观行为方式上主要表现为违反有关监督管理法规,未经许可经营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以及从事其他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虽然生产、销售“瘦肉精”也可以列入非法经营范围内的“物品”,但对研发“瘦肉精”行为却无法予以制裁。在研发、生产、销售“瘦肉精”三行为中,研发具有首要的作用。如果从研发、生产、销售三行为能成立吸收犯的角度而言,研发是其中最重的行为,生产、销售相对研发而言则是比较轻的行为,因此,研发能够吸收生产、销售成立吸收犯,却非生产、销售吸收研发而成立吸收犯。据此,在刘襄等人具有研发、生产、销售“瘦肉精”三行为中,即使较轻的生产、销售“瘦肉精”行为可以非法经营罪论处,但无法对较重的研发“瘦肉精”行为也定为非法经营罪。这也就是刘襄案件最终没有采用以非法经营罪定性的根本原因。
2.不符合原有司法解释中以非法经营罪定罪的有关规定。笔者认为,定罪与量刑两者具有逻辑上的先后性与因果性,必须是定罪在前而量刑在后。换言之,法定刑的轻重只有在确定犯罪性质之后才能作出裁量;否则,犯罪性质不能确定,法定刑的轻重也就成了空谈。在刘襄等人的“瘦肉精”案件中,确实存在非法经营罪的法定刑相比“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法定刑轻的问题。但是,对刘襄等人的研发、生产、销售“瘦肉精”不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而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其关键理由在于:刘襄等人研发、生产、销售“瘦肉精”的行为并非完全符合两高司法解释中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的有关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发的《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两高《办理“瘦肉精”案件应用法律解释》)第1条与第2条分别规定了两种生产、销售“瘦肉精”行为可以定性为非法经营罪:一是“未取得药品生产、经营许可证件和批准文号,非法生产、销售盐酸克仑特罗等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品,扰乱药品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可以依照《刑法》第225条第(1)项“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二是“在生产、销售的饲料中添加盐酸克仑特罗等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品,或者销售明知是添加有该类药品的饲料,情节严重的”行为,可以依照《刑法》第225条第(4)项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规定,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
以笔者所见,两高司法解释所确定的两种生产、销售“瘦肉精”行为可以定性为非法经营罪,是在刑法条款中没有直接可以适用罪名的前提下,而采用“比附援引式”的类推方式将两种生产、销售“瘦肉精”行为解释为“非法经营罪”的。其实,这两种生产、销售“瘦肉精”行为与非法经营罪的“非法经营行为”并不完全相符,甚至差别还很大。其中第1条的“未取得药品生产、经营许可证件和批准文号,非法生产、销售盐酸克仑特罗等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品,扰乱药品市场秩序”的行为,两高司法解释认为可以依照《刑法》第225条非法经营罪中的“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其强调的是生产、销售“瘦肉精”行为仅仅是“未取得药品生产、经营许可证件和批准文号”与非法经营罪中的“未经许可”相同,而并非是生产、销售“瘦肉精”行为与“非法经营行为”相同。第2条的“在生产、销售的饲料中添加盐酸克仑特罗等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品,或者销售明知是添加有该类药品的饲料”的行为,两高司法解释认为可以依照《刑法》第225条非法经营罪中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两者更加不对称、不相符。
二、刘襄案件能否定性为生产、销售假药罪
刘襄等人的生产、销售“瘦肉精”行为能否定性为生产、销售假药罪?首先应当明确“瘦肉精”是否属于“药品”与“瘦肉精”作为“药品”能否构成“假药”,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对生产、销售“瘦肉精”能否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作出准确判定。
1.“瘦肉精”是否属于“药品”?“瘦肉精”的正式化学名称是“盐酸克伦特罗”,通常作为一种人体平喘药物,对心脏有兴奋作用,可扩张支气管平滑肌。将它添加在饲料里可以提高饲料的利用率、加快动物生长速度、使猪的瘦肉率提高近10%,因此有了“瘦肉精”之称。②毫无疑问,在涉及“药品”的有关行政管理法规中,“盐酸克伦特罗”(俗称“瘦肉精”)一直是被当作“药品”而加以管理的。
需要指出,“盐酸克伦特罗”作为“药品”既可供人服用,也可用于牲畜,不能因为将其用于“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而否定其“药品”的属性。这在两高《办理“瘦肉精”案件应用法律解释》中即对“盐酸克伦特罗”属于“药品”予以肯定,特别是在其中的第6条更加明确规定,列入农业部、卫生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告的《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物品种目录》的“盐酸克伦特罗”等药物品种属于“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品”。
2.“瘦肉精”作为“药品”能否构成“假药”?《刑法》第141条第2款规定:“假药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属于假药和按假药处理的药品、非药品。”但是,刑法的这一假药定义仍然不能直接界定某种药品或者非药品是否属于假药,而是需要依据《药品管理法》的有关规定来加以判断。③《药品管理法》第48条规定了两种“假药”:一是药品所含成分与国家药品标准规定的成分不符的情形;二是以非药品冒充药品或者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的情形。按假药处理的药品、非药品包括: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禁止使用的;依照本法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或者依照本法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使用依照本法必须取得批准文号而未取得批准文号的原料药生产的;所标明的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超出规定范围的。《药品管理法》第48条规定的“属于假药和按假药处理的药品、非药品”,这在刑法理论上可以归结为“自然属性上的假药”和“法律属性上的假药”两类。“自然属性上的假药”是不具备药品应有的用途的假药;而“法律属性上的假药”就其自然属性来说可能并非假药,也具有药品的正常用途,但由于违反了特定的程序性规定,同样也破坏了国家药品监督制度,因此,才按假药处理。④
3.生产、销售“瘦肉精”能否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刑法学界存在肯定与否定两种观点。笔者认为,肯定与否定生产、销售“瘦肉精”能够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的两种观点其实并不矛盾,而是完全一致的。两种观点统一的基础主要在于,生产、销售的“瘦肉精”是否直接给“人体健康造成危害”。既然生产、销售的“瘦肉精”未直接给“人体健康造成危害”,那就不符合《刑法》第144条规定的生产、销售假药罪的构成要件。此种理由依据,也是两高《办理“瘦肉精”案件应用法律解释》第1条与第2条所解释的两种生产、销售“瘦肉精”行为没有按生产、销售假药罪定性,而是按非法经营罪定性的根本原因。
三、刘襄案件能否定性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刘襄等人能否定性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只有明确了以下问题,才能对刘襄等人作出客观、准确的定性。
1.刘襄等人研发、生产、销售“瘦肉精”行为是否符合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构成条件。根据《刑法》第144条规定: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是指故意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行为。此罪的成立,应重点把握两个主要构成要件:一是主观方面必须是故意,即在生产食品过程中明知是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而掺入食品中,或者明知是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而予以销售;二是客观方面必须具备在生产食品的过程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或者销售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行为。⑤例如,2010年11月至12月,李保清使用从他人处购买的盐酸克伦特罗药品(俗称“瘦肉精”)添加到猪饲料中,给其猪场的40头育肥猪喂食。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李保清使用禁止在饲料中使用的盐酸克伦特罗药品喂养供人食用的动物,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提请法院依法惩处。2010年9月5日,河南省鹤壁市淇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李保清有期徒刑七个月。⑥在此案中,被告人李保清主观上明知是“瘦肉精”而从他人处购买并使用,客观上也具备“使用禁止在饲料中使用的盐酸克伦特罗药品喂养供人食用的动物”的要件,因此,其行为应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笔者认为,所谓“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可以从两方面进行理解:(1)掺入食品中的对象应是“非食品原料”。如果将食品原料掺入食品中,即使由于某种原因,如被污染、变质,致使对人体产生毒性或者造成损害,也还是“有毒、有害的食品原料”,而非“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不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2)被掺入的“非食品原料”应有毒、有害。如果向食品中掺入的非食品原料无毒、无害,未对人体造成损伤,不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⑦两高《办理“瘦肉精”案件应用法律解释》第3条与第4条规定,使用盐酸克仑特罗等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品或者含有该类药品的饲料养殖供人食用的动物,或者销售明知是使用该类药品或者含有该类药品的饲料养殖的供人食用的动物的,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追究刑事责任。而在刘襄案件中的生产、销售对象仅仅是“瘦肉精”,并未将“瘦肉精”掺入食品中或者销售该掺入“瘦肉精”的食品。既然刘襄的行为是研发、制造、生产、销售“瘦肉精”,并没有直接向食品或者食品原料中掺入该物质,这就不符合“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客观要件,因而不宜定“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⑧
2.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否属于法条竞合问题。有学者认为,从法条规定看,两罪对于造成不特定多数人生命、健康损害即危害公共安全方面存在交叉关系,这种交叉关系不需要附加任何条件、不受具体案件影响,因而属于法条竞合而非想象竞合关系。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属于特别法条,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属于一般法条。当一行为在犯罪行为方式、犯罪对象等要件不完全符合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犯罪构成时,可以转而适用一般法,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认定。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在其行为方式上要求: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犯罪对象必须是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但是如果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掺入的对象不是食品,或者销售的是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本身,则不能认定为本罪,可以适用一般法条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⑨
笔者认为,上述学者的前提观点是正确的,即认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两罪属于法条竞合而非想象竞合关系。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两罪关系,究竟是属于“法条竞合”还是属于“想象竞合”,这需要从“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区别中才能加以判定。按照刑法学界通说,“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可以同时表现为“一行为同时触犯两法条”,这也是两者的相同之处。“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两者的不同之处则表现在:如果同时触犯的两法条表现为“一法条能包容另一法条”的包容关系,包括全部包容关系与部分包容关系两种情形时,应界定为“法条竞合”;而如果同时触犯的两法条不具有全部包容与部分包容的包容关系,这却属于“想象竞合”。从行为方式上来看,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两者存在包容关系,即“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仅仅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一种“具体危险方法”,单纯由此而言,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两罪应属于“法条竞合”,却并非属于“想象竞合”。
按照上述学者的前提观点,既然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两罪属于法条竞合,那就应当按照法条竞合的处理原则来解决两法条的适用问题。但是,上述学者的结论性观点却并非如此。在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两法条的竞合关系中,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属于特别法条,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属于普通法条(又称“一般法条”),按照法条竞合的“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处理原则,应当选择属于特别法条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来解决两法条的竞合问题。然而,上述学者的结论性观点则与此相反,而是选择了属于普通法条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解决两法条的竞合问题,即“当一行为在犯罪行为方式、犯罪对象等要件不完全符合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犯罪构成时,可以转而适用一般法,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认定”。
概而言之,上述学者观点为“普通法优于特别法”,这与法条竞合的通行处理原则“特别法优于普通法”是不相协调,甚至是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的。其谬误产生的根源在于偷换了概念(或者属于前后概念不一致):即从前提中构成犯罪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变成了结论中不构成犯罪的“非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四、刘襄案件能否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法院最终认定刘襄等人共同研制、生产、销售“瘦肉精”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主要是因为:这几个罪名在犯罪构成的行为方式、犯罪对象等要件上,并不完全符合刘襄等人共同研制、生产、销售“瘦肉精”的犯罪特点。比较而言,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更符合刘襄等人共同研制、生产、销售“瘦肉精”的犯罪特点。当然,搞清为何被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有必要进一步探析如下几个与此罪相关的问题。
1.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以其他危险方法”的内涵问题。在相关刑法条款及其刑法司法解释中,均未见有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以其他危险方法”内涵的具体解释,因而导致学者们的解释不相一致。有学者认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构成条件之一是,其手段与爆炸、放火等一样具有暴力性。以和平手段、平和方式进行的,即使可能危害公共安全也不能定此罪。⑩另有学者认为,“生产、销售瘦肉精行为本身不具有瞬间即时破坏性与杀伤力特征,其对人身健康威胁具有潜在性,危害后果远非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引发人身安全性质可比,瘦肉精对人体的危害符合刑法规定生产、销售有毒食品犯罪中被添加有毒物质特征”(11)。总体来看,这两位学者的表述观点大体是相同的:前者主张“以其他危险方法”应当“是手段与爆炸、放火等一样具有暴力性”,而后者则主张“以其他危险方法”应当具有“瞬间即时破坏性与杀伤力”的特征。在这种相同主张的基础上,两位学者得出了相同的结论:由于生产、销售“瘦肉精”行为不具有“以其他危险方法”的“暴力性”、“破坏性与杀伤力”的特征,因而不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构成要件,最终也就不能以此罪来解决生产、销售“瘦肉精”行为定性问题。
笔者认为,上述学者如此理解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以其他危险方法”的内涵,并不符合《刑法》第114条、第115条规定。因为在这两条规定中并没有任何限制性条件,如果加入“暴力性”、“破坏性与杀伤力”作为“以其他危险方法”的限定,无疑会缩小“以其他危险方法”的构成范围,这显然属于有违立法精神的“限制解释”。事实上,要准确理解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以其他危险方法”的内涵,比较符合立法精神的做法应当是围绕该罪的本质特征来进行解释。“本罪与其他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具有相当性,并不是犯罪方法、手段的相当性,而是本罪与爆炸、放火、决水等犯罪均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危害公共安全。”(12)因此,判断“以其他危险方法”就是要看是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即是否侵害到“不特定多数的人身、财产及社会利益”。“危害公共安全”具体表现在法条中,就是《刑法》第114条中的“足以造成严重后果”与《刑法》第115条中的“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如果一种危险方法不足以产生这种后果而没有发生后果,或者后果发生了是其他原因所导致的,就不能视为‘危险方法’”。(13)
2.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兜底性条款”与想象竞合犯的区别问题。2011年7月25日,在焦作中院一审宣判刘襄等5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罪名之后,针对不少学者及百姓就“瘦肉精”案件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疑惑,郑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德法、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赵新河对此作出了学理性解释,其要点性内容有二:(1)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属于概括立法方式,是排除了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之外的危险方法,即“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作为兜底性的法律规定,这类概括性的危害公共安全的方法,通常是指与法律明示的放火、决水等危害性相当的方法,其在本质上同样危害的是公共安全。(2)刘襄等被告人明知“瘦肉精”作为猪饲料添加喂养生猪,被人食用后对人体有害,故意生产并将其销售到生猪养殖业的行为,应被评价为一个完整的行为,其在构成要件上同时符合非法经营罪,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四个不同的罪名。这属于由一个犯罪行为触犯数个罪名的想象竞合犯,应当按照其触犯的罪名中最重的犯罪定罪处罚,即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刘襄等被告人的刑事责任。(14)
笔者认为,上述两位学者的释疑观点,虽然在定性结论上的解释是完全可取的,即刘襄等5人应当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但在解释内容中将“兜底性条款”与想象竞合犯混为一谈,这却是不可取的。事实上,属于概括式立法方式的“兜底性条款”与属于罪数形态的想象竞合犯两者应当是有严格区别的。况且,“兜底性条款”与想象竞合犯两者内容带有一定的矛盾性,因而也不宜同时适用。因为在刑法理论上,类同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以其他危险方法”的罪状表述被称为“兜底性条款”,其主要功能是严密刑事法网,堵截可能遗漏的犯罪行为。从其功能来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作为“兜底性的法律规定”,应当是在无其他罪名可选择的情形下才能加以考虑适用。否则,能有其他罪名可构成适用,那就不能选择以“兜底性条款”命名的罪名来适用。而想象竞合犯则与此不同,由于其主要特征是“一个犯罪行为同时触犯数个罪名”,这就意味着想象竞合犯是在数个能够构成犯罪的罪名中选择适用哪一个的问题,它与在无其他罪名可选择的情形下只能加以考虑适用该“兜底性条款”的罪名显然是不相同的。
3.“源头犯罪”、“二道贩子”与饲养者具体使用“瘦肉精”的定性应当有所区别。有学者认为,法院对刘襄案件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却对河南省获嘉县法院审理的第二批“瘦肉精”案的韩文斌等7名被告人,以“非法经营罪”判处1年至10年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显然,河南法院将生产、销售“瘦肉精”的被告人刘襄等人与后续“二道贩子”们严格区别,差别性刑罚适用,此与河北法院审理毒奶粉案件审判思路雷同,存在严重逻辑矛盾。(15)另有学者认为,“如果对制售瘦肉精的行为人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那么养殖户明知瘦肉精的危害而仍然用其喂猪,然后卖猪的农民明知含有瘦肉精而仍然屠宰、销售给不特定公众的菜市场的经营户,这些人的行为又该如何定罪呢?如果也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是否太重,罪刑不均;如果定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与刘襄等定罪是否也是不均衡”(16)?概而言之,这两位学者的观点可以归纳为这么一个问题来探讨:即对刘襄等人的“源头犯罪”能否与“二道贩子”差别性适用刑罚?
笔者认为,对刘襄等人的“源头犯罪”能否与“二道贩子”差别性适用刑罚,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该问题的关键理由在于:犯罪行为性质不同,会符合不同的犯罪构成要件,因而应被确定为不同的罪名。刘襄等人的“源头犯罪”行为是研发、生产、销售“瘦肉精”,应被确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二道贩子”的犯罪行为是“非法经营‘瘦肉精’”,应被确定为非法经营罪。例如,“二道贩子”韩文斌等7人先是购买“瘦肉精”原粉,经过淀粉稀释后,再以每包110元至140元不等的价格卖给生猪养殖户,直接导致含有“瘦肉精”的生猪流向市场。他们明知“瘦肉精”是国家禁止用于喂养生猪的药品,但为牟取利益,仍将“瘦肉精”及含有“瘦肉精”成分的稀释粉出售给生猪养殖户并传授饲喂方法,这显然违反了我国对“瘦肉精”等药品实行限制经营的规定,因而构成非法经营罪。(17)此种将刘襄等人的“源头犯罪”行为与“二道贩子”的犯罪行为予以适用不同罪名,正是在遵循犯罪构成、符合形式逻辑要求的前提下而作出的“差别性刑罚适用”结果,对此应当给予充分肯定,而不能以“此与河北法院审理毒奶粉案件审判思路雷同”而得出“差别性刑罚适用”就“存在严重逻辑矛盾”的结论。事实上,如果认为“河北法院审理毒奶粉案件审判思路”是比较妥当、适宜的话,那么此后审理包括“瘦肉精”在内的类似案件而予以参考或借鉴,也是无可指责、无可厚非的。
至于饲养者具体使用“瘦肉精”的行为与刘襄等人研发、生产、销售“瘦肉精”的“源头犯罪”行为,两者当然也是不能等同的。犯罪行为性质的不同,当然会体现在定性罪名上有重要区别。刘襄等人研发、生产、销售“瘦肉精”的“源头犯罪”行为,如前所述,应当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饲养者具体使用“瘦肉精”饲养猪、牛、羊等行为,是一种“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行为”,这并不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构成要件,但却符合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构成要件,因此,应当定性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例如,2011年7月29日,河北省昌黎县人民法院宣判一起“瘦肉精”案件。昌黎县龙家店镇西刁坨村38岁的农妇韩立荣违反我国食品卫生管理法规,明知“瘦肉精”是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且国家明令禁止给家畜喂食,仍故意给其饲养的育肥羊投喂,法院认定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以此罪判处韩立荣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万元。(18)
那么,“卖猪的农民及屠宰后卖肉的明知含有瘦肉精而仍然屠宰、销售给不特定公众的菜市场的经营户”,这些人的行为如何定罪呢?笔者认为,贩卖含有“瘦肉精”的生猪的农民,以及“屠宰后卖肉的明知含有‘瘦肉精’而仍然屠宰、销售给不特定公众的菜市场的经营户”,对这些行为人可以认定为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两高《办理“瘦肉精”案件应用法律解释》第3条与第4条规定了两种生产、销售“瘦肉精”行为可以定性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一是使用盐酸克仑特罗等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品或者含有该类药品的饲料养殖供人食用的动物,或者销售明知是使用该类药品或者含有该类药品的饲料养殖的供人食用的动物的行为;二是以明知是使用盐酸克仑特罗等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品或者含有该类药品的饲料养殖的供人食用的动物,而提供屠宰等加工服务,或者销售其制品的行为。例如,在南京“瘦肉精”案件中,张运能等人于2011年3月13日至15日间,从河南孟州、浚县等地购买100头至145头不等的生猪,经检测,6家屠宰户的生猪抽样中,24%至100%不等的猪尿中含有盐酸克伦特罗成分,其中7头中还含有来克多巴胺,其明知所购生猪含有“瘦肉精”等有毒有害成分,仍在建邺区兴旺屠宰场进行销售、屠宰,其行为已经触犯《刑法》第144条的规定,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应追究刑事责任。(19)
注释:
①《聚焦河南“瘦肉精”案:危害公共安全罪还是非法经营罪》,载《人民时报》2011年7月26日。
②赵雪、李颖:《“瘦肉精”为何屡打不死》,载《科技日报》2011年3月21日。
③徐雅飒:《试论生产销售假药罪的犯罪对象》,载《中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④魏地:《生产销售假药罪犯罪构成研究及立法完善》,载《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
⑤顾保华、苗有水:《俞亚春生产、销售有毒食品案》,载《人民法院报》2002年7月22日。
⑥曲昌荣:《河南惩处食品安全犯罪:治乱用重典公众增信心》,载《人民日报》2011年9月7日。
⑦王玉珏:《刑法第144条中“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的合理定位》,载《法学》2008年第11期。
⑧魏东:《再议河南“瘦肉精”案的刑法解释论意义》,载正义网-法律博客2011年8月13日访问。
⑨李莹:《〈刑法修正案(八)〉中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法理解析》,载《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年第3期。
⑩李勇:《河南瘦肉精案是否有撑大“口袋”之嫌》,载正义网-法律博客2011年7月26日访问。
(11)孙云康:《最高法院无权保持沉默》,载新浪博客网,2011年8月13日访问。
(12)赫兴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司法认定》,载《法制日报》2006年1月13日。
(13)孙万怀:《醉酒驾车肇事案件定性问题研究》,载《现代法学》2010年第5期。
(14)陈菲等:《制售“瘦肉精”何以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载《检察日报》2011年7月26日。
(15)云康:《最高法院无权保持沉默》,载正义网,2011年8月13日访问。
(16)同注⑩。
(17)陈和耀:《河南第二批“瘦肉精”案宣判》,载《人民法院报》2011年8月12日。
(18)朱峰:《农妇明知瘦肉精危害仍投喂家畜被判5年徒刑》,载新华网,2011年7月29日访问。
(19)《南京昨开审“瘦肉精”案6屠户均承认有罪求轻判》,载《扬子晚报》2011年9月7日。
标签:瘦肉精论文; 刑法论文; 非法经营罪论文;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文; 法条竞合论文; 法律论文; 食品生产论文; 公共安全论文; 药品管理法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