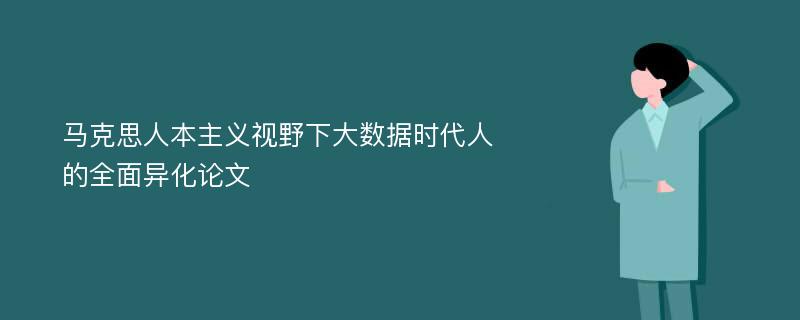
马克思人本主义视野下大数据时代人的全面异化
粟盛玉 郭凤海
摘 要: 大数据时代已高调到来,它以迅猛的节奏深刻重构着现代人的存在方式,但当前对它的人本主义审视尚处于缺位状态。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框架是我们理解大数据时代人的生存处境的一把重要钥匙,有助于使事实的意义逐层展开,呈现出全新存在方式的生存论内涵。在大数据时代,人的异化被扩展到了更加普遍的维度,大数据革命推动了人的全面异化。但这一观点背后的价值取向并不悲观,因为全面异化具有历史合理性,全面异化本身就是对异化的全面扬弃,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只能在持续发展中得到解决。
关键词: 大数据;马克思;人本主义;异化
2008年 9月,《自然》(Nature)杂志策划了一期大数据专刊,从多个角度向人们展示:电子数据在各领域的大规模使用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人类对世界的理解,我们的组织和文化也将随之深刻地变迁[1]。以此为节点,作为一个概念的“大数据”迅速走热,并逐渐进入国内外人文社科研究者的视野,相关研究至今仍是显学。那么在哲学话语中,大数据对于当代人的生存处境究竟有着怎样的意义?若站在马克思人本主义的视角加以审视,这个问题的答案——人的全面异化——将被呈现得无比清晰。
一、对大数据时代进行人本主义审视的必要及缺位
人类已经或即将进入一个大数据时代,数据将成为我们理解世界、他人及自身最有效甚至是唯一有效的路径。这已是个不可忽略的事实,而与这个事实同样重要的是,它对人的存在所具有的意义。在各个历史时期,意义问题都更难被清晰地把握,也更容易被我们所忽视。胡塞尔早就敏锐地意识到:“现代人的整个世界观唯一受实证科学的支配,并且唯一被科学所造成的‘繁荣’所迷惑,这种唯一性意味着人们以冷漠的态度避开了对真正的人性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单纯注重事实的科学,造就单纯注重事实的人……它从原则上排除的正是对于在我们这个不幸时代听由命运攸关的根本变革所支配的人们来说十分紧迫的问题:即关于这整个的人的生存有意义与无意义的问题。”[2]离开对大数据的人本主义审视,我们很可能错过这个时代真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
但回顾此前对大数据问题的人文社科研究,人本主义视角下的探讨尚处于缺位或半缺位状态。总体上,已有研究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第一,高度聚焦实用。典型的观点是:“大数据分析是一个认识世界可以利用和升华的新工具。”[3]很多研究讨论了大数据作为一种工具在人文领域的使用价值与使用方式——如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培育[4]、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5]、对人文研究方法的颠覆[6],但却没有触及这一“工具”对人之存在本身的重塑,而这种重塑总是伴随着此前人类的每一次重大技术变革。第二,维度总体单薄。一些研究触及了更深的理论维度,如范式转换[7][8]、对传统认识论的超越[9]、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重新理解[10],但基本都停留在知识论、伦理学或经济学范畴内,尚未触及人的生存论维度,这就使得对大数据进行意义审视的文献群在整体上显得单薄。第三,重视价值评判,论证略显武断。也有极少数研究深入到了生存论层面,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挖掘。但遗憾的是,由于受研究者先在价值悬设的影响,他们对大数据的价值立场普遍正面而鲜明,这当然好,但立场背后的具体论证却常常稍显武断。例如,将“大数据技术对人的主体地位的消解”直接指认为是“人的本质的双重复归”[11],或者认为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与人类社会的划分“恰恰与‘小数据时代’和‘大数据时代’的划分相对应”[12]。结论很惊艳,只可惜都没有给出足够充分的事实或文本依据。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优越,就在于超越了先在的价值悬设,描绘出历史本身的辩证运动以及现实的人在历史中的具体处境。面对工业时代,马克思开启了他深邃的人本主义追问:“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13]从广义上讲,马克思的人本主义立场并非只存在于写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而是一种自始至终的,对人的存在的关照。有必要回到马克思这一贯穿终生的伟大结构中,使我们有可能突破现有的认识水平,让我们对大数据时代的理解更加多维、立体,更加客观、坚实。沿着马克思的逻辑,本文得出如下结论:大数据革命推动了人的全面异化,我们正在背离现实、自由、人之本质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二、大数据革命对人的存在方式的深度重构
首先必须明确,大数据时代所依归的不是某个单向度的技术变革,而是一套从基础设施到观念意识的完整体系,它包括:高覆盖、高带宽、低成本的网络基础设施,如光纤网络和4G移动网络;广泛使用的终端电子设备,包括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电子监控设备、传感器及一切可在线化的物品;用于各种场景的海量应用软件,如工作、社交、购物、出行、学习、运动、娱乐软件等;日趋成熟的数据记录与挖掘技术、机器学习技术和区块链技术;对数据的意义及使用方法的全新理解。这些革命性的变化,给现代人的存在方式带来了深度的冲击与重构。
根据调查发现,针对农村小学存在的教师结构不合理情况,政府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例如,在年轻教师的引进上应向农村小学倾斜,在教师性别的选择上适当向女教师倾斜,在学科配置上引进音乐、体育、美术、外语以及信息技术等学科的教师配置,并且确保农村学校的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开设。
(一)生存场域的普遍在线化
马克思很早就洞察到“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14],我们周遭的一切都应该以对象性的(gegenst ndliche)方式被理解。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将马克思在生存论意义上使用的“环境”进行了哲学的术语化表达,形成“场域”(field)的概念。在现实中,人的存在绝不是漂浮在一种抽象的真空中,而是置身于一片结构化的场域,在场域里与他人和世界发生作用、构建意义[15]。生存场域由人的感性实践活动所投开,但同时像自然界中的场一样,对在场存在者的行为方式产生着不可排除的影响。与通常意义上的环境不同,生存场域不是外在的,它就是我们存在的一部分。
纵观人类历史,每一次重大的技术革命都会改变人的生存场域,进而带来存在方式的重构。“万物互联,尽皆在线”是大数据革命的一个基本特征,也决定了此轮生存场域重塑的方向。一是生产场域的在线化。无论是新兴行业还是传统行业,O2O(Online To Offline)模式几乎已经成为标配,各生产部门都在逐步向线上转移。同时,通过传感器的大量使用,很多具体的生产过程都实现了在线的实时感知和控制。一旦离线,很多现代生产活动将寸步难行。二是人际场域的在线化。当前,大量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都是在线上完成,语音、视频、发朋友圈、评论、点赞已经成为我们与绝大多数人发生关联的全部手段。三是观念场域的在线化。人们观念的获得、调整、碰撞都大比例地在线上发生,一个在过去可能很不起眼的话题性事件很容易发酵为全民的狂欢,作为整体的社会观念也越发清晰地在线上进行自我呈现与演化生长。四是席卷其他一切场域的全维度在线化。我们的个人行为——如消费、浏览、出行、运动,我们的身体状态——如睡眠、心率、身体姿势,我们的生活空间——如家庭、私家车、公共场所,几乎一切的生活内容都正在转化为线上的数据。生存场域正在走向普遍的在线化。
21世纪初中国推出文化“走出去”战略以来,成绩斐然,“译介在其中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1]。谢天振教授提出的“译介”致力于“揭示译语文化系统中的政治、意识形态、文学观念、经济因素等对文学翻译的操纵和影响”[2]。由此,“译介”的概念不再局限于自身框架中,它突破传统意义上的翻译研究,从其他学科汲取养分丰盈自己,获得更为长久的生命力。传播学不仅是一门探讨传播现象与规律的学科,其交叉学科的属性也使得它成为一种研究方法。从传播学的角度来审视文学作品的译介,不仅完善了传播学的知识体系,推动传播学理论建设,也为译介研究提供新思路、新方法、新收获。
(二)认知空间的极度过载
[13]John McMurtry, The Structure of Marx’s Worldview,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p.70.
在日常生存的维度里,大数据时代的信息爆炸与此前的信息增长相比还有一个明显区别,那就是信息获得了主动的渗透性与侵入性。它们会主动侵入我们的认知空间,被无死角地植入到我们的一切触目可及之处,强势地吸引眼球,争夺注意力。且不说满街道、满地铁、满候车大厅的电子屏,单是一部小小的智能手机就足以占满一个人的认知空间。社交网络的互动点赞,新闻头条充满吸引力的标题,深谙成瘾之道的手机游戏,网页上处处闪现的弹窗……一切都在竭尽所能地掌控使用者当下的认知轨迹,让他偏离本初的认知诉求,在无意识状态下不断将大量无用信息填充进自己的认知空间。无论在哪一个领域,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大数据时代人的认知空间都处于普遍的过载状态。
(三)社会的去中心高密度互联
互联是大数据时代的一个核心逻辑。在一个复杂网络中,数据的总量与维度将随着质点间连接数目的增多而发生指数级的跃迁。可以说,没有足够的连接,就没有成规模的数据。而互联又恰恰是人类社会的本质,正如马克思所言:“市民社会的成员根本不是什么原子……每一个人都必须建立这种联系,这样就相互成为他人的需要和这种需要的对象之间的皮条匠。”[17]一个时代的技术水平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种联系的性质和密度,进而系统性地规定了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存在方式,马克思就亲眼目睹了工业时代是如何推动世界互联、如何使人类历史成为真正的世界历史。
同时在另外一项研究中发现:孟鲁司特对于成年特应性皮炎的患者、中度和中度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对患者按照10gm/次的剂量进行服药,对两组患者连续采取治疗4周和8周,研究结果表明孟鲁司特在具体的治疗中,具有较好的耐受性,并无明显的不良反应。
首先,人的行为活动和生存轨迹在以数据的形式被售卖,并作为人性的镜像被转化为促进资本增殖的手段。借助于普遍的在线化和高密度的互联,个人的日常行为数据得以在网络空间里成规模地积累。这些数据记录无孔不入且高度真实,是各大互联网公司竞相争夺的资源。一方面,它们利用这些数据帮助自身攫取更多利润。如对于同一产品或服务,给不同的用户提供有差别的定价,开展所谓的大数据“杀熟”[25]。另一方面,它们将这些数据开发成特定的服务打包转卖。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就多次花巨资购买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的数据服务[26]。该公司能通过对脸书用户的大数据分析,总结出选民的心理诉求和空间分布。
三、新的存在方式下人的全面异化
另一方面,社会的去中心高密度互联使得人与人的关系得以全面抽象化。马克思早已经发现,市场交换使“人的依赖纽带……被粉碎了(一切人身纽带至少都表现为人的关系);各个人看起来似乎独立地(这种独立一般只不过是幻想,确切些说,可叫作——在彼此关系冷漠的意义上——彼此漠不关心)自由地互相接触并在这种自由中互相交换”[24]。而在大数据时代,这种“彼此漠不关心”已经远远超出了交换领域。由于普遍的数字化的连接,任何人与人之间的交互都在逐步摆脱感性现实,感性的相互依赖被虚拟的呈现所消解。“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24]111
在大数据时代,人的存在方式发生了深度重构。若将这种重构放置在马克思人本主义的框架里,放置在他广义的异化逻辑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大数据时代,人的异化已经远远超出了生产领域,已经拓展到人的生存的每一个维度。我们正在更加普遍的意义上,背离感性现实、变得不自由、被物所奴役。大数据革命将人推向了全面的异化。
(一)感性现实的全面抽象化
在马克思的哲学体系里,“人的感性的活动”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13]168。但在工业时代,抽象劳动成为了大多数人赖以生存的手段,人们的主要活动不再是自己生命的外化和呈现,而是将自己抽象化、非现实化,以使自己的劳动力或劳动产品能够在市场上被售卖。于是,“劳动的这种实现表现为工人的失去现实性,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13]91。如果说工业时代感性现实的抽象化还主要发生在生产领域,发生在工人进行抽象劳动的场景中,那么在大数据时代,这种抽象化、去现实化则全面贯穿于人的每一个生存领域。
一方面,普遍的在线化意味着普遍的抽象化。现实生活的感性内容被一点点从我们的生存场域里剥离,抽象的数据成为了人和世界主要的自我呈现方式。例如,在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那里,数据绝对高于感性,每一个用户都会完全地被数字化描述。比如性别,相较于收入、学历等,性别可以算是最为感性化的一个特征。但即便如此,阿里巴巴仍将感性的“男”“女”抽象为18种性别标签,以此对每一个用户的性别进行抽象的数字化描述。这么做的理由,首任阿里数据委员会会长车品觉解释得很清楚:“真实的性别只有0与1的关系,而现实却是0—1的关系,或者70%是男性、30%是女性……静态的‘真实’性别在A/B测试中的表现不如动态的虚拟性别有效。”[23]感性的真实被打上了引号,一如马克思当年的感慨:“感性失去了它的鲜明色彩,变成了几何学家的抽象的感性……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17]164
(1) 试验矿样中的主要金属矿物为黄铜矿、孔雀石、自然铜、蓝铜矿、褐铁矿等;主要脉石矿物为石英,其次有碳酸盐矿物和绿泥石、绢云母等。含银矿物包括银黝铜矿、辉银矿、深红银矿及少量自然银,银大部分产于铜矿物中,而脉石矿物中含银较少。
“异化”(Entfremdung)是一个在马克思早年文本中高频出现的概念,是其思想在人本主义维度里的一个重要承载。虽然这一概念作为能指本身在《神圣家族》后已使用不多,但其精神指归却贯穿了马克思的整个哲学体系,成为他毕生的关切。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已系统描绘出工人的异化处境,如:“工人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他个人的生命,就是不依赖于他、不属于他、转过来反对他自身的活动。这就是自我异化。”[13]95到写作《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时,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他的活动不是他的人的生命的自由表现,而无宁说是把他的力量售卖给资本,把他的片面发展的能力让渡(售卖)给资本……是非自由的、非人的、非社会的。”[13]254再到《资本论》中,马克思还在深入地讨论:“他自己的劳动就同他相异化……不断物化在别人产品中。”[22]类似讨论在马克思留下的文献中比比皆是,它们未必都使用了“异化”一词,但却都是对同一客观事实的理论指认。这一事实就是:人——主要是工人——非人的生存状态。这一非人状态就是异化概念所指的内核。在马克思的一系列表述里,人的异化根植于生产活动,突出表现为三个特征:第一,背离感性现实;第二,非自由的;第三,人被物化,沦落为手段。
大数据时代的一个最直接特征就是数据的爆炸。据估算,从文字被发明到2006年的数千年间,人类共计积累了约180EB的数据(1EB=1024PB,1PB=1024TB,1TB=1024GB)。而从2006年到2011年,仅五年时间,这一数据总量就猛增了近8倍,变为约1600EB。按当前的数据产生速度,这一数值大约每三年就会翻为原来的4倍。如果把现在人类一天产生的数据等量转化为文字出版物,可以将美国现有的所有图书馆装满8次[16]。经历过知识匮乏年代的人会对我们今天的认知处境感到震惊。问题已经不是数据不够,而是数据已经多到超出了任何人的认知能力。所以在今天,作为生产者或研究者的所有个人,其认知范围通常都被严格限制在一个十分狭窄的细分领域内。若不这样,一个人可能穷尽一生都无法掌握足够的专业知识或技能,进而无法在社会价值链条中占有一席之地。对于很多具体问题,海量的数据只能交由人工智能来理解和驾驭,人类只能掌握其基本过程和最终结论。曾经一度明晰的外部世界再一次从我们的直接感知中退隐,退隐到了数据的黑箱内。
(二)自由的全面丧失
不同于自由主义哲学家笔下的外部自由,在马克思的人本主义语境里,自由是人的本质力量、是有个性的生命的积极彰显。“人不是由于有逃避某种事物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是自由的。”[17]167但是,在工业时代的生产活动中,“异化劳动把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13]97。个性与生命被压抑,自由被剥夺。在大数据时代,自由的丧失同样超出了生产领域,且不仅仅局限于工人或劳动者,全体人类都在一步步失去个性、失去对自身命运的掌控。
自由的全面丧失发端于认知和思维领域。在根本的意义上,大数据使得人类自身的理性思维系统失去了终局性的决策能力。前面已经论述,数据化之后的客观世界变得空前庞大、复杂,人类一直以来基于模型的思维方式已无力再将之充分领会。现在,对数据世界的理解只能通过不断训练人工智能的方式来完成,而人的理性已无法独立验证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给出的结论。这就形成了大数据对人的智识上的强制性。
这种强制已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日渐显现。对于工业时代人的不自由,马克思曾这样描述:“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性行为,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13]94足见那时的人,至少在生产领域外、在日常生活中还可以是自由的。但生活在大数据时代的人,即使在最基础的衣食住行中,可能也不再有真正施展人的本质力量或自由个性的空间。买衣服该选哪一款?淘宝的评分告诉你。出去吃饭该选哪家饭店?美团和大众点评告诉你。开车走那条路线?实时路况导航告诉你。乃至买房、治病、匹配婚姻对象……都已有可运用的大数据技术宣称能给我们提供最优方案,而方案背后的理由我们已没能力也没兴趣去理解。在几乎全部的生存领域中,人的自由选择权就这么逐渐转让给了数据和算法。我们要做的可能只是最后在形式上点击一下“同意”或者“接受”,同时不再过问这“同意”或“接受”所代表的全部意义。
在废水pH值为6、石墨烯加入量为3 mg/L、H2O2加入量为7 mL/L、n(Fe2+)∶n(H2O2)为1∶1.5条件下进行反应动力学分析,并以最适条件下的传统Fenton反应体系作为对照。
(三)人的全面物化
马克思很早就洞悉到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中存在的“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22]133。资本增殖,这一物的内容变成了一切的目的,而人则沦为了手段,变成了物的附属。马克思曾因此不无惆怅地怀念起前工业时代尚未物化的人的处境:“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24]486随着产业革命的推进,技术进步使人的物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一切资本主义生产……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22]463-464。工人成为了更加彻底与纯粹的劳动力出卖者,以非人的方式投入到产品生产与资本增殖的往复循环中。进入大数据时代,这一趋势还在延续,人的物化采取了新的、更加彻底的形式。我们不光售卖自己的劳动力、技能和知识,我们的存在本身也成了被售卖的对象。
在大数据时代,社会成员的互联呈现出全新特点:一是高密度,连接高度致密,世界越来越小;二是去中心,由树状结构变为网状结构,人际网络越发扁平,中心节点越发模糊;三是由间接变成直接,更多个人直接地嵌入到整个社会网络中,与所有人产生直接交互,而不再像过去那样需要依托行业、单位或社群。1967年,哈佛心理学教授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为了测量当时美国社会成员的互联情况,做了著名的“连锁通信实验”。他将一名波士顿的股票经纪人设为通信目标,然后征集志愿者,让他们给自己认识的人寄信,收信人再给他们认识的人寄信,如此层层传递,目的是将信最终寄给通信目标。最终有44人寄达目标,他们与目标之间的平均人际隔为5.43人[18]。2003年,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者将身处13个不同国家的18个人作为通信目标,从166个不同国家选取了61168名互联网用户作为发件者。通过电子邮件联系上目标的发件者与通信目标间的人际间隔的中位数,若两人在同一国家为5人,在不同国家为7人[19]。2008年,所有脸书(Facebook)用户间的平均间隔为4.28人;2011年,脸书活跃用户数为7.21亿,用户间的平均间隔降为3.74人[20];2016年,脸书活跃用户数达到16亿,平均间隔进一步降至3.57人[21]。从7到3.57,全球范围的社会网络正在变得更加致密、扁平,人与人的联系方式正在变得更加直接。
其次,人的认知空间也在作为资源被抢夺和售卖。我们手机里的每一个应用,无论是新闻、游戏、社交还是视频,都在想尽办法让人上瘾、让人停不下来,以获取更多的注意力。在互联网商业中,这些注意力被称作“流量”。在取得的流量里插入广告、链接或其它应用的入口,就实现了“导流”。最后通过广告收入、销售产品和服务的方式将流量变现,完成“转化”。
(3)加快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产品的创新。金融机构应该发展各类碳金融产品,形成 “全产业链”配套综合金融服务,充分发挥金融市场支持绿色融资的功能,积极引入与循环经济发展有关的各类风险投资基金。要建立绿色金融发展的长效机制,将绿色金融作为长期战略来抓,持续加大对绿色环保行业的资金支持。以金融创新推动绿色产业发展,提供多样化的绿色金融产品体系,满足绿色企业和项目需求。
在人的存在结构里,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具有基础性地位,但二者现在却都成了大数据时代资本增殖环节中的原材料。人的物化采取了比前数据时代更加全面、更加彻底的形式。
四、全面异化的历史合理性及扬弃的路径
经过前面的论证,结论已十分清晰:大数据时代,人的异化被扩展到了更加普遍的维度,大数据革命推动了人的全面异化。这似乎是个悲观的结论。其实不然,这只是个客观的描述。对于人的异化,马克思的看法从不悲观。比如在谈及如何应对异化时,马克思使用的字眼大多是“扬弃”(Aufhebung)或“积极的扬弃”(positive Aufhebung),像《黑格尔现象学的结构》中的“扬弃异化等于扬弃对象性”[13]237、《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13]120,而没有使用在他笔记与著作中高频出现的“批判”(Kritik)。“扬弃”一词继承自黑格尔哲学,具有否弃与保存的双重含义。马克思的谓语使用清晰地折射出这样的信息:人的异化有需要否弃的内容,也有必须保留的历史合理性,它是人的发展的一个必要环节。
事实上,异化是人的本质力量得以释放、人得以作为人而存在的必要条件。马克思早就指出:“人使自身作为现实的类存在物即作为人的存在物实际表现出来,只有通过下述途径才是可能的:人实际上把自己的类的力量统统发挥出来(这又是只有通过人类的全部活动、只有作为历史的结果才有可能),并且把这些力量当作对象来对待,而这首先又是只有通过异化的形式才有可能。”[13]163由此可见,马克思认为异化本身就是扬弃异化的道路,正如他自己所言:“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13]117在大数据时代,数据革命对于生产力的释放确实是有目共睹的。生产变得不再盲目,要素与产品的流转变得更有效率,人的发展可能性变得更加丰富,个人的生活也变得更加便捷。我们有理由相信,大数据时代人的全面异化是人的全面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必经之路,全面异化本身为异化的全面扬弃开辟了道路。
我们当然渴望全面扬弃异化,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但正确的道路不是退回原点,而是继续向前。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如此写道:“全面发展的个人……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24]108-109沿着马克思的逻辑,我们完全可以说,大数据革命在加深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促进了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留恋前数据时代原始的自由、简单和具体,是可笑的。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只能在持续发展中得到解决。
参考文献 :
[1]Frankel F,Reid R.Big data:Distilling meaning from data[J].Nature,2008,455(7209):30.
[2]〔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M].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8.
[3]吴基传,翟泰丰.大数据与认识论 [J].哲学研究,2015,(11):110-113.
[4]陈云云,卫璐琳.大数据时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培育的双重境遇与破解之道 [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6,33(3):139-143.
[5]李亚青,郭跃军.大数据时代马克思主义网络传播研究[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6,(8):15-17.
[6]Wiessner P.The rift between science and humanism:What’s data got to do with it?[J].Current anthropology,2016,57(S13):S154-S166.
[7]方环非.大数据:历史、范式与认识论伦理[J].浙江社会科学,2015,(9):113-120+160+2.
[8]Kitchin R.Big Data,new epistemologies and paradigm shifts[J].Big Data&Society,2014,1(1):1-12.
[9]吕乃基.大数据与认识论 [J].中国软科学,2014,(9):34-45.
[10]吴欢,卢黎歌.数字劳动、数字商品价值及其价格形成机制——大数据社会条件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再解释 [J].东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8,20(3):310-316.
[11]李君亮,陈艳.超越主体性:大数据技术对人的本质的双重复归[J].理论月刊,2018,(2):43-47.
[12]马拥军.大数据与人的发展 [J].哲学分析,2018,9(1):105-115+198.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6.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7.
[15]Bourdieu P.The force of law:Toward a sociology of the juridical field[J].Hastings LJ,1986,38:805-853.
[16]Floridi L.Big data and their epistemological challenge[J].Philosophy&Technology,2012,25(4):435-437.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53-154.
[18]Milgram S.The small world problem[J].Phychology Today,1967,1(1):61-67.
[19]Dodds P S,Muhamad R,Watts D J.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search in global social networks[J].science,2003,301(5634):827-829.
[20]Barnett E.Facebook cuts 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 to four[N].The Telegraph,2011-11-22(14).
[21]Bhagat S,Burke M,Diuk C,et al.Three and a half degrees of separation [R].Palo Alto:Facebook Research,2016.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26.
[23]车品觉.决战大数据:大数据的关键思考[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116.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10.
[25]王钟的.用户数据不应是“杀熟”武器[N].科技日报,2018-03-02(07).
[26]Persily N.The 2016 US Election:Can democracy survive the internet?[J].Journal of democracy,2017,28(2):63-76.
The Total Alienation of Human Beings in the Big Data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Humanism
SUShengyu,GUOFenghai
Abstract: The era of big data has come,and it is profoundly reconstructing the way people exist.Based on Marx's humanistic framework,thearticleanalyzesthehumanexistencein theeraofbigdata.On theonehand,bybrowsinga largenumber of frontline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earch papers,itsummarizeshowpeoplearereconstructed.Ontheother hand,bybrowsing Marx'sclassicalexpressionofalienation,itunfoldsthemeaningofthefactsin Marxist humanistic context and the existential connotation of the new forms of existence.Finally,it concludes that the alienationofhuman beingsintheeraofbigdatahasgonefar beyond thefield ofproduction,and thebigdatarevolution haspromoted thetotal alienation of human beings.Thisconclusion isnot pessimistic,becausetotal alienation hashistoricalrationality.Problemsarisingindevelopmentcanonlybesolved insustainabledevelopment.
Key words: big data;Marx;humanism;alienation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811
文章编号: 1003-1502(2019)05-0094-09
作者简介:
粟盛玉(1989—),男,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博士研究生。
郭凤海(1966—),男,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博士。
基于学科用户的资源需求汇总分析,可以发现,学科用户需求与学科特点、学科层次、学科定位及资源建设现状密切相关。各学科都希望通过学术研究或创新应用提升自身整体实力与影响力,均提出对研究型、电子资源的迫切保障需求,这是不同学科共同的发展诉求。而“高峰”学科与“高原”学科则有冲击国际一流学科建设的压力与动力,率先提出对评估型文献资源与服务的要求。
责任编辑:翟 祎
标签:大数据论文; 马克思论文; 人本主义论文; 异化论文; 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