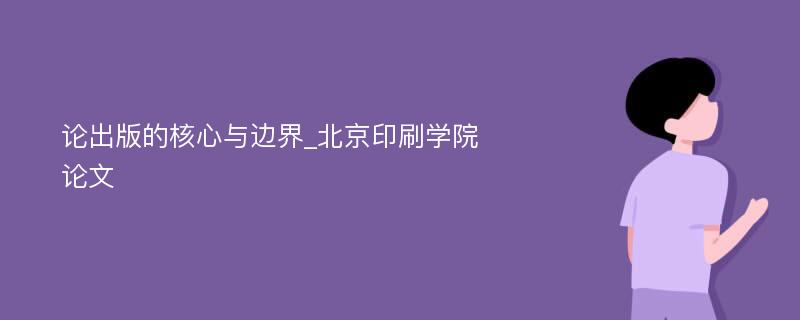
论出版学的核心与边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边界论文,核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09)04-0031-11
一、问题及理论背景
本文提议重新思考并建设出版学基于一个假定:我们是否处于与当年出版学开创者们类似的关键性转型期?有专家考证,出版学称名于1933年,文献学家杨家骆在其所编《图书年鉴》中第一次提出“出版学”。对出版学的积极呼吁和较为自觉的理论探讨则在改革开放之后。如果明确中国出版改革30年作为自洽的出版学科范畴,如果建立出版学作为知识论与出版改革作为制度变迁两者之间的联系,并正视而不是回避其中的内在紧张,则不难发现出版学的“试错”形态及对中国出版改革30年进程的一定影响:出版学学科建设滞后不是推动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出版改革的整体进程和发展水平。其象征形式是北京印刷学院校名悖论。
198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要加速建设北京印刷学院,在以后条件具备时,可改为出版学院。”[1]39这一文件是“建国以来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由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做出的出版决定,有着很强的思想性、理论性和政策性,是新时期指导出版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具有长远的指导作用”。历经30年,北京印刷学院条件一直不具备,成为中国高教史上更名写入党中央决定而即使历经全国性高校更名风潮也没有执行决定的惟一高校,成为《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没有完成的两件具体事情之一①。这样,北京印刷学院建院30年(办学50年)的实践形成了一个悖论:要么中共中央、国务院1983年建议更名的决定错误,北京印刷学院不更名的发展路线正确,要么北京印刷学院违背中央决定错了,中央决定正确。
本文主旨在讨论出版学,无意探究行政指令、“高校大跃进”为何在这里相继失灵。指出这悖论的逻辑起点是:由北京印刷学院与国家出版局—新闻出版署的隶属关系,认同它与出版学科发展的进程安排、学科建设水平存在内在关联性。将北京印刷学院没有遵中央决定更名视如出版学发展滞后的重要表征,提请关注、讨论其对中国出版改革的影响。这一逻辑起点有两个方面涵义:
第一,中央政府决定北京印刷学院更名基于出版行业在人才、理论等方面的系统要求,首先表现为对出版人才的渴求。出版系统一直力求在本系统内解决出版专业人才匮乏问题。建国之初,出版总署办了出版学校。1958年,文化部直属的北京文化学院建有出版系、印刷系等,可惜该校于1961年解散。改革开放之初,编辑出版队伍青黄不接,严重制约出版业发展,为突破瓶颈,有关部门多次积极商讨解决之道。1981年1月13日,国家出版局和中宣部出版局邀请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24位出版部门负责人座谈。袁亮会后起草了《当前出版管理工作需要解决的五个问题》,其中说:“把正在筹建中的印刷学院办成出版学院,培养编辑人才”。[2]468为了“提高现有编辑的水平,需要办一个出版学院,或者把正在筹建中的印刷学院改为出版学院,增加一些专业,以适应这个需要”[2]316。
第二,决定北京印刷学院更名反映了中央政府将出版学科纳入制度化建设的意图,这是对出版制度绩效的期盼。1979年的“长沙会议”是新中国出版史上继往开来的重要会议。其主旨报道就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希望出版《出版概论》、《出版史》、《编辑学》等基本读物,引导同志们把编辑出版工作当作一门科学进行研究”[3],这表明新时期中国出版初始制度安排与出版学呼吁、兴起同时进行。其对出版学的呼唤就是对出版制度绩效的期盼:“对社会科学知识的需求是由对更为有效的制度绩效的需求中派生出来的。社会科学知识可能会经由现存的制度或通过促进新的更为有效的制度的发展和创新而导致更为有效的制度绩效。”[4]352“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已为制度创新的效率开辟了新的可能性。”[4]352基于社会科学与制度创新、制度创新绩效的关系,有学者进而追寻制度失效的原因:“政府在建立最有效的制度安排方面导致失败的原因很多,例如: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集团利益冲突以及社会科学知识的限制等等。”[4]374
北京印刷学院校名悖论还折射了出版政府代理人群体行为矛盾:一方面积极呼吁提议将出版学列入国家学科目录,以推动出版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另一方面,默许、容忍下属的北京印刷学院更名延宕。诚然,这牵涉到多方面复杂因素与关系,在中国出版改革30年中存在北京印刷学院校名悖论则为事实。出版学、出版理论研究的后续发展无法完全回避对这一悖论的思考乃至清理。
北京印刷学院校名悖论的本质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系统化与去系统化两种观念、两种力量的博弈。其校名及坚守浓缩、包裹了去系统化涵义。在21世纪初全国高校调整管理体制以前,北京印刷学院是新闻出版署直属惟一的本科院校,它不执行“决定”的结果是,全国出版服务业链环难以衔接成系统,如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决策咨询难以得到系统解决;学院发展限于印刷,出版业优势资源难以转化为办学资源,因而在中国出版业兴旺发达时期也尴尬于捧着“金饭碗”讨饭吃。出版、印刷、发行共同构成出版产业系统链环,这三个关联部门由于性质、开放时间及程度不同,其利润水平相差悬殊,分配不公长期存在。“从图书不同环节的利润结构看,利润过分向图书出版环节倾斜,印刷环节的利润率过低。例如2000年全行业利润总额为52.71亿元,其中出版为38.09亿元,发行为12.02亿元,印刷为0.62亿元,考虑到从业人员人数为发行大于出版,印刷大于发行,这里的不平等和不合理的情况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5]245专家调查发现,1988、1989年,陕西省新闻出版局直属7家出版社人均创利分别为23356元和23474元,3家印刷厂人均创利分别为1910元和1850元,新华书店人均创利分别为1700元和1868元。出版社人均创利高于印刷厂和新华书店10倍以上。[6]4
以北京印刷学院校名悖论为表征的去系统化正是出版理论研究滞后的关键阻滞所在。这种去系统化还有其他表现形式,当下出版理论研究突破的有效途径首先是批判和扬弃这种去系统化,不再割裂编辑与出版的有机关联,不再切割可能的出版学与现实的传播学之间理论工具与知识资源等方面的联系,让出版理论研究回归到出版系统自身。
基于对本文开头所述假定的思考,本文意在唤醒出版学术圈的危机认同,并在中国出版改革30年、出版理论学术史批判的基础上寻觅新共识,如能引来同行社会科学工具和方法的自觉,并尝试、创建出版学学科范式①,或许可以摸索着闯出新路。本文拟提出两点不成熟的思考向同行请教:明确“出版学”而不是其他称名成为出版学科的核心范畴与目标指向;探究出版学的内在结构,明确出版制度结构为其核心,从而力求较清晰地认识建设中的出版学在社会科学知识谱系中的层级与地位。
二、出版制度结构
出版活动是出版学研究的对象,出版制度结构是出版学研究的核心。这一陈述强调:出版领域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整体性;出版制度结构作为核心概念指称了出版活动的深层结构与动力机制、出版学理论核心,它作为新兴学科在当下社会转型期的价值诉求。对此,拟分三个步骤展开论述:第一,界定出版并简要阐述出版活动与出版制度的相关性;第二,描述出版制度结构;第三,以刘杲命题1为例对出版的制度结构予以实证性分析。
(一)出版活动受制于出版制度结构
本文所说的出版是指现代出版,是人类工业文明时期的平面印刷媒体传播方式。这首先认定现代出版是人类传播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基本理论范畴是人类传播;其次,指出现代出版所采用的方式是平面印刷媒体,使其与农业时代的手工复制和信息时代的电子、网络媒体区别开来。当然,这种区别只是基于个人认识、学科发展现实水平的理论描述和问题探讨策略,并非人类传播历史实践的人为切割。第三,指明现代出版在人类传播中的时代序列:它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其传播载体——纸张是工业产品,以书报刊为代表的现代出版物的印刷过程是以机械动力大批量的工业化复制过程。
19世纪以来的社会科学发展揭示出,人类群体行为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三个假定领域,人们习惯于把与市场相关联的现象视如经济现象,把与政府决策相关联的现象看作政治现象,而把与心灵状态相关联的现象叫做社会—文化现象。出版行业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共存一并纠结、矛盾乃至冲突的社会领域。出版活动是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三种力量相互作用下的社会文化活动。从更深层意义上说,它是出版资源通过某种制度下的出版人行为转换成更有价值的出版物的实践过程。从出版资源到出版物的转换过程中,有实践主体的创造性、活动形态的专业性、知识和能力要求的专门性,更值得重视和思考的是其中的社会性。出版活动在进行过程之中受到各种社会力量的激励与限制,集中而言是布坎南所说的“通过制度性结构对个体行为进行的调整”[7]30。这种在一定时期一定国度的出版领域存在的制度性结构对当时当地的出版活动的参与者产生有形或无形、直接或间接、正式或非正式的深刻影响,因此,制度性结构成为出版人个体、群体及其活动创造性、专业性、文化思想性的主宰。中国以往的出版理论研究为外在现象、表层假象所蒙蔽,忽略了出版制度结构的存在及其意义,主要研究出版活动的外在的显性的表象,没有深入到决定出版活动成效的内在的隐性的制度结构而轻易断言“出版无学”,今后的出版理论研究不仅要将注意力指向出版活动及其过程,更要集中指向出版活动得以发生并形成的制度结构。
“所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现象都是在特定制度框架内发生的,而且制度对它们的发展历程具有重大影响。”[8]3诺斯说:“重要的是说明经济制度结构,以便有意义地探讨一种经济绩效的动力”[9]14,并把其视为《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的两个基本问题之一。沃勒斯坦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存在一个持续的结构,它在长期(longue durèe)里左右着我们的群体行为——我们的社会生态,我们的文明模式、我们的生产方式。这些结构的运作也存在周期性:经济的扩张和紧缩、政治主题的变换,以及规则发生的文化现象”[10]162。
以上大家针对人类一般活动的理论描述被援引为分析出版活动与制度结构关系的理论前提。既然出版活动是人类活动,以换质位法的逻辑推理不难得出结论:出版活动受制于出版的制度结构。
胡正荣先生对美国包括出版在内的传媒业的考察所得支持这一演绎推导性假定:“即使在市场经济和媒介产业都最为发达的美国,媒介的生存与发展也首先不是由市场决定的,而是由市场规则决定的,即国家有关的公共政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游戏规则’。”[11]204这里的市场规则、游戏规则就是制度。
诺斯曾断言,制度是重要的,出版理论工作者同样需要认识到,出版制度结构是很重要的。在确立了出版活动与出版制度的内在关系视角和方法,并假定出版活动受制于出版的制度结构后,是否可以明确以下两个观点:出版制度和出版资源一样成为出版活动重要的生产要素;出版工作的效果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出版制度绩效,是出版人在出版制度结构中与相关方面展开博弈的结果。
出版活动中有预设的或者说前置的出版制度,是对出版活动的最一般的理论说明,出版实践者无时无刻不切实地感知其存在以及规约力量。值得讨论的是,为何过去30年的出版理论不研究出版制度(更不用说出版制度结构),这对出版学理论建设、出版业的发展产生了并还将产生什么影响?
检视中国过去的出版理论成果,不难发现,大多集中于出版单位的生产供给与读者的购买消费,忽视、忽略了出版制度对出版领域中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的深刻影响。这可能源于:(1)受意识形态影响而相信政府全知全能,无意识地认同或有意识地坚信一个假定:出版制度毋庸置疑地高效、公正、公平。也就是说,因出版制度的意识形态内涵与性质,出版制度“先天”地被假设为出版实践的逻辑前提,并被置于理论探讨之外,出版制度被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出版理论对象中屏蔽出去,认定出版制度安排乃政府所为,非关出版学术。(2)中国出版改革30年的实践进程逐渐质疑了其不可质疑性,逐渐觉悟到真理的假说性,但面对出版制度的复杂结构,现有的出版理论工作者拘于目前的理论工具准备和认知水平,只能犹疑乃至茫然失措。
出版制度研究缺席的影响,可以这样描述:在出版改革走向深入的进程中,出版业有识之士深感出版制度变迁中制度安排的困惑、矛盾、不一致等种种困境,而出版理论界表现出一定意义上的“集体无意识”——对出版活动的研究中没有制度的维度,在理论对象的认定中没有出版制度的存在,从而对转型期的出版制度及变迁“无知”或者说不深入,进而导致在出版改革的制度安排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丧失话语权,沦为对政府官员话语的随声附和与解释。
(二)出版制度结构的意义与内涵
1.出版制度结构的意义
出版制度结构是对科斯“生产的制度结构”的移用。科斯1991年获诺贝尔奖的演讲就以《生产的制度结构》为题。他说:“对于经济体系的运转来说,生产的制度结构是重要的。”“我的梦想就是建立一种能使我们对生产的制度结构的决定因素进行分析的理论。”[12]350,301移用目的有二:以出版制度结构替代出版体制,以更理论化的范畴标示其的结构化内涵;尝试借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基本研究范式研究中国出版,以求更、清晰解析出版体制的内在结构系统。
笔者主张,制度结构是重要的,其生成方式是群体性的,在认识方法上是可分解的。制度结构在现实社会中整体地运行与为认识制度结构的复杂性、运行机制而对其不同维度、层面的截面式剖析是两个不同概念,前者属于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后者属于对客观世界的主观认识,是逼近客观现象的认识方法。运用一定的方法分解制度结构,并不抹杀其整体性存在。“把体制看成一个整体,强调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8]3是制度范式的基本内容,也是本研究的基本立场。本文主张在认识方法上分解制度结构,并在维护其整体性的基础上尽可能条分缕析。就当前中国出版理论水平而言,提升对中国出版制度变迁的分析水平首先是分析模式的转换,转换的重要方面是,通过对中国出版制度结构的部分拆解和重新组装来认识其整体性和结构化,从而更好地把握出版的制度结构的构成形态与运行规律。
出版制度从属于传媒制度。有学者采取横截面切片的方法解析了传媒制度的三层重叠的静态结构:“依照基本功能,中国传媒制度可以自上而下大致分成三个层面,即宏观管理制度、采编运作制度和经营分配制度。”“位于制度体系顶层的宏观管理制度将‘传媒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奉为圭臬,包括传媒的所有制,传媒与政府的关系,传媒之间的关系等。”“居于中间层的采编运作制度涉及传媒内部业务运作的种种规范和例律,其核心是‘宣传至上’。”“位于底层的经营分配制度是管理传媒的广告、发行等经营活动,以及工资、奖金和福利分配的法规和政策,其基本原则是‘经营服从宣传,级别决定分配’。”[13]在对传媒制度类型分析的基础上再做结构化处理,对认识出版制度结构很有启发,制度实施机制的揭示较为清晰。
总结前述:出版制度结构是出版活动以及由此展开的出版行业、出版产业部门等出版系统的内核。出版活动的周期性、循环性、规则性运动的动力核心在于此,出版体系的演变、出版制度的变迁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的具体进程的变化源于出版制度结构的某一两个制度参数的变化引起制度结构的转型。
2.出版制度结构的内涵
皮亚杰提示:“对于他所发现的结构的存在方式,要在每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里加以说明。”[14]3就中国语境而言,能否结合中国出版业的本质和特征发现出版制度结构,并将其发展为理论分析工具,是出版学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重要课题。
出版制度结构的组成部分。林毅夫指出:“制度结构,它被定义为一个社会中正式的和不正式的制度安排的总和。”[4]378出版制度结构就是指出版领域中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的总和。非正式出版制度是历代出版人在长期实践中积累、形成的不成文规则,它内化于出版人的思想意识之中,是出版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出版价值观念、出版伦理规范、出版道德观念以及相关的意识形态等。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为德国制度学者柯武刚创设的术语。出版业的内在制度是出版从业人员随经验而演化的规则,外在制度则是“外在地设计出来并靠政治行动由上面强加于社会的规则”[15]19,如三审制等。
出版制度结构的形态。出版制度结构是以出版企业—政府为核心,在政府和出版企业之间展开的经济、政治、文化层面(维度)的规约关系。出版界常说的出版者与作者、读者的关系等,都只是在企业与政府关系基础上的衍生关系。出版企业生产什么、为谁生产是受到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制约的。出版制度结构的形态是二元三维的网状立体结构,二元是企业和政府,三维是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
作为企业的出版社和作为政府的出版行政管理机关的矛盾是出版制度结构中的主要矛盾。“经济变迁的动态模型需要把对政府的分析作为模型整体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因为正是政府具体规定并执行了正式规则。”[16]9经济体制决定了这二元核心的重心偏移: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是核心,出版企业遵令完成指令性计划;市场经济体制下,分散决策成为基本制度,企业是核心,政府为其提供服务或指导性建议。目前中国出版业正在进行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艰难转型,还处在从以政府为核心到以企业为主体的转轨、过渡过程中。在这过程中,出版企业家、出版人、政府官员的交往行为是企业与政府之间博弈,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三种力量矛盾冲突的载体,也是力量转化、结构与功能置换的枢纽性关节。要以此为视角审视出版人个人与群体行为,评价其历史使命担当与价值实现。
3.出版制度结构的特征
皮亚杰指出:“结构是一个由种种转换规律组成的体系”,“一个结构包括三个特性: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14]2-3出版制度结构也可如是观。依此描述其特征主要由于皮亚杰的一般理论陈述与作为研究对象的出版制度的对应与契合。
一是整体性。整体性指整体性制度安排。诸多制度经济学家注意到“制度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依赖”,但指称与表述方式有所差异。林毅夫说:“因为制度结构由一个个制度安排构成,所以一个特定制度安排不均衡就意味着整个制度不均衡。许多制度是紧密相关的。一个特定制度的变迁,也将因此引起相关制度安排不均衡。”[4]389“社会中各种制度安排是彼此关联的。不参照社会中其他相关的制度安排,就无法估价某个特定制度安排的效率。”[4]374“最有效的制度是一种函数,尤其是制度结构中其他制度安排的函数”。[4]384青木昌彦继承前人对制度相互依存性的理论观察而命名、称谓为整体性制度安排,其相关表述有:“把制度及其复合体视为均衡现象”[17]22,“经济可认为是由不同域——共用资源、经济和社会交换、组织和政治——混合体组成的”[17]29等,基于此,青木昌彦把“经济中跨域的共时性制度集合称为整体性制度安排(overal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17]28。青木昌彦所撰名著《比较制度分析》的主要贡献就在于:“揭示各种各样的整体性制度安排背后的规律性”[17]29。
二是转换性。转换性指出版“制度之间共时性与历时性相互依存的本质”[17]188。这一描述指向两个方面:其一是结构自身的转换功能。“一项起结构作用的活动,只能包含在一个转换体系里面进行。”[14]7“‘结构’就是要成为一个‘转换’的体系,而不是某个静止的‘形式’。”[14]6“结构从来只是一个转换的体系,不过它的根基是运算系统。所以是有赖于适当工具的预先形成的。”[14]11其二是提议并提示出版理论工作者“从制度关联和制度的互补的角度对制度的相互依存性进行理论概括”[17]19。
制度是一种社会建构。制度范式的“重点是研究具有不同社会功能的各个领域之间的互动关系(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8]3,因而“对于社会功能的不同领域(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之间所发生的交互影响给予了特别的关注”[18]21。这样的“互动关系”既是出版制度结构中转换性特征的具体形态,也是出版理论探讨的焦点与难点。
三是自身调整性。“结构的第三个基本特性是能自己调整,这种自身调整性质带来了结构的守恒性和某种封闭性。”“节奏、调节作用和运算,这些是结构的自身调整或自身守恒作用的三个主要程序。”[14]10,12自身调整性指制度结构由变迁而导致的均衡与适应。青木昌言将其称为“历时的制度互补性”(diachronic 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ly)。“如果存在一种互补的制度,或者在另一领域发生了同方向的变化,那么在这两个领域之间的相互强化就会为新制度的建立创造出一种契机来。通过这种机制,博弈形式在参数形式上的外生变化,比如说对政策进行系统的改革,可以传播并扩大其影响,有时会产生一个全新的制度安排。”[19]42
制度变迁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社会转型的最理想模式是提出一揽子方案,同时段同步调完成经济、政治、文化三个领域的转型,但人类受有限理性制约,不可能拿出理想的一揽子方案;且政治、经济、文化各有其行动逻辑,在转型速度、演进道路等方面各有所不同,因而造成整体转型的部分之间呈前因后果式的链环,构成转型中常见的互动而不同步、时空错位的非同步现象。有学者主张“多维度考察转型”,多维度诚然有助于在单个维度上认识的深入,但在各个维度的深入考察之后如何综合呢?如何化“多”为“一”呢?在分解之后又如何组合呢?
既然出版领域存在各有其中心和逻辑的三种力量,这三种力量又是如何关联的呢?有人提问“什么是经济变革所需的政治条件?而什么又是政治变革所需的经济条件?”[18]24这样整体性地探讨出版问题应该成为出版制度结构研究的重要关注点。
(三)刘杲命题1分析
刘杲命题1的话语形态为:出版改革“关键在于精神文明建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语出刘杲2004年7月在中国编辑学会年会发言《关键在于精神文明建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出版业改革和发展必须坚持的正确指导思想,也是出版管理必须坚持的正确的指导思想。”[20]162
1.命题的观念史追溯
刘杲命题1是自觉的实践命题。称其自觉,因其提出有理论动机和思考过程。称其为实践命题,因它源于中国出版改革30年的历史实践,历史借这位沉思的出版老人说出了对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的必然性要求。对它的解析既需要在过去和当下的实践中进一步求索乃至完善,更需要在理论层面上清理其内在要素及其关系。刘杲自白:“我关心出版业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因为指导思想是行为的依据,成败的关键。我们在认识上和实践上的某些曲折,大多源于对正确指导思想的某种偏离。出版业改革和发展的顺利推进,要求我们大家都努力坚持中央提出的正确的指导思想。”[20]169 1997年7月,他指出国家出版行政管理部门“不足之处在于指导思想的把握不够全面”[20]194。巢峰1998年撰文《出版改革与造大船》疾呼:“指导思想上的模糊和碰撞,缺乏明确的战略目标,是出版业改革、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21]168据此可以基本把握这一命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深化出版改革,包括制度创新、机制创新在内的全部工作,都要贯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这条红线。这是出版改革的指导思想,也是对出版改革的基本要求。这是出版改革的特点和难点,也是出版改革成败的关键。”[21]164
刘杲命题1有其形成过程。受启发于1994年初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在当年7月全国编辑理论研讨会和11月全国出版科学研讨会上,刘杲都就此做系统发言。1995年3月,他在全国政协八届三次会议上书面发言《关于出版改革总提法的建议》:“能不能设想,出版改革要逐步建立新的出版体制,以多出好书为目标,以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为基本特征,一个目标、两个基本特征的出版体制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是完整的指导思想”[22]556。此为该命题的完整表达形式。后来所说出版改革关键在精神文明建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是其浓缩和发展。
出版改革的核心对象是出版体制。巢峰认为,“我国出版业始终没有建立起既适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又适应社会主义物质文明要求的市场经济体制。十年前如此,现在仍然如此”[23]。可见刘杲命题1的意义。
2.命题的隐喻分析
刘杲命题1以“精神文明建设”合指文化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构成隐喻。他1992年明确指出:“出版体制改革还要同政治体制改革相适应。”[22]499但他后来回避出版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矛盾关系,2003年撰就并引起较大反响的《出版: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② 就避而不谈出版领域的政治问题,这是否只是行文与写作的技巧?刘杲命题1中消解政治内涵的话语本身就耐人寻味,是否表明他背上了沉重的意识形态包袱?出版与政治的关系至少有政治体制决定出版体制,出版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服务政治思想工作两个方面。“文革”后期强调出版为政治服务,出版领域因而成为重灾区,那诚然让人后怕。周蔚华后来明确表述为:“我们要建立的是适应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要求的全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出版体制”[5]305。这一表述更为明朗。
3.命题探讨的可能维度与层次
刘杲命题1包含了对出版制度结构这一出版理论重要范畴的期盼。其理论意义或者说核心价值在于提示出版界,启发出版人深刻关注出版改革的主要矛盾关系,提示、引导人们思考出版领域中政治、经济、文化三股力量及其关系。出版理论界对此没有继续推进,诚为遗憾。回答刘杲命题1是一个较为艰难的理论任务,对其求证讨论可有多个层面和维度。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相互交错的中国出版改革实践来看,该命题是否存在?未来的出版改革是否存在着和谐一致的价值观和价值取向的可能区间?如果存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三股力量的交集点在哪里?平衡点在哪里?是在何种程度上,在何种条件下以何种结构形式与运行机制存在?也就是说,刘杲命题1存在的逻辑前提和基础是什么?如何将刘杲命题1在出版改革实践中具体化操作化?如果该命题不存在,某种非同步和谐的单一决定力量对出版改革、出版文化生态将会产生什么影响?进而出版改革的目标该如何预设?改革进程将如何安排?对出版改革的绩效将如何期盼?
三、出版学与相邻学科的关系
(一)对本文所说相关学科的说明
本文所说的出版学相关学科主要指编辑学、新闻学和传播学。杜敏曾主张编辑传播学[24],李新祥主张出版传播学,还有人主张文化传播学[25],似乎应和者不是太多,姑不置论。近几年来,有一部分同行称名和使用编辑出版学。笔者认为编辑出版学是在1997年全国高校本科专业目录调整时由行政性主导而临时拼凑的本科专业名称,并不具有学科范式意义。在我的不一定准确的记忆中,当时按教育部要求要将图书出版发行学和编辑学两个专业或保留一个,或压缩成一个。武汉大学有教授提议定名出版学,另有其他大学教授提议保留编辑学,有关人士便决议称名编辑出版学,获知此名,有年轻教授提议在更大范围内讨论,未被采纳。编辑出版学作为专业名称颁布之前并未在出版学界、出版教育界展开较为严肃、充分的研讨,由教育行政部门颁布赋予了它本科学历教育的合法性,但未必有学科合法性,它自身概念重叠且概念结构关系指代不明,并非较严格的学科概念,只增加了编辑学、出版学的相互关系紊乱。随着出版专业教育的发展、出版理论研究的深入,其负面影响凸显。其一,引起培养目标到底是编辑还是出版的犹疑,并进而对核心课程设置产生影响。其二,不少研究者自觉不自觉地认为“‘编辑出版学’代表了目前这一领域的正式学科建制”[26],进而以此为前提撰著著作、撰写教材,在笔者看来,是出版学科发展的深重遗憾。
对出版学与相邻学科边界问题的探讨,理想的话语形态是从知识谱系的层面或角度指陈、描述出版学与相邻学科的结构关系,即其上下层次、前后位序、包含与交叉等,笔者难以置喙。王振铎先生在《编辑学原理论》中有专节论述“编辑学与出版学”,靳青万先生在《编辑学基本原理》中有专节论述“编辑学与新闻学、传播学的关系”,阙道隆先生2001年完成的《编辑学理论纲要》中以节题“编辑学的性质和学科地位”概要言说了“编辑学与出版学、新闻学、大众传播学既有交叉,又有区别”[27]149。诚然富有见地给人启发,值得商讨的是:这种学科关系的宏大叙事到底该以怎样的言路才能以小搏大,以短章说长篇,才能在学科理性上显示出价值中立,才能将主观的个人理解甚至想象最小化?面对一个广博、深邃的关涉人类传播的知识对象,不能不要求言说者保持学科历史、理论工具、话语逻辑等方面的敬畏与持重。
基于前述理由,本文悬置对出版学与相邻学科知识谱系的清理,而将重心指向出版学边界模糊的路径分析,重在揭示导致出版学边界模糊的路径依赖,也就是说,要试图弄清楚到底是哪些主客观因素影响、导致了对出版学边界的模糊认识。从理论上说,既有知识对象上交叉重叠的客观性因素,也有认识主体的主观局限性因素。因而,探讨需要基于当前学科认识水平的共时态的横截面分析,更需要历时态的出版学学术史的方法自觉。这种自觉不应只停留在撰著出版时间、成果分类等外在表象描述,更应以发生学的视角和方法探究学科启动的意识形态根源;既要认同过去30年中,以编辑学为代表的理论性研究成果,以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为代表的人才培养实绩,更要对与此相关并构成出版学学科发展的路径依赖予以批判和扬弃。中国社会转型的加速已经并正在强力雕塑着中国出版结构转型,中国出版的结构转型要求新世纪的学人杠起出版学科的旗帜,形成出版学科历史转折而不是直线延伸前辈的足迹。
基于前述逻辑前提,出版学与相邻学科的关系是否可以这样描述:从学科内在结构关系着眼,传播学是出版学的上位学科;从学科发展历史着眼,新闻学是出版学的先行学科;从学科开拓程度和目前现实认知水平,或许可以认同一些专家提出的编辑学是出版学的平行交叉学科。
(二)“胡乔木烙印”的必然性与内涵
有专家指出:“20年前,我国著名理论家胡乔木连续三次向教育部建议在高校试办编辑出版专业,这一提议对推动编辑出版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28]1“胡乔木烙印”正是对这一历史功绩的肯定。在认同“胡乔木烙印”的前提下,进一步提出“胡乔木假设”或许有助于相应学科关系认识的深化细化。在笔者看来,这是出版学学术史分析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解析出版学边界模糊的重点。胡乔木倡导有关编辑的理论研究与人才培养是出版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是他个人学识、所处社会地位决定了的必然行为,其中既有他个人的思考,也有管理部门的意志,这就是其历史复杂性所在。支持“胡乔木烙印”历史必然性与复杂性的观点和材料如下:
关心、推动出版人才培养是胡乔木建国后出版管理思想的自然延伸。1951年8月,胡乔木在第一届全国出版行政会议上做《改进出版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其第四节《党的组织对出版工作应怎样领导》说:“党也要负责领导教育和培养出版工作的干部的工作……学校中也没有这样一系,应该有这一系。应该包括出版业中各项的业务,在这系中学习的学生还应当受到严格的训练。现在应当筹备在大学中设立这样的系,还要设立训练班”[29]464。这成为他新时期关注大学相关专业设置的思想基础。
出版人才培养制度化是出版业发展的必然要求,胡乔木顺应历史要求将呼吁变成党和政府的意志,有效地推动了高校编辑学专业的设置,从而积极影响了高校出版人才培养的制度化发展。从披露材料看,胡乔木最早关注编辑教育在1981年。当年12月,中央统战部将民进中央常务委员会《对出版工作的建议》上报中共中央,胡耀邦、胡乔木、习仲勋等人都有批示。胡乔木批示说:“民进的这个建议我看了一遍,认为调查考虑得比较周到。总的看来值得采纳”。[30]110民进中央建议中说:“要有计划地培养编辑人员。国家出版局应商同教育部与若干大专院校共同研究,在某些系内把培养编辑人员作为他们的任务,定期为出版机构的编辑队伍输送新生力量。”[30]113人才培养的基础是知识体系,出版科学理论研究的兴起是改革开放后出版业发展的必然要求,胡乔木以其洞察和地位顺应了这一历史趋势。
袁亮回忆:“1984年3月6日、6月7日和7月25日,胡乔木同志连续三次同出版部门和教育部门负责人谈话及写信指出,要在大学设立编辑专业,要研究编辑学。”[2]702 1984年11月2日,胡乔木在接见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代表时的谈话中说:“编辑工作人员的缺乏是个很突出的问题,所以要在大学新闻系或者中文系办编辑专业。”[29]373 1986年1月4日,胡乔木在《同浙江出版部门负责人的谈话》中说:“大学办出版系,是我的建议。不要办那么多的新闻系,要办出版系。出版是个很大的领域,但很薄弱。全国有五十多个新闻系,不需要这么多。有的对编辑、卖书兴趣不那么浓。杭大办出版系好,早点定下来。”[29]539
“胡乔木烙印”的文本形态集中表现在他1984年7月致教育部信。“胡乔木烙印”的复杂性在于认同并如何区分胡信中的中央政府意志与胡的个人意见。中央政府意见体现于《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中央决定在前,胡信在后,因而胡信只是中央决定的落实措施之一。而中央决定又是对当时出版业现实情况反复调研、思考的结果,既体现政府意志,也反映了相当一部分出版家、出版工作者的要求。这样的钩沉应该说有助于理解胡信的意义与价值。
“胡乔木烙印”首先指从胡愈之倡议出版专业到胡乔木命名编辑学专业的名称转换。胡愈之1979年12月20日在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祝词中说:“在大学应该有出版专业”[31]380。不同的是,胡愈之提议出版专业在前,胡乔木提议编辑学专业在后,胡愈之作为一个民主党派的老人,建议没有被采纳,胡乔木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其建议在政府推动下贯彻执行。就此而言,转换既成为“胡乔木烙印”的关键内容,也是理解出版学与编辑学关系的关键节点。胡乔木改换的只是专业名称,“两胡”有某种一致性。胡愈之说:“实际上出版工作者同新闻工作者一样,是一种专业,并不是每一个出版工作者都可以做新闻工作,也并不是每一个新闻工作者都能做出版工作。因为出版工作、编辑工作有它的一个特点。”[31]379胡乔木指出“编辑学在中国确无此种书籍(编辑之为学,非一般基础课学得好即能胜任,此点姑不置论)”[29]530,强调专业性、专门性,“两胡”相同。比较分析“两胡”意见的一致性与专业名称的差异性是有意义的,是解开相关问题的节点。胡愈之的出版从业经历主要是“五四”以后在商务印书馆等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出版机构,由此经验积累而形成出版思想。胡乔木的出版从业经历主要是在延安主编《中国青年》,协助毛泽东编选《六大以来》等重要历史文献,其出版经验积累主要源于此。“两胡”的不同经历是否决定了其对大学设立出版专业还是编辑学专业的分歧?是否可以这样推断,胡乔木的出版从业经历、在计划经济时代主管意识形态决定了他不可能提倡出版学?如果这样的推断成立,是否又可以进一步推断,在市场经济中,在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出版领域更需要的是出版学?
“胡乔木烙印”其次指编辑或编辑学研究对象从出版领域的系统性切割。这里所说的系统性切割,主要指离开出版系统讨论编辑和编辑学的学术思维路线。需要讨论从出版专业到编辑学专业转换的思想意识根源与学科发展的客观历史效果。
这里所说的思想意识根源就是编辑工作中心论。这种割裂编辑与出版关系的话语形态有两个典型形式。其一是胡乔木关于“编辑是独立的学问”的表述。1990年,胡乔木说:“编辑是编辑,出版是出版,出版离不了编辑,但编辑是独立的学问。”[32]编辑诚然可以想象为“独立的学问”,但它作为“独立的学问”而存在的社会基础和理论前提是什么?如果脱离社会基础和理论前提来认证“编辑是独立的学问”,那“独立”的含义是什么?在笔者看来这是需要回答的。其二是编辑学的英文译法。林穗芳先生认为:“在国际范围内,‘编辑学’这个术语很可能是我们首先使用的。按照国际术语学的命名规则,似可以考虑使用redactology(英语形式)或redactologie(法语形式)作为编辑学的国际用语,redact一词在欧美主要语言中都只有‘编辑’而无出版的意思,不会有歧义。”[33]这一译法为中国编辑学会正式采用。
编辑工作中心论见于《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编辑工作是整个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是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又是艰苦细致的创造性劳动。”[1]38“编辑工作是整个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到底该如何认识其逻辑前提,如何估量它所包含的普适意义?尽管胡愈之也说“出版工作主要的是出版社,是编辑工作”[31]378。这陈述提出于1983年,贯彻和推广则在此后,1985年出版市场形态变化、1992年出版业态变化后,对它到底该如何深化认识,出版理论界似乎并没有给出有说服力的答案。有些出版理论人士是否由编辑工作在出版工作中的中心地位出发,采取类似逻辑学中的换质法,进而推导出编辑学在出版理论中也处于中心地位?达到底是假设性的,还是实在性的,个别的还是较为普遍的,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求证。刘杲重视出版理论,且德高望重。他1996年说:“理论问题是根本问题。我们在出版方面的理论准备显然不足。因此加强出版理论的研究自然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198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加强出版、印刷、发行的科研工作’。这个指示及时地有力地推动了出版理论研究的开展。”[34]546 1994年12月在中国编辑学会青年编辑研究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刘杲说:“编辑理论研究以及编辑学的建立,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一项带有根本性的工作”[34]494。刘杲在这里将出版理论研究、出版学置换为编辑理论研究、编辑学,置换的潜意识或者说无意识就是编辑工作中心论导致了编辑学研究中心论。
编辑工作中心论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理论命题,历史地深层地看,有丰富的出版体制、出版类型意义。这一陈述与30年来编辑学的单科突进有无关联,有什么关联?笔者对近30年中国出版理论发展的基本假定之一是重编辑学轻出版学,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到底是哪些影响因素以怎样的结构关系导致了这一结果?编辑学列入本科专业目录进而学科建设制度化,可以说是影响因素之一,是否还有别的因素?比如高校学报编辑人员作为出版理论研究的主力军,学科队伍的知识结构、从业经历是否局限了他们对出版学功能、体系的认知与追求,出版理论界长期受计划经济时代出版业态的影响,在潜意识中存在“编辑有学”、“出版无学”的理论假设,或者说,编辑学单科突进、出版学非同步发展的学术现实有意无意地强化了“编辑有学”、“出版无学”的思想意识。而这种意识到底是学术路径所致还是某种思想意识所致?
从编辑工作中心论到出版理论研究中编辑学研究中心论,在诸多出版理论工作者中或许是潜意识的复制与拷贝。值得质疑的是,出版工作以编辑工作为中心,即使成立也是属于实践领域,而出版理论研究属于认识范畴,认识方式与实践方式该如此简单对接吗?简单对接的历史效果是中国出版理论界重编辑学轻出版学,出版理论的话语形态和学术操作都将出版活动从出版领域内广泛而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割裂开来,脱离出版领域中社会关系的整体性,偏向单维地研究编辑活动或出版活动,整体性认知方法的缺乏难免不使出版理论话语成为变形的哈哈镜,难有全面、真实地反映出版世界并引导人们认知出版世界的功能。
皮亚杰说:“一切有关社会研究的形式,不管它们多么不同,都是要导向结构主义的;因为社会性的整体或‘子整体’都从一开始就非作为整体来看不可”。[14]83在结构主义理论看来,出版理论研究中的编辑学偏向是否从一开始就留下了致命的缺陷?
检视近30年编辑学理论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围绕编辑工作中心论而展开了两套学术话语。偏重编辑工作的“创造性”、“专业性”者,借以强调其文化创造性,并论证三审制也在各自的审级分别追加了创造元素;偏重编辑工作的“政治性”、“思想性”者,为三审制张本立基,潜话语的核心是强调意识形态安全。简单地判定这两套话语的对错是非无意义,更值得思考的是为何有这样使用同样话语却仔细听来表达不同声音的“二重唱”,这矛盾现象的背后是否有出版制度根源,再进一步,如何认识编辑学、出版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中国的编辑学理论、出版学理论是否有意识形态色彩?如果有,是否要、能否可能去意识形态?在学术探讨的过程中如何借助工具,使用什么工具和方法去认识这两者的关系,在理论形态中以怎样的视角,使用哪些概念与命题来建构,在哪些维度和层次上建构这两者的关系?在笔者看来,这是未来出版学的理论发展难以回避的关键问题。而且,如果局限于人文学科一隅难以提出并回答这些问题。再进一步追问,过去近30年的编辑学、出版学理论研究是否走错了知识谱系?在出版工作中弘扬人文精神与在出版学理论研究中遵循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是两个概念,是两种行为,今后的出版学理论研究是否更应该在社会科学而不是在人文科学的知识体系中进行?
(三)从“胡乔木假设”看学科边界
“胡乔木假设”以“胡乔木烙印”为逻辑前提,进一步推敲、分析一个细节:学科与专业名称选择及其影响。操作方法是,尝试提出两个反设事实:一是假如胡乔木当时倡导传播学;二是假如胡乔木当时倡导出版学。
提出胡乔木假设1,着眼于出版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传播学理论研究始于1940年代,成熟于1960年代,最早提出和形成均在美国。1982年11月,胡乔木任院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由新闻研究所举行中国第一次传播学座谈会,“传播学之父”施拉姆应邀前来讲学。这次座谈会“明确了‘既然传播学是一门新学科,就应当了解、介绍、分析、研究’,并提出了‘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的16字研究方针。”[35]128传播学由此在中国成规模兴起。1983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写的《传播学(简介)》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大陆第一本传播学著作,一经出版立即成为风行一时的普及性读物”[36]。胡乔木的社会地位,当时“反精神污染”的运动决定了他不可能提倡传播学。
提出胡乔木假设2,借以讨论编辑学专业命名、选择及其中长期影响。胡乔木的多次指示使得大学设置编辑学专业,出版人才培养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制度化。它后续的直接影响是,1992年10月成立的中国编辑学会以胡乔木信作为前提预设之一,筹划者谋划以中国编辑学会推动编辑学建设,而不是以中国出版学会推进出版学的发展。而中国编辑学会作为学会组织、学科建设制度装置的存在与运行自觉不自觉地加强了编辑学的研究而淡化了出版学的研究。颇有意味的是,筹建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最早叫中国出版发行科学研究所)并从1985年起任副所长的邵益文先生在1992年4月撰文《时代呼唤出版学实践需要出版学》[37],担任中国编辑学会常务副会长后,其学术组织工作的重心、个人研究的重心都在编辑学而不在出版学了。
尽管没有详细材料实证中国编辑学会成立后全国出版科学资源配置、学科力量的转向及其力度,但难以否定转向存在。1986年12月,宋木文在南宁召开的全国出版局(社)长会议中说:“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出版学,建立自己的出版理论体系。出版理论建设的基础差,难度大。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当前,要做出规划,组织力量,分头编写。我们要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在我们这一代,结束‘出版无学’的历史。”何其豪言壮语。宋木文所说(完成学科目标的时间设定、学科建成的评价标准)缺乏学科依据,但提出了一代出版人的学科研究目标,这一指令的贯彻执行,另当别论,由此可以肯定的是,政府一度明确表示了建设出版学推动出版学的理论研究。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导入假设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历史。“胡乔木假设”非为文字游戏,而是借以说明某些难以超越的个人局限、单位局限虽为小概率的偶然事件,但其传导、波及则可能是深远的。出版学学科发展的历史约束促成了、放大了出版制度设计中的有限理性,出版制度设计中知识资源的缺乏严重影响了出版制度绩效。其中的连带关系惊醒出版界认识发展出版学的意义。
出版学发展的滞后集中表现在学科发展的现实水平、学科格局与出版业发展需要错位。传播学是国际通用中国政府也认可的学科,历经60多年已为国际显学,有相对成熟的学科范式。因为胡乔木,中国编辑学的开创者们当初高举编辑学旗帜,编辑学的旗手及其旗手的追随者、旗帜的捍卫者们对传播学始则不屑继则观望目前依然游离。出版学是中国出版业为可持续发展而急需建设的学科。中国社会转型的加速导致出版领域的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矛盾越来越走向潜在冲突,错综复杂的出版媒介现实越来越期望出版学给予认识世界意义上的揭示和发展趋势、方向等方面的提示,出版理论界着力发展的却是编辑学而非出版学,而社科学术界对可以作为学术对象的出版业缺乏应有的关注,使出版学滞后程度更为严重。1980年代编辑学发展初期学缘庞杂,一直没有遵循良好的研究规范,近10年来人文社会科学在问题探讨、理论工具等方面获得较大发展,编辑学研究基本游离于全国社会科学发展之外。这些因素导致出版理论界的主攻方向、学科边界等核心问题一直不清晰,不明确。因经历而近30年来真正较有分量的编辑学理论著作屈指可数,面对转型加速期的整体性、结构性变迁的出版现实,出版理论界中一部分人自以为可作为学科建设成就的编辑理论作为认识工具解释乏力,学界难以自信,出版业界更难以确信。长此以往,令人堪忧。
四、结语与讨论
在申述社会科学与制度创新的关系,具体说是出版学与中国出版改革存在变量关系之后,细致分析出版体制改革与出版学建设和发展的关系,以下命题基本存在:出版学相对编辑学而言的沉寂、清冷,相对出版改革发展的强力需求的供给不足严重制约了出版业的发展。也就是说出版学发展的滞后导致中国出版改革缺乏制度创新的知识资源与智力支持。正如韬奋出版奖获得者周常林所说:“理论上的混乱、经济政策上的失误对出版业性质在认识上的左右摇摆,以致我们出版业不能建立健康的正常的商业生产秩序不能不说也是一个重要原因。”[38]105
出版学的核心是出版制度结构,出版学的学科边界以出版学与相邻学科的关系为限。这只是假设,还需要求证。尤其是出版制度结构中的内在转换,出版制度结构影响出版活动的路径、过程与机理还需要做相当艰苦、细致的理论工作,这里只抛砖引玉。基于传播学的社会科学背景与渊源,基于出版学的核心为制度结构,出版学要以社会科学而不是以人文科学为基本知识谱系,以出版人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的求解、破译、建构成为这一学科知识生产的中心任务,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方面的基本范式成为该学科可以借鉴应该借助的基本理论工具。
出版学是什么,出版学是否成为可能,在笔者看来是两个相互关联的重要问题。至于关联是否如一枚硬币之两面,另当别论。第一个问题关涉出版学之核心与边界,严格说来是期望中的出版学的内在问题;第二个问题讨论出版学与出版业、出版业与当今信息社会等更为广泛而深远的关系,更多的是学科发展的外在关系。在对前述两个问题深具疑虑的同时,一种倾向一种情感似乎越来越坚定:面对愈显衰象颓势,愈益边缘化的出版业,唯有开展直面出版业态现实和出版理论现实的规范性学术研究,才有助于业内外人士清醒,或许才能摸着那个不知到底是悬置还是漂移还是别的什么运动状态的“石头”以到达彼岸。这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内在缘由。文中陈述难免不当,请前辈谅解、同好指正。
收稿日期:2008-06-07
注释:
① 在2005年12月23日高等教育出版社召开的《中国编辑》2006年工作研讨会上,我谈及“新世纪出版学科的发展主题是潜学科的范式创建,学科建设既重要又迫切,应该‘瞄准问题,深度参与’。我们应该想办法梳理两个问题清单,或者说,其实是一个问题清单,即中国出版学科核心问题的清单”(见《中国编辑》2006年第1期《新春寄语》)。
② 发表于《中国编辑》2003年第6期,后收入《出版笔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标签:北京印刷学院论文; 出版学论文; 出版传媒论文; 命题逻辑论文; 印刷行业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文明创建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传媒产业论文; 经济学论文; 印刷厂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