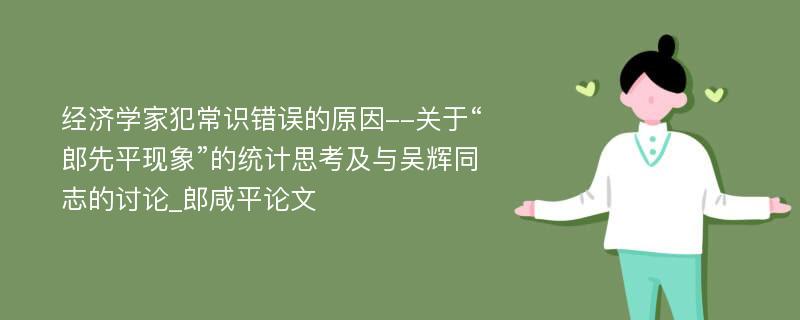
经济学家何以会犯常识性错误——“郎咸平现象”的统计学思考并与伍装同志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常识性论文,统计学论文,并与论文,经济学家论文,郎咸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最近出版的《学术月刊》2004年第12期上发表了署名伍装同志的文章,题为《经济学 家能够超越价值判断吗——兼评郎咸平事件》(以下简称伍文)[1],该文通篇对香港中 文大学经济学教授郎咸平的观点大加赞赏,而对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的观点则一 概否定。当然,对某种学术观点的赞同、否定或批评,完全有各人的学术自由。既然是 学术争端,尤其是经济学方面的争论,就应当用经济学和统计学的方法去分析,去论证 ,用大量的统计数据来说话。然而,伍文将其扩大上升到意识形态和主义之分,这种上 纲上线的推理,不知是否偏离了学术研究的轨迹,而这与作者文章中所讲的“一个真正 的经济学家更应该遵循科学理性分析原则”,又是否自相矛盾?把一项尽管问题复杂, 但毕竟气氛还算和谐轻松的学术争论,升级到了严肃紧张的主义之争,似乎是没有这个 必要的,它只会让人觉得不免有点徒然。下面,就此谈一些粗浅看法和商榷意见。
一、切莫将学术争端扩大化
我们知道,所谓“郎咸平现象”,是郎咸平教授2004年8月在上海复旦大学的一场演讲 中,质疑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在“国退民进”过程中席卷国家财富,从而引发“郎顾 之争”。而张维迎教授加入讨论后,又转化成“郎张之争”,进而引起了中国经济学界 的轰动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在伍文作者的笔下,张维迎教授是典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表,而“在他们 的思想观念中已先验地假定新古典经济学是唯一正确的科学理论,并将其作为中国经济 转型中指导性经济理论,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经济转型唯一可供选择的目 标体制。实际上,他们企图在中国建立一种西方式的资本权力等级制度社会。”他们“ 所说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实际上是指国有企业产权私有化。基于公有制效率必定低于 私有制效率的信念,他们认为产权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以及相应出现的贫 富差距拉大属于正常现象,这是改革必须要付出的成本。”
而另一派又是如何主张的呢?伍文写到,“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坚决反对国有产权的 私有化道路,反对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反对权钱交易的寻租行为 。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基于‘公有制未必是低效率’的价值判断,认为中国的经济改 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市场经济体制,而不是通过 经济改革转向西方式的市场经济体制;坚持以国有经济为主导、以公有制为主的多元化 所有制结构;坚持公平与效率统一。应该承认,这是一种基于中国国情的正确的价值判 断。”
在伍文作者看来,“就国有企业改革来说,基于两种不同的价值判断。中国新自由主 义经济学和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改革路径选择和目标体制选择上都存在着根本的区别 。两者争论的核心问题体现在国有企业的改革路径和目标制度。”伍文指出:“郎咸平 事件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学术争鸣,而是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 之争,它甚至是关系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方向和目标制度选择的争论 。”对于国退民进、MBO,“郎教授指出这是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而“新自由主义 经济学者则称这些人为现代企业家,提出这些人是在创造财富而不是瓜分财富”(张维 迎的话)。
那么,被作者推崇备至的郎咸平教授又如何定位呢?这位作者没有明说,只是这样表述 :“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将郎咸平教授划归为某种经济学派,但郎教授‘说真话’的行 为却体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学术良知。”然而,事实上,作者通篇大 量的论述,包括引证的籍以支撑“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材料,均出自这位“说真话 ”的郎教授之口。在伍文的字里行间所暗含的,郎咸平教授严然是一位“新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作者之所以没有“简单地将郎咸平教授划归”,不知是否觉得还 应加上“伟大的”、“杰出的”,或“大师”之类的词语,才显得不那么“简单”,才 显得隆重?
其实,稍了解经济学识、经济学界和经济学家基本状况的人,都不会把一个台湾生长 、美国求学、香港就职的经济学教授定义为中国“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一个在“ 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长期熏陶的学者,已年近半百,只是近几年来,偶尔登 上中国大陆作一些学术交流或讲学,怎么会如此之快地被感化,摇身一变变成了“新马 克思主义经济学派”了呢?
这位仅凭“郎教授‘说真话’的行为”而一厢情愿地把郎咸平教授拉进“新马克思主 义经济学派”的作者,从郎咸平教授身上“体现”的“社会责任感和学术良知”,还发 现了什么珍贵的“价值”和“意义”呢?伍文的结尾是这样写的,“经济学家的社会责 任感体现在他的理论应当为社会公众的利益服务,经济学家的学术良知体现在他敢于坚 持真理,不说假话、不说违心的话,只尊重客观事实和科学逻辑。郎咸平事件的意义在 于,它提醒人们保护国有资产的紧迫性和所谓‘国退民进’过程中极端的社会不公正性 ,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到了呼唤经济学家良心的时候了”。文章似乎“暗含着”这样的意 思:以张维迎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你们本在中国大陆生长,接受马克思 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多年,“仅从一己私利出发来分析问题”(尚不知 伍文有何证据?),却在今天国企改革问题上失去了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学术良知”, 你们的良心到哪里去了?你们还不如一个台湾生长、留美归来、定居香港的属于资本主 义社会的郎咸平教授,“郎教授‘说真话’的行为却体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应有的社会责 任感和学术良知,”而这正是“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天然所具有的品格。你看人家 郎教授多么有良心!
在“郎顾之争”中,郎咸平教授声称,他决不畏惧强势,绝不容许顾雏军以威胁口吻 发律师函来践踏以研究为本的学术自由风气,誓言坚决保护国有资产和中小股民利益, 为弱势群体代言。这种学风,这种精神,当然难能可贵,并且可敬可佩。的确,精明的 学者自然懂得,高举代言“弱势群体”旗号更能打动人心,更能吸引眼球。
显然,对于国企改革,专家学者的意见的确非常重要,但不能只偏听偏信某一位学者 的意见。再著名、再伟大的学者,即便是像马克思这样的学术巨人——如果他老人家能 活到今天,恐怕也不可能由他开一张药方,便马上药到病除。另外,也没有必要将学术 问题例如经济学的一些问题意识形态化。务实,实事求是的精神是最重要的。口号终究 不能当饭吃。郎咸平也好,张维迎也好,他们都只是学者。对学术问题的讨论争鸣是非 常正常且非常必要的。没有必要将他们分为“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和“新自由主义 经济学派”。并且,不仅“不能简单地将郎咸平教授划归为某种经济学派”,尤其“不 能简单地将郎咸平教授划归为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
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且不说历史上各轮阶级斗争刀光剑影,生灵涂炭,至今令 人胆寒,令人生畏;即便新中国成立后,在那个所谓史无前例的时期,那种动辄针锋相 对,甚至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给人们留下的沉痛教训,不也是 太多,太深刻吗?当今中国,谁还愿意“重复昨天的故事”?再去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 、思想斗争?再说,现在回过头来看,过去搞的两种路线、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 ,孰是孰非?邓小平曾是中国“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二号人物(仅次于 刘少奇),后来不是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吗?他还是共和国的党政军第二代领导 核心呢!而被成“右派”的朱镕基,后来不是也成了共和国的总理吗?邓小平在接见外宾 时讲过,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还不够格。他的意思是说,现在搞马恩当年设想的社会 主义,条件还远远不够。所以,他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有一句言简意 赅,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他还有一句经典语言 :发展是硬道理!
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将“郎顾之争”,“郎张之争”上升到什么意识形态的高度;也 没有必要将张维迎、郎咸平两位教授划归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和“新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派”;更没有必要把不同学术观点之争拔高到“它甚至是关系到中国经济体制改 革的社会主义性质、方向和目标制度选择的争论”。
作为学者,在学术探讨上,学术观点的不同甚至有严重分歧,都是正常的。每一个学 者,在治学方面,都会有自己的学术个性,学术风格。从观察问题的角度,研究方法, 思维方式,到学术观点,语言文字表述,讲话风格等,都会有所不同,有所区别。在学 术领域,甚至必须提倡观点交锋,思想碰撞。只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上才能多 出成果,出好成果;才能有所突破,有所创新。从而,也才能为经济改革献出良策。
二、科学研究与统计数据
郎咸平事件的主角,除了郎咸平,还有顾雏军和张维迎。首先是“郎顾之争”,之后 才是“郎张之争”。而这个“郎张之争”,被伍文归纳为“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与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之间的争论。伍文开宗明义地指出:“在中国经济改革尤其是 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香港中文大学郎咸平教授大胆地揭露了在中国国有企业‘ 国退民进’或产权制度改革中所出现的‘瓜分国有资产’、‘官商勾结造成国有资产大 量流失’等问题,并提出‘私营经济未必比国有经济好’、‘国有经济未必就低效率’ 等命题,引起中国经济学界、官方和公众的广泛关注。”这些,也都是伍文对郎教授高 论广泛关注的基本内容。
其实,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弄清楚:首先,郎教授“大胆地揭露了”的“问题”,究 竟是学术问题,还是法律意义上的有真凭实据的铁的事实。其次,他提出的“两个未必 ”的命题,究竟是大量统计数据严密分析的总体结论性描述,还是个别现象或个案分析 ,抑或是科学探讨意义上的假设。第三,郎教授据此给出的结论:MBO叫停,产权改革 叫停,“停止以民营化为导向的产权改革”,是否科学,是否可信可取,是否可以采纳 。
所谓郎教授“大胆地揭露了”的“问题”,在这场“郎顾之争”中,郎咸平教授本人 声明,这是学术研究,决不道歉!学术尊严不容践踏!这也就是说,它并非是法律意义上 的有真凭实据的铁的事实。当然,谁都不能否认,在“国退民进”过程中,国有资产流 失的现象是存在的。多年以来,各地报纸均有报道此类事件。而不是像伍文所说,是“ 郎咸平教授大量地揭露了在中国国有企业‘国退民进’或产权制度改革中所出现的‘瓜 分国有资产’、‘官商勾结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等问题”。
那么,如何看待郎咸平教授提出的“私营经济未必比国有经济好”、“国有经济未必 就低效率”的命题呢?伍文对郎教授的“两个未必”的命题当然是表示赞同的。并且, 还就“国有企业为什么要存在”进行了研究,从“国有经济与政府的主导作用”、“国 有经济体现公众的意志和代表公共利益”、“国有经济具有私有经济所不具备的效率和 公平功能”三个方面,论证了“有其必要性和客观必然性”。同时,还指出:“与国有 经济相比,私有经济具有诸多缺陷”。当然,对这些缺陷的分析,是引用的马克思早在 《资本论》中就“曾深刻地剖析了”的经典语言。不过,这些大量篇幅(占文章1/3强) 的分析论证,竟未用一个数据(当然,在伍文全篇也竟未发现任何数据——引文编号除 外)!也就是说,全是“定性分析”,而没有什么“定量分析”。
关于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张维迎教授认为,“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可能存在着国 有资产流失,但是我强调的是,这个总体过程是创造财富的过程而不是瓜分财富的过程 。”他指出:“现在很多人还是抱着这样的推理——任何交易,只要买的人赚钱了,卖 的人一定吃亏了,国有企业卖给私人,如果私人赚钱了,那么国家一定是吃亏的。实际 上,交易是双赢的过程”[2]。他还说,“一个企业的效率只能通过市场竞争来检验。 如在原来国有条件下生存不下了,市场额不断缩小,而卖给民营企业,它的市场份额不 断扩大,营业额不断增长,国家的税收不断增加,你怎么能说这种改革不对呢?”[3]笔 者曾在《统计与决策》2004年第12期上撰文提到:中国有一种奇特的现象,许多国有企 业资不抵债,惨淡经营,甚至严重亏损,多年无人问津,不得已而拍卖转让。一旦被民 营企业老板收购后,起死回生,有了利税,则马上又有人站出来说话:“这是国有资产 流失”!好像拍卖之前的任何亏损或损失,不能叫“流失”,拍卖之后,尽管资产变了 现,在买者那里被盘活或重新增殖了,就要被称为“流失”。在后者苦心经营下,增加 了社会产品,增加了社会就业,增加了国家税收,这些似乎被视而不见。而老板最后的 利润,哪怕是很少(即便是很多,但它将继续转入投资,用于扩大再生产),对此,有些 人也会红眼。当然,至于交易过程中的猫腻,那是我们的管理漏洞问题,这与交易的游 戏无关,总之,不能将收购者的收益与国有资产流失划上等号[4]。
据统计,截止2003年底全国非公有制经济已占GDP的60%以上。既然民营经济或非公有 制经济已由“尾巴”、“补充”逐步变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然 我们现在提出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或非公有制经济;既然许多国有企业资不抵债,惨淡 经营,甚至严重亏损,那么,将它拍卖,使它起死回生,我们为何还要老是说什么“流 失”呢?我们千万别忘记:民营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民营企业家,如今早已不是什么 “要割掉的尾巴”,不是什么“异己力量”!
我们知道,郎咸平教授有一个独特的论点:国企效率比民企好。“好的公司基本上都 是国有企业”。郎先生以自己所做的数据说:“我发现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国有企业跟香 港本地的家族企业相比,……每单位资产创造市场价值国有企业是1.113倍,民营企业 是0.97倍,所以以这个数字来看国有企业比较好。”但不知他有没有发现,这些在香港 上市的国企多为垄断性的。所以,二者没有可比性。此外,中国的上市公司,尤其是在 香港的上市公司,占企业总数的比重太小,它并不能反映中国企业的整体面貌。勿庸置 疑,这些恐怕都属于统计学、经济学的常识。
《博览群书》杂志2004年第12期发表了署名张晓群的一篇题为《国有资产要不要转换 及如何转换》的文章,文中写到:今天,国有企业效益低下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20 03年1月3日《中国经济时报》报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说:国有工业占 工业总资产的一半,占总工业贷款的2/3,却只创造了工业总产值的1/3。这种局面长期 不改变,必将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中国企业家联合会和中国企业家协会合作出 的“2004中国企业500强”报告显示,在资产利润率方面,500强中的民营企业和港台外 资企业,分别比500强中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高出5.57倍和10.19倍。更重要的是,50 0强中的这些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大多集中在行政垄断行业,比如电信、钢铁、石油、 电力和石化等,它们能赚钱,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行政禁止民营企业进入这些领域得来的 ,没有得天独厚的行政资源,实在难以说它们就能赚钱。张晓群在文中引用了大量的统 计数据,说明不仅仅是中国的国有企业效益低下,其他国家也是一样。“其他各国的实 践已经充分证明:国有企业效益低下是世界性的普遍现象”[3]。
对于这些道理,郎咸平教授也一定明白,他自己也曾说过:“人们的思维误区,总认 为一些老总创造国企奇迹,其实不然。实际上,是政府和社会给了他们机会,无论是资 金支持,还是政策倾斜,都为他们营造了民营企业所不可能面对的优质环境”。可是, 当他要论证MBO叫停,产权改革叫停,“停止以民营化为导向的产权改革”之时,则又 眼睛一闭:国企效率比民企好。“好的公司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
说“私营经济未必比国有经济好”、“国有经济未必就低效率”,无异于说“广东人 未必就比四川人有钱”、“成都人未必就比深圳人节奏慢”。一位哲人说过,天下最容 易的事,莫过于胡乱抓两个材料来证明某个问题。虽说“不到广东,不知道自己的钱少 ”是广为流传的顺口溜名言,但你在四川找出几个(甚至几十个或更多)千万富翁,与广 东的打工一簇相比,当然是这些四川人比这些广东人有钱。但你不能因此而得出,“广 东人未必就比四川人有钱”。同样的道理,你用一些上市的国有企业甚至仅是在香港上 市的国有企业,来与相对应的民营企业比,从而得出“私营经济未必比国有经济好”、 “国有经济未必就低效率”。或者,你干脆目标锁定几个著名企业:格林柯尔、海尔、 TCL……,来证明MBO有问题、国退民进有问题、国企改革有问题……必须停止国企改革 。然而,我们不能以偏概全,不能“连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泼掉”。
对同一问题,给出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答案,且还是用数据说话?!以上这些,当然称 不上是弄虚作假。但我们也并不希望出现弄巧成拙,更不希望弄假成真。这里,我们只 是要问:郎教授的上述“独立研究”方法,与伍文中所讲的“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更应 该遵循科学理性分析原则”是否相符合呢?郎先生称得上一心为公、学术尊严不容侵犯 的学者吗?其“敢于坚持真理,不说假话、不说违心的话”的“学术良知”又如何体现 呢?
三、学者风范与理性思雄
张晓群在《国有资产要不要转换及如何转换》一文中通过大量的事实、数据和论述, 对郎咸平的观点和学风提出了质疑,称郎咸平指责的三家公司:海尔、TCL和格林柯尔 ,对于真正要讨论的“国企改革”,没有代表性。郎咸平是在整体上论述国企改革的, 他就必须在统计学意义上描述所有国企(比如说100万家)的整体风貌,他找的例子也应 该是体现这一统计学意义的典型样本。打个比方,他要给我们描述今天台湾青年的总体 恋爱状况,为此找了三对恋人做例子,结果他找了一对香港人、一对台湾同性恋者、还 有一对不知所云。为什么要找这三对完全不能代表台湾青年总体恋爱状况的恋人做例子 ?就因为这三对恋人都是明星?能吸引眼球?“所以说郎咸平经常自相矛盾、思维混乱。 他还自称财务方面是‘亚洲第一’,有这种思维混乱的‘亚洲第一’吗?如果谈动机的 话,郎咸平对公平的大声疾呼,更多地是出于哗众取宠、博取眼球;他在接受《南方都 市报》记者采访时,十分可爱地、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出名后的喜悦之情:‘我现在真是 在内地大大地出名了。’他之所以会提出一些荒谬的、自相矛盾的观点,正是因为这些 观点能够耸人听闻;至于这些观点对不对、有多少理据、相互间是否连贯一致,那是次 要的,关键是要一鸣惊人,让自己的大名在短时间内家喻户晓”[3]。
随心所欲,违背随机抽样的统计科学原理,主观地选几个样本资料,去“推导”出总 体结论。郎咸平教授这种“独立研究”方法,且不说与伍文中所提到的“更应该遵循科 学理性分析原则”、“只尊重客观事实和科学逻辑”的要求相去甚远,恐怕甚至有悖于 一般统计分析和经济分析的常识。这似乎类似人们常说的:一个极其聪明的人,犯了一 个极其低级的错误。
当然,其动机或许是好的,是出于一片好心,是爱国心切,是“为弱势群体代言”, 自觉不自觉地、一不小心而“出了小小漏洞”。但君不知,在科学研究领域,有些小小 的差错或误差,甚至往往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或曰“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对于“郎顾之争”问题,国务院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先生表示,“郎咸平教授说科 龙在整个转制过程中,出现了新所有者瓜分或者侵吞国有资产的现象。因为我没有研究 ,所以无法作出回答,也无法判断郎咸平教授的意见究竟对不对。……但是他说的有一 条我觉得是对的,就是在国有企业改制中确实出现了蚕食和侵吞国有资产的情况。”但 对郎咸平叫停国企改制,吴敬琏明确表态:“这个观点我不同意”[5]。上述这段语言 ,反映出吴敬琏先生作为老一辈的著名经济学家的学术宽容、冷静和理智。这或许让我 们领略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学者风范和理性思维。
而另外,则有一些学者表示:坚决支持郎咸平。“我坚决站在郎咸平一边,坚决支持 他反击顾雏军的一切行动。一切有良知的人都应当行动起来,支持郎咸平先生”[6]。 还有学者竟如此宣称:“郎咸平的文章我没有看明白,可能有错误,但我坚决支持”。 我们的一些学者,一向奉行的严谨的治学方法,科学的理性思维,为何被置之脑后?或 许,是被郎咸平先生巧妙地“拿弱势群体当自己的礼服”,誓言“坚决保护国有资产和 中小股民利益”的这种“迷人光环”所吸引;或被郎咸平教授决不畏惧强势,“绝不容 许顾雏军以威胁口吻发律师函来践踏以研究为本的学术自由风气”的这种“斗士精神” 所打动。这样,学者所固有的科学的理性思维,也就不知不觉地被眼前的感人的因素所 “催眠”。
经济学研究离不开统计学研究,这类学术研究或科学研究,它毕竟不同于文艺创作。 文艺创作需要想象,甚至也需要幻想。比如现在还流行“大话什么”、“戏说什么”、 “某某颠覆版”等等。而经济学研究这种科学研究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我们从小在幼 儿园所受的教育就是:说假话不是好孩子,说真话才是好孩子。科学研究力求客观真实 ,而科学研究之大忌乃是弄虚作假。玩弄数字,做数字游戏,与学术研究,与科学精神 ,压根儿就是两码事,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经济学研究,需要搜集大量的统计数据 资料,建立数学模型,以进行严密分析,科学论证。诺贝尔经济学奖开设以来,可以说 几乎所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既是经济学家,同时也是统计学家或数学家。
不严格遵循随机抽样的统计科学原理,不严格遵循统计分析的大数法则,主观地选几 个样本(我们姑且不论这些个案分析准确与否),用极少的样本资料,去推导出总体结论 ,这种“独立研究”,难道就是郎教授“在美国养成的习惯”?难道这就是郎教授的用 数据说话的严谨学风?这种“郎氏模型”,或许不仅堪称“亚洲第一”,甚至可以称得 上“世界一流”。遗憾的是,这样的学术成果,未被诺贝尔委员会发现。不过,这没有 关系,好在它终于被自诩为“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的学者给发现,它的价值,用伍 文中的一句话来说,“这是一种基于中国国情的正确价值判断。”然而,人们不禁要问 :素称治学严谨,而蔑视别的学者“拍脑袋”的郎教授,上述“独立研究”方法和风格 ,称得上科学研究吗?不难发现,它与伍文中所讲的“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更应该遵循 科学理性分析原则”,实在是离题太远,格格不入的。如果善良而善意的人们知道他们 所爱戴的、具有“学术良知”的教授先生是如此自相矛盾,甚至(不小心)亵渎科学,真 不知会作何感想?!
看来,郎咸平先生上述“在美国养成的习惯”,“独立研究”的方法和风格,怎么说 也无法使人把它与“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联系起来。
从“郎顾之争”到“郎张之争”,无非都是围绕着这样一连串的问题:国有资产流失 、“国退民进”、MBO、转制、产权改革、效率与公平等等。这些不可回避的理论问题 ,正是长期困扰我们的,难以解决而又必须解决的重大难题。这里,郎咸平观点的对错 本身,其实也就显得并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郎咸平现象”所激起的社会各界的反 响。当然,它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场轰动,它将带给我们更多的思考。而这种思考 ,不单是学术理论问题本身。现在,已有学者在研究“郎顾之争”的蝴蝶效应。它给我 们的最终启示是:国有资产流失现象(包括“体制性流失”和“交易性流失”)不容忽视 ,国有资产产权转让,必须在阳光下进行,必须是透明的,必须公开、公平、公正。任 何形式的暗箱操作,偷梁换柱,巧取豪夺,说到底,终究是既不合情,又不合理,更不 合法。而关键的问题恐怕还在于: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正如财政部财科所研究员周放 生所说:“体制性流失更与国有企业改制的必要性紧密相关,只有改制才能解决体制性 流失”[7]。
总之,国企改革“决不是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能证明的”,叫停国企改制,叫停产权 改革,显然是不可取的。事实上,我国的国企改革的步伐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就中 小企业来看,正如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所指出,“国有中小企业改革进一步深化。目前, 山西、辽宁、湖北、湖南、宁夏等省份国有中小企业改制面已达80%以上。地方国有中 小企业普遍实现了产权多元化,经济效益明显提高”[8]。中国的经济改革已进行了二 十多年,眼下已深入到明晰产权的核心问题。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实际上是一道绕不 开的结。“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这乃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
标签:郎咸平论文; 经济学家论文; 国有经济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派论文; 产权理论论文; 社会经济学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国有资产管理论文; 产权保护论文; 科学论文; 国企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