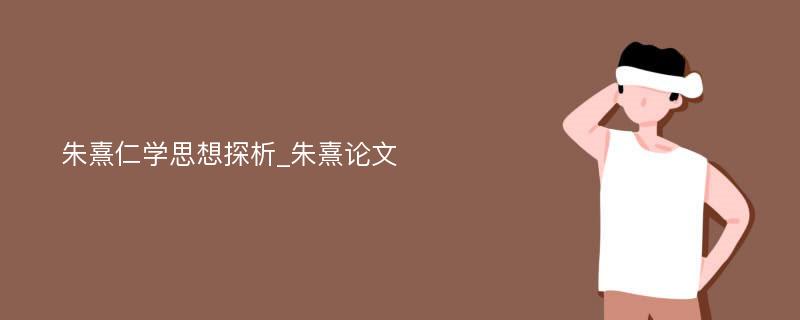
朱熹《仁说》剖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朱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朱熹完成“中和新旧说”以后,乾道八年(公元1142年)写《仁说》。《仁说》承前启后,发天人之蕴,对于了解朱熹思想体系的特点,具有重要意义。下面分四节予以剖析。
一 天地生物之心
《仁说》最为特别的地方是,以“天地生物之心”为仁的天理根源。故如何理解“天地生物之心”,成为剖析与了解《仁说》的关键。朱熹说:
“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乎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已矣。”
“请试详之,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其远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
“故论天地之心则曰乾元坤元,则四德之体用不待悉数而足……。盖人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
“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则怏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贯四端者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七)
这里“天地生物之心”可以有三种诠释或理解。(1)实体的心,即思虑情感、发号司令之心,这是神学的说法。如基督教《创世纪》,如董仲舒天有意创生万物以为人用;(2)假说虑托之辞,没有任何实质意义。这是牟宗三先生的说法,牟先生说:“天地生物之心,若从正面有心而观之,心只是理之定然义,心被吞没于理。‘天地无心而成化’,若从反面无心之义而观之,心只成气化之自然义,心被吞没于气。”“天地生物之心被融解为理与气,其自身遂成虚托。”①(3)“目的”义,即天地以生物为目的。它介于前两种之间。作为非思虑营为之心而言,它是“无心”;作为某种生物活动之主宰、导向而言,它是“有心”。《朱子语类》说:
“天地之心不可道是不灵,但不如人恁地思虑。”
“道夫言:‘向者先生教思量天地有心无心。近思之,窃谓天地无心,仁便是天地之心。若使其有心,必有思虑,有营为。天地曷尝有思虑来!然其所以四时行,百物生者,盖以其合当如此便如此,不待思维,此所以为天地之道。’曰‘如此则《易》所谓复其见天地之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又如何?如公所说,只说得它无心处尔。若果无心,则须牛生出马,桃树上发李花,他又却自定。程子曰:‘以主宰谓之帝,以性情谓之乾’。他这名义自定,心便是他个主宰处,所以谓天地以生物为心。”
“今须要知得他有心处,又要见得他无心处,只恁定说不得。”(《语类》卷一)
心,按通常的了解,就是思虑营为之心。所以道夫说,要么天地有心,那就有思虑营为;没有思虑营为,那就是无心。朱熹认为道夫这种非此即彼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天地没有思虑营为,其春生、夏生、秋收、冬藏是一个自然活动,故是无心。但虽然如此,却不能说生物活动没有“主宰”。如果没有“主宰”,会牛生出马、桃树上发李花,生物会成为一种无方向、秩序的盲目的活动,而事实却不是如此。之所以如此,固然是气化与理数使然,但最重要的,在朱熹看来,则是天地有生物之心,以为此气化与理数之主宰,从而使自然之气化与理数,皆为着一生物的目的。亚里士多德说:
“以为我们既然看不见动作者在思考,因此并无目的存在,这种想法乃是荒谬的。技艺也并不思考。如果造般术是在木材里面的话,它就会由于自然(此自然即自己如此之意。引者)而产生出同样的结果。由此可见,如果在技艺中有目的存在,那么在自然(此指自然界。引者)也有目的存在。最好的例子是一个医生医疗自己。自然就是像那样。”②
朱熹的思路正和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所说的一样。
王弼说:“凡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皆有所由。有所由焉,则莫不由乎道也。”“道者,万物之所由也。”(《老子注》第五十一章)王弼这里所讲的道,既包括气化之自然,亦包括理数之定然,但两者皆自然如此,非有为之者(即主宰、目的)。朱熹则认为,此气化之自然与理数之定然,背后尚有为之者(主宰、目的),此为之者不仅使物得以生,功得以成,而且使物只是生,功只是成,而不是非生非成,或反生反成。此为之者,即“天地生物之心”。
朱熹答张敬夫十八书之第三书说:
“复见天地之心说,熹则以为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虽气有阖辟,气有盈虚,而天地之心则亘古至今,未始有毫厘之间断也。故阳极于外而复生于内,圣人以为于此可以见天地之心焉。盖有复者气也,其所以复者,则有自来矣,向非天地之心生生不息,则阳之极也,一绝而不复续矣,则何以复生于内而为阖辟之无穷乎?此则所谓动之一端者,乃一阳之所以动,非徒指夫一阳之已动而为言也。夜气固未可谓天地之心,然正是气之复处,苟求其故,则可以见天地之心矣。”(《文集》卷三十二)
按道家自然论的说法,气有阖辟,物有盈虚,只是自然如此,不必也不能再问其所自来,事情到此就终结了。但朱熹却认为,其“所以复者”(理)尚有“所自来”,“向非天地之心生生不息,则阳之极也,一绝而不复续矣,尚何以复生于内而为阖辟之无穷乎?”就是说阖辟无穷之所以能如此,归根结底,是由于天地以生物为心,。故“天地闭关”之时,阳气终于七日来复,使大地回春,万物复苏。如果不是天地以生物为心,一阳极于外也许就将不复续于内了。
答何叔京三十二书之第十七书中,朱熹指出:
“来教云:天地之心不可测识,惟于一阳来复乃见其生生不穷之意,所以为仁也。熹谓若果如此说,则是一阳来复以前,别有一截天地之心,谟然无生物之意,直到一阳来复,见其生生不穷,然后谓之仁也。如此则体用乖离,首尾冲决,成何道理!(王弼之说便是如此,所以见辟於程子也。)”(《文集》卷四十)
何叔京否认有“天地生物之心”,但含糊其词,只说“不可测识。”但既不可测识,就不可能肯定其存在。所以朱熹指出何陷入了王弼自然无为论的错误。朱熹认为,必须肯定有天定生物之心,才能解释一阳来复、生生不穷(用)之何以可能。天地生物之心是体,生生不穷是用。有体才能有用,无体则不能有用。何叔京的说法,实际是以无为体。这种体用乖离,是不能成立的。这里一阳来复之“用”,既指气化之实然,也指此“实然”中含寓的理数之定然。而两者的最后的所以然——即体,朱熹认为是“天地的生物之心”。
在答《张敬夫论仁说》书中,朱又批出:
“盖天地之间,品物万形,各有所事,惟天确然于上,地聩然于下,无所为,只以生为事。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程子亦曰‘天只以生为道’。其论‘复见天地之心’,又以‘动之端’言之,其理亦已明矣。然所谓以生为道者,亦非谓将生来作道也。凡若此类,巩当肯认正意,而不以文害词焉,则辨诘不烦,而所论之本指得矣。”(《文集》卷三十二)
“将生来作道”,即是以生之气化之实然与气化之理以为道。朱熹认为,这不是《易传》和程子(明道)的意思。朱认为,《易传》讲“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是就元亨利贞四德和“乾元、万物资之以为始”来说的。故赞美的不是“生”这一事实,不是“生道”本身,而是使生成为生、成为生生不息的天地之“大德”。因此,否认天地有此生物之心,生只是一自然现象,“大德”的说法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动之端见天地之心,是程颐《易传》提出的。王弼认为“复见天地之心”,复是静止的意思。王弼发挥老子“万物芸芸,静复归其根”的思想,认为动是暂时的,不是根本。程颐强调“动之端天地之心见也”。动才是天地与万物的根本。动指阳动。阳动,万物复苏、生长、发育。所以程颐《易传》崇尚动、崇尚生,以仁为生道。但程颐没有明确提出“天地以生物为心”,朱熹才明确地提出。
在同书中,朱又指出:
“又谓仁之为道无所不体,而不本诸天地生物之心,则是但知仁之无所不体而不知仁之所以无所不体也。”
仁之无所不体,一指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就主体言;一指仁之为道无所不体,就理言。就理言,仁之无所不体,表现为仁为“众善之长”,“仁包四德而贯四端”。但何以仁能如此?朱熹认为,其根据即在于仁是“天地生物之心”。因此,“天地生物之心”不仅不是被理吞没了、消融了,相反是由“理”而愈益彰显了。
《仁说》以后,朱熹在其它重要著作如《周易本义》、《语类》及《四书集注》中,也一直坚持这一思想。
《周易本义·复卦彖传注》云:
“积阴之下,一阳复生。天地生物之心几于灭息,而到此乃复见耳。在人则为静极而动,恶极而善,本心几息而复见之端也。”
以人之本心对应天地生物之心。以一阳复生显见天地之心,对应恶极而善,显见人之至善之本心。这说明“天地生物之心”对朱熹而言,确是一真实的实存。
朱熹《孟子章句》说:
“天地以生物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乎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离娄上》)
对“天地生物之心”亦坚信不疑。
因此,朱熹的天地、自然观,实包含有两种系统,一是自然的阴阳理气系统;一是天地生物之心的价值道德系统。前一系统表现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后一系统表现为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两个系统不是互不相涉的,相反,是相辅相成的。春夏秋冬之所以有序,既是理、气之自然,亦是元亨利贞四德的作用。从体用看,元亨利贞是春夏秋冬所以如此运行之体,春夏秋冬是元亨利贞所以生物之德之用。离开春夏秋冬,元亨利贞无所凭依与附著,而无以表现其生物之德,离开元亨利贞,春夏秋冬也将只是一纯自然现象,而无以表现其生物长物收物藏物之大功大用。就自然法则言,春夏秋冬之为春夏秋冬之自然法则,是阴阳二气在天地间消长盛衰所遵循的规律,有如《淮南子》及董仲舒所描绘者。《春秋繁露·阴阳出入》说:“天之道,初薄大冬,阴阳各从一方来,而移于后。阴由东方来西,阳由西方来东。至于中冬之月,相遇北方,合而为一,谓之曰至。别而相去,阴适右,阳适左……冬月尽,而阴阳俱南还……。”这种阴阳运行的规律,只是一种自然法则、自然规律,不具道德的意义。元亨利贞却是道德的属性,“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事之和也,占者,事之于也。在《易传·文言》中,它是用以形容乾的纯粹至善的德性的”。③在《仁说》中,朱熹将其归之于“天地生物之心”。董仲舒曾说:“天常以爱利为意,长养为事,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仁,天心”。④朱熹正是继承了董仲舒这一目的论思想,从而把宇宙道德化,反转来又以之为仁——人性的根源。因此,如果离开“天地生物这心”,离开“元亨利贞”、“乾元坤元”这一宇宙道德系统,而以纯自然的阴阳理气系统作为人的生命价值之源,就将如道家一样,把人看作是纯粹的自然人而与儒学背道而驰,也就完全不能理解朱熹《仁说》了。
二 “心统性情”
《仁说》接着说:
“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乎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人之为心,其德亦不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则恻隐之心无所不贯。”
“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发,而此体已具,情之既发,而其用不穷,诚能体而存之,则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
“诚能克去已私,复乎天理,则此心之体无不在,而此心之用无不行也。”
“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则怏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这心,包四德而贯四端者也。”
这里,朱熹反复以“心”说仁,以“心之体”说仁,以“得乎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说仁,以“温然爱人利物之心”说仁。没有“性即理”、仁即理的字样。那么,这里的“心”含义为何?
这里,心不指人之思虑营为的自然之心,但它也不离乎此思虑营为的自然之心究其实,它之所指,是一存在于人之思虑营为之气之灵之心中的道德本也,也即“心之体”。它不离乎思虑营为之心,故具有“理性”的特征,能随思虑营为之心的发用流行而起用,但它不是此思虑营为之心本身,而是道德之源,众善之本,故是道德理性。此道德理性之实质内容是“爱人利物”,故朱称之为“仁心”。当仁心未随人心之思虑营为之活动而起用(未发)时,它无形、无象,不落时空,不落有无,不过是人心所先验地具有的一应当如此做(应当爱人利物)而不计条件、利害的道理、道德命令、道德律则而已,故可称之为“理”。它得于天而具于心,是人之为人(道德人)的本性、善性、善根之所在,故又可称之为“性”。这也就是性即理的意思。⑤当仁心、爱人利物之道德理性随人心思虑营为、喜怒哀乐在在皆合乎天理,在在皆是爱人利物而不是害人残物。这时,它表现自己为侧隐、是非、辞让、羞恶等道德之情(百行众善)。两方面合起来,就是所谓“心统性情”。
要之,仁——仁心、仁性是得之於天而内具於人心的。心是合人心与仁心、道德本心(性)而为一的。故朱熹说:“仁字、心字,亦须略有分别始得。”(《文集》卷四十答何叔京书四十三第三十书)“略有分别”,即指两者不能分开,离心无性,但又不能笼统地以心为仁、以仁为心。就是说,不能笼统地讲心即理,必须讲性即理。但讲性又绝不能离乎心,不能外心以求性。以为性在心外,仁在心外,那就完全背离朱熹的思想本意了。故朱熹反复申说:
“心性本不可分。”(《语类》卷六十)
“性,不是有一个物事在里面(指在人心里面)唤做性,只是理所当然者便是性只是人合当如此做底便是性。”(同上)
“性无形质,而含之于心。故一心之中,天德是足,尽此心则知性知天矣。”(同上)
“心之全体湛然虚明,万理具足,无一毫私欲之间;其流行该偏,贯乎动静,而妙用又无不在焉。故以其未发而全体者言之,则性也,以其已发妙用者言之,,则情也,然心统性情,只就浑沦一物(指心)之中,指其已发、未发而为言尔;非是性是一个地头,心是一个地头,情又是一个地头,如此悬隔也。”(端蒙)(《语类》卷五)故求仁的功夫归结到一点,也兴是“灭私欲,存天理”,求放心。
《语类》卷六说:
“孔孟只教人求仁。求仁只是主敬,求放心。若能如此,道理便在这里。”(方子)
“学者须是求仁。所谓求仁者,不放此心。……今看《大学》亦要识此意,所谓‘顾天之明命’,无他,求其放心而已。”(方子)
“或曰:存得此心,即便是仁。曰:此句甚好。……今且只以孟子‘仁,人心也;义,人路也’,便见得仁义之别,盖仁是此心之德;才存得此心,即无不仁。如说‘克已复礼’,亦只是要得私欲去后,此心常存耳。”
“耳之德聪,目之德明,心之德仁,且将这意去思量体认。”
朱子文集卷四十,答何叔京三十二书之第三十书说:
“人之本心无有不仁,但既汩於物欲而失之,便须用功亲切,方可复得本心之仁。”
“人未尝无是心,而或至于不仁,只是失其本心之妙而然耳。”
这些言论,十分明确,都是建立在以道德本体这心,亦即爱人利物之心论仁的基础上的。
牟宗三先生说:
“依孟子学,道德的必然性是性分之不容己,此不容己不是强制,是从本心即性之本身说,不是关联着我们的习心说。”⑥
朱熹的仁说正是如此。
三 “仁者心之德而爱之理”
《仁说》的思想,用一句话来概括,即是“仁者心之而爱之理”。
在与张敬夫《又论仁说》第二书中,朱熹说:“仁乃性之德而爱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爱,但或蔽于有我之私,是不能尽其体用之妙。”《又论仁说》第三书中,则说:“仁本吾心之德。”第四书说:“仁只是爱之理,人皆有之。”⑦《答胡广仲》说:“须知仁义礼智四字一般,皆性之德,乃天然本有之理。”⑧《答吴晦叔》说:“仁者性之德而爱之理也,爱者情之发而之仁用也。”⑨在这些论述中,朱熹或说仁是“心之德”,或说仁是“性之德”。“心”、“性”交互替代,异名同谓,所指皆是心之道德本性或道德本心。只是从其无形、无象、不落时空、不落有无,是一超越的、应当爱人利物的道理而言,称为“理”;从其作为人的本质本性之所在而言,称为性;从作为心之体、道德理性而言,则称为心之德。所以爱之理是不能离开心之德而独立存在的。《语类》卷二十说:
“爱之理,即是心之德,不是心之德了,又别有个爱之理。”
“爱这理,是偏言则一事;心之德,是专言则包四者。故合而言之,则四者皆心之德,而仁为之主;分而言之,则仁是爱之理,义是宜之理,礼是恭敬、辞逊之理,知是分别是非之理。”
“仁只是爱底道理,此所以为‘心之德’。”
爱底道理,即是心所认为合当爱底道理。因此,朱熹所讲的“仁者爱之理”与新实在论所讲一般(理)与特殊(殊相)的关系是大不相同的。
在新实在论体系中,爱之“理”是从形形色色的爱的殊相中抽象出来的爱的“共相”,将其本体化的结果,此理存在于一超时空的理世界中。如程颐所说:“冲膜无朕,万象森然已具”、“百理俱在,平铺放着”、“儿时道尧尽君道,添得此君道多”、“母尽爱道,添得些爱道多”、“元来依旧”。⑩爱之理(共相)与“心之德”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但在朱熹体系中,此爱之理只是心所认为合当爱人利物的一道理,因而其发出的爱,与新实在论体系中的种种特殊的“爱”之不带道德价值的意义不同,是具有先验道德的性质的。也就是说,它包含有一应当爱的“标准”在内,即是爱所应当爱者。而此“应当”的标准亦只是心所先验地认为应当者。因而亦可以说,它虽然表现为人的世俗的喜怒哀乐。但其实质却是一超越的、纯道德的爱。追本索源,它之所本是人所得于天之天地生物之心。而在新实在论体系中,爱的殊相则是种种世俗的具体的爱,爱的“共相”则是独立自存,永恒固有的,与“天地之心”等等,毫无关联。
另一方面,此“应当”亦包含有随具体名分、境遇等等之不同,而爱之具体表现亦自不同的“标准”。也就是说,理自身(仁)是能随经验条件之“分殊”而表现自己为一“分殊”的。
程颐论《西铭》说:
“《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老幼及人,理一也,爱无差等,本二也。分殊之敝,私胜而失仁;无分之罪;兼爱而无义。分立而推理一,以正私胜之流,仁之方也;无别而述兼爱,至于无父之极,义之贼也。”
朱熹发挥说:
“大抵仁者,正是天理流动之机,以其包含和粹,涵育融样,不可名貌,故特谓之仁。其中自然文理密察,各有定体处,便是义。只此两字,包括人道已尽。义固不能出乎仁之外,仁亦不能离义之内也。然则理一而分殊者,乃是本然之仁义,前此乃以从此推出分殊合宜处为义,失之远矣。”(《延平问答》)
又说:
“仁,只是流出来底便是仁;各自成一个物事底便是义。仁只是那流行处,义是合当做处。仁只是发出来底,及至发出来,有截然不可乱处,便是义,且如爱其亲,爱兄弟,爱亲戚,爱乡里,爱宗族,推而大之,以至于天下国家,只是这一个爱流出来;而爱之中便有许多等差。且如敬,只是这一个敬;便有许多合当敬底。如敬长、敬贤,便有许多分别。”(《语类》卷九十八)
这里,爱之理所以能分殊,原因即在于它不是僵死的、静止的爱之共相,而是“心之德”,是心所认为应当做的一爱人利物的“道理”。
《语类》卷二十,朱熹论仁与孝弟等的关系说:
“仁是理之在心,孝弟是心见于事。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曷尝有孝弟!见于爱亲,便唤做孝;见於事兄,便唤做孝。如‘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都是仁。性中何尝有许多般,只有个仁,自亲亲至于爱物,乃是行仁之事,非是行仁之本也。故仁是孝弟之本。推之,则义为羞恶之本,礼为恭敬之本,智为是非之本。自古圣贤相传,只是理会一个心,心只是一个性。性只是有个仁义礼智,都无许多般样,见於事,自有许多般样。”
“仁只是理之在心者,孝弟是此心之发现者。孝弟即仁之属,但方其未发,则此心所存,只是有爱之理而已,未有所谓孝弟各件,故程子曰:何曾有孝弟来!”
这里,“理之在心”即内具于心,与心为一。以后王阳明论“心即理”说,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实是发挥朱熹此说,不过更加简易直截,不讲“仁”是“心之体”,是性,本于“天地生物之心”而已。
牟宗三先生说:朱熹“一概由存在之然以推证其所以然以为理,而此理又不内在于心而为心之所自发,如是其言之理或性乃只存一属于存有论的存有之理,静摆在那里,其于吾人之道德行为乃无力者,只有当吾人敬以凝聚吾人之心气时,始能静涵地面对其尊严。”(11)朱熹“视性为只是理,是一个普通的理,而爱与侧隐乃至孝弟都视同一律,一律视为心气依这普遍之理而发的特殊表现,而表现出来的却不是理,如是,仁与侧隐遂成为性与情之异质的两物。……如此言理或性,是由‘然’以推证其‘所以然’之方式而言,是属于存有论的存有之理,而不必是道德之理”。(12)这是用新实在论来理解朱熹思想的结果,可以说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了”。
冯友兰先生说:“理是形而上者,是抽象的,无迹象可寻。不过因吾人有侧隐之情,故可推知吾人性中有侧隐之理,即所谓仁。因吾人有差恶之情,故可推知吾人性中有差恶之理,即所谓义。……盖每一事物,必有其理。若无其理,则此事物不能有也。”(13)牟先生的说法即本于此。这种由“然”以推证其“有所以然”的推证方式,完全避开“心之德”,从而把朱熹讲的仁性、仁理,一概讲成—“存有论的存有之理”(共相),可以说与朱熹思想是背道而驰的。
四 人心与道德之心
在《仁说》中,心,一方面是气之灵、是知觉、是思虑营为;一方面是爱人利物之心,那么这如何可能?就是说人心、气之灵的心如何能含寓一超越的道德本心?
照牟先生的说法,两者是不能并存的。要么是气之灵,那就不是,也不可能是超越的道德本心;要么是超越的道德本心,那就不是也不可能是气之灵之心。因此,牟先生认为,朱子之仁之名义应修改如下:
“仁是爱之所以然之理,而为心知之明之所静摄(心静理明)。常默识其超越之尊严,彼即足以引发心气之凝聚向上,而使心气能发为‘温然爱人利物之行(理生气)。久久如此,即可谓心气渐渐摄具此理(当具)以为其自身之德(心之德,理转成德)。”
“简言之,即是:仁者爱之所以然之理而为心所当具之德也。”(14)
也就是说,朱熹的道德仁性思想,究其实是告子的义外系统、道德他律系统,与康德所谓道德只能是心之自律、理性之自律完全不同。
本文前已指出,这实际上是对朱熹《仁说》及其心性思想的曲解。这里要着重指出,从一般哲学看,牟先生这段话,本身也是完全不通,根本不能成立的。
朱熹在《答张敬夫论仁书》中曾说:“仁本吾心之德,又将谁使知觉之耶?”(《文集》卷三十二)就是说,仁不是如冯友兰、牟先生所讲的“共相”,有如飞机之理、舟车之理,能为心知之明所静摄、所认识。仁是得于天而具于心者,因而是根本不能成为认知、摄取的对象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客观的冷暖,可以温度计量之知之,自我的冷暖,除自我自知以外,别人是不可能知之觉之的。仁作为人所得于天,而已具的“心之德”亦不可能成为心知之明的认知、摄政的对象。它只能为自我所先验地、内有地知,但此种知,即是张载所谓“天德良知”,孟子所谓“良知良能”,朱熹所谓“明德”。因此,牟先生所谓仁为心气所摄取而为已之德的说法,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朱熹更尖锐地提出对道德认知的动力与主体问题。按牟先生的说法,心气是中性的、无色的,心气之知也是中性的、无色的、没有价值取向的。(15)那么它如何有一种动力、兴趣或内在需要要去认知摄取仁以为己之“德”?心既然只是中性无色的认知工具,又如何能摄取仁以为己之德?说它“常默识其(仁)超越之尊严。”。超越之尊严是一强烈的道德情感,无色的中性的认知如何能起此超越之尊严之感?这些,如果不假定人有一道德之本心,显然都是讲不通的。所以要么是义外、他律系统,那么“道德”本质上就不是道德,而是理性对利益的计算;要么是自律系统,那么道德就只能是“心之德”,是天德良知。朱熹一贯坚决、明确地把道德、天理与人欲、私欲——即对理性而言的他律的存在对立起来,因此,朱熹的“仁者,心之德”属于道德自律系统,是毫无疑问的。牟先生的“修改”恰恰是把朱熹弄错了。
那么,人作为现实的形而下的气的存在,其理实的心及其喜怒哀乐、思虑营为,无不受经验条件和自然法则的制约,它如何能同时是一自由的不受经验条件与自然法则制约的道德理性?!用康德的话也就是说,纯碎理性其自身如何就能是实践的?朱熹没有提出这一问题,更没有提供任何答案。因此《仁说》的一些说法,如“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既不能理解为只是思虑营为之心,亦不能理解为只是道德之心,它是两者的结合。但如何结合?何以能结合?何以道德本心能为人心之体?等等,朱熹都没有解答。
孟子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人之异於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讲的“心”也是思虑营为之心与仁义本心的并存。因此也有两者如何联结与统一的问题。王阳明讲“心即理”。同时也讲“存天理,灭人欲”,其心亦有纯乎天理之与人欲之心、私意之心的区别,故亦有道心与人心的关系问题存在。只有把人讲成圣人或上帝,“道成肉身”,肉身的存在只是“道”的感性形象,因而其愉悦、兴趣纯然全是天理;或者把人讲成纯然的自然物,仅受自然法则的制约,上述的矛盾才不再存在。但朱熹、王阳明和康德等等,都清醒地看到人作为人,其存在是两重性的,既是天使,又是魔鬼;既是自由的,又是不自由的;即有“神性”,又有人性,因而其道德本心与人心、人欲之心的矛盾纠结,是无可避免的。
牟先生不想人有这种矛盾,认为人可以纯然是道德的存在:“当本心仁体或视为本心仁体之本质的作用(良功良能essential function)的自由意志发布无条件的定然命令时,即它自给其自己一道德法则时,乃是它自身之容人己,此即为‘心即理’(孟子、王阳明)义。它自身不容已,即是它自甘如此它自甘如此,即是它自身悦此理义(理义悦心)。本心仁体之悦其自给之义理,即是感兴趣于理义,此即是发自本心仁体之道德感、道德之情、道德兴趣,此不是来自感性的纯属于气性的兴趣。”(16)这里,这种纯德本心的愉悦、兴趣,实际上有如观士音和上帝的“微笑”一样,但可惜这已不是人的道德学,而是神学的道德学了。兴趣、愉悦本身只能是肉体的气性,理、形而上、超越的东西,不能有兴趣与愉悦。说兴趣、愉悦不纯属于气,也属于理性与非感性的道德,是不通之论。所以牟先生自以为超越了康德,实际则是在人欲与道德的矛盾中,而完全没有拔出。
孟子说过“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但孟子的这种比喻实际是不恰当的。这一说法不是孟子道德思想的深刻之处,相反是其肤浅和缺乏深思之处。牟先生对此大加发挥,以之为中国儒学道德学的正宗。显然是把儒学的道德学的肤浅和错误当成宝贝和精华了。
孔子说:“吾夫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民之于仁甚於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也,未见蹈仁而死者也。”(《论语·卫灵公》)孟子说:“人之异於禽兽者几希。”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传习录》卷一)“须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心,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出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同上)“戒惧之念,无时可息,若戒惧之心,稍有不存,不是昏愤,便已流入恶念。”(同上)康德说:“如果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竟然能够完全乐意实践一切道德法则,那么,那就无异于说,他心中永远不可能有些许欲望,引诱它背弃那些法则。因为倘有这样一种欲望,就需要加以克服。而要克服这种欲望。就总要当事人割爱忍痛,因而需要他自行强制,并且从内心强制他实行也并不完全乐意实行的事情。……他既然是一个被造物,而且总是有待于外面的条件,才能完全满意自己的处境,所以他就永远不能摆脱欲望和好恶。这些欲望和好恶,因为是以体的原因为基础,所以并不能自动符合于来源完全不同的道德法则,并正因为它们的原故,才使人们永远不得不把自己准则的意向,建立在道德的强制力上,而不建立在心甘情愿的嗜好上;建立在要求人遵守法则(不论其乐意与否)的敬重心上,而不建立在内心原不害怕意志对法则发生憎恶的那样一种爱上。”(17)朱熹的《仁说》,一方面说:“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发而此体已具,情之既然而其用不穷”;一方面说“孔门之教所以必使学者汲汲于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复礼为仁’。言能克去己私,复乎天理,则此心之体无不在,而此心之用无不行也。又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则亦所以存此之心也。又曰:‘事亲孝,事兄弟,及物恕’,则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则以让国而逃,谏伐而饿,为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杀身成仁’,则以欲甚于生,恶甚于死,能不害乎此心也。”其所发挥的,正是中外先贤对“道德”的共同的、基本的见解。而它是以两种心的并存为基础的。
“仁”、道德,是庄严、神圣的,但并不是曲折、深奥、令人难解的。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通过道德的庄严和人对道德的敬重之情,把人引到了自由的存在,引到上帝与灵魂不死。朱熹的《仁说》,通过仁心、仁德的追本索源,把人引到了超乎物欲、私欲的超越的自由的本心,引到了“天地生物之心”及其普照一切的爱,他们的目的都在鼓励人由卑鄙、渺小、自私、纵俗、犯罪走向崇高、光明、圣洁,因为只要你愿意,人人都可以求仁而得仁。这也就是《仁说》的中心与主旨。
注释:
①(11)(12)(14)(15)(16)《心体与性体》第三册第四章《中和新说后关于〈仁说〉之论辨》台北正中书局1969年6月版,第236页,第242页,第241页,第244页,第244页,第195页。
②《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58页。
③陈来《朱熹哲学研究》说:“作为宇宙普遍法则的元亨利贞在人类社会和人的本性上表现为仁义礼智。”这是把元亨利贞当成自然法则了。陈来认为这是朱熹的错误。实际朱熹从来也没有把元亨利贞当成自然法则、宇宙普遍法则。在朱熹体系中,人有两个系统:自然系统(与禽兽无别)与道德系统;宇宙亦有两个系统:自然之阴阳动静系统(包括天地动静之理)及道德系统。元亨利贞乾元坤元等,即属于道德系统,其源则是“天地生物之心。”(引文见第86页台北文津出版社90年12月版)。
④《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⑤“性即理”有两种含义:1、性即天理。这里就性之天命来源说;2、心所具之合当如此做的道理。这是就天理落于气化、落于心说。
⑥牟宗三:《实践理性批判、论纯粹实践理性的动机》注解。
⑦《文集》卷三十二。
⑧《答胡广仲》五,《文集》卷四十二。
⑨《答吴晦叔》十,《文集》卷四十二。
⑩《二程遗书》卷二上。
(13)《中国哲学史》第十三章《朱子》。著于1933年,引自《三松堂全集》第三卷第332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7)《实践理性批判》,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85-8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