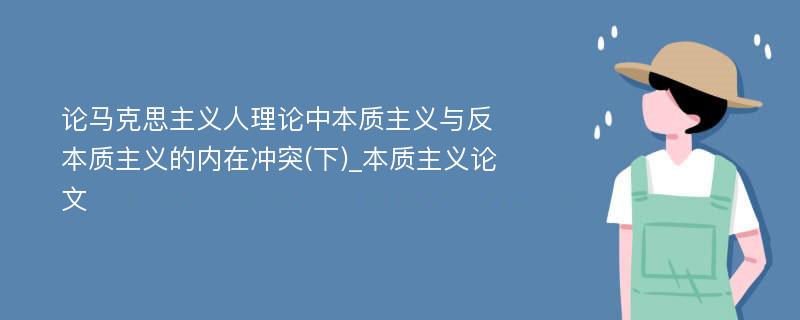
论马克思人论中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内在冲突(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质论文,马克思论文,主义论文,冲突论文,人论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7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4)03-0034-06
三、马克思人论对本质主义的复归
马克思在价值上向往一种具有足够丰富性的人的生活状态,他的人论的反本质主义意蕴主要包含在这种价值设定里。问题在于,这种丰富性远不是异质性。丰富性是一种和谐系统中的多样性,即在每一个个人那里,各种各样的属性都各得其所,并相安无事。马克思关于“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的比方最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特点。但异质性则意味着不相干性、甚至相互冲突性。打猎不仅有危险,而且有可能触犯野生动物保护法;捕鱼不仅是一种艰辛的劳动,而且被污染的河里可能根本就没有鱼(注:有意思的是,马克思也谈过河里的鱼跟污染的水之间的矛盾。当然,他针对的是其他问题(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7-9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傍晚才有闲暇和心情去畜牧,可牲畜不能饿着肚子等上一个白天;批判需要长期枯燥的专业训练,而且话一出口就会得罪人,有时后果不堪设想。不仅如此,你打猎,可能会斫伤你孩子的恻隐之心,让孩子觉得你残忍;你捕鱼,可能会因技不如人而心生不快,乘兴而去,败兴而归;你想傍晚畜牧,你夫人却希望你陪她散步;你晚饭后从事批判,你父母可能会骂你吃饱了撑的。就算这些事你都顺心遂意地做了,夜里躺在床上,你照样可能觉得生活没有意思。就算你怡然自乐,甚至不知老之将至,到头来你还是得黠然退出历史舞台和人生舞台。可见,马克思将人的理想生活设想为一种内容丰富的状态,虽然比那些干巴巴的精神等抽象本质少了很多本质主义气息,但也并非没有本质主义的思维品质。
对马克思的人论来说,单就其价值设定而言,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是同时存在的,理论的演进既有可能朝着反本质主义方向前行,也可能复归本质主义的轨道。使得马克思人论最终复归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主要不是他对人的价值的设定本身,而是他对人的存在事实的解释,尽管这两方面在马克思那里不是截然分开的。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他的有关解释的具体情况。
虽然马克思在价值上崇尚人的属性的丰富性,但是,在解释人的存在事实时,他从未放弃过使用“人的本质”之类的概念,从未放弃过以抓本质的方式来说明人的状况的做法。
在马克思开始理论活动的初期,他对政治问题最为关注。当时的德国人既是普鲁士君主的臣民,又是法兰西式民主的向往者。对于德国人的这两种属性——前者是实然的属性,后者是可能的属性——马克思从价值上肯定的是后者,他所给出的理由是:这是人和动物的区别所在——专制制度下的人不是人,而是动物;只有民主制度下的人才是人[1](P407-415)。这时的马克思不仅在理论观点上以亚里士多德的“人是政治动物”的命题为本,而且在思维方式上也采用亚里士多德所发明的办法——把臣民之类的属性看作人的非本质的偶性,把公民之类的属性看作人的本质属性。他说:“如果德国的亚里士多德想根据德国的制度写一本他自己的‘政治学’,那末他会在第一页上写道:‘人是一种动物,这种动物虽然是社会的,但完全是非政治的。”[1](P410)因为政治在德国是专制王朝的专利。马克思的言下之意是:如果他写一本“政治学”,其中的人的定义必定是符合亚里士多德的原义的。马克思的这种把人的众多属性区分为本质和非本质,从而给人的存在事实以理论说明的思维方式,正是典型的本质主义,也是最简单的本质主义。
到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马克思所理解的人的本质有了重大的变化。尽管马克思在价值上高度重视人的属性的丰富性,但他在为这种价值设定寻找理由时,仍然明确将一种特殊的属性判定为人的本质,这就是“人的类特性”——“自由的自觉的活动”[2](P96)。马克思论证这一观点的基本思路仍然是寻找人与动物的区别。马克思说:“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2](P96)“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2](P96-97)应当说,马克思所找出的人与动物的这种区别是非常有新意的,在人的自我认识的学说史上又增添了浓重的一笔。这无疑是需要充分肯定的。但是,不能否认的是,正是这种区别同时又使得马克思对人的理解显露出了明显的本质主义特征。
把“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看作人的类特性,亦即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从内容上看,比把政治民主看作人与动物的区别更加富于理论的独创性和新颖性。但是,从思维方式看,二者是一样的,即都是在人所具有的众多属性中挑选一种作为本质。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的这一时期,被当作人的本质的属性,不论是政治民主,还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相比其他属性来说,不仅具有价值上的合理性和优先性,而且具有事实上的决定性和恒久性。反之,那些非本质的属性,不仅在价值上不合理或不重要,而且能够在事实上加以改造或剔除。特别是在“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被确认为人的本质之后,所有那些与该本质不相符合的生活现象、社会关系,比如分工、市民社会、私有制、雇佣劳动、资产阶级人权、宗教信仰等,不仅在价值上受到了否定,而且被认定必然会从事实上加以消除。马克思的革命学说正是建立在所有这些坏的属性均能从事实上加以消除的基础之上的。由此可见,对人的属性作本质和非本质的区分,尤其是根据人和动物的差异性所作的区分,往往蕴涵着重大的理论与实践后果。
或许有人会讲,马克思所认定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这一人类本质,并不是黑格尔的精神那样的抽象的东西,而是有着丰富多彩内容的十分具体的东西。对这一点,笔者在前面已经充分肯定了。马克思对人的属性的丰富性的强调本来就是为了反对黑格尔式的抽象。也正因为如此,本文才认为马克思的人论具有反本质主义的倾向。但是,我们同时又必须看到,马克思所指出的那些丰富性有着很强的本质设定的约束,即人的属性的丰富性程度不得超过本质所允许或容忍的范围。也就是说,马克思所认可的那些属性,跟他所确定的人的本质在理论逻辑上是同质性的。本质主义的限度也就在这里:它不可能去认可跟它所确认的本质毫不相干或互相冲突的属性。
马克思所确认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具有明显的费尔巴哈的痕迹。在后来的思想发展过程中,马克思有意淡化这一痕迹,并对人的本质提出了新的看法,即把社会关系看作人的本质。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说:“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费尔巴哈没有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因此他不得不:(1)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2)因此,本质只能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3](P56)这里,当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时,他不仅仅是在批判费尔巴哈,实际上也对自己所提出的关于“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的观点有所反省。这时的马克思已深感批判的武器和震撼世界的词句在面对顽固的旧世界时的软弱与乏力,所以将目光投向社会生活的深处,投向那些实际牵动着大大小小的生活事件的社会关系,并且认定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关系决定着人之所以为人,而实际地改变社会关系就能改变人之所以为人。
把社会关系看作人的本质,就等于否定了先前流行的那种从人的某些固定属性中挑拣本质属性和非本质属性的做法,同时也就否定了人具有任何意义上的固定不变的本质。不仅如此,由于社会关系是变异的,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社会关系总有这样那样的差别,甚至有互相矛盾之处,因而以社会关系为人的本质不再意味着本质即善、非本质即恶的价值二分。再者,把社会关系看作本质,就解除了自然界对人的问题所应负的责任,意味着人的问题的根源在人的社会关系状况而不在人的自然本性,从而彻底变革社会才是必要的和可能的。当然,这不是说马克思因此否认人具有自然禀赋并受自然界的制约,相反,马克思是高度重视自然界对人的基础性的制约作用和人的天赋资质与机能的价值地位的。马克思的意思不过是:社会关系的问题是人的问题的罪魁祸首,改造社会关系是解决人的问题的根本途径。
这样一来,在马克思人论的演化过程中,被认定为人的本质的东西就从一种价值合理性的东西变成了一种事实决定性的东西。“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被看作本质,是因为它是马克思心目中的人所应该成为的样子;“社会关系的总和”被看作本质,是因为它是造成人的问题的决定性因素,也是解决人的问题所应抓住的根本。如是,又引出一个新的问题:是否马克思在提出社会关系是人的本质的看法后,完全抛弃了“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是人的本质的看法?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如果马克思完全抛弃了“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是人的本质的看法,那么,社会关系也好,人的本质也好,就无所谓合理不合理了,一切都不过是一连串的事实之间的冲突与替代而已。要真是这样的话,马克思提出人的本质在于社会关系,就不仅不是本质主义的表现,而是反本质主义的深化了。实际上,马克思在提出社会关系是人的本质后,虽然对“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这一价值预设有所反省,但并未放弃,否则,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批判和对共产主义社会关系的憧憬就变得不可思议了。事情的合理解释似乎是这样:马克思在提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新观点之后,作为价值预设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就隐退到了思想的幕后,并继续发挥价值尺度的作用。也可以这样说,至少在写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时期,马克思有着一显一隐两个“人的本质”:“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人的事实本质,“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是人的价值本质。
还应指出的是,把社会关系看作人的本质,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越了通过寻找人和动物的差异性来确认人的本质的做法。把人和动物作为某种现成的东西摆在面前去寻找它们的差异性,这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做法,也是黑格尔所批评的知性思维的做法。这种做法能够将对象界定清楚,但难以将对象的变化着的事实纳入到一套特定的逻辑化的解释框架之中。以社会关系为本质,将人的本质置于社会关系的历史变动之中,既能说明人的本质的流变性,又能维持对人的本质的解释的逻辑确定性。这种做法就是大家熟知的辩证法。马克思人论的辩证法不同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地方就在于:在黑格尔那里,历史地变化着的实体兼主体是精神本身,人及其意识只是精神演化的一个环节;在马克思这里,历史地变化着的实体兼主体是人的社会关系,人及其本质均应从社会关系来理解。当然,这里并不是说马克思在提出人的本质在于社会关系的观点之前没有辩证法,他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作为对象性的活动、作为扬弃异化劳动的历史结果也是富于辩证精神的。不过,相比之下,“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之为人的本质是先设定再交付给历史的,而社会关系之为人的本质直接地就在历史之中。如是,人的事实的辩证的本质和价值的知性的本质在一段时间里就并存于马克思对人的思考之中。从理论逻辑上整合这两者,就成了马克思此后的主要工作,同时也成了马克思进一步复归本质主义的契机。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实现了理论逻辑上的彻底化,表现为:他不再泛泛地将社会关系看作人的本质,而是将生活资料的生产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所在。他说:“这些个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3](P67)“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3](P67-68)进而,马克思又指出了物质生产跟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之间的关系,并在这种关系中进一步规定了人之为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3](P71-72)由此可见,这时的马克思已经明确地将物质生产看成了全部社会关系的决定因素,进而看成了人的本质的决定因素。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还解决了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人的事实本质和价值本质的统一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将物质生产客观化,让物质生产的客观规律内在地包含人的价值本质,从而达到物质生产的规律性和人的价值的目的性的辩证统一。不少人认为,马克思在发现物质生产的决定作用之后就抛弃了人本主义的价值观。其实,与其说马克思抛弃了先前的价值观,不如说他抛弃了先前价值观的表达方式。如前面的分析所显示的那样,马克思先前的价值观主要是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直接设定的,采取的是纯粹主观性的形式。这种做法同时也是费尔巴哈、施蒂纳等人的做法。一种纯粹主观性的价值诉求固然容易打动人,但总会给人依据不足、缺乏底气之感。这也是马克思看不起“批判的批判”的地方。马克思需要的是能够实实在在起作用的价值,显然,这种价值首先必须是有充分的客观依据的,最好直接就是一种客观的必然的东西,或者说既是合规律的又是合目的的。这样一来,马克思又回到了黑格尔那里,回到了依靠某种实体兼主体的自我运动来统一事实和价值的辩证法上,其间的差别不过在于黑格尔的实体兼主体是精神,而马克思这时所确定的实体兼主体是物质生产罢了。物质生产通过自己的辩证运动最终使人类获得彻底解放,从而“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作为人的价值本质就跟物质生产作为人的事实本质整合到了一起。至此,马克思的人论就获得了自己独到的品质,并跟先前各种人论区别了开来。
然而,这样做并非没有代价。代价之一就是马克思人论在回归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我们知道,黑格尔本质主义的关键在于他所设定的实体兼主体是一种抽象本质,实存的个人只是这个抽象本质的外在显现和自我实现的环节。费尔巴哈把感性的人确立为实体兼主体,为反叛本质主义开显了一个方向。施蒂纳和马克思都不满意费尔巴哈的地方在于,他所说的人仍然是一种本质化的抽象东西。马克思曾经明确将现实的个人作为实体兼主体,可以说走到了反本质主义的门口。如果将这一立场贯彻到底,个人所杂有的逻辑异质的属性就必然彰显出来,并要求一种非本质的思维方式与之匹配。施蒂纳拒绝给个人规定任何本质,从而将“我”树立为实体兼主体,算是为后来的反本质主义思潮开了个头。但施蒂纳在乎的并不是本质主义在学理上的问题,而是一种极端利己主义价值观的理论宣泄。马克思和施蒂纳虽然互相指责对方的“人”抽象,但对于如何从理论上守住具体的个人作为实体兼主体的地位,二人都没有给予圆满的解答。人类思维走到这一步,实际上已经在一个向度上触到了自己的边界。如果要理论地把握人,就必须将关于人的阐释逻辑化,而一旦这样做,就必然遗漏人身上那些跟这套逻辑无关或冲突的属性。反之,如果要在认识中兼容人的异质性属性,就只能满足于就事论事式的现象描述,而无法上升到理论的层面。这样一种困境也从马克思和施蒂纳的理论走向中反映出来。施蒂纳拒斥一切本质的结果是走向了价值上的彻底利己主义,即走向了一种新的本质,而且这种本质的纯粹性丝毫不亚于黑格尔的精神。其结果是:“我”似乎是指具体的个人,但实际上是指这些个人所共有的那个“我”性;以具体的个人的名义争得的实体兼主体的地位最终还是被他们的一种属性所篡夺了。马克思的情况有相似之处。他最大限度地认可了人的丰富属性,但当他试图给这些属性一个逻辑化的说明的时候,尤其是当他决心为人的各种属性的彻底合理化寻找现实途径的时候,他最后还是在人的众多属性中挑选了物质生产属性作为本质。这样做的结果是:被确认为本质的物质生产取代具体的个人成了实体兼主体。
虽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及之后,马克思始终坚持个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这样的价值理想,也照样讲人的主体性,但是,既然物质生产成了社会历史的最终决定因素,人作为实体兼主体就越来越有名无实,甚至反主为客了。重要的并不在于人和物质生产究竟哪一个更应充当实体兼主体,而在于究竟是人的某种本质充当实体兼主体,还是杂有无数异质性属性的个人充当实体兼主体。其中的关键在于是否承认与重视异质性属性以及如何理解和对待异质性属性。如果不能在理论上给人的异质性属性一个合理的安排,即使把人奉若神明也不意味着对人的地位的尊崇。比如,费尔巴哈的人就是自己的神,但那并非真实的个人,而只是一种号称“人”的属性。如果是在认可异质性属性的前提下把人当作实体兼主体,人论的思维方式就转向了非本质主义;反之,如果不认可异质性属性,不论将什么看作实体兼主体,其思维方式都是本质主义的。
马克思看到并揭示了物质生产的巨大作用,这无疑是他作为伟大思想家的独到之处。甚至他的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也为此作出了贡献。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当马克思指认物质生产为社会历史的决定因素,从而也是人的决定因素时,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使得他一方面不可避免地无法看到从其他理论视角可能看到的东西,另一方面同样不可避免地要把从自己的理论视角所看到的东西当成唯一真实的东西。在马克思之后,许多思想家又确认了不少新的人类本质,又提供了对于人、对于社会历史的新的说法,这些说法也无不各有所见,同时也各有所蔽。不管怎样,它们合在一起,最真切地向我们展示了人的属性的异质性状态,表明了一个深刻而朴素的道理:人的全部异质性属性无论如何不可能在一套逻辑一贯的理论体系中得到有效的说明,它们必定只能由许多不同的逻辑化理论体系分别加以说明。如果事情仅仅是解释人、解释世界,那么,本来片面却自以为全面倒也无关紧要。如果事情是彻底改变世界,那么,把一种特定视角的所见当成世界的全部或决定性的方面,其后果就不堪设想了。自从马克思把物质生产确定为人及其社会历史的本质以来,实践中的大量深痛教训不断将人和社会历史的其他属性逐一揭示在我们面前,让我们觉悟到:解决社会人生的问题,特别是历史长期积淀下来的问题,完全依靠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是肯定不行的。
在确认物质生产是人的本质之后,马克思的精力主要投入到了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研究之中。对他来说,大的原则性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剩下的问题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规律的发现问题和无产阶级革命任务的制订问题。在这一漫长的研究时期,马克思在理论上最重要的成就是演绎了“资本的逻辑”。这个逻辑实际上就是物质生产在资本主义阶段所表现出来的客观必然规律。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扮演着实体兼主体的角色,资本的逻辑支配着社会人生的所有方面,资本就是人的本质,也是世界的本质。资本的运行遵循自身的逻辑,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资本的逻辑支配下,个人只是机器、奴隶或拜物教徒,即使无产阶级也不过是资本逻辑自我演进的一个环节。资本的本性就是通过吮吸人的劳动而不断膨胀,并且把绝大多数人逼向生活的绝境,但它运行的终点却是自身的灭亡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资本仿佛一枚威力无比的运载火箭,只有它才能将人送到足以脱离物质必然性束缚的地方,让每一个人都能在自由王国中成为“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的人。显而易见,在这里,马克思所运用的思维方式就是标准的黑格尔式的本质主义,资本的逻辑跟绝对精神的逻辑在思维方式上没有什么两样。马克思也公开承认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甚至说自己在《资本论》的有些章节是在卖弄黑格尔的表达方式[4](P24)。
至此,马克思完成了向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复归。因为这一缘故,生动的、丰富的个人被放置到了历史的彼岸,而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的个人则被还原成了统一的本质——没有个人,只有资本;没有个人,只有阶级。个人及其所杂有的众多属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从一开始就没有被马克思注意到,而到最后则连被马克思注意的可能性都丧失了。
沿着这条本质主义的思路,后世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人论最终走到了本质化的极端,将人仅仅解释为阶级的人,并仅仅按照其阶级身份加以对待。实存着的千差万别的个人,有着种种感性的个人,在这种强大的本质化潮流的洗刷下都成了阶级性的千篇一律的符号,自由的全面发展的个人即使作为彼岸的理想也无由奢望。这样的理论和实践后果一定是马克思所始料未及的。他预设的是一个富于反本质主义内涵的价值目标,可走的却是一条彻底本质主义的道路。只是当这条路已经无法走通的时候,人们才发现,他们沿路实际所看到的人的景象跟马克思所预言的人的景象大相径庭。
这种变化过程跟马克思所批评的旧唯物主义的变化过程何其相似——“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的唯物主义到头来变得敌视人了。
结语
本文从个人与其所拥有的众多属性的关系出发,对马克思关于人的理论的思维方式做了一番较为系统的考察,得到的基本结论是:马克思早期所树立的关于人的价值理想是个人所拥有的丰富的资质和禀赋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理想所反对的是把具有丰富属性的人变成一种片面的人,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人论富于反本质主义的意蕴;但与此同时,马克思又赋予了这一价值理想以“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这一本质,在其后的思考中,在为人的价值理想探寻现实道路的过程中,他又进一步将人的本质规定为社会关系的总和,规定为物质生产活动,规定为资本及其运动的必然逻辑,从而回到了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轨道上。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人论中,存在着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的内在冲突。
下面还有一些补充性的说明。
我们过去的研究大多倾向于将马克思的人论解释为一个逻辑上无矛盾的圆满体系,而不愿意去想象马克思的理论也可能存在某些问题,或者情愿将马克思的问题归咎于那些可以从其思想内核中剥离出来的部分。总之,人们乐于塑造一个无问题的纯真的马克思的形象。本文的分析显示,思维方式上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的冲突就是马克思人论的思维程序方面的问题,并且该冲突贯穿于马克思对人的思考的始终。
过去的研究习惯于无语境的操作,将马克思的思想观点从其活动的具体过程中孤立出来,将其思想活动从其思想的具体环境中孤立出来,将其思想环境从其环境的社会历史方位中孤立出来,从而使马克思的思想成了一种无语境的超历史的抽象的真理体系。对马克思人论的研究也不例外。本文的分析表明,马克思对人的问题的思考是在一个复杂的社会历史语境和学术语境中进行的,或者说是在一个思想的生态系统中进行的,其中,马克思的观点只是复杂的互动关系中的一方,其观点的不断调整也是这种互动过程的结果。因此,马克思人论确实是关于人的思考的一条颇有特色和成效的路径,但绝非唯一可能和唯一合理的路径。只有把马克思的人论还原到它的实际语境之中,看成其所属的生态系统的一个部分,我们才能更加真切地理解它的含义和价值。
我们过去对马克思人论的研究还往往是缺乏立场或隐瞒立场的操作。究竟从什么样的视角出发来分析马克思的人论?采取该视角的学理依据是什么?究竟用什么样的价值尺度来评价马克思的人论?该尺度是从哪里来的?研究者个人在分析、评论马克思人论时的学术主张究竟是谁的?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这些问题不是被有意回避就是交代模糊。有鉴于此,本文明确地把个别事物与其众多属性间的关系问题作为分析的视角,把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的对立关系作为评价的尺度,并说明了该视角和尺度的学理渊源与现实根据,以及笔者本人在这方面的心得,以尽量限定本文观点的适用范围。也就是说,本文对马克思人论的种种论断都是从一个明确规定了的前提出发所得到的结论,跟从其他前提出发所看到的看法不必然构成反驳关系。这样一来,本文可能存在的问题也都可以从纯粹学理上加以检视了。
认为马克思人论存在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的内在冲突,不意味着对马克思人论的全盘否定。一个思想家的高明不在于他的理论无所不备、完美无缺、永远正确,而在于他能见他人之所不能见。只要马克思人论所开显的人的特定逻辑扇面不能被其他理论所兼容,它的意义和价值就是永恒的。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马克思人论也只是对人的众多解释体系中的一种。既然我们都同意柏拉图的人论、亚里士多德的人论、黑格尔的人论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就不肯承认马克思的人论也存在自己的问题呢?既然我们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批评丝毫无损于他们在思想史上的杰出地位,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必要担心对马克思的反思性研究会有损于他的历史地位呢?
归根到底,反思马克思人论的思维方式,是为了检讨我们自己在人的问题上的思维方式。如果我们到今天还看不到马克思人论的思维方式的问题,就意味着我们还在犯同样的思维错误。当然,我们领悟到马克思人论的思维方式的问题,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就此可以迎刃而解。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问题并非马克思人论所独有的问题,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它是人类思维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在一个更深的层面上去思考和解决这个问题,正是当今时代需要我们承担的一个重要课题。无论如何,马克思人论对理解这个课题、完成这个课题都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
[收稿日期]2003-10-09
标签:本质主义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社会冲突论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社会属性论文; 异质性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动物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