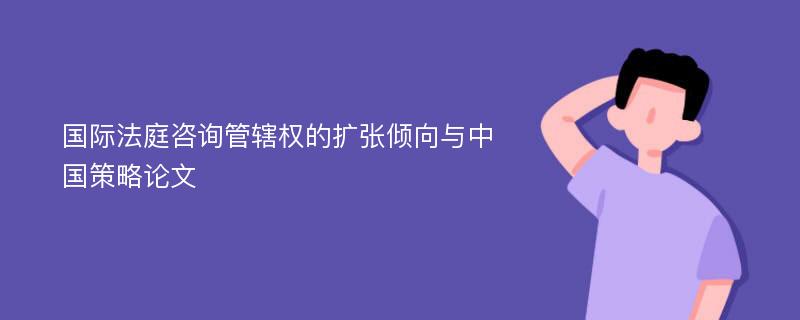
国际法庭咨询管辖权的扩张倾向与中国策略 〔*〕
罗国强, 于敏娜
(武汉大学 国际法研究所,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国际法庭咨询管辖权整体上呈扩张倾向。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来看,联合国时期,国际法庭的咨询管辖权相比于国际联盟时期发生了较多变化:国际海洋法法庭全庭创新性地建立起咨询管辖权,国际法庭咨询管辖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国家同意原则”的限制性作用不断降低。因此,有必要分析国际法庭咨询管辖权扩张对其自身和国际社会可能带来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结合中国利益的需要,全方位、分层次地提出应对之策。
〔关键词〕 常设国际法院;国际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咨询管辖权;国家同意原则
纵览国际法的历史,通过发表咨询意见在阐明和发展国际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国际法庭主要包括常设国际法院(PCIJ)、国际法院(ICJ)和国际海洋法法庭(ITLOS)(以下简称“海洋法法庭”)。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国际法庭咨询管辖权呈现出扩张的倾向,且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与警惕:1997年《国际海洋法法庭规则》(以下简称“《海洋法法庭规则》”)第138条将咨询主体扩展至“任何主体”(whatever body),这意味着国家也可能直接向海洋法法庭提出咨询申请;2015年4月,国际海洋法法庭全庭(以下简称“海洋法法庭全庭”)对第21号案〔1〕第一次发表了咨询意见,通过演进解释的方式将其咨询职能的法律依据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附件六《国际海洋法法庭规约》(以下简称“《海洋法法庭规约》”)第21条及相关国际协定上,这一举措被一些国家和学者视作海洋法法庭咨询管辖权的“激进”扩张;2017年6月,联合国大会向国际法院申请就“查戈斯群岛从毛里求斯分离的法律后果案”发表咨询意见,英国强调该问题实质上属于英毛两国之间的争端,国际法院应当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适用“国家同意原则”,作出拒绝发表咨询意见的裁决。〔2〕2019年2月,国际法院仍就该问题发表了咨询意见,此案之后,“国家同意原则”与国际法庭咨询管辖权之间的关系问题再次引起国际社会热议。
事实上,国际法庭的咨询职能并非用以裁断国际争端,咨询意见对争端当事国没有拘束力,其主要功能在于解答咨询主体提出的法律问题并提供法律建议。回顾国际法庭咨询实践的历史,咨询意见无疑在指导和调整国际法主体的行为、预防和解决国际争端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咨询事项往往兼具法律性与政治性,有时会涉及双边或多边争端,有时具有较强的政治敏感性,例如在“科索沃独立咨询意见案”〔3〕、“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案”〔4〕、“查戈斯群岛从毛里求斯分离的法律后果案”等咨询案件中,一些国家基于咨询事项具有政治敏感性、实质上属于双边争端等理由,认为国际法院或海洋法法庭对此类案件不具有咨询管辖权或不宜发表咨询意见,但国际法院和海洋法法庭至今尚无因缺乏相关国家同意或案件具有政治性质而拒绝发表咨询意见的先例。因此,有必要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研究国际法庭咨询管辖权的发展历程,梳理咨询管辖权扩张的具体表现并探清背后的原因,分析对国际社会、国家可能产生的影响,据此提出中国应对之策。
一、国际法庭咨询管辖权的演进与扩张
(一)海洋法法庭设立咨询职能
国际法意义上的咨询职能源于常设国际法院,最初是为了弥补国联体系中国际组织不能成为诉讼当事方这一缺陷而创设的。〔5〕作为常设国际法院的继承者,国际法院保留并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职能。此后成立的许多国际法庭也都设置了咨询职能,海洋法法庭便是其中之一。但UNCLOS在设计争端解决机制时,希望建立起导致拘束力裁判的强制程序以解决争端,〔6〕并未期待海洋法法庭全庭发挥咨询职能,仅规定了法庭内部的独立司法机构——海底争端分庭为配合国际海底管理局(以下简称“管理局”)的工作而发表咨询意见的义务。
从国际法庭的发展历史来看,国际社会倾向于通过使用咨询程序了解和测试新成立国际法庭的运作情况。常设国际法院受理的前四个案件均为咨询案件,国际法院设立之初,咨询程序的使用频率也比较高。与之相反,海洋法法庭全庭的咨询职能是随着司法实践的需求逐渐建立并发展起来的。UNCLOS及其附件中并未明确规定海洋法法庭全庭具备咨询职能,1997年,依据《海洋法法庭规约》第16条通过的《海洋法法庭规则》第138条首次规定了海洋法法庭全庭咨询管辖权的行使条件,此时海洋法法庭已经投入运作一年有余。随后数年中,海洋法法庭的法官们在国际社会持续发声论证海洋法法庭全庭咨询职能设立的必要性和合法性。从这个角度来看,2015年,海洋法法庭全庭通过第21号案明确自身咨询职能的法律基础并首次发表咨询意见的结果似乎也在国际社会预料之中。
2013年3月,西非次区域渔业委员会(SRFC)向海洋法法庭全庭申请就在第三国专属经济区内从事IUU捕鱼活动〔7〕船舶的船旗国义务与责任承担问题发表咨询意见。就管辖权问题而言,在参与发表意见的国家和国际组织中,过半数表示支持海洋法法庭全庭行使咨询管辖权,包括中国、英国、美国在内的另一部分国家则持反对态度。不同意见之间争议的核心问题在于海洋法法庭全庭的咨询管辖权在UNCLOS中是否有法律依据。参考各方意见之后,海洋法法庭全庭重点审查了UNCLOS第288条、《海洋法法庭规约》第21条及《海洋法法庭规则》第138条。
首先,海洋法法庭全庭阐明《海洋法法庭规约》与UNCLOS具有同等法律地位,二者之间无附属关系,解释《海洋法法庭规约》第21条不需要以UNCLOS第288条为前提或限制;其次,法庭以演进解释的方式解读《海洋法法庭规约》第21条规定的“一切事项”(all matters),认为“一切事项”区别于“一切争端”和“一切申请”,其内涵包括咨询申请;再次,法庭认为《海洋法法庭规约》第21条与本条规定的“其他国际协定”共同构成海洋法法庭全庭咨询管辖权的法律基础。其他国际协定在本案中即为《关于在次区域渔业委员会成员国管辖海域内最低限度利用和开发渔业资源的决定公约》(MCA Convention)〔8〕。基于上述理由,海洋法法庭全庭认为自身具备咨询职能。最后,法庭指出《海洋法法庭规则》第138条并非其咨询职能的法律基础,而是咨询管辖权的行使条件,即由符合UNCLOS目的的国际条约特别规定、咨询事项为法律问题、咨询主体为相关国际条约规定的任何主体。在本案中,审案法官全体一致认为本案情形满足上述三个条件,海洋法法庭全庭有权就本项申请发表咨询意见。
第21号案是海洋法法庭全庭受理的首例咨询意见案,本案的管辖权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因为这关系到海洋法法庭对UNCLOS的解释态度及其在未来海洋争端解决中扮演的角色。但在本案中,海洋法法庭全庭仅用寥寥数语就完成了最具争议的管辖权问题的论证。不得不承认,以《海洋法法庭规约》第21条和“其他国际协定”共同作为海洋法法庭全庭咨询职能的法律依据,既避免了依据UNCLOS第288条第2款面临的咨询程序与“导致有拘束力裁判的强制程序”之间无法调和的冲突,又避免了直接依据《海洋法法庭规则》第138条效力层级过低、生效时间太晚的问题,而且还可以据此主张UNCLOS的缔约国已经事先概括性同意接受海洋法法庭全庭的咨询管辖权。但很多缔约国表示无法接受此种推定,在国际法学界也依旧面临质疑之声。〔9〕参与本案审理的科特法官在其声明中表示:海洋法法庭忽略自身与国际法院咨询程序的区别,一味沿用国际法院的做法不合时宜。
从本案的管辖权裁决来看,海洋法法庭倾向于以发展的眼光解释UNCLOS之规定。一方面,作为唯一一个由UNCLOS创设的、专门解决海洋权益纠纷的国际法庭,海洋法法庭全庭缺失咨询职能使其在解释UNCLOS和其他国际条约的规定、指导缔约国行为等方面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设立海洋法法庭全庭的咨询管辖权确实能够起到完善海洋法法庭职能、推动和平解决海洋争端、增强海洋法法庭国际影响力的作用;但另一方面,UNCLOS起草过程中各国并无授予海洋法法庭全庭咨询职能之意图,其对第21号案行使咨询管辖权并发表咨询意见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缔约国授权的范围行事,可能会引起一些国家的反感情绪,影响法庭的公信力。
(二)国际法庭咨询管辖范围的扩张
常设国际法院设立咨询管辖权至今,国际法庭咨询管辖范围的扩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咨询主体范围不断扩大,二是咨询事项边界模糊,国际法庭运用扩张解释逐渐扩大咨询管辖范围。
第一,咨询主体范围不断扩大。国际联盟时期,根据1920年《国际联盟盟约》(以下简称“《国联盟约》”)第14条规定,有权提出咨询申请的主体只有国联行政院和大会。联合国时期,国际法院继承并发展了常设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在申请主体方面,《联合国宪章》(以下简称“《宪章》”)第96条第1款延用了《国联盟约》第14条的规定,授予联合国大会(以下简称“联大”)和安全理事会(以下简称“安理会”)申请咨询意见的权利,〔10〕同时新增第2款,规定了经联大授权的联合国其他机关(Other Organs)和各种专门机关(Specialized Agencies)就其工作范围内的任何法律问题请求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的权利。实践证明,这一新规定在扩张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国际法院在其存续的74年间共发表了27项咨询意见,虽然咨询程序的使用频率相比国际联盟时期有所下降,但从咨询主体的分布情况来看,有16项和1项咨询意见分别是由联大和安理会提出申请,10项咨询意见是应联合国的其他机关和各种专门机关的申请而发表的。海洋法法庭的咨询管辖权包括两部分:海底争端分庭的咨询管辖权和海洋法法庭全庭的咨询管辖权。为配合管理局履行组织和控制“区域”内活动的职能,海底争端分庭对UNCLOS第十一部分“区域”及其有关附件、规则的解释与适用和由此产生的争端享有专属的咨询管辖权。〔11〕因此,只有管理局的大会或理事会有权向其申请咨询意见。与海底争端分庭严格限制咨询主体的做法相反,有权向海洋法法庭全庭提出咨询申请的主体几乎是不受限制的,“相关国际条约授权的任何主体”均可,这一宽泛规定意味着国际组织、国家、国内法院、公司甚至个人都可能成为向海洋法法庭全庭提出咨询申请的适格主体。
这件事情终于惹恼了一个人,小六子。一天,我像往常一样,从西山煤窑下班回来。那一天煤老板发了工资,我特意多走几步去一家小卖部买了些酒和肉。我这天仿佛感觉到了,他们家里的气氛还算不错。小六子当然在家,他正抚摩着一根他父亲曾经在煤窑上做工时使用过的榆木镐柄,笑容可掬的。他的神态让我有点莫名其妙。不过,我还是摆出一副男人特有的自如和傲气来。我进到屋里。
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已成为临床常见的下肢静脉疾病之一,在下肢静脉疾病中,下肢深静脉瓣膜功能不全约占40%~50%[1-2]。目前,临床常用于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的辅助诊断和功能评估方法主要包括彩色多普勒超声、数字X线引导下下肢静脉造影、磁共振成像静脉造影、计算机断层扫描静脉检查等[3-4]。其中,彩色多普勒超声作为常用的无创性检查方法,在下肢静脉疾病诊断中的价值也逐渐受到关注[5-6]。本研究对比分析彩色多普勒超声与数字X线引导下下肢静脉造影在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中的诊断价值。现报道如下。
第二,咨询事项范围不断扩大且边界模糊。国际法庭自由裁量空间较大,且在咨询实践中倾向于作出适合发表咨询意见的裁决。1920年《国联盟约》第14条规定,常设国际法院可以就任何争端(dispute)或问题(question)发表咨询意见。联合国时期,国际法院成为联合国的司法机关,其咨询职能向服务于联合国的整体运行转变。在可以申请咨询意见的事项方面,《宪章》第96条第1款用“任何法律问题”(any legal question)代替了《国联盟约》第14条规定的“争端或问题”,以表明国际法院咨询职能的目的是解释法律问题,而非裁断国际争端。向海底争端分庭申请咨询的事项必须是发生在申请机关活动范围内的法律问题。海洋法法庭全庭则有权对“与UNCLOS目的相关的国际条约中特别规定向法庭申请咨询的法律问题”发表咨询意见,将咨询事项的范围扩展至UNCLOS之外,涵盖了“与UNCLOS目的相关的国际条约”中产生的法律问题。
在前文提到的咨询意见案中,申请咨询的问题大多与国家之间的争端紧密相关。1975年“西撒哈拉案”起源于西班牙在西撒哈拉地区实行非殖民化运动与摩洛哥王国和毛里塔尼亚实体对该地区提出的主权要求之间的冲突。联大申请咨询的问题是西班牙殖民地时期,西撒哈拉地区是否是无主地?如果不是,该地区与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之间存在什么法律关联?国际法院发表的咨询意见认为:西班牙殖民地时期,西撒哈拉地区不是无主地;该地区与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之间存在法律关联,但不存在主权关联,不影响联大关于西撒哈拉非殖民化的第1514(XV)号决议的执行,特别是该地区人民自由而真实的表达意愿的民族自决原则。〔34〕2019年“查戈斯群岛从毛里求斯分离的法律后果案”事关英国对查戈斯群岛的管理行为和毛里求斯对查戈斯群岛的主权主张之间的冲突,联大申请咨询的问题是:(1)在查戈斯群岛与毛里求斯分裂后并考虑国际法,毛里求斯在1968年获得独立时,其非殖民化过程是否依法完成?(2)根据国际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继续管理查戈斯群岛将产生何种后果?〔35〕国际法院发表的咨询意见认为:(1)毛里求斯在1968年获得独立时,其非殖民化过程尚未依法完成;(2)英国有义务尽快停止管理查戈斯群岛;(3)会员国有义务与联合国合作完成毛里求斯的非殖民化运动。〔36〕
扩张倾向最为明显也最具争议的是海洋法法庭全庭的咨询管辖权。海洋法法庭全庭的咨询职能建立较晚,目的在于保障UNCLOS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良好履行,侧重于阐明海洋法问题。因此,《海洋法法庭规则》第138条对海洋法法庭全庭咨询管辖范围的规定非常宽泛。一方面,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来看,本条规定并未限制申请咨询意见的主体资格,相关国际条约授权的“任何主体”都满足条件。也就是说,只要是由两个国际法主体(国家和国家、国家和国际组织均可)签订的、符合UNCLOS目的的国际条约授权主体即可,包括国家和个人。尽管部分学者试图对本条进行严格解释,将申请主体限制为国际组织,不包括国家。但是法庭第21号案中已经对《海洋法法庭规约》第21条进行了演进和扩大解释,若对对应的《海洋法法庭规则》第138条进行严格和限制解释,似乎不合逻辑。〔13〕另一方面,《海洋法法庭规则》第138条对咨询事项的限制条件有二:由符合UNCLOS目的的国际条约特别规定;咨询事项为法律问题。海洋法法庭全庭在第21号案咨询意见中认为次区域渔业委员会提请咨询的问题符合本条对咨询事项的要求。第一,咨询请求是依据MCA Convention及其相关决议提起,MCA Convention的前言部分写明,“本公约考虑到1982年UNCLOS关于提倡在渔业和其他相关国际条约领域签订区域或次区域协议的规定”,意在确保“实现在不同海洋区域内更好开发渔业资源的活动和次区域渔业委员会成员国国内法律政策相协调”。因此,MCA Convention与UNCLOS的目的紧密相关。第二,次区域渔业委员会的咨询事项属于“法律问题”。爱尔兰曾在书面意见中表示,申请咨询的法律问题应当与MCA Convention的具体条款有关,不应广泛扩展至对UNCLOS的解释与适用。〔14〕这种观点最终没有得到采纳。在海洋法法庭全庭看来,《海洋法法庭规约》第21条使用的“一切事项”一词,表明只要次区域渔业委员会申请咨询的问题属于MCA Convention的框架范围内即可,不需与具体条款直接相关;至于判断某个问题是否属于MCA Convention的框架范围内,法庭全庭引用了国际法院“一国在武装战争中使用武器合法性问题的咨询意见案”〔15〕中使用的标准——“足够联系”(sufficient connection),也就是说,只要咨询事项与MCA Convention的原则与目的之间有足够联系即可。由此可见,海洋法法庭全庭在咨询主体和咨询事项两个方面都采取了非常宽松的规定和解释方式:任何经授权的主体都可以就与UNCLOS的目的与宗旨相关、与相关国际公约目的与宗旨相关的法律问题提出咨询申请。这表明海洋法法庭全庭已经做好通过发挥咨询职能参与未来海洋权益纠纷解决的充分准备。
随着区域教育现代化的强力推进,近几年,中小学校的教学设施设备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普通的中小学校,体育馆和塑胶操场不再是奢侈品。据笔者统计,笔者所在市区9所较大规模学校中,每所学校都建有室外塑胶田径场和篮排球场,建有室外足球训练场地的学校有8所,拥有室内篮排球训练馆的学校有7所,拥有室内乒乓球、羽毛球训练场馆的学校有6所,可见,目前学校的体育场馆设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6)6—9月份,田间卵果率达到1%时,及时喷25%灭幼脲1 000倍液或2.5%溴氰菊酯乳油3 000倍液。
当今时代,国际法在各个领域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全球性、区域性国际法庭纷纷设立,在无政府的国际环境下,国际法庭为更好地解释和发展国际规则、增强自身影响力,建立咨询管辖权并扩张管辖范围也无可厚非。值得注意的是,从国际司法实践的历史来看,国际法庭咨询管辖范围的扩张并不一定导致咨询程序的高频率使用,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范围相比常设国际法院有所扩张,但咨询程序的使用频率却远低于其前任。对于国际法庭而言,提高各项程序的使用几率固然重要,然而最重要的依然是保证自身客观中立,建立公信力,维护司法权威性。
二、国际法庭咨询管辖权扩张与“国家同意原则”
的冲突
“国家同意原则”与国际法庭咨询管辖权之间的关系问题自国际联盟时期就一直存在。近年来,国际法庭咨询管辖权扩张倾向愈发明显,特别是2019年国际法院对“查戈斯群岛从毛里求斯分离的法律后果案”发表咨询意见后,这一问题再次回到国际社会的视线当中。
(一)国际法庭咨询管辖权与“国家同意原则”冲突的原因
传统国际法认为,“国家同意原则”〔16〕是国际法的重要基石,也是国际法的效力根据。〔17〕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和国际法的基本特点决定了“国家主权原则”是一项最重要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因此,只有获得了主权国家明示或默示的同意,现代国际法体系才得以建立和顺利运行,国际法规则才能发挥约束力。〔18〕“国家同意原则”是国际法体系建立和运行的基础,贯穿在国际法的各个领域。它在国际条约的缔结与修改、国际习惯的认定、国际组织的设立与运作、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运行、国家间的交往等方面,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国际司法领域,“国家同意原则”是国际司法程序运行的基本原则,现代国际法庭通常通过国家明示或默示的同意获得对争端的管辖权并保障裁决履行。〔19〕“国家同意原则”能够在国际关系中抵御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对国家主权的侵蚀,并能够保证国家在参与国际事务时表达自己的意志,维护自身利益,提高各个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积极性,由此达成的规则也更容易被相关国家接受和推行。〔20〕
但是,“国家同意原则”究竟是否适用于咨询制度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在国际法庭看来,咨询职能与诉讼职能分工不同、彼此配合。诉讼职能是为了定纷止争,法律效果直接作用于争端当事国和主要利益相关国家,还伴随着一定程度上的强制执行力,因而在行使诉讼管辖权时,需要获得相关国家的同意。而咨询职能的目的是为申请者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只是建议性质,不针对具体争端,也不具有拘束力,自然不受到“国家同意原则”的限制。因此,从近半个世纪的司法实践来看,国际法庭在行使咨询管辖权时对“国家同意原则”采取一种“轻视”“漠视”的态度,引起主权国家的普遍担忧:若解除“国家同意原则”的限制,国际法庭很可能为了增加咨询程序的使用机会,激进地扩大管辖范围,从而被有心人士用作诉讼程序的替代品,将双边或多边争端“加工包装”后提交国际法庭申请咨询意见,以达到裁断国际争端或影响争端的政治解决进程之效果,加上难以预判的后续影响,如以咨询意见为依据的联大决议、国际组织的新规则、国际社会的舆论导向等,都可能导致自身丧失争端解决的主动权。从这个角度来说,国际法庭违背国家意志发表咨询意见可能导致矛盾升级,不利于国家之间和平解决争端,也会引起国家对国际法庭的反感情绪,丧失对国际法制的信心。〔21〕
除此之外,十堰天舒感应设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伍祥先生、金巨达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蔡明芳先生也分别进行了主题演讲,向大家分享了感应加热技术及电化学加工领域等实践案例和生产经验。
由此可见,这一冲突从本质上来看是国家寻求维护主权和国际法庭追求发挥更大作用之间的矛盾,〔22〕也表现出不同国际法主体对同一国际法原则理解的差异。想要协调冲突、消除差异,有必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结合具体案例,对比不同的国际法庭在行使咨询管辖权时对待“国家同意原则”的态度与方式并分析原因。
(二)“国家同意原则”是常设国际法院行使咨询管辖权的基本原则
总而言之,基于复杂的周边环境,中国目前处理和解决国际争端,特别是海洋争端的战略依旧需要以协商合作为基本出发点。中国应当继续推动双边和多边条约的缔结,将争端的解决方式尽量限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但是,不主动使用不代表没有应对能力,国际法庭的诉讼职能和咨询职能都应当成为中国解决国际争端有力的辅助工具。有必要全面深入地研究国际法庭的咨询职能,在立法环节和参与咨询程序的过程中,坚持符合中国利益需求、符合国际法基本原则的立场,做好积极的应对准备,避免出现措手不及的局面。在必要时也需主动使用国际法庭的咨询程序,以免落入被动局面。
“东卡雷利亚案”是常设国际法院唯一拒绝发表咨询意见的案件,在本案中,常设国际法院明确确立了“国家同意原则”适用于咨询管辖权领域,被称为“东卡雷利亚原则”。该案涉及对芬兰与苏联(非国联会员国)签订的《和平条约》第10条、第11条及苏联代表团关于东卡雷利亚地区自治地位的声明进行解释一事。首先,常设国际法院指出,提交给法院的是芬兰和苏联之间实际存在的争端(actual existing dispute),对该问题发表咨询意见实质上是裁决两国之间的争端。其次,本案的当事国苏联并非国联的会员国,应当适用《国联盟约》第17条。“国家主权独立原则”(the principle of the independence of States)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未经一国同意,不得强迫以调停、仲裁或任何其他和平方式解决它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争端,已经在国际法上得到确认,〔23〕国际法院不能忽视这一原则作出司法决定。对于表示同意的方式,法院表示,国联的会员国既可以通过自愿承担义务的方式一次性表示同意,也可以针对具体案件表示同意;非国联的会员国不受《国联盟约》约束,对于发生在非会员国与会员国之间的争端,只有征得非会员国的同意,才能按照《国联盟约》解决。〔24〕在本案中,苏联多次明确表示拒绝国际联盟介入。再次,由于苏联拒绝合作,导致法院难以查明对案件至关重要的事实问题。综合上述多方面理由,法院裁定拒绝发表咨询意见。
这一做法在咨询职能备受质疑和担忧的时代背景下,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一个声音:常设国际法院的咨询职能不会违背“国家同意原则”,也不会被随意用以裁断国家之间实际存在的争端。
东莞石排产业转型的过程中,面临着众多的困境,限制了东莞石排产业的快速发展,落后的企业产能,在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下,生产成本不断提升的情况下,众多行业呈现了竞争同质化的问题,导致众多品牌企业的核心技术处于同水平的状态,是阻碍东莞石排产业转型的重大问题。此外核心企业的外迁会导致迁入地发展锁定,与承接地区处于价值链和产业链的地段,拉大输出地与承接地技术差距的威胁,使得地区发展陷入锁定的风险。甚至因为投资政策、生产成本等因素,造成核心企业的污染再一次转移,使得迁出地区的产业空心化。
2.进一步确认“国家同意原则”
国际联盟时期,大会或行政院采取“一致同意”的表决机制,然而,在1925年“关于《洛桑和约》第3条第2款的解释咨询案(关于土耳其和伊拉克的边境线)”中,土耳其在表决环节中投票反对将该问题提请常设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行政院依旧提交了咨询申请,同时提出“与案件利益相关的国家是否有投票权”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常设国际法院发表的咨询意见认为:行政院作出的决定必须全体一致通过,与案件利益相关的国家也应参加投票,但它们的投票不影响表决结果的一致性。〔25〕本案再次印证了常设国际法院在“东卡雷利亚案”中表达的“国联的会员国可以通过自愿承担义务的方式一次性表示同意接受常设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这一观点。土耳其作为国联的会员国,已经概括性同意接受《国联盟约》第14条之规定,针对具体案件表示反对是无效的。
1926年3月2日,美国告知国联大会欲加入《常设国际法院规约》1920年议定书并提出五条保留,其中第5条第2句为:“未经美国同意,常设国际法院不应对美国为当事国的任何争端或美国主张利益的任何争端或问题发表咨询意见”。该项保留是此次会议中争议最多的一项,但是为了吸引美国加入,常设国际法院最终认为:第一,对于美国为当事国的争端,因为美国并非国际联盟会员国,应当适用已经建立起来的“东卡雷利亚原则”;第二,对于美国主张利益的争端或问题,国际联盟会员国有义务遵守《国联盟约》,非会员国则不承担此类义务。〔26〕虽然本次讨论的结果没有令美国满意,直到1929年美国才恢复与常设国际法院的谈判,但在讨论的过程中,常设国际法院再次明确确认“国家同意原则”是其行使咨询管辖权的基本原则。
常设国际法院咨询制度设立之初,咨询管辖权与诉讼管辖权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它可以直接针对国际争端发表咨询意见。为了解除国际社会的担忧,常设国际法院在行使咨询管辖权时秉持审慎的态度:一方面,《国联盟约》第14条使用了“有权”(may)一词,即常设国际法院在是否发表咨询意见方面享有自由裁量权,有可能会拒绝发表咨询意见;另一方面,常设国际法院在行使咨询管辖权时严格遵循“国家同意原则”。因常设国际法院并非国联的司法机关,而是独立运作的国际司法机构。它并非直接将“国家同意原则”适用于自身的咨询管辖权上,而是通过说明争端当事国作为国联的会员国,便概括性同意《国联盟约》第14条之规定,允许国联大会或行政院向常设国际法院申请咨询意见。在1925年“关于《洛桑和约》第3条第2款的解释咨询案”中,土耳其也并未质疑常设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而是质疑国联行政院的表决程序。
2018年10月12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社会保险领域严重失信“黑名单”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列举了六种应将其列入社保“黑名单”的情形,并指出社保“黑名单”信息将被纳入当地和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在政府采购、交通出行、招投标、生产许可、资质审核、融资贷款、市场准入、税收优惠、评优评先等方面予以限制。
通过前文的历史梳理和案例分析可以发现,国际法庭咨询管辖权整体上呈现出比较明显的扩张倾向:拥有咨询职能的国际法庭越来越多、咨询主体和咨询事项的范围越来越大、“国家同意原则”对咨询管辖权的限制性作用越来越小。
(三)国际法院视“国家同意原则”为自由裁量因素
截至目前,联合国共有193个会员国,相比于国际联盟最多时的58个,会员国数量大幅增加,且二战后至今的国际局势发生了巨大改变,国际法院在行使咨询管辖权时对待“国家同意原则”的态度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对此,有必要结合具体案例分析其真意。
1.缺乏联合国会员国特别同意的情形
在1971年“关于纳米比亚的国际地位咨询意见案”、1975年“西撒哈拉案”、1989年“《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第6条第22节适用案”和2019年“查戈斯群岛从毛里求斯分离的法律后果案”中,作为联合国会员国的争端当事国均主张未获得其特别同意构成阻碍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的“强有力的理由”(compelling reason),遭到国际法院拒绝。理由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国家同意原则”仅适用于国际法院的诉讼管辖权,不能适用于咨询管辖权。即使申请咨询的案件涉及国家之间悬而未决的争端,也不需要获得当事国同意。因为咨询意见的目的是指导申请机关的行为,而非针对当事国,对当事国并无拘束力,也不影响当事国之间解决争端的法律立场及权利义务分配。〔28〕第二,国际法院在确定是否具有咨询管辖权时一般只需考虑两个因素:申请机关是否适格、申请咨询的事项是否是法律问题,对这两个问题作出肯定答复之后,国际法院即可裁定其对案件具有管辖权。〔29〕同时,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有义务积极参与和配合联合国的行动,原则上不应拒绝发表咨询意见。第三,《国际法院规约》第65条是任意性规范,国际法院应根据实际情况行使自由裁量权,决定是否发表咨询意见,即考察是否存在阻碍其发表咨询意见的“强有力的理由”。对于“强有力的理由”的范围,国际法院没有明确说明,总结上述案例的咨询意见来看,若发表咨询意见会出现裁断国家间争端的法律后果或违背国际法院的司法性质(judicial character),便构成“强有力的理由”。〔30〕第四,国际法院多次强调“东卡雷利亚案”的情况不适用于上述案件。主要理由在于,上述咨询意见案所涉争端之当事国均为联合国会员国,已概括性同意接受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不能再以未经其同意为由提出抗辩。〔31〕
其中,1989年“《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第6条第22节适用案”中,国际法院面临的情形更为复杂。在本案中,罗马尼亚主张国际法院不具有咨询管辖权,因为罗马尼亚已经就《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第8条第30节〔32〕作出保留,未经罗马尼亚同意,经社理事会不得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申请咨询意见。虽然经社理事会在申请咨询意见时并未援引该节内容,而是以《宪章》第96条第2款为依据,但因其咨询的内容属于《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规定的实体问题,不应割裂对待,也应当属于罗马尼亚声明保留的范围。对此,国际法院首先说明,罗马尼亚是联合国会员国,应当遵守《宪章》第96条和《国际法院规约》第65条之规定。接着又指出:第一,经社理事会依据《宪章》第96条第2款向国际法院申请咨询意见,罗马尼亚无权干涉,如果经社理事会是依据《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提出咨询申请,国际法院会作出拒绝发表咨询意见的裁决;第二,咨询事项的性质和目的是关于《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中条款的适用问题,而非裁断争端;第三,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不会改变罗马尼亚依据公约承担的义务。国际法院据此裁定罗马尼亚的保留不影响其发表咨询意见。
调查研究不仅可以起到督导作用,还可以发现好的经验和做法。比如,这次督导组在江苏召开的两场座谈会,一场是企业的,另一场是银行的。在企业座谈会上,江苏省无锡市一家汽车模具企业负责人说,“欧洲客户在等着我们的订单,而我们在等着银行的钱”。另一场金融行业座谈会上,银行方面称,“不是我们不愿意贷,而是看不清、摸不透这些小微企业的风险”。
由此可见,在处理涉及联合国会员国为当事国或利益相关国的咨询案件时,国际法院沿用了其前任的做法,即已概括性同意《宪章》之规定,不需要再针对具体案件获得专门同意。国际法院在此种情形下发表的咨询意见是建立在“国家同意原则”的基础之上,不存在冲突与违背。
2.缺乏非联合国会员国同意的情形
〔16〕19世纪以来,国际法学界深受实证主义思潮影响,主流观点是:国际法的效力来源于国家明示或默示的同意(consent)。中国学者将其归纳为“国家同意原则”“国家意志合意”等多种说法。关于“同意原则”与国际法庭咨询管辖权之间的关系问题,有的学者使用“当事国同意原则”一词,但当事国一词一般在诉讼程序中使用,咨询程序中称为利益相关国家更为合适,何况咨询意见的内容也常涉及争端当事国以外的第三国的利益,这甚至可能构成咨询意见的主要内容,1943年“罗马货币案”在诉讼程序中确立了一项原则:当第三国利益构成判决的主要内容时,未经该第三国同意,国际法院对争端没有管辖权。这一先例是否适用于咨询程序也是本文研究的范围。因此,本文使用“国家同意原则”一词,既包括所涉争端当事国的同意,也包括主要利益相关国的同意,而不仅限于“当事国同意原则”的范围。
尽管国际法院对本案发表了咨询意见,但学者们对于“国家同意原则”和国际法院咨询管辖权扩张之间关系的争论并没有停止。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并未采纳国际法院咨询意见,联大随后请求国际法院继续对后续事项发表了第二阶段的咨询意见。此案似乎没有对保、匈、罗三国造成实质影响,1955年12月,它们依旧加入了联合国。
3.“国家同意原则”对自由裁量权的影响
尽管国际法院一直坚持“国家同意原则”不是国际法院行使咨询管辖权的基础原则,但是也并未完全否定其在咨询程序中发挥的作用。在1975年“西撒哈拉案”中,国际法院明确表示,“缺乏利益相关国家的同意不影响国际法院咨询管辖权的成立,但影响其发表咨询意见的恰当性。”然而截至目前,国际法院从未因缺乏当事国或利益相关国的同意而作出不适合发表咨询意见的裁决。实际上,国际法院认为:单纯以缺乏国家同意为理由,不会影响咨询管辖权的成立,也不会影响恰当性。国际法院会针对案件的具体情况审查是否涉及国家之间悬而未决的争端,是否属于国家内政,发表咨询意见是否违背自身的司法性质等,如果出现此类情况,且相关国家是基于上述强有力的理由表示反对,可能会导致国际法院拒绝发表咨询意见。但是,上述理由达到何种程度才能构成“强有力的理由”,目前没有可供参考的明确规定,国际法院在实践中倾向于作出适宜发表咨询意见的裁决。
通过历史梳理和对比分析可见,国际法庭咨询管辖的范围随着咨询职能功能定位的演变而发生变化,整体上表现出扩张的倾向。咨询主体和咨询事项两个要素应当共同发挥作用,起到规范和限制国际法庭咨询管辖范围的作用。常设国际法院作为独立的国际性法庭,有权就特定国际争端或一般问题发表咨询意见,但申请主体的范围十分有限,加上常设国际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坚守“司法性质”,〔12〕谨慎地行使咨询管辖权,这一时期咨询程序的使用频率很高,咨询意见的权威性很少受到质疑。国际法院为更好地履行联合国司法机关的职责、区分诉讼职能与咨询职能,将咨询主体扩展至经联大授权的联合国其他机关和专门机关,咨询事项限制在“法律问题”的界限之内,不再针对“争端或其他性质的问题”发表咨询意见。这一时期,咨询主体的范围虽然出现一定程度的扩大,但是依旧限制在联合国机关的范围之内。咨询事项范围变动的本意是缩小管辖权范围,但是从之后的司法实践来看,国际法院对法律问题的解释非常宽泛,几乎涵盖了国际法的所有领域,而且处理政治问题与法律问题混合的咨询案件时,只要咨询事项和法律问题“沾边儿”,一般就会作出有咨询管辖权且适合发表咨询意见的裁决。海底争端分庭的咨询职能本质上是为了协助管理局更好履行职责,因此申请主体和咨询事项的范围都严格限制在管理局的活动范围之内,而且其发表咨询意见是义务,不享有自由裁量权。
在上述两个案件中,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实质上已经对国家之间的争端作出了裁断,但因为咨询意见不具有约束力、不会改变当事国承担的义务与处理争端时的法律立场,而且这两个案件中的咨询事项都与联合国非殖民化运动有关,这表明国际法院以配合联合国的需求为己任。对此,Morozov法官表示:“这种做法可能导致一种危险的局面,国际法院可以收到咨询意见的申请为理由,自动介入任何有关联合国机关的宪章性权利和行为的问题或有关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中。”〔37〕尤瓦·沙尼认为,如此激进的咨询管辖权实际上已经绕过“国家同意原则”,建立起国际法院全球性的强制管辖权。〔38〕在1975年“西撒哈拉案”中,摩洛哥建议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未得到西班牙同意,摩洛哥便将问题提交联大,1974年,联大通过3292号决议,请求国际法院对西撒哈拉的法律地位发表咨询意见,尽管西班牙强烈反对,国际法院仍旧于1975年对该问题出具了咨询意见。2019年“查戈斯群岛从毛里求斯分离的法律后果案”中,毛里求斯和英国多次试图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争端,但一直没有达成一致结果,2017年6月,毛里求斯将查戈斯群岛问题提交联大,发起投票程序,并以94比15票的比例通过A/RES/71/292号决议,〔39〕请求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
本文选择2010—2015年深沪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删除金融类、ST 类企业,删除股东权益小于零的公司,并选取证券行业分类为制造业(C)、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I)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M)的企业,最终样本得到10 174个观测值。专利数据、企业财务数据、R&D研发项目投入和政府补贴等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为消除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数据在1%水平上进行了Winsorize处理。
与常设国际法院相比,国际法院咨询管辖权的范围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扩张。作为联合国的司法机关,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在《宪章》有明确规定,联合国会员国签署《宪章》即表示事先概括性同意接受其咨询管辖权,在特定咨询案中不需要表达专门同意,自然也不得以未经其同意为由提出抗辩。自1950年“对保、匈、罗和约的解释案”起,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就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国家同意原则”的限制,在此后的司法实践中,国际法院重复表达的观点是:从本质上来看,咨询意见只是发生在国际法院和申请机关之间的关系,咨询职能的目的是为申请机关提供法律建议,不针对具体国家,也不具有约束力。虽然国际法院承认,会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考虑“国家同意原则”,但其至今尚未因上述理由拒绝发表过咨询意见,这一做法引起了一些国家的不满情绪。
(四)海洋法法庭明确否定“国家同意原则”适用于咨询管辖权
〔14〕Written Statement of Ireland,28 November 2013,para.3.2.
一方面,海洋法法庭全庭的咨询职能并非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议题,其法律基础也未明确规定在UNCLOS之中,实际上是法官对《海洋法法庭规约》第21条进行演进解释的产物。因此,部分国家认为,海洋法法庭全庭超出缔约国授权范围建立咨询职能并对第21号案行使咨询管辖权违背了“国家同意原则”。另一方面,海洋法法庭全庭在自由裁量环节拒绝考虑“国家同意原则”。《海洋法法庭规则》第138条为任意性规定,在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过程中,对于是否将“国家同意原则”列入裁量理由存在争议。在本案中,次区域渔业委员会申请咨询的事项涉及该委员会会员国之外第三国的权利与义务。对此,一种观点认为,未经这些国家同意,不应当就其权利与义务发表咨询意见;另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咨询事项不涉及潜在的纠纷(dispute),因而不适用“国家同意原则”。在最终发表的咨询意见中,海洋法法庭全庭并未采纳上述两方观点,而是采取了更为“大胆”的做法。它援引了在咨询管辖权问题上充满争议的“对保、匈、罗和约的解释案”,认为咨询意见的目的只是为次区域渔业委员会自身采取行为提供参考和指引,不具有拘束力,即使咨询意见的内容涉及该委员会会员国以外的国家的权利与义务,也不需要经过这些国家的同意。
如前文所述,国际法院在1950年“对保、匈、罗和约的解释案”中违背“国家同意原则”行使咨询管辖权并发表咨询意见的做法,引起了国际社会和学界的普遍不满,此后,国际法院再也没有出现过违背国家意志、以非会员国权利义务为主要内容的咨询实践。然而,在半个多世纪以后,海洋法法庭全庭再次援引了国际法院在“对保、匈、罗和约的解释案”中关于咨询管辖权问题的观点并仿效其做法,再一次明确突破“国家同意原则”行使咨询管辖权。海洋法法庭全庭通过这一举措向国际社会强调:咨询程序的功能是通过回复问题、发表咨询意见,帮助咨询主体更好地采取行动,推动实施UNCLOS。〔40〕“国家同意原则”既非其行使咨询管辖权的前提条件,也非自由裁量的考虑因素。它意图建立起服务于任何国际法主体、阐明一切海洋法法律问题的咨询制度,不限于UNCLOS的范畴。本案作为海洋法法庭全庭处理的首例咨询意见案,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必将对今后国际法庭的咨询实践产生重大影响。
整体来看,“国家同意原则”在国际法庭咨询管辖权中的限制性作用不断降低:从常设国际法院咨询管辖权运行的基本原则到国际法院行使咨询管辖权的自由裁量因素,再到海洋法法庭全庭在第21号案中拒绝将“国家同意原则”纳入考虑因素。从理论角度来看,一方面,“国家同意原则”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基本原则,国际法庭的咨询程序是国际争端解决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可完全抛弃与违背“国家同意原则”这一基本原则;另一方面,正如国际法院和海洋法法庭在咨询实践中反复重申的观点一样,咨询意见只是国际法庭对某个法律问题的司法意见,没有拘束力,〔41〕而且相应的国际公约中都未明确将“国家同意原则”列为国际法庭咨询管辖权的行使条件或考量因素,取消这一限制并不存在国际法理论上的问题。从实际效果来看,国际法庭通过适用国际法发表的咨询意见,长期上,代表了国际法庭对特定法律问题的态度与看法,作为重要的国际法辅助渊源,对国际法规则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短期上,当申请咨询的问题涉及国际法主体之间实际存在的冲突,属于法律问题和政治问题混合事项或者高度政治敏感事项时,如果国际法庭不加区分地发表咨询意见,很可能对国际争端的解决进程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综合衡量理论因素与实际效果,“国家同意原则”应当对国际法庭咨询管辖权的行使起到限制性作用,至少应当是自由裁量的考虑因素。
由此便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国家同意原则”对国际法庭咨询管辖权的限制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以及判定标准为何?海洋法法庭全庭目前只对第21号案发表了一项咨询意见,且在本案中比较强势地否定了“国家同意原则”的限制性作用,在这一问题上参考作用不大,本部分将以国际法院为例进行分析。国际法院多次在咨询意见中表示,若相关国家基于“强有力的理由”提出反对,国际法院可能作出不适合发表咨询意见的裁决,因此,通过咨询实践明确和细化“强有力的理由”的范围和程度,能够提高国际法主体对国际法庭咨询管辖权裁决的可预测性,维护国际法庭的权威性和公信力。通过前文的梳理归纳可得,国际法院需要明晰的要素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三点:第一,“法律问题”的概念,这是国际法院行使咨询管辖权的前提条件,国际法院也曾面临咨询问题属于政治争端而非法律争端的反对意见。如果将政治争端和法律争端混为一谈,有违国际司法机构的司法性质。第二,“国家间未决的法律问题”(a legal question actually pending)的判定标准。《国际法院规则》第102条使用“国家间未决的法律问题”,而非常设国际法院在“东卡雷利亚案”中使用的“实际存在的争端”(actual existing dispute),从浅层的文义角度分析,常设国际法院的用词范围更加广泛,只要涉及“实际存在的争端”,就需要获得相关国家的同意。1950年“对保、匈、罗和约的解释案”与“东卡雷利亚案”的情况十分类似,都是关于和约条款的解释问题。国际法院认为,在1950年“对保、匈、罗和约的解释案”中,咨询问题主要是程序性问题,而非关于人权的规定,所以不属于“国家间未决的法律问题”。这样的区分标准实际上使得这一要素的边界更加模糊不清,这意味着需要区分咨询事项是国家间争端的主要事项还是非主要事项,后者并不触及国家间争端的实质部分,国际法院就有权发表咨询意见。这样的区分标准操作性较差、司法确定性也很低,几乎完全依靠法官的主观裁断。第三,“产生裁断争端的法律效果”。因为咨询职能不用于裁断争端,如果发表咨询意见将产生裁断争端的法律效果,将构成“强有力的理由”,阻止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但证明这一点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方面,咨询问题是“国家间未决的法律问题”;另一方面,发表咨询意见是对国家间的争端裁定是非曲直。第一方面在前文已经进行过探讨且证明难度很大。因咨询意见不具有拘束力,国际司法机构基本不会将发表咨询意见等同于裁断争端。所以,国际司法机构应当从案件的实际情况、可能造成的实际影响方面入手,而非仅仅依靠咨询职能和诉讼职能的理论差别,考虑是否会产生和裁断争端类似的法律效果。
三、分析与策略
(一)国际法庭咨询管辖权扩张倾向分析
国际联盟时期,常设国际法院在行使咨询管辖权时从未背离“东卡雷利亚原则”,其咨询职能在这一时期得到大量且有效的运用。由于存续时间较短、会员国数量有限,常设国际法院审理的案件数目并不是很多,共包括29项判决和27项咨询意见,但咨询意见的数量与诉讼判决的数量几乎等同。此外,国际联盟时期,常设国际法院发表的咨询意见多与一战遗留问题的解决有关,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关于凡尔赛体制生效后的东欧重组问题,〔27〕在当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除此以外,未来,货币政策仍需继续发力。业内人士表示,从央行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以及各方数据来看,市场流动性相对充裕,但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仍偏低,放贷意愿不足,继续稳定融资、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已经并将持续成为下一步政策的重点。宋清辉认为,未来货币政策应该重点关注小微企业和“三农”领域等,并通过实施定向降准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同时,货币政策方向应该朝民营企业倾斜,消除“梗阻”同时刺激金融市场对于民企的支持力度。
对国际法庭自身而言,与时俱进地发展自身咨询管辖权并审慎行使这一权利,方能实现主权国家与国际法庭之间利益的平衡。国际联盟时期,常设国际法院十分审慎地行使咨询管辖权,建立起非常完美的逻辑结构,既能通过发表咨询意见阐明国际法、加强与国际联盟的合作、增强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又能避免介入和裁断国际争端、保持司法性质。联合国时期,国际法院和海洋法法庭都基于自己应承担的职责相应地调整了咨询职能的功能定位和咨询管辖范围。但在涉及非联合国会员国或非与UNCLOS目的相符合的国际条约缔约国的国家利益时,国际法庭咨询管辖权与“国家同意原则”之间存在明显冲突。
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国际法庭的咨询程序为其提供了国际争端解决的新思路,涉及国家间争端时,渴望启动咨询程序的国家一般是发展中国家,它们在与大国发生争端时,以政治手段解决纠纷不占优势,诉诸国际法庭的诉讼程序又需要获得当事国同意,随着管辖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国际法庭的咨询程序确实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寻求法律支持的新渠道。咨询意见本身不具有拘束力,但它在解释国际法规则、影响国家实践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加上申请机关以此为参考通过的相关决议,在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利、构建反映其需求的国际法律新秩序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对于国际争端解决体系而言,如果不断扩大咨询主体和咨询事项的范围,取消“国家同意原则”的限制,国际法主体可以通过申请咨询意见对未来的情形作出预判并指导自身行动,预防和辅助解决国际争端。但是,国际法庭的咨询程序也很可能沦为诉讼程序的替代品,被一些国家滥用,间接影响国际争端的解决进程,反而不利于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
对于国际法理论体系的发展而言,国际法庭扩大咨询管辖权的范围,可以实时跟进国际社会面临的最新法律问题并提出法律建议,解释和发展国际法规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法律规则滞后性的弊端,同时,咨询意见和司法判决一样,都是通过公开途径发表。不同国际法庭的不同程序之间可以互相参照引用,有利于国际法理论的整体向前发展。
综合来看,国际法庭咨询管辖权扩张对国际法庭自身和国际社会都能带来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国际法庭不宜过于激进地扩张咨询管辖权,而是应当在与国际法主体的互动当中,逐渐寻求一条平衡主权国家和国际法庭双方利益的通道。
(二)中国应对国际法庭咨询管辖权扩张倾向的策略
作为现行国际法体系的后来者,中国对国际司法向来持尊重的态度。但受历史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中国对国际司法程序整体上参与程度不高、运用能力较弱。〔42〕在世界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西方主导的国际体制存在诸多不合理性、国际新秩序尚未形成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作为国际社会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应当有适应新情况的大国战略。〔43〕在这个国际法规则边界模糊且呈碎片化的时代,国际法庭的咨询意见具有很强的指引作用。正确运用国际法庭的咨询管辖权,有利于弥补中国利用国际司法途径解决争端能力不足的短板,加强中国在构建和发展国际法律秩序中的话语权。
2010年“科索沃独立咨询意见案”〔44〕是新中国首次参与国际法院咨询程序的案件,这一历史性开端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然而,尽管本案的最终结果与中国的国家利益息息相关,但与英美国家的书面意见相比,中国提交的书面意见篇幅较短、内容也比较简单,既未涉及管辖权问题,也未提交书面评论,更重要的是,我国的意见似乎没有对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造成影响。〔45〕2010年7月22日,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认为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不违反国际法。随后,在美国的积极鼓励下,科索沃得到许多国家的承认。这一咨询意见是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的强烈打击,无疑为全世界的分离主义分子打了一剂强心针,成为他们随时得以援引的行动指南。2019年“查戈斯群岛从毛里求斯分离的法律后果案”中,中国再次参与咨询程序并提交了14页的书面意见,希望国际法院考虑本案的“双边争端性”,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重点考虑“国家同意原则”的限制,拒绝发表咨询意见,这一观点并未得到采纳。国际法院的上述两份咨询意见对于中国解决“台独”等问题都极为不利,体现出国际法院咨询管辖权强势扩张的趋势。2015年国际海洋法法庭通过第21号案确立起法庭全庭的咨询管辖权,否定了中国书面意见中法庭全庭的咨询职能没有法律依据的观点,扩大了咨询主体的申请范围,不利于我国处理、解决与周边国家的海洋权益纠纷。
除此之外,国际社会上已经出现了擅长绕过“国家同意原则”,将国家间主权争端包装成国际法庭具有咨询管辖权的事项,提请国际法庭发表咨询意见的做法和专业人士。〔46〕从目前的实践情况来看,国际法庭往往迫于各方压力与扩张管辖权的动力,寻求折中的做法,忽视咨询事项背后国际争端的本质核心。长此以往,很可能引发国际社会对国际法庭的信任危机。
中国领土与14个周边国家接壤,有9个海上邻国,在这21个国家中,〔47〕大部分都与中国存在或曾经发生过争端,在9个海上邻国中,除新加坡外,其余8个海上邻国都与中国存在海洋争端,且涉及的争端类型复杂、数目繁多,既包括领土主权争端、海洋划界争端,又包括资源开发和利用争端、管辖权争端。因此,即使中国不主动利用国际法庭的咨询程序处理争端,也不能保证其他国家不会将双边争端包装后,利用咨询程序裁断国际争端,引导对中国极为不利的国际法发展走势和国际舆论导向。有鉴于此,中国必须改变以往规避国际法庭解决争端的思路,深入研究国际法庭的咨询管辖权,坚定“国家同意原则”作为解决国际争端基本原则的地位及对咨询管辖权的限制性作用,建立起全方位、分层次的国际争端解决战略。
第一,做好法理和人才储备,向国际法庭输送中国籍法官和工作人员。自国际法院成立以来,共产生过108名法官,其中中国法官5名;〔48〕海洋法法庭投入运作至今,共有3名中国籍法官。〔49〕尽管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籍法官数量仍旧偏少,但他们的卓越表现表明中国有能力也有条件充分研究和参与国际司法机构的运作。中国法官可以通过参与案件审理、发表独立意见等方式,表达符合中国利益的态度和观点,维护咨询制度的客观公正性。〔50〕
第二,中国必须充分利用联合国会员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UNCLOS缔约国等身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和更加专业的做法影响和参与国际法庭的咨询程序。这首先需要中国更多地参与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的议事和表决程序,勇于在安理会行使“一票否决权”,坚定“国家同意原则”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基本原则,严防境外势力将有损中国国家利益或涉及中国国内事务的事项提交国际法庭申请咨询意见,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其次,中国对国际法庭的咨询程序依旧不太熟悉,有必要借鉴与学习英美国家参与咨询程序的策略方法和起草书面意见的技巧,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法庭的咨询程序,通过书面和口头环节表达看法和观点。
人民币升值、绿色壁垒、反倾销以及福利取消交易的一系列交易环境变化,变化的最大值在国际交易和企业利润空间收到挤压类,在以往低税收控股公司以及交货方式的价格将会被税务机关关注。甚至是严厉稽查,根据新的税收,在早期的情况下,这是一个问题,对这两家公司的股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实质是中资的外资企业(俗称假合资企业)在企业中占比较高,这类企业实际上增加了运营成本。
第三,密切关注各个国际法庭规约、规则修改或解释的动向,积极表达自身观点和态度。通过前文分析可得,国际法院咨询管辖权的法律依据和行使程序都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细致的规定,短期内《国际法院规约》和《国际法院规则》修改的可能性不大,但国际法院在处理具体咨询案件时,对相关条款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尽管1950年“对保、匈、罗和约的解释案”突破了“国家同意原则”的限制,但饱受国际法学者的批评和主权国家的抗议。此后,尽管国际法院在咨询意见中依旧坚称“国家同意原则”不应适用于咨询管辖权,却不得不承认这属于自由裁量因素,对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的恰当性产生限制作用,而且也不曾发生第二个类似1950年“对保、匈、罗和约的解释案”的咨询案件。由此可见,国际社会的态度对国际法庭咨询管辖权的扩张能够产生一定影响。
第四,鼓励中国国际法学者在国内外不同场合发出符合中国立场、维护国家利益的声音,引导国际法学界的理论导向。国际法庭的法官都是在国际法学界占有一席之地并能对国际法规则的阐明和发展产生一定影响的法学家,但是由于受到其本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和其已经接受的法学思想的影响,他们有时会对国际法规则作出不利于中国利益的解释。中国的国际法学者已经意识到参与发展国际法理论的重要性并已经开始行动,不断深入研究国际法基础理论,从符合中国利益的角度解读国际法规则,建立起维护中国利益的国际法体系,影响和引领国际社会对国际法理念和规则的理解。
1.“东卡雷利亚原则”的确立
注释:
〔1〕〔40〕Request for an Advisory Opinion submitted by the Sub-Regional Fisheries Commission,Advisory Opinion ,2 April 2015,ITLOS Reports 2015,pp.4,26.
〔2〕Written State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pp.101-116.https://www.icj-cij.org/files/case-related/169/169-20180215-WRI-01-00-EN.pdf.
〔3〕〔44〕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Unilateral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in Respect of Kosovo,Advisory Opinion,I.C.J.Reports 2010,pp.403,403.
我想,阅读对于人的一生,都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我对那些大力提倡孩子的课外阅读并为此做出不懈努力的校长和老师们以及无数阅读推广人,充满了深深的敬意!因为有他们,现在的学校和家长们才越来越重视阅读,现在的孩子们才能接触到更多的优秀作品,从书籍中汲取成长养分,在阅读中变得更加自信和快乐!
〔4〕Legal Consequence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Wall in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y,Advisory Opinion,I.C.J.Reports 2004,p.136.
〔5〕刘芳雄:《国际法院咨询管辖权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页。
〔6〕UNCLOS第十五部分第二节(第286-299条)详细构建了一整套能够作出有拘束力裁判的强制程序。
〔7〕IUU捕鱼活动是指非法的(illegal)、未报告的(unreported)和非管制的(unregulated)捕鱼活动。
〔8〕该公约第33条规定SRFC部长会议可授权常任秘书(Permanent Secretary)就法律问题向海洋法法庭全庭申请咨询意见的权利,并且依据该条通过一项决议确认该授权。
农民合作社组织文化形成路径研究——以新疆沙湾县双泉农业专业合作社为例………………………………………胡宜挺,梁丹霞(1):52
〔9〕Yoshifumi Tanaka,“Reflections on the Advisory Jurisdiction of ITLOS as a Full Court:The ITLOS Advisory Opinion of 2015”, Law &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 Tribunals ,2015,Vol.14,p.339.
〔10〕《联合国宪章》第96条第1款规定:“大会或安全理事会对于任何法律问题得请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
〔11〕参见UNCLOS第187条“海底争端分庭的管辖权”。
〔12〕Western Sahara,Advisory Opinion,I.C.J.Reports 1975,para.23.
〔13〕Tom Ruys,Anemoon Soete,“‘Creeping’ Advisory Jurisdiction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The case of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6,Vol.29,p.164.
如前文所述,海底争端分庭咨询管辖权的法律依据在UNCLOS中有明确规定,海底争端分庭应管理局大会或理事会的申请发表咨询意见是一项义务,不存在自由裁量的空间,因此不涉及“国家同意原则”的适用问题。与之相反,在第21号案中,海洋法法庭全庭咨询管辖权的确立和行使都与“国家同意原则”产生了冲突。
〔15〕Legality of the Use by a State of Nuclear Weapons in Armed Conflict,Advisory Opinion,I.C.J.Reports 1996,p.66.
1950年“对保、匈、罗和约的解释案”中,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当时均非联合国会员国,而且都明确表达了拒绝国际法院对本案行使咨询管辖权的主张,它们的主要观点是国际法院对本案发表咨询意见将违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对于国家之间存在冲突、尚未解决的法律问题,未经当事国同意,不得适用司法程序。对此,国际法院认为:首先,这一主张是混淆诉讼管辖权和咨询管辖权的表现,“国家同意原则”只适用于前者。在咨询程序中,即使咨询事项涉及国家间未决的法律问题冲突,无论相关国家是否是联合国的会员国,都不能阻止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其次,本案与“东卡雷利亚案”情况不同,主要区别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东卡雷利亚案”中,申请咨询的问题是两国之间实际存在的冲突的核心问题,发表咨询意见实际上会产生裁断争端的效果,而本案申请咨询的问题是和平条约规定的程序适用问题,并未触及国家间争端的核心问题;二是苏联的拒绝参与导致至关重要的事实无法查明,因而无法审理。再次,国际法院重申,作为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发表咨询意见是其积极参与联合国行动的表现,目的是为申请机关提供法律建议,不针对争端当事国,也不具有拘束力,不影响当事国之间争端的解决进程与结果。在本案中,国际法院使用了“义务”(duty)一词来表达自己发表咨询意见的行为,表明其倾向于使得咨询申请有效的态度。〔33〕
〔17〕〔英〕劳特派特修订:《奥本海国际法》(上卷),第一分册,石蒂、陈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1年,第12、18页;Andrew T.Guzman,“Against Consent”, 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52,2012,p.747。
〔18〕See Anthony Aust,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2nd e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3;参见翟玉成:《论国际法上主权问题的发展趋势》,《法学评论》1997年第3期。在“荷花号”案判决中,常设国际法院指出:“国家同意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See S.S.Lotus (Fr.v.Turk.),1927 P.C.I.J. (ser.A) No.10 (Sept.7),para.309。
〔19〕苏晓宏:《简论国际司法的运行原则》,《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See John A.Perkins,“The Changing 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From State Consent to State Responsibility”, Bosto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 Vol.15,1997,p.442。
〔20〕〔22〕何志鹏、鲍墨尔根:《主权与职权之争——国际法院咨询管辖权与当事国同意原则关系的争议与解决》,《北方法学》2018年第6期。
〔21〕〔38〕尤瓦·沙尼:《国际法院与法庭的竞合管辖权》,韩秀丽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年,第10-13、353页。
〔23〕〔24〕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Series B:Collection of Advisory Opinions,No.5,pp.27,27-28.
〔25〕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Series B:Collection of Advisory Opinions,B12,p.33.
〔26〕Minutes of the Conference of States Signatories of the Protocol of Signature of the Statute of the 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p.79.
〔27〕例如,1923年突尼斯和摩洛哥国籍法令问题案,1923年东卡雷利亚问题案,1923年在波兰的德国移民问题案,1923年波兰国籍的取得问题案,1923年亚沃齐那问题案,1931年在但泽港的波兰军舰问题案等。
〔28〕Legal Consequences of the Separation of the Chagos Archipelago from Mauritius in 1965,Advisory Opinion,25 February 2015,General List No.169,p.23;Legal Consequences for States of the Continued Presence of South Africa in Namibia (South West Africa) Notwithstanding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276 (1970),Advisory Opinion,I.C.J.Reports 1971,pp.24,25.
〔29〕〔35〕〔36〕Legal Consequences of the Separation of the Chagos Archipelago from Mauritius in 1965,Advisory Opinion,25 February 2015,General List No.169,pp.17,18;7;43,44.
〔30〕Western Sahara,Advisory Opinion,I.C.J.Reports 1975,p.25;Legal Consequences of the Separation of the Chagos Archipelago from Mauritius in 1965,Advisory Opinion,25 February 2015,General List No.169,pp.22,23;Legal Consequences for States of the Continued Presence of South Africa in Namibia (South West Africa) Notwithstanding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276 (1970),Advisory Opinion,I.C.J.Reports 1971,pp.24,25.
〔31〕Legal Consequences for States of the Continued Presence of South Africa in Namibia (South West Africa) Notwithstanding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276 (1970),Advisory Opinion,I.C.J.Reports 1971,pp.23,24;Western Sahara,Advisory Opinion,I.C.J.Reports 1975,p.24.
〔32〕本节规定:“除经当事各方商定援用另一解决方式外,本公约的解释或适用上所发生的一切争议应提交国际法院。如联合国与一个会员国间发生争议,应依照宪章第九十六条及法院规约第六十五条请法院就所牵涉的任何法律问题发表咨询意见。当事各方应接受法院所发表的咨询意见为具有决定性效力。”
〔33〕Interpretation of Peace Treaties with Bulgaria,Hungary and Romania(First Phase),Advisory Opinion,I.C.J.Reports 1950,pp.71,72.
〔34〕Western Sahara,Advisory Opinion,I.C.J.Reports 1975,pp.28,29.
〔37〕Application for Review of Judgement No.273 of the United Nations Administrative Tribunal,Advisory Opinion,I.C.J.Reports 1982,Dissenting Opinion by Judge Morozov,p.439.
〔39〕参见http://www.un.org/en/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RES/71/292。
〔41〕〔德〕马克斯·普朗克比较公法及国际法研究所主编:《国际公法百科全书——争端的解决》,陈致中、李斐南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92页。
〔42〕苏晓宏:《变动世界中的国际司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0-143页。
〔43〕王逸舟:《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研究的若干问题》,《社会科学论坛》2002年第8期。
〔45〕余民才:《“科索沃独立咨询意见案”评析》,《法商研究》2010年第6期。
〔46〕叶强:《国际法院就“查戈斯案”发表咨询意见》,《世界知识》2019年第8期。
〔47〕越南和朝鲜既是中国的陆地邻国,又是海上邻国。
〔48〕徐谟(1946—1956):首位出任国际法院法官的中国人,顾维钧(1957—1967):1964—1967年曾担任国际法院副院长,倪征燠(1985—1994):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首位国际法院法官,史久镛(1994—2010):2003—2006年担任国际法院院长,薛捍勤(2010至今):2018年当选为国际法院副院长。
〔49〕赵理海(1996—2000)、许光建(2001—2007)、高之国(2008至今)。
〔50〕王淑敏、吴昊南:《国际法院关于“查戈斯群岛从毛里求斯分裂案”的咨询管辖权研究》,《法律适用》2018年第17期。
作者简介: 罗国强,武汉大学珞珈特聘教授,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于敏娜,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博士生。
〔*〕本文受2016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重大项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国际法理论创新”(16JJD820011)的资助。
DOI: 10.3969/j.issn.1002-1698.2019.10.015
〔责任编辑:邹秋淑〕
标签:常设国际法院论文; 国际法院论文; 国际海洋法法庭论文; 咨询管辖权论文; 国家同意原则论文;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