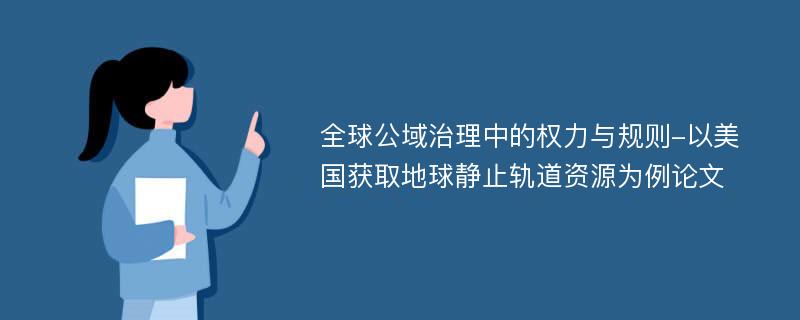
全球公域治理中的权力与规则
——以美国获取地球静止轨道资源为例
沈 鹏1
(1.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720)
摘要: 国家经常通过权力塑造全球公域治理的议程和规则。地球静止轨道资源的分配是全球公域治理中的一个案例。美国作为空间活动大国,通过自身的技术、知识和制度优势在国际电信联盟就如何分配地球静止轨道资源的安排方面占得了先机。20世纪70年代,当发展中国家开始积极要求公平利用地球静止轨道资源后,美国力求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反对改变现状。近几十年来,美国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这种争端一直持续地发生在国际电信联盟的历次会议上。未来如果没有根本的技术革命,这种轨道资源之争还将持续下去。
关键词: 全球公域;地球静止轨道;权力;美国外交
中图分类号: D83/8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049(2019)07-0015-12
收稿日期: 2018-12-25;修订日期:2019-04-01。
基金项目: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国内政治分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印太战略视阈下南海问题新态势与我国应对策略研究”(18AGJ0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DOI: 10.14015/j.cnki.1004-8049.2019.07.002
沈鹏:“全球公域治理中的权力与规则——以美国获取地球静止轨道资源为例”,《太平洋学报》,2019年第7期,第15-26页。
SHEN Peng, “The Power and Rules in 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Commons: In the Case of US’s Acquisition of Geostationary Orbit Resources”, Pacific Journal , Vol. 27, No. 7, 2019, pp.15-26.
作者简介: 沈鹏(1977—),男,山东烟台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美国政治外交、全球公域资源问题。
* 作者感谢《太平洋学报》和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公海、外层空间、极地等全球公域作为一个相对较新的战略领域,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① 关于这个概念的界定并不非常明确。国内外的一些机构以及学者给出了相近但又不完全一致的定义。例如,联合国的一些机构,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把“全球公域”界定为“处于国家管辖之外的资源或区域”;“国际法认为公海、大气层、外层空间及南极洲属于‘全球公域’”。参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网站:http://www.unep.org/delc/GlobalCommons/tabid/54404/;联合国统计司(UNSD)网站:http://unstats.un.org/unsd/environmentgl/gesform.asp?getitem=573,访问时间:2018年12月24日。 在近几十年间,全球公域治理问题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取得了长足进展,国际社会建立了一系列对公海、极地以及太空的治理体系,但目前全球公域治理方面仍存在很多问题。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以及资源、环境等全球性问题的凸显,全球公域内的资源开发与利用、环境保护与治理以及秩序与安全问题引发了多个学科的关注。资源问题是全球公域治理的主要问题之一,其核心议题是如何恰当分配和管理这些资源的问题。不恰当地开发、利用公域资源可能会导致“拥挤效应”和“资源枯竭”等多重问题。② 韩雪晴:“全球公域治理: 全球治理的范式革命?”《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4期,第2-3页。 对此,许多理论模型被提出来用以考察公共事务治理中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与困境问题。[注] 参见Paul. C. Stern, “Design Principles for Global Commons: Natural Resources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Commons , Vol. 5, No. 2, 2011, p. 214;[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著,余逊达、 陈旭东译:《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中文版译序。而在各种解决方案中,将全球公域资源进行分割的“圈占”方式是一种治理方式,实力强者通常能获得更多利益。另一种解决办法是由利益相关方组成一个组织来共同管理资源,即使在这种治理方式中,仍然存在着权力不均衡的情况。参与治理的国家实力或贫富的不同,导致权力的不均衡,会影响治理的效果。全球公域目前在概念、划界和权责等方面仍存在相当多模糊的情况,权力政治渗透到全球公域治理的规则安排中,为实现公平、合理的治理带来持续的挑战。全球公域治理中的权力通常是通过制度性权力来体现。国家通过在全球公域治理中谋取制度性权力,对国际组织的规则设定形成深远的影响。方式通常可以是掌握治理活动中议程设置的能力,或将个体的偏好嵌入规则制定之中引导集体偏好的形成,从而使全球公域的治理方向有利于自己。治理制度和规则的创设和运行本质上是一个成本核算、相互博弈的复杂过程。[注] 任琳:“全球公域:不均衡全球化世界中的治理与权力”,《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6期,第119页。
括号内为T值,调整后的R2为0.2240,F值为7.35,并在5%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由结果可知资本产出弹性α=0.6454,劳动产出弹性为0.3546。因为二阶差分后,弱化了常数项,所以常数项并不显著。将α值代入(3)式,即可得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结果见表2。
美国作为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通过权力塑造全球公域治理的议程和规则,阻碍治理公平的现象是存在的。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全球治理,通过对治理规则的修正,可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不公平的情况。美国在全球公域治理的领域处于强势地位,并力图取得有利于其国家利益的制度安排,例如公海治理、远洋渔业治理、国际海底资源治理、南极治理、外层空间治理等方面都是如此。要改变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过度掌控制度性权力的现状,需要推动国际组织从更专业的角度监督治理、防止权力阻碍善治,推动全球公益的实现。
本文拟从全球公域治理中一个较少关注却又非常重要的案例——即美国获取地球静止轨道的位置资源——出发,来较为细致地观察权力影响全球公域治理的过程和现状。美国作为空间技术最发达的国家,在地球静止轨道资源的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和政治较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长期以来,美国政府把外空相关活动的政策和法律制定放在重要位置。美国等发达国家强势占用地球卫星轨道,尤其是地球静止轨道的行为早已引起发展中国家的关注。20世纪70年代的《波哥大宣言》体现了争夺地球静止轨道资源的激化。长期以来,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关于卫星轨道资源分配的规则制定体现了这一领域的国际博弈。下文将着重梳理美国如何为确保地球静止轨道资源的充足供应,而在国际组织的制度设计和规则安排中与其他国家进行博弈,从而更好地理解权力在全球公域治理中的作用。
一、 美国使用地球静止轨道资源的背景
通信卫星的出现和广泛应用已取得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作为承载卫星活动的地球卫星轨道,也是一种信息和通讯资源。地球卫星轨道以及与它相联系的无线电频率具有明确的经济价值,但不会被生产或破坏。经过一段时间,它可以得到更新,但在某一特定时刻和位置,可用的轨道位置和频率是有限的。[注] Marvin S. Soroos, “The Commons in the Sky: The Radio Spectrum and Geosynchronous Orbit as Issues in Global Poli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 Vol. 36, No. 3, 1982, p. 666.目前还没有办法可以让人们无限地共享这种资源。这种特殊且有限的资源是外层空间商业化程度最高的一类资源,也是人类目前利用最广泛的外层空间资源。但当今地球卫星轨道上的卫星,大部分是由发达国家发射并放置的。对于没有强大太空活动能力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只能任由技术先进的国家使用这种有限的资源。
1958年12月13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1348(XIII)号决议,确认外层空间是人类共同利益所在,“人类对于外空祸福与共,而共同之目的则在使外空仅用于和平之途”,强调有必要在外层空间活动方面开展国际合作,并且必须完全为和平目的使用外层空间,规定成立 “外空和平使用问题专设委员会”。联合国大会于1961年通过题为《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中的国际合作》的决议,于1963年通过《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的法律原则宣言》。虽然这些联合国决议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到1963年后,一系列有关使用外层空间的总体原则已经在国际社会中达成共识。[注] E. R. C. van Bogaert, Aspects of Space Law , Kluwer 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 1986, pp. 17-18. 本段提到的联合国决议的具体内容皆可参见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办公室(即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秘书处)网站:http://www.unoosa.org/oosa/zh/SpaceLaw/gares/index.html,访问时间:2018年12月24日。1966年5月7日,美国总统约翰逊宣布“对于保证月球和其他天体开发仅用于和平目的的国际协议有一个紧迫的需求”,并公布了美国的基本原则:“月球和其他天体应当被自由地用于所有国家的探索与使用。不允许任何国家有主权宣称;应当有进行科学研究的自由,所有国家应当在有关天体的科学活动中合作;应进行避免有害污染的研究;一个国家的宇航员应当给予另一国家的宇航员以必要的帮助;不允许任何国家在天体上放置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应当禁止武器试验和军事动员。”[注] 张杨:《冷战与美国的外层空间政策:1945—1969》,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第143页。
1.1 早期的美国空间政策与产业发展
20世纪50—60年代,美国的空间技术和空间法还处于草创阶段。这一时期,国际社会对地球静止轨道这种特殊的自然资源的竞争尚处于酝酿阶段,美国早于其他国家意识到这类资源的重要性。
无论在空间技术和国内空间法律的制定方面,美国都发展较早,并且还大力发展与卫星发射相关的经济和商业活动。美国于1958年发射世界上第一颗实验通信卫星。由于当时处在美苏冷战背景下,争夺外层空间军事优势是美国和苏联这两个主要外空竞争对手首先考虑的问题。[注] 1955年5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外层空间的第一个政策文件,即NSC5520号文件。外层空间政策被认为是一个涉及国家安全层面的重要领域。参见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 1955-1957, Vol. XI, pp. 723-732; [美]威廉·J·德沙主编,李恩忠等译:《美苏空间争霸与美国利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美国在进入外层空间初期未特别关注地球卫星轨道资源问题,[注] 在空间活动起步初期,美苏两国也担心对方通过“先占原则”提出对天体的主权问题,但由于双方的互相制约,苏美达成共识,不把在地球上的争夺带到外层空间去,规定了任何国家都不能将外层空间和天体据为己有。因此,在外层空间基本没有发生激烈的主权争夺。可参见:Glenn H. Reynolds and Robert P. Merges, eds., Outer Space :Problems of Law and Policy , 2nd ed., Westview Press, 1997, pp. 69-70.但很快就开始制定关于卫星发射和航空航天方面的法律。美国国会于1958年制定了《国家宇航法》,明确了美国民用空间发展计划,并依此成立了国家宇航局(NASA)。该法的目的在于“促进人类对空气空间以及外层空间的了解,促进宇航运载工具的发展,制订长期计划研究外空活动可能带来的利益和问题,确保美国在航天科技方面的领先地位,提高国际合作水平”。[注] The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ct , Public Law 85-568 (As Amended), http://www.nasa.gov/offices/ogc/about/space_act1.html,访问时间:2018年12月24日。随着空间科技的快速发展,美国于1962年颁布了《卫星通信法》。
亲子阅读满足了孩子们听故事的需求,诱发了他们的求知欲。孩子们在听中感受形象,在听中分辨善恶,在听中思考,在听中收获,在听中增进了他们对语言文字的兴趣,进而产生了对书籍的热爱。亲子阅读极大地提高了孩子们的阅读能力。在家长与孩子的互动中,孩子们的语言发展了,智力开发了,在阅读、积累、想象、表达的过程中,他们的创造思维能力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读书策略的渗透使孩子们逐步掌握了阅读的“金钥匙”,会读才能乐读,乐读才能真正产生书籍的影响。
地理位于赤道上的国家(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正好处于地球静止轨道的下方。自从人造卫星大量出现在它们上方之后,这些国家显得相当焦虑。因此,它们考虑采取行动表达自己的关切,对“先登先占”规则发起根本性地挑战。1975年,哥伦比亚在第30届联合国大会上首次对位于其领土上方的那一段地球静止轨道提出主权要求,并认为地球静止轨道不属于《外层空间条约》规定的外层空间的一部分。1976年,厄瓜多尔和巴拿马两国也采取了相同的立场。[注] Stephen Gorove, “The Geostationary Orbit: Issues of Law and Policy”,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 Vol. 73, No. 3, 1979, p. 450.1976年11月,巴西、厄瓜多尔、哥伦比亚、扎伊尔、刚果、乌干达、印尼和肯尼亚八个赤道国家在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召开会议,统一了它们对地球静止轨道法律地位的立场。八国共同发表了《波哥大宣言》,声明地球静止轨道是有关“赤道国家在其上行使其国家主权的领土的组成部分”、“是在赤道国家主权之下的”;在赤道国家上空的静止轨道上放置卫星等装置,“应得到有关国家的事先和明确的认可”,其“操作应受该国国内法支配”,已在该轨道内运行的物体, 并不因此取得合法地位;赤道国家承认公海上空的静止轨道属于“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允许各国自由运行、使用和开发;[注] 王铁崖、田如萱编:《国际法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1年版,第566-570页。 宣言明确提出了地球静止轨道的法律地位问题,并将整个轨道分为公海之上和领土之上两部分。由此,围绕着地球静止轨道归属权的争端开始变得激烈。
此后越来越多与卫星有关的经济活动在美国逐步发展起来。主要包括卫星的制造、销售、发射和租用,以及卫星通信、遥感等方面服务。美国的卫星服务虽然在起步阶段是国家行为,但是随着外层空间活动的发展,卫星服务活动主要由商业组织来承担,其中波音公司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业卫星制造商。[注] 1996年,波音收购了罗克韦尔公司的防务及空间系统部,1997年又兼并了麦道公司,2000年1月波音公司与通用汽车公司达成协议,出资3.75亿美元收购其下属休斯电子公司的航天和通信业务部。 20世纪80年代,空间领域开始出现商业渗透,90年代进入空间技术应用的时代。美国于1984年通过《商业空间发射法》,鼓励、促进和提升私营商业空间发射活动;1998年通过《商业空间法》,表明美国在商业领域发展外空事业的意愿。这些法律所促进的商业行为很多都与卫星轨道的利用有关。到2006年2月,美国共发射了332颗地球同步卫星,占世界总量的近一半。[注] 周丽瑛:《外层空间活动商业化的法律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第146-147页。
1.2 早期国际空间法的发展与美国的态度
在美国等国的阻挠下,多数赤道国家立场有所软化,不再坚持对地球静止轨道的主权要求,而提出对其上空的那一段静止轨道享有某些优先权。[注] Stephen Gorove, Developments in Space Law :Issues and Policies ,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91, pp. 41-46.此后,在历届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的最后文件中,哥伦比亚等赤道国家仍提出与《波哥大宣言》中的立场一致的保留或声明,美国等国家则针锋相对地做出反保留或反声明。虽然《波哥大宣言》的法律效果并未如愿,但却取得了一定的政治效果,引起了各国对静止轨道的关注。太空法学家们设立了一个委员会, 再次评估领空和太空主权问题。《波哥大宣言》的出现说明,外层空间技术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世界各国在争夺外层空间技术、军事优势的同时开始逐渐意识到外层空间资源问题的重要性。无论这些资源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只要它们不是取之不尽的,就会引起利益分配问题。但美国通过其在国际电信联盟中的权势并联合利益相似的国家,确保了“先登先占”规则没有受到根本改变。美国的权力当然是以其对核心技术能力的掌握为前提的,只有较少的其他国家及地区行为体能掌握从事太空活动的技术手段。这导致规则的设立必然有利于美国等国家,很难为全球各国公共占有,平等使用。各国主权的形式平等面对着权力地位的不平等困境。后起之国只能依靠自助机制争取自己的权利,但这与国家的实力和意志关系很大,通常美国等强国比弱国更易捍卫它们的主张。
在多种地球卫星轨道中,地球静止轨道最具经济和实用价值。[注] 地球静止轨道(geostationary orbit,GEO),又被称作“地球静止同步轨道”、“地球静止卫星轨道”、“地球同步转移轨道”。地球静止轨道其实是一种特殊的同步轨道。关于地球静止轨道与地球同步轨道的区别,可参见慕亚平:“地球静止轨道法律地位初探”,《西北政法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第49页。 它是位于赤道平面上空距离地面约35 786公里[注] 对此也有不同的说法,但相差不大。 的一条与赤道平行的圆形轨道。该轨道上的卫星运行的方向和角速度同地球自转的方向和角速度完全相同。因此,从地面上看,这个轨道上的卫星似乎处于静止状态。[注] Stephen Gorove, “The Geostationary Orbit: Issues of Law and Policy”,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 Vol. 73, No. 3, 1979, p. 445.从理论上说,若以等距离方式,在该轨道上放置三颗卫星,其信号就可以覆盖全球。地球静止轨道的这些突出特点,使得它对空间通信、直接广播电视、卫星导航、气象观测等领域具有非常重要的实用价值。[注] 贺其治、黄惠康主编:《外层空间法》,青岛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 地球静止轨道的周长约为265 000公里,这条轨道上能够放置的卫星总数取决于卫星的体积、轨道的稳定程度以及抗干扰能力等因素,但数量非常有限。这条轨道在1963年由美国最先发现并开始利用,到20世纪80年代,该轨道上的卫星已超过150枚。近年来,许多国家纷纷自行或联合制造卫星,抢占地球静止轨道资源,各国卫星之间出现干扰需要协调的情况时有发生。技术成熟的C和Ku频段卫星数量已达到饱和,而开发新频段的卫星又受到技术能力的限制,因此各国都在寻求规则方面的有利因素。[注] 张虹:“WRC-12 上的卫星资源争夺战”,《中国无线电》,2012年第2期,第23页。 到2013年底,地球静止轨道上已有447颗卫星(其中美国拥有177颗),平均不到1度间隔就有一颗卫星。
到1966年,由于美苏两国在外层空间的探索都已经取得相当的成果,因此双方都同意签订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条约规范外层空间活动。在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的主持下,《外层空间条约》的起草工作仅用了6个月的时间。1967年的《外层空间条约》是对人类在外层空间活动进行法律规范的第一个条约,各缔约国对一些总体原则达成一致。但具体到开发外层空间资源,包括地球卫星轨道资源问题上,条约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控制展示模式通过前端jQuery调用Silverlight内的方法实现,集成第三方网页方面通过服务器上定制过滤规律,移除X-Frame-Options HTTP响应头,让部分无法嵌入网页展示的网站可以嵌入到展示平台中。平台通过PDF插件将文件转化为保存在服务器,通过Viewjs插件实现文件的在线预览、下载。采用Highcharts控件,通过调用Highcharts API,结合自定义的json配置文件,支持直线图、曲线图等数据可视化展示,同时可集成在同一个图形中形成综合图。
《外层空间条约》确认的一般原则包括:外空探测和利用为全人类之事务,外空不因主权行为的行使而为国家占有,宇航员被认为是人类的使者,外空探测和利用应为所有国家的利益而为之,不管各国的经济与科技发展水平如何,各国在空间活动中加强合作,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注] 该原则制定后对其内容的理解就出现了两种相反的解释,由此产生了许多理论上的分歧。其中的焦点之一就是《外层空间条约》的“不得据为己有”原则是否允许私人对外层空间及其资源主张私人财产权?正面解释观点认为,无论国家或私人采取了何种方法,以何种名义,通过何种途径,凡是从法律上限制或绝对地排除其他主体自由使用外空资源的做法,都是该原则所禁止的。反面解释观点认为,《外层空间条约》仅禁止国家主张主权和权利,并没有明确禁止私人主张权利,因而私人财产权是允许的。参见:Glenn H. Reynolds and Robert P. Merges, eds., Outer Space :Problems of Law and Policy , 2nd ed., Westview Press, 1997, pp. 77-82。《外层空间条约》第一条规定了“外空自由”的原则,即对于外层空间资源的使用、开发和利用,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商业用途,无论是国家还是私人实体的外层空间活动都是被鼓励的和被允许的。[注] 参见《外层空间条约》第一条。在条约谈判时,苏联代表认为外层空间活动仅能由国家专属从事。对此,美国认为私人企业从事外层空间活动的权利已经在1962年美国的《卫星通信法》中确立了,美国第一个研究空间开发应用的商业公司美国通讯卫星公司(COMSAT)也于1962年就已成立。作为妥协折衷,美国提议、并且苏联接受的条款是《外层空间条约》第六条:“国家应当对其本国所从事的空间活动承担国际责任,无论这些活动是由政府或非政府机构从事的”。参见Stephen Gorove, Developments in Space Law :Issues and Policies ,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91, p. 7;Nathan C. Goldman, Space Policy :An Introduction ,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6;[荷兰]盖伊斯贝尔塔·雷伊南著,谭世球译:《外层空间的利用与国际法》,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94页。 《外层空间条约》第二条规定了外层空间“不得据为己有”原则,即“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不得由国家通过提出主权主张,通过使用或占领,或以其他任何的方法,据为己有”。[注] 参见《外层空间条约》第二条。 也就是说,《外层空间条约》禁止“据为己有”但鼓励“外空自由”,只是不能将“自由使用”等同于“占有”。
《外层空间条约》只是规定了指导外层空间开发利用的基本原则,而且采用了比较模糊的语言。正因如此,美国国会于1967年顺利地批准了《外层空间条约》。[注]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 1964-1968, Volume XI, pp. 430-431.从谋取权力的角度看,美国在这一时期的行为其实为自己在外空公域治理中的优势地位打下了基础。它一方面努力发展硬实力,成为卫星和轨道应用强国;另一方面,它领先于国际社会制定相关国内法律,并在国际规则谈判中争取有利于自己的规则,为其外空实力的进一步发展争取空间。
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各国对地球静止轨道资源的争夺逐渐升级。
将经优化配方制备的甲维盐微乳剂置于(54±2)℃恒温箱中,静置贮存14 d后取出,按实验方法进行外观、pH值、自发分散性、稀释稳定性、透明温度范围、冷贮和热贮稳定性的检测,其结果列于表4.由表4可知,微乳液的热贮稳定性良好,平均分解率为2.81%~4.25%,并且各项物理指标符合标准规定.
比如说在轴对称的教学中,教师可以这么来进行。教学伊始,教师就可以先提问学生让他们说一说对轴对称的看法。在此之后,教师就可以准备三个图形工具,分别为轴对称图形、中心对称、不对称模型。并为学生分组,让他们去辩论三种图形的对称状况,并概括他们的不同。通过学生们的讨论,轴对称这一概念学生可以形成一种较为深入的思考模式,他们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得到有效的激发。
二、轨道资源分配规则的确立与《波哥大宣言》的抗争
自从越来越多的人造卫星被送入地球静止轨道后,世界各国开始围绕着如何分配轨道位置展开争夺。作为分配卫星轨道和无线电频率资源的国际组织,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注] 国际电信联盟只是一个行政和协调机构,并无执法权和有效的控制权。因此,卫星轨道和无线电频率的使用实际上基于国家间的善意和多边利益协调,以避免低效率的使用和有害干扰。尽管如此,国际电信联盟出台的各种规则基本得到了世界各国的严格遵守。参见Marvin S. Soroos, “The Commons in the Sky: The Radio Spectrum and Geosynchronous Orbit as Issues in Global Poli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 Vol. 36, No. 3, 1982, p. 670。对分配规则的设立和修改成为国际博弈的焦点。国际电信联盟于1865年在巴黎成立,1947年成为联合国专门机构,其最初管理领域是电报,当今的工作涵盖整个信息通信领域,包括从数字广播、互联网到移动技术等各个方面。管理卫星轨道资源和国际无线电频率是国际电信联盟无线电通信部门的核心工作。国际电信联盟下设的国际频率登记委员会(International Frequency Registration Board)负责登记成员国所使用的卫星轨道和频率。按照规定,成员国在使用频率以前,有义务在国际频率登记委员会进行登记。为防止有害干扰,各成员国必须在分配给各项空间业务的频率范围内,在双边或多边协调后,向国际频率登记委员会登记所确定的地球静止轨道位置和无线电频率。指导地球静止轨道、非静止轨道以及无线电频率使用的国际条约是国际电信联盟的《无线电规则》。《无线电规则》及其“频率划分表”可定期进行修订。每隔三至四年召开一次的国际电信联盟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orld Radiocommunication Conference, WRC)[注] 在1993年之前,“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被称作“世界无线电行政会议”(World Administrative Radio Conference, WARC)。在1992年于日内瓦举行的一次委员会上,国际电信联盟重组,这个会议随后成为“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 审议并修订《无线电规则》,不断改善已有的无线通信规则程序和频率及轨道分配以适应新技术、新业务的发展。[注] 参见Leslie J. Anderson, Regulation of Transnational Communications , Boardman Co., 1984.每届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都要举行上千场不同议题和范围的会议,技术性很强,各方关注的焦点不仅仅是单纯的技术问题,其实质是国家权益之争。
实践教学是双创教学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只有为高校学生提供与实际环境相匹配的双创实践环境,才能激发学生参与的积极性。让学生们真正了解创业的内涵,这些实践包括公司的运营、团队的协作、产品的销售等。但目前大部分高校对于双创实践教学活动重视不够,只是停留在双创计划书的提交的理论层面和理想化的预测模式。
发展中国家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就地球静止轨道的利益博弈持续发生在国际电信联盟的历次会议上。发展中国家要求公平使用地球静止轨道的声音得到了一些反响,但还远未达到他们的要求。印度在20世纪80年代也向国际电信联盟提出应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最低限度的“轨道产权保障”。[注] 何奇松:“太空安全治理的现状、问题与出路”,《国际展望》,2014年6期,第126页。 从美国的立场上看,其在这个领域的经济收益是非常现实的,各大公司的卫星商业业务都要以卫星轨道资源的占有为基础。一旦不能确保卫星轨道资源的供应,必将直接威胁到它们的经济利益。因此美国在国际电信联盟历次会议上的目标是,努力确保既得的卫星轨道资源,尽量维持分配规则的现状。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地球静止轨道资源的需求和权益维护日益增强,国际电信联盟内部的规则之争日益激烈。
尽管《波哥大宣言》遭到许多国家的反对,但不少国家在反对的同时也提出了比较折中的意见,主张应作出适当安排,以公平地照顾赤道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例如,英国表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让所有的国家都能公平的分享地球静止轨道带来的好处;澳大利亚表示理解赤道国家的担忧,支持研究建立一个管理轨道资源的国际体制;比利时表示赤道国家正在寻求发展经济,因此其要求并不荒唐,应在《外层空间条约》的框架内对有关问题进行仔细研究。[注] 同③, pp. 454-455.
工科新教师作为知识的转化主体、技能的养成主体、能力的发展主体缺失。作为成人的工科新教师,在培训过程中,往往表现为知识的被动接受者、技能的被动受训者、能力锻炼的承受者,缺乏将工程知识转化为课程知识与教学内容、将教学知识内化为教学意识与教学观念的主动性,缺少将自身基本素质与能力转化为教学设计、教学组织与实施、教学管理与评价能力的自觉性。表现为对教育教学知识不主动反思、对教育思想理念无内化吸收、对教学技能的生成不积极强化、对教学能力的提升无行动自觉。
1963年2月14日,美国宇航局发射第一颗试验同步通信卫星“辛康”1号(Syncom-1),但由于卫星上的无线电设备失灵,通信实验没有成功。结果,进入了地球同步轨道的“辛康”1号因无法正常通信而成为太空垃圾。7月26日,美国宇航局发射了“辛康”2号通信卫星。这颗卫星进入了地球静止轨道,但它的轨道平面与地球赤道平面之间的夹角不是零度,所以最终也没有成为静止通信卫星。1964年8月19日,美国发射的“辛康”3号通信卫星成功地进入倾角为零度的地球静止轨道,定点在东经180度的赤道上空,成为第一颗真正的静止通信卫星。[注] 关于“辛康”系列卫星的情况可参见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网站:http://nssdc.gsfc.nasa.gov/nmc/spacecraftDisplay.do?id=1964-047A,访问时间:2018年12月24日。
《波哥大宣言》标志着赤道国家对地球静止轨道提出了主权要求,它们提出的主要理由包括:(1)外层空间的界限不明确,国际社会缺乏支持地球静止轨道包括在外层空间之内的论点,这便不能否认以该轨道作为国家领空的上限的说法。这意味着《外层空间条约》第二条“不得据为己有”原则的规定不适用于地球静止轨道。况且由于各赤道国家均未批准《外层空间条约》,该条约对它们也没有法律约束力。(2)地球静止轨道是有限的自然资源,赤道国家上空的静止轨道属于有关国家的领土,应由有关国家对这一自然资源行使主权。(3)目前地球静止轨道上的卫星对静止轨道的分配和占用, 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先占”,必将导致少数空间大国长期占据轨道局面。赤道国家目前没有空间大国那样的技术和财政手段,但一旦它们有能力发射卫星时,轨道上的位置可能已没有空余。(4)国际电信联盟的分配方案有利于发达国家对地球静止轨道的占用,这种不公平的状况应该改变,使赤道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享有更多利益。[注] 贺其治、黄惠康主编:《外层空间法》,青岛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页。 其他理由还包括:地球静止轨道各部分是完全由地球所发出的引力而造成的,因此不属于外层空间,而是各国领空的一部分。赤道各国在宣言发表之后,还多次在联合国外空委员会和法律小组委员会会议上加以重申和论证。
《波哥大宣言》的出现立即遭到了美国的激烈反对,其他国家如苏联、澳大利亚、英国、法国、比利时等也都提出反对。主要理由是:(1)地球静止轨道是由整个地球的引力造成的, 而非仅是赤道国家的那部分土地引力的结果。并且,人造卫星不能单靠自然力在静止轨道上稳定运行,而必须依靠机械力的帮助,所以任何国家都不能仅根据地理位置就对静止轨道提出主权要求。因此,地球静止轨道不能属于几个赤道国家,而应属于各国共同所有。(2)尽管国际上关于外层空间尚没有一致的法律定义和下限, 但在实践中已形成“凡不低于卫星轨道的最低限的空域便为外层空间”的观念。所以地球静止轨道也应位于外层空间。如果某些国家可以拥有卫星轨道的主权,“不得据为己有”、“外空自由”等公认的外空国际法原则就如同虚设。[注] 慕亚平:“地球静止轨道法律地位初探”,《西北政法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第51-52页。
美国认为《波哥大宣言》违反了外层空间自由原则,在科学和法律上都站不住脚,垄断地球静止轨道的行为将使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受到损失。[注] Stephen Gorove, “The Geostationary Orbit: Issues of Law and Policy”,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 Vol. 73, No. 3, 1979, p. 452.美国强调,在地球静止轨道上放置的卫星并不构成对该轨道的占有,因为《国际电信公约》已经明确规定,地球静止轨道上位置的分配不赋予任何持久的优先权或占有权。地球静止轨道与其正下方的土地毫无关系。
20世纪70年代,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地球卫星轨道资源关注大大加强。这与这一时期发展中国家谋求“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努力有重大关联。[注] The Charter of Economic Rights and Duties of States , G.A. Resolution 3281 (XXIX), December 12, 1974.1973年的《国际电信公约》(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Convention)将地球静止轨道和无线电频率规定为“有限的自然资源”。由于各国开发外层空间的经济和技术力量相差悬殊,许多发展中国家只能望空兴叹,对“先登先占”规则非常不满。它们面对发达国家占用了大部分地球静止轨道和频率的现实,开始强烈要求更改分配原则,以保证它们未来的需求。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一直要求有序地分配地球静止轨道和频率资源,降低新卫星系统进入轨道的技术标准,结束发达国家事实上对卫星轨道的永久占用。
20世纪50年代末,国际社会已意识到有必要制定国际空间法以规范各国对外层空间的探索活动。美国是这一领域国际制度的发起者和积极参与者。
由上式可知,不发生汽蚀的基本条件是:NPSHa>NPSHr。工程设计中应有一定的安全裕度,一般以 NPSHa>1.25NPSHr作为给水泵不发生汽蚀的条件。因此,除氧器的布置以及泵的 NPSHa应保证在机组负荷骤降工况下,尤其是最严重的暂态工况汽轮机全甩负荷时,给水泵入口叶片不发生汽蚀。
三、国际电信联盟会议上的长期博弈
在人类进入太空初期,一些国家发射卫星并不需要征求国际电信联盟的同意,也并没有遭到任何国家的抗议,因为当时还没意识到看似广阔的外层空间也会出现“公地悲剧”问题。随着对卫星轨道需求的增加,在1959年举行的世界无线电行政会议(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的前身)上,国际电信联盟首次开始进行卫星轨道和频率的登记和分配。采用的方式基本上是长期以来适用于地面无线电通讯的“先登先占”方式。所谓的“先登先占”(first come, first served)原则是指登记国通过协调和登记后,有权使用某一卫星轨道位置和频率,先行登记的国家在使用某一卫星轨道位置和频率方面将优于后来登记的国家。[注] Michael Sheeha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Space , Routledge, 2007, p. 136.这种规则实际上让登记国取得了一种“永久占有”的权利,因为可以通过发射新的卫星来取代其淘汰的卫星,进而继续占有这个轨道位置和频率。这一规则使得美国等技术发达的国家在利用卫星轨道资源上占得了先机,而后发射卫星的国家为了不干扰现有卫星的信号,就需要对自己的卫星系统进行一定的技术调整。这会导致费用的增加和卫星功能的受限。
(1)在发展中国家不断呼吁下,国际电信联盟逐渐修改了地球静止轨道的有关规定,将“公平利用”这一原则加入公约。美国也难以阻挡这种由众多发展中国家推动的追求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潮流。例如,经过1971年世界无线电行政会议的讨论,国际电信联盟在1973年《国际电信公约》第33条第2款中规定:“在使用空间无线电业务的频带时,各会员应注意,无线电频率和地球静止轨道是有限的自然资源,必须有效而节省地予以使用,以使各国或国家集团可以依照无线电规则的规定并根据各自的需要所掌握的技术设施,公平地使用无线电频率和地球静止轨道。”[注]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Convention of 1973, Malaga-Torremolinos, Art. 33(2). 这一方面承认了无线电频率和轨道资源是有限的自然资源,另一方面要求成员国节约使用轨道资源,以确保所有国家都能“公平地使用无线电频率和地球静止轨道”。
根据牛顿-欧拉式(1)-式(6),在知道各个关节变量θi,角速度和角加速度的情况下,依次向外递推,可以得出机械手各杆件的速度、加速度。
1982年国际电信联盟再次修改了《国际电信公约》,将第33条第2款修改为:“在使用空间无线电业务的频带时,各会员应注意,无线电频率和地球同步卫星轨道是有限的自然资源,必须有效而节省地予以使用,以使各国或国家集团可以依照无线电规则的规定并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和个别国家的地理位置的特殊需要,公平地使用无线电频率和地球同步卫星轨道”[注]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Convention of 1982, Nairobi, Art. 33(2). ,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求加入了《国际电信公约》。公约有两个规定明确了“公平使用”这个术语的含义:(1)在使用地球静止轨道位置时,必须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和特定国家的地理情况;(2)各国只有遵守国际电信联盟的无线电规章,才能公平地享有使用频率和轨道的机会。
(2)在历届国际电信联盟召开的会议上,围绕着地球静止轨道的分配问题美国与发展中国家都展开了激烈争论。结果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电信联盟对地球静止轨道资源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规划。但面对发展中国家的压力,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是对“公平利用”原则抵制最严重的国家。
在1973年的世界无线电行政会议上,阿尔及利亚代表团提出的提案要求国际频率登记委员会在作出有关地球静止轨道的决策时除了考虑“有效和经济”原则还必须考虑“公平”原则。这一提案遭到一些国家的反对,但经过投票表决,该提案以65比43票的多数获得通过。[注] Thomas A. Hart Jr., “A Review of WARC-79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atellite Communications Services”, Lawyer of the Americas , Vol. 12, No. 2, 1980, p. 449.因此,1973年《国际电信公约》关于国际频率登记委员会的规定是“向会员提出咨询意见,以便在可能发生有害干扰的频带内开放尽可能多的无线电路和公平、有效、经济地使用地球同步卫星轨道。”[注]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Convention of 1973, Malaga-Torremolinos, Art. 10 (3c).
1979年的世界无线电行政会议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它继1959年日内瓦世界无线电行政会议确立“先登先占”规则之后首次全面修订了《无线电规则》。参加这次会议的国家大约有一半在20年前还不存在。在1959年,非洲国家中只有加纳加入了国际电信联盟,而到1979年非洲48个独立国家中的绝大多数都加入了国际电信联盟。发展中国家在投票权上也占据了多数。[注] 同①, p. 443. 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次会议上指出占世界人口10%的国家控制着90%的无线电波段,[注] Kim Alaine Rathman, “The ‘Common Heritage’ Principle and the U.S. Commercialization of Outer Space”, Ph. D. Dissertation, Graduate Theological Union, USA, 1996, p. 52. 并与发达国家就地球静止轨道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在会议召开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集团与发展中国家集团在会议主席人选问题上产生对立。美国力图把这次会议依然界定为一次技术性会议而不愿讨论政治问题,而发展中国家呼吁发达国家向它们提供技术援助以使发展中国家可以“公平使用”地球静止轨道,以应对技术进步带来的挑战,并讨论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共享频率和轨道资源。[注] 同①, pp. 444-446. 发展中国家在这次会议上提出,最好建立一个长期机制来为每个国家分配特定的轨道位置和无线电频率,美国等发达国家认为这种方式会阻碍技术进步,并会导致轨道位置闲置。[注] Magnus Wijkman, “Managing the Global Comm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 Vol. 36, No. 3, 1982, p. 535.
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也随之而发展,其中,发展比较快的技术为无人机技术,这种技术也是目前比较领先的技术,基于使用此种技术促进相关行业的快速发展,所以其被积极使用在多个领域之中。在土地整治当中也引入此种技术,基于此,土地在治理过程中更加科学化的同时土地资源被积极有效地利用起来。本文针对无人机摄影技术进行有关阐述,比如,介绍了无人机摄影技术的具体情况,分析此技术的优势之处,以及阐述了如何使用这种技术在土地整治中。
在1985年和1988年,国际电信联盟召开了两次专门针对地球静止轨道和无线电频率问题的世界无线电行政会议,这两次会议所通过的最后文件,打破了沿袭20多年的“先登先占”规则的唯一性。国际电信联盟首先在1985年的会议中同意在分配某些频带给“固定卫星业务”使用时,实施“事先计划”程序,称为“分配计划”。这种针对“固定卫星业务”的计划程序取代了“先登先占”原则,在 1988 年的会期中进行了确认。
针对有可能的规则变化,美国声称国际电信联盟的政策要求促进卫星轨道和无线电频率的“高效”使用,因此,唯一的途径就是给予技术最先进的国家以优先权,而不应将分配给某些国家的轨道资源空置。在1979年世界无线电行政会议上,针对发展中国家要求公平分配轨道位置的提议,美国代表团要求国际电信联盟应考虑有技术能力的国家对轨道“明显的需求和使用能力”。[注] Marvin S. Soroos, “The Commons in the Sky: The Radio Spectrum and Geosynchronous Orbit as Issues in Global Poli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 Vol. 36, No. 3, 1982, p. 674.在1985年和1988年,欧洲和非洲区域以及亚洲和太平洋区域都通过了预先分配卫星轨道位置的机制,即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分配到一个卫星轨道位置,而美国在美洲地区抵制了预先分配卫星轨道位置的机制,而是使这些卫星位置空置留待日后使用。
(3)虽然美国反对国际电信联盟在现有的分配方式中对发展中国家做一定的倾斜,但并未发展到像当今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及万国邮政联盟那样的程度。由于这一领域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美国以多种方式积极维护有利于自己的规则。例如,国际电信联盟的某些预备性会议通常只有发达国家积极参加,而这些预备性会议实际上达成了许多重要的交易。发展中国家没有足够的资源和技术能力参与这些决策过程。[注] Gregory R. Viggiano, “A History of Equitable Access to the Geostationary Orbit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atellite”, Ph. D. Dissertation, The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USA, 1998, p. 184. 这使得美国等发达国家在这一领域仍然占有绝对优势,可以左右许多重要的决策。发展中国家短期内无法改变这一现状。国际电信联盟的卫星轨道资源和频率分配虽然有了“先登先占”和“公平使用”两种原则,但到目前为止,“公平使用”地球静止轨道只能通过两种分配方案来实现:一是,广播卫星服务(BSS)在12GHz波段和相连的支线链接中操作;二是,固定卫星服务(FSS)在6/4GHz到14/11GHz的波段进行操作。除此以外,“先登先占”规则仍然适用于所有卫星通讯服务的所有频率波段。[注] 周丽瑛:《外层空间活动商业化的法律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第105页。 而且根据2003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的决议,即使某一国家分配到了某一轨道位置,也不能为其提供任何永久性的优先权。
近年来,一个国家申报网络资料而由另一个国家发射或使用卫星的情况非常常见。一个国家将其从国际电信联盟申请到的卫星轨道位置和无线电频率出租或者出售给另一个国家的行为,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90年代。当时,太平洋岛国汤加[注] 汤加国内生产力水平不高,严重依赖外援,工业不发达,农业、渔业和旅游业是国民经济的三大支柱,缺乏经济实力来开展大规模空间活动。 向国际电信联盟申请了16个地球静止轨道位置,并声称其他国家可以向其设立的汤加卫星公司(Tongasat)租用卫星轨道。此后,汤加卫星公司对外出租了一个轨位,并将其余轨道位置以每个位置每年200万美元的价格进行拍卖。此举震惊了各国,遭到了美国一些私营部门和国际组织的反对,美国哥伦比亚通信公司向美国政府提出应拒绝任何使用汤加轨道位置的公司申请“着陆”的权利。对此,汤加认为其行为符合国际电信联盟规则和程序。尽管有很多组织反对汤加的行为,但汤加的行为并未违反国际电信规则的字面含义,只构成对国际电信联盟规则的精神的违反,并且国际电信联盟没有强制性的争端解决机制。因此,国际频率登记委员会最后决定允许汤加从其递交的16个轨道位置申请中选择6个。汤加对此表示接受。汤加案说明国际电信联盟分配轨道位置的规则是有漏洞的,很难杜绝租赁行为。国际电信联盟不推荐出租轨道位置的行动,但在实际案例中,还需要根据情况处理,并且需要进一步研究租赁在卫星轨道资源分配方面的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越来越认识到卫星轨道资源的重要性,国际协调工作也变得越来越困难,甚至可能需要进行政治和外交层面的交涉。
为了占有轨道位置,目前国际电信联盟的规定仍无法阻止“纸卫星”现象。所谓“纸卫星”是指有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在国际电信联盟登记但并没有实际发射,也不准备近期发射的卫星信息。“纸卫星”的作用就是通过登记占用轨道资源。这种“纸卫星”现象,就是源于轨道资源的稀缺的特点和注册登记费用低的现状,这不仅耗费了国际电信联盟的大量经费,也严重阻碍了轨道资源的公平使用。但国际电信联盟无法有效地区分真实合法的申报与投机的申报,并且也没有“执法权”来控制成员国指配频率和轨道位置的活动。
2012年,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了2012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随着非洲国家卫星通信应用的增加,卫星轨道资源异常紧张。为使后来的卫星操作者也有使用的机会,大会对卫星轨道资源使用的一些原则性问题进行了讨论,对使用方法和程序进行了规范,以确保各国能合理、正常并相对公平地使用。[注] 张虹:“WRC-12上的卫星资源争夺战”,《中国无线电》,2012年第2期,第23页。 这些修订关系到各国卫星频率轨道资源使用权益的得失,因此争论异常激烈。当下,许多国家在获得新的卫星轨道资源来满足卫星通信业务的发展方面越发困难,不得不想尽办法进行规划。
美国在这一领域的长期行为,相当典型地体现了一个权力护持者对规则变化的敏感,他所使用的应对措施也是多种多样的。面对发展中国家修改已有规则的要求,美国细心地掂量各国的意图,有重点地控制局势的发展方向,这也显示出当今时代对国际制度主导权竞争的复杂性。推进外空公域治理的优化,美国的态度最为关键。应推动主要外层空间国家,认识到合作与分享更有利于实现各自的国家利益。[注] 徐能武、曾加、刘杨钺:“维护和促进外层空间安全的‘向善’关系——外层空间安全合作机制的复合建构与持续进化”,《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4期,第4页。
四、结 语
目前国际电信联盟对地球静止轨道的分配基本还能确保有需要的国家得到满足,并且地球静止轨道和无线电频率的使用效率和容纳能力可能会随着技术的进步而提高,例如通过数字压缩技术、更多的使用近地卫星轨道以及使卫星间隔更近等方式。但总的趋势是世界各国对轨道资源的需求在不断增加,技术进步不可能完全解决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国际电信联盟现有的分配方式对发展中国家和美国等发达国家来说都不甚满意。长期以来,作为空间活动大国,美国在地球静止轨道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上保持着相当大的优势。未来美国的政策选择可能是,继续在国际电信联盟机制内主导地球卫星轨道和无线电频率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例如确保国际电信联盟中的某些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条款不被修改。由于美国国内利益反对强大国际机构干预资源分配的传统以及美国国会积极鼓励美国企业商业利用外层空间的行为,美国政府将抵制国际电信联盟进一步向资源分配领域演进。为了解决国内外利益冲突,并且考虑到外层空间商业化的迅速发展,美国政府的立场是倡导地球卫星轨道和无线电频率的商业化分配方式,例如通过拍卖卫星轨道位置等方式。这一立场也会得到美国商业组织和国会的支持。
科学决策可以进一步提高政府社会治理能力,不断解决发展过程中各种实际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科学决策要把握社会现实,并以大量事实为依据而实施决策。传统的政府决策模式,主要依据经验以及直觉,经常出现“长官意志”的非理性决策现象,很难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精准性。大数据时代,政府决策是建立在全面数据分析基础之上,它依据大量数据信息的支持,对社会各个领域的数据进行分析整理,准确地把握社会发展实际情况,形成数据分析的决策机制,政策制定更加科学合理,同时对政策实施效果进行监控,随时改进纠正,增强了政府决策的准确性,实现政府从经验决策向数据决策转变,极大提高了政府决策能力。
美国获取地球静止轨道资源这一案例显示,我们依然生活在一个民族国家主导的时代。国家仍是全球公域治理的核心。全球公域治理离不开权力的运作和规则的设定。既有的治理规则主要是发达国家制定的,存在着诸多不合理、不公平的问题,同时规则还天然地具有维持现状的功能。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 原来由发达国家主导的规则越来越难以为全球提供令人满意的公共产品。治理是否有成效决定着规则的权威性。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群体所掌握的权力,如资本、技术、知识、人才等不断增强,它们在全球公域治理中的投票权和话语权提高,开始参与全球公域治理的顶层设计,必然影响和塑造着全球公域治理的走向。然而,全球公域治理新旧格局的逐步转换过程是动态和一波三折的,因为权力的衰退和增长都不是线性的。在权力逻辑的支配下,全球公域治理不可能那么“和谐”,国家会在全球公域治理谈判中竭力维护自己的利益,以增加本国的权力和提升国民的福利。全球公域治理中的权力依然是最重要的力量,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将维系其强大的权力,发展中国家要想获得有利于自己的规则安排仍然面临艰难的挑战。合作仍是全球公域治理中的必然趋势,规则的变化需要在合作的前提下平衡各行为体之间的利益, 以消解权力流变所可能造成的消极后果。
在卫星应用产业空前发展的时代,轨道资源的战略地位日益显现。世界各国利用国际规则对轨道资源的争夺不断从技术层面延伸到外交、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推动这一领域的治理朝“善治”的方向发展?笔者认为,首先国际社会应大力提倡节约和高效使用卫星轨道这一有限的资源,并增加现有的轨道容量。各国应努力将所使用的频谱范围限制在提供业务所需的最低限度,尽可能采用最新技术。研发使用同频但覆盖不同的业务区、同覆盖区但采用不同的频率等技术。卢森堡等国的多星共轨技术也是应对轨道资源短缺的有效手段之一。其次,过去10年,国际电信联盟成员中的私营的制造商或运营商数量大量增加,私营部门在这一领域中的话语权肯定会持续增强。考虑到空间商业化趋势和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的趋势,国际电信联盟应研究允许通过租赁等经济手段使频谱和轨道位置流转,但产生的经济利益应部分地为各国人民分享,这方面可以参考国际海底区域资源平行开发制度的经验。这种做法的前提是维持《无线电规则》中频率和轨道位置分配的现有规则,由主管部门确认租赁安排,对卫星网络资料申报的发出许可和发出通知职责继续负责,以避免对其他卫星网络造成有害干扰。总之,若不维护国际电信联盟的机制,轨道资源将逐渐流向最有
编辑 邓文科
The Power and Rules in 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Commons: In the Case of US’s Acquisition of Geostationary Orbit Resources
SHEN Peng1
(1.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20,China )
Abstract: Countries often use power to shape the agenda and rules in 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commons. The allocation of geostationary orbit resources is subject to 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commons. As a major country in space research, the US has taken the lead in the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s arrangement of geostationary orbit resources by virtue of its advantages in technology, knowledge, and institution. In the 1970s, when developing countries began to actively demand “equitable access” to geostationary orbit resources, the US spared no effort to maintain its vested interests and opposed the change of the status quo. In the past decades, this kind of disputes betwee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the US have been taking place at meet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repeatedly. Without a fundamental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in the future, resource politics would inevitably continue.
Key words: global commons; geostationary orbit; power; the US diplomac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