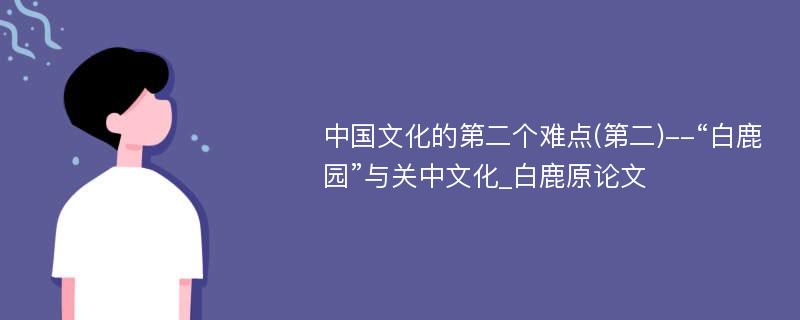
中国文化之二难(中)——《白鹿原》与关中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中论文,之二论文,中国文化论文,文化论文,白鹿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宗族之二难
《白鹿原》对关中宗法社会的展示
关中宗法社会的根基,可以用宗族两个字概括。
关于宗,《说文》:“遵,祖庙也,从宀从示。”《白虎通义》:“宗者,遵也。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辞源》解释为祖庙或祖先。《礼记·丧服小记》:“尊祖故敬宗。”综合上述之义,宗是与古代祭祀有关的一个字。上古祭祀,祭鬼神亦祭祖先,故而宗与祭祀之庙宇有关,有宗社之义,又与祭祀之对象先祖有关,有尊祖之义。宗是中国文化祖先崇拜的代码,它由英雄祖先的神话中诞生,并从上古氏族社会一直走到当今的文明社会之中。
关于族,《说文通训定声》:“族,假借为属。”“属,连也,从尾蜀声。”《中文大字典》亦同意假借“属”的说法,具体解释为直系亲属或同姓亲属。综合上述之义,族乃与血缘有关,指那些在血统上相连之人。族是中国文化血亲心理的代码,它小则指家族,泛则指种族民族,无论涵义的广狭,族均是对血缘亲近的人的总称。
在中国文化中,宗与族是相依赖而存在的,同宗者,必是同一血缘,共祭同一祖庙;同族者,必有共同所亲之祖、所敬之宗。于是,宗族的连用就十分普遍,《尔雅·释亲》:“父之党为宗族,”《墨子·明鬼下》:“内者宗族,外者乡里。”在宗族这一概念之中,祖先崇拜和血缘关系被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血缘关系是祖先崇拜的基础,祖先崇拜又是强化血缘关系的纽带,随着宗族概念的反复运用,祖先崇拜和血缘关系不断地被强化和延续,成为中国封建社会赖以存在的核心。
小说《白鹿原》以关中地域为基点,虚构了滋水县的白鹿村,叙写了以白鹿为姓的大家族,展示了这一家族从清末至建国的近百年历史变迁中的生存状态。小说的视点不是一个人几个人,而是一个家族,小说的背景不是几十年,而是近百年。象这样的在近百年历史变迁中写家族变迁的小说,在国外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在中国就是陈忠实的《白鹿原》。从《白鹿原》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农村以家族为核心的社会形式和社会群体,它的特征,它的作用;看到了贴着宗族标签的社会人,他的社会化过程,他的生存状态。于是我们发现,以前所知道的宗族,只是教科书的阐述,只是辞典的解释,唯有《白鹿原》真实地再现出关中地区的宗法社会状况,才给我们原本有限的宗族知识库存中,增加了具体真切的感性内容——宗族并不是一个空洞虚浮的概念,它具有实实在在的内容,组织上的和经济上的,它在白鹿村这一小社会中,起着协作扶助和管辖控制的双重作用;同时它又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作用于人的灵魂,渗入于人的血液之中,并在白鹿一族的每个成员的社会化进程中,发挥着陶冶教化和禁锢束缚的双重作用。这些具体真切的感性内容,使我们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审美感受,一是慨叹,二是恐怖。
关中宗法社会是以宗族为本的。《白鹿原》所叙写的白鹿一族是以婚姻和血亲关系组成的社会群体,群体成员不过二百户,不足一千口,尽管祠堂里记载着列祖列宗显考显妣的神轴和椽子檩条,被洪水一冲而光,被大火焚烧殆尽,然而,这一族的种系血脉、族规家法却一直绵延着。族长由长门白姓子孙承袭下传,“仿效着宫廷里皇帝传位的铁的法则。”族权的象征是一面锣和一个黄铜钩圈的钥匙,敲锣可召集族人,钥匙掌管着祠堂的大门。族有公田,祠有账薄,乡约规范着成员的行为,学堂教育着本族的后代,族长有权有威,族人恭顺服从,一个村庄就是一个大家族,一个大家族就是一个大家庭。宗族就是这个村庄、这个家族、这个大家庭的核心。在数不清的年代里,在白鹿一族繁衍生息的艰难历史中,正是这充分体现祖先崇拜和血缘关系的宗族之本,把历代子孙凝聚在一起,使他们面对无数次天灾人祸,能共济于危难之中。与这一主题有关的有三个具体情节:第一是白狼威胁了白鹿原,人们燃火拒狼,每到夜里,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族长白嘉轩决定修补堡子残破的围墙,他提着大锣,沿村街一路敲过去,人们就丢下活计,扔下饭碗到祠堂集合,随着“哇一声的响应”,各户依照惯例出粮出工,自觉热情,紧张有序,充分体现出关中农民团结一致求生存的生命意识,给宗族赋予了一种激昂悲怆的生命意蕴。第二是瘟疫威胁了白鹿原,人们一致要求修庙葬尸救助生灵,族长白嘉轩把族人召集到祠堂,复读族规乡约,表示只能按族规乡约行事,并提出造塔镇邪的方法。这一场充满神秘色彩的情节,把族长族权族规凸显到了本体的位置上,它揭示出,个体是弱小的,是没有力量抵御灾祸的,然而,只有全家族乃至整个原上的人的合力,才能与一切莫名的灾祸抗争。这是一种带着血缘色彩的原始集体主义的,也许正是这种原始集体主义,才使我们的祖辈历经灾难而不衰,生生息息,繁衍至今,也许正是这种原始集体主义,才构成了关中文化注重宗族的内在原因。因此,从对人的凝聚和对群体的组织方面来说,宗族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第三是干旱威胁了白鹿原,族长白嘉轩决定伐神取水。族里十二岁以上的男人全部参加,一连四个伐马角的人都失败了,白嘉轩毅然决然地充当了第五个马角,他舞动着刚出炉的铁铧,又把烧红的钢钎从自己的左腮穿到右腮,带领一族人到山岭深处的黑龙潭去取水。这一浸透着迷信色彩的祈雨活动,并没有让人感到丝毫的愚昧和可笑,相反,其势之浩荡,其气之威武,其情之悲壮,令读者震惊不已,感慨不已。读者看到的是,中华子民们在强大的无法驾驭的自然面前所表现出的一种牺牲自我的英雄豪气,正是族长白嘉轩的这种豪气,才使全族的人具体感受到宗族的实实在在的存在,感受到宗族的强大,从而聚拢在宗族这一核心的周围,扭结成一个整体,向命运抗争。在这里,宗族在生存层面的积极意义,被最大限度地凸显出来。也许,这就是关中一带从古至今一直保持着聚族而居的原因?也许,这就是关中文化所具有的超常的凝聚力之所在?——对此,读者怎能不慨叹不已?
然而,揭去扶助共济的面纱,我们还看到了宗族对族人的强行管辖与严密控制,对个体的人的血淋淋的压迫。任何社会的维持和巩固,都必须借助一定的社会结构形式。中国封建专制社会结构是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宗法制度体现和深藏于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之中,尽管这四种权力都“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注: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见《毛泽东选集》一卷本P33,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但是,相比之下,族权则是最切近个体的、最有组织的全方位的管辖和控制,它发挥着政权所不及的作用,蒙着血缘的面纱,对族人实行着近距离的“皇权”统治,可以说,它实质上是封建政权统治的一种补充形式;它又没有父权那种亲情的局限,能更严厉更无所顾忌地代表父辈教育和惩戒子弟,所谓“牧令所不能治者,宗子能治之,牧令远而宗子近也;父兄所不能教者,宗子能教之,父兄可从宽而宗子可从严也。”(注: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下卷,《复宗法议》。)于是,在民间乡里,尤其在关中农村,族权的位置超于政权父权之上,它可以任意施刑,对族人进行处罚。处罚的方式有罚跪、罚款、罚粮和鞭抽板打。白嘉轩为维护乡约、整肃民风,敲锣召集全部男性族人,在祠堂惩治赌徒烟鬼一次就达十人之多,对赌徒用沸水烫手,对烟鬼用大粪填口,其态度之绝决,手段之诡毒,非族权所不及。处罚淫乱男女,破例召集女人入祠,在发蜡、焚香、叩拜和诵读乡约族规之后,“庄严宣判”,“对白狗蛋和小娥用刺刷各打四十”。族长开刑之后,族人便轮流施刑,结果是小娥被打伤,狗蛋被打死。由此,族权对族人的管辖乃至任施酷刑、草菅人命被尖锐地揭示出来。从那庄严的祠堂里,从那充弥着香蜡气息的厅院中,我们看到了血淋淋的统治和冷酷的杀人。这一情节的意义还不仅仅是这些,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白狗蛋并未淫乱,而真正的淫乱之人是鹿子霖。对此,族长并不是未曾风闻,族人也并不是心无疑绪,然而,他和他们都不想落实甄别,竟然还让鹿子霖充当行刑者,甚至还以反咬为名对狗蛋“加打四十”。显然,宗族处罚也是选择对象的,对鹿子霖这样的富豪乡绅,大事可做小事,有事可化无事,至于白狗蛋这样的穷光蛋,没事也得有事,喊冤就是反咬。处罚这样一个一人喊打众人应之的下等人,族人没有疑虑,打死这个孤身无助的游荡鬼,族长没有顾忌。显然,宗族对于它的族人们并不是平等的,一脉相亲的血缘实际上也带着金钱的锈渍,维护着富人,欺压着穷人。显然,对于*
豪乡绅来说,宗族也许是他们身心依托之所在,但是对于穷苦农民来说,宗族是一架可怕的控制他们压迫他们的机器,它的人吃人的血口,随时都有可能向穷人张开。——对此,读者怎能不恐怖不已?
由上述可见《白鹿原》真实地展现出关中社会的状况,揭示出宗族在生存层面的积极意义,表现出对祖先崇拜、血缘关系的依恋的情绪,同时也揭露了宗族对个体的管辖控制乃至残酷的欺压,指出了它的不公和虚伪。作者以自己对宗族的二难情感,展示了关中文化的宗族二难景况,并带给读者一种二难的审美感受——虔诚的慨叹和深层的恐怖。
宗族的可慨叹可恐怖之处,并不仅仅在于它的组织上、经济上的扶助共济和管辖控制,还在于它以一种意识形态的形式渗入了人的灵魂中血液中,随着一代一代的血缘的承继而被永久地延续着、强化着,它超出了社会的、组织的、经济的范围,作为一种思想,对关中的社会人产生着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其正面影响,是促进人在社会化进程中自觉地进行道德完善,在教化后代、培育民族整体意识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其负面影响,是控制禁锢人的思想,使人向宗族求认同,向祠堂寻皈依,其扼杀人的个性和创作性的能量远远超越了宗教等一切意识形态,其通过统治人的灵魂而达到统治宗族统治社会的负面作用也远远超过了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思想文化政策。
人的社会进程中,离不开所在社会提供的教科书,也离不开所在社会提供的一切具体的社会化形式。《白鹿原》的社会教科书是白鹿一族的族史,是白家和鹿家的家史。《白鹿原》的社会形式是围绕祠堂而展开的一系列祭祀仪式、宗族文化活动和谪长子继承制度。那个“没有任何竹册片纸的典籍保存下来”的族史,淘去了平平之人和平平之事,保留了璀璨的悲壮的环节,编组成为令人奋发和警戒的一个个故事,被白鹿一族的后人们口耳相传。尽管人们已不能说清第一位到原坡凿窑洞搭茅屋的始祖的姓名,尽管人们不能不无遗漏地列数和供奉每一位先祖,但是这明断实续的族史链条,把一个完整的家族精神传输下来,以耕织为本,以节俭为本,以谦恭为本,以仁义教悌为本第一整套精神体系,集中衍化为族纲族规,在白鹿宗族中世代承传着,绵延着,无一遗漏。家史比族史更切近个人,也更生动更具体。白家的家史凝聚为一个有进口没出口的钱匣子,这个白家传久不衰的故经,通过老大败家老二兴家的故事,告诉子孙后代道德与兴家的密切联系;鹿家的家史集中体现为马勺娃熬过三关污辱学成手艺发家致富的故事,这个卧薪尝胆的发家史,向子孙后代灌输了忍辱负重以图出人头地的先苦后甜的人生模式。可以说,族史家史是一笔“看不见摸不着的财富”,是经“村村寨寨一代一代富的穷的庄稼人咀嚼着品味着删改着充实着传给自己的后代”的“经典性乡土教材”,它把人们在家起家落族兴族衰的变迁中所把握到的立身之本,从宗族繁衍、个体生存的高度予以解说。在人类文化的浩繁万卷的教科书中,哪一本教科书能像族史家史这样,从人的先祖、人的血缘出发,贴近人的生存,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哪一本教科书能像族史家史这样,生动具体形象,可感可知,被人们自觉地传诵着遵循着?没有!真的没有!于是,宗族意识便由这宗族的教科书而得到传播。另外,与教科书配套的是围绕着祠堂厅院所进行的一系列宗族祭祀仪式和宗族文化活动,是与皇族传位法则一样的谪长子继承制度。祠堂是族人活动的中心场所,初一祭祖的仪式,族中大事的商议,族谱的续写,乡约的诵读,学堂的开学典礼,新婚夫妇的叩拜祖先,浪子的归门认宗等等,都要在这里举行。仪式是庄重的,分蜡上香叩拜,谨严而不紊,一切外在的形式,最终都以宗族的强大感、个人的安全感,使族人与宗族之间具有了不可分的精神联系;内心是虔诚的,宗族的尊严,个体的满足,以及种种内疚愧悔的情绪,令每一个族人的心灵受到祖先的陶冶,洗涤和鞭挞。鹿三就是在全族召归亡灵的祭祖仪式上,在那庄重的氛围中自责教子的失误,最终因“承受不住心灵的重负”而哭喊“我造孽呀”,并用头在砖地上磕碰。这一次次宗族文化活动和仪式,是以形式开始的,最终却都是以内容的收获而告结束,可以说,《白鹿原》的每一个人从小到大都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强化了自己的宗族意识,并又将宗族意识传输给一代代后人们。谪长子继承制度对人的作用同样不能低估,白孝文在新婚妻子面前无法克制自己的情火欲求,其祖母想尽办法也无法令其节制,然而白嘉轩的一句话,却令他倏然猛醒,那句话是:“你得明白,你在这院子里是——长子!”长子,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责任,它的份量白孝文是知道的,它是家庭的代表,宗族的代表,这个责任不能不使白孝文猛醒。在关中文化中,长子历来是被器重的,长子的人生历来是沉重的,其器重在于它是宗族血脉的代表,其沉重在于它须对家庭对宗族承担起供奉先祖承延血脉的重担,我们从白氏一个个族长的功绩中,从白嘉轩、白孝武的行迹中,从当今关中人的言谈举止中,不能不感受到其中有着惊人的相似的思想渊源,那就是谪长子继承制带给他们的高出于其他族人的宗族意识。
宗族意识能够促使人自觉地进行道德完善。在宗族里,道德不仅仅是民风乡俗,个人的小节,而是关乎到宗族生死存亡的大事,是宗族之本体,因此,宗族意识越强的人进行道德完善的自觉意识也越强。白嘉轩就是这样。他处罚烟鬼的动机是嫌他们“丢尽了白鹿一村的脸”。他记清祠堂的帐目,为的是“不能给祖宗弄下一摊糊涂账”。他用“最果断最斩劲的手段”处罚白孝文,目的是要洗刷孝文给他和祖宗以及整个家族所涂抹的耻辱,他说:“忘了立家立身的纲纪,毁的不是一个孝文,白家都要毁了。”竞争对手鹿子霖被逮,白嘉轩没有丝毫的幸灾乐祸,当即做出搭救的举措,其出发点就是要“在白鹿村乃至整个原上树立一种精神”。他认为,“人行事不在旁人知道不知道,而在自家知道不知道;自家做下好事刻在自家心理,做下瞎事也刻在自家心里,都抹不掉;其实天知道地也知道,记在天上刻在地上,也是抹不掉的。”这一席话,是白嘉轩一切义举的脚注,充分体现出他维护宗族风气家庭道德、进行自我道德完善的高度自觉性。这种自觉性是渗入心灵和血液的宗族意识启示给他的,是人的宗族繁衍血脉绵延的本能所促使的。白嘉轩的这种自觉性,在关中人文精神中可以找到印证。数千年来,聚族而居的关中乡土共同体中的关中村民,一方面遵从孔子《论语·子路》的“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的信条,以宗族为孝,以乡党为父老兄弟,敬宗重族,一方面自觉地修养道德,陶冶情操,寓耿直强悍的天性中以忍让温良的因子,使道德与力量,使阳刚与阴柔在关中人的人格体系中化为中庸涵容。这种中庸涵容的人格,不仅限于关中文化培养出的关中人,而且在中华文化培育出的中国人群中,也处处可见。由此,宗族意识在人的社会化进程中的积极意义就不言而喻了。
宗族意识有益于凝聚群体成员和培育民族整体意识。白鹿村的宗族是一种社会群体,白鹿村的宗族意识是一种社会群体意识。尽管它是以血缘为纽带,有着一定的偏狭性,然而,群体所具有的优势,群体意识所有的积极作用,它也同样具备。它联结着个体,凝聚着个体,同时又使个体的思想超越个体的小局限而进入群体的大境界,于是个体就具有了群体的力量,就有高尚的情操,于是群体意识又反过来凝聚群体。翻开族史,一位族长大旱年领着族人打开,吐血而亡;一位族长领着族人打贼人被刀劈成两截……族人的忘我牺牲精神得惠于带有宗族血缘色彩的群体意识,反来,族长为维护宗族整体利益所做出的奉献,又沉积在整个宗族群体的感性经验之中,对宗族群体形成巨大的凝聚力量。于是在这样的家族环境中生长,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生存的白鹿一族的个体们,关中乡土共同体的个体们,便都有了族与家共存亡的宗族集体意识,这种族与家共存亡的宗族集体意识引申开来,小则体现在落叶归根、故土难移的心理定势上,大则体现在国与家共存亡的民族整体意识上。现实也正是如此,一代代中华民族的子孙在口耳相传的英雄神话中形成了民族整体意识,这种民族整体意识又培育出民族的英雄,造就出英雄的民族,这一切最终积淀成为以民族英雄和英雄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文化,使中华民族由重家庭到重宗族,由重宗族到重民族,最后延展为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和强烈的爱国精神,这种民族的自尊感和爱国精神最终潜入人们的集体无意识之中,并随着民族生命的承继绵延着。在我们的价值坐标系上,民族意识爱国精神总是被高度赞扬和充分肯定,宗族意识却不免因其偏狭而遭到责诘,不过,通过《白鹿原》这一文本对宗族意识的解说,我们确实应该看到,它作为一种群体意识在人类社会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看到它对凝聚群体、培育民族意识的有力促动。——于是,面对那绝无仅有的教科书、隆重的祭祀仪式和继承制度,面对那道德完善的自觉性,面对那凝聚群体和民族的积极作用,读者又怎能不慨叹不已呢?
然而,在我们受惠于宗族意识的同时,我们同时也被它紧紧地拘束住了。我们生活在和睦稳定的社会中,体味着宗族之安谧,满足着族脉之绵长,得意着文明之悠久,却没有注意到,家庭、宗族带给每一个人精神上的控制和异化。社会的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成熟着,适应着社会,同时也被社会所扭曲控制。这是一个怪圈,谁也跳不出。这是一个谜,人人都欲解说。《白鹿原》的作者跳到这一怪圈外面去窥视这一现象,去解说这一个谜,于是,他揭示出了宗族意识的另一个侧面,那就是宗族意识对人的精神的禁锢。解说集中体现在黑娃和白孝文身上。黑娃是宗族叛逆的代码。他从小就与宗族文化极不和谐,他不情愿去念书,宁愿“挎笼提镰去割青草”,他走进学堂的第一个举动就是用凳子砸了先生的脚背,冰糖让他感到甜蜜,也让他痛苦。一个生活在下层的充满原始生命力的小“慌慌鬼”,在一块冰糖面前感受到了人生的不平,他的主体意识觉醒了,强烈的主体意识与底层生存状态的矛盾,使他的心灵受到煎熬,他发狠说:“我将来挣下钱,先买狗日的一口袋冰糖。”这是一句宣言,是叛逆者对不平境遇的反抗宣言。反抗的第一步就是冲出传统伦理观念,带回一个漂亮的名声不好的女人,他不听族长和父亲的劝说,宁愿被赶出家门,在堡子外的破窑安身。鹿兆鹏对此给予高度赞扬,说他“顶住了宗族族法的压迫,实现了婚姻自由,太了不起太伟大了”。反抗的第二步就是烧粮台,进农讲所,成立农民协会,砸祠堂处罚恶棍,掀起一场“风搅雪”。反抗的第三步是当土匪。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叛逆角色,最后竟然也匍匐在祠堂的祖宗牌位面前。黑娃的皈依宗族并不是没有思想基础的,他曾对鹿兆鹏表示过叛逆的苦恼:“村里人不管穷的富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斜眼瞅我,我整天跟谁也没脸说一句话。”黑娃的苦恼道出了宗族意识从外在舆论和内在精神上给敢于反叛的人所造成的巨大压力,乡村的冷漠斜眼是一张无形的宗族大网,笼罩着黑娃,压抑着黑娃,有脸无脸以及对祖先的内疚折磨着黑娃,这就使他在历史的推动中走向叛逆,在精神的驱动中又走向宗族的回归,这两极矛盾运动的结果,最终是宗族意识的砧板铸压和湮灭了叛逆精神,黑娃走上了回头之路。他对新妇说:“我以前不是人。”他对朱先生说:“想念书求知识活得明白,做个好人。”于是朱先生收他为弟子,并题字曰“学为好人”。于是黑娃经过诵读论语而渐生儒雅气度,经过自觉修身而胎骨尽换。经此一番道德修炼,黑娃有了回乡祭祖的资格,他终于不再是无宗无根、祖先不认父母不要的浪子,他走回了原上,而且他是被朱先生陪着回来的,被族长白嘉轩迎接进门的。面对全族人的“伸头踮脚”,他下跪磕头,哭喊着“黑娃知罪了”,把自己“洗心革面学为好人”的决心倾诉给列祖列宗。与黑娃叛逆的人生轨迹比较接近的是白孝文。这个从小受着良好家风教化的未来族长,一步失足就成了“逆子”。他的失足,是人的主体意识向压抑人性的伦理观念的反叛,是渴望自由的个体对社会禁锢的冲击。这种反叛和冲击的代价是惨重的,亡妻败家,如狗一般蜷在土壕里,于是,乖顺时的自尊感安全感成就感,叛逆时的被羞辱被遗弃以及无以生存的惨境,从正反两方面教育着白孝文,使他必然要走回原去,走进那个曾经惩罚他的祠堂。白孝文的人生走了一个圆圈,从乖顺的原点走向反叛,最后又从反叛回归到乖顺的原点,在祠堂里找到了人生的归宿,在拜祖的仪式中寻回了一个宗族的自我。白孝文和黑娃的认祖归宗,把关中人文精神的道德感化主题、祖宗崇拜主题推上了顶峰,其隆重严肃的仪式和悲壮感人的气氛,让每一个读者切身体会到中国传统宗族文化的巨大力量,为之激动,为之震惊。不过,在激动震惊之余,又不禁发问:叛逆之黑娃与回原之黑娃,哪一个是人?哪一个是非人?孝文有脸时的性无能与无脸时的性有能,何者是人,何者是非人?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从宗族意识出发,用道德标准去衡量一切事物,如果我们放弃这一出发点,不把道德做为衡量事物的唯一标准,那么结论将该如何?用伦理道德为标准,顺从者为人,反抗者非人,有脸者为人,无脸者非人;用人性主体的标准,有自我者为人,无自我者非人,性有能者为人,性无能者非人,究竟如何评价回原认祖这一行为呢?对此,鹿兆鹏曾对黑娃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你怎能跑回原上跪倒在那个祠堂里?你呀你呀!……”鹿兆鹏的话引发出我们的同感,遗憾,深深的遗憾,我们为一个人的自我的消冥而遗憾。对此,白嘉轩也做了一个注释,不过,他是从反方面注的,他说:“凡是生在白鹿村坑脚地上的任何人,只要是人,迟早都要跪倒在祠堂里头的。”白嘉轩的话,把我们从遗憾的情绪中引向深层的思考,思考之余,不能不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恐怖。宗族意识对人居然有如此巨大的统摄能量!是的,谁能走出那个原?谁能挣脱宗族意识对自己的束缚?在人的社会化进程,在人走向文明的征途上,宗族打着道德的旗号,把许多非人的东西强加给人,同时又扼杀了人身上许多宝贵的东西,创造力量,反思能力。关中祖辈的“认”与“不认”,关中家庭的“让进门”与“不让进门”,是祖先父辈对每一个人的人生价值的判决。害怕“愧对先人”,“羞先人的脸”,“被赶出家门”,是关中人做人处事的内在驱动力。一切都围绕着宗族,人的精神只能在宗族意识中存活,人的价值只能在宗族舆论的认同和肯定中才能得以确认,宗族,这个在虚幻中存在的抽象的概念,这个在现实中的没有生命的牌位,制约了活着的人的思维和行为。——于是,体验着黑娃和白孝文的叛逆与回归,面对着欲离不得欲近不能的宗族意识的大网,读者又怎能不恐怖不已呢?
由上述可见,《白鹿原》对宗族意识的解说也是真实的,成功的。宗族意识的向善的力量,凝聚的力量,令人慨叹,宗族意识对人无形的禁锢的扼杀,又令人恐怖。我们每一个宗族人慨叹着欲向它的圆心靠拢,又恐怖着企图背离它的轨道。站在21世纪界石前的中国人,对宗族意识究竟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呢?——虔诚的慨叹和深层的恐怖。
人类学认为,不管一个社会的政治组织采用什么形式,也不管它可能做什么事情,“它总是要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社会控制有关。”(注:《当代人类学》威廉·A·哈维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版,P479。)宗族组织和宗族意识说透了就是一种社会控制。宗族组织是外在化控制,代表整个社会或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对某一种行为做出反映(即制裁),或赞成该行为方式(即正性制裁),或反对该行为方式(即负性制裁)。宗族意识是内在化控制,它通过巫术和信仰对社会的人起着强有力的控制作用,祖灵的关心和庇佑,祖灵的不满和惩罚,对现世人的心灵进行着安抚和威吓,使他们遵循着既定的社会规范来行事。《白鹿原》对关中宗族社会的展示,正是十分透彻地揭示了宗族组织宗族意识对社会和社会人的极大的控制作用,在这样的社会中生存的人,在这种意识笼罩下的人,谁能跳出它的控制?思之念之,不寒而栗和恐怖万状油然而生。
综上所述,在关中文化氛围中生长和都市文化氛围中生存的陈忠实,对关中文化核心的宗族——宗族的社会、宗族的意识形态,具有天生的依恋亲和之情和后天的理性批判之思。情是血脉的联系,是生命的赋予;思是灵魂的启迪,精神的光闪,把这两者有机地融合在自己的创作境界之中,发之而为对关中宗法社会全面的展示和对关中宗族形式宗族意识的解说,揭示出宗族对于关中人以及中华民族的支撑哺养和摧残禁锢之作用。于是,面对宗族之二难,带着二难之感受,读者们所能做的,是思考,向深层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