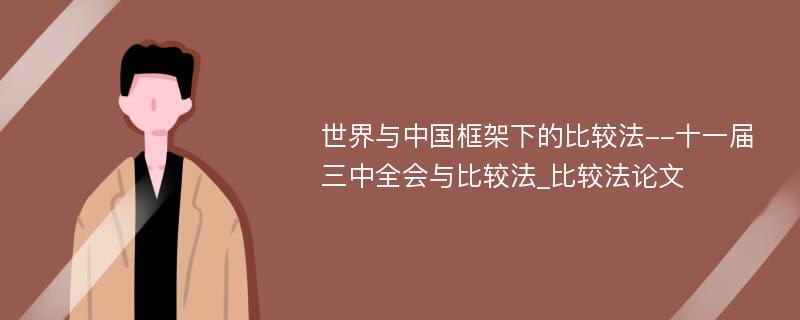
世界与中国框架中的比较法——十一届三中全会与比较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比较法论文,中国论文,框架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20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对外开放的路线,它对于中国比较法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比较法是一门研究不同法律制度之间关系的学科。 (注: See Alan Watson,Legal Transplants:An Approach to Comparative Law,th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1974,PP.5—9.M.A.Glendon,M.W.Gordon & C.Osakwe.Comparative Legal Tradition,West Publishing Co,1985,PP.6—8,朱景文:《比较法导论》,检察出版社,1992 年,第8—9页。)不同国家、地区法律制度之间的相互交往,是比较法产生和发展的直接动力。在中国历史上比较法获得较法获得较大发展的机会有两次,它们都与开放相联系:一次是清末沈家本的修律及以后民国时期仿照德国的立法,但那次开放是被西方列强的洋枪洋炮打开的,由于清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这些法律改革没有也不可能挽救它们的灭亡;另一次则是三中全会以后所出现的法制建设的高潮,在立法、司法、法律职业、法学教育等各个领域根据中国的国情,借鉴外国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注:参见沈宗灵:《比较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6—27页;潘汉典:《比较法在中国:回顾与展望》,《比较法研究》1990年第2期:朱景文上引书,第55—56,66—70页。)这次开放则是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吸取了文化革命的教训,根据国际关系的新特点,所作出的英明决策。20年来,在立法领域,我国在制定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一系列法律时,在许多问题上都大胆地借鉴了国外的有关法律,如宪法的基本框架问题,刑法的基本原则问题,民法中的严格责任原则,刑事诉讼法中的有利被告原则、无罪推定原则,公司法中的有关公司组织结构和不同公司类型的规定,等等(注:详细论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立法领域借鉴外国法的论文,参见沈宗灵《当代中国借鉴外国法律的实例》,《中国法学》1997年第5—6期。);在司法领域,我国正在进行的从法官中心到当事人中心的司法改革;在法律职业方面,我国80年代以来推行的律师资格考试制度,不同形式的律师事务所制度,近年来推行的法律援助制度,法官、检察官资格评定制度;在法学教育领域,8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的学位制度,特别是近年来实行的法律专业硕士学位制度,派遣大量的留学生到欧美日本等国学习、进修,在教学实践中尝试运用案例教学法,等等,都参照了许多国家的有关法律制度和实际经验。
比较法不是一件放置在学者书斋中的高雅的装饰品,也不是简单地把两个或几个没有实际联系的法律制度比较,没有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互交往,比较法的发展必然受到阻碍。70年代国际比较法学会曾有一个由德国著名比较法学家茨威格特(K.Zweigert)主编的编纂《国际比较法百科全书》的庞大工程,其基本框架除了各国的国家报告之外,各个学科的比较研究分卷处理。为此,一些前苏联和西方国家的比较法学家曾主张,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应另册处理,因为社会主义法与资本主义法没有可比性。(注:参见[瑞典]米凯尔,博丹:《不同经济制度与比较法》,潘汉典译,《法学译丛》1980年第5期,第2—4 页:[苏联]季列:《法的体系是比较法学的研究对象》,崔永列译,《法学译丛》,1983年第5期。)显然, 这种观点除了受到当时两大阵营对立的影响之外,另一重要原因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特别是它们的人民及民间团体之间很少发生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交往有关,当时需要用法律手段处理他们之间交往的可能性极其有限,缺乏了解对方的法律制度的实际动力。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有比较法的话,也只是为了证明自己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即所谓“反衬的比较法”。(注:See M.Bogdan,Comparative Law,Khuwer Norstedts juridik Tano,1994,PP.61—67。)在当时情况下, 中国更是远远地隔离于或被排除在世界法律大家庭之外。《国际比较法百科全书》由法国比较法学家达维德( Rene David)主编的《世界各国法律体系》卷关于远东法部分是由日本学者主持的,其中中国法部分也不是由中国学者撰写(该卷的其它有关部分都分别是由各该国的学者撰写),而是由日本学者写的。 (注: See R.David (ed.),Legal Systems in the World (IntemationalEncyclopaedia of Comparative Law.Vol.Ⅱ),Ch.8.)
20年来我国比较法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就是突破在不同社会制度的法律体系之间只有对立而没有统一,因而不能把它们放在同一层次上加以比较的思想束缚。比较法的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如果说古代,甚至中世纪的法律制度可以在各国相互隔绝的环境中而独立发展,现代世界各国法律制度发展的环境则是开放的、与其它国家的法律制度相互接触,相互影响。现在,很难找到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的全部,包括它的制度、规则、概念、法律实践和法律意识,都完全是自己独立创造的,而不吸收、借鉴其它法律制度的相关因素。在现代世界各国的法律制度中,这种借鉴,吸收或移植不仅发生在同一法律集团(包括同一法的历史类型和法系)内部,而且在大的法律集团之间也经常发生。(注:参见朱景文上引书,第168—179页;王晨光:《不同国家法律间的相互接见与吸收》,载沈宗灵,王晨光编:《比较法学的新动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13—224页:沈宗灵,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教出版社,1994年,第94—96页:孙国华,朱景文(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5年,第117—119页。)比如所谓两大法系之间的趋同就是这一现象的反映;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法律制度之间相互借鉴,利用对方的某些制度、规则、经验的现象更是人所共知的。(注:参见大木雅夫:《比较法导论》,范愉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即将出版,第6章第2节,关于1922年苏俄民法典借鉴德国民法典的论述。)
一般来讲,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创立可以通过两种途径,一种是通过本国自己的实践,自己在实践中逐步摸索,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不断完善的过程,最后上升为法律;另一种则是自己缺乏调整某一类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情况下,通过借鉴外国的相关法律,弥补空白。相比较而言,前一种方法的优点在于扎实可靠,符合实际,但缺点在于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和精力,才可能形成符合实际的法律调整办法;后一种方法的缺点我们后面再谈,但其优点则恰恰可以弥补第一种方法的不足,避免代价高昂的法律实验。在当代世界,各国遇到的问题有共同性,解决共同问题的方法也有共同性。因此,各国在解决同一问题时,完全可以借鉴其它国家的行之有效的经验。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不吸收其它国家的有益经验,关起门来搞实验的经验爬行主义做法,是愚蠢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比较法学家把自己的学科看作是调整社会关系的武器库,把不同国家调整同一类社会关系的不同方法储存起来,供各国立法者、法官、律师和法学教授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二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外国经验、外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注: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页。 )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也是我国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所总结的一条十分宝贵的历史经验。对于比较法学,这条经验更具有特殊的意义。
在比较法的历史上,一个国家借鉴、吸收、移植其它国家法律制度的情况举不胜举。但同样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样的借鉴、吸收、移植,有的国家成功了,有的国家失败了。60年代美国的法律与发展运动,曾经把哈佛、耶鲁、斯坦佛和威斯康星大学的一些名牌教授派到第三世界国家,援助那里的法律改革。就学问而言,这些教授的法律知识都是一流的,他们帮助秘鲁起草了秘鲁的统一商法典,并声称在技术上它超过了美国的统一商法典。 几乎是同时, 法国的比较法学家达维得(ReneDavid)也被派到埃塞俄比亚,帮助起草那里的民法典。此后, 他也声言,他所起草的埃塞俄比亚民法典在技术上超过了100 多年前的拿破伦民法典,但结果怎样?它们在秘鲁和埃塞俄比亚的命运都表明,这些技术高超的法典根本不能适应那里的国情。 (注:See
Intemationallegal Center,Law and Development, The Future of Law anddevelopment Research,Intemational Legal Center,New York, 1974;James A.Gardner,Legal Imperialism,American Lawyers andForeign Aid in Latin America,The Ur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0.)
上述实践涉及到比较法的另一个基本原理,即不能仅仅把法律制度理解为由规则和技术组成的体系。一种法律制度的优劣,不能由规范本身或其它国家类似的规范来评价,归根结底看它是否适应它赖以产生和发挥功能的社会关系。比较法的历史表明,同一法律规范、法律概念,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可能发挥不同的功能;而不同的法律规范、法律概念在不同环境下可能会发挥相同的功能。而法律规范、概念的功能的发挥,又有赖于其它社会调整措施的配套。(注:See K.Zweigert &
H.Kotz.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Law,Vol.1.Clarendon
Oxford press,1987,p.31—33,M.A.Glendon,M.W.Gordon & C. Osakwe,comparative Legal Traditions,West Publishing Co,1985,p.12,R.S. Miller, APPles
vs
Persimmons -Let's
stop drawinginappropriat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legal profession in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Law Review,Vol.17,No.3,July,1987,PP.201—204;朱景文《从规范的比较到功能的比较》,《法学家》1993年第2 期。)正是由于有上述种种条件的限制,所以在一种社会环境中能够很好地运作的法律制度,在另一种社会环境中可能很难达到同样的效果。这也就是一些学者这些年来反复讲的“南橘北枳”的道理。(注:参见王晨光上引书,第219 页。)回顾近年来的我国立法,其中许多都参考了外国的相关立法,为什么有的效果明显,有的效果不明显,有的甚至产生负效果,除了现在人们经常谈到的执行机制和人们的法律意识方面的原因外(其实这方面的问题也属于立法时应该考虑的立法的社会环境问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立法是否符合中国的实际。不错,立法需要借鉴外国经验,需要增加科学性,需要法学家参与,但它们的最终目的和检验标准,都只能是中国的实际。否则,它最多不过是一张纸。
三
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形势与70年代末、80年代初相比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全球化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它为比较法的大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机遇,也为比较法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挑战。
2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使我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具有了更多的全球色彩:在经济领域,我国对外贸易已经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38%,成为世界第十大贸易国;我国的平均关税已经由80年代初期的40%下降到18%;连续多年我国成为世界仅次于美国的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和接受世界银行贷款最多的国家;随着入关谈判的进程,我国面临着不得不对国内的现有产业结构及有关法律进行改革的问题;在政治领域,我国已经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面临着如何与我国现行宪法及其它法律的有关人权条款协调问题;(注:参见谷春德:《简评“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法制日报》1998年11月7日第8版。)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其他领域,环境保护、卫生、知识产权、社会保障等等,都面临一个如何协调国际标准和国内法律规定的问题。一方面,与国际的通行作法接轨,履行我国的国际条约的义务;另一方面,又要适合中国的国情,维护我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独立。实践证明,拒绝接轨,得不到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只能把自己排除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发展潮流以外;而盲目接轨,不顾各国现有的条件和改革开放的时间表,只能给各国经济与社会生活带来更大的混乱。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这方面的例证。我认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研究我国国内法与参加的国际条约之间的关系,并制定相应的对策,应该成为我国比较法学今后相当长的时期的主要任务。
作为研究不同法律制度之间关系的比较法学,当前它的另一个任务是研究法律全球化问题。法律全球化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国内领域,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一体化,随着争夺市场和投资的国际竞争的加剧,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和前苏联及东欧国家,出现了一股以市场导向的法律改革潮流。据世界银行的统计,90年代以来,已经有15个多边发展机构和20个发达国家参加到120个国家的400个有关法律改革方面的援助项目中。(注:See Mohan Gopalan Gopal(1996 ) ,"law and Development;Towards a Pluralist Vision",paper at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temational Law.)而这些法律改革的基本原则和最终目的就是增加法的可预测性、可计算性和透明度,即实现法治,以保证资本的跨国界的自由流动,保证世界范围内的贸易自由。为此,这些国家制定、修改或重新制定了投资法、贸易法、合同法、公司法、税法、金融法、知识产权保护法、反倾销法、刑法、行政法、诉讼法、仲裁法、律师法等等,使这些法律尽量满足投资者的要求。第二,在国际领域,世界银行(World Bank)、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世界贸易组织(WTO)在世界贸易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其目标不仅在于排除对外商的歧视措施,而且试图调节“国界背后”的政策内容和国内市场结构。世界贸易组织通过的以保障市场准入为核心的《服务贸易总协议》(GATS),《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 )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协议》(TRIMS)就是法律全球化的典型例证。 法律全球化的国内与国际领域又是相互渗透的,国内法律改革的潮流往往直接影响了国际法律秩序的变化,而国际法律规定又为国内法律改革提供了指引。(注:参见朱景文:《关于法律和全球化的几个问题》,《法学》1998年第3期。)
另一方面,全球化又对国家主权形成了严重的挑战。按照一些西方学者的观点,全球化意味着非国家化,即减少国家在国际资本、服务、商品、金融流动中的干预,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废除一切对外国资本的歧视措施,降低以至取消关税。经济全球化、非国家化以跨国资本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如果主权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民族经济,采取高关税等贸易保护措施,跨国公司会撤消投资,把资本转移到较少贸易障碍、适于其获取更大利润的地区。面对强大的压力,主权国家不得不作出让步。有些学者认为,这种强大的跨国资本力量正在取代国家,而形成一种全球资本主义的“利维坦”,任何公众力量和主权国家在它面前都显得无能为力。(注:关于法律全球化与国际化的关系,学者们有不同的意见。有的学者认为,法律全球化就等于国际化,它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行的法律制度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而变为国际性的普遍现象的过程。有的学者认为,法律全球化不同于国际化,法律国际化属于国际法领域,它与国家主权并不矛盾,如果主权国家认为某项国际法律规则不符合自己利益,它不可能在该国生效;而法律全球化则意味着非国家化,它要求排斥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保证资本的跨国界的自由流动。还有的学者认为,法律全球化实际研究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国际法是怎样被纳入到国内法之中。 See
Jost
Delbruck(
1993),"Globalization of Law,Politics,andMarkets—Implicationsfor Domistic Law—A European Perspective", 1 Indiana Joumalof Global Legal Studies 1-26; MartinStapiro( 1993) ,"TheGlobalization of Law",1 Indiana Joumalof Global LegalStudies 27—64;David M.Tmbek,Yves Dezalay,Ruth Buchanan &John R.Davis(1994),"Global Restructuring and the Law:Studiesof the Intemationalization of Legal Fields and the Creationof Transnational Arenas",Vol.44,2 Case Westem Reserve LawReview 407—498.)全球化作为一种经济力量,是不依任何人,包括主权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某种程度上,它表明资本的力量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它要冲破国境的界限,实行经济的一体化、非国家化。传统的、在一国范围内、属该国管辖、受该国法律调整的经济模式,由于跨国资本的介入,股份制的发展,受到了挑战,国家主权本身也受到了挑战。研究全球化形势下主权观念的变化,研究国家对经济活动的管理权限及管理方式方面的变化的理论意义,同样是当前比较法研究面临的新课题。
20年前的三中全会为我们确定了“解放思想,事实求是”的思想路线。正是依靠这条路线,我们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否定了文化革命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从而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开放的道路。20年后的今天,虽然国际与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我们相信,只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勇敢地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就一定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标签:比较法论文; 法律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国内经济论文; 全球化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