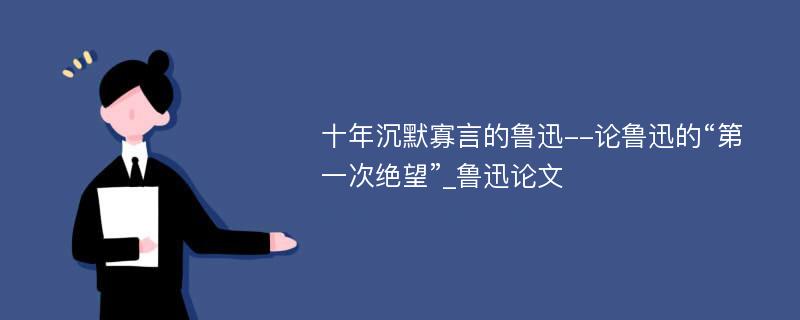
十年隐默的鲁迅——论鲁迅的“第一次绝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绝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09)12-0115-05
鲁迅与绝望,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话题。但学界谈到鲁迅的绝望,受《〈呐喊〉自序》等自述性文章的影响,多指向日本时期弃医从文的挫折,并以北京绍兴会馆的六年为其标志。其实在笔者看来,鲁迅的一生经历过两次绝望:一次如上所述,开始于日本时期,以北京绍兴会馆六年的沉默为标志;一次形成于《新青年》解体,以1923年的沉默为标志。对于鲁迅的第二次绝望,笔者已有专文论述[1],本文基于对鲁迅第二次绝望的发掘,回顾和重新梳理鲁迅的第一次绝望,意在把它放到鲁迅整体的精神结构和心路历程中来重新把握,连接起两次绝望的内在逻辑线索,并就其对于鲁迅的意义作出新的评判。
一
1909年,鲁迅提前中断了留学生活回国,广采博收、激扬文字的日本时期结束了。从是年回国到他发表《狂人日记》的1918年,约十年时间,鲁迅在国内辗转于杭州、绍兴、南京和北京,经历了从教员、中学堂监督到教育部官员的频繁转换的生涯,其间1912至1918六年,鲁迅只身寄居于北京的绍兴会馆,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寂寞”的S会馆时期。这十年,与他频繁转换的生活轨迹相比,笔述生涯则暂显停顿,比较于其前的慷慨激昂的日本时期和其后的“一发而不可收”的五四时期,显然独自构成了一个“心声”隐默的十年。《鲁迅全集》所收这期间所著文字,仅见1912年的《〈越铎〉出世辞》、《辛亥游录》、《怀旧》,1913年的《儗播布美术意见书》,另有1915年一篇、1916年一篇、1917年四篇、1918年两篇,除了1916年者为文牍“签注”,其它皆为据手稿编入的短篇金石、文献考订手记,写作月日不详。通观这些文字,1915至1918年者多为学术札记,是作者思想论战和文学创作之外的学术研究及个人爱好的文字遗留;1913年的一篇为发表于教育部部刊的带有行政呈文性质的文章;1912年之《辛亥游录》是日记性质的生物考察的记录,署名“会稽周建人乔峰”,《〈越铎〉出世辞》为《越铎日报》创刊绪言,《怀旧》为文言小说。显然,这些大约都不能算是所谓“迫切而不能已于言的”[2](P419)、主动积极的文字。因而可以说,无论从文章篇数还是性质上,言说者鲁迅的确进入了一个沉默时期。细加辨别,其中较能见出思想状态及其价值的文章主要为1912年的《〈越铎〉出世辞》、《怀旧》和1913年的《儗播布美术意见书》,并且整个看来,1912至1918年,此类文章呈逐年减少趋势。文章的减少与事务的繁忙或有关联,但对于以“心声”为“志业”的鲁迅,“心声”之消失该与心情(“内曜”之状况)有关。
无论对于人生还是社会,十年都不算短。揪心于中国之命运的鲁迅,即使在隐默状态中,也应有伴随近代中国的“仓惶变革”而波动的心情和思想的曲线。就是说,所谓隐默,对于鲁迅并非完全静止的状态,也经历了一个过程。这十年是急剧变革的十年,中国经历了辛亥革命、中华民国建立、袁世凯篡权、护法运动、二次革命及其失败、袁世凯称帝及其倾覆以及围绕它的种种闹剧、北洋军阀统治和张勋复辟等一系列大事,应该说是历史上的中国近代变革达到最高峰又开始急剧回落的关键时期。辛亥革命爆发并迅速胜利的1911年,鲁迅刚辞去在绍兴府中学堂的教职,此时的他已三十一岁,是他回国的第三年。鲁迅对辛亥革命的态度是复杂的。通过前文对鲁迅五篇文言论文的分析我们知道,日本时期的青年鲁迅,已经对民族救亡形成了自己的“立人”思路,“立人”思路形成于围绕中国之前途而激烈纷争的言论背景——主要是反清革命派和立宪保皇派之间的论战,在现实的政治立场上,应该说鲁迅偏向于前者,这从鲁迅与章太炎及同乡革命党的关系可以看到。但是,青年鲁迅的“立人”主张在对洋务派和立宪派进行批判的同时,其“重个人”而“张精神”的思路,对于当时注重行动而忽视思想启蒙的革命派也应是一个批判性的超越。因而,由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的成功,对于鲁迅其含义是复杂的:一者,从他的“立人”设计看,辛亥革命大概不是他理想中的革命;二者,辛亥革命颠覆满清的实际成效对于“立人”设计陷入困境中的鲁迅来说,无疑也是一次社会变革的巨大契机。因此,身在绍兴的鲁迅,听到辛亥革命成功的消息,反应还是颇为积极的。
鲁迅此时期的文字,较能见出其思想状况者,为《〈越铎〉出世辞》。《越铎》创办于1912年1月3日,为辛亥革命后创办的先进报纸,受到革命后接管绍兴的都督王金发的资助,得到鲁迅的大力协助,此篇为鲁迅应邀而写的创刊词。既为《越铎》立辞,自然立足于绍兴,而视野则在整个民族的兴衰。开篇从绍兴历史人文入手,赞颂“于越”自古地灵人杰,这和早期五篇论文一样,注重人文传统的梳理。然而,“世俗递降,精气播迁,则渐专实利而轻思理,乐安谧而远武术,鸷夷乘之,爰忽颠陨,全发之士,系踵蹈渊,而黄神啸吟,民不再振。辫发胡服之虏,旃裘引弓之民,翔步于无余之旧疆者二百余年矣。”[3](P39)文言语式,直接承接了日本时期的文风,“黄神啸吟”一语,早见于1903年之《中国地质略论》和1908年之《破恶声论》,“实利”和“思理”(“神思”、“精神”等)的对举,亦承接了五篇文言论文的思路。显然,“鸷夷”、“辫发胡服之虏,旃裘引弓之民”和“索虏”皆指辛亥革命推翻的满清,鲁迅的表述说明,他之对于对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统治,是大快于心的,这正符合鲁迅青年时期强烈的民族情结。文章申发创刊原委:“爰立斯报,就商同胞,举文宣意,以翼治化。纾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而吾人公民之责,亦借以尽其什一。”[3](P39-40)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话中的“自由”、“共和”、“天权”及“公民”等等,都属启蒙主义的政治观念,曾经是鲁迅站在1 9世纪末个人主义立场试图加以超越的对象,但在这里,成为其直接倡导的关键语词。个中原因,笔者认为不是鲁迅思想的一种退步,而可能在于:其一,鲁迅起初并非站到启蒙主义的对立面,他援引施蒂纳等对启蒙主义诸观念的批判,既有学理层面,亦有对现实的针砭;其二,这些都是辛亥革命的口号及目标,鲁迅的运用是对这些观念的实践层面的肯定。但不管怎么说,鲁迅此处对启蒙主义政治观念的充分肯定,与他几年前在日本的批判与主张确实有一些距离,我觉得,在《〈越铎〉出世辞》中,鲁迅并没有把自己的所有见解和盘托出,换言之,鲁迅面对现实在实践层面对辛亥革命诸观念的呼应,并没有触及他心中对中国革命的真正设想。如果是这样,则辛亥革命对于鲁迅,是他在理念上并非完全认同但却因带来巨大的实际成效而被他视为中国变革的巨大契机的一次革命,因而,他在现实行动中充分认同的同时,在心中一定有着自己的距离感吧。
鲁迅一生对“民国”有着很深的感情,并实际参与了辛亥革命胜利后的建国实践。1912年2月,鲁迅受时任民国教育部总长的同乡蔡元培之邀,赴南京任职于新建立的临时政府教育部,5月初又随部北迁至北京。鲁迅从南京到北京的为宦历程,正伴随着辛亥革命的成果一步步被侵蚀的过程,亲眼目睹了一次轰轰烈烈的革命如何渐渐被蚕食的经过——袁世凯称帝、护法运动失败、二次革命失败、军阀篡权、张勋复辟……。身为袁氏政府的一名职员,这些几乎是发生在鲁迅身边的事情,但在他当时的文字中,却很难找到对这些事件的记录,仅在1916年6月28日袁世凯出殡日,日记中记下:“袁项城出殡,停止办事”[4](P224)。鲁迅不作文字记录,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暂停了笔述的事业;另一方面伴随着的应是内心中深深的失望,一场他虽不完全认同但曾经寄予很大希望的革命,终于在他的身边流产了。正如他后来回忆的:“经过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二次革命、张勋复辟,看着看着,逐渐消沉、颓唐的得很了。”[5](P455)这段时期,正是鲁迅寄居北京绍兴会馆的隐默的六年。
二
鲁迅蛰居绍兴会馆陷入隐默的几年,对于鲁迅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本身就是谜一般的问题,历来研究者对此有种种说法。竹内好发现,这是鲁迅生平中“最不清楚的部分”[6](P44),并认为在这一时期中孕含着可称之为文学家鲁迅的基点的东西,竹内称之为“无”。竹内直观式的描述带有日本式的幽玄,其意不过是说,诞生于1918年的文学家鲁迅,就孕育于绍兴会馆时期,而所谓“无”,即来自于对政治革命的绝望而产生的自觉。通过分析《狂人日记》,他认为:“由于这种稚拙的作品表现了某种根本的态度而有其价值”[6](P48),声言在《狂人日记》背后,发现了鲁迅“文学上的自觉”,亦即“罪的自觉”,在这“无”的绝望之中,文学家的鲁迅才得以产生。伊藤虎丸的鲁迅在竹内鲁迅的思路中进一步延伸,伊藤同样重视会馆时期对鲁迅的意义,强调在会馆时期形成的文学自觉,但对这一自觉的内涵有新的发挥。他委婉地批评了竹内的文学—政治的对立观[7](P104-105),认为鲁迅并非因为由于政治绝望才回到文学,他认为《狂人日记》是“作者的告别青春,获得自我的记录”[7](P120-121),是“个的自觉”,即“确立了‘真正的个人主义’”,也是“科学者的自觉(即现实主义小说家的诞生)”[7](P122-123)。总之,落实在S会馆这个焦点,竹内和伊藤都试图在这一隐默时期发现鲁迅之成为鲁迅的秘密,把会馆时期看作真正的鲁迅得以形成的“原点”。但是,如若把这一次绝望绝对化,就会同样遇到一些难题:一是必须突出这次转变在鲁迅人生中的唯一性。竹内为了突出、强调鲁迅的文学自觉就是源于此时,不得不努力压低日本时期“弃医从文”的重要性,并着重对“幻灯片事件”进行解构,以强调鲁迅这时并未形成真正的文学自觉,而面对鲁迅在自述性文章中不断回顾、强调“幻灯片事件”的事实,又不得不花大量篇幅去淡化这些强调的意义;二是务必使鲁迅五四时期的“呐喊”成为他完全主动的行为。其实,鲁迅五四时期的“出山”,起初并非他主动的出击,而是在钱玄同劝说下的权宜之举。如果过于放大会馆时期的转变,则可能遮蔽前此的日本时期和后此的其它重要时期——比如说“第二次绝望”——在鲁迅人生和思想转换中的意义。
1922年12月的一个深夜,鲁迅编定完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取名《呐喊》,并作《〈呐喊〉自序》。这篇《自序》通过回顾小说创作的由来,把笔触延伸至从未触及过的绍兴会馆时期,使之成为鲁迅惟一一篇披露隐默十年的心路历程的珍贵资料。对这一资料的考察,从来都是鲁迅研究的重要依据和途径,而有意味的是,当鲁迅开始回顾自己的第一次绝望时,已陷入第二次绝望的时期[1],鲁迅对第一次绝望的叙述,无疑叠印了第二次绝望的色彩。《自序》是一篇糅合了鲁迅第一次绝望和第二次绝望的绝妙文本。
开篇申言,《呐喊》的创作来自于“不能忘却”的过去的“寂寞”,接着,作者回顾了自己从家道中落到南京求学、赴日留学、S会馆时期的经历。回忆是片断性的,所择取并祥加叙述的应该为作者印象中最深的事。正是在这里,作者第一次提到了著名的“幻灯片事件”、《新生》的流产和S会馆中的对话。竹内好为了突出后来S会馆六年对鲁迅的原点意义,怀疑“幻灯片事件”的真实性,日本学者也因没有发现所叙述的幻灯片而倾向支持竹内的怀疑。其实,没有找到并不能就推出其不存在,何况在日俄战争时期的日本,报刊杂志上也不难发现同类的照片。在鲁迅的叙述中,从这一事件的刺激到弃医从文的决定,其间的推理层层明晰,无论怎么说这都应是鲁迅理智作出的一个重大决定,而且,对这一过程的叙述在他后来的自述性文章中还经常重复提及,可见其事件的深刻性和真实程度。
《新生》的创刊是弃医从文决定的具体实施,但结果中途夭折,使这一举动蒙上淡淡的悲哀。作者有意克制而冷静的叙述,并自此转向对“无聊”和“寂寞”的描述: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2](P417)
“寂寞”在《自序》的后半部分成为关键词。因为对“寂寞”的描述紧接着《新生》事件,研究者多把《新生》的夭折看成鲁迅“寂寞”的直接或唯一的原因,而忽略了作者叙述的跳跃性和对其间重要情节的带过。事实上,《新生》失败之后,鲁迅并没有马上陷入“无聊”,作为补偿,鲁迅又有其它的计划,这就是《域外小说集》的翻译和出版,以及《河南》杂志上长篇系列论文的发表。应该说,这两大工程都是极为可观的,前者由周氏兄弟共同完成,从当时所撰《序言》看,鲁迅对此颇为踌躇满志,且《域外小说集》确实是中国近代文学翻译史上的里程碑之作;《河南》刊发的系列文章亦可视为鲁迅、周作人和许寿裳三人集体思想行为的一个重要部分,其思想价值无需多说。然而,这两件事情的结局对鲁迅来说同样是失败的:精心制作的《域外小说集》(上册)结果只售出20本,洞幽烛微、高瞻远瞩的五篇文言论文似乎没有受到任何人的注意。这样的结局,大概更使鲁迅感到“寂寞”和“悲哀”吧!因此,“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这句颇为模糊的话中,就可以理解为“无聊”并非仅仅源于《新生》事件,而是经过《新生》事件“以后”的一系列事件而引发的。这也让鲁迅有了新的自我反省。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2](p417-418)
日本时期的鲁迅曾以自己所称颂呼吁的“精神界战士”和“独具我见之士”自许,但《新生》及其“自此以后”的事情让他首先对自身能力产生了怀疑。这一怀疑同时指向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自身行动能力的有限性;另一方面是启蒙对象的不可改变性,而后者可能是鲁迅“反省”背后的真正潜台词。因此可以说,鲁迅的启蒙在日本时期已经面临着危机,这一危机源于对民众的可启蒙性及中国变革之可能性的绝望。
三
驱除寂寞的正途是寄望于民众的“内曜”而达到与先觉之士“心声”的共振,然而,“寂寞”的不可驱除正说明了绝望的事实。在S会馆,鲁迅白天赴教育部坐班,晚上回来抄古书、校古碑,就像是典型的旧式官吏,掩藏起内心世界,过着影一般的生活。此时,一个带有使命意味的人物出现了,钱玄同的到来打破了这种局面,二人并由此展开了一场关于“铁屋子”理论的交锋。
“铁屋子”理论建立在“铁屋子”“万难破毁”的大前提之下,传达的无非是中国已不可救药的绝望认识及其痛苦体验。“铁屋子”之“万难破毁”,是因为“铁屋”本身的牢不可破?还是因为“铁屋”中人的无法唤醒?鲁迅没有指明,但是,相对于唤醒者之主观性,这两者都构成了绝望的客观存在。
然而几个人既已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2](P419)
钱玄同这其实极普通的一句回话,却击中了鲁迅隐秘的一个心结,使他不由自主地转换了立场: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的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复他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2](P419)
“铁屋子”“万难破毁”的大前提,是由过去的经验归纳出的,而“希望”则在于“将来”,这是面对未来的一种价值态度。如果说前者是经验感受,那么后者则是一种理性信念。本来,“铁屋子”理论已经涵盖着“较为清醒的几个人”起来,由于大多数的注定不能被唤醒,就仍然没有破毁铁屋的希望的意思。这正是前述觉醒了的鲁迅又不得不“麻醉”自己的原因。而鲁迅之所以终于答应了钱玄同,是因为真正触动鲁迅的,是原本就交战于他心中的另一种声音——希望。“希望”对于鲁迅,终其一生都是一种信念式的存在。然而,鲁迅又说:“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们不惮于前驱。”[2](P419)这里强调“在我自己”,就是说在自己的意愿中,写作的第一个直接动机是作为外在因素的同情,而本应作为内在动因的启蒙主义的希望,却是由“同情”的外在因素所催生的行动的可能性结果。鲁迅在说到自己小说中的“曲笔”时,指出有两个原因:一是“须听将令”;二是“并不愿意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2](P419-420),即都是为了他人。所谓“曲笔”,在鲁迅那里是不如实去写,也就是说,“寂寞”是真实的,“好梦”是虚幻的,鲁迅对真实的保留其目的就是不唤醒他们,免得遭受“寂寞”之苦。这似乎又回到“铁屋子”理论的立场,无论是不把人从“昏睡”中唤醒,还是不把人从“好梦”中唤醒,两者都肯定了绝望的事实。看来,《呐喊》是一次勉为其难的出行。
总之,通过解读我们看到,在《新生》事件等一系列文学启蒙的挫折中,鲁迅产生了他的第一次绝望。绝望首先源自对自身能力的怀疑及其孤独体验,以及对民众可启蒙性的绝望,这就是“荒原”、“寂寞”和“无聊”感。随着国内政相的恶化,这一绝望愈加严重。钱玄同的出现成为一个契机,一次貌似平静的心灵撞击终让鲁迅把希望放到未来的“可有”之上,暂时中止了这次绝望,而开始了新的启蒙行动——虽然这是一次有保留的行动。
那么,S会馆时期寂寞的鲁迅,到底想了些什么?有什么新的觉悟?因为在这一时期找不到佐证的资料,研究者只能从后来的创作中寻找可能的信息。作为鲁迅隐默十年后写出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应藏有第一次绝望中的诸多信息,包括竹内和伊藤在内,对《狂人日记》的解读可谓多矣,并新见迭出。但我认为,“吃人”和“救救孩子”,仍然是该篇不可动摇的思想主题。《狂人日记》刚发表,许寿裳来信探问小说的真正作者,鲁迅在回信中谈到了该篇创作的思想动机:“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此成篇。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8](P353)对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的新发现,无疑把中国的危机放到了进化论的视野中来,进化视野的介入,突出的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人类进化过程中被淘汰的危机及其紧迫性。《狂人日记》渲染了一个整体性的“吃人”氛围,人与人均处在“吃人”和“被吃”的关系中,“狂人”所恐惧的,不仅是自己的可能“被吃”,更怕的是“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以及“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由此,“狂人”一再呼告:“你们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只要与“吃人”脱不了干系,即使侥幸不被人吃,也最终逃脱不了被淘汰的命运——这将是一个民族整体的命运。在这里,“吃人”被描述成这个民族的原罪,因而也注定了这个民族的宿命。“狂人”对“吃人的人”被淘汰的忧心,已远远大于自身被吃的恐惧,所以,这第一声“呐喊”并非个人的抒愤懑之作,而是发向民族的呼吁。不难看出,鲁迅的第一次绝望与第二次绝望不同,它不是源于个人生命层面的意义虚空,而主要是源于对民族危亡的忧心。
另外,笔者感到,鲁迅这第一声之“呐喊”,其实并没有完全喊出来。作者采取了一个非直接的表达方式,这从《狂人日记》的小说形式即可看出:其一,小说采取了象征主义的格式,通过“狂人”对外在客观世界的扭曲与变形,试图通向隐藏在“狂人”内心的真实。其二,与一般象征小说不同的是,作品提供变形的“狂人日记”本身,又是我们这个客观世界中某种真实的存在,它首先隶属于外在的真实世界,如果读者以为这是真的疯子日记,小说的象征世界就无法达成,且鲁迅又有意在文言小引中给小说盖上了一个确凿的现实印章。所以,鲁迅的第一声呐喊确实是隐晦曲折,吞吐再三。十年隐默中的沉思与洞察,使他发现了几千年的大秘密,那就是“吃人”。隐藏在温情脉脉伦理秩序中的“吃人”本质如果直接说出来,受害者也难以相信,而且反说你是疯子,故只有首先佯装疯子,才能说出真实。鲁迅常引庄子之言:“察见渊鱼者不详”,又常言他的话往往没有说尽。对于“吃人”的真相,鲁迅能够说的,只是后果的严重性——“给真的人除灭了”!最后的“救救孩子”,无异于一个民族的救命呼号。
危机意识和紧迫感确是鲁迅复出后文章的中心意识。在1918年8月20日给老友许寿裳的信中,鲁迅表白道:“历观国内无一佳象,而仆则思想颇变迁,毫不悲观。盖国之观念,其愚亦与省界相类。若以人类为着眼点,则中国若改良,固足为人类进步之验(以如此国而尚能改良故);若其灭亡,亦是人类向上之验,缘如此国人竟不能生存,正是人类进步之故也。大约将来人道主义终当胜利,中国虽不改进,欲为奴隶,而他人更不欲用奴隶;则虽渴想请安,亦是不得主顾,止能佗傺而死……此仆之所为乐也。”[8](P354)可以看到,绝望的事实没有改变,改变的是面对它的态度,但无论如何,这都是鲁迅的一次自我调整。把中国的灭亡放到生物进化论的大视野中,似乎使他暂时自我解脱地超越了此前绝望悲观的心态。其实,进化论视野中对中国灭亡的旷达只是表象,在同时期写的《热风·三十六》中,鲁迅说:
现在许多人有大恐惧;我也有大恐惧。
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2](P307)
生物进化论在此时提供给他的,是中国人的“生命”及其“生存”的真理性和紧迫性,因此不难理解,“生命”和“生存”,成为鲁迅五四时期言说的一个主题。
标签:鲁迅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域外小说集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周氏兄弟论文; 狂人日记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读书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 自序论文; 绍兴论文; 怀旧论文; 鲁迅中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