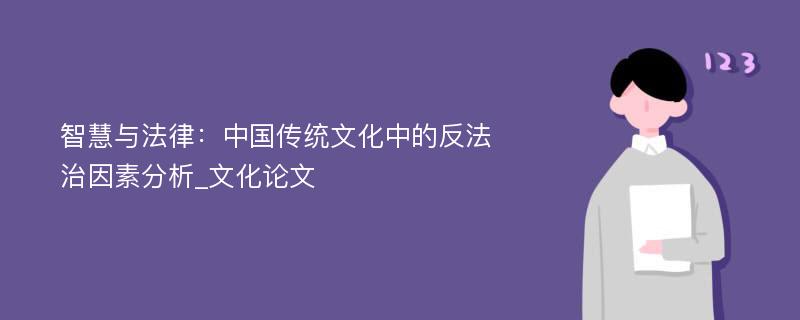
智谋与法律——中国传统文化中一项反法治因素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智谋论文,法治论文,中国传统文化论文,因素论文,法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060(2010)05-0064-06
在中国,有着异常发达的智谋文化传统,它源远流长,深入人心。以智取胜,而不是以力取胜,乃是高明的象征,为古往今来的中国人所崇尚。诸葛亮在中国社会长盛不衰的高知名度和影响力,乃至被神化,概源于此。其他如姜子牙、张良、刘伯温等,经由文学与民间传说的虚构创造,并因与中国人对智谋的崇尚心理相契合,而获得了超乎历史真实的名望与地位。智谋之士,糅合了历史与传奇、真实与想象,是活跃于中国人心中的一个星光闪耀的独特群体。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是他们共同的形象。有很多的人可能不知道张衡、祖冲之、蔡伦、沈括等历史上杰出的科学家、发明家。却极少有人会不知道姜子牙、张良、诸葛亮、刘伯温等智谋之士。关于他们算无遗策、用计如神的故事,广传民间,即便是贩夫走卒,也能娓娓道来。从古至今,研究智谋之学者络绎不绝,以兵书为中心,关于智谋的书籍可谓是汗牛充栋。如著名的武经七书《孙子兵法》、《司马法》、《尉缭子》、《六韬》、《吴子》、《三略》、《唐李问答》,以及《黄帝阴符经》、《孙膑兵法》、《将苑》、《百战奇略》等,包括在精英阶层与民间都有很大影响力的《鬼谷子》、《三十六计》,还有明朝冯梦龙辑撰的包含了民间谋略事例的历朝智谋故事集《智囊》、《智囊补》等等。至于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也主要是以其机变百出的谋略大集成而闻名于世。甚至《周易》、《老子》,也多有从智谋角度进行解读的。如《老子》,苏轼就认为其“此几于用智也,与管仲、孙武何异?”(《老子解》卷二)王夫之则说其“言兵者师之。……老氏者,持机械变诈以邀幸之祖也。”(《宋论·神宗》)章太炎也认为“老聃为柱下史,多识故事,约《金版》、《六韬》之旨,著五千言,为后世阴谋者法。”(《訄书·儒道》)一部二十四史,更是有多少人从朝代兴替、治乱之道,从君臣斗法、宦海沉浮,从宫廷内帏、夺嫡争宠中,总结出了登龙自保、尔虞我诈的权谋智术。如此发达而深入人心的智谋文化传统,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并对法律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此,我们应该有冷静、客观的分析与思考。
一
智谋,或称谋略、计谋,历来无明确的概念。班固曾对相似的概念“权谋”做过一个定义:“权谋者,……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也。”(《汉书·艺文志》)这里的“权”即“称”,本意为度量衡器具,引申为权衡、衡量、算计之意,非后人所臆解的“权力”、“权位”之意。班固的概念还揭示了战争与智谋的紧密联系,这点我们在后文中也将论及。一般认为,智谋是一种精心谋划的奇妙手段与方法,它要求以冷静理智的思维权衡各种形势与相关要素。而谋略、计谋、权谋与智谋,则是一组类似的概念,并无严格的意义上的区分。
为更好地理解智谋,需要厘清智谋与智慧的区别。基于中国崇尚智谋的传统,在人们一般的认知与理解中,往往混同智谋与智慧,把具有高超智谋的人视作智慧的化身。虽然,智慧本身也是一个歧见颇多的概念,但显然智谋与智慧有着重大的区别。至少,智谋与古希腊哲学意义上的“对智慧的爱”或“爱智慧”的“智慧”有着本质的不同。智谋与智慧都诉诸理性,但智谋以某种功利性与实用性为目的,追求效果的确定性;智慧则不同,作为人类精神之无限的理想境界,它不以某种功利性与实用性为目的,而是为摆脱无知而展开的对知识的追求,并以人类精神的终极意义与价值为其希冀实现的理想;智慧的本质在于求真,以诚实面对所认识对象为根本态度;而智谋的本质在于利益与效果的最大化,为达致目的,可以利用包括欺诈在内的各种手段,甚至在很多的情况下,真实与诚实恰恰是智谋的敌人。洛克的一个比喻也许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洛克曾形象地把计谋与智慧的区别比喻成猴子与人类的区别。他认为狡猾的计谋模仿智慧,但它与智慧相距最远,就像一只猴子一样只有人类的外表,没有人类的实际。所以,洛克在谈及如何培养儿童的智慧时说,应当使儿童习惯于获得关于事物的真实观念,把精神用在伟大的有价值的思想上,不要接近虚假与具有大量虚假成分的狡诈。① 在洛克看来,智谋是与狡诈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人类智力开出的虽令人迷醉,却是丑陋的花朵。
笔者认为,中国的智谋之学既非古希腊哲学意义上的智慧之学,更非究天穷地、探索客观规律与真实观念的科学。它起源于战争,是以人际关系为经纬,在政治、军事、外交、商业、人事关系等诸多领域中,为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对手利益最小化的目的,针对敌与友、利与弊、强与弱、众与寡、正与奇、虚与实、真与假、柔与刚、得与失、攻与守、动与静、进与退、成与败等诸要素,经过极其冷静、理智、周密的衡量、算计和谋划后而采取最具有实际效果的方法与行动的一种实用理性。作为一种实用理性,它首要关注的是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与途径,而非价值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所追求的是一条最快捷的通道与方式。甚至,即便其所达致的目的是正当的,其采取的手段也可能是非正当的。
二
考察智谋文化的源头,还需从人类早期的战争经验中寻找。研究中国法制史的都知道,刑的起源与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样,智谋的起源与战争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刑也者,始于兵。”(《辽史·刑法志》)智谋亦始于兵。
李泽厚认为“中国自新石器时代中期以来,充满了极为频繁、巨大、复杂的战争。”② 《路史》中则说“自剥林木而来,何日而无战?大昊之难,七十战而后济;黄帝之难,五十战而后济;少昊之难,四十八战而后济;昆吾之战,五十战而后济。牧野之战,血流漂杵。”(《路史·前纪》卷五)夏、商、周三代亦复如此,战争频繁、巨大而残酷。一方面,为使乌合之众组织成有战斗力的军队,须有严格的规范与纪律约束,并以严明的赏与罚为后盾。古代的刑罚便是由主管兵政的长官掌管。最早的法官,本身就是军官,如士、士师、司寇、廷尉。施行的刑具也由兵器充任。而最重的刑罚仍是以战争形式出现的大规模军事征讨与镇压,如《国语》所谓的“大刑用甲兵。”(《国语·鲁语上》)另一方面,长期、繁复、剧烈而又残酷的战争的现实经验,使得如何通过冷静、理性的战争谋划以最小代价而取得最大的胜利成为生死攸关的大事。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乃至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争谋略也因此得以产生与发展。至春秋战国,诸侯争霸称雄的战争更显繁复。根据《中国军事史》所集“历代战争年表”,春秋战国时期,有文字记载的战争共计发生614次。③ 与此同时,始于兵的刑与源于兵的战争谋略也发展到了一个更为高级、全面的理性化阶段。前者以商鞅在秦国的变法为代表,后者以孙子的《孙子兵法》为代表。
由于战争的结局关系到成千上万人的生死乃至一国一族的存亡,因此取胜就成了唯一被关注的结果,而过程的是非善恶、是否合乎道义就成了无关紧要的事。故而宋襄公不击半渡之兵被讥之为“宋襄公之仁”,为历代兵家所耻笑。所以,孙子说:“兵者,诡道也。”(《孙子兵法·始计》)战争就是双方指挥官在狡猾、机智、应变和诡诈方面的较量。故兵不厌诈,兵以诈立,战争谋略的核心就是欺诈。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是暗中算计,故曰“运筹于帷幄之中”,是不能置于阳光下的“阴谋”。与孙子同时及之后,研究战争谋略者众多,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并很早形成了系统而成熟的一系列兵法谋略专著。据《汉书》记载:“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汉书·艺文志》)如前所述的武经七书、《三十六计》等,在历朝历代都是公开或地下出版的热门书籍,并且注家甚多。
韩非子曾说:“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韩非子·五蠹》)兵家学说对智谋的崇尚,造就了中国人对智谋的迷恋,以至原本与军事争斗的关系最为密切,并运用到政治与外交斗争的计谋韬略,最终弥散到了整个社会生活与人际关系之中,成了从社会精英到普通民众的思维方式与内在精神之一。“军事是政治的继续,在这里,可以说是倒过来了:政治是军事的继续。人事关系就好象一场无情的战争,各人为着一己之利害而拼命争夺,人生就是战争。从而孙子、老子那一套兵书也完全可以适用在政治领域和生活领域中。”④
从而,兵家智谋文化,与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等一样,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秩序的重要构建者。它参与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与心灵,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而智谋文化的核心便是以战争的思维与法则来经营人生可能面临的一切,如政治、外交、商业乃至人事等等。
三
考察历史,诸如君王驭臣的南面之术,外交上的合纵连横,官场中的勾心斗角,宫帏里的夺嫡争宠,商场上的机变韬略等等,可以说是不绝于史书。至于人际交往上的斗智斗勇,乃至尔虞我诈,更是层出不穷。下面我们以历史上的商业以及讼师群体为例。
战国时期的大商人白圭,以擅长经商而名满天下,后世商人称其为“治生祖”,或称“人间财神”,被尊为商人的祖师。白圭总结自己经商成功的经验,认为善用智谋是其中关键的一条:“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也。”(《史记·货殖列传》)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谋士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覆灭吴国后,急流勇退,弃官从商,化名鸱夷子皮,来到齐国,以其卓越的智谋,在商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三次散尽财产,又三次成为巨富,“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史记·货殖列传》)他也被后世商家尊为祖师。战国末期另一位著名的商人吕不韦,用制造舆论、美人计和金钱贿赂等手段,做成了一桩桩一本万利的买卖。而吕不韦最成功的一桩买卖便是在邯郸结识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国公子子楚后,认为子楚奇货可居,遂一方面以金钱资助子楚,另一方又到秦国游说华阳夫人,用尽各种计谋促使秦孝文王立子楚为太子。子楚即位为秦庄襄王后,“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候,食河南洛阳十万户。”(《史记·吕不韦列传》)被后世认为是“谋圣”的张良,其最后结局有多种传说,其中之一就是他功成身退后改名换姓,以帷幄之术运筹于商场,成为巨贾。这一传说虽不可考,但传说本身却反映了人们把商场与智谋紧密相联的理念。
此外,本该坦荡正义的法律领域也遭智谋之术的浸淫而未能幸免,为智谋所“谋”。如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讼师群体,他们被讥称为“讼棍”,人们常常用舞刀弄笔、教唆词讼,混淆黑白、颠倒是非,诱陷乡愚、欺压良善,贿通官吏、恐吓诈财等贬斥之词来形容描述他们的作为。因为他们专营诉讼,所仰仗的不是事实与法理。而是谋略与诈术。清朝王又槐就曾斥责其“以假作真,以轻为重,以无为有。捏造妆点,巧词强辨。或诉肤受,或乞哀怜。……诡诈百出,难以枚举。”(《办案要略》)他们以战争的思维经营词讼,所谓“机有隐显、奇正;罪有出入、重轻。……得其法,则如良将用兵,百战百胜,无不快意。”(《折狱明珠·十段锦》)讼师学习词讼有专门的教材。这些教材在师徒间传授而不为外人所道,故被称为秘本。著名的词讼秘本有《新鎸法家透胆寒》、《新刻法笔天油》、《新刻法笔惊天雷》、《刀笔余话》、《萧曹遗笔正律刀笔词锋》、《刀笔菁华》、《折狱明珠》、《两便刀》等。书名中“透胆寒”、“笔天油”、“惊天雷”、“刀笔”、“两便刀”等的表述方式,便足以让人心惊。这些秘本不探讨律理,更罔论公平、正义,专教人的就是如何用各种诡计赢得诉讼。以《刀笔词锋》为例,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被编者称之为“法家无可奈何”的所谓“状谋大全”。状谋大全主要就是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串招式”,是教人如何串供套招的;另一部分是关于如何以各种计谋兴讼或应诉的范文汇编。事实上,被讼师们尊为祖师,春秋战国时期以善于雄辩、长于词讼闻名于世的邓析,即因专教人“以非为是,以是为非”,虽善辩,但不循正当之理,虽知法,却不合义理之道而被称之为“诈伪之民”。邓析有一个有名的操两可之词的案例。……洧水很大,郑国有个富翁不小心被淹死了,有人得到了富翁的尸体。富翁的家人想花点钱赎回尸体,但那人要价很高。富翁的家人找到了邓析,邓析说:“别管他,反正那人一定没地方去卖尸体的。”得到尸体的人很担忧,也去找邓析,邓析说:“你安心等待,反正这家人一定没别的地方再去买尸体的。”(《吕氏春秋·审应览·离谓》)邓析的后辈在狡智诡道上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有关的记载在历史典籍中俯拾皆是,单是《清稗类钞》中就有大量记载,试摘其中一例:“讼师龚某多诡计,有以醉误杀其妻者,盖酒后持刀切肉,妻来与之戏,戏拟其颈,殊矣。大惊,问计于龚,龚曰:‘汝邻人王大奎者,狂且也,可诱之至家刃之,与若妻同置于地,提二人之头颅而谐官自首,则以杀奸而毙妻,无大罪也’。”(《清稗类钞·狱讼类》)因为按照大清律,凡是妻与人通奸,本夫在奸所亲获奸夫、奸妇,登时杀死者勿论。这种逆节绝理、悖法妄为的狡智诡道确是令人心惊胆寒。虽然,词讼秘本中也有一些道义教化的堂皇之词,甚至讼师群体中也有很多为小百姓助讼申张道义的,但不立足于正道,唯图以奇谋诡计玩法弄讼,确是这个群体为人所贬斥诟病的缘由。
四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市场经济的不断扩大发展,似乎给各种谋略的施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智谋文化,在中国式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似乎更加具有了生命活力。商场如战争,为市场经济的各式主体所认同并津津乐道。几乎与建设市场经济的进程同步,图书市场兴起了“谋略”热。近几年,这一热潮也未见衰退,只是更显平稳。历史上的各种智谋之书一版再版,并被紧密联系市场经济进行了各种新的解读。其中,各式各样的所谓商战兵法充斥坊间,仅笔者近年所见就不下数十种,如《孙子兵法与商战智谋》,《孙子兵法与现代商战谋略》,《商战智谋奇、巧、绝》,《商战奇谋三十六计》,《三国谋略与商战秘诀》,《红顶商人胡雪岩经商智谋全书》),《孙子兵法与现代商战论》等等。还有一本专讲证券投资谋略的书,借用谐音题书名为《投“基”三十六计》。这些出版物,把商场视作战场,竞争视同战争。有的直接宣称“商者,诡道也”,有的提出要用“一计千金”来替代“一诺千金”,有的直接间接地教人如何用瞒天过海、借刀杀人、趁火打劫、浑水摸鱼、偷梁换柱、美人计、反间计、苦肉计等计谋来赢得市场,获取财富。更有甚者,不仅教人如何投机取巧,还暗示人们要通过依附权贵、行贿纳贡来赢得财富。同时,各种商战兵法与智谋也作为一门重要课程进入了管理学科的讲堂之上,许多名校的MBA和EMBA课程中都包含了这门课程。许多地方还开办了各种形式的所谓商战谋略培训班,且很受欢迎。如地处北京的某著名大学已开办了多年的以董事长、总经理为对象的“国学与商战谋略企业家特训班”。⑤
然而,我们都知道,市场经济同时也是法治经济。良好的法治系统和商业伦理是市场经济运行正常的基础。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一定是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有序经济。显然,智谋文化传统是与此相冲突的。
法律的功能之一是在于促使合作者、竞争者之间在关注、尊重彼此利益基础上的合理合法性的竞合,其目的在于促进彼此利益或价值的增加,其要害在于以增加自身的竞争力和素质为根本点,反对、禁止以损害对方利益为取胜、获利的手段,并进而促进某个领域或整个社会的利益及价值的增加,所期望的是双赢或共赢。而智谋之学,所崇尚的是在超出自己的实力之外,寻求致胜、获利之道。在自身力所不逮的时候,首要的不是通过提升自己的整体素质,增加自己的内在能量,加强自己的实力来赢得机会和最终的胜利,而是以策划、施行各种诡计、诈术以增加对手的困难,置对手于困境或损耗对手的实力来争取自己获胜的机会。以智取胜而不是以力取胜,往往以削弱、摧毁对手的实力为目标,施以所谓四两拨千斤的“巧计”、“巧劲”,来达到目的,而不是追求你强,我更强。所以,在中国,往往较少有双赢的观念和双赢的结果,最终的胜利者也往往不一定是实力最强者。
法律应当是良善、公正社会秩序的构建者。法治的社会是一个具有共同认可的、公开的规则和中立裁判者的有序社会。法律本身可以说是以正义为标杆,通过社会各种复杂利益主体之间的商谈、对话而确定彼此的权利与义务、范围与界限的集合体。良好的社会秩序,包括良性的市场经济秩序,可以说是社会各主体或市场主体之间的通过法律而商谈达致的一种共同认可的结果。公开、有序、规范是它的核心原则,必须遵行。而智谋之学,所重却在于如何在不讲规则与秩序中进行竞争和搏杀。智谋的最高境界就是无规则可寻。所谓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实者虚之,虚者实之,实者实之,虚者虚之,用而示之不用,能而示之不能。所追求的是越出常情,真伪莫辨,一团迷雾。所谓“兵者,诡道也”正是如此之谓。兵以诈立,智谋运用之妙正是在于诡道、诈道。公开、有序、规范完全是它的对立面。显然,这种不讲规则与秩序,更没有共同、公开的规则与公正、中立裁判下的竞争,与法治的精神可以说是完全相悖。
进一步地,作为诡道、诈道的智谋之学,更是与法律的核心价值理念——正义相悖。智谋的运用,一切以达致目的为标准,以利害关系为依归,以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为出发点,而忽视甚至无视对正义与良知的关注。从著名的三十六计中的一些计名即可明了此点,如瞒天过海,借刀杀人,趁火打劫,隔岸观火,笑里藏刀,浑水摸鱼,偷梁换柱,假痴不癫,上屋抽梯,反间计,苦肉计等。在这一利害原则下,为达目的甚至可以不择手段。早在春秋战国之时,就有所谓“仁术”之说,即作为一种高尚目的本身的“仁”,也可以成为一种“术”。当时著名的谋略家吴起,曾为士卒吮出了痈疮中的脓水。士卒的母亲听到后便痛哭不已,因为她知道,儿子也会象其父亲一样,为了感恩而效死命战死疆场。“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正是因此,后人批评吴起所为并非真正出自仁心,乃是一种“仁术”。庄子也曾敏锐地指出,真正践行仁义的人很少,而从仁义中取利的人却很多;有机心的人,利用仁义,只会造成诈伪。仁义已经成为了许多人贪求的工具。(《庄子·徐无鬼》)在这种为达目的不问手段的谋略观之下,美丽的女人常常被当作妙计来使用也就不足为奇了,所谓美人计是也。历史上以美人为计者比比皆是,在崇尚谋略文化的传统氛围中,历来大众的感受似乎也并不以此为耻。所谓著名的四大美女西施、王昭君、貂婵、杨贵妃,可以说是无不为韬略诡计所用,甚至有的是因此而闻名历史。她们都是那些讲解计谋的书籍中用来阐释美人计的代表人物,而犹以西施、貂婵为典型。现代商战中,美人计的影子仍然可以经常见到。
智谋的运用,关键在于通过最巧妙、便利、快捷的方法与手段达致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因此,只重视结果,而忽视或无视过程与程序的合理性、合法性与道义性是其重要的特点,其极端就是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因此,即便是智谋所“谋”的结果合乎道义(人们往往会以这结果的合理性、道义性来作为手段、方法与程序的不正当性的辩护理由),也是与法治的原则相冲突的。我们知道,法治的一项重要原则与精神就是强调过程的完备、合理以及程序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五
因此,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为国人所崇尚的智谋文化传统对包括市场经济秩序在内的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的建立所构成的扭曲与损害。智谋文化传统在本质上是与法治的精神相悖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项重要的反法治因素。
吴敬琏先生曾通俗地把市场经济分为好的与坏的,并认为好的市场经济应当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是由诸多要素组成的一个复杂系统,其中包含有两个核心理念:一是机会均等,一是诚实信用。而这两个理念要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得以真正实现,就必须依赖于一个良好的法治的环境。然而,机会在现实中并非人人均等,在一个公平正义的实现机制缺失的社会,机会除了可以被专断的权力侵占,被豪强掠夺,被金钱收买,还可以被诡道诈术骗取。从“兵者,诡道也”到“商者,诡道也”,谋略的手段千变万化,多种多样,但欺诈而不讲诚信是其不变的法则。在视利益竞争的另一方为敌方,没有公开、公平规则的规范与制约,缺乏中立、独立裁判者的参与,唯以利益为依归而无正义价值之追求的谋略竞技场上,各种形式的关系主体是不能讲诚实信用的,因为诚实信用者面临的将是失败与灭亡。今天,我国在推进市场经济进程中所面临的,并且日益向全社会各领域弥散的诚信缺失问题,虽然其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但与中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至今仍为国人所津津乐道、身体力行的智谋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市场经济,乃至整个社会中诸多混乱现象的根源与世人的攻心伐智、竞相伪饰,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
孟德斯鸠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中曾这样评述古代中国的法律与商业贸易环境:“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这特别表现在他们从事贸易的时候。虽然贸易会很自然地激起人们诚实的感情,但它却从未激起中国人的信实。……中国人贪利之心是不可想象的,但法律并没想去加以限制。一切用暴行获得的东西都是禁止的;一切用术数或狡诈取得的东西都是许可的。……在中国。欺骗是准许的。”⑥ 无独有偶,黑格尔也同样指出了这方面中国人不道德的一面:“他们以撒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朋友欺诈朋友,假如欺诈不能达到目的,或者为对方所发觉时,双方都不以为可怪,都不觉得可耻。他们的欺诈实在可以说诡谲巧妙到了极顶。”⑦ 孟德斯鸠与黑格尔的看法未必完全公允,但却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在对智谋相对热衷的中国社会,国人对机巧诡计有着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人们对此有一种厌恶乃至痛恨的心理,把其贬之为“奸巧”、“阴谋”;另一方面,人们又总是渴望自己也能通过各种奇计妙招所达致的轻巧捷径来获取成功的果实,或者至少人们对机变权谋显得比较宽容,且容易忍受。孟德斯鸠与黑格尔的话,虽然刺耳,却值得我们深思。今天,如何消除智谋文化传统对国人正直心灵的蔽掩与正当行为选择的不良影响,让所有利益的竞争置于公开、公平、公正的规则与裁判之下,以诚实信用的声誉与自身强大的实力为依靠,从而建立起能达致双赢、多赢、共赢的公平正义之市场秩序、社会秩序,当为我们努力的方向。
收稿日期:2009-12-08
注释:
① [英]约翰·洛克:《教育漫谈》,杨汉麟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第132页。
②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第1版,第78页。
③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军事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12月版,附卷“历代战争年表(上)”。
④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第1版,第99页。
⑤ http://www.szceo.com/html/open_class/20060829/200608292357180250.html。2008年9月19日查询。
⑥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11月第1版,第316页。
⑦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2001年8月第1版,第13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