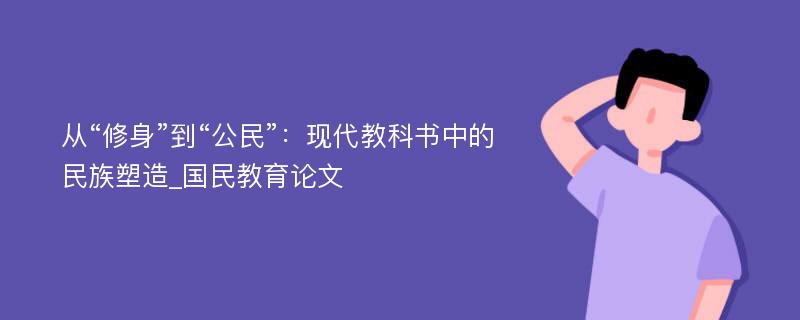
从《修身》到《公民》:近代教科书中的国民塑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书中论文,近代论文,公民论文,国民论文,教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教科书在近代中国的产生,是近代社会变迁的结果。它从诞生之时起,就烙上了大变迁时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印痕。整个近代史,建立民族国家的诉求是精英与民众共同关注的最宏大的时代话题。教科书密切参与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多层面多角度体现了国家权力意志。因而可以说,近代教科书也是体现“民族国家”这一宏大叙事的历史文本。在这个话语下,国民教育的重要性得到充分凸显,从而深刻体现了中国从晚清开始蝉蜕传统、融入新时代的特征。而晚清时期的修身教科书向民国以后公民教科书的转换,正是展现这一历程的生动模本。
一、从修身教科书看晚清的国民教育
修身教科书是晚清才出现的新事物。因为传统社会,“我国之教初学,向用《大学》、《中庸》等书”,[1]除了几种童蒙读物外,还有诸如《颜氏家训》、《朱子治家格言》之类。传统时代的小学教育,“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2],其中反映出的传统道德教育之核心,正可以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简单概括。晚清社会变迁,新观念、新思想的冲击,必然使传统道德教育面临着挑战,迫使它注入新内容,展示新面孔,显现出从传统到近代的过渡色彩。
晚清时期,读经与修身是官方规定的承担道德教育重任的两种科目,“前者所以严古尊圣,而后者所以达用适时”[3],这是它们的区别。在国人自编的修身教科书出现之前,修身教科书实际上就是要求以经书为本,讲授人伦道理。对修身教科书的选用,清政府是有相关规定的。1902年京师大学堂编书处成立时,对修身伦理课本的编纂,“拟分编修身为一书,伦理为一书,均略取朱子小学体例分类编纂。”[4]同年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中规定,中学堂要求本《论语》、《孝经》之旨趣,授以人伦道德要领;小学堂应取《曲礼》、朱子《小学》浅显易懂者教授。1904年1月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初等小学堂要摘讲朱子《小学》;高等小学堂讲《四书》之要义;中学堂摘讲陈宏谋五种遗规:《养正遗规》、《训俗遗规》、《教女遗规》、《从政遗规》和《在官法戒录》。严格讲,这些教本都只是将传统内容放进新科目下,新瓶旧酒,不能算是近代教科书。但此时在中国的一些学堂中,已经开始使用新式的修身教科书。因为1903年京师大学堂颁布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其中有教育改良会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高等修身教科书》;[日]元良勇次郎著、广智书局本《中等教育伦理学》;还有[日]井上哲次郎著、樊炳清译、江楚编译局本《伦理教科书》等。这些修身教科书显然不再是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教本,这说明至迟在20世纪初,中国已有学堂开始采用近代意义上的修身教科书。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译自日本和欧美的修身、伦理等教科书对中国近代性质修身教科书的诞生起到了催化作用,但它在中国社会的生存根基并不牢固。中国人更多的是学习外来事物、改造传统教本。因此,近代中国的修身教科书就更多地表现出与传统教育的关联与承续,而不是断裂或移植。
晚清以后,修身与读经,开始承担不同的教育任务。严复就曾建议过,将嘉言懿行另列修身课本中,与读经分为两事。修身科比之经书较为简单易懂,易被儿童吸收,所以渐渐承担起了道德引导的历史重任。有关读经的教本在道德教育方面开始向修身教育体例靠拢:“我国道德之书,莫备于经。特陈义过高,幼年骤难领解。本书采取群经中合于日常须知之道德,分对己、对家、对群三大纲,讲经义各按德目依类列入;另撰教授法,纯用通行官话。教员按书讲授,兴趣横生。”[5]其中这“对己、对家、对群三大纲”,就是晚清修身教科书中最通行的内容体例。
修身科,“所以示道德之方法者也”[6](P1)它担负着“启德育之径,敦蒙养之基”[7]的任务。晚清的修身教科书,将道德教育和国家观念的教育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小学教育之修身科,所以达道德教育及国民教育之目的者也。欲国家文化之进步,不可不谋国民程度之进步;欲国民程度之进步,不可不养成国民之道德心;欲养成国民之道德心,不可不令国民修身。”[8]晚清修身教科书表现出了传统时代不可能容纳的国民教育内涵。其内容特点主要有如下三方面:
1.以孝为首的纲常伦理观念。晚清修身教科书仍然传输着传统社会的孝道观念和三纲五常的等级秩序。在一种《中学修身教科书》中,第一章开篇课文就是:
吾国圣人,以孝为百行之本。小之一人之私德,大之国民之公义,无不由是而推演之者。是以有五伦之教,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6](P1~2)
该教科书每叶的书眉上都标有该章的若干主题,第一章从道德说起,接着讲了修己之道、五伦之教、十义之教,之后论行之于社会和行之于国家。晚清修身教科书中有所增进的是,联系西方的道德教育,将其与传统相比较。比如另一部修身教科书,其总纲中写道:
道德之要,我国以仁、义、礼、智、信为五常,西洋以智虑、正义、勇气、节制为四纲,今准之以智、仁、勇者,因教育之事,智育德育体育,遵道而行,最为简明切实,而与五常四纲,亦互相包括。[9](P2)
小学修身教科书亦首重孝行。比如《最新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第一课为“孝行”,讲述古代黄润玉少时孝敬长辈,长大终成大儒的故事,并辅以插图。[10]以孝为核心,自然重视家族观念。多数修身教科书中会专列一章,论述宗族、父母、子女、夫妇、兄弟姊妹等专题。这些课文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孝道”为核心的伦理观念的补充。
晚清修身教科书中颇有特色之处还有对“仆役”的论述:
总地讲,
一家之有主仆,亦如一国之有君臣,“忠实驯顺者,仆役之务也。
具体来讲:
为仆役者,宜终始一心,以从主人之命。不顾主人之监视与否,而必尽其职,而不以勤苦而有怏怏之状。同一事也,怡然而为之,则主人必尤为快意也。若乃挟诈慢之心以执事,甚或讦主人之阴事,以暴露于邻保,是则不义之尤者矣。
“主人”的义务则如下:
是以为主人者,亦常存哀矜之心,使役有度,毋任意斥责,若犬马然。至于仆役俸银,即其人沽售劳力之价值,至为重要,必如约而畀之。[11]
有关孝道和仆役的课文,说明晚清社会在伦理层面上,基本保持并延续了传统社会的特点。
2.个人修养。晚清时期对学生的道德要求,多不外乎传统道德中美善的方面,只是以“我国古圣贤道德之原理”加上“东西伦理学大家之学说”,从而显示出近代社会变迁特色。
教科书中首先肯定,道德修养不是大而空泛的话题,“道德之本,固不在高远而在卑近也。自洒扫、应对、进退,以及其他一事一物一动一静之间,无非道德之所在。”[6](P15)因此,道德教育应从小事做起,培养良好的个人习惯。比方说,做人要诚实、正直、勇敢、谦虚、知耻、好学、能立志;生活要节俭、要注意仪容;待人要宽厚礼让、尊长爱幼等等。这些品格是被中华文化一直认可的良好品质,到晚清时仍然是教育的材料。对于传统社会提倡的某些个人道德,晚清修身教科书中给于肯定。比如仁义礼智信,克己、自制等品格,尤其是“忠恕”,《中等修身教科书》中讲道:人不能孤立存在,于一身关系重大者有国、家、他人、社会和万物,而“凡所以致其修者,一曰知、二曰仁、三曰勇,一以忠恕贯之,而基始于诚。”[9](总纲第1页)这说明了晚清时期道德教育对传统的肯定和延续。
3.国家社会观念的培养。晚清修身教科书中较为注重对社会、对国家的道德意识培养。例如强调对社会要注重公益、慈善,珍惜名誉,存博爱之心,对国家要认真履行国民义务,保有为国捐躯之理念:“国无事,谋保公众事业,不使权利为外人所夺。国有事,轻生以赴义,以救危亡。”[12]
由国家而国际、全人类,修身教科书中还突出外交启蒙教育。蔡振所编著的《中学修身教科书》第四卷,专门有一章讲“国际及人类”。课文叙述国际道德进步史,论述战争时期道德的特点,还涉及红十字会等知识,教育国民当知外交和国家自卫和权利。
修身教科书中的道德修养教育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强调个人对于国家的意义,这主要表现在有关的政治教育中。比如《蒙学修身教科书》中有“政治”一课,课文讲道:“天下无无政治之国家。然不合公理之政治,与无政治等。故同一政治,比民之多数以为可者,方著为令。”课文后小字讲解:“次课言政治以合公理为断。”[13]这里“政治”在词义上显然是接受了近代涵义,体现了晚清时人对近代政治概念的理解和接纳,说明晚清教科书已经能够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社会变迁。
晚清时人已有讨论德育、智育、体育三者的关系。严复指出德育教科书的不可或缺,强调“德育尤重智育”。”[14]应该说,知识界舆论对于道德教育多持肯定态度,但实际教育效果却不容乐观。修身科是晚清学堂列于首位的必修科目,但由于政治动荡使教科未能规范,弊病丛生,修身科的讲授往往落于空文,且教且忘,学校教员常常慨叹:“修身科最无谓,最无效”[15]。但是,由传统向近代的社会转型应该是艰难的、缓慢的,即便是从这并不尽如人意的教育中,我们仍能明显感受到近代化微风的吹拂,看到中国人近代国民意识的萌芽。
二、民初国民性改造和20世纪30年代的公民教育
近代中国屡受列强欺凌,“修齐治平”的道德指向已经无法适应时代变革、担负起引导中国走向近代的历史重任。许多有志之士深感唤醒民众、和改造国民性的重要。正如蔡元培所说的中国国民性之柔弱,如问小学生“有人侮你,你将何如?”学生多半回答“让之”。[16]而近代中国的国民,更需要以竞争精神来挽救衰颓的国势。军国民主义在晚清就已经是一种有力的教育思潮,民国建立后,在蔡元培的倡导下,教育宗旨加入了“军国民教育”的内容。反映在教科书中,有关“去争”、“让功”等课文减少消失,代之的是竞争、尚勇精神的灌输。民初的教科书中,常有许多学生赛跑游戏的课文:
群儿集运动场,为竞走之戏。一儿奋力争先,夺得红旗,众皆拍手。[17]
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以卫国为由确定尚武宗旨,北洋政府的《特定教育纲要》中专门强调,高等小学以上体操科,应注重兵式;此后教育部也多次规定,男生要加授兵式体操。这一时期的教科书中就有很多关于兵式操练的课文。比如《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第三册第二十一课,为《兵队之戏》,课文中一队儿童肩扛竹刀木枪,习为兵队。类似的课文在民初各种教科书中都较为常见。这些都是使儿童树立争先意识,培养其向往军人的昂扬之气。民初还有的地理教授法指出,该书“要旨在使儿童知地球表面及人类生活状态而于人种竞争之关系”[18],这说明教科书中体现出来的“竞争”,是在认识到中国民族性弱点及其与近代国情之关系的背景下,自觉倡导和灌输给学生的精神气质。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后惨状使中国人对武力产生了不信任,“军国民教育”的口号受到非难,教育宗旨中一度消除了这种提法。但由于国内军阀混战,外国侵略步步深入,军事教育思潮因五卅运动而盛大。1925年全国教育联合会上决议,高中以上学校一律施行军事训练,小学及初级中学施行强迫童子军训练。[19]此后由于抗日战争局势的压迫,军国民教育实际上持续了整个近代时期。
20世纪30年代,因为国民党政权的建立,国民教育的重点有所转变,“公民”教育得到突出。
何谓公民?“能够享受法律上规定的权利,担任法律上规定的义务的人民,叫做公民。”公民的资格有下列五项:“一、年龄;二、户籍;三、财产,指动产和不动产的价格说的,就是必须有若干财产,才得做公民。四、学识,指学校毕业的程度说的,就是必须毕业于某等学校,才得做公民;五、经验,指曾任公职的等级说的,就是必须曾任某种公职,才得做公民。”[20]由此可见,国民党政权下的公民是有资格限制的。这些条件,并不是任何一个中国民众都能达到。这种限制充分表现了国民党政权下中国政治文化对于“公民”理解的历史局限。
为什么国民政府要提出公民教育的口号?“公民教育的意义,为培植社会上有效率的个人,合全体个人有效率的社会行为,以达到社会效率的目标。”公民教育的目标则是:“发扬中国民族固有的道德,以忠孝、仁爱、仁义、和平为中心,并采取其他各民族的美德”,包括公民的体格训练、德性训练、经济训练和政治训练。[21]这就传达出了国民政府“恢复旧道德”的用意:公民教育,不是为别的,是回复到传统时代道德约束下的国民性。有《恢复旧道德》的课文讲道:“中国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而“固有的旧道德,首忠孝,次仁爱,次信义,次和平”。[22]旧道德中,忠孝的地位是最重要的。
实际上,恢复旧道德的提法和忠孝的道德要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理解、无可厚非的。孙中山特为“忠孝”意义的时代区别作过说明,指出现在的“忠孝”不同于古代的“忠孝”:“古时所讲的忠,是忠于皇帝;现在没有皇帝,便不讲忠字,以为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那便是大错。现在人人都说到了民国,什么道德都破坏了,根本原因,就是在此。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上说,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23]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特殊国际环境下,国民政府以此种道德标准来要求中国民众,不能不说是有其一定统治目的的。
国民政府规定,公民教育要以孙中山三民主义为主要内容。在一种公民课本中,有一课为《信任政府》,这篇课文的末尾是学生们齐呼口号:“拥护我们的政府!信任我们的政府!政府努力替我们做事!政府努力实行三民主义!我们的政府万岁!”[24]可见三民主义对于公民教育的指导作用。
事实上,国民政府的公民教育不仅是政治教育,它容纳了广义的社会、家庭、职业和个人修养等内容。有关教材研究的著作指出,公民教材应包括如下几方面:1.公民知能,如党旗国旗教育和民权初步、公民权利与义务等;2.社会关系和活动,如家庭、邻里、学校生活及公共场所,还有地方自治、市政教育等;3.道德故事,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道德故事;4.三民主义大要。[25]而1934年的《复兴公民教科书》这样安排其4册教材的内容:“第一第二两册研究总理遗嘱、道德故事、民权初步与三民主义,使儿童彻底了解三民主义的精神,期养成三民主义共和国的良好公民。第三第四两册分述家庭、社会、风俗、经济、权利、义务、职业、政治、法律、地方自治、时事研究等重要问题,使儿童深切明口公民对于社会的种种任务。”[26]可以看出,公民教育是前此道德、政治教育的延伸。
国民政府对于公民教育是极为重视的。我们随意抽取一种课本,比如1933年世界书局出版的《初小国语教学法》第七册[27],这册教材一共有40课,课文的性质包括公民、党义、历史、地理、自然、文艺、卫生等,每课性质为其中一种或兼有数种,教材的编排者已经对此做出了细致安排。其中:
具有公民性质的课文 共17课 占42.5%
具有党义性质的课文 共5课 占12.5%
具有历史性质的课文 共16课 占40%
具有地理性质的课文 共5课 占12.5%
具有自然性质的课文 共11课 占27.5%
具有文艺性质的课文 共10课 占25%
具有卫生性质的课文 共1课 占2.5%
很明显,在这40课中,具有公民性质的课文是最多的。
“公民”课程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几年后就被取消,“公民”、“党义”等内容都要求融入“社会”一科,“社会”科就成为包纳公民、历史和地理的思想政治教育科目。“公民”向“社会”的转变从某种程度上表明,国民政府试图以长远的教育眼光,培养宽广、宽容的国民心态。商务出版的一种社会教科书这样说明其编辑宗旨:“于适合儿童教育之范围内尽量提倡党义”,“极力灌输革命的与进步的思想,造就实用的与科学的技能,养成平民化与团体化的性格。”[28]这表明社会教育的总方针延续了公民教育的基本原则。
公民科的内容融入社会科后没有发生多少变化,而作为社会科一部分内容的历史科,其教材要求包括的内容有:纪念日的历史事实,纪念地纪念物的历史事实,名人故事,国耻史,初民生活,社会组织的演进,中国政治上和中华民国开国以来的历史问题,关于民族的中外历史大事,关于民权的中外历史大事,关于民生的中外历史大事,以及时事。地理科教材应该包括:乡土地理,我国的地理情形和世界大势的关系,和关于地球的知识等等。[29]很明显,历史和地理在知识点上都要求围绕对国家、社会的了解和培养公民意识来取材,不能仅仅是单纯历史、地理知识的灌输。社会科教育一直持续到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终结。
结论
修身本是儒家宏大抱负的起点,它是传统时代以“平天下”观念为指向的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在教育内涵上则以对儒家经典的学习、阐发和身体力行为主。然而晚清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颠覆了“修齐治平”的儒家理想,天下观念逐渐开始被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所取代。面对这种尴尬的境遇,修身教育不得不选择了摆脱经学笼罩、迎接近代国民教育的路径。在这个过程中,传统修身教本逐渐剥离了经学教材,在时代大潮中、在学习日本和欧美修身教科书的过程中改变自身,表现出在内容上与传统道德不离不弃、又掺杂了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特点,国民教育自此开始描绘出第一笔近代色彩。
而20世纪30年代“公民”及其后“社会”教育的出现,标志着晚清直至民国20年代末的“修身”教育断裂终结。这种历史的替换有其必然性,正如当时有教育界人士指出的,修身科有许多弱点:范围太狭;标准太旧;太重学理;教材支配不适当;不能造成法律的观念等等。[30]总而言之,修身科从内容到形式都已落后于时代,不能满足社会前进对教育的要求。
当然,不无遗憾的是,“公民”教育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无法获得充分的生长空间,因而更多地带上了政党色彩,表现出历史局限性。而且,它在中国基础教育历程中就像是倏而划过的流星,没能在中国教育史和近代国民性改造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社会环境条件的不允许,另一方面也有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内在理路因素。即使如此,我们仍然不能轻视这一短暂光芒对于中国近代国民教育的重大意义。正是“公民”教育的出现、实施,中国国民教育才在完全意义上成为近代国民教育,中国国民才真正走向近代。因此,“公民”教育对于近代中国的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起始意义。这一实践更为后人留下了许多思考空间和经验教训的源泉。
标签:国民教育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社会论文; 道德教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