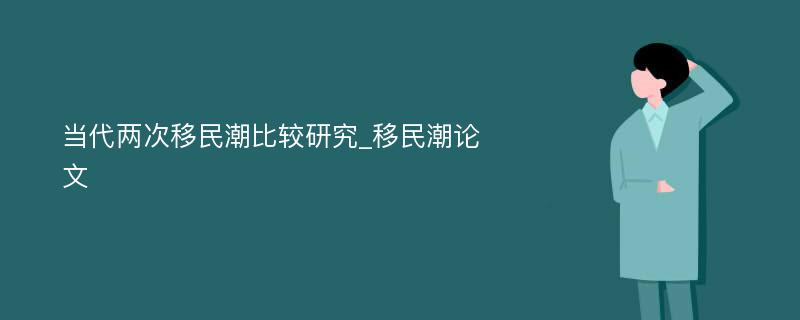
近代与当代两次移民潮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次论文,近代论文,移民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1;K27;D63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2)09-0058-09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侨民最多的国家。近代以来,中国人川流不息地向海外迁移,其中大规模的移民潮有两次。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爆发后,外国列强疯狂地侵略中国,不但大肆掠夺中国的财物,还肆无忌惮地掳掠贩运华工,由此掀起了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潮。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走出去,请进来”,再一次掀起了较大规模的移民潮(通常称新移民)。
两个世纪发生两次大规模的移民潮,具有不同时代的特征,本文拟将这两次移民潮加以比较研究,侧重探讨新移民的特点及影响。
一 两次移民潮的基本情况
19世纪中叶,欧美及亚洲的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发达时代,船坚炮利,大肆向外扩张;而当时的中国处于封建社会末期,清政府的专制统治腐朽没落,闭关锁国,朝纲不治,民生凋敝。在这种背景下爆发了鸦片战争,古老的中国被外国侵略者弱肉强食,任其宰割。
西方侵略者在大肆劫掠中国财物的同时,还疯狂地掳掠华工,将他们贩运到国外做“苦力”。大量贫穷破产的中国人被胁迫、拐骗或绑架强行运往国外。1846年12月,西班牙轮船在福建厦门贩运第一批华工,贩运华工的罪恶活动便从此开始。至1852年,从厦门被贩运出洋的华工约在8000-15000人之间。1853年厦门发生反抗拐卖华工的暴动,贩运华工的中心便移往汕头,至1858年,从汕头被掠出洋的华工达4万多人。随后,香港、广州、澳门等地的贩运华工活动相继兴起。据不完全统计,1864-1873年间从澳门贩运到秘鲁、古巴的华工达147729人(注:这里介绍移民的地点和数宇参见李春辉、杨生茂主编《美洲华侨华人史》,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第57-58页。)。19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人烟稀少的美国西部发现金矿,矿主派人到华南大力宣传金矿的诱惑力,大批华工被骗或被胁迫至美西淘金,至1882年抵美华工约达29万人。与此同时,美国西部修建中央太平洋铁路,及横贯加拿大的太平洋铁路,亦招募了数万名华工。
西方侵略者在大肆掠夺落后国家的资源和劳动力的同时,还向殖民地国家和落后国家进行资本输出,这一时期,欧美强国对南洋各殖民地的开发也需要大批劳动力,这些国家的中国移民也随之剧增,如新加坡1836年有华侨13749人,1901年增至164681人;1833年槟榔屿有华侨11010人,1901年增至97471人,马六甲1827年有华侨5006人,1901年增至19408人。此外,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被清政府镇压后,不少起义者逃亡南洋定居成为华侨。
澳洲和非洲华侨也是在此前后形成的。1848年第一艘贩运华工船只抵达澳大利亚,至1881年抵澳华侨达38533人;1904年第一批华工被贩运到非洲,两年后抵非华工猛增至51427人。
欧洲华侨形成稍晚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俄协约国在华招募20多万华工为战争服务。战后有部分华工定居下来成为华侨,随后还有少部分勤工俭学生定居成为华侨。
19世纪下半叶的华人移民,绝大多数是被迫的强制移民,其中虽有少部分自由移民,也是因生活所迫而出洋谋生的。关于近代华工在海外的数量说法不一,有学者统计,从1801年至1925年我国在外的契约华工达300万人;另有学者统计,从19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初为华工出国的高潮期,此间至少有700万华工在世界各地(注:参见陈泽亮:《十九世纪盛行的契约华工制》,载《华侨史研究论集》(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50页;林金枝主编:《华侨华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不管哪种说法确切,但都足以说明,鸦片战争以后的几十年间,大量中国人被迫出洋形成一股浩大的移民潮的悲惨事实。“自一八五0年以后,至一八八0年,三十年间之猪仔吁天录也,人间地狱,何以加兹,实为贩运猪仔最猖撅时代。”[1](p175)贩卖华工是西方侵略者对广大的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招募人的罪行在中国沿海一带已造成相当严重的混乱局面,无数妇女因丈夫或儿子被劫,到处哭诉”[2](第六辑,p153)。
被贩运出洋的华工命运十分悲惨,当时人们把贩运华工的船只称作“浮动地狱”或“鬼船”,贩运出洋的华工被污称为“猪仔”。连贩运华工的人贩子也直言不讳地供认:“华工船再现了黑奴船上的恐怖景象”,“即使是非洲奴隶贸易最盛时期——也比不上中国奴隶船上那样可怕”[2](第六辑,p186)。这里仅以运往古巴的华工为例,从1847年6月第一艘贩运华工的“苦力”船来到古巴,至1859年抵古的华工共有50123人,其中在途中死亡者达7622人,约占15%。
早期华侨在国外均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历经艰难困苦,尝尽人间的辛酸苦辣,以拓荒者的骨肉血汗,以中华民族的勤劳智慧,为当地经济的发展繁荣、社会进步、文化交融,作出了世所公认的贡献。但在很长时期里,他们的处境如奴隶一样。世界各地此起彼伏、接连不断的排华暴行,酿成了无数次惨绝人寰的惨案。早期印尼、菲律宾屡屡发生排华惨祸,数万名华侨成为刀下鬼;法属印度支那对华侨的税收多如牛毛;美国“天使岛”洒落着无数华侨的斑斑血泪;加拿大的老华侨皆晓得“人头税”的耻辱;在秘鲁挖掘“鸟粪”的华侨流血流汗;“澳大利亚是白人的澳大利亚”是排华时的响亮口号;在英属非洲殖民地,华侨“只能与驴子同履车道”。
近代第一次移民潮回落后,华人移民仍持续不断,并时而掀起小股浪潮。至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大陆调整内外政策,实行改革开放,再次掀起新的较大规模移民潮。如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美国华裔人口增加了102.6%;至1999年底,“中国新移民数量居加拿大首位”;目前欧洲华侨华人总数达100多万,增长速度最快,与大陆新移民的涌入有直接关系;澳大利亚现有华侨华人约60万人,大陆新移民占14万;近十年间,日本华侨华人由15万多人增加到27万余人,新加坡由23.6万多人增至30.8万余人;“中国改革开放后,来南非的新移民逐渐增多”,“据保守估计,在7万左右”[3](1997年7月28、29日)。
20世纪后20年间新移民潮的出现,有着一定的国内国际背景。就国内来说,70年代末,结束了50年代后期至“文化大革命”较长时间的“左”倾错误,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纠正了对“海外关系”的许多错误认识,广大侨眷及海外侨胞成为对外开放、对外联系的最活跃的一部分,他们之中蕴藏着经济和智慧的潜能,是现代化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时人们也认识到,中国的发展需要走向世界,自我封闭难以发展,中国必须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先进的知识才能走向繁荣富强。70年代后期,中国与长期敌对的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关系的改善并建立了外交关系,放宽了移民政策,尤其是向发达国家派遣了大量留学生,为新移民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改革开放,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很大变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大变化就是人心思动,农村人涌向城市,内地人涌向沿海,而沿海人则将目光盯向海外”[4](1999年12月16日)。因此说,大陆新移民的形成,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中国大陆走向开放、走向世界的一种标志。
从国际方面看,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国际关系趋于缓和,世界许多国家亦愈加认识到,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和贡献,它们废除了对华人的歧视性法令,放宽了对中国公民入境的限制,欢迎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东南亚国家也相继放宽了华侨、华人与中国交往的限制。另外,中国大陆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生活等方面差距仍然较大,加之东南沿海早就有移民的传统,在海外有较广泛的“移民链”,这些原因成了新移民的重要拉力。
就新移民的类型考察,大致有留学生移民、专业技术移民与投资移民、涉外婚姻移民与家庭团聚移民、非法移民等四种类型,下面分述之。
第一,留学生移民。严格说来,中国在国外的留学生不能笼统地算作移民,但其以各种方式取得当地国籍并永久留居当地,则属于移民。中国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了,从1872年至1978年间,出国留学人员共约13万人。从1978年至今,大陆派往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及欧洲等国家的留学生有32万人,学成回国者约11万人,约有2/3留居当地,成为新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最近20年大陆派到国外的留学生是过去100多年的近2.5倍。至1999年,大陆在美国的留学生为46958人,占在美留学生的第二位(日本为47073人,排位第一)。至2000年夏,“留学美国的中国大陆学生已超过任何其他国家”,其中“有些大陆留学生是设法取得美国公司的高科技工作,再以就业移民的身份进入美国居留”的[5](2000年6月9日)。至1999年,在日本的外国留学生共有55755人,其中中国大陆有26000名,居日本外国留学生之首。“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四万中国大陆留学生获得永久居留后,亦于最近纷纷加入澳籍。”[3](1999年6月26日)这表明,在澳大利亚的留学生移民至少在4万人以上。另据估计,大陆自费留学或出国后转为留学身份的有10万人,回国者占3-4%。公费与自费留学人员合计约40万人。由上可见,留学生是新移民的重要来源之一。
第二,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大陆企业陆续转向国外,这是大陆有史以来较少见的。中资企业的一部分工作人员,正在逐渐转变为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亚等国尤为欢迎这两种移民,前两者允许这两种移民并可立即取得永久居留权。近些年来,加拿大“增多贸易投资新来移民近廿万,给与当地政府经济帮助很大”[6](1998年12月11日),其中包括台湾移民。而最近两三年,“中国大陆成为加国移民来源地的首位”,1998年为2万多人,1999年增至2.9万多人,他们“多是技术移民”。9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的国外技术移民上升至最高比率达52%,并逐渐取代家庭团聚移民,这里无疑包括大陆的这类移民。日本、新加坡等也不限制这两种移民。由此可见,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受到不少国家的欢迎,成为大陆新移民的类型之一。
第三,国际婚姻移民和家庭团聚移民。由于种种原因,第一代华侨较少与外国人通婚;而现在有许多中国人以国际婚姻为荣,也有不少外国人属意中国配偶。因此近20年,国际婚姻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种新现象。涉外婚姻主要有如下两种情况成为新移民:一是在国内与来华外国人或华侨、华人结婚,然后办理移民签证,出国定居;二是已在国外有就职签证者或短期签证者(包括留学等),甚至非法移民与外国人、华侨华人结婚。其只要维持几年的婚姻关系,一般即能在国外定居。
近些年来,欧洲新增加一支家庭团聚及亲属关系的新移民队伍。据统计,福建省改革开放以来向海外移民50多万人,其中90%以上是以家庭团聚方式移居海外的。其中晋江以家庭团聚方式移民国外的高达98%,不少非法移民也是以探亲名义出境的。浙江青田现有15万华侨华人分布在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大多数是近20年通过亲属关系出国的。国际婚姻移民和家庭团聚移民,已经成为大陆新移民的一种“连锁链”。
第四,非法移民。这种是指没有通过正常法律渠道或采取违法手段的移民,包括非法出入境(即通常所说的偷渡)非法居留、合法入境非法居留及非法入境后因大赦等原因转为合法移民。
非法移民是一世界性的社会现象,当然,中国也存在非法移民。据美国西区移民官员透露,1997年度共有656名中国大陆“偷渡客”被移民局查获拘留。由于加拿大法律上有规定,当局不能驱逐任何进入加领海的难民船,偷渡者抵加辖区时,只要自称“难民”,便有权出席入籍听证会及上诉,其间还可享受加国人权赋予的权利,不但不被拘留,还可在当地工作。这样即有不少非法移民自称“难民”涌加,其中也自然有些大陆移民。如1999年12月在加拿大温哥华等地即查获五批大陆“偷渡客”。20世纪90年代苏东巨变以来,一批批中国人经俄罗斯来到巴尔干经商,全盛时达十多万,近期仍有四五万,他们在巴尔干经商,流动性较大,有相当数量属于非法移民。欧洲其他国家及澳大利亚等也都有些大陆非法移民。闽西北的明溪县共有11万人口,有4200多人出国打工、做生意,其足迹踏遍欧洲、美洲、亚洲、大洋洲的23个国家,其中15%集中在匈牙利、意大利等国,被称为“福建人旅欧第一县”,他们之中有些属于非法移民。大陆在南非的新移民,非法移民也占较大比例。
中国政府对非法移民是明令禁止的。1992年我国公安等部门联合制定了进一步防范我国公民非法移居国外的意见,1994年全国人大做出了关于严惩组织、运送他人偷渡越境犯罪的决定和措施。中国政府代表在1999年春的一次移民问题的国际会议上声明:“中国政府历来反对偷渡和非正常移民,尤其是贩卖妇女、儿童等行为,并为制止上述行为付出了巨大努力,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7]从1994年至1998年,大陆共抓获境内外偷渡集团的“蛇头”2000多人。这方面已有一些文章论及,不再赘述。
应当说,非法移民是世界现象,中国的非法移民不是最多的,对此既不能视而不见,也不应借此夸大其词;甚至借此宣扬“中国威胁论”,更是别有用心。
以上阐述了近20多年来新移民的情况。至于新移民数量问题,至今没有确切统计,学术界说法不一,多数学者认为已超过100多万(注:关于我国新移民的数量学术界看法不一,郭玉聪认为有108-128万,谭天星认为约有110万。参见庄国土主编《世纪之交的海外华人》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33页。)。据美国《侨报》估计,“近20年来至少有200万中国公民移居海外,其中60万人定居北美”[5](2000年4月6日)。这里没有说明是否包括台湾、港澳移民。笔者认为,大陆新移民约在100-200万人之间。在这20年的时间里,如此大量的中国人移往国外,谓之“移民潮”是恰如其分的,而且这股移民潮还在发展,延续到21世纪,成为跨世纪的移民潮。
二 两次移民潮的特点
与19世纪下半叶的第一代移民比较,由于时代的不同,社会制度的更替,国力强弱的悬殊差别,人们的思想观念的重大更新,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使得20世纪末大陆新移民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其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由被动移民转变为主动移民。鸦片战争以后的移民潮,是在清政府闭关锁国、视臣民出洋为非法,反而被外国侵略者用大炮强行轰开国门,眼睁睁地目睹外国侵略者恣意掳掠自己的国民,却无力加以保护状况下的移民。绝大多数华人出国是“被绑架”或“受了蒙骗”的,成群结队地被人贩子抓“猪仔”,强行贩运往国外,或为生活所迫而出国。无疑,这次移民潮,对于绝大多数当事者来说,完全是违背自己意志的移民,是一场空前的灭顶之灾,是身不由己的、强制的、非正常的被动移民。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大批移民,绝大多数是寻求自身发展的主动移民,是一种出自移民者自发的、和平的、友善的、高质量的移民,是当代世界人口正常的国际性流动的一部分。前面介绍的几种移民均是自愿的、主动的,有些为了达到个人移民的目的,甚至采取了不择手段,诸如偷渡等非法移民;即使有不自愿的移民也是极个别现象。这方面的情况,不言而喻,不必细述。
(二)移民地域和结构发生变化。前一次移民潮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各地,以各个开放港口为贩运点,内地和边陲移民较少。这与当时中国的交通不发达,对外贸易及交通主要通过海上运行有关,当然也与当时的“人贩子”深入内地贩买华工不便有关。
新移民则不同,除了东南沿海传统的移民地域外,不断向内地和边陲地区发展,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农村到城市均有移民。其中过去少见的一些内地城市如北京等地也有大量移民。如近几年,在俄罗斯经商的一批新移民,有许多是来自北京,他们不少已取得俄罗斯国籍。但就规模移民而言,依然多在具有传统移民的沿海省份,如闽、粤、浙、沪、鲁等。地缘、血缘的牵引仍然是大陆新移民的重要拉力之一。一般来说,留学生移民、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城市居多,包括内陆城市;涉及婚姻、沾亲带故移民、非法移民多在农村或沿海省份。
19世纪的移民潮,绝大部分是男性单身移民,主要是西方国家由于开发本国或其殖民地资源而需要大批廉价的劳动力,因此数百万华工被贩往世界各地,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举家移民者较少见。而新移民则不同,举家移民者比比皆是。其中由留学人员转变为新移民这部分人绝大多数家属随其移民;此外,跨国婚姻、同族亲戚的连锁移民亦不在少数。
(三)新移民文化程度高于老移民。随着时代的前进,科技的腾飞,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的劳动就业部门,已经从劳动力的密集型转向高科技型,从繁重、简单的体力劳动转向轻松、复杂的脑力劳动,不需要或较少需要文化层次低下的劳动力,因而当代发达国家对移民入境有严格的限定,文化程度低的移民受到严格限制。因此,大陆新移民中受过高等教育、学有专长者占相当大的比例。这里仍以留学生为例,据1999年中国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改革开放的20年来,大陆共有32万人在海外留学,还有约10万人以其他身份(如陪读等)出国后转为留学身份的自费学生。这些留学人员分布在103个国家和地区,而90%集中在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及西欧等发达国家。他们中完成学业留在当地成为新移民者达20多万人,其中在美国获得“绿卡”者8-9万人;在日就职、定居或入籍者约6万人;获澳大利亚、加拿大永久居留权者分别约在4万人和1万人以上;还有不少人则在欧洲获得了永久居留权。这些人占新移民的很大比例,其整体素质较高,多任职于大学、各类研究机构、公司企业、政府部门和国际性组织等,有相当一批人已获得较高的职位,可称作大陆新移民的主体之一,这是老移民所无法比拟的。前述的投资移民、技术移民也多具有较高的文化层次。再以1999年美国华侨华人的教育程度为例,小学五年级以下教育程度者占9.4%,具有高中以上教育程度者占73.6%,受过大学教育的占59.1%,获得学士或更高学位者占40.7%,从中可见“华裔总体教育水平较高”[3](1999年10月30日)。
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新移民文化程度较低,一般说,福建、广东、浙江等省及广大农村乡镇的移民文化偏低。以浙江青田为例,1979-1995年该县合法出境的4万人中,农民占50%;工人占25%,商人占12.5%,学生占7.5%,干部占5%。这一组数字可清楚地看出青田移民的文化程度较低,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即使这一部分移民,也比第一代目不识丁的华工移民文化程度高些。
(四)新移民职业呈多元化,不少人从事优异的职业并脱颖而出。第一代移民大多从事简单而繁重的体力劳动,一般集中在开矿筑路或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里。如美国西部的开矿淘金、修筑铁路,开中餐馆、洗衣店等;加拿大、墨西哥的筑路开矿;秘鲁挖掘鸟粪,古巴种植甘蔗,巴拿马开凿运河,南非的金矿,澳大利亚的牧场,欧洲各国的开港,东南亚城市开埠、垦殖拓荒、胶园矿场等,均将华侨作为主要劳动力。他们像奴隶一样日以继夜地劳作,为侨居地的开发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新移民则突破了老移民的行业取向,涉足于居住国的商业、科技、教育、金融、服务等各行各业,其中有不少人崭露头角,成为本行业的骄子。在美国,多数大陆留学生设法找到各类公司的高科技工作,其中硅谷有25%的工程师是中国留学生;大陆留学生创办的2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在硅谷注册,大多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成就,其中格里克通信公司和维亚多软件开发公司还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成为华人企业佼佼者。格里克通信公司的总裁陈宏自豪地说:“这些企业的兴起使美国人开始认识到,中国不但有优秀的厨师和工程师,而且有优秀的企业家。”“现在的华人,其地位与一百年前进入美国的中国劳工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8]来自上海交大的李安渝,在硅谷开创两家网络公司时,还是一个未出茅庐的学生。2000年初,他将两家公司分别以200万美元和370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是年青学子成功的典型。还有像施晨阳、姚勇等一批身手不凡、朝气蓬勃的科学家。1982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的杨向中赴美后,先后获得康乃尔大学硕士、博士学位,现任康大教授。1999年6月,他在自己的实验室成功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头以非生殖细胞克隆奶牛;翌年1月,他发表论文宣布:用公牛耳皮细胞培养3个月以后,克隆产生了6头小牛犊。其论文发表后,“引起了美国生物学家的普遍重视”,认为这“将在生物学的许多领域发生重大影响”[9],《纽约时报》等报纸纷纷作了报道。1995年获美国总统教育奖的5位华人,都是80年代从大陆移居美国的。还有一些新移民在世界知名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当教授;纽约华尔街金融机构、芝加哥摩托罗拉总部、底特律汽车公司等著名企业机构均活跃着一批大陆新移民。小说家金雪飞,1985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外语系英美文学专业后留学美国,获得英美文学博士。1999年11月,他以“哈金”的笔名撰写的英文作品《等待》一举夺得全美“国家图书奖”。2000年7月,有5名大陆画家、歌唱家、表演艺术家受纽约移民局办事处的表彰。还有不少大陆优秀的体育运动员,如跳高的朱建华、体操冠军李月久等,退役后移民美国,操起老本行并占有优势。
大陆新移民在欧洲除继承先驱们传统的中餐业等外,有许多人利用大陆经济发展带来的商品价格优势,经营商品的批发、零售与进出口贸易、超级市场,房地产及金融业。意大利罗马崛起的中华商业街及商业中心,占地20多万平方米,有150多家中国公司经营,成为欧洲最大的中国人拥有的商贸中心。还有许多新移民在西班牙从事服装加工业,在匈牙利开办公司企业等。
有诸多华人新移民在澳大利亚的电脑科技及电子商务方面显示才干。目前,居澳华人新移民创办的公司、企业近千家,其中汪人泽创办的EDGE品牌电脑公司生意火爆,执澳同行业之牛耳,闻名遐迩。华人占1/3的电子网络企业的技术员,有不少为新移民。
黑龙江大学英语系毕业的刘煜,1985年去非洲的毛里求斯,一年后转到南非发展,先是任香港保利集团驻南非总经理,后转从事进出口贸易,生意兴隆;继之在约翰里斯堡附近的布朗区开发一个占地10平方公里的“伊坎工业区”,并成立了“中南友好工业区发展有限公司”,成为新移民在南非创业成功的典型。还有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的刘女士,1997年赴南非的知名大学金山大学学习,她目睹南非语言学校混乱,遂和丈夫精心准备,与金山大学达成协议合办“升腾语言学校”,该校创办后势头良好。
(五)新移民比老移民政治经济地位大有改观。如前所述,早期的华人移民生活贫困,政治地位低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世界民族民主运动汹涌澎湃,各国相继废除种族歧视制度,废除了对华人的歧视性法令,使华侨华人的处境得以改善。另外,长期以来,华人移民大多数已融于当地社会,成为居住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参与当地的政治经济事务,其地位大有提高。近些年来,各国的华人精英掀起了一股参政运动,并取得了成功,当然也有新移民参与其中。
从总体上考察,华侨华人经济和生活方面大有改善。由于笔者掌握美国华侨华人的资料较多并较典型,这里仍以美国为例,据统计,美国华人家庭年收入不到5000美元者占总数的7.5%,年收入在5000-14999美元者占14.4%,年收入在15000-34999美元之间者占26.4%,年收入在35000-74999美元者约占34.7%,年收入达到或超过75000美元者占17%[3](1999年10月30日)。福建明溪县在欧洲的移民,把国内的轻工产品大量打入欧洲市场,其在欧洲创办的智胜公司和东华公司,均有数百万美元的资产。
当然,说新移民的职业、地位有很大改观,只是与老移民相对而言,不少国家种族歧视的阴影犹在,某些大陆新移民的处境仍然不佳。“无数华裔专业人士移民到美国以后,难以找到适合发挥自己专长的工作,在餐馆、衣厂做工,郁郁不乐地渡过人生的黄金时光。”[5](2000年2月22日)移居加拿大的一对华人夫妇均在欧洲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且有大陆十多年外科手术经验,但移加后不被承认而难觅工作,落到在餐馆打工的地步。此种情况其他国家也不乏其例。至于非法移民的处境更是可想而知。
三 两次移民潮的影响和作用
19世纪与20世纪的两次移民潮,均对中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前者对祖国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后者对祖国大陆的经济建设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外侮日亟,内患愈重,社会日益沉沦,民族危亡不断加深。为了挽救中华民族,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掀起一次又一次的反帝反封建的救国浪潮,其中孙中山发动和领导的辛亥革命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推向最高峰,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最初即是从海外华侨中开始的。海外华侨参与创建革命团体兴中会,踊跃加入革命政党同盟会,“凡华侨所到之地方,莫不有同盟会员之足迹”。如孙中山所说,“同盟会之成,多赖海外华侨之力”,“惟吾深知同盟会中非有华侨一部分者,清室无力而覆,民国无由而建也”[10](上,p1040)。华侨前仆后继地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清武装起义,“是革命起义行动的最佳人力支援来源”。他们在起义中表现了英勇无畏、十分感人的献身精神。辛亥革命在“经济方面,多赖诸于华侨的力量”。“华侨义士,咸怀振兴祖国之思,竭汗血,倾脂膏,短衣食,燃眉济急。”华侨创办报刊,抨击封建专制,谴责改良保皇,开展革命宣传;他们万里迢迢,参与创建中华民国。凡此种种,说明华侨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基础和动力之一。华侨支援辛亥革命是近代华侨爱国运动史上的第一次爱国高潮。
辛亥革命的成果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篡夺并建立了封建军阀的专制统治后,华侨不屈不挠地跟随孙中山讨袁护法,为捍卫辛亥革命成果立下汗马功劳;随后,他们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参加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成为国民革命的一支重要的进步爱国力量。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中国觊觎已久的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地发动侵略战争,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空前灾难,海外华侨同祖国同胞一道投入到挽救民族危亡的抗日救国浪潮之中,继支援辛亥革命之后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第二次爱国高潮。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起,华侨即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七七事变后,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达到高潮。他们奔走呼号,呼吁团结抗日,有力地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他们节衣缩食,开展各种形式的捐款活动,为祖国抗战捐献巨款;他们纷纷回国投资,开发祖国战时资源,以利长期抗战;他们捐献大宗物品,如救护伤员的各种药品,天上的飞机,地上的卡车及前线将士身穿的冬夏服装、铺盖的被褥毛毯等,甚至为抗日伤病员献出鲜血;他们万里迢迢回国参战,组织各种医疗救护队、慰劳考察团,回国服务;在崎岖蜿蜒的滇缅公路上抢运战略物资的3200多名南侨机工的英雄事迹可歌可泣,其中有1000多人英勇献身;有许多归侨健儿驾驶战机,迎击日本空中强盗,血洒蓝天,威震敌胆;华侨开展抗战的舆论宣传,争取国际援华抗战,参加侨居地的反法西斯战争配合祖国抗战。广大华侨对祖国抗战做出的巨大贡献,有口皆碑。如国民党的一会议指出:“抗战以还,我海外侨胞踊跃回国,投效军旅,及服务交通运输机关者,为数至多;其仍在海外者,则慷慨解囊,尽量捐输助饷,或汇款回国增加外汇。”华侨“对于祖国之抗战,实予以巨大之助力”。[11](上册,p121)中共在延安的《新中华报》社论指出,华侨“所有这些直接间接参加抗战的工作以及对政府财政上的帮助,都说明了华侨在抗战中的伟大作用,没有他们的努力,国内的抗战一定是更加困难的”[12](1940年4月6日)。
抗日战争期间,占华侨社会总数的50%左右为第一代移民,他们的民族意识及爱国爱乡思想甚为浓厚,在他们的带动和影响下,其后辈们也踊跃投入抗日救国的洪流之中。因此,可以说第一代移民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民族民主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随着时代的变迁,华侨华人社会结构、思想观念等都发生了诸多的变化,但在他们身上仍保存着中华民族的血统,仍保存着爱国(祖籍)爱乡的光荣传统,这就决定着20世纪大陆新移民与祖(籍)国仍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对大陆的经济建设有着重大的影响和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心大陆的经济建设。新移民和老移民一样,十分关心祖籍国的经济建设,改革开放以来热情更加高涨。据统计,从1979年至1990年,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在祖国大陆的投资约为115.2亿美元(其中来自港澳地区的资本占绝对多数,约为111.6亿美元)。90年代以后,投资额逐年增加,呈明显上升趋势,截至1997年年底,大陆累计批准外资投资企业30.48余万家,合同外资金额5211.64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金额2218.71亿美元,其中海外华侨华人及港澳同胞的资金占60-70%。[13](1998年2月11日)
上述介绍的投资包括老华侨和新移民的投资,具体比例占多少难以确切统计,但新移民回大陆投资不乏其例。美国成功集团总裁李玉玲,1985年于北京财经学院毕业后去美国创业,经过锲而不舍的努力,她创办的美国成功集团已成为美国的“三A”企业之一,其经营额超过50亿美元。作为一名成功的跨国公司企业家,李玉玲不忘祖籍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在国内创办了30多家合资或独资企业,横跨环保、高科技、航空、房地产、旅游、服装等多种行业。2000年8月初,她在新疆乌鲁木齐投资5亿元人民币于小西门旧城改造的“成功广场”项目正式开工,成功广场集购物、住宅、餐饮、娱乐、写字间于一体。李玉玲是新移民回大陆投资的典型代表。
大陆留美博士朱敏1996年在硅谷创建美国网讯(Webex)公司的软件企业,生意兴隆,至2000年8月市值达到20亿美元。在海外取得成功后,朱敏把目光转向国内,网讯先是派斯坦福大学和旧金山大学的两位教授到浙江大学和浙江工业大学协商联合大规模培养研究生事宜,得到双方的认可。同时,网讯又在杭州滨江购买152亩土地,筹备建立一所软件学院,投资额为2亿元人民币,实现产、学、研相结合。新移民向大陆投资的事例还可以举出一些,如广州侨界拥有4000多家企业,其中有不少是新移民的投资。
第二,关心大陆的政治。新移民是在大陆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形成的,因此,他们都关注大陆的改革开放政策,希望改革开放取得更大成就,使中国愈加强大。1997年和1999年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海外新老移民雀跃欢呼,以此为契机,在海外举行了两次庆祝中华民族大团结的盛典。他们普遍认为,这是“雪洗我民族耻辱,振兴光大我中华”的扬眉吐气的时刻。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都不同程度地参加和参与了庆祝港澳回归活动,活动规模之大,历时时间之长,活动次数之频繁,形式之多样化,在华侨华人的历史上是前所少有的。
2000年8月26日,由大陆新移民张曼新发起,在德国柏林召开了全球华侨华人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大会,来自世界各地60多个国家的华侨华人代表、中国内地和港澳台的代表共600多人出席了会议。本次大会的两位名誉主席——中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万国权和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台湾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梁肃戎等出席大会并作了演讲。大会通过一份《共同声明》,指出,一中原则是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是对两岸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的客观陈述。“柏林大会的声明反映出海外华侨华人共同的希望:希望海外华侨华人将反独促统的意愿化为行动,希望全球中华儿女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为促进中国的和平统一努力奋斗。”[14]可以说,这是20世纪末海外新老移民共同关心中国政治的一次盛大活动,
关心国际政治、改善中美关系,是华侨华人关心中国政治的扩大,也是新老移民共同致力的事业。2000年4月16日,美国南加州100多个华侨华人团体联合发起在南加州美籍华人中征集万人签名活动,呼吁美国国会议员在5月下旬的投票表决中赞成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这项活动的发起者表示,凡是投票赞成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的议员,美籍华人在当年11月的大选中将支持他们连任;对那些不赞成该议案的议员,美籍华人选民将投反对票。当地华人还给所在选区议员写信、发电子邮件来表达这一意见。发起者还公布了致美国国会众参两院议员公开信,陈述中美关系及中美正常贸易的意义。他们这一举动,推动了美国众参两院投票最终通过对华永久正常贸易议案,对克林顿总统提出、努力通过并最后公布这一议案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第三,为大陆科技事业的发展出力献技。新移民与老移民的重要区别之一,是他们当中有相当一批学有所成、出类拔萃的科技精英,其主要集中在三四十万名海外留学生之中。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后,确立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政策,同时提出吸引在外留学人员“为国服务”的口号,并尽量为他们报效国家创造良好的环境,如科技部启动有10亿元人民币拨款和20亿元贷款的“中小型企业创新基金”等,为留学人员回国创办科技型企业大开方便之门;内地各省也纷纷“筑巢引凤”,已建成了设施较完善的30多个留学人员创业园区,如此等等,使“八十年代出国留学热之后,留学生们回归创业的热潮和趋势,正在新世纪快速地形成”[15]。目前已经有11万多留学人员回到大陆创业,而且回流的势头继续高涨,他们正在为大陆科技的腾飞贡献才智。
原海军总医院血液科医生陈晓宁,1988年赴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深造,现为洛杉矶加州大学副教授、洛杉矶塞达西纳医学中心分子实验室副主任、北美华人医学遗传学家协会主席。从1992年起她建立一套世界顶级的DNA及BAC克隆基因库,外国专家评价她“在人类基因、基因组学及物理定位方面做出了杰出的成就”。2000年夏,陈晓宁和丈夫经过多年筹划,征得研究伙伴的同意,先期投资了3000万元人民币创办了北京博宁基因工程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博宁医学遗传研究中心,把世界上最全的三大基因库移到了中国,其中最大的“人类基因克隆库”将赠送给国家基因北方中心。陈晓宁的愿望是“尽快把三大基因库转化成产品为医疗事业服务”[16],如果实现这些,将掀开生物研究和产业开发的新篇章。
年轻的留美博士龚学锋出生于广州郊区,他在高分子领域有所建树。为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他以技术参股的形式创办了广州第一家高分子材料创业基地,三年来已经发展成为规模壮观的高科技园区,其高科技产品被誉为“中国厨房的革命”。目前,广州已吸引了50多位各有特长的留学博士,从海外回来从事科研教学或创办企业。
还有些在美国深造网络、电脑的学子回国创业。离开大陆14年的叶忻于2000年春夏,放弃在美国硅谷任职的机会,离开妻女回到北京,到因特网网站之一搜狐公司任高级职务。唐海松、陈一舟分别在美国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获得硕士文凭后,在美网络系统工作,近来他们带着一笔风险投资回到国内创业。
1986年由天津医科大学被送到澳大利亚墨尔本读博士的王宝忠,十几年来以深厚的基础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受到澳肝移植权威罗伯特·琼斯教授的青睐,两人合作进行了300多例肝移植手术,达到了一年存活率达95%以上,5年存活率达85%的世界先进水平。王宝忠看到中国医学在器官移植方面落伍于世界,非常着急,决心把所学技术介绍到国内来。自1993年以来,他平均每年到国内讲学、学术交流3-4次,走遍了全国30多个城市,与30多家医院建立了联系,被聘为客座教授、兼职教授等。在他及国内医学界的努力下,如今背驮式肝移植技术已被国内多家医院掌握,成功率、成活率均有明显提高。
新移民或留学归国人员在高科技领域大展才华的事例多不胜举。联合国“通过海外侨民回国传授技术”志愿服务项目(英文简称TOKTEN)在中国取得显著成效,截至2000年,中国利用TOKTEN项目共聘请海外华人专家近2000名,涉及1000多个项目,占全球总量的1/7,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新移民专家。据统计,大批留学归国人员近几年来在国际权威杂志发表论文1000多篇,获国际奖100多项。在现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留学回国人员超过80%;现任中国的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863计划”等工程计划中,近年来留学归国人员比例均占到半数以上;目前北京大学有300多名留学博士凤还巢,在清华大学任教的也有近300位留学博士;解放军总后勤学院在改革开放后派出留学人员2000多名,绝大多数学成归国,其中有10人任“两院”院士。总之,改革开放后的大批留学生走出国门,让中国走向了世界;他们归来,则把世界带给了中国。
第四,为祖籍国和侨乡兴办公益福利事业。新移民继承老移民的优良传统,他们热心祖籍国和侨乡的文化教育事业、医疗卫生事业及修桥筑路、兴修水利、赈灾济贫等各种公益福利事业和慈善事业,为侨乡的进步与发展作出了贡献。据中国大陆侨务部门的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即1979年底至1998年,华侨华人向侨乡及大陆各地捐赠总值约合人民币405亿元,1985年至1998年全国接受华侨华人捐赠总值约为人民币393亿元,其中捐献物资折合人民币为321.7亿元,占总数的81.8%,直接捐款71.3亿元,占总数的18.1%。这些大量的捐赠中用于科研8.3亿元,用于文教88.8亿元,用于医疗卫生37.8亿元,用于公益福利89.9亿元,用于工农生产114.4亿元。近年来,大陆每一次发生洪涝、地震等自然灾害时,华侨华人及港澳台同胞都踊跃捐款,如1991年华东水灾共接受捐赠25亿元人民币,其中华侨华人捐赠达9亿多元;1998年长江、松花江特大洪灾,全国共接受捐赠人民币总值约115亿元,其中有相当数量为华侨华人捐赠,自然包括新移民的捐赠。[17](1999年5月28日)
广东省改革开放的20年间,接受华侨华人及港澳同胞捐赠人民币约200亿元,其中用于兴办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公益事业的项目达到2.6万宗,金额达人民币155亿元。福建省1992年至1997年间,接受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同胞捐资36亿元人民币,兴办教育、铺路架桥等公益事业达13600多项。沿海其他各省及一些内陆地区也都大量接受华侨华人的捐赠。前述的李玉玲除了向大陆投资外,还慷慨捐赠,1998年的特大洪灾,她一次即为灾区捐献人民币3000万元,创下个人捐赠的最高纪录。几年来,她先后为甘肃、西藏、山东、山西、辽宁、吉林、河南、河北、北京等地的教育及社会公益事业捐资捐物累计达2.5亿元人民币,她还两次向中国扶贫基金会捐资人民币2100万元作为科教扶贫基金。这方面的事例还有许多,不再列举。
新移民对大陆的影响与作用还表现在经贸、外交、传播中华文化等方方面面,在以上诸方面影响中,当以经济建设及科技振兴居主要地位,而且这种影响将会十分深远。
[收稿日期]2002-03-20
标签:移民潮论文; 移民论文; 华侨论文; 移民欧洲论文; 移民加拿大论文; 移民澳洲论文; 加拿大历史论文; 非法移民论文; 人贩子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