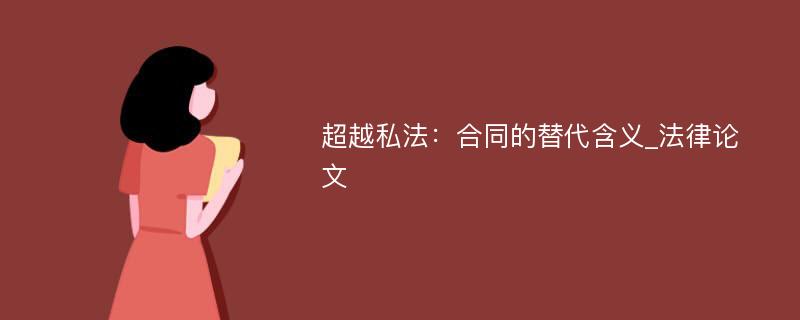
超越私法:契约的另类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私法论文,契约论文,意义论文,另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4-0049-09
有论者言:“我国及世界各国基本上都是从民商、经济法的角度来界定契约范畴的”。[1](P9)这种观点得到了契约适用理论的力证:私法中所谓“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原则”一般得到认可,只要不违反公序良俗以及与公共秩序相关的所谓强行规定,当事者可以自由地缔结任何契约。与此相反,公法关系一般由国家立法来规定,同时与私法中原则上是任意规定不同,这些规定是与公益相关的强行规定,任何人不得以意志自由作出与之相反的决定。公法关系正好与私法关系相反,契约不自由是原则,只有在法律特别规定的时候,才能用当事者的契约来规定公法关系。[2]在我国,契约的确局限于民法、商法的私法领域,① 《说文·大部》所谓“契,大约也”,以及《周礼》郑玄注曰“大约,邦国约也”,并不具有国际公法的意义,而是指邦国之间进行土地交易的文约,具有典型的私法意义。《民法通则》与《合同法》显然尊重了这种用语习惯,在解释合同一词时,《民法通则》写道:“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合同法》第2条写道:“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在协议前加上限定词“民事关系”、“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表明了契约的纯私法意义。
而西方文化中的契约范畴,与中国大异其趣。梅因对罗马的契约演化史做了详尽的论述。按照他的说法,契约的古代用语为“耐克逊”,是一种用铜片和衡具的交易,是罗马财产权从一人转向他人的庄严仪式的象征,于是最初的意义与“让与”相混淆;后来,为了将旨在转移财产与旨在使契约庄严化,分别使用“曼企帕地荷”与“耐克逊”之名。此后,“在一个契约合意下的人们由一个强有力的约束或链锁联结在一起,这个观念一直继续着,直到最后影响着罗马的契约法律学,并且由这里顺流而下,它和各种现代观念混合起来。”[3](P176-189)据此,有人认为“罗马的契约观念是整个罗马法的灵魂,也是罗马人政治与宗教生活中的一个有力因素”。[4](P38)罗马法中,不仅私法上有契约的概念,公法和国际法上也有这个概念。《学说汇编》就把协议分为国际协议、公法协议和私法协议三种。于是,在西方学术传统中,对契约的界定小心翼翼,人们进行定义时尽量少用限定词,特别是忌讳使用“民事”、“商事”等定语,因为西方的契约不仅具有私法上的涵义,而且被广泛地公法化,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宗教、社会意义,出现了政治契约、宗教契约、社会契约等,他们似乎唯恐此类限定将妙趣横生、丰富多彩的契约内涵弄得索然寡味、挂一漏万。罗马人将契约界定为“由于双方意思一致而产生相互间法律关系的约定”。[5](P159)《不列颠百科全书》则言:“按照最简单的定义,合同就是可以依法执行的诺言。”美国律师学会《合同法重述》的表述也很有技巧:“合同是一个诺言或一系列的诺言,对于违反这种诺言,法律给予救济”。② 在西方世界权威的法学教科书中,契约是这样一个协议:“它通常采用一个或一组允诺的形式,也就是说,它是出于两个人一致同意的、其中的一方将因此而对另一方承担义务的声明,它自然要采取这样一种承诺形式,即一方将对另一方履行由此而产生的义务。但并不是每一项允诺都等于一项契约,订立契约不仅需要作出实施某个行为的允诺,而且需要直接地或隐含地把实施某个行为当作一项法律责任的允诺……一项契约的本质形式不在于我向你承诺做某事,而在于我同意你将因此而获得要求我为你做某事的合法权利。”[6](P385)其中的关键词是允诺、责任、权利,与“民事”、“私法”之类的词则无多少关联。
其实,从西方契约的起源看,古希腊比古罗马的契约范畴表现出更加浓厚的超私法色彩,将法律、政治看作是契约的产物,几乎成为古希腊思想家的时尚。公元前5世纪的智者普罗塔哥就认为,道德、法律既非自然也非神的创造,而来自人们的约定,其约束力以对人是否有好处为转移;[4](P8)在稍后的智者之间,将法律看作契约成为普遍的观点,如安提丰认为,成文法是人们约定的结果,并非产生于自然本性自身,而自然法则与生俱来,渊于自身,并非人们之间约定的产物;[7](P113)吕科弗隆认为,法律只是一种互相保证正义的约定,并没有使公民善良和正义的实在力量。[8](P144)智者们在将法律看作一种人定契约的同时,或肯定之,或否定之,大大启发了后人的思路。到苏格拉底,则表现出对法律这一人定契约的严格遵守,在他看来,一个公民若同意成为某城邦的成员,就是与城邦订约,并有责任虔诚地遵守之。③ 他将自己与雅典城邦的关系看作是一种自由合意的政治契约关系,并付出生命的代价来践约。通过契约制定法律,这种思想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亦获得共鸣。按照柏拉图的说法,智者格劳孔在与苏格拉底讨论正义的本质和起源问题时提出了法律来源于契约的思想。格劳孔认为人类从本性来说都是在法律的强迫之下才走到正义这条路上来的,“人们在彼此交往中既尝到过干不正义的甜头,又尝到过遭受不正义的苦头。两种味道都尝过了之后,那些不能专尝甜头不吃苦头的人,觉得最好大家成立契约:既不要得不正义之惠,也不要吃不正义之亏。打这时候起他们中间才开始订法律立契约。他们把守法践约叫合法的、正义的,这就是正义的本质和起源。”[9](P46)亚里士多德说:“以一寡头或僭主政体的转变为平民政体为例,有些人在这时就拒不履行公共契约或相类的其他义务,说这些契约不是城邦所订,只是那个僭主的措施。”[10](P116)而伊壁鸠鲁则从契约的角度来讨论国家起源:“自然的公正,乃是引导人们避免彼此伤害和受害的互利的约定”,“对于那些不能相约彼此不伤害的动物,是没有公正或不公正这种东西的。如果有一些民族的分子不能或不愿有一种尊重相互利益的约定,则上述情形对于那些民族也是一样。”[8](P347)有见及此,马克思断定:国家起源于人们相互间的契约,起源于社会契约这一观点,就是伊壁鸠鲁最先提出来的。卢克莱修发扬光大了其师伊壁鸠鲁的社会契约思想,并以优美的韵律使之广为流传。[11](P326-332)卢克莱修对国家形成以前的状况——自然状态——的描绘,以及国家形成于契约的假设,与近代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的契约理论形成明显的渊源关系。可见,在概念的起源上,西方契约即已表现出超越私法的特点。此后,契约在不同语境下使用,呈现出争奇斗妍之势,为西方契约超越私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如贺卫方教授所说,“契约已不仅仅只是一个民法上的概念,而且成为一种社会观念,一种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度。”[12](P95)
一、宗教语境下的契约
希伯来文中的“契约”一词,是指对于立约双方而言具有较强约束力的严肃诺言,它涉及人类所有一切的社会交往活动,立约的双方可以是人与人,也可以是神与人。《圣经》记载了诸多宗教契约,有个人之间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订立的协议,如押尼洱与大卫立约,承诺结束战争并使以色列归服于大卫;(《撒母耳记下》第3章,第12-13节)拉班在追上带着妻儿、财物逃离的雅各时,以石头为证与其立约,言明以后互不干犯,“你我二人可以立约,作你我中间的证据”,“我们彼此离别以后。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鉴察,你若苦待我的女儿,又在我的女儿以外另娶妻,虽没有人知道,却有神在你我中间作见证。”(《创世记》第31章,第43-53节)有国王与臣民之间的盟约,如所罗门与示每的约定、(《列王记上》第2章,第36-46节)大卫与以色列的长老们就大卫作以色列的王立约、(《撒母耳记下》第5章,第1-5节)祭司耶何耶大使年幼的国王约阿施与耶和华立约,作耶和华的民,又使王与民立约。(《列王记下》第11章,第17节)上述这些契约大都提到“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鉴察”、“有神在你我中间作见证”等,因此应归入宗教契约的范畴。有人认为,这些契约“具有与古代近东契约相似的格式和文字之表达形式,具体表现在契约的条文和规定、祝福和诅咒、立约程序等都有相似之处。”[13]《圣经》更多的记载是神与人之间立约的宗教历程。有神与大卫王之约;有神与诺亚之约,神应允不再有大洪水毁灭人和大地,并以天虹为记号,让人记得神的慈爱和永恒的应许;(《创世记》第9章)有神与亚伯拉罕之约,神赐他作“多国的父”,“后裔繁多”,并以割礼为记,要他们世世代代守神的约;(《创世记》第17章)有西乃之约,神应许以色列人作神的子民,他们要遵守包括“十诫”在内的“约书”,同时以献祭和洒血为立约的凭据;(《出埃及记》第19-24章)以及神人之约的不断重续,比如约书亚将以色列各支派的民众聚集在示剑,重申神的律法,再次立约。(《约书亚记》第24章)《圣经》宣称,《旧约》、《新约》是神、神子与人之间订立的契约。于是,宗教契约被假定成了人类社会的基础。当人类忘记、毁弃、亵渎它的时候,就遭受诅咒中的民族灾难、战争、疾病与死亡;而当信守它时,就得到约的福祉。与其他契约不同的是,这种契约是建立在宗教和道德的基础上的。契约在宗教语境中的应用,使契约获得了诸多超越私法的意义。
首先,由于神代表公平和正义,因此宗教契约论强调,世俗国王从神手中被授予权力后,必须本着公平正义的原则行事,否则,上帝及上帝在人间的化身——教会,即可放阀暴君;人民亦可秉承上帝之意,替天行道。④
其次,由于契约的当事人往往以宣誓的方式来表白订约的诚实、担保履行的信用,而宣誓暗示着对上帝的债,是一种不可侵犯的、永恒的债。因而,契约必须严格履行和遵守便成为各种契约的重要原则。《圣经》告诫订约人不可背誓,无论如何要实践向神立的诺言。它警告说:“背信的人自食其果”;(《箴言》第14章)在《加拉太书》第3章,更明确地写道:“以人与人之间的契约来说吧,契约一经签署确立,就不能废弃或更改了”。⑤ 如果说近代的“契约自由”原则是受惠于罗马法的话,那么,“契约神圣”、“契约是当事人之间订立的法律”这一原则,则主要是继受于《圣经》及与基督教有关的宗教契约。
最后,宗教契约推动了殖民政府和领地的建立,并将政治契约推向人们的视野。“根据中世纪晚期欧洲各国奉行的神学契约原则,任何基督教王室,只要发现了为异教徒和野蛮人所占领的土地,即有权宣布对其拥有主权。”[14](P3)正是在宗教契约论的指引下,1630年春,马萨诸塞公司总督约翰·温斯罗普带领700多名清教徒分乘11条货船,在波士顿附近的海湾登陆。登陆前,温斯罗普在船上宣读了那篇题为《基督教博爱的楷模》的布道词,宣称清教徒之所以敢冒风险到新大陆建立新的宗教世界,是因为上帝将保持神灵圣洁的使命交给了他们;清教徒是上帝的特别选民,为了信仰能够忍受痛苦和磨难;正是因为这种对上帝的崇敬和服从,清教徒与上帝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契约关系,而在清教徒之间也因为完成上帝赋予的神圣使命和争取共同的事业而相互结成了一个特殊的团体;在这个具有神圣意义的团体中,所有的成员必须团结一致,以兄弟之情相待,甘愿为了他人的需要而牺牲自己的利益,肩负共同的使命,承担同等的责任,享有同等的权利。[15](P10-23)这种在宗教契约的名目下再订立政治契约组建政府的方式,在北美大陆成为普遍的实践。普利茅斯、罗德岛、纽黑文、康涅狄格的政府组建方式,就是在宗教契约的基础上,殖民者以共同的宗教信仰为政治纽带,以相互订约的方式结成政治团体,产生政府,实现了宗教契约和政治契约的融合。正如王希所言,清教徒的这种宗教契约思想与后来出现的洛克的社会契约思想在契约内容的表述上不同,但两者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两者都强调社会或宗教组织成员之间为了实现共同的目的,必须建立一种相互承诺,形成一种契约,通过这种承诺契约,社会成员的地位和权利得到相互承认,从而获得了一种法律上的意义。而这种为了保护和争取共同利益的承诺和契约也就成为政治和政府的基础。[14](P15-16)
二、政治语境下的契约
政治语境下的契约,关注的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契约不是在个人之间,而是在人民与统治者之间达成的,旨在规定政府与人民各自的权利与义务。蔡拓认为,这种契约是在国家生活中以人民服从君主、君主保护人民为条件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约定,可称为政治契约。[4](P40)这种契约并不讨论国家的起源,而是探讨在国家已经建立的前提下政府的产生及对国家权力的运用和限制。因为这种契约以法律形式确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权利和义务,体现了现代宪政主义的精髓,因此在西方多被称为宪政契约。与宗教契约亦不同,它关注的并非宗教的原则和理想,而是世俗政权。但应该承认,中世纪西方政治语境下的契约是一个从属于宗教语境的话题,与宗教契约不可分离。
在中世纪的欧洲人看来,专横、绝对统治的思想是可诅咒的,[16](P150)因此,政治语境下的契约在中世纪被频繁使用。已有的资料表明,用契约理论来分析统治者和人民关系的奠基者是阿尔萨斯的僧侣曼尼戈德。11世纪后期,他大致勾画了政治契约的理论要点:“国王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名称,而是一个职务的头衔。人民把它抬高到自己之上,并不是赋予他行使暴政的权力,而是要他保障人民免于暴政。一旦国王开始施行暴政,他就必然丧失人民赋予他的高贵地位,因为很明显,他首先撕毁了授予他职位的契约。如果一个人以公平的报酬雇请某人看护他的财产,却发现那人不仅没有尽看护之责而是在监守自盗,那么,雇主难道不要解雇他吗?……既然没人能够自立为王,那么人民推举某个人为统治者,他就必须依据公正的原则来进行管理和统治,尊重个人权益,保护良善,惩罚邪恶,使正义如阳光普照。如果他违反了他当选的契约,人民理所当然地可以解除对他的服从义务。”[17](P203)生活在1401-1464年的尼古拉写了著名的《和谐的天主教》一书,对“统治契约”进行阐释:“凡人既然天生自由,故每一政府……只有靠其臣民之协议与同意而获得存在……任何法律的约束力量,均在于这一默契或昭彰的协议与同意。”[18](P192)甚至保守的耶稣会教徒也抱持政治契约的观点,如西班牙耶稣会教徒马连纳认为,王权起源于人民的同意,并且王权的行使是有范围的,人民并未把一切权力让于国王,如征税权、立法权、宗教信仰等,并指出了王与人民订约的功利动机:“王与人民最动心的是自己的利益,如果没有利的希望,决不会有长久的友谊或契约。”[19](P57)政治契约论的代表作当推16世纪法国莫耐的《反暴君论》,该文认为,一个王国建立时有两个契约,一是上帝与王及人民的宗教契约,另一个是王与人民订立的政治契约。前者表明王和人民在上帝面前平等,任何一方亵渎神灵,另一方都有权加以干涉和制裁,以维护上帝的权威和神圣,在后者中,王以承认、维持正义为统治人民的条件,若为王者违反这一条件,人民可行使废黜、惩罚之权。莫耐写道:“第一契约将虔诚变成义务,第二契约将正义变成义务。在第一契约王承认虔奉上帝,在第二契约王承认以正义治人民。第一契约在发扬上帝的光荣,第二契约在维护人民的福利。第一契约的条件是王要服从上帝的法律,第二契约的条件是王要使人民各得其分。不遵守第一契约的王要蒙上帝的谴责,不遵守第二契约的王,全体人民或监护人民的贵族对他有处罚的权利。”[19](P42)迈克尔·莱斯诺夫评价道:莫耐思想中所体现出的根据契约来看待义务的倾向,“使得契约论首次上升到政治理论的中心地位,并在此后的数个世纪里一直保持这种地位”。[20](P40)
迈克尔·莱斯诺夫断言:“在一个彻底封建化的社会中,每一个单独的人都将是一个准政治契约的一部分。”[20](P17)这个结论在欧洲社会得到了典型体现。政治契约观念之所以在西方中世纪异常强烈,主要是因为当时欧洲盛行着政治契约的实践。首先是王权的产生。虽然在中世纪君主世袭的原则取代了原来从王室成员中选择国王的权利,但在许多地方,王位依然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之上。阿拉贡的贵族就是依据这样一条准则来选举他们的国王的:“只要你能维护我们的法律与自由,我们这些与你一样优秀的人就推举你为我们的国王与君主;一旦你没有做到这一点,你就不再是我们的国王。”苏格兰宗教改革运动中,新教贵族于1567年强迫天主教徒玛丽女王退位。这样的举动自然需要理论上的声援,于是布坎南写成《苏格兰人的王权》一书,论证国王与人民的关系,指出苏格兰王与苏格兰人民的关系完全是一种契约关系,订约的任何一方如果违约,契约的束缚力就立即消失。[4](P48-49)布坎南的这些观点为当时的官方文件予以了浓墨重彩地复述:“苏格兰人派遣大使拜见伊丽莎白女王,为他们废除玛丽女王的行为进行辩护。在一份书面公告中他们宣称,他们对玛丽女王的惩罚与她应得的惩罚相比是宽宏大量的;他们的祖先曾经处死或放逐国王;苏格兰人过去是一个自由的民族,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国王,并且,如果他们觉得必要的话,他们同样可以自由地罢免国王,其依据就是至今犹存的古代法律和礼仪,以及苏格兰高地居民中仍然保存的选举其部落或家族首领的古老习俗。所有这些加上其他诸多理由都说明,王权不是什么神秘之物,它只是国王与人民之间的一种相互协议或约定。”[17](P204)政治契约对英格兰王权也产生了重大影响。1570年的英国硬币正面印着年幼的国王詹姆斯六世接受加冕的图像,背面印着一把出鞘的剑及如下的文字:“如果我的命令恰当的话,就用它来支持我;否则的话,就用它来反对我。”詹姆斯国王在1609年对国会的演说中也使用了政治契约的理论:“国王以一种双重的誓言来约束自己遵守他的王国的根本法律:一方面是默契的,即既然作为一个国王,就必须保护他的王国的人民和法律;另一方面是在加冕时用誓言明白地表明的。因此在一个安定的王国内,每一个有道的国王都必须遵守他根据他的法律与人民所订立的契约,并在这个基础上按照上帝在洪水之后和诺亚缔结的契约来阻止他的政府。”[21](P122)1689年国会将斯图亚特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赶下王位,其理由依然是浓烈的政治契约措辞:詹姆斯国王“破坏了国王与人民之间的原始契约,企图推翻王国的宪法”。[22]其次是层层的领主契约关系。国王与大领主、大领主与小领主、小领主与附庸之间,无不处于在以土地所有制为核心的相互依赖的连锁关系之中。这种土地所有制,伴随着领主的政治统治权与附庸的被保护权、小领主的忠诚宣誓义务与大领主的庇护责任,因此上下等级之间形成了一种自愿的政治契约关系:在下的保证忠实地经营采邑,在上的保证不逾越其法律权限;如果在上的违背保护的义务,在下的就有权撤回忠诚;如果在下的拒绝履行服骑兵役之类的义务,在上者有权惩罚或驱逐之。从下面这份墨洛温王朝时期一个自由民呈与领主的文件,可看出二者之间的政治契约关系:“在我活着的时期,我将在合乎我一个自由人的身份之下,为您服务,维护您的荣誉。我不得退出于您的统治与监护,将毕生投靠在您的势力与保护之下。因此,您我之间,如一方欲退出此种契约,必须付与对方若干先令作为赔偿;此种谅解,永久不得破坏。”[23](P145)最后,在欧洲有许多基于特许状建立的自治城市,这种城市特许状也是一种政治契约。伯尔曼分析道:“许多城镇是依靠一种庄严的集体宣誓或一系列誓约而建立起来的,这些誓约是由全体公民为捍卫曾公开向他们宣读的特许状而作出的……像封建陪臣契约或婚姻契约那样,特许状是一种进入某种身份的协议,即进入一种其条件由法律规定并且不能由任何一方意志所更改的关系之中的协议。”“在某种意义上,特许状是一种社会契约:实际上,它是近代政府契约理论产生的主要历史渊源之一。”[24](P475-476)特许状的政治契约属性其后通过英王给北美的马萨诸塞、弗吉尼亚、马里兰等殖民地颁发的特许状进一步体现出来,像王希观察到的那样,“清教徒们自称他们与上帝之间有契约关系,但在现实中,他们所宣称的抽象意义上的宗教契约(包括他们与上帝之间和他们相互之间的)却通过英王的特许状而转换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政治契约。”[14](P16)
三、国家语境下的契约
从16世纪起,西方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科学发现,如日心说、行星运动规律以及物理运动的一些基本定律和规律,对宗教神权的一些基本假设和信仰提出了挑战,使人们对基督教教义所规定的社会秩序的合理性甚至对整个传统社会的合理性产生了怀疑;人文思想,如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等,用人的眼光来观察世界,主张尊重事实,并力图摆脱神学的束缚,这些著作中理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隐含着巨大的社会变革启示;宗教改革运动破坏了传统神学的权威,对确立个人的思想自由和经济活动自由、实行政教分立打开了方便之门;国家主权学说的盛行,必然要求国家权力组织形式和运作方式的相应变化,并要求为这种变化提供正当化的理由。于是,面对传统的国家合法性理论话语丧失的现实,一些思想家以世俗理性为指导,进行新的社会设计和国家合法性论证。以霍布斯、洛克、卢梭为代表的古典契约论者,“在不同程度上都拥有一个共同的预设前提,这一预设的前提使之既区别于古希腊和中世纪的理论家,也区别于当代的契约论者,它就是国家的人格化。”[25](P16)国家语境下的契约是关于人民相约而组成国家的一种假定:在人民相约之前不存在国家、政府,他们只是契约的产物,所有的个人为了保障自由、人权和公共福利等,相互同意建立国家、设立政府和授予政府权力。
不应忽视的是,在宗教契约论、政治契约论的传统包裹之中,已隐藏了国家源于契约的珠玉。英国神学家胡克尔(1553-1600年)在《教会政府的法律》中写道:“政治社会有二基础焉:一为人性愿享社会生活之天然趋向;二为人与人公然或默然相约共同生活之同意。”有社会生活,必然要有统治者,胡克尔认为,统治者“须得公共同意。无此同意,则一人无为他人君长之理也”。[26](P18)胡克尔提出了双重契约的见解:一是相约而建立社会,二是相约而建立政府。曾于1604-1638年在德国的自治城市爱姆登执政的阿徒休斯认为,人类一切社会生活的基础是个人间的契约,个人契约构成公社、城市、省等公共团体,“国家是由许多城与省联合成的公共团体,在这团体中,城及省合并他们的财产与活动,以契约建立、维持、并保障一个主权。”他将主权看作社会的最高权力,并将其放在人民手中,统治者若破坏契约,人民不但可以反抗、驱逐、处死暴君,还可以脱离该国而加入他国。[19](P48)阿徒休斯的契约思想已近似近代的社会契约论,这种近似表现在:强调社会生活的基础是个人间的契约;高扬了国家生活中人民的地位。英国诗人、政论家约翰·弥尔顿(1608-1674年)通过对正统基督教中人类前政治的、失去伊甸园后的状态的描述,对国家的起源进行了一种契约论的诠释:“从亚当的堕落所带来的原罪开始,人们便陷入了罪孽与暴力之中,由于预见到如此下去必然会导致所有人的毁灭,于是,他们同意通过共同的盟约来互相约束,以防止相互的伤害,并联合起来共同反对任何破坏或违背这种协议的行为。”[20](P51)
1651年霍布斯最伟大的著作《利维坦》出版,作为一种超越私法的契约理论,“它在结构的系统和论证的严密上超越了它所有的先驱”。[20](P57)霍布斯契约论的最大创新在于完全放弃了人们所熟知的国王与臣民、政府与人民之间存在一个契约的假设,而以一般契约说为基础来解释和构建国家的起源。他论述道:首先,这种契约有其订立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人们相约成立国家,是因为人们都认识到了国家之“利”,在国家统治之下的不愉快比自然状态下的战争、掠夺、悲惨、灾难要更好一些;其次,这种契约的订立有可能性,因为人在自然状态下是平等的并可以自由表达意志,因为每人都有一些天赋的自然“权利”,可以放弃这些权利为代价来完成契约的交易;其三,这种契约必定有约束力,因为它是人们平等、自由的意志选择并放弃个人权利而换来的结果,更因为人们畏惧毁约后所产生的恶果。于是,通过协议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付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国家,便成了唯一的选择。⑥
在运用契约来论证国家的起源这一点上,洛克所作的工作远不如霍布斯那样巨大,他不但可以借用霍布斯的论证模式、术语和概念,而且可以重复其观点。但洛克的理论依然具有巨大的创造意义。首先,他认为自然状态是一个美好的自由状态,但存在着一些缺陷,⑦ 为了消除这些缺陷,人们理性地、自愿地订立建立国家的契约。其次,他为这种依契约而建立的国家设定了一些最基本的限制。他所描述的自然状态下的自由平等,特别是人们在自然状态下享有生命、自由和财产权,为设立的国家确定了一个基本限制,即国家必须保护财产、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平、公共福利和各项自由、权利。洛克的理论预设是,既然人们在自然状态下已经拥有了这些,如果国家不能提供更多更新的便利和自由权利,人们就没有理由通过契约来建立国家。于是洛克以他的自然权利说为依契约建立的国家确立了一个基本下限,为限制国家权力、权力分立理论提供了合法性论证。第三,洛克的契约论亦为革命的正当性作了注释。如果在国家的统治下人们的基本权利不能得到保障,表明统治者违约在先,那么人们不仅可以而且必然愿意废除原来的契约,回到自然状态,然后重订契约,建立新的国家。如果说霍布斯国家语境下的契约论,通过强调主权者绝对的统治权和人民对能够有效运用权力的统治者的始终服从义务,从而背离了之前政治语境契约的反专制反暴君传统的话,那么洛克国家语境下的契约论,通过强调以个人主义和自然权利限制国家权威,实现了对霍布斯的矫正和对契约论传统政治倾向的回归。⑧
卢梭不满意霍布斯、洛克及整个自然法学派用主观的意志、思想随意表述和解释国家的起源。⑨ 卢梭断言,人们并没有为了获得公民间的安宁而把自己所有的权利都转让给某个首领,也就是说,人们并没有先签署一项“社会契约”,再签署一项“服从契约”。实际上人们要努力寻找一种能够保护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的形式,这种形式一旦找到,每个结合者便把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共同体,这就是社会契约。通过这一契约,便形成一个代替每个订约者个人的“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这个公共的主体称之为“国家”;至于结合者,他们整体上称之为“人民”。卢梭认为,政府要服从于国家主权,立法权属于人民;政府只是在人民与主权者之间建立的一个中间体,它负责执行法律并维持公民以及政治的自由;每一种政府都是过渡性的,国家必须永远准备着为人民而牺牲政府,却不是为政府而牺牲人民。
然而,休谟、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对契约论的批判,使国家语境下的契约话题几乎销声匿迹。这当然与国家语境下的契约理论的结构性缺陷有密切关系。对这些缺陷,人们可以基于各种理由进行批判:对政治生活的描述是机械的而非有机的、对政治义务的说明是法理的而非伦理的、对政治社会和政治权威的解释是先验的而非经验的。[27](P1)在休谟看来,人们现在的政治义务并不来自于原始契约,而来自于政府明显的优点,诉诸契约是不必要的和不相关的迂回之路;在黑格尔看来,契约是适用于经济领域而不是政治领域的概念,它不能恰当地处理国家的庄严与崇高以及国家因此而加诸个人的义务,根据个人的自我利益来解释国家的合法性,会严重地贬低国家;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既然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以契约为基础的,那么以契约来解释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是一种合适的政治理论,但由于契约的个人主义内涵,它在最终意义上并不适合于所有的社会形态,更不适合于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但是,随着布坎南、罗尔斯和高蒂尔等当代契约理论的兴盛,表明超越私法的契约话题在西方的又一次愈久弥新。
总之,在西方社会,契约话题并没有固定在私法领域,相反,它被用于各种各样的目的,来证明各种现象的正义性、合理性、合法性和神圣性。具体说来,人们可以用它来解释社会、国家、政府、主权者、程序原则和道德宗教的权威。它可能是一个具有永久约束力的契约,也可能是一个需要每代人重新认可的契约;它可能是历史的真实,也可能是一种理想或假设;它的形式可能是公开的,也可能是默认的;订约可能在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上帝之间、人民与统治者之间、家族首领之间、自治团体或城市与国王或领主之间进行,主体多种多样;订约可能是出于宗教权威、政治义务、人身安全、自由权利、经济福利或道德自觉,动机多姿多彩。针对国家语境下的契约话题,柏克曾写道:“社会确实是一项契约。对于那些单纯以偶然的利益为目标的各种附属性的契约,是可以随意解除的,但是国家却不可被认为只不过是一种为了一些诸如胡椒或咖啡、布匹或烟草的生意,或某些其他不关重要的暂时利益而缔结的合伙协定,可以由缔结者的心血来潮而加以解除的。我们应当怀着另一种崇敬之情来看待国家,因为它并不是以单只服从属于暂时性的、过眼烟云的赤裸裸的动物生存那类事物为目的的一种合伙关系。它乃是一切科学的一种合伙关系,一切艺术的一种合伙关系,一切道德的和一切完美性的一种合伙关系。由于这样的一种合伙关系的目的无法在许多代人中间达到,所以国家就变成了不仅仅是活着的人之间的合伙关系,而且也是在活着的人、已经死了的人和将会出世的人们之间的一种合伙关系。每一个特定国家的每一项契约,都只是永恒社会的伟大初始契约中的一款,它联系着低等的自然界和高等的自然界,连接着可见的世界与不可见的世界,遵循着约束一切物理界和一切道德界各安其位的那项不可违背的誓言所裁定的固定了的约定。”[28](P129)柏克的这种评价,同样适用于其他超越私法的契约话题。高蒂尔断言:契约主义已经逐渐由隐蔽到公开地体现在我们的自我意识中,那些不是以契约论为理据的制度和实践正在遭到抛弃或拒绝。[29]这或许是一种夸张,但正是这种夸张,为本文的撰写提供了主要动能。
注释:
① 当然,从单独的“契”或“约”的字源意义考察,二者均具有超越私法的广泛内涵。如唐太宗“执契定三边”,“契”为兵符之称;《礼记·学记》中有“大信不约”之句,孔颖达疏云:“约,谓期要也”;《汉书·高帝纪》有“初,怀王与诸将约,先入关中者王之”,颜师古注曰:“约,要也,谓言契也。”此外,“约纵连横”、“约法三章”等也明显超出了单纯的私法意义。但“契约”连在一起使用,只具有私法上的意义。
② 《法国民法典》第1101条的契约定义稍为注重契约的私法特性:“契约为一种合意,依此合意,一人或数人对于其他一人或数人负担给付、作为或不作为的债务。”但是,“债务”依然并非纯私法用语,译成中文责任或义务也极为顺畅,对照《苏联大百科全书》“合同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公民或法人关于设定、变更或消灭民事权利和义务的协议”的表述,法国人对契约私法意义的有意淡化或模糊,是很明显的。
③ 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后羁于狱中,好友克利同劝他逃出雅典,以保性命,苏格拉底坚决拒绝,他说:我本有离开雅典之可能,而70年来却一直居住在这里,并享受雅典法律带给我的好处,那么我实际上和雅典订立了一种契约,从而默认了雅典的法律。我怎么能当法律给我好处时就遵循它,判处我死刑就违反它呢?况且我接受法庭的审判亦是订约的证据,订约后转瞬背约,岂不是荒谬吗?所以我不能够逃走。参见何怀宏:《契约伦理与社会正义——罗尔斯正义论中的历史与理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21页。
④ 阿奎那认为,如果出现了暴君,那么限制王权,甚至废黜国王,都是合乎正义的:“那就是咎由自取,因为他的臣民就不再受他们对他所作誓约的拘束。”参见《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树槐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60页。
⑤ 教会法院对由宣誓订立的契约有绝对的管辖权,当宣誓达成的契约与教会法有抵触时,宁肯教会法让步,也不要使宣誓而成立的契约受到破坏。
⑥ 下述这段话是霍布斯解释国家起源之契约理论的集中概括:“如果要建立这样一种能抵御外来侵略和制止相互侵害的共同权力,以便保障大家能通过自己的辛劳和土地的丰产为生并生活得满意,那就只有一条路——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付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这就等于说,指定一个人或一个有多人组成的集体来代表他们的人格,每一个人都承认授权于如此承当本身人格的人在有关公共和平或安全方面所采取的任何行为、或命令他人作出的行为,在这种行为中,大家都把自己的意志服从于他的意志,把自己的判断服从于他的判断。这就不仅仅是同意或协调,而是全体真正统一于唯一人格之中;这一人格是大家人人相互订立信约而形成的,其方式就好像是人人都向一个其他的人说:我承认这个人或这个集体,并放弃我管理自己的权利,把它授予这人或这个集体,但条件是你也把自己的权利拿出来授予他,并以同样的方式承认他的一切行为。这一点办到之后,像这样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称为国家,在拉丁文中称为城邦。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31-132页。
⑦ 洛克认为,自然状态下有三个缺少:第一,缺少了一种确定的、规定了的、众所周知的法律,为共同的同意接受和承认是非的标准和裁判它们之间一切纠纷的共同尺度;第二,缺少一个有权依照既定的法律来裁判一切争执的知名的和公正的裁判者;第三,缺少权力来支持正确的判决,使它得到应有的执行。[英]洛克:《政府论》下篇,瞿菊农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7-78页。
⑧ 其实,洛克之前,德国的普芬道夫已经放弃了霍布斯那些令人震惊而反感的论证,缓和了霍布斯的直言不讳,并批判和修正了霍布斯的某些观点,如强调战争似的自然状态不是人类的最初状态、遵守协议的义务先于政府的建立而存在,在政治权威的形成方式上,普芬道夫也与霍布斯发生了冲突。但是,普芬道夫通过为暴政下的良好公民选择逃亡或继续容忍,为霍布斯的政治结论投了赞成票。
⑨ 可参见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71页对洛克及自然法学派的批评、第98页对霍布斯的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