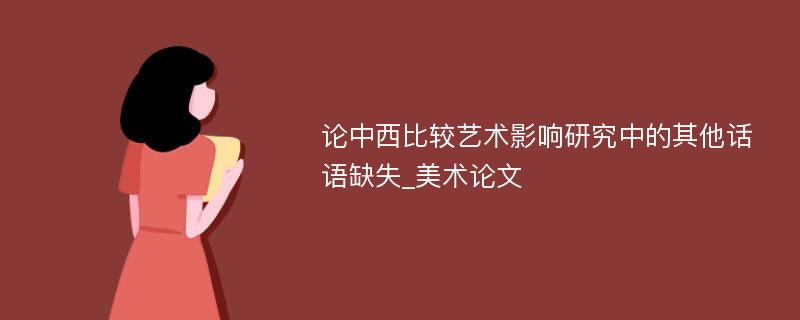
论中西比较美术学影响研究中他者话语的缺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缺失论文,中西论文,中他论文,话语论文,美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0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2854(2010)06-0080-05
影响研究在美国和英国的比较美术中被广泛运用,成为美、英等国家比较美术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如今,影响研究也成为中西比较美术学的研究方法之一。影响研究主要以放送者或影响者的视角研究对他者美术的影响及其关系,基本方式和基本话语是以主体者的身份研究主体文化对他者文化所形成的“亲缘”事实和“精神交往”的联系,在研究他者文化的过程中,考察这种“亲缘”事实和“精神交往”的联系。就是说,中西比较美术学影响研究的基本观点是:寻找中西不同国别或民族的美术在历史的交往中相互影响的“事实联系”,通过事实联系研究中西美术的发展轨迹或路径。可以说影响研究是中西比较美术学中最重要和有效的研究方法之一。但是,由于西方的影响研究在进行中西比较美术学的研究工作中,其话语立场往往忽视“他者”美术自身的发展逻辑所形成的美术形态的基本事实,而把这种“事实”作为主体者对他者影响的结果,有时甚至夸大主体者对他者的影响,成为一种受夸张法影响的某种策略,超出了学术的内在规定性,使影响研究变异为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立场。因而,西方美术史学者在中西比较美术学的研究中所运用的“影响研究”带有明显的他者话语的缺失,并导致研究结论的失效或不准确。
一、西方美术学者的研究视野
我们熟知对我国影响较大的西方美术史学者,比如沃尔夫林、潘诺夫斯基、克拉克、布伦特、詹森、贡布里希、巴克森德尔、夏皮罗等,他们在研究世界范围的美术史中,较少研究非西方国家的美术史。贡布里希在他的《艺术发展史》(The Story of Art)中对非西方国家提及很少,基本上是西方国家的美术发展史,在这部几十万字的巨著中,只是在第7章的“向东瞻望”中用了仅4千字提及伊斯兰教国家和中国的美术。沃尔夫林的《美术史的基本概念》(Principles of Art History,中译本为《艺术风格学》)也没有包含东方的美术,他的“风格学”是建立在阐释西方美术历史的基础上的。潘诺夫斯基在《视觉艺术的含义》(Meaning in The Visual Arts)也没有把非西方国家的美术纳入分析研究之列。西方美术史学者基本上把大量的研究精力和时间投入在自己的美术史方面,对非西方国家尤其是中国古代成熟的美术风格、流派、美术家以及美术批评史论搁置起来不做研究。即或论者,也是作为陪衬西方美术史的地位来做研究,再或者就是研究西方美术对非西方国家包括中国美术的影响。常宁生博士在《扩展的视野》中指出:在美术史研究中,西方中心主义表现非常突出。他写道:“我们从英美国家最有影响的艺术通史教材的编写体例来看,这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表现也是十分明显的,这些著作主要有弗里德里克·哈特(Frederick Hartt)的《艺术史:绘画、雕塑和建筑》(Art:A History of Painting,Sculpture,Architecture)、休·奥纳和约翰·弗莱明(Honour Hugh/John Fleming)的《世界艺术史》(A World History of Art)、海伦·加德纳(Helen Gardner)的《加德纳艺术通史》(Gardner’s Art Through the Ages)、H.W.詹姆斯的《艺术史:从历史的黎明到今天主要的视觉艺术概论》(History of Art:A Survey of the Major Visual Arts from the Dawn of History to the Present Day)和苏珊·沃德福特(Susan Woodford)等编著的《剑桥艺术史》(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Art)。仅以詹姆斯的巨著《艺术史:从历史的黎明到今天主要的视觉艺术概论》为例就很能说明问题。这本在美国高校被广泛代用的艺术史教科书,……这部重要的艺术史教材所讨论的内容除了西方世界艺术的发展历程外,并不包括世界其他民族和文化的艺术。……作者在该书的‘后记’中写道:‘这里的美术主要是指大西洋两岸的文明产物。印度、中国、日本以及前哥伦布美洲的艺术传统早已丧失其生命力,而且这些艺术风格并未对西方艺术产生过重大的影响。’”[1]这个事实说明了西方美术史学者在研究世界美术史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忽视非西方国家的美术史,其研究视野基本集中在西方国家的美术史方面。
20世纪70年代以来,虽然说西方学者也开始思考把研究视野扩展到非西方国家的美术史研究中,也把以前的美术史教材作了一定的修改,加进了一些非西方国家美术史的内容,有的西方美术史学者还专门研究了中国美术史。但是,西方美术史学者的研究视野无不带上西方中心主义的痕迹。尽管英国的美术史家苏利文、美国的美术史家罗樾、高居翰等西方美术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富有新意并对中国美术史学者富有启发,然而他们的研究视野基本上是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研究话语立场上的,用西方的方法论阐释中国绘画。比如罗樾借用沃尔夫林的风格学研究中国绘画,尽管风格学研究有一定的成效,但如果完全局限在风格的研究中,就难以整体看到中国绘画的全貌和解决其它相关问题。甚至罗樾自己也认为:“真伪问题造成了一个真正的悖论:(1)不了解风格,我们就无法判断个别作品的真伪;(2)不确定作品的真伪,我们就无法形成风格的概念。”[2]不难看出,仅仅用风格研究局限了研究者的思维和视野,造成悖论是必然的。西方美术史学者在研究中国美术时,往往用的是西方的概念、观点和方法,必然会对中国美术产生硬伤性的误读,也会有更多的误解。
美国美术史学家埃尔金斯极力克服西方学术研究视野局限的思维模式。他认为:“确定一幅中国画的特征为‘巴罗克’,这么做看来是错误的,至少是不准确的,但是把它称为‘有力的’、‘曲线的’,或者用许多别的巴罗克传统特性的术语来描述,则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3]2埃尔金斯看到了直接套用西方美术史中的概念研究中国美术存在的问题,但是,如果不使用这些概念,埃尔金斯又认为无法研究,这说明西方美术史学者面临了视野问题。詹姆斯·埃尔金斯在《西方美术史学中的中国山水画》(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 as Western Art History)尽力想纠正过去西方美术史学者站在西方主义立场的研究状况。但最后他也不得不承认:“我认识到,即使再熟悉中国绘画,也不能使之显得和西方绘画相平等。最终我认定艺术史本身就有偏见,它崇尚西方艺术:它的叙述、概念和价值都是西方的,有关艺术家的艺术史研究的那种写作观念也是西方的。”[3]3像埃尔金斯这样的西方美术史学者,尽管意识到了艺术史的撰写本身就有偏见,但也难以改变其中以西方为观点的学术视野。这就是西方美术史学者的研究方法和视野中的那种特有的中心主义问题。视野出了问题,其结论必然有问题。尤其是西方美术史学者在中西比较美术学研究中,对中国明清时期的美术一边倒地认为是受到西方美术影响,其中的研究结论有许多值得商榷。
二、“影响论者”话语模式的偏颇
即使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美术史学家把研究视野逐渐朝向东方或中国,但在受视野局限的西方美术史学权威潘诺夫斯基、贡布利希、夏皮罗、贝尔廷等的学术研究氛围中,西方美术史学家话语的偏颇特征非常明显。因为西方美术史学者崇尚西方美术及其西方美术史学的建立结构,显现了西方美术史学本身就带有偏见。从文本到叙述、从概念到价值等都是西方的,对中国古代画家及其作品所进行的美术史研究的观念依然是西方的。也就是说,西方美术史学家把西方美术作为理解和评判中国美术的依据或参照。我们把局限在西方思想理论体系框架中所操行的影响研究的模式论者称为“影响论者”,“影响论者”的基本话语立场是在西方知识体系结构的主导思想中建立起来的话语系统——影响研究模式。“影响论者”的影响研究模式,基于西方的话语立场研究和阐释西方美术对中国美术影响的状况,看到的仅仅是西方美术对中国美术的单向影响。在比较的视域中,用西方的概念阐释中国绘画,用西方的理论架构进行比较,尤其把“他者”的一些传统文脉看作是西方美术影响的结果,使我们看到了影响论者话语模式存在的问题。埃尔金斯在《西方美术史学中的中国山水画》中给我们分析了很多西方美术史学家的中西比较美术学研究的案例,这些案例大部分被埃尔金斯所质疑,主要原因就是比较的基本话语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态度。
用“风格学”的方法做中西比较美术学研究是影响研究的基本话语之一。李雪曼(Sherman Lee)的《中国山水画》(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运用“风格学”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山水画诸问题。我们都知道“风格论”是沃尔夫林创建的研究美术史的方法体系,它观照西方美术和美术史,并不观照中国的美术与美术史,“风格学”基于西方美术风格的演变,研究西方不同时期的美术风格以及艺术家的个人特征等。但是“风格学”不一定完全适合对中国美术的研究,正是意识到这一点,埃尔金斯认为“风格学”方法在中西比较美术学研究中有很大的问题。他说:“风格比较已经变得名声不那么好了,一方面因为这些比较难以理解,另一方面他们会导致两件极不相同的作品之间容易使人误解为相似。”[3]17
本杰明·罗兰(Benjamin Rowland)在他的《东西方的艺术》(Art in East and West)一书中用西方的“浪漫主义”的概念研究中国南宋山水画家马远的作品。他认为马远的作品“是浪漫主义观点的东方的对应物”。[3]24事实上,中国的美术史学家都知道马远的作品到底有没有浪漫主义的因素。显然,用“浪漫主义”的研究方法研究马远的作品是不会太有效的。迈克尔·苏利文(Michael Sullivan)在其《东西方美术的交流》(The Meeting of Eastern and Western Art)中用西方的立体主义观念来比较和研究中国清代王原祁的绘画作品。他说:“甚至连西方现代艺术的立体主义所持有的观点和采用的手法在某种程度上都和清代初年中国的山水画家王原祁相接近。王原祁将山石等风景因素加以分解,然后再重新构成有机整体,这种具有半抽象意义的构成手法曾经被有的研究者比作塞尚的手法。”[4]苏利文把王原祁与西方现代艺术之父的后印象画家塞尚作比较,其中的可比较性是否有效,是值得商榷的,还可以再探讨。劳伦斯·比尼恩(Laurence Binyon)在他的《远东绘画》(Painting in the Far East)著作中把中国的传统美术史比作一个假设的西方传统美术史,这是典型的以西方视角看待中国美术。埃尔金斯因此批评他的“文化价值观绝对是欧洲中心论”。[3]9
即使在以美学为核心的形态研究方法中,往往也有一些“影响论者”的因素,以西方概念为前提,力图用西方的审美观念比较中西方同时期的绘画作品。因而,“以各个时代的审美定义为基础的比较也不见得有益。”[3]17
西方美术史学家认为,“写作艺术史的方案是西方,因此任何中国山水画的历史也是一种西方的尝试,哪怕这段历史是由中国历史学家用中文写给中国读者的也一样。……对一个中国画家的语汇作极微妙的描述,仍然是西方的艺术史。换言之,艺术史,无论它研究什么,都是西方的。”[3]61西方美术史学者不承认中国有自己的美术史写作和叙述,因为他们用西方史学观来观照中国的美术史的写作方式和叙述方式。“中国山水画从来也没有呈现为西方的艺术史,但是它总是必须被构造成西方的艺术史。”[3]62故此在西方学者的眼中,像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显得“古怪”、“不可吸纳”和“格格不入”。[3]62其原因就是西方美术史学者认为《历代名画记》没有西方美术史比如瓦萨里的《意大利建筑家、画家、雕塑家名人传》的叙述结构和表述逻辑。美术史的写作方式或模式,西方美术史家也认为只有西方的写作方式或模式才是“史”的体系与方法,这些都是非常偏颇的话语模式。埃尔金斯一直质疑西方学者包括在西方的中国美术史学者用西方的历史方法研究中国的美术史。
三、他者话语缺失的例证
如前所述,西方美术史学家“影响论者”的基本话语是站在西方中心文化价值观的立场研究“他者”的美术形态,因而,在研究中缺乏客观的真实态度。如果仅仅看到西方美术对中国美术的单方面的影响,往往会放大这种影响因素,由此使“影响论者”研究的结论失去有效性。只要我们粗略地分析中西比较美术学中的“影响论者”代表人物的研究成果,譬如美国的詹姆斯·凯希尔(James Cahild)、高居翰和英国的苏利文(Michael Sullivan),就会发现在他们的中西比较美术学的学术研究成果中,其“影响论者”的结论的有效性值得怀疑。高居翰的主要研究成果有《山外山——晚明绘画》、《气势憾人——十七世纪中国绘画中的自然与风格》等著作以及《明清绘画中作为思想观念的风格》等论文;苏利文的主要研究成果有《东西方美术的交流》著作和《明清时期中国人对西方艺术的反映》等论文。尽管他们的研究成果卓著,而且对中国学者也有较大的影响,但在他们的著作或论文中,由于比较偏重西方的学术话语,造成“影响论者”研究结论有效性的缺失。
影响论中他者话语最大的缺失结果就是:在中西比较美术学的研究中,把研究的视域局限在西方,并没有真正做到跨越中西国界或民族美术的视域与汇通它们之间的文化深层结构,研究成果难以有效。譬如张宏在山水画作品中抛弃结构、秩序的构图规则,而注重如实地描绘自然景物等特征,高居翰则认为“如此忠实地再现视觉经验,以致于牺牲了主题及构图的明确性的现象”,“促使他(张宏)走向描写性自然主义的新画风,这很可能是来自他与欧洲绘画的接触。”[5]27但是高居翰无法证明张宏是否真的见到过他所列举的《全球城色图》这些铜版画。因此高居翰所说张宏受《全球城色图》中铜版画插图影响仅是一种推论或猜测。苏利文也有相似的论点,认为张宏至少看到过传教士带来的书籍,并凭借张宏说过“依靠自己的眼睛”,“画自己看到的东西”的话,就表明张宏不受传统的中国画法约束,而是受到了西方绘画的影响。事实上,“师法自然”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一贯主张。高、苏二人的“影响论者”话语中彰显了较强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遮蔽了自己的研究视野,看不到“师法自然”这个“他者”自身文化发展的逻辑,使研究结论失去了有效性。
再譬如山水画家吴彬。苏利文认为吴彬的山水画“在画中表现出来的特色(仅限于1600年-1610年的作品)很难以其它任何方式来作确切的解释。”[6]32也就是说,吴彬的这一段时期的作品难以用中国传统的技法去衡量,只能用西方的概念来解释。高居翰更是相信吴彬受到了西方绘画主要是版画的影响。高居翰说:“直到1620年代去世为止,吴彬主要往来于南京、北京两地,故时有机缘造访该地的耶稣会,并极可能会看到利玛窦于1601年献呈给万历皇帝的油画与图画书。万历皇帝曾命宫中画师将利玛窦进献的一幅描绘炼狱众魂的铜版画作,加以复制放大并填彩,吴彬或有可能参与其实。”又认为,“无论吴彬是否曾参与上述制作,我们仍可从他的作品看出他与西洋绘画接触的痕迹。”[5]106这些研究结论,难以令人信服。因此有的研究者认为“仅凭主观臆断,或许会将画家们一种自身寻找突破的内在契机都归于外来的刺激,这是十分危险的。”[7]同样,对于有很大争议的龚贤,苏利文虽然认为“完全没有证据能说明他与西方艺术的联系,或称他与传教士有联系”,但是又认为“我们仅能指出他风格中的特定现象,并表示怀疑。”[6]324尽管苏利文也知道没有证据来证明龚贤是否受到西方绘画的影响,但苏利文还是运用了沃尔夫林的“风格学”概念来研究中国绘画和怀疑龚贤的传统因素。这种研究结论值得商榷。高居翰则肯定地认为龚贤受到了西方绘画(主要是版画)的影响。高居翰说:“龚贤与其他画论家曾一再指出其风格的渊源乃是出自北宋。不过,我相信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则是来自欧洲版画的影响。”[5]222用西方美术风格特征来说明龚贤绘画风格特征的相似性,就以此证明龚贤受到了西方绘画的影响,显然正如埃尔金斯说的“导致两件极不相同的作品之间容易使人误解为相似”。可见仅用“风格学”进行中西美术比较的确有问题。高居翰还对龚贤作于1674、1676年左右的两幅山水画与《全球城色》中的一幅铜版画《城市景观》进行了比较,认为这种“观者的视野乃是一近景的山坡眺望远处的村集,江河与地平线。”[5]228实际上,这种构成形式乃属中国传统的最受文人喜爱的“平远”构图形式。郭熙在《林泉高致》就提出了“三远”说,其中就有“平远”。郭熙是11世纪的画家兼理论家,龚贤绘画中的“平远”显然是受传统“平远”说的影响。用中西双方美术都有“平远”的风格特点,以此来印证龚贤绘画受西方美术的影响,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由于“影响论者”的基本话语是以西方文化价值观为中心的立场,因此,研究成果中有效性的缺失就自然难免了。西方美术史学者在进行中西比较美术学研究中,由于身份和文化传统的原因,很难真正做到不偏不倚地进行跨视域的中西比较美术学研究。就连美国美术史学者埃尔金斯也承认:“如果说中国艺术是平等的伙伴,那么只有在多元的文化论的话语中才如此。我们建立了有关其平等地位的理论,但我们并不认真实行它。”[3]10当然,苏利文的认识也有比较符合情理的论点:“不论东方西方,艺术家的创作心理都有某种相似的过程,在人们的心理过程相近时,便可能同样出现类似的山水风景。”[8]不过在实际操作中,他们似乎又忘记了这一点。
影响研究在中西比较美术学的研究中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方法,而且还是主要的研究方法,但如果研究者的立场有问题,其研究结果也会有问题。从以上对于西方美术史学者研究立场的分析来看,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影响论者”的西方美术史学者,在进行中西比较美术学的研究中,研究视域、观念、概念、价值等等都是西方的。以高居翰、苏利文等西方美术学者为代表的研究很大程度上都使用西方的观念系统对中西比较美术学进行研究。西方学者埃尔金斯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特别指出:“在高居翰的系统阐述中,风格已成为观念。就是说,艺术家们寻找和采纳风格,在这种风格中,观念已经在西方被传达,成为基本的有时是专有的含义的载体。概括地说,这种被夸张的风格系统是西方现时艺术界的特征,在西方艺术界它被包含在‘多元化’名下,并被视为对早期艺术明显限制型标准的一种健康选择。”[3]131-132
潘耀昌翻译完埃尔金斯的《西方美术史学中的中国山水画》后,在该书的后面写了一篇题为“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困惑”一文。文中说:“像发展、进步、时空、图式、表现、再现、崇高、优美、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古典主义、矫饰主义、自然主义、反自然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概念都源于西方艺术史,并构成体系,只有在西方才讲得通,其移用于非西方艺术只不过是一种比拟而已,并不是真正的理解。……西方美术史方法论的不断发展深化和西方术语的连续入侵取代了传统的中国话语,从而使中国自身的美术史学萎缩和退化。如今,中国美术史的概念已经不可逆转地西化了,整个史学构架和价值观理论都是西方的。”[9]面对这个基本事实,在中西比较美术学研究中,我们应该重新用自己的话语立场书写中国的美术史,比较研究中国的美术。我们不能完全拒斥西方美术史研究中的有效的方法,但必须注意防止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对中西比较美术学研究的负面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