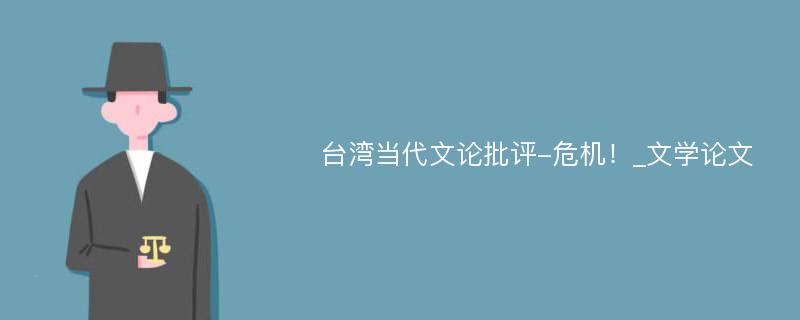
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台湾论文,当代论文,批评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所取得的成就可观,主要表现在: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有建树的学者,出版了不少有份量的学术著作;扶持了不少文学新人,评论了大量的当代作家作品;形成了与中国其它任何省市不同的文学理论批评特色。
但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也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危机。如同他们在国家认同、经济畸形发展、社会生活失调、精神文明崩溃方面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一样,在当代文学理论发展的问题上,他们也处境维难。具体说来,有这样几方面的危机:
一是西方文化对他们的侵袭和腐蚀,使传统价值几乎失落,传统世界观几乎崩溃。本来,台湾当局“经常声称是传统文化的正统继承者,要复兴中华文化。但大家常认为执政党推行的是西化政策,政府在整体表现上也不具民族性格”。这就难怪在50年代,台湾文论界特别是诗论界出现过“恶性西化”的倾向。近几年虽然是“善性西化”,但毕竟还是“西化”。近看80年代后新引进的各种西方文论及流行的各种批评术语等等,就可见当前的台湾文论界西化的严重。尽管有曾昭旭这样头脑清醒的人士呼吁:“建构我们自己的文学理论”“什么时候我们能脱离文学理论的翻译与抄袭阶段,而拥有我们自家的理论体系?什么时候我们能独立地宣示中国文学的民族风格,不再依傍在西方文学的阴影之下而成为人家的附庸?”但响应者寥寥。可以说,目前在台湾文坛成气候的仍然是西方文论的模拟或改头换面和生搬硬套。也有反其道而行之的,也有对西方文论能融汇贯通的,但毕竟不是主流。
二是大陆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冲击。两岸实行民间文学交流以来,大陆的当代文论随着“探亲船”徐徐登陆台湾。以大陆研究和翻译西方当代重要文论的专著为例,透过台湾合法的或地下书商的多方面引进,其作用不仅在于提高台湾文学研究和运用西方文论的水准,而且严重地威胁着那些资深评论家所树起来的霸权地位。那些资深评论家长期以来依赖他们熟练的外语能力,抢先研读西方最时髦的思想文化理论,而不愿意去翻译介绍,以便用这些一般人未见过的理论去制造一鸣惊人的轰动效应。用台湾青年评论家孟樊的话来说,这些评论家的心态是:“与其10个人懂解构理论,不如我自己一个人懂,过样才能巩固我批评的霸权地位。”现在大陆有关解构理论一类的译介和研究专著在台湾书市的出现,无疑改变了这些重量级评论家垄断知识的局面,并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他们的霸权地位。再以文体方面的评论——以现代诗为例,大陆诗评家“对台湾诗作的评述,正从海峡对岸以不能估计的数量倾巢而来。”以至使一位台湾著名诗评家感叹:如果台湾诗评家不坚守岗位,“台湾现代诗的诠释、评鉴,将被岛外的声音所代替、所淹没”。大陆学者对台湾文学的勤奋研究态度及其取得的丰盛著述,也使台湾学者汗颜,并使“海外学者刮目相看。以至留意此间状况的人,不免要发出‘总有一天,国际性的台湾文学研讨会,将在中国大陆召开了’的警告。以及‘台湾面对大陆研究的状况,再不做出回应,未来趋于繁络的国际性台湾文学研讨会,台湾必定丧失发言权’的感慨!”刘绍铭先生在《读书岂能无史》一文中也说:“如果台湾学者不迎头赶上,逼得海外研究台湾的人到广州厦门去找资料,那就怪难为情了。”
这些外来压力,虽然积重难返,克服不易,但只要重视和努力,还是可以将局面扭转过来,但来自内部的压力和危机,台湾当局却长期缺乏应有的检讨和纠正的自觉性。
一是台湾社会“因民主化之不足,经济畸形膨胀,造成了对思想文化发展的若干压制”。试看“经建会”与“文建会”,两者虽同为“行政院”部属机构,但预算却有天地之别。可以说在号称外汇最多的台湾各项建设中,文化建设的投资是最少的,具体说来,还不足当局总预算的百分之一。就是这点可怜的预算,又被不分朝野的立法委员群起而删之。这些政治家——其实是争权夺利之徒,关心的是自己得选票的多少,而设法消解权力和热心发展文化的政治官员是如此稀少。难怪一位研究大陆的当代文学评论家激愤地说:“凡此种种,谈什么教育与文化是百年大计!朝野合力剥削文化人的结果,台湾的文化风貌如此不堪,我们求仁得仁,又有何怨?”
二是经济的迷失,使大部分人热衷于做发财的大梦,这严重地摧毁了作家和评论家的价值观。先拿出版界来说,评论家的专辑和专著早已成了“票房毒药”,偶尔出现的批评年选或年鉴也早成了负债类。这就难怪有人把尔雅出版社停止出版当代文学批评年选(仅出了1984—1988年5册)看作是壮士断腕之举。正因为“这是一个不思不想的时代, ”许多原来的读书人已委身于“不读书界”,再加上评论专著的出版得不到扶持和赞助,所以学界的朋友纷纷相许,升到教授后不再写书,以免自讨苦吃。因此,我们看到台湾文论界的一种怪现象,如果出书,大多数都是已发表过的论文汇编,绝少事先未发表过的系统专著。他们之中“不乏经常上电视5分钟,出席座谈会半小时, 发表演讲两个钟头皆能侃侃的学者,却10年也写不出一本书来。”
三是大学文学教育的迷失。台湾的大学文学教育有大陆不可代替的长处。尤其是培养了众多作家和当代文论家的外文系。可台湾各大学中文系的文学教育,却极不利于文学理论人才的成长。长期以来,大学中文系的文字声韵训诂课程,占了垄断地位。有的学者甚至坚称搞文学必须精通声韵学。这声韵学知识,自然是用来培养古典文学研究人才的。在台湾各大学中文系,很少有人强调学文学必须了解“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尤其是当前文学现状(更不用说大陆文学),这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尤其是师范语文科,现行的《国文教学法》,与文学教育相差十万八千里。1992年,台湾师范大学举办了好几场有关台湾本土作家杨逵、钟理和的学术演讲,可该校中文系不少教授,看到这个演讲的海报,连杨逵、钟理和是谁都不知道。现在有识之士已认识到这一点,提出中文系科要增设现当代文学的教学研究机构,可研究人员和师资力量却无从谈及。只好让那些训诂字词、剖释文法修辞的古典文学教师来充数。这其中虽然有像吕正惠、李瑞腾那样的学者可以胜任,但更多的成绩平平。如果台湾各大学不再把现当代文学当作一门学科来建设,不成立公办和公助的台湾、大陆文学研究机构(现有的机构都是自发性成立的),或把大陆同行研究台湾文学的成绩仅仅视作“统战”的手段,或因其由于资料局限等原因出现的一时失误而不屑一顾,不把其当作激励自己研究的手段,要提高台湾地区的当代文学理论研究水平必然是“戛戛乎其难哉”。要知道,有了公办的研究机构或刊物,就有了凝聚力量,就可减少因山头过多而引起的文坛“内战”。目前,台湾由于缺乏统一的文学家组织和权威的当代文学研究机构,以至弄成派系林立,“文化圈的‘角头’心态往往不逊于黑社会”。比起政界和商界的人群,无论是评论家还是作家都是处于一盘散沙的局面,要他们像大陆评论家那样协作编著大型文学工具书和当代文学史,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当前朝野一片统独辩论声中,“统派”所写的文学史不可能有“独派”,“独派”写的文学史更是将“统派”拒之于千里之外。
可以说,从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台湾整个当代文学在“大滑坡”。目前,台湾仅存的以严肃文学取胜的大型月刊《联合文学》,为了适应“票房价值”的需要,已出现媚俗倾向。由于“孤岛文化”情结,再加上“轻薄文学”连年横扫文坛,使台湾难以出现洪钟大吕式演奏时代的交响乐式作品,难出大作家、大诗人,同样的难出大师级的评论家,这正好与大陆醇厚严谨、稳重凝练、自立豪迈、大气磅礴的文化品格形成鲜明的反差。不过,在“俗文学向纯文学招降”、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在视像文化和速食读物的挑战下难以招架时,文学评论在危机中也好似有了转机。仅以报纸副刊为例,最抢手的不再是文学创作而是短评和短论。“不少文艺营或写作班附设的文学奖比赛,也开始增列文学评论奖。即以恢复停办5年之久的台大文学奖为例, 便增设了第一届台大评论奖;至于文学批评与评论之类的课程,早在一般大学及写作班就已开办,修习的学生人数愈来愈多。”但不要以为这是台湾评论家呼唤了多年的文学评论时代的来临,这里讲的“文学评论”其实是泛文学评论,即用文学的笔法写的政论和短文。80年代,小说家宋泽莱几乎不再搞创作,只写这种文学性的政论;陈映真的小说也“不过是另一种政论形式罢了。”在解严之后,炽热的政治发烧在社会上成了流行病,与政治有密切关系的短评、短论诸如《自由时报》叫座不叫好的“老包专栏”便大行其道,而纯文学评论则随之萎缩。纯文学评论家自命清高,缺乏参与政治的热情,这使台湾文坛不少号称文学评论家的人其实“都是批评家(而且是‘轻批评家’)”。真正称得上有思想(更不用说是博大精深思想)的批评家屈指可数。这就难怪广大读者很少读文学批评,即令龙应台式的为消费者服务的大众化批评也缺乏异军突起,后继乏人。在这种“纯文学”和“新批评”的神话业已被打破的时代,台湾的学者专家及广大读者,对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多半漠不关心,不仅对当代文论,就是对历史文化本身也没有了理想和热情,众多作家乃至评论家对台湾当代文学研究和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建设自然缺乏充分的自信心和盼望。对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市场大幅滑跌也毫不在意。这是严酷的现实,谁也不能否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