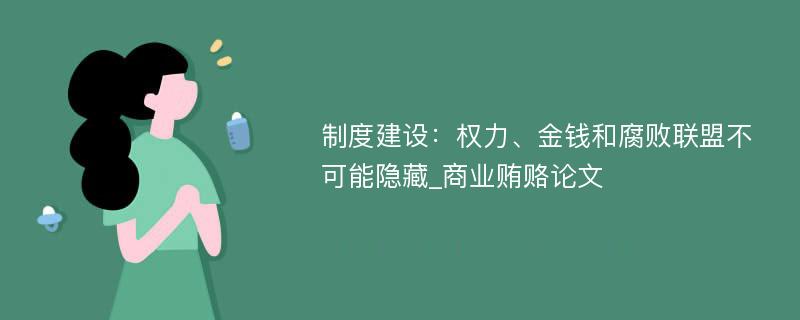
制度建设:让“权钱腐败联盟”无法藏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制度建设论文,腐败论文,权钱论文,联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促进社会和谐的紧迫任务。学习《决定》精神,笔者认为必须将“倡”与“督”在深层次上相结合,开展对“权钱腐败联盟”的坚决、持久而有效的斗争,让其无法祸害社会和百姓。
“权钱腐败联盟”在我国的存在已是客观事实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成就令世人瞩目。与此同时,权钱勾结的腐败犯罪也在社会利益博弈中,呈现出“禁而难止”的蔓延之势。据有关统计,“十五大”至“十六大”期间,平均每月有一个省部级、每天有一个地厅级和15个县处级领导干部因腐败犯罪受到惩罚。2003年1月至2006年8月,国家监察机关共查处贪污贿赂犯罪67505人;仅去年一年,各级纪委就调查了14.7万宗腐败案件,被开除党籍的有1.1万人。这些腐败案件绝大多数都不是简单的个案, 而是具有“窝案”和“串案”性质,腐败金额也越来越大。又据国家商务部估计,最近几年以来,中国大约有4000名大小官员,携带约500亿美元公款外逃。[1] 以上这些并不等于事情的全部。根据国际上犯罪学的“黑数”理论,通常查处的案件往往只是实际发生的一部分,其余的并不一定能够得到完全的揭发和惩办。这样看来,问题的确是够严重的,而且已成顽疾,用触目惊心形容也不为过。
“权钱腐败联盟”的最大特点,就是权力和资本的非法结合,以获取巨大利益为目的,共同实施对社会和国家财富的疯狂侵占和掠夺。譬如,上海滩上的“首富”周正毅,还有号称“公路大王”的张荣坤,他们“一夜暴富”,成为“亿万级富翁”的办法,一不是依靠科学技术,二不是通过合法竞争和经营,三更不是自己艰苦创业所致,唯一的就是依附腐败权力的庇护、支持、怂恿。以张荣坤为例,他2002年初以32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上海城投持有的上海路桥99.35%的股权, 从而取得沪杭高速公路上海段30年经营权;2003年又花50亿元,获得嘉金高速公路25年的收费经营权;2004年福禧投资(张荣坤为其董事长)又出5.88亿元,收购苏州苏嘉杭高速公路有限公司20%的股权,获得30年的收费经营权。人们会问,张荣坤的巨资是从那里来的?不是来自他的口袋,也没有经过较长一段时期的积累,其中60%左右来自银行贷款,30%左右来自上海市的社保基金,其余10%左右则来自对上海电气的重组投资。① 人们还会问,别人不能做到的,为什么张荣坤能做到?唯一的原因就是他有特殊的“权力依靠背景”,所以能够“近水楼台先得月”。
“权钱腐败联盟”的另一特点,就是具有“黑”“红”两面性。权力与资本的非法结合,其途径是见不得阳光的,全部都是“暗箱操作”,党纪国法和规章制度被视为儿戏;其获得之巨额财富,全部属于“来路不明”的不义之财,经不起法律和道德的“追问”和透析,人民利益全都被置之度外;其活动方式是依靠自己的“小圈子”和“一帮哥们”,充满匪气、霸气、江湖义气。以上属于“黑”的一面,然而另一方面,权力与资本勾结的表现形式,往往又总是要千方百计染上“红”的颜色,以便招摇撞骗、混淆视听。腐败分子在台上都是一本正经,给人以“良好印象”,一部分还身居高位,甚至是地方上的“第一把手”;而那些被庇护的不法奸商们,常常又被包装成“红色”。张荣坤的“红帽子”就有“上海市慈善总会名誉副会长”、“上海市工商联副会长”、“上海市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全国青联常委”等数顶。“黑”是本质,“红”是假象。“两面性”使得“腐败利益联盟”对社会的欺骗性和危害性更大,更难以被发现和惩治。
“权钱腐败联盟”是“权力寻租”和“商业贿赂”这两种腐败的结合
所谓权力腐败,就是党和国家干部利用公共权力,损害人民群众的权利和利益,沦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为个人或小集团谋取私利。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认为,从国家的起源和发展来考察,“公共权力”是从“社会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的一种力量,它在历史上(阶级社会中)日益同“人民大众相分离”,并造成国家公职人员“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2] 恩格斯曾经指出,在古代东方,掌握了政治权力的“社会公仆”,正是在从事灌溉、治水等公共工程的过程中上升为“暴君或总督”的。[3] 西方学者亨廷顿,把权力腐败形象地叫做“政治寻租”,就是将手中掌握的权力蜕变为“商品”,谋取非法的、损害社会的利益。他说:“腐败的基本形式就是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的交换。”在这个交换过程中,政府官员不只是扮演一个被动的、被利用的角色,而是以“主动出击”的方式,进行“政治创租”和“抽租”。[4]
社会主义国家按其本质是与腐败不相容的。但是在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特殊的社会转型时期,某些干部手中握有权力这一社会的稀缺资源,确实存在着资本化的欲望和可能,这种情况如果得不到有效遏止,一旦权力转化为商品,并作为资本加以运用,就必然会产生权力腐败。为此,吴敬琏先生将这种现象叫做“权贵资本主义”②,即一种畸形的或坏的市场经济,其中一些人通过权势和关系网寻租致富,而在成为既得利益者后,则对种种合理的市场化改革从各方面大加阻挠。邵道生先生提出了“权力资本腐败”③ 的概念,特指一些“有权人”和“有钱人”之间的“权力与资本的交易(运作)”,无偿地占有国家的财富和百姓的财富。例如,在土地批租中,普遍存在政府官员给农民和住户很少的赔偿,而将土地以低廉之价转手给开发商,使其获取暴利;震惊国人的厦门远华案、湛江走私案、沈阳慕马案、上海社保基金案等等,都是地方上腐败分子的“权力”与不法富豪的“资本”相互“交易”(腐败)的结果。
腐败分子手中的“权力寻租”,往往需要通过不法企业家和商人的“商业贿赂”才能实现。所谓商业贿赂犯罪,指的是发生在资本和商业领域中严重破坏交易秩序的钱权交易行为。这种行为在我国开始是以“回扣”形式出现,现在则在国有企业改制、土地出让、工程建设、产权交易、资源开发、市场经销等领域大行其道。商业贿赂滋长腐败,官商勾结侵蚀吏治。据有关统计,部分省市商业贿赂案件在全部贿赂案件中的比例已经达到九成[5],更可怕的是, 商业贿赂已经被视为资本和商业运作的“潜规则”和“润滑剂”。据悉,房地产开发商“公关”成本就普遍占到楼盘总成本的3%到5%或更高,有了权力做靠山,资本就更加霸道,导致房价虚高,目前已经揭发出来的不少腐败案件都与房地产相关。
又如工程招投标,近几年全国已经有十几个省市的交通厅长在公路建设工程中因贪污受贿而被判刑,河南省交通厅更是连续三任厅长锒铛入狱,而这些工程不少只能是“豆腐渣工程”。
再如鉴于小煤矿矿难事件不断,2005年中央着手清理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投资入股问题,一年就有4878人申报,登记入股金额达7.37亿元[6], 基本上都是由矿主们送的“干股”,作为回报就是官员庇护他们非法经营和获取暴利。值得注意的是,商业贿赂还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一是行贿人和受贿人的职位都具有比较高的“两高”特点;二是不仅以金钱,而且以“美色”对干部进行贿赂,不少高官落马都与此有关;三是贿赂“期权化”,往往是在官员离职或退休后给予兑现。
要从政治的高度认识“权钱腐败联盟”的危害性
历史证明,腐败如同社会机体上的毒瘤,任其扩散,势必危害社会,葬送政权。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打天下化了整整18年,由于不能清廉执政,进入北京城仅40余天很快就垮台了。鉴于此,黄炎培先生在访问延安时提出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问题。当时毛泽东自信地回答道,中国共产党能够跳出这个周期律,靠民主和人民监督来解决腐败问题。1949年在党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京时,毛泽东又意味深长地说,这是进京去赶考;并且表示中国共产党人绝不学李自成,我们会考出好成绩来。但是事实证明,尽管党中央几代领导人都高度重视反腐败问题,也取得一定的成效;尽管执政党的主流是好的,大多数党员和干部是廉洁奉公的,然而真正解决腐败问题决非易事。特别是在党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在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的环境中,面对“权钱腐败联盟”的日益蔓延,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如何卓有成效地拒腐防变,已经成为执政兴国、执政为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过的“坎”和“关”。
政权是政治的核心。我们必须学会从政治的高度去认识腐败问题,又从政治的高度去增强反腐败的能力。目前有一种观点是错误的,即重经济轻政治,甚至认为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成本”和“代价”,“权钱腐败联盟”能给地方带来GDP的增长。在这种错误认识下,腐败分子甚至成了当地的“能人”和“功臣”,社会不同程度产生“腐败认同感”和“羡腐心态”。这是很可怕的现象。列宁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7]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是必须遵循和不可违背的。因此邓小平强调指出:“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8] 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经济搞不好会垮台。经济一时搞上去了,如果腐败现象泛滥,贪污贿赂横行,严重脱离群众,也会垮台。因此,如果听任腐败现象发展下去,执政党就会走向自我毁灭。广大老百姓对“权钱腐败联盟”的忧思和强烈不满表明,腐败分子的恶劣行径已经成为导致社会不公平的重要因素,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障碍。
现代政治围绕政权运转有两个基本轴心,这就是权力与权利。权力,主要是掌握在领导和管理国家事务的党政官员手中;权利,主要是社会全体公民应当享有的各种利益。所谓从政治的高度看问题,归根到底就是正确处理好权力与权利的关系。执政党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权力不是为群众的权利服务,并且受到群众权利的监督,而是利用权力鱼肉百姓。事实一再证明,领导干部如果把自己当作个别特殊利益的代表者,甚至不惜出卖手中的职权,与那些特殊利益群体的资本相勾结,就一定会形成“权贵资本”,必然导致对社会、群众、国家权益的吞噬。因此,“权贵资本”是产生腐败的社会基础,必须予以铲除。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定要搞市场经济,要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鼓励各种所有制企业的共同发展。这一点是不能有任何怀疑和动摇的。但是江泽民强调指出:“我们搞的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如果离开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的市场经济的性质。我们的创造性和特色也就体现在这里。”[9] 因此,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反对“商业贿赂”。从根本上说,市场经济是以公平竞争为前提的,而“商业贿赂”则扭曲了市场公平的基础,使大批诚实信用的经营者失去公平交易的机会,这是对市场秩序的破坏,更是直接导致腐败产生的原因。现在国际上盛行“企业公民”这一术语,其核心观点就是,企业的成功与社会的健康发展密切相关。因此,企业要负有社会责任,其中包括遵守法律法规,维护合法的市场竞争秩序。我们要用普遍加强“企业公民”建设,来抵制和反对“商业贿赂”。
反对“权钱腐败联盟”需要深层次的“倡”“督”结合
“反腐倡廉”,反映了执政党和政府对腐败和廉政的两种根本对立现象的鲜明态度:对于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坚决反对;对于为官清明、廉洁奉公,积极提倡。一个“反”,一个“倡”,善恶分明,有利于加强干部队伍的“自律”。为此,对党员干部就要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防止和克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防微杜渐,增强抵御各种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侵蚀的能力。所以“反腐”的同时,必须进一步做好“倡廉”。然而,多年来的实践说明,制度才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这就需要监督。“廉政”对于干部不只是提倡之事情,而是一定要做到的;也不是靠提倡就能完全解决问题的,更加需要的是加强体制、机制、法制“三位一体”的监督。哈耶克说:“所有权力都易腐败,绝对的权力则绝对地腐败。”[10] 所谓绝对的权力,就是没有监督的权力。由此,孟德斯鸠提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会休止”;也就是说,“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 [11] 鉴于我国“权钱腐败联盟”的严峻形势,反对腐败必须“倡廉”、 “监督”结合,着力加强制度建设,着重解决监督缺乏和不力的问题。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好的体制可以有效地预防和制止腐败的发生,反之,不好的体制,则会导致腐败的滋生和蔓延。
反腐败的制度建设有两个基本方面:一是防范腐败的制度,二是揭露、追查和惩治腐败的制度。没有制度就谈不上监督,有了制度没有监督也不管用。监督对行为主体来说是一种“他律”,是外在力量的监察、督促、控制和制约。“自律”是“他律”的内化。如果没有“他律”的监督,“自律”就有可能沦为空谈,“倡廉”就有可能变成“唱廉”。现在我们有的干部权力大了,就放松对自己的要求,直接监督他的人也少了,利用他、为他抬轿子的人则多了,如果不及时教育和监督,就会产生特权思想,置党纪国法于不顾,就很容易出问题,甚至出大问题。对干部强化经常性的监督管理,实质上是一种爱护,反之则是害干部。
我国开展对“权钱腐败联盟”的斗争,现在已经进入制度建设的阶段。从一定意义上说,好的制度就是让人不敢和无法腐败的制度。为此,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法规,如近期颁布的《反洗钱法》,将贪污贿赂犯罪及金融犯罪的违法所得,首次确定为反洗钱的重点监控对象,这就有利于及时发现贪官赃款的来源和流向,为查处提供了线索和保障。类似的法规今后还需要不断完善,如尽早出台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等等。有了法规更要防止流于形式,要加强依法行政的力度。2006年年初,胡锦涛总书记就要求将反商业贿赂列为今年六大要务之一,接着又颁发了《关于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意见》,但是落实查处仍进展不快。如近期发生的“郎讯案”和“德普案”,暴露了中国商业贿赂的严重性,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至今受贿的中方人员似乎还没有受到中国法律的应有处罚。因此惩治腐败要加强监督力度,加强惩罚性的体制和法制建设,加强党和政府在控制腐败方面的权威性。
监督是一项社会阳光工程,只有将公权置于阳光普照之下,增强体制的透明度,有效地受到专门机关和人民群众的监督,才能有效地防止和打垮腐败。监督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应当相互配合,形成反对“权钱腐败联盟”的强大社会综合压力。从政治体制结构的角度看,应当有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协监督、司法监督。从关系的角度看,应当有群众监督、工会监督、民主党派监督。从层次的角度看,应当有纪律监督、舆论监督、法律监督。从组织的角度看,应当有中央、地方、部门的专门机构监督。从形式角度看,既要有自上而下的监督,也要有自下而上的监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要发挥社团、行业组织和中介组织这样一些非政府、非营利性民间组织的监督作用,使“公民社会”在反腐败斗争中发挥作用。现在的问题是,我国有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但其反腐败的政治功能发挥不够充分、不够理想,尤其是群众对干部的监督、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几乎是虚的,很难落在实处。在这方面不妨借鉴以色列的经验,他们有一个“国家廉政运动”(MQG)的民间反腐败组织,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个组织的主要目的就是告诉大家:“即使政治家们都是圣人,他们也可能犯错误”;“腐败也许不可能根除,但遏制腐败不再是天真的想法,每一个人都能为反腐败出一份力。”[12]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加强反腐败的国际性合作,致力于高效率的反腐败机构建设。通过上述监督力量的配合,可以对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发挥多方面的功能:预防性功能(尽早觉察和排除问题,防患于未然);参与性功能(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惩罚性功能(对犯罪分子绳之以党纪国法);信息性功能(提供和反馈各种社情民意);促进性功能(对反腐败和廉政的实效进行评估);以及教育性功能(舆论和政治思想导向)。
“督廉”从根本上说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因此,它更需要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保证。在这方面确实有许多工作要做,根本的是通过制度建设,保障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并引导一切公民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这就要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提高他们的权利自我保护意识,参与到反腐败的斗争中来。要努力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树立社会主义法制权威,实现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要完善司法体制和机制,维护司法公平正义,切实发挥司法在反“权钱腐败联盟”中的积极作用。特别是要充分发挥人大对“一府两院”官员的任命、罢免和监督权,要充分发挥政协对党政干部廉政情况的民主监督权。要通过各种民主程序考查干部,用民主机制保证干部的“德才兼备”,防止搞“小圈子”,杜绝任人唯亲的少数领导“一锤定音”的做法。
注释:
① 关于张荣坤收购国企的数据,可参见周瑞金发表在“炎黄春秋”2006年第10期《从周正毅到张荣坤》一文。
②③ 这两个概念可参见2006年8月24日光明网《权力资本严重破坏社会公平》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