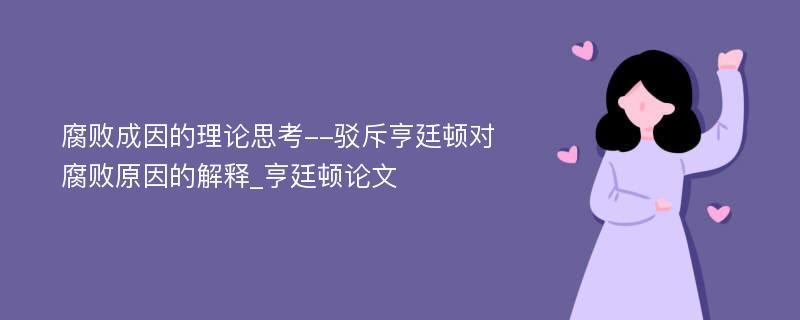
关于腐败根源的理论思考——驳亨廷顿对腐败根源的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根源论文,腐败论文,理论论文,驳亨廷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腐败是与人类文明共生的痼疾,自从私有制社会的产生和政治权力的出现以来,所谓政权的腐败问题也就出现了。随着社会的发展,腐败问题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人们渴望消除腐败,代之以廉洁的政治,因而试图对腐败的根源加以思考。在这方面,美国当代学者亨廷顿(S.P.Huntington)对腐败现象的解释成了人们经常引用的经典性思考。亨廷顿说:(1)现代化使社会基本价值观念发生变化,过去的准则可以容纳的行为用现代标准来看不能接受,现代政治中的平等、自由、公正、人权等价值观念排斥传统价值观念指导下的某些行为;(2)现代化开创了财富和权力的新来源,拥有新财源的新集团运用经济实力参与或影响政治过程,穷者用政治权力换金钱,富者用金钱换权力;(3)现代化在政治体系的输出端发生的变化促进了腐败,即现代化要求政治体系强化管制,强化管制提供了腐败的机会。[①]
亨廷顿的这个解释看上去是从历史与现状二个方面对腐败现象的全面思考,而实际上却是非常片面的。因为,他把腐败问题从社会的总体中孤立出来,仅仅将其看作是一种政治现象,而解决政治问题只能采取政治的手段,所以反腐败的唯一选择就只能是通过政治制度的健全和法律制度的完善。事实上,自从有了政治以来,人们从未松懈过改造政治制度和完善法律制度的努力,但腐败问题却日甚一日,如果我们继续将此作为唯一的选择,仅仅从政治制度的健全和法律制度的完善这条道路上去实现对腐败的根除是永远不可能的,因为政治制度的健全和法律制度的完善本身就是一种有待证实的可能性。将一种现实的要求寄托在一种可能性的基础上,是一种非常不现实的和浪漫的空想。更何况亨廷顿对腐败现象的解释本身就存在着故意忽略诸如所有制因素、政权的阶级性质因素、精神文化的历史性质因素、价值观念对政权结构和运行方式的影响问题等许多不足,那么,根据这种解释设计出来的任何具体方案,都必然是不切实际的。鉴于亨廷顿对腐败现象所作的这一解释在我国学术界和思想界已具有了思维导向的意义,我们对其作简要的分析是有必要的。
二
根据亨廷顿的意见:从历史的角度看,本来就存在着某种政治现象,但是,人们由于持有某种价值观念而不认为那是腐败,现在,由于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那些原先不称其腐败的东西成了腐败;从现状看,一方面“财富”与“权力”相分离,而另一方面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又越来越增强,政府干预为公务人员的腐败提供新的机会,在政府中从事公共管理的“穷人”必然会与经济活动中的“富人”进行权钱交易。
亨廷顿对腐败的这种理解乍看上去似乎是合理的,其实不然。
首先,在现实中是否存在着一些原先不被认为腐败的腐败现象呢?回答应当是肯定的,特别是当一个社会处于过渡时期,是存在着这个问题的。但是,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却不应是亨廷顿的解释。因为,亨廷顿是把这种现象解释为从属于旧的价值观念的政治行为与新的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对那些从属于旧价值观念的政治行为的否定性认识。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旧的政治行为会存在于新的价值观念之中呢?我们知道,人的行为是受利益驱动的,而实现利益的方式则取决于人们所持有的价值观念,特别是在充溢着理性的政治活动领域,人的价值观念对人的行为的支配作用愈显突出。因为,在这个领域中,人的情感、情绪是受到限制的,它们即使要发挥作用,也必须被理性化为人的价值观念之后才会得到合理的形式,更何况政治本身就倾向于价值观念的共享、共有或共同遵守。就一个社会而言,可能会存在着作为整个社会主体的阶级、集团等的思想与行为、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和冲突,但是,在政治活动的领域中,在作为个体的活动主体身上,是不存在不可避免的价值观念与行为之间的冲突的。除非在执行一种错误的强制性命令的时候,才能有可能出现违背自己的价值观念的行为。但据常理推测,在所有来自上层的错误命令中,强制腐败的命令将是极其有限的,是理论研究可以不予考虑的。所以,价值观念与行为之间是一种从属的关系,不可能有亨廷顿所说的所谓新价值观念与旧行为或传统行为的矛盾,只存在着新旧价值观念之间的矛盾。
在社会的转型和过渡时期,一些在原来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下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旧的特权被作为腐败现象,这是客观事实。一些特权的享有者继续固守着原先的价值观念,并极力维护其已有的特权,也是常见的。但是,这种意义上的腐败毕竟是暂时的,随着新的价值观念的确立和社会转型的完成,这种意义上的腐败也会在人们意识到它的存在而逐渐消除。总之,人们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这种腐败,它也就会在多大程度上失去其存在的权力。所以,这种腐败从来都不会成为政治腐败的一种重要形式和主要部分。因而,亨廷顿在这种意义上来思考腐败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从我国的情况看,在改革开放之初,的确有过反对旧特权的斗争,但却很少有人将这种特权看作是腐败,人们只是把这种特权看作是与旧的体制相伴生的存在物,看作是旧体制弊端的一种表现形式。在渴望改革和呼唤新体制的情况下,是把反对旧特权作为改革的一部分来看待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当人们开始意识到腐败问题的时候,能够引起人们普遍不满的特权已经很少了,而且也很难准确确定哪些特权是属于腐败范畴的东西。可见,认为由于价值观念的变化而把一些原来可以接受的东西看作腐败是一种不合乎实际的臆断,在现实中并不存在这个问题。从西方发达国家来看,80年代后期以来,恶性的腐败事件不断地被曝光,以致于人们把腐败看作是人类世纪末的一场政治灾难,但是西方发达国家在价值观上的变化却是很少的,可以说,平等、公正、自由、人权的价值观在近300年也未发生过重大变化,那么,如果说这些腐败问题一直存在的话,为什么过去一直能够容忍,而现在基于同一个价值观,却不愿容忍呢?
腐败是客观存在和不断滋生着的,一切对腐败的认识都是事实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如果把腐败看作价值观念变化的主观意识,就必然会造成思想混乱,它使人们以为腐败问题不是“正在产生的”而是“原生的”,是一个本来就已存在着的问题,只不过过去人们没有意识到它,而现在才开始认识它。也就是说,在人们面对腐败的情况下,亨廷顿的这种解释会使人们造成错觉,而这种错觉要么是淡化了腐败的消极社会影响,要么是让人容忍腐败,如果人们不愿容忍腐败的话,那么也只会把腐败归因于过去,从而,淡化了对腐败的现实根源应作的批判性审视。
三
关于腐败的现实根源问题,亨廷顿的解释可以分为两个层次:(1)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开辟了财富和权力的新来源;(2)在这种条件下,有权的“穷者”与有财富的“富者”之间发生了权钱交易。
的确,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开辟了财富和权力的新来源,但是,财富和权力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中是否存在着必然分离的趋势?亨廷顿认为所谓权钱交易必须是在权与钱相分离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如果权与钱之间是直接统一的,那么权钱交易就不可能发生也没有必要发生。同样,在“穷者”与“富者”之间是否必然存在着交换关系呢,或者说必然发生着“穷者”与“富者”的权钱交易吗?在亨廷顿看来,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陈述。实际上并非如此,亨廷顿之所以会作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他把社会分为财富和权力的两极,以为掌握财富的人必然是没有权力的富者,而掌握权力的人必然是没有财富的穷者。
在近代社会的开端,是存在亨廷顿所讲的“财富”与“权力”的分离过程的,特别是在欧洲各国资本主义社会从中世纪的土壤中萌发的过程中,存在着固守封建特权的阶级和阶层,作为第三等级中的部分成员是在远离政治权力的经济领域中取得了成功和获取巨大的财富积累的。随着财富积累达到可以左右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的时候,年轻气盛的资本家阶级开始提出权力要求,因而权钱交易变成了一种客观现实。而且,在一些资本家那里,用金钱交换爵位也是被允许的,并且不被视为政治腐败的行为。但是,这种意义上的权钱交易早已成为历史,我们所讲的腐败是专门指称晚近政治社会中的一种消极政治现象。而现代社会中“权力”与“财富”的成长往往是同步的,即使存在着一些例外,也不可能把“权力”与“财富”的分离概括为一种普遍现象。我们知道,在以选举为特征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手段的民主方式越来越把权力和财富联结在一起。没有“财富”的背景和金钱的基础,是根本不可能实现向权力的进军的;同样,掘取权力无非是实现财富合法增长的手段而已。所以,从总体上看,当代社会并不存在着普遍的所谓“财富”与“权力”的分离。在掌权者的阵营中是没有所谓“穷者”的,在拥有财富的“富者”之中,即使存在着不直接掌权的人,也是与权力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
亨廷顿为什么会提出这种“假说”呢?
我们认为,亨廷顿是停留在权钱交易的表层来看问题的。在现代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以权钱交易为特征的腐败现象,而权钱交易作为一种“交易”与发生于市场中的一般意义上的交易有相似的特征,即交易者是以自己手中所有的东西交换自己手中所没有的东西。由此出发,亨廷顿首先想到交易双方手中的所有物分别是“权力”与“财富”,继而假定交易双方手中由于各自没有对方所有的东西而形成所谓“穷者”与“富者”的概念。其实,权钱交易与一般意义上的交易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因为,虽然这种交易发生的前提是:权钱需要分别掌握在交易双方手中,但权的非私有性质决定了这种交易的深层是一个政治伦理或行政伦理的问题。也就是说,即使存在着“权力”与“财富”分离的情况,也并不意味着必然发生权钱交易的问题,并不是所有掌权的“穷人”都会用权去与金钱相交换,反过来,掌了权的“富人”也并不是每一个都会拒绝权钱交易。
亨廷顿的“假说”潜含着一种思维导向,那就是要求“权力”与“财富”必须结合在一起,在政府权力机关彻底排斥“穷人”。因为,根据亨廷顿的意见,权力机关中的“穷人”就意味着腐败,最起码,“穷人”是可疑的腐败者。正是在亨廷顿的这种思维导向下,我国近年才出现了所谓“高薪养廉”的论调。这实际上完全是一种误导,如果高薪能够养廉的话,那么就不会出现王宝森之类的大案。因为,对于穷奢极欲者来说,再高的薪金也是极其微薄的。所以,我们认为,亨廷顿把腐败与“穷人”联系在一起是极其不公正的,由此引导出来的任何反腐败对策性设计也必然是不合理的。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存在着亨廷顿所说的“财富”与“权力”分离的事实,但是,如果将此看作腐败的根源,那是非常肤浅的。因此,许多人希望作出更深一层的思考,认为制度的不完善和法律的不健全,是腐败得以滋生的根源。实际上,这是从亨廷顿的解释中进一步推导出来的。无疑,制度的完善和法律的健全是非常重要的,但制度的完善和法律的健全并不是根除腐败的唯一保证。在西方发达国家,是有着令他们引以为骄傲的所谓民主制度和健全的法律,为什么却又存在着那么严重的腐败问题呢?而在我们国家,同样的制度和法律条件下的不同地区或单位,为什么在廉政建设方面却大有区别呢?所以,把反腐败完全寄托在制度和法律建设上,必然会走入死胡同,只有把制度、法律建设与政治伦理或行政伦理建设结合起来,才能在内外多个角度上实现抑制腐败的目标。
腐败的总根源深植于私有财产制度,从长远的观点看,只有彻底消除私有财产才能彻底根除腐败。然而亨廷顿对此避而不谈,只是在“现代化”的名义下揭示腐败的根源,认为现代化造成了腐败。这样一来,势必给人造成历史悲观主义的印象。事实上,我们极力促进经济的发展,推动现代化的进程,正是为了全面推动社会进步,以求以一种全新的社会取代现存的私有制社会,并彻底清除现存社会所派生的政治腐败等阴暗面。但是,反腐败是一个系统工程,行政伦理建设正是这个系统工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这一方面却长期遭到了忽视,即使在大力倡导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在如何行动的问题上也是模糊的。所以,我们认为,关于反腐败的理论探讨是不能满足于亨廷顿的解释的,而是应根据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对此作出积极的思考。
注释:
①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65—6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