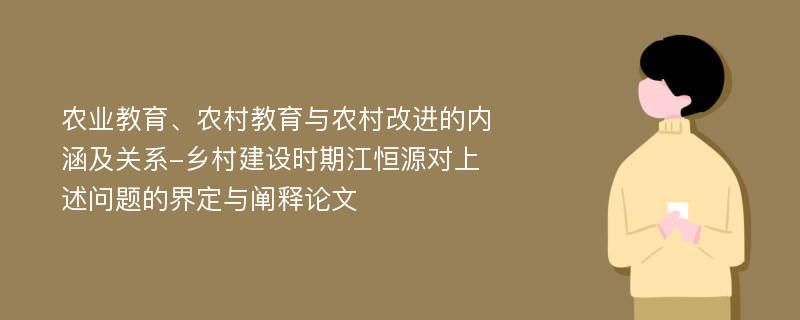
农业教育、农村教育与农村改进的内涵及关系
——乡村建设时期江恒源对上述问题的界定与阐释
王志蔚 刘旭光
摘 要 农业教育、农村教育和农村改进是一组内涵相对独立而又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概念群。界定其内涵,阐明其关系,是20世纪20年代末职业教育由城市转向农村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开展农村改进事业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江恒源基于“大教育观”的科学认识,丰富和拓展了农村教育和农村改进的内涵,划清了农村教育与农业教育的边界,在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对于当下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 农业教育;农村教育;农村改进;内涵关系;理论意义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五四”新文化思想感召下,一批关注农村破产、秉持力图民族复兴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为救活农村,纷纷奔波于农村之中,从事乡村建设实践。他们“或从农业技术的传播入手,或致力于地方自治与政权的建设,或注重于农民文化教育,或从经济、政治、道德三者并举开端,试图为破败的中国农村寻找一条救济与复兴的出路”[1],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在乡村建设实践中,时任中华职业教育社办事部主任的江恒源以极大的热情和浓厚的兴趣,积极投身于乡村建设(黄炎培称之为“农村改进”)运动,在总结徐公桥试验区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写出了《农村改进的理论与实际》《村治与农村教育》等多部农村教育著作,提出了“富教合一主义”等具有重要影响的农村改进理论,厘清了农业教育、农村教育、农村改进(以下简称为“三农”)等概念内涵及其关系,清晰地回答了农村改进工作中的一些疑难问题,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农村教育思想体系,在乡村建设运动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Costanza等人 [2]对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cosystem Services Value,ESV)进行了定量估算,其研究成果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原理和方法从科学意义上得以明确。谢高地等人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考虑到苏州市的具体情况,确定苏州各类型土地的生态服务价值系数(表1)。根据谢高地等人的方法计算苏州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其公式为:
一、什么是农业教育
(一)农事教育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黄炎培是较早关注农业教育的职业教育家。民国初期,他在《江阴、南通、苏州农业教育调查报告》《在山西三星期间之工作》等文章中多次运用“农业教育”“农事教育”等概念。然而,对于什么是农业教育、什么是农事教育,黄炎培并没有给予明确的界定和解释。作为黄炎培职业教育事业的紧密合作者和中华职业教育社农村改进工作的具体执行者,江恒源对黄炎培提出的两个概念进行了认真思考。他把农业教育放在农事教育的大范畴中加以认识,认为“农事教育可以分农学教育、农业教育和农人教育”。其一,农学教育。“所谓农学教育即是大学教育”,“偏重研究学理,属高等教育范畴。农学教育任务首先是结合中国情况学习传播国外先进的农业知识技术工具材料,其次是研究改良本地农业的土壤、技术现状”[2]。如民国金陵大学、中大农学院、岭南大学等。其二,农业教育。“农业教育是指在正式的农业学校、农业补习学校或临时的农业讲习所,在农事试验场及农业推广部对农民进行的农事知识教育”,属于中等教育或高等教育层次,是“社会式的农业教育”。农业教育的培养对象,“一种是技术的人材,直接从事于实地工作,一种是推广人材,受高等农业人材之指引,将各种新的智识,新的方法,直接的或间接的向农民介绍,将农科大学所研究的结果,依照计划努力推销”[3]。其三,农人教育。农人教育即农民教育,“指对农村青年、成人、儿童的教育,既包括普通教育,也包括农业教育。”从上述界定可以看出,农学教育属于高等教育,培养研究型农业人才;农业教育有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两个层次。农业教育是一种广义的教育,包括正式的农业学校和非正式的农民补习学校、讲习所等。其教育对象是农业技术人才和推广人才;农人教育是小学教育、补习教育和农业教育,其教育对象是农村青年、成人和儿童。
(二)农学教育、农业教育与农人教育的联系和区别
江恒源认为,农学教育、农业教育和农人教育是农事教育的三个方面,三者是相互联系的。农学教育“为大学专科所有事,目的在研究关于一区域的农事农业问题,得着解决之方,可以推行于农民”[4]。也就是说,农学研究是针对某一区域农事农业问题的研究,其研究成果有赖于农业教育的应用和推广。“农业教育是培养实际经营农业和推广农业新方法,指导农民的实施人才”,以农业学校和农业补习学校为主体,大都属于中等职业教育。农业教育是衔接农学教育和农人教育的中心环节,地位十分重要。农人教育中,“青年和成人是推动农村社会的中坚人物,农童是中国将来农村组织的柱石,必须加以相当教育,农事才有进展可言,农村才有进步的希望”[5]。在农事教育三个层级中,农业教育是关键。因为没有这一层级的教育,“大学所研究出来的方法,就无推广到农村的希望;而一般中等农业学校毕业生,也就与农民无接近的可能”[6]。在江恒源看来,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体,农业是农民赖以生存的产业,农学是研究解决人类“吃饭穿衣”问题的科学。与之相适应,“农民教育是谋农业的维持,农业教育是谋农业的发展,农学教育是谋农业的改进。”“前二种是关于农事教育的实施成分居多,后一种是关于农事教育的研究成分居多,三者是相因而非各别”[7]。应该说,江恒源对农事教育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和把握十分准确,对其内部关系的认识和阐述也很透彻。从农事教育的属概念具体阐述各个种概念内涵及关系,加深了人们对农业教育内涵的认识和把握。
二、什么是农村教育,它与农业教育有什么区别
农村、乡村是同一概念,是指城市以外的地方。1930年,江恒源对此有过具体而形象的解释:“我们要知道农村是什么,然后才可以讲农村的教育,不然便是隔靴搔痒。”“农字的上面,是臼或林,下边是辰。他的意思,便是朝夕操井臼造林的工作叫农,农人住的村落,就叫农村。农村有山村水村平原村的分别:山村的人,住居山旁,他们靠种植和打猎来度日,民性大都刚直强悍。水村的人,是依水而居,他们除种榖之外,还去打鱼,民性活泼敏慧。平原村人,靠树艺五谷,以谋生计,民性和平宽大”[8]。1937年,陈兆庆《中国农村教育概论》认为:“今之所谓农村,不是像我国古书上所说的以万二千五百家为乡的一种机械式之划分,而是以教育为立脚点,无论其为城,为市,为镇,为乡,如其文化低劣,教育幼稚,工商业等不大发达,而仍以农业为其主要之职业的地方,都称之为‘农村’”[9]。陈兆庆认为“农村”既是一个地域概念,也是一个产业概念,是“以农业为其主要之职业的地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学界更多地认同和使用“乡村教育”,而很少使用农村教育概念。《教育大辞典》没有收录农村教育词条,就是一个例证。我国最早重视农民问题、关心乡村教育的是李大钊。最早界定乡村教育内涵的是教育家余家菊,她指出:“从地域上界定,认为乡村教育与都市教育相比较,并无特殊内容。它是包含除都市教育外的一切教育在内的一种教育形式”[10]。黄炎培是乡村教育的重要代表之一,他的《农村教育〈弁言〉》第一次使用了“农村教育”的概念,不过,他当时所说的“农村教育”,主要是指“乡村职业教育”。从现有资料看,最早界定和具体解释“农村教育”内涵的应该是江恒源。他在《农村改进的理论与实际》中指出:“在农村特设机关认定一般农民生活需要,以实施种种改善农民生活的方法,是为农村教育”。其教育机构和教育方法多种多样。有乡村小学、补习学校,还有农品陈列室、农品展览会、各种讲演会、农民教育馆等。“教材是随事随时供给的,教法是因地因人设施的”,教育对象“并不限定何人,而总以促其反应,开通其知识,增长其经验,为惟一目的。”上述教育机构是“农村学校教育”,也是“农村社会教育”。“所谓农村教育,则为混合二者之总名”[11]。由此可见,江恒源界定的“农村教育”是广义的概念,是指在农村区域面向农民多种形式的教育,是以试验区全体农民为对象,不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富的、贫的、驯良的、狡黯的、健全的、残废的,一齐在内”的教育。它不仅包括乡村小学,乡村中学,临时设立的种种讲习所、传习所、民众夜校式的补习教育,也包括农民教育馆、农民问字处、讲演会等不同方式的社会教育,还包括农民生计、农民健康和娱乐、农民组织、农村建设、农村防卫等村治教育。江恒源为什么把村治纳入农村教育范畴呢?他认为,农民如何促动,如何启迪,如何指导,如何推行,离不开教育的方法。总之,农村教育是一种大教育,是“乡村全民教育”和农村生活教育。
转化思想是把未知解的问题转化到在已有知识范围内可解的问题的一种重要的数学思想方法.我们经常通过不断的转化,把不熟悉、不规范、复杂的问题转化为熟悉、规范甚至模式化的、简单的问题.
三、什么是农村改进
农村教育与农村改进有什么关系?江恒源认为,农村改进是随着农村教育功能的扩大而产生的概念。“乡村教育要从学校的活动进而为社会的活动,将课室里的活动搬到农村社会去活动,真正的乡村教育,要把农村改良,就是乡村改进”[21]。在他看来,农村教育不是单纯的教育活动,而是社会的活动,农村教育的目的就是改造乡村。因此,农村教育与农村改进,部分内涵是相同的,但并非完全一致。“因为教育事业,原包括于改进事业之中,而改进事业,却不限于教育一种。又照通常习惯,所谓农村教育,大率指农村小学而言;而在农村改进事业中,所包括的教育范围,则至广且大;凡一切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皆属之”[22]。由此可见,农村教育与农村改进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农村改进的内容包括农村教育,农村教育只是农村改进的一个方面或一部分,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综上所述,培养农业人才,推介农业研究新成果、推广应用新技术、新方法,改进农业教育,离不开农村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补习教育,也离不开“有组织、有卫生、有建设”“自给、自立、自治”的农村改进。农村教育是实施农业教育的依托和平台,是农村改进的重要途径,是衔接、贯通农业教育和农村改进的“渡桥”。农村改进是一个包含农业教育和农村教育以及农村经济、农村卫生、农村自治等内涵的系统工程。三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而又相互促进,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四、“三农”之间有什么关系
农业教育、农村教育、农村改进是一组关系十分密切的概念群。在《乡村教育——上海县学员听讲笔记选录》中,江恒源指出,农业教育和农村教育“关系甚为密切”,主要理由有二个:一是“农村教育之设施,注重农人生计,生产之改良,然必须有农业专门人材,为之指导”;二是“近来学者,对于农村教育,因何如是之热烈,考其原因,即昔者农业教育,将对于农村之关系,完全置诸脑后。学校设于都市,与农人隔绝,平时实习,纯系贵族式的,卒业之后,不能实用于农业”。他认为,农村教育的主要对象是农民,农民的生产技术需要农业专业人才为之指导。如果脱离农村实际,“与农人隔绝”,农业教育就失去了依托和实际意义[19]。在《乡村教育》中,他再次强调农村教育和农业教育的关系“却是很大,因为要注意农村教育,须改良生产。要改良生产,全靠农业教育”[20]。这两者互相依存,相互促进,是农村改进的两个重要方面。
又是农业教育,又是农村教育,两者有什么区别?针对农村改进工作中遇到的疑惑,江恒源从教育目的、教育层次、教育范围、教育内容等方面进行了具体说明。他说:“农村教育与农业教育,两者不同,未可相混。农村教育,是为改良农村生活而设;农业教育的目的,是要养成农业专才。农村教育,是平民的初等教育;农业教育,是有大学中学小学的等级。农村教育,范围广阔,内容有五:农民生计(物质的);农村的建设(道路桥梁);农民的健康;农民的娱乐;农民教育(读书识字)。所以农村教育,是改良农村生活;农业教育,则专为养成农业专门人材与知能,与什么健康娱乐,完全无涉”[12]。他在《农村改进的理论与实际》中又指出:“农村人民以农业为生活主体,农村教育为适应农民生活计,当然以发展农业,增加农产为惟一中心,虽然农村小学,谈不到农事教育,但关于职业陶冶,势必以农事为重要教材,这是无可疑惑的。不过要说到农民整个生活,却又不是农业一端所能包括殆尽。通常人往往会把农村教育,认作农业教育,这显然的是一种错误了”[13]。在这里,江恒源认为“农业教育是职业教育,这个概念至今仍在沿用”[14],这不能不说是江恒源对农村教育理论的一大贡献,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具有开创意义。
农村改进是黄炎培在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之后试办农村试验区过程中提出的概念。他说:乡村是整个的问题,教育只是其中的一种方法,“把全部农村改进的事务,统统包在我们责任范围以内”“不应该单从教育入手”[15]。在这里,黄炎培第一次使用了“农村改进”的概念,但对“农村改进”同样没有界定或解释。当时,江恒源经常与黄炎培一起深入徐公桥试验区开展调查,指导工作,非常了解黄炎培的乡村职业教育思想,他根据黄炎培“划区施教”原则作了如下解释:“农村改进”是指“一农村或若干农村,划定一个适当区域,依照理想的能实现的预定计划,用最完善的方法技术,以化导训练本区以内的一切农民,使全区农民,整个生活,逐渐改进,由自给、自立,以达自治,俾完成乡村的整个建设。此种区域,称做‘农村改进区’,或‘乡村改进区’。改进区内所办各项事业,称做‘农村改进事业’,或‘乡村改进事业’”[16]。他认为,农村改进有教育、经济和组织三大目标。其中,教育目标是“使全区儿童,完全入学,不识字之青年成人,完全减除,知识开明,风俗敦厚,发挥互爱互助之精神,共谋本区文化之进展”;经济目标是“使农事改进,生产增多,家给户足,百废俱举,村容野容,焕然改观,健康安乐,疠疫不兴,养生送死,毫无遗憾”;组织目标是“使人人能自治,能合群,视公事如己事,扩大爱家爱乡之心以爱国”[17]。从三大目标可以看出,“农村改进”的主要内容是教育、农事、组织、卫生等。江恒源认为,农村改进是改良农业的最好工具,“是地方自治的渡桥,是辅导人民达到生活改善的过程”“是适应中国农村特殊需要除去中国农村贫、愚、弱、散的危症的特殊方法,是救济农村衰落,完成农村建设,实现教育救国的根本办法”[18]。
他盯着我,我也没有把目光移开。他不是狗(个性测试中出现的恶狗),但其中的道理大致相同:移开目光就等同于屈服,直视他的眼睛是挑衅,而这正是我所选的。
五、江恒源“三农”内涵阐释的时代价值
(一)丰富和拓展了农村教育的时代内涵
农村教育是一个历史概念、动态概念,其内涵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发展而变化。弄清其内涵,划定其边界,历来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农村教育有狭义广义之分。在江恒源看来,农村教育涉及范围很大,应该是一个广义概念。“抑知今日中国农村所需要的教育,绝不是这样,应该放大范围,以全村人民的生活为对象”。农村教育不仅包括农业知识和技术教育、乡村小学教育、农民补习教育,也包括“农品陈列室、农品展览会、各种讲演会、阅书报室”等形式多样的活动教育,是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社会教育、正式教育和非正式教育的总和。今天,学界对农村教育内涵的理解分歧依然很大,主要观点有三种:第一种是指面向农村地区的教育,第二种是指以农民为教育对象的教育,第三种是指为农村建设发展服务的教育。国外给农村教育的界定,首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处,其内涵是指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包括有文凭的全日制正规学习和短期非正规的成人扫盲学习以及技能培训[23]。第一种观点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处的定义是“地域论”,把教育限定在农村地区。第二种观点是“对象论”,限定农村教育的对象是农民。这两种定义综合起来与江恒源的界定完全相同。第三种观点较为切合当下实际,它与前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农村教育中还包括“城市里的直接或间接服务于乡村发展需要的普通高等教育与中等、高等职业教育等”[24]。虽然江恒源的定义并不完全符合当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日益变化、农村人口和村落正在减少、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现实,但它准确地反映了乡村建设时期的客观实际,为当代更科学地界定农村教育的内涵和外延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揭示了农村改进内涵关系的辩证统一
在农村改进过程中,江恒源从普遍联系的观点看待农村教育相关概念,具有很强的启示性。在农事教育概念群中,江恒源把农业教育放在农事教育的属概念中加以认识,阐述了农学教育、农业教育和农人教育的内涵及相互关系,突出了农业教育在农学教育和农民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乡村建设时期,甚至在今天,人们常把农业教育与农村教育混为一谈,是因为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叉关系。农村教育包括农民文化知识、生产技能、吃饭穿衣、卫生健康等农村生活。在农村生活中,发展农业生产,帮助农民致富,改善生产条件,解决生计问题的过程是实施农业教育的过程,是提高农民文化知识、技术知识、思想道德水平的农村教育过程,也是提高村政自治水平和能力的农村改进过程。江恒源把这种辩证统一的过程概括为“教富政合一”。这里的“教”显然是指农业教育和农村教育,“富”即发展农业生产,促进农民致富,“政”即村政自治。他认为,“教”“富”“政”三位一体,共同构成了辩证统一的农村改进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实现“富”和“政”,教育始终是一个重要手段。农业教育、农村教育贯穿在发展农业生产,组织农民自治,改进农民生活的全过程,是农村改进的一条主线。教育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同时也是服务政治。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毫无疑问,江恒源的“教”“富”“政”辩证统一的思想对于当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
(三)提出了农民精神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在阐释农村教育、农村改进内涵时,虽然江恒源重视“以经济生产为惟一中心”,以教育为主要手段开展农村改进,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但同时,他也强调农村改进内涵的文化要义。他说,农村改进“不外经济、文化、政治三端”“这三端”“文化最大的效用,在启发自动”。无论组织民众,训练民众,还是教育民众,首先应启发民众,激发和凝聚民众的自动力量。“讲农村教育的人,要以农民生活为对象,讲到农民生活,要先注意到物质一方面,不要把他们一个最根本的问题——‘穷’字忘掉!因为今日农民的一切病象,皆是从一个‘穷’字发出,则治病之要,当然要使他富,而于教他致富之际,施以适当教育,便是最良好的知识教育和道德教育”[25]。在《何谓农村改进——农村改进的意义、范围与目的》中,他特别强调“物质问题以外,对于精神方面,亦绝对不容漠视”[26]。做好农村改进工作,只有首先解决农民温饱问题,同时渗透文化教育,提高其精神文明水平,才能促进农民致富与精神致富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否则,农村改进就变成了脱离教育、脱离伦理道德等精神文化层面的物质主义。对于农村教育来说,农民教育是根本。农村学校无论正式与否,都是农村文化的中心,也是农村中智慧最密集的地方。农村改进不仅需要农民有知识、有特长、有能力,还需要有高层次的精神追求。“救活旧农村”,要在致富的同时,更多地关注农民精神品质的提升,改造国民精神。当前,由于功利主义等诸多因素影响,农村扶贫工作中仍有一些干部以为农村教育就是科技教育、职业教育,把过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扶智、扶贫、脱贫,这当然必要,但是,扶贫、脱贫终究离不开“扶志”。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美丽乡村,不能忽视农民精神文明建设。没有农民精神文明的现代化,就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也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
(2)签证工作。重视签证工作,签证前必须现场察看确认工程实施及工程量,联系单和签证单内容应认真审核,严谨出具签证意见。
参考文献
[1]孙君,廖星臣.乡村建设实践与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4:28.
[2][3][4][6]江恒源.关于中国职业教育的六个中心问题[J].教育杂志,1935(9):9-18.
[5][7]米靖.二十世纪中国职业教育学名著选编[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304.304.
[8][12][13]江恒源.乡村教育[J].中华教育界,1930(4):1-13.
[9]陈兆庆.中国农村教育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1.
[10]余家菊.乡村教育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1934:20.
[11][25][26]江恒源.农村改进的理论与实际[M].上海:生活书店,1935:4.55.59.
[14][20]刘桂林.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思想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258.
[15]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教育文集(2)[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453.
[16][22]江恒源.农村改进与农村教育[J].中华教育界,1934(4):1-12.
[17]江恒源.中华职业教育社之农村工作——农村改进事业之动机[M]//章元善.乡村建设实验(1),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34:39-51.
[18]江恒源.中华职业教育社之地方自治辅导工作[J].地方自治专刊,1937(1):109-117.
[19]江恒源.乡村教育——上海县学员听讲笔记选录[J].上海县教育月刊,1929(22):13-33.
[21]江恒源.乡村教育与乡村改进[J].湘湖生活,1932(1):1-4.
[23]国家教育委员会,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当代国际农村教育发展的改革大趋势——农村教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上)[C].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225.
[24]李森,汪建华.我国乡村教育发展的历史脉络与现代启示[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61-69,190.
Connotation and Relationship of Agricultural Education,Rural Education and Rural Improvement——Defini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Jiang Hengyuan in Period of Rural Construction
Wang Zhiwei,Liu Xuguang
Abstract Agricultural education,rural education and rural improvement are a group of concepts that are relatively independent,interdependent and mutually reinforcing.Defining theirs connotation and clarifying their relationship are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s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to shift from urban area to rural area in the late 1920s.It is also a theoretical problem that Chinese Vocational Education Society urgently needs to solve in carrying out rural improvement.Based on the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the“Great Education Concept”,Jiang Hengyuan enriched and expanded the connotation of rural education and rural improvement,and laid out the boundary between rural education and agricultural education.It has a pioneering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and it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current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Key words agricultural education;rural education;rural improvement;connotation relationship;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中图分类号 G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9)33-0076-05
作者简介 王志蔚(1961-),男,江苏师范大学连云港校区高教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黄炎培教育思想(连云港,222006);刘旭光(1973-),男,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质量监督处处长,教授,研究方向:江恒源教育思想
基金项目 2018-2019年度连云港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江恒源教育思想研究”(19LKT0003),主持人:刘旭光
Author Wang Zhiwei,professor of Lianyungang Branch of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Lianyungang 222006);Liu Xuguang,professor of Lianyungang Teachers College
标签:农业教育论文; 农村教育论文; 农村改进论文; 内涵关系论文; 理论意义论文; 江苏师范大学连云港校区高教研究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