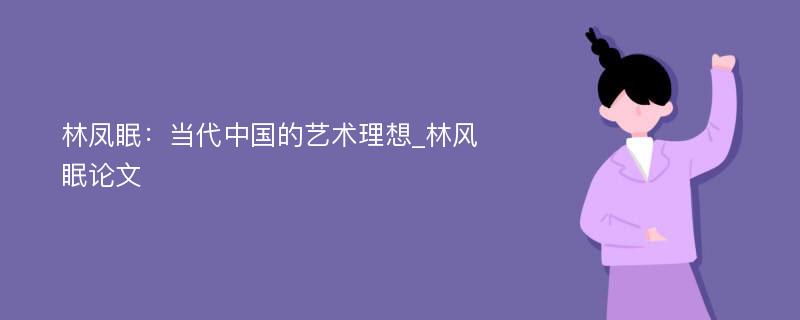
林风眠:现代中国的艺术理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理想论文,艺术论文,林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即使是在二十一世纪,林风眠的画作仍然给人以浓烈、新鲜的感受。如果将这些作品还原到上个世纪,想象它们在民国一九三零、四零年代众多庞杂的作品中给人的观感,在新中国建立后慷慨激昂的主题创作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林林总总的中国现代艺术中的面貌,对比同时期的西方艺术,这种独特性就愈发凸现,它们所呈现出来的新鲜浓烈的“现代感受”和“现代品质”就愈发独特。
中国近代的特殊精神诉求一方面要求突破传统,成为“现代”的;另一方面又必须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建构成为“民族”的。林风眠的艺术理想不是传统文人画所代表的知识阶层或贵族阶层,也不是现代的个人的表达,而是可以象征代表中国社会理想和民族精神的艺术。林风眠在 1934年就认识到,艺术必须同时传达出时代性和民族性,这成为他对待中西艺术资源的出发点①。在《什么是我们的坦途》中,艺术家这样论述其艺术理想:
……从个人意志活动的趋向上,我们找到个性,从种族的意志活动力的趋向上,我们找到民族性,从全人类意志活动的趋向上,我们找到时代性;一切意志活动的趋向,都是有动象,有方法,有鹄的的;……(把它们)再现出来,或从不分明的场合表现到显明的场合里去,这是艺术家的任务,也是绝佳的艺术的内容。②
这里的“时代性”,就林风眠的整体艺术论述而言,核心在于“现代”的意义。艺术家对于个性和时代性的理解,是以“时间”作为切入点的,与时间紧密关联的经验成为艺术家关注的中心。终其一生,林风眠都在努力地找寻能够表达他的时代经验的艺术语言。在从艺术的起源来思考艺术的特性和发展历史时,林风眠非常强调艺术形式的发展与人类文明的进程有同样道理,艺术形式好比方法,都经由经验产生与变化:“人类能应用其所有之经验,而产生方法,又能利用方法将其所有之经验传散于群体之中,不断的增进其经验而伟大其后代”③。而“艺术……表现之方法,需要相当的形式,形式之演进是关乎经验及自身,增长与不增长,可能与不可能诸问题。”④对于经验的强调,对于经验对形式的主导位置的强调,表明林风眠艺术理想鲜明的时代意识。正是这个时代意识,使他获得突破传统艺术和西方现代艺术双重束缚、创造自己民族的现代艺术的动力。他指出国画“最大的毛病,便是忘记了时间,忘记了自然”。国画模仿抄袭的方式不能够“直接表现画家本人的思想感情”,导致“绘画的内容与技巧不能跟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⑤
他所热切期望的,是寻求现代感觉的表达,这种“现代感觉”在其艺术中所体现的,是情感热烈饱满,表达直接、强烈,充满现代的新鲜感觉,充满了力与美的艺术,是将民族性与时代性融合的艺术。这一艺术理想源于艺术家使命的自觉:处在近代转折的中国所需要的,一方面是以西方现代的新精神打破旧的文化思想禁锢,造就充满了力与美的新文化;另一方面,中国的文化艺术又面临着西方和现代的双重压迫,构建自身的民族文化身份成为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人必须面对的精神焦虑。林风眠在借鉴西方现代艺术的同时,几十年所苦苦探索的,是如何建构自身完整饱满的精神内涵。他从中国传统民间艺术、古代艺术和西方现代艺术中找到了精神、审美和语言表达的资源,并通过不懈的努力将它们转化为真实饱满的表达。
从林风眠艺术的语言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怎样在传统资源(包括壁画资源、民间资源、文人画资源)和西方现代艺术资源之间取舍、借鉴、融会与创造,最终旨向表达中国现代民族艺术的理想。这种表达方式和语言特征,是含混繁杂的,但经过艺术家顽强意志力和艺术理念的统摄,又以直接而单纯的面貌呈现在观者眼前,以饱满热烈、摄人心魄的力量打动凝视它们的观者。
光与色成为林风眠艺术表达的重要因素。他所表现的光与色和西方的自然主义写实传统没有丝毫的相同。统一的光源,每个物体在光线照射下统一的受光部与背光部,这些原理没有被采纳;法国印象派绘画所赋予光色的有如细胞般的分解与表现也不存在。林风眠综合野兽派和象征主义的表现方法,强调原色的运用、突出色彩的质感和直接的情感表现,同时赋予色彩以一种诗意的、象征意味的角色。他的色彩既强烈、直接,又抒情稳重,充满力量和热情,又具备民间的质朴感和浓郁的抒情气息。他赋予每一棵树、每一座山以不同的色彩,在同一个意境中彼此联系着,微妙地呼应着。秋林中,每一棵树都是那么简单,一个粗黑挺拔的老树干,上面是一串串饱满的叶子,使树披上一个椭圆的饱满的外衣;每一棵树都有不同的颜色:墨绿色的,嫩绿的,火红的,藏在后面的,半个身子露在前面的,它们紧紧挤在一起坚实地站立着,构成一片幽深灿烂的世界……那些静物也是一样的,在幽暗的室内勃然盛开着、充满生机地站立着或温柔地沉默着,原来是什么颜色并不重要,只是在那一个整体中高高兴兴地安静地生长——的确,林风眠的静物是在生长着的,它们不要做没有生气的东西……
林风眠用色的方法,很可能从西方野兽派所赋予色彩的情感表达的功能、野兽派和象征派的用色方式中获得启发,回过头来从中国传统中找到更加贴切的表达方式:魏晋时期和唐代的敦煌壁画、五代的设色山水、宋代绘画,以象征的方式运用色彩,用色单纯、强烈而效果丰富。林风眠在此基础上挖掘色彩的直接性和表现力,拓展了传统色素的领域,结合野兽派中卢奥、德朗等人对原色、补色的大胆运用和充满原始稚拙和力量感的笔法,赋予色彩一种灿烂感、厚重感和深邃感,借助色彩表现出一种新的审美体验。
林风眠对于色彩的运用与西方野兽派存在许多差异:以色彩的心理内涵和情感表达的强度而言,他都未达到后者的深度。他的作品没有后者那种被压抑之后的情感表达的粗野和叛逆性,色彩元素的探索领域相对狭窄,在挖掘内心自我意识的变化和深度上、在表达的直接和微妙程度方面都不及后者。这样的状况源于表达目的之不同:林风眠的艺术想要构建的是一个成年人遭遇外来的困境后重新获得精神力量和更生的信念而诞生的灿烂境界。这个世界与西方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早期、中期的艺术世界截然不同:它摈除了西方艺术充满了压抑、愤懑、不安和焦虑的世界,它不需要生活在边缘位置的艺术通过个人传达出无力感与躁动以及越来越主观化和极端化的表达形式。林风眠需要用色彩作为象征塑造一个稳定而热烈的情感世界,这个世界没有怀疑、质问、颓废和骚动,而是充满着自信、成熟、灿烂和力量的美。
他作品中的光线运用也是非自然主义的。在自己创造的密实饱满、充满幽深感的空间中,灿烂的阳光使他的作品始终保持着明朗健康的情感特质,他不愿自己创造的意境令人产生恐惧感或生出世之想。当人们沉溺于传统文人惯常以文弱的笔法描出的岸边细柳,再遇见林风眠那秋岸边以一抹满溢着阳光的浓浓的嫩绿表现的柳树,人们会惊叹原本脆弱细碎衰颓的东西被他赋予了怎样坚强、灿烂而优美的精神与外形。在这一抹绿色中,阳光创造了一个明朗新鲜、充满成熟的力量和优美情怀的精神世界。林风眠的作品摆脱了对于光线的直接描绘,用水墨、水彩等混合材料创造出一片片映透着光感的色域。在没有直接光源的室内静物作品中,艺术家以源自画面整体结构需要的、打破写实的物与物、物与空间的塑造关系的主观描绘的空白来替代光线,配合干脆利落的造型与笔法,使得幽暗的室内沉睡的花花草草坛坛罐罐获得一种大气舒展、明朗健硕的美。光由外在物质内化为一种诗意的核心品质,成为作品的灵魂。
在林风眠盛期的艺术中,隐现、灵动、闪烁着的光线所代表的,是一种经历了世界与内心的起伏走向灿烂成熟的诗意与美,它超越了具体对象而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在1958年的一本名为《印象派的绘画》的小画集序言中,林风眠这样描绘印象派的世界:
印象派这种油画技法,使阳光下的一切像舞蹈般的跳跃着,使人感到万物变化无穷,永不休止,一个如此光辉灿烂的万千世界霍然呈现在人们面前……⑥
对印象派的这一描述透露出艺术家自身的艺术理想—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花鸟实验作品直至二十世纪末,林风眠始终顽强追求着这一种精神品质与艺术境界:灿烂、明朗、热烈,充满诗意,充满着“力与美”。这个生机勃勃的光辉灿烂的世界可以拯救、涤荡那些在现实的物欲与争斗的苦痛中的人们,让人们感受到生命的力量、世界的美好。对这一理想的追求与实现,使一个个体在不断变化的历史境遇中,在遭遇丰富的人生经验的同时逐渐走向坚定和成熟。
新的造型成为林风眠审美理想的另一重要表达手段。在林风眠的作品中,抽象性与直观性始终并置,严格整饬的几何形式与强烈鲜明的视觉效果始终结合在一起。
他的艺术从西方现代艺术中吸收了几何造型作为画面结构和物象造型的基本构成形式,这些形式更多地得益于欧洲二十世纪早期的艺术,如立体派艺术、莫迪里阿尼和抽象派艺术。他作品中几乎没有“不成形”的因素:大气磊落的直线、水平线与垂直线、饱满优美的曲线、整饬鲜明的方形与长形、变化的三角形、浑厚而充满张力的圆形构成了画面的主体。这些形与线以和谐单纯的方法组合,每一个物象在经过概括之后都以比自身更加单纯鲜明的面貌出现在观者面前,充满了健硕、饱满的力量,这无疑体现了林风眠经常强调的“现代人”所感受的“快感”。配以同样单纯鲜明的色彩,使得作品既充满了力度和形式语言的美感,在视觉表现上又非常直接强烈,与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的表达方式颇为神似,也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文人画的构图模式和造型方式。
实际上,无论是在色彩、造型、用线等艺术语言的把握上,还是在追求鲜明、直接的表达方式上,林风眠都从中国民间艺术和古代艺术中获益良多。这也是他得以与传统文人画和西方现代艺术拉开距离的根本点。在这一点上,林风眠的艺术道路无疑受到齐白石的启发。
田黎明先生曾经说齐白石的作品“在感觉上很近,在审美上很远”⑦,我觉得这是在说齐白石的艺术在形式语言上经过对传统的深入研究和探索之后具备了深厚的审美内涵,而他又有意借鉴民间传统,部分地变革了文人画的语汇,使表达更加直接而强烈,让人感受到一种亲切性。齐白石的革命性正在于此,他汲取了民间传统的养料使文人画的表达获得了新鲜的生命力、质朴的力量与亲切的面貌,这体现在物象造型、笔墨和色彩的运用,意境、趣味、主题的开拓等多个方面;同时文人画传统中充满的哲思和文人意境的深邃精妙,又在其笔下得以延展,并且表达得更加简练、味道更加朴拙淳厚。齐白石将民间的表达方式、欣赏趣味带入传统文人画之中,不仅更新了文人画的趣味与意境、提炼了文人画的语言,还发展了传统,表达出新鲜的现代经验。
林风眠在1927年回国之始即认识到齐白石探索道路的价值⑧,经过十年的探索,在三十年代末期才真正找到表达的方法。就对待传统文人画的态度、表达语言和审美趣味而言,林风眠的艺术追求与齐白石差距很大,但齐白石对于民间传统的摄取无疑给予林风眠极大的启发,正是传统民间精神、审美趣味和表达方式的启发使林风眠获得借鉴西方现代艺术、寻求到现代感觉、反拨传统文人画趣味的根基和切入口,防止他在借鉴西方现代艺术语汇的同时陷入盲从与皮相的模仿。应该说,齐白石在二十世纪初期开拓了中国近代艺术的新路径,民间艺术的资源尤其对中国近代的现代派艺术发展发挥了深刻影响。
林风眠作品的几何造型从西方现代艺术中借鉴了不少内容,但根本上不同于后者。他力求从对象的特征出发进行整体性的鲜明概括与抽象化,不具备西方现代派意义的“变形”所带来的语言的晦涩感与反讽性质,空间的变换、压缩、重叠实质上更多地借鉴了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的观念与造型方式,为达致表达的直接而打破真实空间与形体表象,画面整体始终保持着完整和谐,与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艺术的空间分割、分解观念有根本的不同⑨。林风眠作品语言的综合性质非常明显,来源、材料,表现方法繁复混杂,但最终的画面品质却力求单纯明朗和意义解读的明晰完整,不追求西方现代派艺术如综合立体主义、达达派等体现的反讽、虚无与颠覆意义。
对线的处理方式反映出林风眠对传统的大胆突破。他作品中的笔触和线条很得中国传统艺术的“写意”“传神”的骨髓,敏锐有力地表达了主体的精神状态,但却舍弃了传统书法的书写方式和训练方法。林风眠推崇宋代梁楷的简笔画,谓之“自由的,冲破一切的创造”,“把复杂繁密的自然界物象,设法使之单纯化”,就是后来的写意画,与现代西方的“速写”具有相同的性质⑩。他看到中国古代传统和西方现代艺术在表达主体精神、在写意方面的共通点,又从晋唐壁画、青花瓷、传统民间年画艺术中体悟到突破传统文人画书法用笔的方式。曾亲眼目睹晚年林风眠作画过程的万青力说“林先生显然不是以书法实践达到他线条圆润沉厚的表现力的。但是他用笔中锋,握笔仍是中国式的五指齐力,经长年的练习,也同样达到了力透纸背,厚重圆浑的线条表现。”(11)他有意弃绝具备稳定的技术操作保障和训练可行性的方法,甘冒由技术训练标准和稳定方法的缺失带来的表达无力、甚至失语的危险,丢弃了作画者精神状态不饱满时技术的弥补作用,将自己充分地暴露在表达的危险之中。这条道路意味着主体精神状态成为语言表现的核心要素。林风眠通过拒绝书法的方法来拒绝传统文人画笔墨程式的必然性和由此可能存在的作画主体精神低靡不饱满、缺乏创造力的状态,他以作画过程中时时刻刻充满饱满的精神强度与创造意识为理想,逼迫自己通过长年的精神磨砺和艺术表现的反复锤炼(构图、色彩、线条等各个方面因素的实验),通过近乎宗教苦修的充满道德内涵的行为,培养出强大的意志力和饱满的精神含量,最终达致表达的成熟。
林风眠的画面,是一个形与形之间协调组合、高度完整的世界。完整意味着作品中没有可以分离出整体独自强调的局部、整体的意境氛围永远大于局部的意义。作品以成热的理性思考和完整的画面框架为基础,在顽强的主体意志力的作用下,几何形这一非自然的、经过高度提炼抽象的形式几乎内化为创作者“自然”的表达。做到这一点十分艰难,林风眠的创作方式是同一主题同一构图反复琢磨锤炼,百中择其一二(12)。每幅画面的形式语言千锤百炼,同时经由这一反复磨炼之后,创作主体最终达致表达的自由。这种创作方式证明了林风眠对于画面每一部分的控制力之强大,也是他的艺术理想所要求的:他所期待用艺术来建构的,是坚毅完整,充满控制力、理性与情感平衡的世界,个体的夸张与极端表达,形式与内容的失衡不是艺术家的追求。
这个世界所创造的空间与时间同样耐人寻味。以多层次的水平线为主干、有时穿插垂直造型的构图和由中心向四周呈放射力量的圆构图是林风眠作品最常见的图式。其山水作品的空间为水平垂直式,大多取中景,符合普通人欣赏风景的视觉习惯,放弃了中国古代山水画带有历史永恒和循环观念的高远的全景图式,营造出具有一定深度、空间层次饱满深沉的世界,将观众的精神牢牢吸纳在其中;花卉作品的空间则更多地从宋人花鸟作品中汲取灵感,取中心放射式的近景,舍弃了传统的文人折枝画图式,给人以饱满的视觉震撼。林风眠创造了不同于中国古典传统的空间与时间;情感非常饱满,观众进入这扑面而来的视野被饱满地拥抱,艺术家没有将观众引导至画面之外的缥缈之处,追求那种出世的淡泊和玄远的哲思,而是将他们吸引在这个新鲜明朗、充满浓郁情感的灿烂世界中。与传统亘古不变的世界不同,它是崭新的,它深厚、饱满,破除了传统空间的玄学性质与游戏趣味。
这一世界又完全不同于西方现实主义和现代派艺术:它不具备现代西方艺术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它追求的不是当下的瞬间感受和极端的个体表现,它企图塑造一种具有稳定与超越意味的象征着时间与理想的空间。林风眠的世界相对中国传统而言是崭新的,但不具备西方现代艺术的终极感、紧迫性、开放性,它没有两极的成熟与明晰,而是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这两极间的一个暧昧含混的中间物。
这种暧昧特征反映了中国近代艺术的真实处境——中国近代的现实本身就模糊暧昧,处在传统向现代的过渡阶段,处在西方现代化和自身民族独立身份建构的逼迫之中,这决定了艺术理想的位置与方向;同时,中国近代艺术与现实的关系始终处在一种模糊状态,面对不断变化、复杂而不明朗的现实,艺术的把握始终游离而困难,这种状况一方面催逼出表达的焦虑,另一方面,这种焦虑本身又很容易陷入空洞虚浮,甚至对无力状态的反思之缺失成为普遍状况。
近代艺术家中,林风眠属于保持此种反思能力的少数,他顽强地从艺术语言中寻找表达其高度道德内涵和社会责任感的艺术理想,以主动的态度处理和开掘诸种资源:
他舍弃了传统文人画最为基本的笔墨程式与训练方法,改变了中国画的图式与空间构成,色彩与光线的引入,将传统文人淡泊、悠远、出世、充满玄学趣味的境界变为灿烂热烈、单纯明朗,充满对现实的热爱与力量的世界,以整饬的形、明朗新鲜的光色、充溢着主体精神力量的笔触与内涵代替了苍白、模仿的、程式化的文人画传统,同时将写意精神和含蓄抒情的诗意内涵保持了下来。
他汲取了西方现代艺术的某些语汇和方法,将印象派的光与色作为建构其中国现代新的审美经验的重要因素,但却以一种象征的而非写实的方式来表现,使光与色获得精神符码的意义;借取西方现代艺术的几何造型和变形的方法,却以完整的方式局部运用它们,摆脱了它们在西方语境中的反讽、叛逆意义。
中国传统民间艺术和古代艺术这些非文人画传统是他最为重要的发现:它们直接、鲜明的表达,强烈、质朴的情感,色彩、线条、造型的表现方式,都成为他突破传统文人画程式、处理西方现代艺术资源的重要出发点,是他建构新的审美经验、表达“民族性”所依赖的最为重要的资源(13)。
而这一切的融合,经过了艰苦的探索,经历了艺术理想的成熟与道德意志的历练:林风眠二十年代的作品受德国表现派、象征派影响较大,追求形式的抽象性和笔触的表现性,情感哀婉忧郁,有些作品略带虚幻色彩,如《沉思的鸱枭》、《春之晨》;回国后北京期间所作的水墨扇面风竹、一九三零年代所作的裸体女像(如1934年的《裸女》)和花鸟作品都处在摸索阶段,多模仿西方现代派艺术中某些造型,没有找到成热的表达方式,作品单薄、疲弱。中后期的作品则饱满圆浑,意境灿烂深沉,柔弱的、过度的表现不见了,好像从忧郁多感的少女变为热烈、健康而充满成熟诗意表达的壮年男子。
在真正意义的林风眠风格形成之前,与同时期的画家一样(如倪贻德、关良、丁衍庸等),经验的迷茫与模糊,势必造成表达本身的无力与表达主体焦虑漂泊的内心状态。抗战时期在重庆郊外仓库茕茕孑立的孤独之中,面对西南苍茫沉郁的山水与纯正质朴的劳动人民,在脱离了平稳的学院生活和个人社会地位,感怀着民族的苦难,充满了愤怒与悲怆之时,艺术家灿烂热烈质朴的艺术理想得以生长、确立与成熟,语言表达也得以清晰和成形,日后种种历史现实的变革都没有再改变这种形式,反而更加强化和充实了它。(14)
在他的作品中,形式语言的严格与整饬和情感的饱满热烈获得完整的结合,没有一个随意或零碎的局部、哪怕是创作瞬间是被允许的:直线、水平线、圆线,形式语言的高度整饬和画面的高度完整,让我们看到艺术家以强大的意志力对待自己的艺术行为。他摈弃精神的任意、疲弱、夸张,铲除精神的宣泄,他要达到表达的纯粹,好像一个人一开口就要好好地说话,不许放肆或随意地说;他的艺术要求的是精神百分之百的虔敬和集中,并且时时刻刻将自己提升到一个尼采的日神阿波罗的清朗明亮的精神境界,这个境界不允许陷入伤感、软弱、放纵、沉沦和颓废,这个世界又必须质朴、直接、明朗、热烈。他要求自己成为强者,在对待自身的严肃甚至严厉的状态中创造出具有道德意味的形式。(15)
林风眠倾尽全力追求的灿烂、明朗、热烈,充满诗意的“力与美”,是他在那个他所经历的特定现实中所理想的现代的中国民族精神和时代品质。灿烂而充满生机的大千世界,是艺术在经历充满磨难的现实、在民族精神和人格精神重塑的历史时期的理想世界;充满了生命的力量和真挚情感的现代中国人,应该在艺术中体会到精神的升华、愉悦,超越自私混乱充满争斗的世俗生活达致精神的完整。或许正是这样的历史境遇与这样的艺术理想,造就了林风眠艺术独一无二的面貌。
注释:
①“在我国现代的艺坛上,目前仍在一种‘乱动’的状态上活动:有人在竭力模仿着古人,有人在竭力模仿外人既成的作品,有人在弄没有内容的技巧,也有人在竭力把握着时代!”《什么是我们的坦途》,《艺术丛论》第154页,《民国丛书》第四编第61册,上海:上海书店,据中正书局1947年版影印。
②《什么是我们的坦途》,《艺术丛论》第154页,《民国丛书》第四编第61册。
③《东西艺术之前途》,《艺术丛论》第3页,《民国丛书》第四编第 61册。
④《东西艺术之前途》,《艺术丛论》第5页,《民国丛书》第四编第 61册。
⑤林风眠作于1933年的《我们所希望的国画的前途》,《现代美术家画论作品生平林风眠》第82页,朱朴编著,上海:学林出版社, 1988年。
⑥《印象派的绘画》序言,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58年。
⑦1994-1998年笔者在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学习,1995年进入水墨人物画室学习,田黎明老师曾对笔者这样概括他对齐白石艺术的认识。
⑧林风眠1927年任北平国立艺专校长,力排众议请齐白石任教,后来任杭州国立艺专校长时也曾请齐白石任教,齐因不愿南下而回绝。林风眠的学生李霖灿先生也认为齐白石与林风眠有精神相通之处。他回忆曾在杭州国立艺专林风眠的校长室里看到林的油画巨作《海滨归舟》,同时“墙上还挂着几幅齐白石老先生的画,册页的形式。当时,觉得其中的《衡岳日出图》‘色调对比得太厉害了一点’”,后来抗战时亲临南岳的经历使他明白了齐白石艺术表现的力量。由此认识到林齐两人“惺惺相惜,一个新派,一个传统,却相得益彰莫逆于心,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第一次认识了林风眠和齐白石”。李霖灿《我的老师林风眠》,《林风眠论》第44、45页,郑朝、金尚义编,杭州: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0年。
诗人艾青在《彩色的诗一读〈林风眠画集〉》中评价林风眠“从石涛到白石老人/从塞尚到高更/不断地扩大视野/具有大无畏的精神”。郑朝、金尚义编《林风眠论》第5页。
⑨笔者认为,即使林风眠八十年代末期和九十年代的作品,虽然脱离了盛期完整和谐的风格,语言稍显晦涩,变形更加强烈,但还是在相对单向度的方向运用变形,在作画主旨和意义上都不可等同于西方现代派的变形。
⑩《中国绘画新论》,《艺术丛论》第119-120页,《民国丛书》第四编第61册。
(11)万青力《化作春泥更护花》,《林风眠研究文集》第426页,郑朝选编,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5年。
(12)林风眠学生回忆说他常常夜里作画,一整晚可作八九十幅,他自己留下几幅其余全部撕去。我们从他留下的作品中也看到这一方法。李可染及多人都曾如此回忆,参见郑朝选编《林风眠研究文集》。
(13)刘开渠认为“林先生的长处,或者说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认识到了中国古代伟大的艺术,但是他以另外的新的意识创造了自己的艺术。”(刘开渠《独树一帜的新创造》,郑朝选编《林风眠研究文集》第2页。)超越文人画传统去寻找其他的传统资源和以新的意识、以民族性的表达为出发点利用这些资源,是林风眠艺术的重要价值。
(14)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即艺术家从大陆移居香港的生命的最后时期,这一对待世界的方式才发生了动摇和变化。
(15)林风眠的学生席德进对老师的艺术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总结林风眠一生经过艰辛努力所解决的三个重要冲突是“感情与理智的冲突”、“民间艺术与文人画的冲突”、“墨与色的冲突”。对于林风眠来说,吸收民间艺术元素尤其艰难:“他后天的培育与环境的影响使他绝对无法回到纯粹民间艺人的纯朴本能流露,因为他已不再纯粹了,他没有齐白石那样幸运。……林风眠的艺术需要费更长的时间来挣扎、解脱,甚至辛苦的经营,才能把外来的影响降低,而多多展现他乡下人的天然本质。”席德进《林风眠的艺术》,郑朝、金尚义编《林风眠论》第80页。
标签:林风眠论文; 齐白石论文; 文人画论文; 艺术论文; 艺术的力量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美术论文; 现代艺术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民国丛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