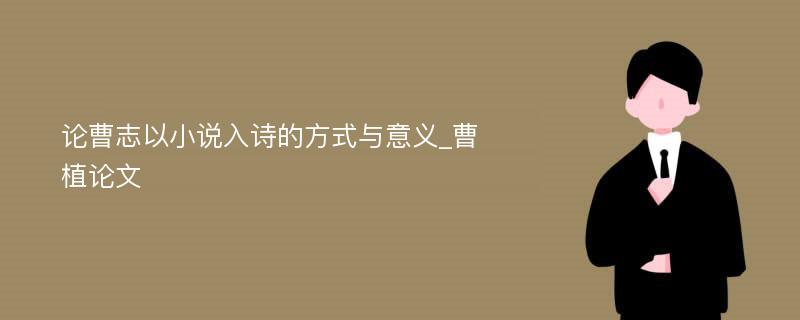
论曹植以小说入诗的方式与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义论文,曹植论文,方式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钟嵘《诗品》给予曹植诗以极高评价:“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嗟乎!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①曹植诗取得如此高的成就除了自身的天禀外,与其博学渊识亦不无关系。他于诗中对经史、诸子广泛征引并灵活化用,推陈出新,语如己出,形成了“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的诗格。正如沈德潜《说诗晬语》所云:“以诗入诗,最是凡境。经史诸子,一经征引,都入咏歌,方别于潢潦无源之学……但实事贵用之使活,熟语贵用之使新,语如己出,无斧凿痕,斯不受古人束缚。”②那么,曹植是怎样对诸子中街谈巷语的小说进行征引和化用,以之入诗,形成其“词采华茂,情兼雅怨”的诗风;反之,其诗征引化用小说后又对小说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二者均是值得关注与探讨的。 曹植主要以征引和化用小说典故的方式以小说入诗,即于诗中征引小说典故或把小说典故直接化用为诗。首先,我们谈谈其于诗作中对小说的征引。曹植征引小说入诗的诗篇甚多,如《精微篇》《平陵东》《九咏》《善哉行》《升天》《游仙》等等。其中,又以《精微篇》所征引小说典故最多。《精微篇》云:“精微烂金石,至心动神明:杞妻哭死夫,梁山为之倾。子丹西质秦,乌白马角生。邹衍囚燕市,繁霜为夏零。关东有贤女,自字苏来卿,壮年报父仇,神没垂功名。女休逢赦书,白刃几在颈。俱上列仙籍,去死独就生。太仓令有罪,远征当就拘,自悲居无男,祸至无与俱。缇萦痛父言,荷担西上书,盘桓北阙下,泣泪何涟如。乞得并姊弟,没身赎父躯。汉文感其义,肉刑法用除。其父得以免,辩义在《列图》。多男亦何为?一女足成居。简子南渡河,津吏废舟船。执法将加刑,女娟拥棹前。妾父闻君来,将涉不测渊,长惧风波起,祷祝祭名川。备礼飨神祇,为君求福先,不胜釂祀诚,教令犯罚艰。君必欲加诛,乞使知罪愆。妾愿以身代,至诚感苍天。国君高其义,其父用赦原。《河激》奏中流,简子知其贤;归聘为夫人,荣宠超后先。辩女解父命,何况健少年!黄初发和气,明堂德教施。治道致太平,礼乐风俗移。刑措民无枉,怨女复何为。圣皇长寿考,景福常来仪。”③此诗作意,赵幼文先生已有说明:“案此篇列叙古代人民负屈含冤,由于精诚终被昭雪之事迹,隐射自身受着监国谒者之诬陷,而期望得获曹丕的宽宥,可与《黄初六年令》参看。”④当然,也有人对此诗体味为另一用心的。朱乾《乐府正义》云:“(《精微篇》)苏来卿、秦女休,俱是为父报仇,看其连叙申缩之妙,非圣于文者不能……曹丕篡汉,废献帝为山阳公,纳其二女,三纲之伦无论矣。而仇女在前,祸生肘腋,亦可寒心。篇中累序诸女报父仇及赦父命,使听者凛然于言外,此植以诗讽谏之微意也,益知《独漉篇》为山阳作已。呜呼!生乎千载而下,不反复讽咏,沈潜体味,其何以得古人之用心哉!”⑤朱乾对曹植作此诗用心的体味亦不可全谓之附会,因其猜测确有一定凭依。但不论如何,他们两人都认为曹植是借故事以讽谏而达到某种目的的想法是一致的。 曹植于《精微篇》中所征引的故事有:杞妻哭夫、子丹质秦、邹衍囚燕、关东贤女、秦女休、缇萦救父、女娟拥棹等。这些故事有许多违背常理的夸饰成分,如“梁山为之倾”、“乌白马角生”、“繁霜为夏零”、“身没垂功名”等。这些故事多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具有小说因素,故多入小说之书。如杞妻哭夫故事,刘向《说苑·善说篇》有载:“华舟、杞梁战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为之崩,城为之陁。”⑥子丹质秦故事,《燕丹子》有载:“燕太子丹质于秦,秦王遇之无礼,不得意,欲求归。秦王不听,谬言:令乌白头,马生角,乃可许耳。丹仰天叹,乌即白头,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⑦邹衍囚燕故事,刘安《淮南子》有载:“邹衍事燕惠王,尽忠,左右谮之,王系之,仰天而哭,五月天为之下霜。”⑧《说苑》、《燕丹子》为后人所公认之小说书。《淮南子》为杂家书,《内篇》论道,《外篇》杂说,杂说之中多引“街谈巷语”。缇萦救父与女娟拥棹两故事俱见于《列女·辩通传》,亦有半史半小说性质。关东贤女、秦女休的故事,史传未详,应源于民间传说,且曹植与左延年最早征引入诗。宋长白所说甚明,其《柳亭诗话》云:“陈思王《精微篇》有云:‘关东有贤女,自字苏来卿。壮年报父仇,身没垂功名。女休逢赦书,白刃几在颈。俱上列仙籍,去死独就生。’左延年亦有《秦女休行》,中云:‘平生为燕王妇,于今为诏狱囚。’延年作于黄初中,当是子建同时事也。但所云‘燕王妇’,史传未详。至苏来卿,非入思王文集,并无由识其姓氏。乃知庞娥亲、谢小娥辈,流传万古者,正不易易耳。”⑨曹植说苏来卿、女休“俱上列仙籍”,“列仙籍”应属于《列仙传》一类书,亦可视为杂传体志怪小说。 曹植不仅一诗征引数篇小说典故,而且还数诗征引同一小说典故。王乔、赤松子的小说故事就多次见引于其诗篇,如其《仙人篇》:“韩终与王乔,要我于天衢。”⑩《游仙》云:“蝉蜕同松乔,翻迹登鼎湖。”(11)《善哉行》云:“仙人王乔,奉药一丸。”(12)《赠白马王彪》云:“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13)王乔故事流传久远,且说法不一。刘向《列仙传》如是记载:“王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凰鸣,游伊、洛之间,道士浮邱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余年后,求之于山上,见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缑氏山颠。’果乘白鹤驻山头。望之不得到,举手谢时人,数日而去。”(14)干宝《搜神记》亦有记载:“汉明帝时,尚书郎河东王乔为邺令。乔有神术,每月朔,尝自县诣台。帝怪其来数而不见车骑,密令太史候望之。言其临至时,辄有双凫从东南飞来。因伏伺,见凫,举罗张之,但得一双舄。使尚书识视,四年中所赐尚书官属履也。”(15)《搜神记》一书虽后出于曹植诗,但它所载的这则故事是汉明帝时事,故事本身是远早于曹植时代的,干宝是在前人流传的基础上记述整理的。尽管这两种说法不尽相同,但细绎其理,它们之间还是有承续关系的。《搜神记》所记王乔故事可看作《列仙传》所记王乔故事的演绎,“尚书郎河东王乔”是“周灵王太子晋”的灵魂所寄。不论曹植诗中王乔所指为周灵王太子晋,还是汉明帝时尚书郎河东王乔,然皆出于小说无疑。赤松子故事,《列仙传》亦有记述:“赤松子者,神农时雨师也。服水玉,以教神农,能入火自烧。往往至昆仑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随风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高辛时,复为雨师,今之雨师本是焉。”(16)《搜神记》亦有记述:“赤松子者,神农时雨师也。服冰玉散,以教神农,能入火不烧。至昆仑山,常入西王母石室中,随风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至高辛时,复为雨师,游人间。今之雨师本是焉。”(17)从《列仙传》与《搜神记》所记述赤松子故事看,其流传亦是十分久远。亦为小说之属。王充《论衡·无形篇》曰:“传称赤松、王乔,好道为仙,度世不死,是又虚也。”(18)王充所言从反面说明赤松、王乔故事源于“街谈巷语”。 曹植化用小说成诗,是其以小说入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能做到圆融妥帖,语如己出,无斧凿之痕。我们可以其诗作《野田黄雀行》为例,作一说明。《野田黄雀行》云:“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19)《野田黄雀行》渊源何自?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一、清人朱乾认为源于《战国策》“庄辛谓楚襄王”事。其《乐府正义》云:“《野田黄雀行》,《楚策》庄辛曰:‘黄雀俯啄白粒,仰栖茂树,鼓翅奋翼,自以为无患,不知夫公子王孙左挟弹,右摄丸,将加己乎十仞之上。’取义于此。大概在相戒免祸,故与《箜篌引》同。子建处兄弟危疑之际,势等冯河,情均弹雀。诗但言及时为乐,不言免祸,而免祸意自在言外。意汉鼓吹铙歌《黄雀行》亦此意也。”(20)朱乾认为此诗为“相戒免祸”之作,故其意此诗所述黄雀故事源于庄辛谓楚襄王所引黄雀故事。二、钱钟书先生认为源于《易·益》之《革》。钱钟书论西汉焦延寿《易林》曰:“《易林·益》之《革》:‘雀行求粒,误入罟罭;赖仁君子,复脱归室’(《师》之《需》等略同),又《大有》之《萃》:‘雀行求食,出门见鹞,颠蹶上下,几无所处’;可持较曹植《野田黄雀行》:‘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又《鹞雀赋》:‘向者近出,为鹞所捕,赖我翻捷,体素便附。’”(21)从钱先生这段话可以明显看出,他认为曹植的《野田黄雀行》诗与《易·益》之《革》,《鹞雀赋》与《易·大有》之《萃》颇有渊源。三、鲁同群先生认为西汉《铙歌》十八曲中《艾如张》一曲对此诗很有启发。鲁先生说:“首先,拔剑捎网、黄雀谢恩这一情节,就明显受汉乐府民歌中许多带寓言色彩的作品的影响。西汉《铙歌》十八曲中《艾如张》一曲有‘山出黄雀亦有罗,雀已高飞奈雀何’之句,对本篇构思的启发,更是显然。”(22)四、胡大雷先生认为此诗源于汉魏时流传的“黄雀报恩”故事。胡先生在其《曹植〈野田黄雀行〉本事说》一文中详细申述了理由,(23)我认为是可信的。 其实,从此诗的主旨可推测出其源于“黄雀报恩”的可能性大。关于此诗的主旨,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云:“《野田黄雀行》,此应自比黄雀,望援于人,语悲而调爽。或亦有感于亲友之蒙难,心伤莫救。”(24)陈氏认为此诗作意或为求救无望,或为救人无力。张玉榖认为曹植是为表达“权势不属,有负知交望救”之意而作的。其《古诗赏析》云:“《野田黄雀行》,此叹权势不属,有负知交望救之诗。首四以树高多风,海大扬波,比起有权势之易于为力,即折到既无权势,空说结交之羞,点醒作意。而无权势,只借剑不在掌作隐语,含而不露。‘不见’六句,反顶‘利剑’句,将少年救雀,指出锄强扶弱作用。文势展拓。末二以雀知感谢,为人必知恩写影。而己之不能如此,更不缴明,最为超脱。”(25)赵幼文先生亦持此意,且所指更显。赵氏说:“考《魏志·陈思王植传》裴注引《魏略》:‘时仪亦恨不得尚公主,而与临菑侯亲善,数称其奇才。太祖既有意欲立植,而仪又共赞之。及太子立,欲治仪罪,转仪为右刺奸掾,欲仪自裁。而仪不能,乃对中领军夏侯尚叩头求哀。尚为涕泣,而不能救。乃因职事收付狱杀之。’疑植此篇,盖因仪之被囚而希有权力者为之营救而作也,故多比兴之词。”(26)尽管赵氏颇怀度测之意,但所指甚明。估量此诗是曹植为救丁仪而不能的感慨之作。胡大雷先生则说:“曹植创作《野田黄雀行》是受这则故事(吴均《续齐谐记》所载“黄雀报恩”故事)的刺激、影响而成,其为杨修被杀而作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又说:“而曹植所写即是救黄雀及‘黄雀报恩’。这样比较起来看,《野田黄雀行》是曹植为杨修被杀而作更确切一些。”(27)从对此诗主旨的推度来看,胡大雷先生的说法的确更合理一些。由此,也可更好地说明此诗源于“黄雀报恩”故事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确实,曹植《野田黄雀行》一诗可以说是对小说“黄衣童子”或“黄雀报恩”的一个以诗歌形式的改写,并以此抒发怨情与期待情怀。“黄衣童子”故事流行于汉代,后干宝《搜神记》有记述:“汉时弘农杨宝,年九岁时至华阴山北,见一黄雀为鸱枭所搏,坠于树下,为蝼蚁所困。宝见愍之,取归置巾箱中,食以黄花。百余日,毛羽成,朝去暮还。一夕三更,宝读书未卧,有黄衣童子向宝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使蓬莱,不慎为鸱枭所搏。君仁爱见拯,实感盛德。’乃以白环四枚与宝,曰:‘令君子孙洁白,位登三事,当如此环。’”(28) 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记述则更为详细:“宏农杨宝,年九岁,至华阴山,见一黄雀为鸱枭所搏,逐树下,伤瘢甚多,宛转复为蝼蚁所困。宝怀之以归,置诸梁上。夜间啼声甚切,亲自照视,为蚊所齿,乃移置巾箱中,啖以黄花。逮十余日,毛羽成,飞翔,朝去暮来,宿巾箱中。如此积年,忽与群雀俱来,哀鸣绕堂,数日乃去。是夕,宝三更读书,有黄衣童子曰:‘我,王母使者。昔使蓬莱,为鸱枭所搏,蒙君之仁爱见救,今当受赐南海。’别以四玉环与之,曰:‘令君子孙洁白,且从登三公事,如此环矣。’宝之孝天下,名位日隆。子震,震生秉,秉生彪,四世名公。及震葬时,有大鸟降,人皆谓真孝招也。蔡邕论云:‘昔日黄雀报恩而至。’”(29)由此可见,这个故事与杨修有直接关系,杨宝是杨修曾祖,杨宝生杨震,杨震生杨秉,杨秉生杨彪,杨彪即杨修的父亲。而杨修又和曹植交往甚密,从某种程度上讲,杨修也是因曹植而死的,所以,曹植为杨修被杀而作此诗抒发怨情符合情理。 除《野田黄雀行》外,曹植在《灵芝篇》中也用诗歌的形式表现了虞舜、伯瑜、丁兰、孝子董永等小说故事。《灵芝篇》云:“古时有虞舜,父母顽且嚣;尽孝于田垄,烝烝不违仁。伯瑜年七十,彩衣以娱亲;慈母笞不痛,歔欷涕沾巾。丁兰少失母,自伤早孤焭。刻木当严亲,朝夕致三牲。暴子见陵侮,犯罪以亡形,丈人为泣血,免戾全其名。董永遭家贫,父老财无遗,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责家填门至,不知何用归。天灵感至德,神女为秉机。”(30) 总之,我们可以通过《野田黄雀行》《灵芝篇》两诗看出,曹植以具有小说性质的民间流传故事为底本,以高妙的技巧进行化用,化俗为雅,不受束缚,语如己出,情由语生,“词气纵逸,渐远汉人”。(31)可谓诗风之一大转变,正如王世懋《艺圃撷余》所云:“古诗,两汉以来曹子建出而始为宏肆,多生情态,此一变也。”(32) 以小说入诗,既要拥有丰富的小说材料,还要有不轻视小说的态度。曹植二者兼备。曹植拥有丰富的小说材料,是不用细论的。丁廙称赞他“博学渊识,文章绝伦”,(33)杨修亦说他“能兼览传记,留思文章”。(34)“博学渊识”、“兼览传记”肯定包括丰富的小说故事,其见邯郸淳所诵数千言之俳优小说便是明证。另外,他诗、文、赋中大量征引小说故事也可充分说明这一点。更为难得的是,曹植抱有不轻视小说的态度,他在《与杨德祖书》中说:“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35)可见,他是不轻弃“街谈巷说”的。把此处的“街谈巷说”视为小说是不为过的,因为它与班固所说的“街谈巷语”意思大致不差。班固《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36)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这两段话,“街谈巷说”与“街谈巷语”,“击辕之歌”与“道听途说”,“匹夫之思”与“刍荛狂夫之议”,基本上是相同的意思而不同的表述。在汉代,“街谈巷说”入于小说家者流,不仅班固如此,荀悦亦同,荀悦《汉纪》重复了《汉书·艺文志》的意见,称“又有小说家者流,盖出于街谈巷议所造”。(37)由此可见,“街谈巷语”、“街谈巷议”、“街谈巷说”均可看作汉魏时小说观念的不同表述。 另外,曹植见邯郸淳而诵俳优小说一事,也说明其未易轻弃小说。陈寿《三国志·王卫二刘傅传》注引《魏略》云:“会临淄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夫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于是乃更着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38)“诵俳优小说数千言”不仅说明他拥有丰富的小说材料,同时还表现了他不轻弃小说的勇气。刘勰《文心雕龙·谐隐》:“自魏代以来,颇非俳优,而君子嘲隐,化为谜语。”(39)既然“魏代以来,颇非俳优”,而曹植见邯郸淳时却自澡傅粉,诵俳优小说数千言,充分说明他具有不苟流俗而不轻弃俳优小说的勇气。曹植不仅诵俳优小说,他还以俳优语入诗。其《妾薄命》云:“日月既逝西藏,更会兰室洞房。华灯步障舒光,皎若日出扶桑。促樽合座行觞,主人起舞娑盘,能者穴触别端。腾觚飞爵阑干,同量等色齐颜。”(40)这首诗化用了齐优淳于髡语,《史记·滑稽列传》云:“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芗泽,当此之时,髡心最欢,能饮一石。故曰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万事尽然。”(41)通过诗、文的两相比对,我们不难发现其间的承传关系。故宝香山人云:“《妾薄命》‘日月既逝’篇,前用淳于髡语……奇绝奇绝,可谓青出于蓝。”(42)其不苟流俗之体性,是他“骨气奇高”诗风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以俳优语入诗,以小说入诗,也是他诗风形成而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 曹植以小说入诗,不仅有助于丰沛诗意、抒发怨情以及诗风的形成,而且,对小说的留存、传播,以及对后世小说的创作也有很大影响。曹植诗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是无须赘言的,从时人和后人对他诗歌的品评即可明显看出其诗影响之大。因品评者甚多,故不赘述。曹植以小说入诗对某些小说的留存和传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如苏来卿故事,史传未详,正是曹植以此小说故事入《精微篇》,才使得苏来卿的姓名与事迹得以流传。正如宋长白所言:“至苏来卿,非入思王文集,并无由识其姓氏。”(43)秦女休故事,左延年有《秦女休行》,宋长白认为“延年作于黄初中,当是子建同时事也”。(44)赵幼文先生认为曹植《精微篇》亦作于黄初中,故他在《曹植集校注》里把《精微篇》编在黄初年间。其谁先谁后虽难以说清,但其影响孰大孰小当是不言而喻的。关于牛郎织女故事的书面流传,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所述较详:“织女牵牛,《荆楚岁时记》曰:‘七月七日,世谓织女牵牛聚会之日。’晋傅玄《拟天问》云:‘七月七日,织女、牵牛会天河。’此则其事。杜公瞻注云:‘此出于流俗小说,寻之经史,未有典据。’……近代有此说耳。曹植《九咏》曰:‘乘回风兮浮汉渚,目牵牛兮眺织女。交有际兮会有期,嗟吾子兮来不时。’注云:‘牵牛为夫,织女为妇,各处河之旁,七月七日得一会同。’”(45)引人注意的是,牛郎织女故事是因曹植诗而落为“口实”的。洪亮吉《北江诗话》云:“牛、女七月七夕相会,虽始见于《风俗通》,至曹植《九咏》注,始明言牵牛为夫,织女为妇。自此以后,遂皆以为口实矣。”(46)洪亮吉所说是可信的。唐李善注《文选》曹丕《燕歌行》引曹植《九咏注》云:“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一旁,七月七日,得一会同矣。”(47)赵幼文先生认为《九咏注》定为曹植所作缺乏确凿证据。赵氏说:“《文选》李注引曹植《九咏注》,严可均《全三国文》列为植作,古人虽有自注之例,然辄定为植作,究乏确证。”(48)其实,赵氏是过于谨慎。清何琇认为自注己作始于王逸,其《樵香小记》卷下《总集自注注赋注诗》云:“自注己作亦始于逸,而戴凯之《竹谱》、谢灵运《山居赋》用其例。”(49)不论是否始于王逸,但王逸自注己作确然可信。王逸《九思章句序》云:“九思者,王逸之所作也……逸与屈原同土共国,悼伤之情与凡有异。窃慕向、褒之风,作颂一篇,号曰《九思》,以裨其辞。未有解说,故聊叙训谊焉。”(50)王逸自注《九思》,曹植自注《九咏》,同为楚辞体诗歌,应有影响承袭关系。由上可见,牛郎、织女本为天上隔着银河而相对的星宿,却被曹植在《九咏注》中发酵为一个动人的爱情小说。 曹植诗作对后世小说亦颇有影响,后世小说或化用子建诗句,使小说变得文雅且富有诗意。胡应麟《诗薮》云:“‘明月清风,良宵会同。星河易翻,欢娱不终。玉樽翠杓,为君斟酌。今夕不饮,何时欢乐?’虽出唐人小说,‘月明星稀’之后,实仅见此。苏、黄谓非子建、太白不能。然太白不如此闲雅。颇类子建《来日大难》中语。”(51)诗句“明月清风,良宵会同。星河易翻,欢娱不终。玉樽翠杓,为君斟酌。今夕不饮,何时欢乐”,出自唐人小说《玄怪录》之《刘讽》篇,宋李昉所撰《太平广记》有载。胡应麟觉得颇类于曹植诗《当来日大难》中语,《当来日大难》云:“日苦短,乐有余,乃置玉樽办东厨。广情故,心相于。阖门置酒,和乐欣欣。游马后来,辕车解轮。今日同堂,出门异乡。别易会难,各尽杯觞。”(52)两相比较,意颇类。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云:“王直方诗话云:明月清风,良宵会同。星河易翻,欢娱不终。绿樽翠杓,为君斟酌。今夕不饮,何时欢乐。此《广记》所载鬼诗也,山谷云‘当是鬼中曹子建所作’,翰林苏公以为然。”(53)苏、黄二人调侃说此诗为鬼中子建所作,说明此诗不仅作得极佳,且颇类子建诗作。不论后世小说家对曹植诗是实在征引还是有意模仿,都可说明曹植诗对后世小说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总之,曹植对小说的认可,并以征引、化用的方式将小说嵌入其诗或变化小说而为诗,语如己出,不露斧凿之痕,使得其诗意蕴更为丰富,怨情更加浓烈,词采更其华茂。他以小说入诗,对小说本身也产生莫大影响,使得大量小说流传更加广泛久远,部分小说因其诗首载而得以发扬,并因其诗“遂皆以为口实”。不仅如此,后世小说还融入曹植诗句,使小说变得文雅且富有诗意。如此这般,小而言之,它使小说更加文雅富丽;大而言之,它会加速小说雅化的进程。 ①[梁]钟嵘著、周振甫译注:《诗品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37页。 ②[清]沈德潜:《说诗晬语》,霍松林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88页。 ③赵幼文:《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332页。 ④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334页。 ⑤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编:《三曹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99页。 ⑥[汉]刘向:《说苑校证》,向宗鲁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73页。 ⑦[唐]欧阳询:《艺文类聚》,汪绍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第1591页。 ⑧[汉]刘安:《淮南鸿烈集解》,刘文典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57页。 ⑨[清]宋长白:《柳亭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76页。 ⑩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263页。 (11)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265页。 (12)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532页。 (13)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300页。 (14)[汉]刘向:《列仙传校笺》,王叔岷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5页。 (15)[东晋]干宝:《搜神记》,曹光甫、王根林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0页。 (16)[汉]刘向:《列仙传校笺》,第1页。 (17)[东晋]干宝:《搜神记》,第17页。 (18)[汉]王充:《论衡校释》,黄晖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4页。 (19)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206页。 (20)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编:《三曹资料汇编》,第197-198页。 (21)钱钟书:《管锥编》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38页。 (22)吴小如等:《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第259页。 (23)胡大雷:《曹植〈野田黄雀行〉本事说》,《文献》2009年第3期,第34页。 (24)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编:《三曹资料汇编》,第188页。 (25)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编:《三曹资料汇编》,第210页。 (26)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207页。 (27)胡大雷:《曹植〈野田黄雀行〉本事说》,《文献》2009年第3期,第34页。 (28)[东晋]干宝:《搜神记》,第156页。 (29)[梁]吴均:《吴均集校注》,林家骊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21页。 (30)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327页。 (31)[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9页。 (32)[明]王世懋:《艺圃撷余》卷首,四库全书本。 (33)[晋]陈寿:《三国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12页。 (34)[唐]李善:《文选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564页。 (35)[唐]李善:《文选注》,第594页。 (36)[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45页。 (37)[汉]荀悦:《汉纪》卷二十五,四库全书本。 (38)[晋]陈寿:《三国志》,第552页。 (39)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271页。 (40)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481页。 (41)[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99页。 (42)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编:《三曹资料汇编》,第164页。 (43)[清]宋长白:《柳亭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76页。 (44)[清]宋长白:《柳亭诗话》,第176页。 (45)[宋]胡仔纂集:《苕溪渔隐丛话》,廖德明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40页。 (46)[清]洪亮吉:《北江诗话》,陈迩东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76页。 (47)[唐]李善:《文选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519页。 (48)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524页。 (49)[清]何琇:《樵香小记》卷下,四库全书本。 (50)[宋]洪兴祖:《楚辞补注》,白化文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14页。 (51)[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第12页。 (52)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467页。 (53)[宋]胡仔纂集:《苕溪渔隐丛话》,第404页。标签:曹植论文; 幼文论文; 野田黄雀行论文; 读书论文; 搜神记论文; 列仙传论文; 黄雀论文; 灵芝篇论文; 王乔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