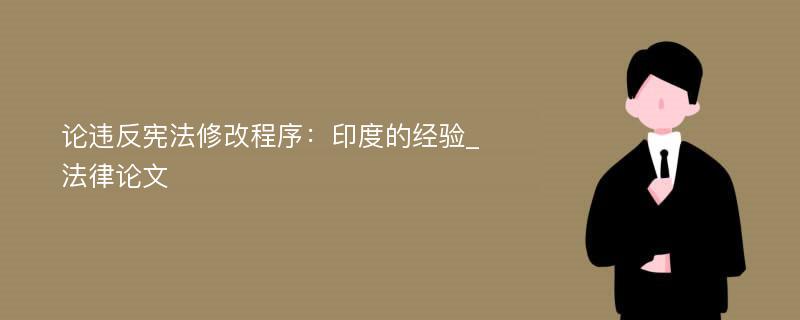
略论修宪程序的违反:印度之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度论文,修宪论文,经验论文,程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951(2008)06-0061-07
一、引言
法律的制定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序,否则,即应无效之;而宪法作为一国基本法,规定了国体、政体、人民的权利义务等重大政治事务。故而,宪法不仅系国民主权的表征,亦系全体国民共识的凝聚,其修改关系宪政秩序的安定与国民福祉至巨,修宪机关应慎重为之①。故此,对于宪法修正程序的规定和要求通常比对普通法律的修正程序的规定和要求更为严格。就此而言,如宪法的修正行为违反宪法上修正程序的强制性规定而有重大明显瑕疵,亦不生其应有的效力②。不过,在一般情形下,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未能遵循法定的程序,其所制定的法律效力如何,须视该程序规定的性质而定[1]:倘若该程序规定只是指引性规定,至于是否遵守,立法者享有广泛的裁量权,而不能以其违反法定程序为由而使之无效;但是,倘若其为强制性规定,而立法者在行为时未能予以遵守,则其行为有可能会因为违反法定程序而无效,并进而导致制定的法律的无效[2]。同样,如果修宪机关在修正宪法时违反强制性的修宪程序亦可能导致宪法的无效。
二、修宪程序违反之情形
修宪程序存在重大明显瑕疵的情形主要包含如下两种情形:
(一)违反宪法明文规定的程序
印度宪法第368条明确规定了修宪的两种程序,并且对提案的方式、两种情形之下的法定的出席人数和批准人数以及批准的程序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违反法定出席人数或者批准人数而为的宪法修正都不能合乎宪法的规定,不过这种情形由于过于明显,所以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但是,在现实中可能存在某些情形,如,宪法的修正并非以法律案的方式而提出;在某一政党在议会中占有修宪所需法定人数时,其只将宪法修正法律案分发本党成员并且不通知其他党派成员开会,或者剥夺其参加宪法修正法律案的讨论与表决;在就但书规定的情形下,议会只将宪法修正法律案送交某些邦议会予以表决;或者,在某些情形下,议会在对宪法第368条第2款但书规定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修正时,并未进一步按照该但书规定的程序付诸各邦立法机关进行表决,便直接送总统签署;或者宪法修正法律案未经总统签署而直接予以公布的。在这些情形下,如果无法对于宪法修正案的合宪性问题作出判断,则可能会致使基本权利、民主原则或者联邦主义遭遇实际性的破坏,从而导致宪法的破毁。
(二)违反议会内部议事程序
由于通常情况下,宪法只是规定修宪的一般程序,对于其细节并无具文,可操作性较差,为此,其实施尚需进一步具体化。就此而言,一般认为其议事所应遵循的程序,除明显抵触宪法者外,乃是内部事项,属于议会依自律原则应自行认定的范围,并非违宪审查机关审查的对象③。但是,应当注意的是,议会内部程序中,有些规定亦具有重要的实体性价值,如采取何种投票方式,匿名投票或者记名投票,议员,特别是反对党的议员发言权是否得到充分尊重与保护,是否按照有关规定举行听证程序等,其对于反映人民的意见、保护少数人的权利以及所制定法律的民主性、客观性和正确性上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此意义上讲,一旦重大明显违反此类规定,亦应使修宪行为无效,并进而使宪法修正案无效,否则,则不仅有可能激化社会矛盾,损害宪法的尊严,严重者亦可能导致宪法的破毁,使之形同具文。
三、印度的经验
(一)修宪程序具有强制性
从一定程度上讲,印度宪法对修宪程序中有关主体、方式及程序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宪法第368条规定了对宪法进行修正的两种程序:除宪法其他条款规定由议会以一般法律程序予以修改且不得认为为宪法第368条所谓宪法的修正的事项及宪法第368条但书条款所规定的事项外,宪法修正案得在议会两院之一以法律案提出,并由两院以各该院所有议员的2/3出席和投票,并以各该院所有议员的多数通过,然后送交总统批准后生效;至于宪法第368条但书条款所规定事项,在送交总统批准前,尚须交由各邦立法机关批准,且须获得半数以上邦立法机关分别以决议的形式通过之后,再送交总统批准,方能生效。
尽管,早期对于该条规定,宪法学家和法官们对于宪法第368条的见解中存在严重的分歧,有的认为其本身乃是一个完全法条(Complete code),即议会在修改宪法时只要遵守第368条的规定,就可以无限行使其修宪权,对宪法进行任意修改;有的则认为该条是不完全法条(Incomplete code)④,只是对修宪程序的规定,并未涉及宪法修改的权限、内容及范围,故而议会在行使修宪权时应当同时参考宪法的其他规定,尤其是宪法有关议会和总统的权限的规定,并在宪法文本之四隅内(Four corners of the text)活动。然而,无论持何种观点,在印度宪法这样一部成文且刚性的宪法[3]下,宪法第368条所规定的修宪程序具有强制性,宪法的修正必须严格遵循宪法第368条的规定,由法定的主体以法定的方式和程序为之,方能生效[4];一旦修宪程序存在重大明显瑕疵,则将必然导致宪法修正案的违宪无效,这一点却是各方所共识的,尤其是在宪法第24修正案在宪法第368条增加了第1款规定后,乃更为明确[5]。
尽管印度宪法第368条有关修宪程序的规定并非典型的命令语句,即,既未完全以“……(主体)应当(shall)或者必须(must)……(为一定或者不为一定行为)”一类语句课予议会应遵循一定修宪程序的义务,也未以“……者……禁止之(shall be prohibited)”或者相似语句课予议会以不作为的义务,更未以“非依照此等修宪程序而为之宪法修正案违宪无效”的形式明定违反修宪程序的法律后果;但是其仍系强制性的规定,尽管其本身并未包含Hans Kelsen所谓的法律所应具有的惩罚性规定(Sanction),即,对于违法行为(delict)的惩罚性条款[6],然而,它本身却规定了宪法修正案生效的要件,就此而言,它亦具有强制性(Coercive),就此而言,它亦具有强行法应有的内涵。正如H.L.A.Hart所指出的:一部对法律制度中的最高立法机关的立法权实行有效控制的宪法,并非通过课以立法机关不得以某种方式立某种法的义务(其也没有必要如此),而是通过规定如此所制定之法律无效来实现其控制的。它所规定的并非法定的义务而是法定的要件[7];另外,还应当指出,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实际上在法律条文中有关程序性的规定中,甚少在条文中明确违反条文的法律效果,但这并非意味着程序性规定就非通常意义上的法律。相反,其在一定程度上授予法院以相应的裁量权,法官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境而采取必要的判断——既可能裁判其违反程序而无效,并课以一定的法律责任;也可能裁判其继续有效[8]。这一点在宪法修正案上亦无不同。
为了进一步明确印度宪法第368条关于修宪程序的规定的效力,笔者以为,应当对其文本规定进行全面的考虑:
修改前印度宪法第368条主文部分规定⑤:
An amendment of this Constitution may be initiated only by the introduction of a bill for the purpose in either House of Parliament,and when the bill is passed in each House by a majority of the total membership of that House and by a majority of not less than two-thirds of the membership of that House present and voting,it shall be presented to the President for his assent and upon such assent being give to the bill⑥,the Constitution shall stand amend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of the Bill.
[参考译文]
(2)⑦对于本宪法的修正得在议会两院之一中仅以旨在修正宪法的法律案而提起之,当该法律案由各该院以其所有议员2/3以上多数出席和投票,且以各该院所有议员之多数批准后⑧,应呈总统批准,总统应批准之,于兹⑨宪法乃依该法律案的规定修正之。
其将宪法之修正程序进一步分为三个阶段:提案阶段、通过阶段和生效阶段⑩。就提案阶段而言,宪法第368条在提案程序中使用了“得(may)”一词而非“应当(shall)”或者“必须(must)”。但对于“得”字的解释,学者认为,在通常情况下,其可能仅是一种指引,即包含该字的规定只是一种指引性规定,不具有强制力;但在一些情形下,“得”字之意乃是“应当”,应视其所处语境而进行解释(11)。就此而言,倘比照宪法第4条、第169条、第239A条、第239AA条、第243M条、第243ZC条、第244A条及第312条等规定进行解读,则可以在这些条文之所以强调其修改并非宪法第368条所谓之修正时,除了表明这些事项可以以普通立法程序予以修改之外,实际上也从另一个侧面强调了修宪程序的特殊性。为此,对于“得”字应作“应当”或者“必须”解释。就此而言,应当认为“得”一词在赋予提案者以权力之时,同时也课予其以相应的宪法义务,即在提起宪法修正案之时,必须亦仅得以法律案之形式(形式要件)提起,在议会两院之一(地点)提起;在议会两院通过之后,即应将之送交总统批准,一旦总统批准之后,则宪法即应受修正(12)。不过,在宪法第24修正案生效之后,修正程序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变化。在之前,对于联邦总统是否享有对宪法修正案提案之否决权虽然存在争议,但是,一般亦认为,总统本人对于宪法修正案提案并不享有实体性的否决权,其根据宪法第74条的规定而遵照内阁的决定而行使其否决权;但是经宪法第24修正案修正之后,只要(宪法修正)法律案按照法定程序批准后送交总统,总统就必须签署,就此而言,总统只是“橡皮图章”,其同意只是一个形式过程而已,并不对宪法的修正过程产生实质影响。不过,这一变化并未改变宪法对于修宪程序的强制性要求。宪法第368条但书规定除要求尚应由1/2以上邦立法机关以决议形式予以批准之外,其规定则相同。
不过,应当注意的是宪法第368条存在诸多缺漏:其并未对提案主体和提案程序予以明确的规定,也未明确本条规定中的(宪法修正)法律案(Bill)为何,与宪法第107条规定的普通之法律案是否相同,是否适用相同的提案程序;以及在(宪法修正)法律案提起之后,受提案的议院是否有权决定是否纳入议事程序并且于何时予以表决,在表决之后应于何时以何种形式送交另一院进行表决,另一院得否对该法律案进行修改后再予以表决,修改之后是否应移交原议院再进行表决,原议院如果不同意修改,应当如何解决。在第二院通过之后,又应当于何时以何种形式送交总统批准,必要时应于何时并以何种形式送交各邦立法机关予以批准。各邦又应在何种期限内作出决议。在批准的邦立法达到法定多数之后,又应于何时、何种形式送交总统批准。总统应于什么期限内作出批准决定。不仅如此,该条也未规定宪法修正案的公布程序。再加上,宪法中亦未对于过渡时期,即第一届议会正式召集之前能否修宪以及如何修宪予以限制。宪法第368条制宪时的这些缺漏为之后围绕宪法修正程序的争议大开方便之门。
(二)印度最高法院对于违反修宪程序的宪法修正案的审查
有关宪法修正程序问题的第一个争议案件是Shankari Prasad案。在该案中,申请人的其中一个主张为:一方面因为宪法第一修正案乃是由临时议会,即暂行其权的制宪会议(Constituent Assembly)通过的,但其并无修宪权。尽管宪法第379条规定在第一届议会正式召集之前,由制宪会议暂行宪法授予议会(Parliament)所有权限;但是依照宪法第368条的规定,宪法修正案应以(宪法修正)法律案之形式在议会两院之一提起,并且以各该院全体议员2/3以上多数出席并投票,且应各该院全体议员之多数通过,才能送交总统批准或者送交各邦立法机关,待其多数以决议形式批准后,才能送交总统批准。无论是20编的标题还是第368条的标题和规范语句中都未出现作为独立主体的“议会(Parliament)”,其主体均为“院(House或者House of Parliament)”,相比之下,宪法其他条款,如第2条、第3条、第33条及第34条等,在授予议会权限时,均明确以“议会(Parliament)”作为其主体,显然,制宪者是有意避免以“议会”作为宪法第368条之主体,为此,不能认为宪法第379条授予临时议会的权限中包括修宪的权力;另一方面,该修正案所增加的第31A条和第31B条限制了高等法院依据宪法第226条的权力签发令状以实施宪法第3编之基本权、最高法院依据宪法第132条和第136条签发令状的权力,其应以宪法第368条但书规定的特殊程序而为修正,但第一修正案的通过显然未遵循这一规定。故应当宣告其违反宪法第368条所规定之程序而无效[9]。对于此,最高法院一方面认为实体上,临时议会有权行使宪法第368条规定的修宪权。该条规定中字面上虽然分别指向议会两院和总统,而非议会,但这并不能得出如下结论,即,宪法未授予议会以修宪权,而是将之授予由两院组成的其他机构。宪法第379条中“宪法授予议会的所有权力”的规定所指称的“权力”并不限于临时议会作为一院能够行使的那些权力,它同样涵盖宪法第368条的修宪权;另外,1951年宪法第一修正案所增加的宪法第31A条和第31B条并未对高等法院根据宪法第226条规定而享有的颁布令状以实施宪法第3编基本权利的权力和最高法院根据宪法第136条和第136条规定而享有的受理对颁布或者拒绝颁布令状决定的上诉的权力。它们只是将第3编基本权利下的某些类型案件予以排除。故此,并无宪法第368条但书规定适用的余地[10]。
然而,笔者以为,在该案中,最高法院在其论辩过程中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即一旦允许两院以联席会议,即以议会作为一个整体的形式,而行使修宪权,无疑可能会降低修宪程序的刚性。而对于那些主张应采取比宪法第368条规定的程序更为简易的程序而对宪法进行修正者,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B.R.Ambedkar博士在向制宪会议作草案报告时就已经提出严厉的批评,他指出,这一程序对于印度而言已经是底线了,“很难想象比这更简单的程序”[11]。为此,只要能够证明这一点,最高法院也就无须对实体性问题进行处理。而这无疑能够从概率统计上得到确证(13):
模式一:两院分别批准
以当下的议会两院为例,上议院为250人,下议院为530人。根据宪法第368条主文的规定:宪法修正法律案之通过:应由上议院议员总数2/3以上(包括2/3)出席并投票,且以该院议员总数1/2以上(多一人)通过,且下议院议员总数2/3以上(包括2/3)出席并投票,且以该院议员总数1/2(多一个)以上通过。则可以
设每个人出席并投票的概率为x系列(即x1,x2,x3,x4…);
设每个投票人投赞成票的概率为y系列(即y1,y2,y3,y4…);
并设x系列大于2/3的概率为Px,其中Px<1;y系列大于1/2的概率为Py,其中Py<1。
该情形下出席并投票的概率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上议院议员总数2/3以上(包括2/3)出席并投票的概率为P1,即P1:250*x1>=2/3*250;
下议院议员总数2/3以上(包括2/3)出席并投票的概率为P2,即P2:530*x2>=2/3*530;
上议院议员总数2/3以上(包括2/3)出席并投票,且以该院议员总数1/2以上(多一人)通过的概率为P3,即p3:P1*y1>1/2*250;
下议院议员总数2/3以上(包括2/3)出席并投票,且以该院议员总数1/2(多一个)以上通过的概率为P4,即P4:P2*y2>=1/2*530。
即该模式下(宪法修正)法律案通过的概率为:
p3*p4=P(P1*y1*250>1/2*250)*P(p2*y2*530>=1/2*530)=P(P1*y1>1/2)*P(P2*y2>1/2)=(Px*Py)*(Px*Py)。
模式二:两院联席,即议会作为一个整体
该模式要求两院以其议员总数之合之2/3以上(包括2/3)出席并投票的概率为P1,则P1:780*x3>=780*2/3=Px:
该合之1/2以上(多一人)通过的概率为P2:768*y3>2/1*768=Py。
该模式下(宪法修正)法律案获得通过的概率为:p1*p2=P(x3>2/3)*P(y3>1/2)=Px*Py。
结果:两种模式下(宪法修正)法律案获得通过的概率的比较
因为Px<1,Py<1,故Px*Py<1,故(Px*Py)*(Px*Py) 由此可知,第二种情形通过(宪法修正)法律案相对要容易得多,或者说(宪法修正)法律案获得通过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即修宪程序的刚性程度被降低了。 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采取一种更为简单的数学办法去进行计算: 模式一:两院分别批准 在该模式之下,上议院需要的法定出席人数为250*2/3,取整数,则应出席167人,(宪法修正)法律案要获得通过,应获得(250/2)+1=126张赞成票;下议院需要的法定出席人数为530*2/3,取整数,应为354人,应获得(530/2)+1=266张赞成票。即总的需要521人出席,应获得392张赞成票。 模式二:两院分别批准 而在模式二之下,则只需要法定人数,(250+530)*2/3之取整数,520人出席,获得(250+530)/2+1=391张赞成票即可。 结果:两种模式下(宪法修正)法律案获得通过的条件的比较。 不然发现,模式二对于出席并投票之法定人数和获得通过的法定票数的要求,都要比模式一相对简单一些。 就此而言,难谓由临时议会对宪法进行修正合乎宪法第368条所规定的程序。 在Sankari Prasad案判决之后,有关宪法的修正程序是否合乎宪法第368条的规定曾经多次地摆到最高法院的面前。如在Sajjan Singh案中,有关当事人再次以第17修正案之通过同时造成对宪法第6编第5章第226条有关高等法院管辖权的规定的修改,而根据宪法第368条但书条款的规定,涉及此类事项之修改应当适用宪法第368条但书条款所规定之特殊程序,即尚须由1/2以上邦立法机关以决议形式批准之后,方能送交总统批准生效,为此应根据宪法第368条之规定判断宪法第17修正案违宪无效。但是,最高法院并未支持此项请求,最后的判决亦是对宪法上基本权利规定是否得受修正的实体问题作出的。而1989年的Builders Association of India案中,申请人同样以宪法第46修正案违反宪法第368条第2款规定为由提起诉讼,认为宪法第46修正案所涉内容应以宪法第368条第2款修正之,但议会却适用主文程序,故主张其违宪无效,不过,最高法院认为,宪法第46修正案所涉内容并无前揭但书条款适用之余地驳回了这一诉讼请求[12]。 在Indira Gandhi案判决中,被申请人在主张系争宪法修正案侵害宪法的基本特征的同时,也提出一个理由,即在修宪前,Indira Gandhi促使当时的总统根据宪法第359条颁布总统令,许多议员于1975年6月26日而被羁押,从而被剥夺了出席议会会议的权利以及言论自由权,并且有关机关并未告知对其进行羁押的理由也未给予其辩护的机会[13]。但最高法院驳回了这一主张,认为此并不能导致宪法修正案的无效,因为宪法系争第39修正案是按照宪法第368条的程序通过的。然而,应当注意的是,由于大部分反对派议员被羁押,这不仅客观上对出席修正法律案表决的议员造成了心理上的压力,使其中某些人可能违背其初衷而投赞成票。另外,由于作为少数的反对派议员被羁押,使得原本就已经获得修宪所需多数议席的国大党,进一步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而由于反对派议员无法在议会上就发表其对于系争宪法修正案的相反意见,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议会丧失作为言论市场的功能,实际上成了多数人的保证,违背民主的精神和实质。就此而言,难谓第39修正案的批准是合乎宪法第368条规定的程序的。 在A.K.Roy案,申请人主张议会,宪法第44修正案第1条第1款本身附有一个前提条件,即中央政府可以在政府公报上以通告的形式指定该修正案的全部或一部之生效,不同条款生效时间亦可不同,其并规定只有在满足这一条件的情形下,宪法修正案方能生效,违反了宪法第368条中的程序性和实体性两方面的规定,故请求最高法院裁定该修正案无效。在判决中,对于程序问题,最高法院对宪法第368条的“shall stand amended”与“shall come into force”两者做了区别,即在经总统批准之后,宪法文本即依据(宪法修正)法律案之规定而受修正,但是,和其他法律之生效一样,此并未排除让修正案生效的必要。据此,宪法修正案仅在其生效时才成为宪法之一部分。其同时指出,修宪机关也可以在(宪法修正)法律案中规定一个条款是在批准之后立即生效,抑或是于规定的未来某一日期生效,或者由行政机关或者其他机关设定的某一日期生效(即“附条件立法”)[14]。故而宪法第44修正案并未违反上揭规定,乃是合宪的。 Kihoto Hollohan案判决是印度最高法院第一个以违反宪法第368条所规定之修宪程序为由而判决宪法修正案无效之判决。在该判决中,最高法院认为宪法第10附录第7段虽然并未改变宪法第136条、第226条、第227条等的文字,但是,其实际上对这些条文进行了修改,故而,按照应当根据宪法第368条第2款的但书规定的程序而对宪法进行修正,但是修宪机关未能遵循这一程序,故而裁定该部分修正案违宪无效。 四、结论 从以上印度最高法院对宪法修正案的合宪性的审查历史来看,最高法院基于程序理由而对宪法修正案的合宪性进行审查的案件并不多,究其原因:首先,可能是因为宪法第368条对于修宪权是否存在界限未曾具文,而系争的宪法修正案多数旨在剥夺或者克减人民的基本权利,或者限制法院的司法审查的权限,而这会在法官中产生一种“可获式启发(Availability Heuristics)”[15]从而导致其认知的偏差(Cognitive biases),使之围绕实体性问题,即修宪权是否存在界限、其界限如何而进行法律论辩,而忽视与修宪权的界限可能具有同等重要性的问题——即议会在行使修宪权时程序本身是否存在瑕疵,这种瑕疵是否足以导致宪法修正案的无效;其次,由于最高法院在行使司法审查时本身就扮演一定的政策制定者的角色,且其法官中有一部分在就任大法官之前乃是检察总长或者邦总督,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最高法院的司法能动主义,积极地参与政策的形成,所以,在其判决中更倾向于就实体问题作出判断;再者,印度宪法所规定的修宪程序刚性本就不强,这使得议会中的多数党很容易就能达到修宪的目的,无需在程序上做文章。 不过,应当注意的是,即使就宪法修正程序的有关规定而言,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两种主张:一是主张应当严格执行宪法有关修宪程序的规定,只要存在违宪情形即应宣告其违宪无效;但与之相对的,则主张进一步将修宪程序进行分割,即一旦有权机关之修宪程序违反的程序,依照宪法本身的目的和规定,体现了重要的宪法价值,如人权保障价值,或者重要的宪法原则,如人民主权、分权原则和联邦主义之时,则应当宣布其违宪无效;但是倘若其所违反的程序并非具有重大的宪法上价值,则违宪审查机关应当对其它机关予以充分尊重,保持司法节制[16]。在此问题上,宜采后者,一方面因为有些程序规定可能是议会的内部程序规定,并不具有实体性价值,其不至于对宪法、宪法修正案或者修宪机关的权威造成巨大影响,或者只有微不足道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因为宪法的修正乃是一民主的过程,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人民的意志,且其内容多涉及国家根本性问题,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对于此,司法机关宜抱持审慎的态度,并保持司法谦抑;再一方面,则由于宪法的修正一般需要支出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耗费甚巨,苟非存在重大明显瑕疵,并且对宪法、修宪机关的权威和运行造成严重损害,亦不可轻易推翻。在这一点上印度最高法院虽然未直接表明其态度,但是其所采取的裁定后向适用原则(Doctrine of prospective overruling)则表明无疑其乃是服膺这一见解的。 注释: ①参见林永谋大法官之“部分协同意见书”,中国台湾“司法院大法官会议解释”释字第499号。 ②参见中国台湾“司法院大法官会议解释”释字第499号。 ③参见中国台湾“司法院大法官会议解释”释字第342号。 ④Referred to AIR 1951 SC 458;1952 SCR 89,in O P.Arora(ed.),The Constitution of India,Vo1.4,Madras:Madras Law Journal Office(1998),p.420.应当注意的是,此处所谓的不完全的规定与Hans Kelsen之谓“incomplete code”并不完全一致。Hans Kelsen认为法律本质在于强制性(Coercion),即违反此类规定会导致惩罚(Sanction),故一个完全的规定必然包括惩罚性条款。就此而言,缺乏强制性规定之条文不能认为其乃所谓“法律”。不过,程序性条款虽然没有强制性规定,但是由于完全条款之实施有赖于不完全条款的规定,故而其仍为法律,只不过乃是不完全法条。Referred to Hans Kelsen,Law and Peace,Cambridge & 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2),p.19~20.至于本文意义上的完全法务的区分,可参见[德]卡尔·拉伦茨著:《法学方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32~144页。 ⑤1971年宪法第24修正案增加了有关条款,故其第3条规定将原来的第一款挪为第二款。 ⑥1971年宪法第24修正案修改为“it shall be presented to the President who shall give his assent to the Bill and thereupon”。 ⑦1971年宪法第24修正案第3款将之改为第2款,在此之前,宪法仅有该款规定。 ⑧此处对宪法该条文的表述作了适当的调整,原文为“…and when the Bill is passed in each House by a majority of the membership of that House and by a majority of not less than two-thirds of that House present and voting…”,若以中文直译,则为“当该法律案由各该院以其所有议员的多数,且以其所有议员的2/3以上多数出席并投票批准后”,在逻辑上则未免有颠倒先后顺序之嫌。 ⑨1971年宪法第24修正案第3款对该部分文字进行了修正,原文为:“……应呈总统批准,在总统批准之后,宪法乃依该宪法修正法律案规定修正之。” ⑩关于第三阶段是否为生效阶段。印度最高法院在Waman Rao案中对“受修正(stand amended)”与“生效(come into force)”作了区分,最高法院在A.K.Roy案判决中指出,宪法修正案在总统签署仍然需要在政府公报上予以公告,故此仅能谓乃其中之一步。 (11)Referred to M.P.Jain & S.N.Jain,Principles of Administrative Law,Vol.1,New Delhi· Agra· Nagpur:Wadhwa and Company(2007)(6),p.158. (12)应注意这里强调的仍只是形式意义上的文本的修正,并未产生实际的效力。即使总统签署了(宪法修正)法律案,其尚须以政府公报予以公告方能正式生效。这在此前的A.K.Roy案判决中已有详论,不赘。至于在总统签署(宪法修正)法律案后至公告前这一段时间,如何适用宪法的问题,印度宪法并未作明确的规定,而就笔者目前的阅读范围而言,亦未发现印度宪法学者对于此问题进行探讨。似乎可以认为,在(宪法修正)法律案公告之前,仍应援用修正前的宪法条文,理由有二:一方面未经公告的(宪法修正)法律案不具有法律效力,故就实质意义上讲,宪法并未受到修正,虽然宪法文本上依照宪法第368条已有变更;二、如果肯认在总统签署之后,则宪法文本的形式上的修正亦导致对其实质性的修正,那么,一方面无疑等于肯认未经公告而宪法即受修正,则违背法治的根本精神,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宪法适用上的真空期,从而导致宪法机制的运作在某些领域和时期出现中断,破坏宪法的连续性。 (13)特别感谢陈后猛(中国人民大学计算机专业2007届硕士)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