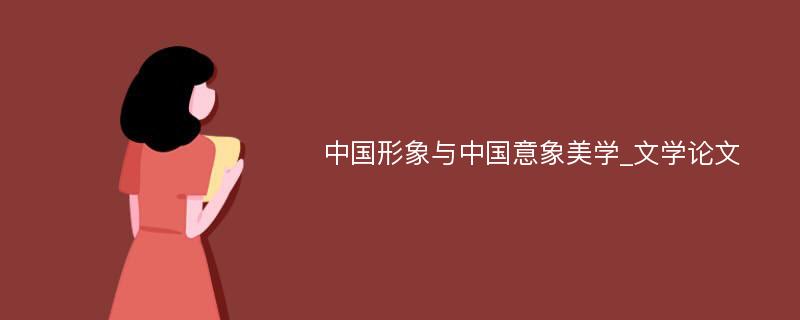
汉语形象与汉语形象美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形象论文,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提出“修辞论美学”主张以来(注:《走向修辞论美学》,《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我由此角度对中国形象及汉语形象问题作了一些本文分析。这种具体批评实践使我认识到,修辞论美学应当依托于更基本的汉语形象研究框架——汉语形象美学,它为修辞论美学提供基本方面。谈论中国文学,其实往往就是谈论汉语文学。而汉语文学的突出特点之一在于,其汉语组织本身就具有美的“形象”,例如,这种美的形象往往鲜明地表现在汉语的语音形象中。朱光潜把诗定义为“有音律的纯文学”(注:朱光潜:《诗论》(1943年),据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98页。),甚至还要求散文也把“声音节奏”作为“第一件要事”(注:朱光潜:《散文的声音节奏》(1943年),据朱光潜《艺文杂谈》,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2-83页。),足见他对语音形象的重视程度。这里的“第一”的特殊含义在于,“声音节奏”不仅本身富于美的情趣,而且正是它才使得文学中至关重要的审美“情趣”得以“表现”出来。这样,我们就不得不面对中国文学中“第一”重要的汉语形象问题。这个问题曾为我们的主流诗学或美学所长期遗忘或压抑,八十年代以来虽时有翻新之举,却始终未能在理论上得到真正明确而具体的落实,这就难免使我们的诗学或美学在表面的神气活现下隐藏着一种内在基础虚空。
一、语言和语言形象
语言在文学中的重要性似乎历来就不容争辩:它作为声音与意义相结合的系统,是文学的表达媒介,因而不能设想当离开语言后是否还有文学存在。但这种表达媒介是否就如西方古典学者所相信的那样,只是一种借以窥见现实的“透明”物而自身并无特殊价值?在20世纪发生的意义深远的“语言学革命”或“语言论转向”中,人们认识到,语言决不是文学的简单物质外壳,而就是文学的直接“存在”,文学也从而被视为语言组织的构成物或创造物(注:参见笔者《语言乌托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有关论述。)。伊格尔顿总结说:“从索绪尔和维特根斯坦直到当代文学理论,二十世纪的‘语言学革命’的特征在于承认,意义不仅是某种以语言‘表达’或者‘反映’的东西:意义其实是被语言创造出来的。我们并不是先有意义或经验,然后再着手为之穿上语词;我们能够拥有意义和经验仅仅是因为我们拥有一种语言以容纳经验。而且,这就意味着,我们的作为个人的经验归根结底是社会的;因为根本不可能有私人语言这种东西,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完整的社会生活。”(注: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6页。)这等于说,不是先有头脑里的文学(意义)而后要求语言去使之“物态化”,而是文学就由语言构成,是语言在构成或创造文学,离开了语言就没有文学。
在文学中语言是以语言形象这一特殊方式存在的。“语言形象”(image of language)是已故前苏联批评家巴赫金(M.Bakhtin)讨论艺术话语、主要是小说话语时的一个核心概念,也是他倡导的“社会文体学”的重要概念之一。他认为,“作为一种文类,小说的特征并非人物形象本身,而正是语言形象”(注:巴赫金:《对话性想象》,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36、416页。)。人物形象是由语言形象构成的,并且与语言形象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不是人物形象而是语言形象才是小说的最直接现实。这里所谓语言形象,主要不是指由具体语言(话语)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如人物形象),而是指使这种艺术形象创造出来的具体语言组织形态,或者说,是创造这种艺术形象的具体语言组织形态。对此,巴赫金说得很明确:“小说所包含的是一个语言的艺术系统,更准确地说,是一个语言形象系统。文体学分析的真正任务就在于,发现小说结构中各种交响性语言;把握各种语言之间距离的尺度,这种距离使各种语言与作品整体中的最直接语义表述相疏离;衡量作品中意向折射的不同角度;理解各语言之间的对话关系;最后,在直接的权威话语占主导的作品中,判断作品之外的杂语喧哗背景及其对话关系(这在分析独白式小说时尤为重要)。”(注:巴赫金:《对话性想象》,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36、416页。)可见,对巴赫金来说,语言形象涉及的是小说中具体而多样的语言组织、形态、声音和对话关系等方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赫金认为,“小说文体学的中心问题可以被表述为艺术地再现语言的问题或再现语言形象的问题”(注:巴赫金:《对话性想象》,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36、416页。)。不过,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巴赫金看来,语言形象不仅指作品中的语言形象,更重要的是,还涉及作品之外的更复杂的社会性语言系统如杂语喧哗。小说中的语言系统与更大的社会语言系统形成复杂的关系——再现。与西方的“摹仿”说或“再现”说传统主张艺术语言再现社会现实不同,巴赫金认为艺术语言不仅再现社会现实,而且再现社会语言形象,或他者语言形象。小说中的话语不仅再现(现实),而且本身被再现。也就是说,在小说中,社会语言成为被再度处置、再度表达、和艺术性地转换的对象。就我们的研究而言,巴赫金有关语言形象具有双重再现功能的思想是有深刻启迪价值的,它提醒我们关注现代汉语在现代文学中展示的前所未有的新形象,并探讨这种形象背后的文化意义,当然,巴赫不可能注意到,汉语形象对于汉语文学具有远为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语言形象是文学的一个基本而重要的方面。约略地说,它是由文学的具体话语组织所呈现的富有作者个性特征和独特魅力的语言形态,是文学的艺术形象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这是说文学语言(话语)组织本身就具有形象性,就是艺术形象。这里,语言形象是文学所创造的艺术形象系统的一部分,而且是最直接和基本的一部分。因此,文学的艺术形象系统只能由语言形象“创造”出来,并且只能“存在”于语言形象之中,所以具有间接性;而倘若离开了语言形象,整个艺术形象系统就不可能存在了。所以,语言形象是文学的艺术形象系统的最直接“现实”,甚至可以说是最基本“现实”。与此相应,人们常说文学的艺术形象总是“美”的,这首先应是指:文学的语言形象总是“美”的。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指出:“语言是我们所知的最硕大、最广博的艺术,是世世代代无意识地创造出来的、无名氏的作品,像山岳一样伟大。”(注:萨丕尔:《语言论》,陆卓元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97页。)一般的语言都是“艺术”,那么,作为一种艺术的文学语言呢?“每一个语言本身都是一种集体的表达艺术。其中隐藏着一些审美因素——语音的、节奏的、象征、形态——是不能和任何别的语言全部共有的。……艺术家必须利用自己本土语言的美的资源。”(注:萨丕尔:《语言论》,陆卓元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01-202页。)在文学中,通过作家对语言这“美的资源”的开发、铸造和组织,语言本身就能显示出它的独特的形象之“美”来。
二、汉语形象及其修辞性
这里的汉语形象,是汉语文学的语言修辞形象的简称。语言形象的性质如何?可以说,汉语形象并不等于文字本身的形体形象,这一点在汉语中尤其应当辨明。首先须看到,汉语形象不等于汉字形象。汉字本身就有着“形象”、甚至可以说是“美”的形象,这是由汉字的方块形体特征决定的。这种由汉字的方块形体组成的汉字形象主要是汉语文字学(即汉字学)研究的对象,而不是诗学的研究对象。同时,汉语形象也不等于汉字书法形象。汉字的一个特殊性在于,当它的笔墨形体本身按专门的书法艺术或美学规范组织起来,形成具有书写者独特个性和特殊感染力的形式、节奏和气韵整体时,就成为艺术形象,这属于汉字书法艺术形象(简称汉字书法形象)。这种形象是中国书法艺术和美学探讨的问题,它同样不是诗学的研究对象。
汉语形象主要不是从汉语的文字形象(即汉字形象)和汉字书法形象而言的,而是从汉语在诗中的具体表现或修辞功能而言的。当然,无可否认,单从语言学角度看,汉语的形式因素如声调、语调、节奏和韵律等本身具有一种形式美。语言学家王力就认为:“语言形式美……是从多样中求整齐,从不同中求协调,让矛盾统一,形成了和谐的形式美”(注:王力:《龙虫并雕斋》,第1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60页。)。然而,在文学中,这种语言形式美只有当其服务于具体修辞目的并取得一定的成功时,才有真正的审美价值。也就是说,汉语形象是当汉语的四声、平仄、音律、对仗、比喻和排比等表现功能被应用于文学的审美—艺术表现并获得成功时,才体现出来的,即是汉语在审美—艺术表现上显示出的修辞性形象。所以,汉语形象的美不是单纯的形式美,而是一种修辞美。启功在论述古代文学语言时说过:“在古代汉语中尤其是诗歌、骈文中,修辞与语法往往是不可分的。修辞的作用有时比语法作用更大,甚至在某些句、段、篇中的语法即只是修辞。所以……语法……同时也包括了修辞”(注:启功:《汉语现象论丛》,香港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3页。)。这种关于文学中修辞统摄或决定语法的见解,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汉语形象的性质和特点。
文学的汉语形象说到底就是一种修辞性的形象。修辞,在这里指调整和组织言语以便造成社会感染效果的方式及过程。作为一种修辞性形象,汉语的审美价值在于,它被精心调整和组织起来,以便成功地实现特定的表达意图,并最终在读者中造成强烈的社会感染效果。换言之,汉语形象的审美价值主要在于它在审美—艺术表现上的修辞性价值。所以,不妨这样约略地描述说(不是严格定义),汉语形象主要是指汉语的修辞性形象,它是文学中的汉语组织在语音、词法、句法、篇法、辞格和语体等方面呈现出来的富于表现力及独特个性的美的形态。
三、汉语形象的具体形态
作为一种修辞性形象,汉语形象的具体修辞形态如何呢?这里暂且提出四个层面:语音形象、文法形象、辞格形象和语体形象。
1.语音形象。这是指汉语的语音组织在表意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艺术形象系统。汉语语音组织当其成功地和富于个性地实现了表达意图时,本身就会展现出特殊的“美”的世界。中国古典文学历来注重语音形象的创造,清代沈德潜说:“诗以声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读者静气按节,密咏恬吟,觉前人声中难写,响外别传之外,一齐俱出。朱子云:‘讽咏以倡之,涵濡以体之’,真得读诗趣味”(注:沈德潜:《说诗晬语》。)。可知语音形象是文学的“美”的重要成分之一,也是汉语形象的“美”的一个极重要方面。轻视语音形象就不能完整地理解文学及其汉语形象的美。林语堂注意到汉语的“单音节性”对于文学的特殊意义:“这种极端的单音节性……造就了中国文学的美。于是我们有了每行七个音节的标准诗律,每一行即可包括英语白韵诗两行的内容,这种效果在英语或任何一种口语中都是绝难想象的。无论是在诗歌里还是在散文中,这种词语的凝练造就了一种特别的风格,其中每个字、每个音节都经过反复斟酌,体现了最微妙的语音价值,且意味无穷。”(注:林语堂:《中国人》(1939), 郝志东、沈益洪译,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222-223页。)朱光潜认为“既然是文章,无论古今中外,都离不掉声音节奏。”(注:朱光潜:《散文的声音节奏》(1943年),据朱光潜《艺文杂谈》,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2-83页。)小说家汪曾祺更把“节奏”视为小说语言最重要的方面:“一篇小说,要有一个贯串全篇的节奏”(注:《汪曾祺文集·文论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1页。)。
从构成上看,语音形象可以分为四个方面:声调形象、语调形象、节奏形象和韵律形象。大体说来,声调(也叫字调)指每一音节所固有的能区别词汇或语法意义的声音的高低升降状况;语调,则指整句话或整句话中的某个片段在语音上的高低升降状况;节奏指由声调和语调共同构成的语音整体在一定时间里呈现的长短、高低、轻重和音质等规律的变化状况;韵律形象则指上述语音变化所形成的内部和谐状况。汉语的语音如声调和语调本身就是丰富的“美的资源”。
2.文法形象。这里的“文法”借自中国古典美学,指的不是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语法”,而是“作文”和“作诗”之修辞“法度”,即文学写作的修辞法则,在这里主要指文学语言的修辞法则。具体说,文法形象是汉语的语词、语句和语篇组织在表意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富于修辞性的形象系统。这一系统包括词法形象、句法形象和篇法形象。词法、句法和篇法分别指特定诗本文内的语词、语句及篇章(还有大型本文如长诗或系列诗)的语言修辞法则。古人主张:“学问有渊源,文章有法度。文有文法,诗有诗法,字有字法,凡世间一能一艺,无不有法。得之则成,失之则否”(注:【元】揭曼硕:《诗法正宗》,《诗学指南》卷1。)。可见文法是极其重要的。当然,文法应是变化的,应是“活法”而不是“死法”。苏轼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正是指此。具体到一篇本文中,则是篇法、句法和字法都重要,都应显示出各自独特而又统一的形象来。王世贞说:“首尾开合,繁简奇正,备极其度,篇法也。抑扬顿挫,长短节奏,各极其致,句法也。点掇关键,金石绮彩,各极其造,字法也。篇法,有起,有束,有放,有敛,有唤,有应,大抵一开则一阖,一扬则一抑,一象则一意,无偏用者。句法,有直下者,有倒插者。倒插最难,非老杜不能也。字法,有虚,有实,有沉,有响,虚、响易工,沉、实难至。……篇法之妙,有不见句法者;句法之妙,有不见字法者:此是法极无迹,人能之至,境与天会,未易求也。”(注:【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1,据《历代诗话续编》。)这里实际上生动清晰地勾勒出文法的形象之美。
3.辞格形象。辞格(在古代还称辞藻或语格),即通常修辞学意义上的辞格,是那种形成一定表现模式的富有特殊审美表现力的言语方式。汉语的传统辞格是十分丰富的,如比喻、比拟、拈连、仿拟、引用、跳脱、排比、反复、对偶、夸张、反语、倒装、回文等;新的辞格也层出不穷,如留白、新典、双饰、用歧、会意、绝语、闪避、别解等。辞格的成功运用往往会使汉语呈现出动人的“形象”魅力。此外,象征、隐喻等方式也可以视为辞格形象的组成部分。然而,文学的辞格形象并不在于已有辞格的简单沿用,而在于它的富于原创性和个性的重新组织。
4.语体形象。语体形象是针对文学本文中的多种文类、语式或体式运用而言的,指文学本文当其为造成特殊的表达效果而综合地混杂或并用多种不同文类、语式或体式时呈现的汉语形象。这里的文类,涉及小说、诗、散文诗、散文、日记、书信、文件、档案、表格、绘画和图案等;语式,涉及口语、方言、习语等;体式,则是指较为具体的表现性文体,如抒情体、叙事体和戏剧性,纪实体和传奇体,写实型和象征型等等。
四、八十年代以来汉语形象举例
汪曾祺的小说《昙花、鹤和鬼火》写道:“昙花真美呀!雪白雪白的。白得像玉,像通草,像天上的云。花心淡黄得像没有颜色,淡得真雅。她像一个睡醒的美人,正在舒展着她的肢体,一面吹出醉人的香气。啊呀,真香呀!香死了!”“绿光飞来飞去。它们飞舞着,一道一道碧绿的抛物线。绿光飞得很慢,好像在幽幽地哭泣。忽然又飞快了,聚在一起;又散开了,好像又笑了,笑得那样轻。绿光纵横交错,织成了一面疏网:忽然又飞到高处,落下来,像一道放慢了的喷泉。绿光在集会,在交谈。你们谈什么?……”。这里,第一段用“像……”的比喻句式反复渲染出响亮而明快的音节效果,而“她像一个睡醒的美人……”的比喻,更传达出昙花的悠长而醉人气息。第二段交替地用了比喻(“一道一道碧绿的抛物线”、“好像在幽幽地哭泣”、“像一道放慢了的喷泉”)和拟人(“好像在幽幽地哭泣”、“好像又笑了,笑得那样轻”、“绿光在集会,在交谈”)等辞格,使绿色的轻盈而美妙姿态生动地呈现出来,短促句式也突出了一种轻快的节奏,从而使画面和声调完满而和谐地组合起来。这些独特的辞格方式有效地烘托出一种汉语节奏,使小说呈现出丰富而意味深长的语音和辞格形象。
海子的诗歌鲜明地呈现出“如歌”的特点,从而使诗歌表现出了歌韵。在这一点上他在当代诗人中似乎是独一无二的。“歌”指歌唱,如歌唱一样;“韵”指韵律。歌韵,就是汉语形象使人产生聆听歌唱一样的韵律感。他的《九月》这样说:“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我把这远方的远归还草原/一个叫木头一个叫马尾/我的琴声呜咽 泪水全无/远方只有在死亡中凝聚野花一片/明月如镜 高悬草原 映照千年岁月/我的琴声呜咽 泪水全无/只身打马过草原”。诗的总体结构服从于歌唱,突出了歌唱的回环复沓要求。反复三次运用“我的琴声呜咽 泪水全无”句式,既是出于语气上的强调,更是出于歌唱上的回环和韵律要求。同时,其他词法也如此:“草原”在第1、4、8、9行反复出现;“野花”在第1和7行形成照应;“远”和“远方”则在第2、4、7行一再出现,而且还出现行内反复(如“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全诗借助歌唱式结构使现代汉语形成了强烈的韵律感。这是如歌的诗创造之韵,是在歌唱中重构之韵。这是海子对于现代诗坛作出的一个重要贡献之一。至少可以说,有了海子,人们有关现代诗不讲或缺乏韵律的苛责,应当可以终结了。他使现代汉诗呈现了自身独特的韵律效果,而这是古代汉语诗所不可能有的汉语形象特征。两者各有其审美特征。
柏桦的《现实》说:“这是温和,不是温和的修辞学/这是厌烦,厌烦本身//呵,前途、阅读、转身/一切都是慢的//长夜里,收割并非出自必要/长夜里,速度应该省掉//而冬天也可能正是春天/而鲁迅也可能正是林语堂”。这里以一种反向修辞方式对现实生活修辞状况的可靠性提出质疑。不妨比较顾城《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里的“黑夜”与“光明”两个词的含义似乎是确定的,它们在触及现实世界时也是确定的。与顾城相信词语的万能而主要质疑现实世界不同,柏桦向日常生活词语修辞的虚幻性和欺骗性发出尖锐反诘:你们所谓“温和的修辞学”掩盖着的难道不是真实的暴虐或残酷?而真实的“温和”却被无限期放逐了。然而,诗人相信,相反事物会转化,虚幻修辞也可能孕育或蕴蓄真实修辞:“而冬天也可能正是春天”,新的春天不正蕴蓄在严冬之中么(想想雪莱名句“严冬已近,春天还会远吗”)?
刘恪小说集《梦中情人》以异体化韵的语体形象引人注目。异体化韵,就是多种不同的语体相互间化合出流散的韵律。语体是不同的,但不同间有化合;韵律是流散的或片断的,但流散中有聚集。例如,小说叙述体与散文和诗歌抒情体常常是随时切换的。叙述人讲故事时会使人不经意中转换到散文语句上去,而散文语句又进一步自然而然地滑向诗,产生小说、散文和诗三种语体相互化生效果。如《梦中情人》写“我”近两年中常有被追杀的梦境,摆出讲故事的架势,但却有如下一段:“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却依然盘腿于棠棣树前,合掌于腹线,空明内心一切陈迹,默默地把思绪寄存于蓝天白云之上,却不知道,我座位已悄悄向黑暗深处陷落,灵魂滴下那一片废止的荒原”。这段显然已变为散文,并逐渐诗化,到末句“灵魂滴下”已是诗句了。接着是如下段落:“月光无法到达那片空地 唯有白色的羊群或驼队 爬过山岗 空下一棵树的影子 如果从后面追赶 诗 或诗意就散落在山那边 一片绿色的草地”。就干脆转为语义丰富而含混的诗了。再接下来又回复为散文句式:“我在都市的躯体内写作,任凭文字在黑暗里流淌。没有想过什么时候开始,也没有想过在什么时候结束,闭上眼睛世界与我分流。让世界燃烧最后一份热量,阳光穿过丛林,照着时间重复后的乡村,唯流水依旧迷人,拱桥支撑着生命,时间筛选人生所有的水滴,不要害怕我曾经储存过黑,只要今夜灵魂透明”。以散文形式排列的语句不仅仍携诗意,且本身就应看作诗,在这里,小说、散文和诗三者之间的传统语体界限轰然崩塌,散化为绵绵诗情,让人感到韵味无穷。这些例子似已表明,汉语形象的美代表了汉语文学的基本方面。
五、汉语形象作为现代性问题
汉语形象在汉语文学中是十分重要的。但这个问题真正成为实质性大“问题”则是在鸦片战争以来的“现代”。因为,在这之前,古代汉语在古代文学中的卓越的审美—表现功能仿佛是无需怀疑的。只是在鸦片战争以来,随着中国的现代性工程的启动,中国人的新的现代生存体验无法在古代汉语中找到令人满意的表现,汉语的形象才受到怀疑,成了实质性大问题。于是,创造新的属于现代的汉语,以便尽情地和完满地表现现代人的新的生存体验,就作为汉语形象问题出来了。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好了,就可能重新树立中国文化在现代世界的令人崇敬“形象”,因而直接牵涉到中国现代文化的“身份认同”。所以,汉语形象问题作为现代性问题,是中国文化现代性的一个高度凝缩形式。可见,现代的汉语形象问题说到底应从审美现代性和汉语现代性相交叉的坐标上来考察,即它是汉语在现代文学中如何有效地和有力地表现中国人的现代生存体验的问题。这样说来,现代汉语形象如何,就不应只是一个通常的现代文学问题了,而是借现代文学问题所披露出的更根本的现代文化问题——现代汉语形象凝缩着整个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形象。
这样的现代汉语形象问题不妨简要概括为如下五个方面:(1)古今语言问题,即现代文学中现代汉语(现代白话)与古代汉语(文言)的关系问题。在现代汉语的新王国里,虽然失势而魅力犹在古代汉语还能重新获得自己表现性权威吗?这是由古代的文言文主导转变为现代的白话文主导以来所必然遭遇的问题。(2)中西语言问题,即现代文学中古汉语传统与西方语言的关系。现代汉语必然要参照西方语言以结构自身,这就有着中国语言与西方语言这两大不同语系的关系问题,如所谓“欧化”与“非欧化”或“中国化”之争。(3)文学语言与官方语言问题,即现代文学中艺术语言与官方语言或政治语言的关系问题。这是在占主导地位的官方语言力求统治文学语言、而后者又试图维护自身自主权时出现的,例如“文革”结束后“朦胧诗”对“文革文学”的语言抗争”。(4)雅俗语言问题,即现代文学中精英语言与日常语言、或雅语与俗语、或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有着密切联系,即都涉及白话或俗语与高雅语言或文人语言的关系,但第一个问题更偏重于时间更替意义上的古今关联,而这里则侧重于社会分层上的雅俗关联。当然,在实际中这两者往往纠缠在一起:古今问题有时就成了雅俗问题,而雅俗问题有时被当做古今问题。(5)文学语言本体问题,即现代文学中汉语自身的内在本性、表达极限或存在价值问题。这实际代表了对汉语形象本身的质疑和探究渴望。这五个问题是贯穿于20世纪初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语言问题,正是在对这些挑战问题的应战中,汉语形象显示出自身的风貌。
六、走向汉语形象美学
汉语形象问题在现代汉语文学中的重要意义似已证明。然而,它在诗学或美学中究竟具有怎样的位置呢?倘用现成的重思想内容而轻语言形式的新的美学模式去衡量,它的重要性又似乎会再度失落。这表明,考察汉语形象这一新问题,需要寻找与它相应的新的研究领域作为框架。我们应当据有怎样的新框架呢?或者说,我们在考察汉语形象时应当把它置放在怎样的新框架之中,以便获得更成熟、有力或有效的理论视点、概念框架或分析模型等呢?看来,从汉语形象描述进展到一种有关汉语形象的美学理论框架考虑,已势在必然。这里,暂且不妨提出汉语形象美学这一新考虑。汉语形象美学,简单说来,就是一种有关文学的汉语形象的审美特征的诗学研究。作为诗学的一个领域或方式,汉语形象美学侧重于从汉语一审美角度探索文学问题。
汉语形象美学,是关于文学的汉语形象的修辞性和审美特性及其在文学中的基本作用的研究领域或方式。这需要从对象和属性两方面阐述。
汉语形象美学的对象,不是一般社会性语言,即不是汉语语言学意义上的汉语,而是文学中的汉语形象。当然,它在研究文学的汉语形象时,又不能斩断与社会性汉语的联系纽带,而是需要密切关注和考察这种联系。因为,前者往往以特殊的修辞方式“再现”并作用于后者。忽视了后者,前者就失去了产生与存在的基本缘由和社会作用场。例如,韩东、于坚等的口语式语言在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前期产生深刻影响的原因之一,正在于它实际上是那时期在社会生活中扮演活跃角色的市民日常口语的“再现”。自从“文革”结束以来,随着改革和开放的进程,过去长期左右人们生活的一体化“语言”,如“斗争哲学”等,日渐显露其“伪崇高”或“伪神圣”本相,所以遭到了市民发自内心的嘲弄或调侃。而如何在文学中更有力和有效地展示这种新的日常生活语言,无疑正是历史的一种必然要求。诗人们适时而幸运地投合了时代的这一强烈的社会性语言需要,使市民的口语化行为激荡起新的波澜。如果看不到社会性语言需要与诗中汉语形象的关系,就会使汉语形象研究误入“象牙塔”歧途,失去“源头活水”。
汉语形象的修辞性集中表现在,文学中的汉语是为着造成特殊的社会感染效果而组织起来,汉语的调整服从于社会效果的获得。因此,汉语形象的美与其说在于汉语本身的美,不如说在于汉语的实际社会效果的获得上:它是否有效和有力地表现了人们的生存体验,并在社会中产生丰富而深刻的感染效果。汉语形象美学正是要研究汉语形象的这种修辞性。与此相应,汉语形象美学要研究汉语形象的独特的审美特性。汉语形象的独特审美特性,是建立在它的修辞性基础上的。当着汉语形象有效和有力地表现了人的生存体验并造成实际感染效果时,它就有可能进而显示出审美上的成熟的个性。汉语形象美学需要在汉语形象的修辞性的基础上进而研究其审美特性。
汉语形象美学对于这种修辞性和审美特性的研究,是基于它对语言的新的认识——语言在文学中不再是从属性的因素,而具有基本作用。这意味着,它研究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具性汉语,即作为内容、思想或意义的从属因素的汉语,而是作为创造内容、思想或意义的基本因素的原创性汉语;同时,不是作为诗美的从属因素的汉语,而是作为它的生成因素和当然成分的汉语。如果我们“忽视”了海子的汉语语音形象的“如歌”特点而单说其思想或内容,那就等于“忽视”了他的诗的全部。等到说完了他的诗的内容后再来以“补充”或“此外”的名义说其汉语特点,那就根本不配谈海子。或许可以说,不懂得“歌唱汉语”,就不懂得整个海子?汉语形象美学正是要把汉语形象作为文学的基本因素加以研究,强调汉语形象在特定的文学世界中起着基本现实的作用。这样,汉语形象美学的对象就是文学中与社会性汉语现象相关的汉语形象的修辞性和审美特性及其在文学中的基本作用。
说到汉语形象美学的属性,需要明白它是否是一门学科或科学。一门学科,通常总是要求有比较确定而严格的立足点、对象、范畴和方法论等,如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和语言学等。而在我看来,汉语形象美学不可能也不应当成为这样一门专门的独立学科或科学。如果真的是那样,那就等于把它窒息在襁褓中,它的意义也就丧失了。汉语形象美学不是一门专门的或独立的学科,而是一个开放的诗学研究领域。研究领域,意味着一个没有固定围栏的自由和思考地带,一种向四周敞开的思索空间。在这里,汉语形象问题将作为诗学的基本问题而与其他问题相遇。换言之,汉语形象美学是一种处处以汉语形象问题为基本的有关文学的美学思索方式。作为一种思考方式,它总是提醒人们要非同一般地关注文学中的汉语形象,并把它置放在基本地位上,在此基础上去衡量文学的其他意义。这样,汉语形象美学不过是诗学研究中一个活跃的和流动的基本研究领域或方式。
所谓活跃的和流动的领域或方式,表明汉语形象美学并不把自己固定在汉语形象这一研究范围内,而是要向诗学的其他各个领域渗透或扩展,即从汉语形象这个视点去透视其他各个领域状况。而所谓基本领域或方式,就是指诗学的所有其他领域或方式所据以建立其上的领域或方式。这就是说,在思考诗学的所有其他问题之前,需要首先思考汉语形象问题;而在思考所有其他问题的过程之中,需要始终不离汉语形象问题。汉语形象问题在诗学问题中具有一种基本现实地位。所以,汉语形象美学对于诗学的真正重要性在于,它把汉语形象这一基本领域或方式引进诗学研究之中,为诗学研究奠定了语言—审美地基。更具体地看,汉语形象美学应当开辟出相互联系的两个领域:古代汉语形象研究和现代汉语形象研究。在这种比较研究中把握汉语形象的古今关联,尤其是显示当前和今后汉语形象发展的方向。
作为一个诗学研究领域或方式,汉语形象美学应当有属于自身的特殊的基本理论表述,而这种基本理论表述可以凝聚在如下具体而明确的理论命题之中:文学是汉语形象的艺术,或者换个角度说,汉语形象是文学的基本现实。这个命题的意思是,文学是汉语形象的艺术。它由流行的传统命题“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改造而成。这个传统命题来自前苏联(注:详见拙文《“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吗?》,《文学自由谈》1997年第5期。)它诚然在字面上一目了然地突出了“语言”的第一重要性,但在我们的实际文学理论体系(即具体语境中的实际用法)里,却从来没有真正被实行过。实际的情形是,语言被认为总是从属于思想或内容,首先有“思想标准”,其次才是“语言标准”。如童庆炳先生所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文学语言问题在文学理论中没有获得应有的位置。虽然也讲一点文学语言的特征,但都浅尝辄止,什么问题都没有讲深讲透。根本原因是只看到文学与政治、与生活的联系,而忽略了文学首先是一种语言,一种特殊的语言,当然,文学与政治、与生活的联系是应该讲的,但不能讲到极端的地步”(注:童庆炳:《汉语文学语言特征的独到发现》,《汉语现象问题讨论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20页。)。同时,这个来自苏联的命题只是在一般意义上谈论“语言”的重要性,而没有触及汉语对于中国汉语文学的特殊的重要性。换句话说,它似乎只满足于全人类或全世界文学的普遍性,而未能看到汉语对于汉语文学的特殊意义。这也与本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性特有的文化想象有关:人们相信现代汉语文字唯一正确出路,在于抛弃古代汉语留下的落后包袱(如象形文字、繁体字、四声等)而融入以先进的西方语言为主流的“世界文学”之中(如拼音化等),而遗忘了我们不能离开自己的母语传统这一简单道理。这样,人们虽然谈“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却很少专门考察汉语作为世界独特的语言的形象问题。这是为着世界语言的普遍性而遗忘了汉语语言的特殊性。
当我们明白汉语形象在汉语诗中具有与西方不同的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时,就需要重新认识汉语本身的特殊的诗学价值。对此,童庆炳先生说得十分坚决:“文学理论可以而且应该把文学语言,特别是汉语文学语言的特征,作为一个重要的部分纳入体系中去。在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注:童庆炳:《汉语文学语言特征的独到发现》,《汉语现象问题讨论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20页。)。我们需要走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传统泥淖,转而看到,文学是汉语形象的艺术。这一命题的焦点是汉语形象在汉语文学中的重要性。这意味着,汉语形象在汉语文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重要性具体表现在,汉语形象是文学的基本现实。基本现实,是说事物的基础的或根本的存在状况,而其他存在状况都需要以此为基础。汉语形象作为汉语诗的基本现实,意味着它是诗的整个艺术形象系统得以存在的具体场所,而如果没有这个具体场所,诗的艺术形象系统就无从存在。我们可以说,诗的“世界”并不只有汉语形象,而是丰富复杂的,如拥有人物形象、器物形象,环境形象等其他形象;但无论如何,倘若离开了汉语形象,这个“世界”就都没有了存在的依托。同时,从美学角度看,汉语形象既是构成文学的美的基本材料,又是这种美的当然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正是汉语形象的美才使得文学的其他可能的美质得以存在。诚然可以说,文学中除了汉语形象的美以外还存在其他多样的美,但是,我们却无法离开汉语形象的美而试图单独发现其他多样的美。因为,其他多样的美是始终不离汉语形象而存在的,甚至是凭借汉语形象才展现出来的。
作为文学的基本现实,汉语形象应当与一般汉语活动中的汉语面貌有所不同,而具有“艺术”性,所以说“文学是汉语形象的艺术”。“艺术”一词在这里当然不是指艺术样式,而是指汉语形象的修辞之美。文学作为汉语形象的艺术正是说文学是汉语形象的修辞之美的显示。修辞之美,是说汉语形象的“艺术”性集中表现在其修辞性上,就是:是否为着表现中国人的生存体验,使其在社会中造成强烈影响而巧妙、有效或有力地组织汉语,直到使其展现出独特的美。文学中的汉语只有当其体现出修辞上的有效、有力或富有感染性等魅力时,它才具有“艺术”性,也才是“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