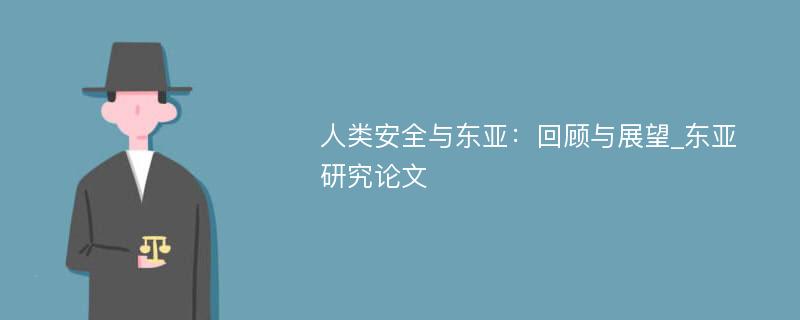
人的安全与东亚: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前言
在东亚地区最近10年进行的关于新安全观的争论中,“人的安全”可能是最具争议的 话题。它始终坚持,在回答安全是为了谁、来自哪里和通过哪些途径解决这些问题时, 个人或单个团体是起码的关注点之一。
亚洲国家对“人的安全”的反应一直是复杂、易变的。最初相当敌对,但近来民间社 会、学术界和政界的态度已经变得积极起来。传统观点认为,亚洲对一些特定的安全概 念总是持抵制的态度,因为这些安全概念在规范层面潜在地侵蚀传统的主权观,在政策 层面要求对资源进行重新分配,以应对一系列超出军事和领土威胁的非传统安全挑战。 特别是在冷战思维仍然产生影响、历史的残留仍未解决、分裂的国家依然存在、防御开 支依然庞大以及地区性机构和合作安全经验仍旧匮乏的东北亚地区,人的安全对许多人 来说就是一棵外来的、没有生命力的嫁接植物。
美国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强行介入(特别是“9·11”以后)大大加深了对人的安全的怀 疑。反恐议程成就了前所未有的国家间合作,美国和中国等其他主要国家间都产生了建 设性互动。不少人也预见了在应对朝鲜半岛核问题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大国合奏曲” 的积极前景。但是,美国对促进人的安全的国际倡议的反对,对东亚人权问题支持的减 弱,使“人的安全”的支持者们顿悟。
我在此文中关注亚洲,特别是东亚(东北亚和东南亚)(注:在学术界,对“东亚”存在 两种不同的定义。一种定义认为东亚包括中国、中国台湾、日本、韩国以及越南的部分 地区。费正清和赖肖尔称之为中华文化圈。另一种定义将东亚扩展到了东南亚国家。在 本文中,作者采纳了第二种定义,因为关于安全和地区机构建设的讨论现在仍是以广义 的东亚地区为中心的,比如东盟“10 + 3”会议等。)的政府和政策圈子是如何诠释和 应对人的安全的。我的基本观点是,尽管最初遭到反对,如今“人的安全”已经逐渐在 国家和地区争论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尽管人们更偏向于探索人类多重性的“人的 安全”的广义定义,但是针对“人的安全”的狭义定义,即在面对剧烈冲突的情况下对 个体的保护,还是发生了一些细微的转变,至少产生了严肃的辩论;尽管目前单个的国 家和地区性组织在接受人的安全的问题上仍然举棋不定,但是人的安全确实在改变国家 义务、主权和不侵犯原则的规范框架过程中扮演着催化剂的角色。
在提出观点的同时,我也注意到,人的安全在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中确实都处于一个 非常不稳定的位置。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东亚,也出现在世界其他地区。除了少数国家 (如加拿大和挪威),人的安全始终处于非主流的边缘地位。这个概念被广泛地批判为分 析上模糊,道义上冒险,不可持续和应用范围狭窄。但是在学术界,“人的安全”得到 了越来越多的支持。2003年的一项调查表明,145名分布在33所大学中的学者声称自己 在“人的安全”领域有研究或者教学兴趣。(注:这份学者的名单和相关的课程提要可 以查阅网址:http://www.humansecurity.info。)但是安德鲁·马克(Andrew Mack)对2 002年主要学术刊物中与安全有关的文章的搜索显示,以“人的安全”或是“非传统安 全”为主题的文章不到总数的5%。显然,人的安全给亚洲带来的冲击更加微弱。
二 人的安全的含义
纵览20世纪的前90年,“人的安全”这个词很少出现在人们眼前。但是自从1994年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对“人的安全”进行了确切的阐述以来,这个概念 开始在全世界的学术论文和政策报告中蔓延开来。与此同时,它还被描绘为一个新的理 论、概念、范例、分析点、世界观、政治议程、规范尺度以及政治框架等,并由此产生 了许多专著、论文、政府报告以及研讨会和教学项目。“人的安全”并非产生于理论反 思,而是来源于变化中的现实状况。直到现在,它的主要支持者还是政治家、外交官、 非政府组织活动家,而不是学术界中挑剔的学者。
关于“人的安全”的性质和含义(即“是什么”和“怎么样”)所引发的争论比比皆是 ,而有关“为什么”和“什么时候”的争论却寥寥无几。支持者总是将问题归咎于冷战 后安全环境的变化;国家内部冲突产生的越来越大的影响;国家间新型外交关系的出现 ;国际组织与民间社团的广泛参与;还有全球化程度加深所带来的信息网络和媒体能力 的加强、失败国家情况的恶化以及为民主化带来的新动力。
谈到“人的安全”的核心,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将这个问题归结为关于安全是为了何人 、来自何方以及通过何种途径实现这些问题的具体答案。根本的假设有:(1)个体(或是 一个单个的团体或社区)是安全指向的对象之一;(2)个体或团体的安全面临着多种威胁 ,来自外部的军事威胁只是多种威胁中的一种,而且很可能不是最大的威胁;(3)在个 体安全和国家、政府和政权的安全之间很可能存在着一种紧张状态。(注:此归纳来自Fen Hampson,et al.,Madness in the Multitude:Human Security and World Disord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1—37。)
基于这样的构架,通过改变切入点和提出超越传统安全战略的问题和方式,“人的安 全”向传统的国家安全概念发起了挑战。从哲理上说,人的安全提出了与道德、国际义 务、发展及国内合法性相关的根本性事宜;政治上,人的安全提出了关于主权、干涉、 地区性机构的角色以及国家和国民关系的问题。除此之外,人的安全还裂化为应对一系 列问题的方法,包括如何对“威胁”从广义上加以定义?如何按重要性对它们进行排序? 要强调国家和个人之间的互补性还是紧张状态?西塞罗认为,“安全就是没有焦虑,而 富足的生活正依赖于此。”如果西塞罗对于安全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人类到底有多少 焦虑需要缓和?通过哪些办法来缓和?这些问题的答案经常交织在一起,使得对“人的安 全”的定义、衡量和应对方法的争论进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
为了分析在东亚进行的争论,所有不同的思想基本可以被归纳为两大族系。第一个族 系强调的是从广义上来看待“人的安全”的定义和范畴。与199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 人类发展报告的最初陈述一样,这个族系的思想认为“免于恐惧的自由”与“免于匮乏 的自由”同样重要。这导致这个目录中囊括的威胁非常宽泛。
对这个广义定义的最完善的阐述出现在由日本政府赞助、绪方贞子(Sadako Ogata)和 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担任主席的人类安全委员会的报告中。具体论述如下:
“人的安全的目的是通过发展人类自由和实现人生价值来保护人类生命至关重要的核 心。人的安全意味着保障人类的基本自由——自由是生命的精髓。它意味着保护人类免 受严重的、普遍的威胁和危险情况的伤害;它意味着通过多种途径增强人类的能力和抱 负;它意味着通过创造相应的政治、社会、环境、经济、军事和文化体系,来建构人类 的生存和尊严。
生命的关键核心是人们享有的一系列基本权利和自由。但是不同的人、不同的社会对 什么是‘生命核心’,什么是‘关键’有不同的答案。因此,人的安全的任何概念都肯 定是动态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没有提出一个关于‘人的安全’包含条目的详细列表的 原因。”
报告中的主要部分论述了暴力冲突的状况、冲突后的重建、难民问题、经济安全、健 康与人的安全以及人的安全的知识及价值。报告的目的性很明确,就是要将保护、权力 、发展与管理等问题联系起来,而且它认为人的安全也必须应对暴力冲突和贫困问题。
第二族系的思想采纳了相对狭窄、但更有针对性的方法来探究人的安全的范畴和人的 安全面临的威胁,关注在暴力冲突情况下对个人和群体的保护。虽然这个族系的思想有 时候也提倡“免于恐惧的自由”,但是它的关注点是极端的脆弱性,其背景通常是一个 国家的内战。它的支持者并不否认人类正常生活面临着多种威胁,但是为了追求条理清 楚的分析和可操作的关注,他们总是选取威胁的一种具体形式加以关注,坚信要探询贫 穷、治理和暴力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必须能够从互相依赖的变量中辨别出独立的因素。 对此,安德鲁·马克是这样论述的:“在‘不安全’这个标题下,将宽泛的领域内完全 不同的威胁综合起来是一项重新归类的工作,而实际上并不带有明显的分析目的。如果 ‘不安全’这个名词能够包括从对尊严的冒犯到种族灭绝等所有形式的危害,那它的描 述能力就是极端低下的……如果要出于分析的目的去探究贫困和暴力的关系,那么这两 个对象应该分开对待。”
在具体实践上,这个族系的追随者认为当前已经存在着一整套探索发展问题的体系。 目前需要的是对于具体某一种威胁加以关注,并建立相应的政治意愿和实用工具来解读 这些威胁。如果将关注点限定在一个特定的领域内,那么人的安全研究将取得最大的突 破。
三 亚洲的反应和理论的创立
尽管可以说人的安全问题在亚洲很有渊源,但是最初的发展情况更像是种子被撒在了 贫瘠的土地上。如阿米塔夫·阿齐亚所说,“人类安全”是“一个独特的概念,它完全 超越了亚洲各国政府之前为‘重新定义’和拓宽它们对主权的传统认识所付出的努力。 传统上,亚洲一直将主权认定为保护主权和领土不受军事威胁。”(注:Amitav Acharya,“Human Security:East versus West,”International Journal,Summer 200 1,p.443.)很少有亚洲的政府和学者对人的安全流露出兴趣。一些评论家也很快推断人 的安全的基本假设和行动议程将无法在亚洲大陆寻求到支持,因为在亚洲,各国政府都 认为国家是最好的(或者说是惟一)安全提供者,而且它们都坚定地维护绝对主权和不干 涉内政的原则。
伴随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亚洲关于“人的安全”的讨论开始发生变化。尽 管这个议题还没有像在欧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那样引发激烈的辩论,但是至少“人的安 全”的广义定义开始得到亚洲学术领袖的关注。(注:William Tow,Ramesh Thakur and In-Taek Hyum,eds.,Asia's Emerging Regional Order:Reconciling Traditional and Human Security,Tokyo: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2000.)
回顾“人的安全”进入亚洲的安全词典10年以来的情况,它通过一些微妙的途径不断 进行着演变。尽管存在多种不同的定义,这个词已经开始缓慢地进入地区性组织的语言 范围。东亚研究小组和东盟“10 + 3”中的高级政府官员从2001年开始使用这个词来处 理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包括环境恶化、非法移民、盗版以及跨国犯罪等。在经历了 长时间的辩论之后,“人的安全”这个词在2002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上第一次被 采用。2003年10月21日,《领导人宣言》声明APEC将“不仅致力于推动各成员国经济繁 荣,也致力于确保人民安全”。APEC促进人的安全的途径主要是打击恐怖组织、消除大 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应对其他直接安全威胁,包括传染病、保护飞机乘客和能源安 全等。“人的安全”的运用将其最广泛的定义与美国提倡的反恐议程融合在一起。尽管 这样可能带来概念上的模糊,但是由此产生的政治上的强制力是毫无疑问的。
最为积极地推动“人的安全”概念发展的两个国家是日本和泰国。日本首相和外交部 长级别的官员使用这个词的频率比其他任何亚洲国家的政府官员都高,而且已经投入了 相当的财力和人力来推动“人的安全”广义定义的发展。绪方贞子被任命为日本国际合 作厅厅长和投资10亿美元建立人类安全发展基金,已经充分体现了日本政府在这个问题 上的态度。泰国也已经建立了人类安全部,应对国内的社会安全事务。
在地区层面上,一些“第二轨道”参与者,包括东盟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和亚太安 全合作理事会已经使用了狭义和广义上对“人的安全”的表述。东亚展望小组在其2000 年最终报告的多个章节中都使用了这个词。在最近5年中,已经有大约30个“第二轨道 ”会议将人的安全作为会议的首要关注点或是主要议题。(注:参见http://www.jcie.or.jp。)亚洲一些新兴民主国家也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特别是韩国和菲律宾。但是 人的安全与政权体制关系的发展还存在缺陷。一些对“人的安全”最强烈的批评出自印 度官员之口。在拥有力量强大的民间社会和运作正常的民主机制的台湾,“人的安全” 概念也仅仅是刚刚开始得到关注。(注:Lee Chyungly,“Human Security:Implications for Taiwan's International Roles,”http://www.humansecurity.info,July 1,2003.)
对于“人的安全”认识最微妙的演变可能发生在中国。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个 词还不被中国的学术界所认知,也没有被政府官员在正式会议或是媒体中使用。目前这 种情况正通过两个主要方面在发生变化:第一,一些国内的人的安全,即来自国家内部 的威胁,已经开始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具体内容主要包括环境问题、贫困问题和社 会安全;第二,人的安全与中国的新安全观的一些关键要素是相互吻合的,特别是对通过联合行动来处理跨国事务的重视。(注:Chu Shulong,China,Asia and Issues of Sovereignty and Intervention,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ovember 2000.)相比“人的安全”,中国的政府官员更偏向于使用“非传统安全”一 词。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共同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 言》,表示共同应对非法毒品和人口走私、拐卖妇女儿童、盗版、恐怖主义、军火走私 、洗钱、国际经济犯罪和网络犯罪等。(注:参见《关于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中 方立场文件》,2002年5月29日,http://www.fmprc.gov.cn。)
说到人的安全敏感的最终目标,即与主权和干涉概念直接联系的,在暴力情况下对个 体的保护,中国在最近7年中的反应比外界的描述要灵活和老练。中国仍然有不少人坚 持对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的严格解释,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联合国宪章》,偏 向人道主义救援(而不是人道主义干涉),提倡维和行动中的严格中立以及洞察干涉行动 是否具有别有用心的目的。他们不断阐述在中国根深蒂固的观点,包括历史上的耻辱, 担心外国势力对台湾、西藏和新疆的潜在干涉以及总是关注国家而不是个体,从而使人 身安全(human safety)与现在的人的安全相分离的政治哲学。(注:Mao Yuxi,“Human Intervention's Dubious,”China Daily,February 25,2002.)当然,不应将这些观点 看做是一成不变的。楚树龙指出,中国的领导层将继续维护基本的国家主权,但是同时 ,来自国际上的压力将使他们在接受新的安全观时变得更加灵活变通,包括人的安全。 “中国认识到在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时代,改变对国家安全的传统立场给该国及其人民带 来的利是大于弊的。”(注:Chu Shulong,China and Human Security,http://www.pcaps.iar.ubc.ca,p.25.)
寇艾伦(Allen Carlson)在最近关于中国的报告中,对中国在主权和干涉事务上的立场 和实践的历史演变进行了很有见地的评估。他将中国在过去的10年中发生的立场变化归 结为政策制定圈内多种理解方法和叙述的综合作用。尽管持有深深的疑虑,但是对国家 利益的理性计算、对国际名声和国家形象的顾忌以及对新规范原则的接受,导致了更加 纷繁的争论。现在许多中国的精英已经开始接受通过多边干涉来解决严重的人道主义危 机的行为。(注:Allen Carlson,“Protecting Sovereignty,Accepting Intervention :The Dilemma of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1990s,”New York: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China Policy Series,No.18,September 2002,p.3.)追溯中国对近期出于保护目的而进行的多边干涉的反应和中国在 一些维和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分析了中国在科索沃问题上的反对立场和在东帝汶问 题上的支持立场,认为中国国内的争论并非都集中于原则问题,更多的是关于西方所说 的人道主义危机、目标选择和执行细则的自由度问题。
从宏观上看,亚洲对人的安全的反应具有五个普遍的特点:
第一,在安全思想的层面,人的安全和地方情况结合得比较好。如阿米塔夫·阿齐亚 所主张的,人的安全与大多数综合安全的阐述是能够共存的;它与许多亚洲国家政府需 求第一的政策主张是相互呼应的;它灵活地将个体和团体都包括在安全所指向的对象内 ;它与发展问题相联系,而且很容易适应人类尊严的地方传统。(注:Amitav Acharya,“Human Security,”pp.444—451.)
第二,只要是人们所渴望的,广义的概念应该更容易被接受。在亚洲,“在理解和发 展‘人的安全’上,免于匮乏的自由超过了免于恐惧的自由。”一些人抵制免于恐惧的 自由,因为它与人权和人道主义干涉的主张联系密切,因此便用“非传统安全”的说法 来取代“人的安全”。非传统安全指一系列超出常规的军事威胁的新威胁,包括国际问 题(比如气候变化、环境恶化、贩卖毒品和人口、跨国犯罪、传染病)和全球化引发的对 一个国家内部的挑战,比如贫困和不平等问题。这种说法在表达安全的对象是国家还是 个人的问题上最为模棱两可,其支持者通常强调国家和以国家为中心的途径是应对这些 威胁的最好方法。
第三,对人的安全的支持仍然有限。支持者们起初多为从事多边外交的政府官员和政 治领袖,然后扩展到学术界,直到最近才发展到民间社团组织中。东南亚地区的非政府 组织和政治活动家开始在类似东盟人民大会(ASEAN People's Assembly)和其他“第三 轨道”的场合使用“人的安全”。皮埃尔·利则(Pierre Lizee)认为,“人的安全”的 出现如同东南亚民间社团组织的战斗口号,因为人的安全为它们反对几十年来以国家为 中心的经济、政治发展模式提供了充足的理由。(注:Pierre Lizee,“Human Security in Vietnam,Laos and Cambodia,”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24,No.3,December 2002.)通过切断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联系,人的安全直接提出:东南亚社会的 团体和个人希望依据人的安全或社会福利来明确他们的愿望和要求,希望更多地参照国 际标准,而不是根据国家制定的规则。这种对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视非常符合“新型外交 ”的概念。这一概念将国际组织、相关国家政府、非政府组织网络以及政策专家联合起 来共同推行一些倡议,比如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和建立国际刑事法庭。
第四,尽管1997年金融危机吸引了亚洲对“人的安全”广义定义的关注,但是当前的 反恐议程使关于“人的安全”的讨论更为复杂。它使新的注意力集中到具有地区和全球 影响力的暴力和国内冲突的根本原因上。与此同时,打击恐怖主义的战略主要是为了巩 固国家和政权,并主要通过传统的强制工具(军事、警察、情报机构)来达到目的。
第五,尽管有证据表明关于主权、不干涉和机构建设的地区规范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 ,但是大多数亚洲国家一直不情愿将注意力完全集中于国内战争的动态。像预防性外交 这样的主张很难被接受。亚洲各国政府认可的是国内的不稳定和缺陷需要相关国家特别 的关注。许多分析家认为,即使是一个不好的政府,也比没有政府或者通过外部干涉而 建立的政府要好。
四 保护的责任
为了理解规范框架是如何及为什么会因为主权和军事干涉这样尖锐、复杂的问题而发 生变化,对近年来最有影响的研究项目所取得的反响进行相应的研究是很有裨益的。这 个项目就是干预和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的报告《保护的责任》。(注:《保护的责任》 全文可以参见以下网址:http://www.dfait-maeci.gc.ca/iciss-ciise/report-en.asp 。)
在关于向索马里、塞拉利昂、卢旺达、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及东帝汶进行人道主义 干涉的争论进行得热火朝天的背景下,干预和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的建立响应了联合国 秘书长科菲·安南的号召,就采取强制行动来保护危险中的人民的原则和进程在国际社 会达成一个共识。该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9月,由加雷思·埃文斯(Gareth Evans)和穆 罕默德·萨努恩(Mohamed Sahnoun)共同担任主席,得到来自加拿大政府和一些基金会 的资助。委员会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磋商,并在2001年10月提交了它的最终报告。
该报告明显地避免使用诸如“人道主义干涉”和“干涉的权力”一类的词汇,而是通 过将主权和干涉事宜框定在保护的责任范围内,关注人们对援助的需求。报告确定了一 系列核心原则,直接关系到国家主权、《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明确的义务以及国家、 地区性组织和联合国安理会的行为。报告拓展了保护的责任,使之囊括了预防的责任、 反抗的责任以及对特定国家提出人类保护要求时的援助和重建责任。报告还对正当理由 的起点标准以及预防性原则、正确的授权、行动原则进行了准确的定义。
报告在“保护的责任”和“人的安全”的广义概念之间建立起直接的联系,并把“人 的安全”定义为“人民的安全——他们的身体安全、经济和社会福利、对他们的人类尊 严和价值的尊重,保护他们的人权;基本自由人民的安全,包括他们的人身安全、他们 的经济和社会的安宁、对其尊严和人生价值的尊重以及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保障”。报 告认为人的安全是不可分割的:“主权与干预问题不仅影响各国权利或特权,而且从根 本上深深影响和牵涉到个人。在这一辩论中将此关键问题表述为‘保护的责任’的好处 之一是,它将注意力集中在最应关注之处,即集中在那些谋求保护或援助的人的需求上 。以此为重点,安全问题辩论所强调的内容,从领土安全和通过军备来取得安全,转到 通过人类发展和获得食物、就业与环境安全来取得安全。‘人的安全’的基本成分—— 面对生命、健康、生活、个人安全和人类尊严的威胁的人民的安全——有可能因外部侵 略或因一个国家内部的各种因素而处在危险之中。许多政府保护本国公民免受不确定的 外部军事袭击的开支,多于保护人民不受常见健康隐患及其他日常‘人的安全’现实威 胁的花费。拘泥于范围仍显狭窄的‘国家安全’概念可能是一个原因。”
如果要列举国家应该保护其公民免受威胁的具体不安全因素,包括饥饿、疾病、犯罪 、失业、社会冲突、环境公害、种族清洗、种族灭绝以及公民被他们自己的安全部队杀 戮等。报告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从关于“威胁”的广义概念和不可分割性转移到了对于 两种具体威胁的分析:大规模的死亡和种族清洗。
干预和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的10位委员中有2位来自亚洲,他们是菲德尔·拉莫斯(Fidel Ramos)和拉梅什·撒克(Ramesh Thakur)。在起草报告的过程中,委员会的10次 研讨会有2次在亚洲举行(新德里和北京),因此报告中也包括了亚洲的态度。
尽管目前联合国安理会还没有将此报告的内容认定为指导方针,联合国大会也没有通 过表示支持的宣言式决议,但是一些成员国已经表明支持报告的原则和建议。缅甸、朝 鲜和印度等国家则已经开始要求七十七国集团拒绝这个报告,认为它为发达国家干涉发 展中国家的内部事务提供了借口。地区性政府间组织,包括东盟、东盟 + 3、亚太经合 组织、东盟地区论坛和欧亚会议都没有对报告发表自己的意见,这反映了在这些组织内 部所进行的辩论和它们对不干涉原则的坚持。
虽然政府机构没有做好接受报告的准备,但是报告引发的问题是如此繁杂以至于它们 自然而然地成为学术研究和“第二轨道”政策讨论的主题。《保护的责任》包含了亚太 圆桌会议和东盟人民大会在内的一些会议的主要议题,以它为主要议题的研讨会在亚洲 各国广泛举行。这些会议都进行了热烈而富有建设性的讨论,并且基本上支持报告的动 议。
20世纪70年代,在柬埔寨的杀戮和在缅甸、菲律宾及印度尼西亚频繁发生的武装冲突 表明,国内冲突依然是地区现状的一部分,尽管这些冲突的规模与25年前相比已经小了 很多。(注:根据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和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提供的数据,从1946年到1 980年,东亚地区发生了3次大规模的战争(中国的内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大约有 4500万人在战场上阵亡,而战争带来的其他死亡人数几乎是阵亡人数的2.5倍。但是自 从1980年以来,整个东亚每年因为战争而死亡的人数基本都稳定在5000人以下。)通过 比较亚洲国家对70年代柬埔寨的种族灭绝和1999年东帝汶暴力冲突的不同反应,可以清 楚地看出亚洲在干涉问题上的态度变化。因为亚洲国家应对现代化和全球化挑战的办法 是经济自由化、社会开放以及加深彼此之间的联系,所以各国与邻国互相作用的事务也 比以往更加繁多、公开和复杂。
对于报告的批评观点也为数不少。有的观点认为,报告是干涉学说的一种新形式,它 曲解并侵蚀主权概念;有的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军事干涉都不是最佳选择;有的认为报 告在行动机制上过于依赖安理会;有的认为正当理由起点标准太过狭窄,要求过于苛刻 ,以至无法应对像发生在缅甸那样的杀戮规模不大但却非常持久的行动;还有一些意见 认为,归根结底,《保护的责任》依赖于强大的行动意愿,而这种意愿只有在没有指导 方针和道德准则影响的情况下,与国家的具体利益相吻合时才会存在,这就无法制止关 于人道主义义务的辩论最终被归结为强权政治的行为。
在仔细研究了正当理由起点标准和预防性原则之后,大部分评论家都认为,《保护的 责任》是促进国家发展的,而不是对国家造成威胁。他们认为《保护的责任》确定的框 架其实减小了军事干涉的可能性,并为发展中国家抵抗单边干涉提供了保障。(注:Ramesh Thakur,“Intervention Could Bring Safeguards in Asia,”The Daily Yomiuri,January3,2003.)当然,即便报告的支持者也意识到,美国入侵伊拉克阻碍了 为人道主义干涉创造一个合适的环境所进行的努力。
从总体上来说,在东亚,关于以保护为目的的各种干涉的讨论已经开始变得越来越复 杂、越来越实际。几乎每个亚洲国家都经历了一个由基于原则和哲理的观点到针对具体 情况和处理办法的观点的转变。在下一个事件出现之前(至少在短期内),亚洲各国领导 人不太可能领导这场争论或是某次干涉行动。如果根据报告中确定的标准,很难想像外 部干涉会出现在东北亚地区。但是在东南亚和世界其他地区,一些国家很可能被卷入预 防和重建的行动,来支持外部力量对冲突的多边干涉,而这种干涉是符合干预和国家主 权国际委员会确定的限度的。用阿齐亚的话说,“出于对主权的考虑,要动用整个地区 进行军事干涉是很难操作的。对于亚洲的地区性机构来说,关键的任务应该是参与冲突 预防或承担保护的责任,而让联合国来承担军事保护的任务。”(注:Amitav Acharya,“Redefining the Dilemmas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56,No.3,2002,p.379.)至少现在可以想像, 在不久的将来,亚洲国家可能加入一个地区性联盟,即使这个联盟的领袖来自亚洲以外 的地区,甚至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授权。
五 结论:处于保守年代和困难环境中的人的安全
东亚地区在后殖民主义时代的倾向一直是崇拜强大的国家、抵制外部干涉、坚持19世 纪保守的主权观。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美国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所采取的以国家为中 心的战略。这两种力量可能会导致一个更为保守的年代的出现,由此可能为打击恐怖主 义甚至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创造更多的国际合作基础,但是对人权或人的安全的支持者来 说,这绝对是一段困难的时期。
然而,这种力量与地区性事务中的其他趋势是相对立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人可 能退回到极端保守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国家主权原则。但是这种情况出现的 可能性并不大。另一个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对于美国强权的恐惧和潜在的行动议程可能 会激发各方面的努力来建立一个基于规则的新框架,以此支持多边联合行动,并成为抑 制单边干涉的力量。支持人的安全的地区性多边主义的建立很可能来自忧虑和需求,而 不是愿望。
对干涉、非传统安全和跨国界事务等相关事宜的重新定义似乎为地区性讨论掀开了新 的篇章。这些对话的内容不仅囊括了人类安全委员会提出的有关人身福利的人的安全, 也包括干预和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提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保护的责任”。“保护的责 任”这样的主张不仅不会给人的安全带来负面影响,相反,通过提出一些过去被认为过 于敏感的话题和促进民间社会行为体的活动,保护的责任为人的安全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下一阶段,东亚国家的领导人可能不会满足于被动地参与关于“人的安全”的辩论 ,他们可能要求更加深入地参与对“人的安全”概念的塑造。我们应该注意到,预防冲 突、干涉和冲突后重建的所有应对方法都基于出自西方国家经验的管理、民主和暴力控 制的理念。当这些理念被运用于东亚,比如联合国临时权力机构管理时期的柬埔寨或者 驻东帝汶的国际部队,效果并不理想。因此,东亚的问题应该更多地关注过去的经验、 教训以及当前的情况。在本地区之外,领导多边行动的风险和收益是什么?如果要将亚 洲的现实和重点考虑在内,应该对《保护的责任》的框架进行怎样的调整?对发展援助 项目要如何加以调整,才能达到人的安全的两大目标,即可持续发展和平息冲突?反对 恐怖主义如何适应人的安全?军事反应和发展事宜如何达到最佳的结合点?当然,关键的 问题是,如何调和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之间的关系。(注:P.H.Liotta,“Boomerang Effect:The Convergence of National and Human Security,”Security Dialogue,Vol.33,No.4,December 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