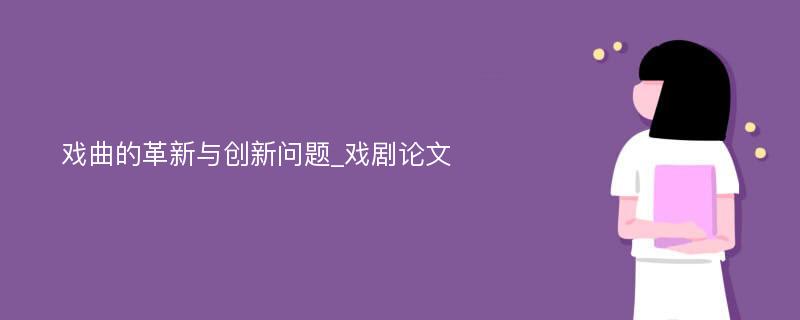
戏曲整旧和创新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戏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导语:张庚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戏曲理论家,从1953年受命组建中国戏曲研究院时起,他的戏剧研究生涯就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他近距离地目睹了20世纪从50年代初极左思潮对戏曲界造成的冲击,在满目疮痍中,数年如一日地推动保护中国戏剧传统的开拓性的理论建设,为戏曲的传承与健康发展,做出了无可比拟的巨大贡献。他在全国各地做了大量学术报告,始终以理性的态度,呼吁以客观与公正的、历史性的态度对待传统戏曲以及传统剧目,尖锐地指出并批评了当时戏曲界流行的束缚戏曲发展的种种“清规戒律”。这些报告,当时就已经有一部分整理发表,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目前公开发表的文献,包括当时印成单行本和后来收录在《张庚文录》第二卷的文章,只是张庚先生所做的大量报告中很少的部分。本文是我去年偶然从上海档案馆找到的一份记录稿,时隔五十多年,读来仍然令人深受启发。感谢张庚先生的亲属张小果的授权,让这篇重要文献初次面世。
(傅谨)
同志们,关于戏曲改革的问题,我对这问题也懂得不多。但我也是剧协的会员,上海剧协叫我讲,所以不能推辞,就来讲一下。今天的内容是比较空洞的,很抱歉。
我讲的题目是整旧和创新问题。分两个部分:一、关于政策方面的一些问题;二、整旧和创新不是对立的也不是矛盾的。
(一)关于政策方面的一些问题
1951年5月政务院发出了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其中有几条,指导着这几年的剧目演出。指示中是这样提出的:“戏曲应以发扬人民新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人民在革命斗争与生产劳动中的英雄主义为首要任务。凡宣传反抗侵略、反抗压迫、爱祖国、爱自由、爱劳动,表扬人民正义及其善良性格的戏曲应予以鼓励和推广,反之,凡鼓吹封建奴隶道德,鼓吹野蛮恐怖或猥亵淫毒行为,丑化与侮辱劳动人民的戏曲应加以反对。”这几年来的戏曲工作都是根据这一条来做的。剧目开放以后,有人以为戏改指示不适用了,或是错了。是否就错了呢?或若另有标准呢?
应当回顾一下这指示发出前后的情况是怎样的。我先讲一讲新中国成立前戏曲界的情况,对于上海的情况我了解较少。北京及其他各地日本统治了八年之久,国民党又来了三年,很多有很好传统的剧团和有修养的艺人都流离失散了。存在的剧团是什么情况呢?又是满台的《纺棉花》和满台的《大劈棺》,谈不到民族遗产。四川听说有的名演员在台上唱黄色歌曲。舞台上出现的几乎是将世界上所能收集的糟粕都集中起来了。当时是那种风气。一解放,对于舞台上这种情况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整顿舞台现象,禁演一些剧目等。这种做法虽然较为粗枝大叶,当时如不这样,又能采取什么办法呢?很难讲。从新中国成立到1951年发出指示,这中间是发生很多粗暴现象的。如把包公从台上抓下来打屁股等,还说我打的是包公不是打演员。这个指示是在纠正粗暴,保护民族遗产的情况下发出的,自指示发出后才产生出《梁祝》、《白蛇》、《秦香莲》等优秀剧目(是根据传统剧目整理的)。因此,这指示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
有了指示后,是不是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呢?不是这样的。譬如说在戏曲演出中产生许多清规戒律。清规戒律的产生是有其社会原因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接连着各种运动(如三反、五反、镇反、土地改革等),那时和敌人的斗争很紧张,假如那个时候要像现在剧目花样这么丰富多彩,观众看来是也不能满意的。那时观众要看现代戏,上海的《罗汉钱》常客满,北京的《刘巧儿》和《小女婿》也很受欢迎,而当时如演《杨乃武与小白菜》等戏只(怕)是要受观众批评的,认为这戏没带革命的味儿。后来《梁祝》、《白蛇》出来了,也必须作新的解释,找出里面的反抗性和人民性,指出这里面体现了民族的革命传统。不作出这样的解释观众是不会接受的。同时这些剧目也不是原封不动的传统剧目,而是经过用新观点修改的,所以它们才能成立。当时有一种风气,任何东西如果不带有革命的意义(当然是比较狭隘的)就不行。后来,这种风气在大城市慢慢扭转了一些,但穷乡僻壤就不同。如陕西有个别的县将旧有的剧目全部禁演,甚至认为靠袍戏都是不好的。当时这种社会风气,是人民的情绪造成的:首先是革命情绪,同时它又是一种较幼稚的革命情绪。这很难怪是哪一个人的错误,当然是有一些人在言论和文字中使它成理论化了,但也不能把过错集中在这少数几个人身上。即使是艺人中间也这样,有的艺人左得很厉害,只肯演时装戏不肯演古装戏,我们也不能怪他们。
有人想找提出清规戒律的人,是找不出的。这个责任不能推在某一个人身上,我们每人都有份,可能在座的就都有些关系,而且群众也都有这种情绪。1951年后,敌我斗争的情况有些改变,群众的情绪也逐渐稳定,许多观众已要看各种各样的戏了,所以剧场上座率慢慢减少。当时我们发现这问题不够敏锐,即未认识到人民群众的情绪思想的变化,首先领导上应承认这一条,戏剧工作者也应承认这一条。我们的脑子是不够敏捷的。有的人感到了也说不出道理来,应当说这是政治上不够敏感的表现。而同时清规戒律一条条都理论化和更细致了,害处也就一天天更清楚了。如封建思想、没有阶级观点、侮辱劳动人民等,可以举好多条例子出来。1951年后没有禁戏,但花样比禁戏更复杂,所谓一言以“毙”之、考虑考虑等等,虽不禁戏,但戏还是演不出来。另有一点,当时如果在创作新剧目上有很大成绩的话,是否情况会好些呢?我看可能会好些的。但当时表现现代生活的剧目好的不多。在创新方面也有许多清规戒律,如:“工人阶级是这样的吗?”“今天还有这种现象吗?”“看不见党的领导!”等等,这仅是举例,清规戒律还要更多一些。写东西是在这种情况下写的。有了清规戒律,作品像解放初期《罗汉钱》、《刘巧儿》等为观众爱护的就渐渐少了。另外一个原因,新的剧作者参加剧目工作的一天天多起来,他们不太熟悉戏剧的创作方法,也是新作品精彩的较少的原因之一。这是当时的情况。
有人怀疑“剧目解放”后还有没有标准?有的人甚至将标准否定了,不感兴趣了,这种看法是否很全面?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我感到不能没有标准。毛主席讲我们封建时代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其中有精华有糟粕,必须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这句话人人皆知,但是何谓糟粕,何为精华,往往分辨不出,要么尽是精华,要么尽是糟粕,问题就在于没有掌握住标准。对标准认识不正确,结果就把中央这标准庸俗化了,曲解了。如:凡是鬼就是迷信,凡是丑的戏都是侮辱劳动人民,这不是标准错而是解释错。现在同志们在报上争论戏曲演出究竟是否搞乱了?可见还是需要标准。不过对这标准我们要作新的认识。
去年全国剧目工作会议,对这个标准有所补充。那些能给人以美感的、有益无害的剧目应当加以肯定。当时给人民的感觉有两头,好的与不好的,没有中间的。没有考虑到大量的由劳动人民创造的剧目中,有一些是没有明显的人民性的,如《小放牛》、《刘海砍樵》之类。其实这些剧目在第一次全国戏曲会演时已拿出来了。
我们必须坚持这个标准,没有标准是不行的。例如《十五贯》,这是一个好戏,但是也有人说它是宣传迷信,侮辱劳动人民,有些地区艺人自动停演的第一个剧目就是《十五贯》。其实标准的问题是不难掌握的。如鬼的问题在上海争论得很热闹,我觉得鬼的问题并非这么难分辨,最主要的一点是看我们拿鬼作为噱头呢,还是鬼是戏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是为了制造恐怖,那是要不得的。上海的鬼戏我没有看过,很难具体讲。有人听说鬼戏开放了、可演了,就将过去的鬼戏有吓人的效果都搬出来,这样即使鬼是反抗的,有人民性,可是由于搞得舌头吐出、血盆大口,形象可怕,人民性也就会没有了。象敫桂英、李慧娘等这些人,生前是善良的好人,从未做过坏事,到了阴间都弄得那么可怕,这是不对的,是把形象给歪曲了。其次,舞台上的丑恶形象,如弄得满脸鼻涕、眼泪、眼屎等,这就不好,连小学生都懂,也不难分辨。如拿这种作号召观众的手段就是不好的。还有用黄色的表演来号召观众也是不对的,但像《西厢记》描写爱情却是好的。爱情和色情在理论上分辨是不容易,但在舞台上是并不难分辨的,写剧本的人心里有数。有少数人为了要多卖些票,想不要标准,在戏里加上黄色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今天我们的戏剧艺术家应有社会主义的自觉,要搞好和提高戏剧艺术,如果不靠艺术家的自觉是不行的。我觉得现在艺术家的社会主义自觉是很高的,在许多地方看戏都有这样感觉,在上海看到的一些戏觉得都是负责的。建设社会主义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如果我们对人民负责,那事情就很好办了。有时有些人或许标准拿不稳,但艺术家却很清楚。去年北京开演员讲习班时,讨论到有些戏目,艺人说:这样的剧目我不演,要演你演好了。这是社会主义高度的责任感的表现。
我几年没有到上海,这次来是为了看通话和滑稽会演。看了一些戏,如通俗话剧和滑稽戏都感到很满意。如滑稽《结发夫妻》,写得很好有感情,艺术水平很高。《板板六十四》写人物性格也好,通话的演技也很好。沪剧《杨乃武与小白菜》也很好。的确,几年来戏曲上的进步是全国性的进步。中央讲这几年来成绩是大的,我感到很正确。外国人对我国戏剧评论可作参考,卓别林从瑞士乘飞机到巴黎看我国的京剧演出,称赞我国现在的戏真了不起,说他以前讨厌中国戏,现在才知中国有很多的民族遗产,是明珠发了光。这说明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是将好东西加以发扬了。
还应当继续清除清规戒律。观众对清规戒律表示抗议的方式,是不来看戏了。但另一方面也不能一味地去迎合观众,去搞低级趣味,这样观众就会看不起我们,到那时就会很悲惨了。所以我们既不能脱离群众也不能迎合群众。上海戏剧运动已五十年了,这类教训很多,好多轰轰烈烈红极一时的剧团到后来烟消云散,就是因这原因。我们要在观众现有水平上带他们前进,也即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我们今天有两种情况,一叫脱离观众,死人不管,这样的剧目有的是;另一种是为了满足观众什么都干。如不及时认识到这个问题,将来很可怕。我们戏剧工作者应将这两种情况作为很惨痛的教训。
另外,我感到现在非常需要公正的实事求是的批评。现在的批评是不能完全令人满意的,不是捧杀就是骂杀,不能从为了戏剧的繁荣和提高出发。今天全国的批评都不够活跃,上海应起带头作用。上海是有革命的艺术批评的传统的。过去上海艺术事业有成绩,批评家起了很大的作用,譬如有人看了批评才去看戏。我觉得认为批评妨碍百家争鸣,这是误解了百家争鸣。今天我们不赞成用行政命令来干涉戏剧,但是应通过批评推动戏剧艺术。任何事情都有真理,求得真理我们才能提高,这是很重要的。我认为剧协应鼓励批评家多写文章。
(二)整旧和创新的关系
1.现在做艺术工作和做文化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去年文化部召开了一次全国省、市文化局局长会议,提出口号要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目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自己的文化艺术,每个时代的生活不同,观众的要求,口味也不同。譬如拿整理传统来讲,像演《梁祝》,过去让观众哭一哭就完了,现在要讲反抗、讲人民性,不讲反抗、人民性,就有人要反对了,至少一部分人反对。梅兰芳先生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一书中有一段话,说戏曲的观众每一时代不同,要求也不同,因此要按照他们需要来给他们演出。作为一个演员,必须了解观众的要求和满足他们。我们改革戏剧,不是坐在屋子里改,而是到舞台上改。对观众究应如何,的确是演员一辈子研究不完的大学问。了解观众就能成功,要不然,是要失败的。在表面上,观众到剧场来是为了消遣,如果我们仅仅抓住这一点是不行的。每一个人生活在世上,至少总有一部分问题要求解答,要求知道,想懂得用何种态度去处理,如舞台能回答这些问题,才能使观众乐意来。他们要求从戏里看到生活中各样的人和各样的事。有的人在看报、听报告中解决这些,但也有人要求戏来解决。如果我们不能给予满足,他们就会对戏剧没有兴趣。如滑稽戏《板板六十四》、《结发夫妻》使观众得到了收获,他们就爱看,当然对我们有教育意义的不只这些现代剧,如《十五贯》是表现古代的生活的,也是有教育意义的。有人说,现在观众对表演现代生活的戏不感兴趣,我以为不能下这结论。反映现代人的生活,是我们这一辈的艺术家们对观众不可推卸的责任。我看了这次通俗话剧会演后有很多的感想。我佩服前一辈艺术家们,他们在比我们艰苦得多的时代中反映了当前的情况,保留下一些剧目,使我们看到那时的情形。没有他们的努力,那清末民初这一个时期不是成了空白吗?这些剧目很可贵,对我们很有意义,对比我们年轻的人就更有意义了。所以我感到我们必须尽自己的责任,即创造反映我们这时代的艺术。这不仅对我们有用,而且可遗留给我们的下一代,了解我们现时的生活和情况。当然整理旧剧目也是必要的,如不改编整理就不会有今天的《十五贯》。我们在创造社会主义的新戏剧时,一方面要整理传统剧目,一方面要创造新剧目。如两者缺一,就好像一辆车子缺了一个轮子。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2.必须继承传统。前辈的思想家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黑格尔是唯心论者,但他是马克思的老师,他有些话是说得很好的。他说什么叫传统:传统如一条河,河总是往前流的,在流的过程中,有许多小河汇合入这条河,而这条河仍是一条,不是两条,也就是传统必须不断向前,在流的中间不断加进新的东西。斯大林也说过,在历史上的事情,不到绝对必要时是不会有重大改革的。反过来就是到了非常必要时,非改不行。他们的话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可看出应怎样继承遗产,推陈出新。
再拿通话为例,中国过去没有话剧(报上争论有人说有的),是从日本介绍来的。要反映那时的生活没有别的办法,就用话剧形式。但是当时老一辈艺术家不是教条主义的死搬,他们采用了许多戏曲的东西。如《张文祥刺马》一剧杀窦一虎后拿出人头,这是由京戏而来。因为不是从教条出发,观众感到不生疏,很习惯,很快就能生根。而且在采取戏曲的东西时,也不是原封不动的。戏曲演员分行是生、旦、净、末、丑,通话演员不分行,而是角色分行,如言论老生,风流老生,激烈老生等等。今日演正派,明日可演反派,这与戏曲不一样。通话是采用了戏曲一部分东西,又具有自己的特点。总之,外国来的剧种,要存在生根,必须与中国传统接起来。但我们在继承传统,发扬传统中是有些思想问题的。如过去有这种思想,先批判后继承,这对毛主席“批判的接受”的理解是错的。我在学校中讲课,有些青年人问,为什么要云手或卧鱼,难道表现现代人用得到卧鱼吗?如不解释清楚,他不学。这种情况很阻碍我们学习。批判的学习是针对那样的思想,即一切都是好的。要知道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我以为应当把基本的东西都学会,将来才可以随时应用。有的人在学习时很害怕,似乎传统中有传染病的细菌似的,用这样方法来对待遗产,是妨碍了我们前进的。
有些青年同志,没有看过传统的东西,造成了错觉,认为我们这剧种没有传统,只能学习所看到的。这不能怪他们,只能怪我们。发掘老剧目时很多年轻演员和编剧等说:“有这么多好东西我没有见过!”前几天我看沪剧会演,感到很好,语汇也很丰富。我不大懂上海话,这次看沪剧,感到语汇特别丰富,如在创作新剧目时能运用上去,那新的剧目就有光彩了。因此我感到在整旧中剧作家应参加进去,不应在旁边看,必须动手做,参加整旧工作。这样在无形中受到了影响,自然而然接受,将来想不用进去都不行。不继承传统,就不能创新,这是第二点。
3.在现在具体情况下,新文艺工作者和艺人要互相学习,互相团结,只有这样才能搞好工作。整旧工作和创新不可绝对的分开来。在整理旧剧目中,新文艺工作者应去补课。现在有些新剧目,语言赶不上旧剧目,干巴巴的,特别是没有动作,有时内心要爆发了,但却表演不出来,老是皱皱眉头。富于动作性是我国戏曲最大的优点。外国人也以为我们戏剧容易懂的原因是动作多。但现在却反过来都成了内心表情,话特别多。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应好好向传统学习。例如在座诸位都知道京剧《翠屏山》,描写杨雄与他老婆的关系,可以从洗脸的动作上表达出来,没有话,而我们看戏的就懂得他们的夫妻关系。《三岔口》是在很亮的灯光下在舞台上表演,但观众知道是在黑暗中摸索。另一方面,传统剧目绝大多数是需要经过整理的,需要新文艺工作者帮忙。以后戏剧界要分工越来越明确,不能再以演员、导演代编剧。剧作家这一行当应更加扩大发展。没有剧作家参加,《十五贯》不会到这地步,当然演员也是有功绩的。《十五贯》之所以好,是经过整理,将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这个主题突出了。所以需要剧作家共同参加发掘旧剧目这个工作。
看了沪剧团《杨乃武与小白菜》感到不错,但有的地方还可改得更好些,这说明整理加工的重要。另一方面,是创作新剧本也应密切与演员合作。过去名演员与作者是密切合作的,作者完全了解演员的一切特点,这样才能写好。现在以为这叫侍候演员,是落后,这不全面。要知道一个剧作者越懂得这演员的特点就越能写得好,越懂得剧团的特点也就越能写得好,这不是落后。莎士比亚的剧本,就是给他们剧团写的,莫利哀剧本也是这样。他两人都是剧团的团长。象关汉卿,他自己还登台演戏。不要以为为了具体演员或剧团写剧本是不好的,这能提高演出质量。在北京有的剧作者很生气,写的剧本人家不要,而演员也不好好将原因说明。应该讲明哪些地方写得不好。听说柴可夫斯基写《天鹅湖》,整天与演员吵来吵去,而最后才得演出。有争论是应该的,只要争论的结果,不是从此不能见面了。主要演员应当重视新戏,应当把排几个好的新戏作为剧团的重要任务。象整旧一样,新戏自然难搞,老戏是经过多年的磨练才好的,所以新剧目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那么完整,这是很自然的事。象梅先生的《宇宙锋》,到现在还在改,一直改才能改好。光演旧戏不能演新戏是不对的,一个演员光是继承而无发展,他能否能为一个大演员,这很有问题。而且整理传统剧目面还应当广一些,一直叫人看《济公活佛》,即使是好东西也要腻的。我们应当赶快搞出新东西,常常能换新的剧目才行。一个剧目一连演几个月,要演到没有人看才放手,叫连满××场,××场,这都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不好。北京演戏的办法不错,他们的剧目常换,这虽是封建时代留下来的习惯,但也不比资本主义的习惯坏。以上是第三点。
4.依靠艺人的问题。我有一个看法,也许是很主观的——依靠艺人即是依靠群众。演员是最直接面对观众的,最懂观众的情绪的。演员是舞台上的实践者,我们说依靠艺人就是这个原因。但并不等于说凡是演员讲的话都对,应当唯命是听。一般说演员的意见都是比较实事求是的,符合观众心理的。其次是老艺人,他们掌握传统,传统就在他们身上,因此要依靠他们。当然编剧们也可以坚持自己的意见。戏的两个极端,一是完全偏重思想性和艺术性,另一是只偏重舞台效果,都不好,所以演员、编导应该紧密合作。
总言之,先了解观众才能提高观众。要从观众现有的基础上去提高他们,这叫群众观点。当然群众的意见也并非全对,我们还须加以分析、批判。但是,如果不重视就不对了。巩固艺人和剧作者、音乐家、导演的合作关系是十分重要的。特别是今天,大家都有弱点,或者文化不高,或者对传统不熟悉,所以谁也离不开谁,必须紧密合作。
今日讲的很空洞,又没有联系实际,天气又冷,耽搁了大家很多时间,很对不起。
1957年1月27日于上海大众剧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