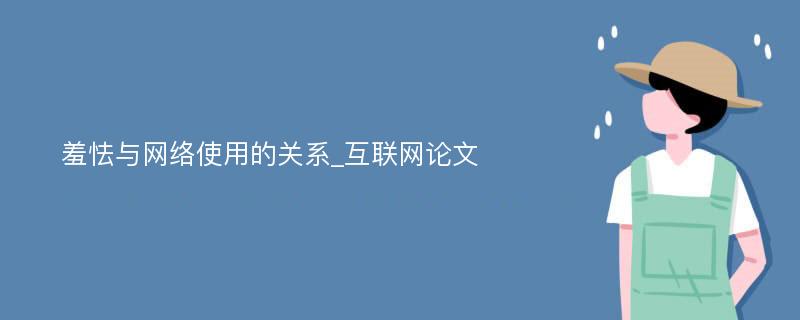
羞怯与互联网使用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联网论文,羞怯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B849:C91;B848
1 引言
研究发现有羞怯倾向的人占总样本的48%(Heiser,Turner,& Beidel,2003)。伍育琦(1999)对大学生进行抽样调查发现,羞怯是阻碍大学生人际交往的首要因素。羞怯可以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包括自我意识、自我保护能力低下,人际关系淡漠以及缺乏交流。这些都被归因为社会隔绝以及交流方式的逐渐改变(Henderson & Zimbardo,1998)。
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时空的界限,让人们即使不用面对面也可以相互进行交流。Henderson和Zimbardo(1998)认为随着信息交流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羞怯水平普遍提升,将导致“现实中”的面对面交流和接触全面减少。多种媒介和交流方式的出现(例如电话,电视等)也会造成社会交流的减少,且增加人们相互之间的疏离感。特别是网络,在早期文献中被认为是在社会交往和个人交流中最能疏远彼此的交流方式之一(Matheson & Zanna,1998)。其中潜在的含义就是网络交往会代替面对面的交流,提供社会补偿,并且人们在网络中进行交流的时候并不需要具备面对面交流所必需的社交技能(Henderson & Zimbardo,1998)。随着网络——这一现代交流工具的出现,人格与实验社会心理的研究者开始使用它来研究人类的心理进程以及社会行为(Bargh & McKeena,2004;Bargh,McKeena,& Fitzsimons,2002;McKenna & Bargh,1998,2000;McKenna,Green,& Gleason,2002)。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社会关系被电脑和网络影响,甚至线下的人际关系也被其影响(Walther,1996;Spears,Postmes,Wolbert,Lea,& Rogers,2000;Wellman,Haase,Witte,& Hampton,2001)。一些研究者发现网络为羞怯者与人交流以及建立持久的关系提供了媒介(McKenna & Bargh,2000)。有研究表明网络交往的特殊性质(匿名性,缺乏产生社交不适感的视觉指标,身体缺场性等)会促进人们进行自我表露(McKenna et al.,2002;Joinson,2001)。网络能够给人们提供在传统的线下环境中体会不到的社会和情感需求(Leung,2003)。在不需要露面的网络环境中,人们可以在网络中改变身份,扮演另外一个人(Turkle,1995)。总而言之,很多学者都研究了羞怯与互联网的关系,并且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已经得到心理学界的广泛关注。但是,有关互联网使用对羞怯的影响的研究却刚刚起步。本文首先介绍羞怯的界定,通过文献回顾,分析互联网使用对羞怯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最后,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2 羞怯的界定
羞怯是一种性格特征,指的是在面对新的社会环境和/或意识到社会评价的情境中个体的紧张和不适(Rubin,Coplan,& Bowker,2009)。羞怯的内涵非常丰富,包括行为抑制,焦虑—孤独,以及社交退缩(Coplan & Rubin,2010)。Karevold,Ystrom,Coplan,Sanson和Mathiesen(2012)对婴儿时期到青少年时期(1.5岁到12.5岁)的羞怯进行追踪研究发现,在此期间的羞怯水平是非常稳定的。
从心理学意义上讲,对羞怯(shyness)的界定从最早的状态描述定义发展到后来的操作性定义,这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最早对羞怯进行定义的Lewinsky就是对羞怯进行状态描述的定义,将羞怯定义为“一种极度抑郁的状态,通常伴随着身体症状,像脸红、口吃、出汗、发抖、脸色苍白、越来越想大小便。个体描述自己的心理状态是感到自卑、被忽略、受到干扰。对自己的感觉、情绪,尤其是外表过分敏感”(Lewinsky,1941)。但是由于这种定义缺乏操作性,所以后来的研究者倾向于对羞怯进行操作性定义。Henderson和Zimbardo认为羞怯是一种“逃避社会交往的倾向、不能恰当进入人际情境的倾向”(Henderson & Zimbardo,1998)。Zimbardo和Pilkonis认为羞怯是“是一种不情愿,不情愿接近他人或者不情愿进入那些不容易逃避他人关注的情景”(Pilkonis,1977;Zimbardo,Pilkonis,& Norwood,1977)。Crozier(2002)认为在一般的表述中,羞怯可以用于描述社会交往的反应和感受以及个人的某个重要的性格特征。现在最常用的是Henderson对羞怯的定义,即认为羞怯是在社交情境中的不舒服以及/或者抑制,是一种对消极评估的恐惧,伴随情绪上的沮丧或抑制,会显著影响对期望活动的参与行为或者对个体和职业目标的追求行为(Henderson,1997)。其将羞怯分为两类:一类羞怯可能是长期的、性格上的,作为自我概念的一种核心人格特质起作用;另一类可能是情境性的,包括在特定的社会交往情境中体验到的羞怯,不是自我概念中的一部分。由此可以总结出羞怯的特点:(1)羞怯发生的情境是特定的,一般发生在社交情境中;(2)羞怯的发生通常是心理、生理以及行为等各方面的综合表现;(3)羞怯往往会对人的正常生活产生影响。
3 羞怯的个体倾向于选择互联网进行交往的原因
Jones和Carpenter(1986)发现与非羞怯的个体相比,羞怯的个体缺乏社会支持,友谊网络较小,而且在线下的生活中处于被动交往的状态。研究发现那些在线下缺乏坚强的人际关系者会选择从网络中进行寻求(McKenna & Bargh,1998)。互联网的匿名性、对交流的可控性以及克服身体吸引障碍等特征对于羞怯者来说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McKenna & Bargh,2000)。互联网的匿名性可以降低羞怯者在交往过程中的自我意识,减少紧张感(Roberts,Smith,&Pollock,2000;Chak &Leung,2004;Stritzke,Nguyen,& Durkin,2004;Parks & Floyd,1996;Scharlott & Christ,1995;Turkle,1995)。Young等人发现虚拟空间的匿名性可以为羞怯者提供一个安全的社会交往环境(Ebeling,Frank,& Lester,2007;Young,Griffin-Shelley,Cooper,O'mara,& Buchanan,2000)。而且网络交往可以让羞怯者最大程度的控制交往的时间和进程,例如对信息的准备时间没有限制,也没有其他人的直接监视(McKenna & Bargh,2000;Carducci & Zimbardo,1995)。羞怯的个体很享受互联网带来的快乐,通过E-mail,ICQ,聊天室以及新的讨论组相遇,交往以及改变想法,可以满足人们在现实生活交往中不能满足的情感和心理需求(Heiser,Turner,& Beidel,2003)。另外,有研究认为网络鼓励自我表露和亲密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增强社会的去抑制化,这点对那些羞怯的个体来说是非常有益的(Morahan-Martin & Schumacher,2000;Roberts,Smith,& Pollock,2000;Joinson,1998a)。
Ward和Tracey(2004)发现羞怯的个体进行面对面交往比进行网络交往更困难并且羞怯的个体更倾向在网络上建立人际关系。还有研究发现线下环境中的羞怯者与非羞怯者在拒绝、建立关系和自我表露方面有显著地差异,然而这些差异在网络环境中却并不存在(Stritzke et al.,2004)。谭文芳(2003)认为内向型的大学生由于在现实生活中较为害羞、腼腆、不善于交际,所以较常选择以沟通交流为主的网络活动形式,如聊天,E-mail等。有研究者认为羞怯的个体多选择网络进行交往是因为他们无法处理现实社会交往中出现的问题(Scealy,Phillips,& Stevenson,2002)。Kelly和Keaten(2007)认为羞怯的个体喜欢使用E-mail进行交流是因为邮件可以延迟回复,这样就降低了回复时的焦虑感。另外,Yuen和Lavin(2004)发现羞怯的个体更倾向于投入网络关系中。
Cheek和Buss(1981)研究了羞怯与社交在个体交往过程中的作用,因为网络交往降低了交往中的焦虑感,因此与喜欢社交的非羞怯个体和不喜欢社交的非羞怯个体相比,喜欢社交的羞怯个体在使用网络过程中的动机是不同的。低社交的个体会认为没有必要使用网络来建立或者保持联系,然而高社交性的个体认为网络对于保持他们线下所建立的关系更为便利。
由上可知,羞怯个体倾向于选择互联网进行交往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1)互联网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吸引羞怯个体选择互联网进行交往。互联网的匿名性,身体缺场性,交流的可控性,克服身体吸引障碍,反馈的非及时性等这些互联网使用过程中的特点对羞怯个体来说都是能够帮助其进行网络交往的条件。(2)羞怯个体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也是促使其选择互联网进行交往的原因之一。羞怯个体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社交情境中,无论生理还是心理上都会产生一定的退缩、抑制和逃避,他们主要是在与人交往的时候容易羞怯,而网络恰好提供了一个不用与人面对面接触就可以进行交往的途径。(3)羞怯个体本身的社交水平高低也是促使羞怯个体选择互联网进行交往的原因之一。高社交水平的羞怯个体更倾向于使用互联网来保持线下所建立的关系。
4 互联网对羞怯个体的消极影响:网络成瘾
互联网使用对羞怯个体的消极影响主要是网络成瘾。国外一些研究认为,网络成瘾者的刻板印象为社交技巧不良、没有友伴、羞怯等(谢静慧,杨淑晴,2001;李望舒,2002)。国内也有一些研究提出,成瘾者羞怯、较为疑心、悲观、缺乏自信等共同特征(黄玉萍,胡红梅,2009)。网络成瘾,也称病态的使用网络,被定义为个体无法控制自己的上网行为,甚至会由此引发人们心理、社会、学校和/或工作方面的问题(Davis,2001;Young &Rogers,1998)。网络成瘾近年来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Melanie & Jacob,2011;喻承甫等,2012;Yates,Gregor,& Haviland,2012)。
很多研究发现羞怯与网络依赖、网络成瘾关系密切(Yuen & Lavin,2004;Engelberg & Sjoberg,2004;Chak & Leung,2004)。Yang和Tung(2007)对比中国台湾高中生中的网络成瘾者与非网络成瘾者发现,具有羞怯这种人格特质的学生比不具有这种人格特质的学生更容易出现网络成瘾。Chak和Leung(2004)认为一个人越是容易网络成瘾,就越害羞,网络成瘾的人会频繁地使用网络,尤其是会通过E-mail或ICQ进行网络交往和在线游戏。这些发现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网络成瘾的趋势越高,越害羞)一致(Huang & Leung,2009)。网络依赖的大学生在面对面交流中表现出高水平羞怯的,在网络交往中并没有表现出高水平的羞怯(Yuen & Lavin,2004)。网络交往可以减少面对面交往过程中伴随产生的负面和令人不悦的情绪,就是因为在网络交往中可以减少这种负面和令人不悦的情绪,所以人们才容易形成网络依赖。当网络交往变成羞怯个体主要的社交方式时,就会对网络或者特定的网络活动产生心理依赖。一项针对中国香港年轻人的网络依赖的研究发现羞怯与被试的网络依赖正相关(Chak & Leung,2004)。Sheeks和Brichmeier(2007)认为在线交流可以满足羞怯个体的社交需求,因此羞怯个体也更加依赖在线交流工具。国内的研究者也发现羞怯与网络成瘾显著相关,一方面羞怯的个体更倾向于逃避现实而进入虚拟情景;另一方面,长时间沉迷于网络会丧失对周围环境的感受力及参与意识,从而更加羞怯(王倩倩,马燕妮,2006)。罗伟(2008)的研究发现,羞怯和网络成瘾倾向显著正相关,羞怯的大学生更容易网络成瘾。Peng和Liu(2010)的研究发现羞怯与网络游戏成瘾正相关。羞怯个体在网络环境中维持社会关系比面对面接触更加轻松(Ebeling et al.,2007)。Orr等(2008)的研究发现羞怯的个体在Facebook上消耗的时间比不羞怯的个体更多。而Ryan和Xenos(2011)的研究进一步发现羞怯的个体耗费大量的时间在Facebook的非社交行为上(例如游戏)。
以往对网络成瘾与羞怯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网络成瘾会促使网络使用者羞怯水平的增加(Caplan,2002;Ofosu,2001;Goulet,2002)。青少年网络成瘾后,推理能力、智商等会减低,还伴有内向孤独、自卑羞怯等(杨曙民,李建秀,2007)。Ebeling-Witte,Frank和Lester(2007)发现羞怯的得分与网络成瘾有关,即羞怯的个体利用网络来建立友谊关系,以此来弥补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不足。此外,羞怯的分数还与在线时间有关,分数越高,网络使用时间越长。
因此,网络依赖、网络成瘾与羞怯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羞怯的个体比不羞怯的个体更容易网络成瘾、网络依赖。这是因为羞怯的个体更容易为了逃避现实或现实交往而选择互联网这个虚拟世界,并沉迷于虚拟世界;而网络成瘾、网络依赖的个体也更容易羞怯。因为长期沉迷互联网,缺乏与人交流,一旦要与人面对面交往,可能会不习惯以及缺乏社交技能而避免与人交往,进而逃避社会交往,个体的羞怯水平就会上升。
5 互联网对羞怯个体的积极影响
Carducci和Zimbardo(1995)曾经担心技术的不断进步会造成羞怯水平的大幅度提升,但是互联网在某些程度上也可以降低羞怯的程度。互联网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区域,缓解了社交的不安全感(Yuen & Lavin,2004)。使用互联网进行人际交往的羞怯个体,在线下的羞怯感也会降低(Roberts et al.,2000)。因此,互联网也可以被看做是羞怯个体的有效治疗工具。
羞怯感的高低并不能表示人们会过多或过少的使用互联网的交往功能,这一点也已得到证实(Roberts et al.,2000)。羞怯者认为网络交往比面对面交往更加简便,这可能是因为在网络交往中不会有其他人出现。因此,在网络交往中可以减少羞怯个体的压力经历,促进社会交往。研究过程中羞怯个体表明在网络环境中其感受到的拒绝更少,在建立关系方面也更加自信,更易于自我表露(Stritzke et al.,2004)。羞怯的个体可以通过网络交往来克服面对面交往时的紧张情绪(Andrews et al.,2002;Barlow,Esler,& Vitali,1998)。
网络交往可以帮助促进线下的人际交往,而且羞怯程度较高的个体也许发现网络交往比面对面交往更能填补线下人际交往时的空虚。但是前者是将互联网作为一个良好的社交促进器;后者的选择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互联网也许会让那些羞怯程度较高的人感受到社会孤独感。根据自我表征理论,网络环境可以减少羞怯经历,而且羞怯的个体在网络交往中会感觉更加安全。因为个人信息的交换主要是根据羞怯个体自我表露的意愿来进行信息输入的。有证据表明网络交往可以促进自我表露(Joinson,1998b),被试报告其在网络交往过程中可以比在面对面交往过程中进行更深层次的自我表露,因此与面对面交往相比,在网络环境中可以更快的建立人际关系(Rice & Love,1987)。Kraut等(2002)进行了一项纵向研究发现网络使用和个体与家人、朋友或者当地社团的面对面交往的时间正相关,符合“富者越富”的模型,即使用网络越多的个体,与家人、朋友或者社团的面对面交往的时间也越多。
此外,即使羞怯个体在网络环境中报告的羞怯水平比较低,但是其羞怯的程度仍然高于在网络环境中的非羞怯个体。这说明虽然网络环境有利于羞怯个体的社会交往,但仅仅只是降低个体的羞怯程度,并不能消除(Stritzke et al.,2004)。
总的来说,互联网对羞怯个体的积极影响就在于互联网的使用能降低个体的羞怯程度。当羞怯的个体由于害怕或者逃避面对面的人际交往时,互联网为其提供了一个与人交往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中,羞怯个体在与人交往时可以降低紧张感和羞怯水平,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来与人进行交往,而不会体验到在线下环境中与人交往时的紧迫感。还可以促进羞怯个体与人进行交往,而且通过网络交往所增加的自信也可以帮助其在现实生活中进行人际交往。
6 网络使用者羞怯的理论模型
随着网络使用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提出了相关模型,虽然并不是针对羞怯提出的,但是都可以解释羞怯个体的网络使用行为。
6.1 使用与满足理论
Suler(1999)从“需要—满足”的观点出发解释网络行为,认为一个人对网络的热情可以处于健康、病态或两者之间。该理论尤其强调潜在需要对个体互联网行为的影响,即在互联网空间的某些功能可以满足个体的这些潜在需要,个体的各种不同的互联网行为正是这些潜在需要的折射。Suler(1999)研究发现与网络成瘾有关的6类心理需要中就包括社会交往的需要,而Sheeks和Brichmeier(2007)的研究发现,羞怯个体也有社交的需要,互联网恰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那么社交需求得到满足的羞怯个体,为什么有的会网络成瘾,有的不会,这涉及到现实满足的问题(邓林园,方晓义,万晶晶,张锦涛,夏翠翠,2012)。如果个体心理需求中的现实满足强于网络满足,那么个体网络成瘾的可能性就会降低;相反,个体网络成瘾的可能性就会增加。该理论认为羞怯个体由于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交往需求得不到满足,才会求助于网络,而当网络满足强于现实满足时,羞怯个体就有很大可能会网络成瘾。
6.2 社会—认知理论模型
Bandura(1986,1999a,1999b)提出的社会—认知理论模型对互联网心理学的研究具有广泛影响。社会—认知理论强调行为、环境以及个人(自我调节、预期、自我反应与反省等)三者的交互作用。在社会—认知理论框架内,互联网使用被概念化为一种社会认知过程,消极的结果预期,自我贬损及自我短视与互联网使用之间是负相关的(Eastin,2001)。而Henderson和Zimbardo(1999)的社会适应模型认为羞怯个体对环境和他人的消极认知是形成羞怯的关键因素。该理论认为羞怯个体对环境和他人具有消极认知,而网络成瘾恰好就是消极认知的结果预期,当个体的羞怯水平越高,就越容易网络成瘾。
6.3 认知行为模型
Davis(2001)从精神疾病的病因学角度提出的认知—行为模型,强调了与病理性网络使用有关的病因性因素,区分了导致病理性网络使用症状的近端原因和远端原因。其中近端原因包括适应不良的认知,社会孤立等。其中适应不良的认知被视为病理性网络使用症状的核心因素。该理论认为羞怯个体由于近因中的不良认知,会不断思考与互联网使用有关的问题,导致其认为网络是自己唯一受到尊重的地方,难以被生活中其他事情吸引,而远因中心理病源的存在,导致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症状的出现。
从上述理论模型可以发现,互联网使用对羞怯个体带来的消极影响的主要原因也许是羞怯个体的社交需求得不到满足(主要是指心理需求的网络满足强于现实满足),或消极认知所导致的,这些与互联网自身性质是无关的(Walther &Reid,2000;Grohol,1999),而与网络使用者自身特征有关。
6.4 心理机制分析
张明(2006)认为有两种心理机制:阳性强化作用和阴性强化作用导致了网络成瘾。
(1)阳性强化作用
行为学习机制中的阳性强化作用在成瘾行为初期起重要作用。阳性强化指的是行为的后果有明显的正向奖励作用,从而使得该行为的发生频率增加。羞怯个体通过网络交往可以得到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建立的关系,使其在建立关系方面更加自信。这种关系的建立产生了情绪上的正向体验,使羞怯个体的社交需求得以满足。这一切增强了羞怯个体的自信,使这一行为得到加强,而这种心理上的正向体验使羞怯个体的网络交往行为得到加强,会不断追求这种心理的满足感,从而倾向于选择网络进行交往,在网络成瘾行为的初期,阳性强化起主要作用。
(2)阴性强化作用
而阴性强化作用发展和维持了网络成瘾这一行为。阴性强化指的是行为的后果可以避免和减轻某些痛苦。与阳性强化一样可以增加某种行为的频率。当个体网络成瘾之后,在外力的介入下(如亲友的劝说和责备),依然网络成瘾,使个体对其本身丧失自信心和控制能力,而摆脱这些不良情绪的最好办法就是再次回到网络中。网络中的刺激、兴奋、成功使其暂时忘记现实生活中的不快。久而久之,网络成为应对现实生活中的负面情绪的唯一手段。这时网络已起到阴性强化作用。阳性强化和阴性强化的相互交替作用使得网络成瘾行为得到发生和维持。
7 小结与展望
近年来很多学者都在研究羞怯与网络的关系。一些研究认为羞怯与网络使用频率的增加有关(Mesch,2001;Morahan-Martin & Schumacher,2000;Morahan-Martin & Schumacher,2003),根据补偿心理,在现实生活中缺乏强有力的友谊网络的羞怯者会选择网络交往来进行补偿(Chan,2011),通过网络交往来进行人际交往,这会直接减少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而且也会增加线下的羞怯程度。由于网络交往不需要具备现实交往中的技巧,并且可以自主掌控交往的进度,也让网络交往更加受欢迎。
另一些研究并不这样认为(Jackson et al.,2003;Modayil,Thompson,Varnhagen,& Wilson,2003)。Madell和Muncer(2006)的研究并不认为羞怯的个体比非羞怯的个体更多的使用网络,以及更多的通过网络进行交往,甚至羞怯的个体比非羞怯的个体更少的使用E-mail,因为羞怯个体的社会联系很少。但是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该研究主要探讨社交恐惧和社交焦虑与互联网使用的关系,而羞怯被作为社交恐惧和社交焦虑的一种情境性的表现形式,研究者将社交恐惧和社交焦虑与互联网使用的结果直接用于羞怯个体,这种结果是否妥当值得讨论。最近有研究发现羞怯的个体与非羞怯的个体在网络上所消耗的时间是一样多的(Roberts et al.,2000)。这些研究认为虽然羞怯者可能更倾向于网络交往,但是通过网络交往,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羞怯个体现实中的人际交往。
现有研究主要局限在研究样本,羞怯的报告方式,样本分布区域,网络使用的测量问卷等问题上。大多数研究所选择的被试都是研究者所在区域的在校大学生,而这部分被试恰恰有很多时间是可以自由支配的,并且他们的教育程度比较高,所以这部分被试是否能够代表全体这个问题值得商榷。而大部分研究羞怯的方法都是靠被试的自主报告,这种研究方法不够客观,可能会受被试自身情况以及社会期许效应的影响。另外,有的研究者直接使用网络成瘾的问卷来测量羞怯个体,有的羞怯个体使用互联网的频率比较多,有的羞怯个体使用互联网的频率比较少,分布不均,如此自然造成最后结果差异显著。
羞怯的研究在西方有一定的积累,在我国还刚刚起步,关于羞怯与互联网的研究更是比较匮乏。目前已有的关于羞怯与互联网的研究结果都是基于两者本身所具有的特点而得到,或者仅仅将羞怯作为造成网络成瘾的相关心理因素之一。未来的研究可以尝试通过中介变量或者调节变量来研究羞怯与互联网使用的关系。羞怯是一种特质,是一种不能被因素分析成更多的特质(Briggs,1988),并且这一特质是难以改变的,但是通过易于调节的中介变量或调节变量可以更好的改善羞怯水平或者羞怯与互联网使用的关系。利用羞怯个体偏好使用网络的这点,为其提供更多的网络资源,让羞怯个体在网络环境中进行学习,或者利用一些中介或调节变量来改善羞怯个体的羞怯水平,例如,有研究就发现人际交往困扰对羞怯与网络交往依赖有完全中介的作用(李菲菲,罗青,周宗奎,孙晓军,魏华,2012),社会支持在羞怯与网络成瘾倾向之间也起完全中介作用(罗伟,2008);上文中提到互联网使用对羞怯的消极影响也许是因为羞怯个体的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或者消极认知所致,这些都可以作为二者的中介变量来研究相互之间的关系。而在研究羞怯与互联网的关系时,研究者认为互联网可以为羞怯的个体提供一个与世界沟通的媒介,但是在经过某些心理测量的时候发现这个媒介可以让他们“成瘾”。在羞怯与互联网的关系研究上过于偏重互联网对羞怯个体的消极影响,也就是认为羞怯一定是与网络成瘾或网络依赖有关,而实际上互联网对人的发展也有促进作用,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尝试研究互联网对羞怯个体的积极影响。并且不管互联网使用对羞怯个体是积极影响还是消极影响,都不要只局限于二者自身的特点。现在已有研究者通过尝试脑电和ERP等多种方法来研究羞怯的生理机制(韩磊等,2010;赖永秀,任鹏,贺强,孙鑫,尧德中,2008),未来可以尝试加入互联网这个变量用脑电或ERP这些不同于问卷法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两者的关系,或者在不同的研究方法中加入不同的相关变量来研究二者的关系。新的研究方法可以让我们更加透彻的了解和认识羞怯这一不易于改变的特质,进而可以通过更多的方法和手段来改善羞怯这个普遍率不断增加的特质;而新的相关变量的加入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认识羞怯和互联网使用的关系,让现代人更好地运用互联网这个在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工具。这对于我们来说将是非常具有挑战意义且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标签:互联网论文; 认知发展理论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互联网社交论文; 社会网络论文; 认知过程论文; 社会交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