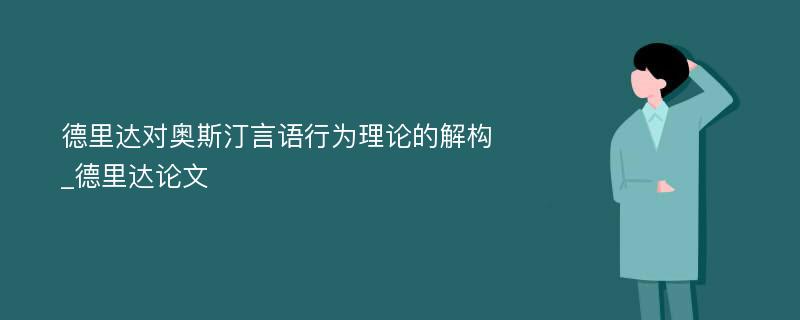
德里达对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解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奥斯汀论文,言语论文,理论论文,德里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66年,正当结构主义在西方如日中天的时候,德里达以一篇题为《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嬉戏》(“Structure, Sign andPlay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Human Sciences ”)的论文宣告了结构主义时代的结束和解构主义哲学的正式登场。然而,从解构主义哲学诞生之日起,德里达及其追随者们所要拆解的目标就不仅仅指向结构主义,而是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哲学传统。在德里达看来,这一传统不仅支撑着欧洲大陆哲学,也规定着英美分析哲学的发展。在《签名事件语境》一文中,德里达便集中批判了分析哲学中日常语言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奥斯汀(J.L.Austin)及其所创立的方语行为理论,从而引发了他和言语行为理论在美国的传人塞尔(J.Searle)的论战。这一论战,可以说是解构主义和英美哲学的首次交锋。虽然双方谁也未能驳倒谁,但论战中双方所表达出的许多观点却发人深省,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本文将简要介绍言语行为理论有关论点以及德里达对这一理论的解构批判,进而尝试着探讨这一论战对文学话语和哲学话语的关系问题、文学的存在价值问题等诸方面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同时也希望能为全面了解德里达解构思想脉络提供一点管窥之见。
一
我们知道,对语言意义的追寻一直是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然而,在奥斯汀提出言语行为理论之前,对意义的研究仍局限于语义学的范畴,“它研究句子和词语本身的意义,研究命题的真值条件。因此,语言学研究的意义是句子的认知意义,是不受语境影响的意义。 ”(注:何自然:《语言学导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7,134页。)也就是说,对于传统语义学而言,真值性(truth value )是判断句子意义的唯一标准:如果一个陈述句所描述的现实情况为真,则句子具有真值意义,是真陈述(normal statement);如与实际情况不符,则句子不具有真值性,是伪陈述(pseudo- statement )。 例如, “Itis cold here”。从逻辑一语义方面入手, 该句的意义就只有两种可能性:或者房间的确冷,则陈述是真;如果房间不冷,则陈述为假。然而,实际情况是,说话人所要表达的意思,远非陈述的真值性所能涵盖。它可能还是一种“请求”(希望说话人弄一台取暖设备来,或者是一种“邀请”(邀请大家转移到另一个较暖和的房间去),等等。(注:何自然:《语言学导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7,134页。)可见逻辑一语义学难以把握住句子所有的意义。而且,还显然存在着一些并不受语义真值条件裁定的句子,如 “ I promise to pay youtomorrow”, 就不是对某一事实的陈述或状态的描述,而只是作出了一个承诺。
经过长期的研究总结, 奥斯汀在其论著《论言有所为》(How toDo Things with Words)彻底推翻了以逻辑一语义的真值性为语言理解的中心这一观点,拆解了normal statement/pseudo-statement这一等级对立。 他引入了另一对概念来对陈述句分类, 既表述句(constatives)和施为句(perfomatives)。 表述句涉及的是“言有所述”属于逻辑一语义问题;施为句关注的是“言有所为”,这主要以语境为转移,属语用学问题。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奥斯汀发现其先前引入的等级对立:施为句/表述句存在着许多不严密的地方,比如表述句其实可以归入隐性施为句。如“The cat is on the mat”一句, 表面上看是一个表述句, 但实际上却可以被看作一个省略了施为动词(performative verb)的隐性施为句:“I hereby affirm that thecat is on the mat”。这样一来, 所谓施为句/表述句的等级对立便形同虚设了。在此基础上,奥斯汀又提出了言语行为三分说,力求使言语行为理论具有更为普遍的涵盖性。他认为,所有的句子都可以被看作施为句, 而每一个施为句都包含着三种言语行为: 以言指事(locutionary act );以言行事(illocutionary act );以言成事(perlocutionary act)。其中以言指事指语句的表述; 以言行事指完成某种行为(如允诺,发誓等);而以言成事指给受话人带来的影响(如使其感到放心,安慰等)。
但是,奥斯汀也清楚地看到,并不是每个施为句都能达到其目的,即并不是每一个以言行事都能带来以言成事,比如“I now pronounceyou man and wife”,如果是演员在电影里讲的一句台词,则收不到言后之果。为此,奥斯汀为言有所为得以有效实施设立了一系列合适条件(felicity conditions),它们是:
(A1)必须存在一套能带来规约性效果的、为普遍认可的规约性程序(conventional procedune);这一程序包括由特定的人在特定的场合所讲的话。再有(A2)在一具体事件中,特定的人和特定的场所必须符合特定程序的要求。(B1)程序必须由对话双方正确而(B2)彻底地执行。(注:J.L.Austin,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pp.14—15,21—22,9.)
显然,在奥斯汀规定的所有这些适合条件中,一个中心的问题就是规约性程式(conventional formula)。奥斯汀以婚礼上男女双方互相作出誓言为例:婚礼上的承诺与其是当时内心精神行为外化而成的物质符号,毋宁说是在重复一句既定的套话,完成一套婚礼所要求的规定程序。(注:J.L.Austin,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pp.14—15,21—22,9.)换句话说,奥斯汀对规约性程式在言事行为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的强调,暗含着他一个重要立场:在决定言语行为的各因素中,必须排除说话主体的意图性(intentionality)。因为一旦涉及到主体意图,就有再度滑向在场的形而上学的危险。索绪尔曾试图以语言系统内部的差异产生意义的立场来避开主体意识,但他同时又设立了speech/writing 的等级对立,强调speech对writing的优先权, 从而再次滑入以指意意图在场为意义之源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注:关于索绪尔设立speech/writing 的等级对立,参见《普通语言学教程》;关于德里达对索绪尔的解构阅读,参见J.Derrida,Of Grammatology(Baltimore:John Hopkings University Press,1976)。)
那么, 奥斯汀关于规约性程式决定示言外之力(illocutionaryforce )从而带来言后之果的立场能成功地摆脱在场形而上学的束缚吗?通过对《论言有所为》的解构性阅读,德里达一针见血地指出,奥斯汀的理论最终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美好设计,“形而上学的困难”(metaphysical difficulties)仍然困扰着奥斯汀的理论设计。
德里达对奥斯汀的解构批判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奥斯汀虽然拆解了performative /constative 这一等级对立, 但他同时又设立了serious/non-serious这一新的等级对立,再次引入了他所力图回避的指意意图在场的观念;二,奥斯汀虽然引入语境因素以求框定示言外之力的功能域,但语境却具有流变性、不饱和性和不可穷尽性。下面我们将就这两点来分别分析德里达的立场。
二
德里达所采取的他自认为无往而不胜的解构策略虽然不失偏颇,但确有其独特的可操作性。他的立论基础是,整个西方哲学就是在场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presence),“所有与本质、 原则或中心有关的名称都总是指向一个恒定的在场。”(注:J.Derrida, Writingand Difference(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5),p.297.)这些恒定的在场便引出了一系列建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的等级对立,言语/写作、意义/形式、自然/文化、超验/经验、真实/虚假等。在这些等级对立中,前一项代表原生性在场,具有先在性;而后者则是衍生性的,是前者的增补(supplement)。然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哲学则根本否定任何本源性在场。没有在场,只有延异(différance)的痕迹(trace);延异通过空间上的置换和时间上的延搁,将本源性在场永远放逐了。这样,任何立足于在场的等级对立就具有难以逃避的自我颠覆性。那么,解构就旨在揭示出等级对立中居于寄生性的、边缘性的因素是如何打破和颠倒这一武断的等级秩序。它“通过抓住‘症候性’问题,展示出文本是怎样与支配它的逻辑体系相抵牾的。因为在这些问题上,文本往往陷入困境、发生紊乱,并显得自我矛盾。”(注:Terry Eagleton,Literary Theory (Worcester:Billing and Sons Ltd,1985),p.67.)
德里达对奥斯汀的解构就是首先抓住了奥斯汀所设立的( serious/nonserious这一等级对立,从而指出,奥斯汀虽然小心翼翼地回避指意意图在主体意识中的在场,但仍难摆脱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窠臼。
我们知道,奥斯汀自己也清楚地看到,并不是每一个以言行事都能收言后之果,即实现以言成事。于是,他便设立了一系列所谓的适合条件来圈定言语行为的功能范围。他并不否定那些不能带来以言行事和以言成事的施为句的存在,但又认为,那些句子只属于非主流的、边缘性的、寄生性的例外,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应将其悬搁起来,存而不论。他说:
和所有话语(utterances)一样,施为句总会受到某些病变(ill)的侵害。尽管它们可以较为全面地被研究,但目前,我们还是有意地将其排除。比如一个施为句如果出自舞台上演员之口,或出现在一首诗里,或只是个人独白,那么,它将是一个很特殊的、意义空洞的句子……不难理解,在这种情形里语言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被使用一不是认真地(not seriously),而是以一种寄生(parasitic)于常规用途的方式被使用……所有这些我们都不予考虑。不管恰当与否,施为句都只应被理解为发生在常规情形里的句子。(注:J.L.Austin,How To DoThings with Words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pp.14—15,21—22,9.)
德里达认为,这段话清楚无误地表明了奥斯汀的增补观念和等级观念:nonserious是外在的、补充的、寄生的,在处理seriousperformatives时应予以排除。其实, 在论言有所为的一开篇, 奥斯汀就设立了serious/nonserious的等级对立。
是否语言为了被“认真”(seriously)听取, 就应被“认真”地讲述呢?尽管不甚明了,一般来说这却是真实的情况——对任何话语的意旨加以研究是一件虽然普通却极为重要的事。比如说,我现在就不是在讲笑话或作诗。(注:J.L.Austin,How To Do Thingswith Words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pp.14—15,21—22,9.)
奥斯汀似乎想尽力避开重新引入指意意图的因素,所以给seriously加上引号。然而,这样做却是欲盖弥彰。这表明奥斯汀和索绪尔一样,仍不能摆脱指意意图在场于主体意识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对于德里达的指责, 塞尔在其《重申差异:答德里达》(“Reiterating Difference:A Reply to Derrida”)一文中论辩道:奥斯汀对nonserious的排除,仅仅出于逻辑先在性(logical priority)的考虑,他说:
在回答一组关于“严肃”话语的、处于逻辑先在性的问题之前,有必要将那些关乎寄生性话语的问题暂时悬置起来……言语行为的佯装形式(pretended form)在逻辑上依附于非佯装(nonpretended)言语行为的可能性,就如同任何行为的佯装形式都依附于其真实形式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讲, 佯装形式是寄生于非佯装形式。 (注:J.Searle,"Reiterating Diference",Jonathan Culler,On Deconstruction (London and Henley:Routledge & Kengan Paul,1985),p.118.)
塞尔以“承诺”为例来具体说明“非佯装形式”的逻辑先在性:如果现实生活里没有承诺的可能性,那么舞台上的演员就不可能讲出承诺施为句。但德里达断然否定塞尔所谓的逻辑先在性,因为“即便是出于方法论和权宜之计的考虑,关键的问题仍然是这种‘理想化’不具有结构的可能性与合法性。”(注:J.Derrida,Limited Inc(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88).pp.67,18,74.)为什么呢?因为在人们习惯性的逻辑思维中,现实生活中的承诺是首要的、真实的,舞台上的承诺仅是真实承诺的摹仿,是承诺程式(formula)的空洞复述(iteration)。但是,反过来,我们为何不可以逆向思维:舞台上的承诺是先在的,而生活中的承诺是衍生的?德里达认为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 因此,他引出了一个重要概念:任何一个指意序列(signifying sequence)都具有某种可复述性(iterability)。
如果施为句不重复某个“被编码的”、可复述的句子,换句话说,我讲出一句套话,从而宣布会议开幕、轮船下水或婚礼开始——如果这句套话不遵从于一个可复述的模式,或以某种方式被当作“引言”,那么,一个施为句能完成言语行为吗?(注:J.Derrida, Limited Inc(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88).pp.67,18,74.)
根据奥斯汀为言语行为所设立的条件,一个施为句之所以能言有所为,在于它必须遵从一套既定的规约性程式,那么,这些程式当然能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被转述或复述。所以,生活中作出的承诺只不过是规约性程式或套话的重复;而舞台上的承诺则可以被看作是这程式本身。为什么呢?笔者的理解是,正因为舞台上的演员所做的承诺不能以言行事,更不能收言后之果,不具有功用实在性,所以它就是被掏空了意义的作为元话语的程式本身的裸露,是话语的话语。至此,我们便明白了,为什么德里达理由十足地拆解并颠倒了奥斯汀所设立的真实施为句(serious
performatives )/虚假施为句(nonseriousperformatives)的等级对立:是前一项依附于、衍生或寄生于后者, 因为后一项是元话语,前者只是元话语的复述。
德里达以话语的可复述性颠倒了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中的等级对立具有重要意义。卡勒指出:
这是一条意义深远的原则。一个指意序列(signifying sequence)之所以能指意,仅仅在于它是可复述的,在于它能在各种真实或虚假的语境中被重复、引用和戏拟。摹仿是本源存在的条件而非附着于其上的偶然事件。海明威的风格具有独创性,只是因为它能被引用、摹仿和戏拟。因为在任何一种风格之中必然存在着可识别的特征,它们使得风格成为风格并产生独特的效果。这些特征能被认识,就一定能被剥离出来并加以重复。因而正是展示于虚假、衍生和摹仿性话语中的可复述性,才使得所谓原初性和真实性成为可能。
(注:Jonathan Culler,On Deconstruction,pp.120,122,113,124—125.)
然而,颠倒等极秩序并不是德里达的目的,而只是其解构在场的手段。一旦施为句不再具有真实/虚假的对立,那么一个真实的施为句所能传达的言外之力(illocutionary force)就因此有理由受到怀疑。当然,奥斯汀也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为了保证一个施为句能真正以言行事、以言成事,奥斯汀不得不求助于语境(“在特定的场合里由特定的人讲特定的话”),以期圈定真实施为句的范围。自然,处于具体语境之外的施为句就是虚假的了。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即使由于程式的可复述性消解了真实/虚假的区分,所谓标准性事例(standardcases)只不过是程式的复述,那么, 语境的引入又能否锚定施为句的意义呢?在这个问题上,德里达提出了另一个重要的论断:意义取决于语境,但语境具有无限的开放性。
前文我们已经提到,奥斯汀为施为句划定的语境涉及到三方面因素。意思是说,只要任何一个施为句符合这三种因素的要求,它就不仅能以言行事,还能以言成事。但问题是,语言功能还存在着另一面,即“将一个语言序列嫁接(graft)到另一个语境里,从而改变其功能。 这种功能同样存在于施为句中。”(注:Jonathan Culler,OnDeconstruction,pp.120,122,113,124—125.)以奥斯汀自己的例子为证。牧师向一对年轻人宣布“I now pronounce you man and wife”这句话如果要带来言后之果,即使他们正式成为夫妻,就必须符合以下条件:宣布者是法定有权主持婚礼的牧师;他所讲的必须是一句既定套话的重复;受话者是一对未婚男女;他们刚刚取得结婚证明并于婚礼前互相起誓愿结为夫妻;地点必须是教堂。但我们很容易就能设想出各种情况使该句不能发挥言语行为的作用。比如这些条件都满足,但那只是正式婚礼前的一次演练。在这种情况下,“Inow pronounce you man andwife ”就不具有示言外之力,更不用说带来言后之果了。
所以,将语境功能绝对化也是行不通的。但这并不是说象索绪尔一样又回头去求助于说话主体的意图。语用学之不同于语义学,在于它将语境作为影响意义的主要因素,这本身是一个革命性的进步。即使在言语行为理论陷入困境时我们也看到,示言外之力之所以游离不定,还是由于语境的变幻莫测,难以框定。然而,关键的问题即在于此——正如德里达所说:意义产生于语境,但语境具有不可穷尽性,“我的立足点就是:语境之外不可能有确定的意义,但没有任何语境是饱和的(sat-uration)。 我这里指的不是意旨的丰富性或语义的多产性,而是结构,是剩余物或复述的结构。”(注:Jonathan Culler,OnDeconstruction,pp.120,122,113,124—125.)
语境为什么是不可把握的呢?德里达认为这里存在两方面的原因。首先,任何给定语境都具有被进一步描述的开放性。许多事实证明,语境的确定性是相对的,语境的边界不可能是明晰的;任何企图穷尽所有语境因素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文学批评史的发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许多长期不为批评家所注意的、所谓边缘性的因素一旦被发掘出来,就会给文本意义的阐释提供一种全新的图景(如格林布莱特(Greenblatt)等一些新历史主义者通过对文艺复兴时期流行于英国社会的一些奇特风俗的发掘,从而对莎士比亚及其作品提供了全新的解读)。但是,问题是怎样来解释语境的这种不可穷尽性呢?德里达把这些现象归结为由于无意识的所用而产生的移位。他认为, 如果把无意识的欲望(unconscious desire)也归入语境因素, 那么许多言语行为的意义和功能将变幻不定。(注:J.Derrida, Limited Inc ( 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88).pp.67,18,74.)德里达想说明的是,由于无意识(主要指说话主体的无意识)是流变的、难以把握的,所以受无意识影响的语境便具有无限的开放性,从而便可以不断地加以描述。那么,决定于语境的意义(或示言外之力)便因语境的无限开放而不可穷尽。
当然,对于语境的流变性,人们会提出另外一项措施:对语境进行人为的、强制性编码(codify),从而限定其任意扩散性。事实上,奥斯汀对虚假施为句的排除就是一种对语境的编码。但是,语境之不可把握的第二层意思正在于此:任何对语境的编码, 总是将自己嫁接(graft)到这一语境上,从而产生出一个逃逸编码的新语境。怎样理解这一论断呢?卡勒举了一个例子:比如某机场的安检处有这样一则告示:“所有关于炸弹与武器的言语将被严肃对待”(“All remarks concern-ing bombs and weapons will be taken seriously”)。 这显然是一种语境编码。它企图通过强行划定语境范围,从而把握住任何在此语境里说出的施为句的示言外之力。当然其主要目的在于防止有人在这种场合里讲“我鞋子里有一枚炸弹”之类的玩笑话(不管说话者的意图是什么,这类玩笑话将被严肃看待)。但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这种语境的编码仍不能阻止意义上的游戏。其失败的结果是必然的”。 (注:Jonathan Culler,On Deconstruction,pp.120,122,113,124—125.)为什么呢?因为语言结构同时又将编码(codification)嫁接到原有语境上,从而便产生出一个不受编码制约的新语境。在新语境里,“我鞋里有一枚炸弹”之类的话就很难被严肃看待。比如,有人会立即十分反感地问道:“如果我说‘我鞋里有一枚炸弹’,就要被严肃处理,是吗?”显然,这句话的含义建立在新语境功能上,它成功地逃逸了先在编码的企图。或许,有关方面会再次编码语境:“任何关于炸弹和武器的言论,包括那些关于炸弹和武器的言论的言论,都将被严肃对待”。显然,这样的编码是可以无限地推衍下去,因为示言外之力逃逸编码的可能性是无限的。所以,依靠语境编码来保证言语行为的企图必然也将遭到失败。
三
德里达从指意序列的可复述性(iterability )和语境的不可把握性(unmasterability )两方面入手, 颠覆了奥斯汀所设立的真实(serious)/虚假(nonserious)的等级对立, 从而消除了施为句示言外之力绝对在场的可能性。然而塞尔等人却一反奥斯汀的小心翼翼,强烈坚持意图决定论。论战终于不了了之而结束。但这场论战却从一个侧面引发我们对有关文学的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如哲学(或科学)话语与文学话语的关系问题、文学存在的价值问题等。
关于哲学话语和文学话语的关系,远自柏拉图起西方文论界就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柏拉图认为,诗歌是“影子的影子”,是“二度摹本”,它远离真理,因此应被逐出其“理想国”。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诗歌比具体历史事件更接近普遍性和真理性,因而具有充分的存在理由。在以后的各种文论流派中,可以说,争论的焦点仍在于文学话语和哲学话语孰真孰假,或谁能传达最高真理这一点上。无论是摹仿论还是表现论,虽然都力图为诗歌辩护,但却又都不可避免地设立了摹仿/被摹仿、表现/被表现的等级对立。即是说,都是把文学话语看成衍生的、寄生的、第二性的。而“语言论转向”以来,对文学话语和哲学话语的界限划分更为泾谓分明了。如理查兹认为文学话语是“非指称性伪陈述”,与哲学真理无关;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等也都坚持文学话语系统的自足自律:诗歌不是摹仿,不是表现,它或者是系统内部的自我陌生化,或者是语言的自我指涉性,均与哲学话语的真理表达无关。这其实也暗中设立了哲学话语/文学话语的二元对立(虽然避而不谈等级性)。言语行为理论拆解了真理表达与非真理表达这一等级对立,但由于引入了serious/non-serious这一对概念,其实仍在哲学话语和文学话语间预设了等级性。显然,按照奥斯汀的观点,文学话语是不严肃的、虚构的,因而也是从属的、寄生的,应排除在言语行为之外。但是,受德里达启发,我们何不这样来思考这一问题:哲学话语和文学话语都是一种言语行为,都不仅能言有所述,还能言有所为。区别在于哲学总是企图传达真理,而文学却从不讳言自己的虚构性(fictional-ity)。 由于此,文学写作作为一种言语行为便是某种程式或元话语的裸露,是元写作。因而,文学比哲学更具有颠覆性和批判性。
综观德里达的思想脉络,我们不难发现,他对言语行为理论的批判,尤其是对奥斯汀serious/non-serious等级对立的颠倒,是与其一以贯之的哲学诗化倾向相一致的。从根本上讲,解构主义与其说是一股哲学思潮,毋宁说是一种将哲学文学化、诗化的努力。哲学的诗化倾向基本上肇始于尼采,发展于海德格尔,到德里达发展到极至。在海德格尔看来,诗是思的最好体现,诗就是存在。但德里达比海德格尔走得更远,他总是极力抹煞哲学和文学的疆界,抹煞诗与思的疆界,因为任何意义的恒定在场(包括海德格尔的存在)均在延异中被彻底放逐了。德里达对言语行为理论的解构批判所隐含的也正是这种哲学诗化的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