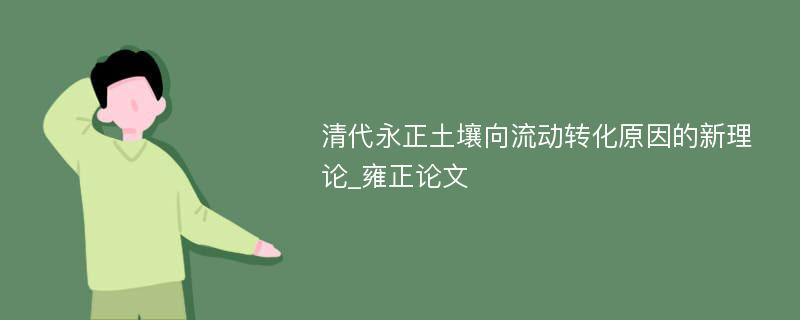
清雍正朝改土归流起因新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起因论文,新说论文,清雍正论文,朝改土归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代雍正朝改土归流无论作为政治制度史,还是边疆民族史,都是一个重要问题,一直为学界所重视。就改土归流起因来说,学界的观点并未统一。关于雍正朝推行改土归流的原因,已有若干综述作了归纳。①由此可知学者的分析是从土司与朝廷两方面以及历史背景进行的。就历史背景而言,学者指出平定三藩之乱后清朝统治在加强、关注西南地区的控制。就土司来说,众口一词认为他们社会经济落后,割据一方,抢夺掳掠,为非不法;而朝廷一方则针对土司的不法与落后,采取措施以维护社会秩序、改变土司地区的落后,控制土司地区,加强中央集权,增加财政收入。 这些论述应当说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但是我们也看到由于受到社会形态进化理论的影响,首先将土司置于落后的方面;受肯定中央集权维护大一统传统的正统论的影响,又将土司置于地方与分权的方面;在史料方面则多相信基于清朝立场而形成的文献,未能充分进行史料批判,不自觉地相信官方立场史料大量对土司的负面记载。如果从今天社会历史理论、民族政治理论讨论提出的问题出发,我们会看到,以往有关改土归流的研究存在着上述问题,需要重新思考,从更客观、公正的立场进行研究。 其实这还是在方法论和叙事逻辑方面的讨论,如果我们深入分析雍正初的历史,充分占有资料分析改土归流的细节,则会发现,以往的研究受到理论思维的束缚与史料占有的制约,与历史的“真实”还存在一定的距离。笔者试图对改土归流的原因重新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 从雍正朝推行保甲、汛塘看改土归流背景 学者论述雍正朝改土归流所指出的土司种种落后、不法的负面问题,其实在此之前长期存在,这些问题在雍正初年并未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而更加严重。同样的问题在康熙朝虽然也有军事征讨、改土归流,但康熙帝并不认为改土归流是最好的办法,而是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总体策略。②雍正帝则与皇父不同,虽然开始继承康熙帝慎重改土归流的政策,但是很快改变初衷,强力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因此,分析改土归流的起因不应该从土司身上找原因,而应当着手分析雍正帝及其政治。 雍正帝即位之初,承袭了康熙帝在土司地区安静为主避免生事的政策。雍正元年(1723)元旦,雍正帝正式登基,遍谕各级官员,讲明对其职责的要求,其中第二项谕巡抚:“云、贵、川、广猺獞杂处,其奉公输赋之土司,皆当与内地人民一体休养,俾得遂生乐业,乃不虚朕怀保柔远之心。嗣后毋得生事扰累,致令峒氓失所。”③经过一年多,雍正帝对于土司的看法有了变化。雍正二年(1724)五月,他谕四川、陕西、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多民族居住省份的督抚提镇等:“朕闻各处土司鲜知法纪,每于所属土民多端科派,较之有司征收正供,不啻倍蓰,甚至取其马牛,夺其子女,生杀任情,土民受其鱼肉,敢怒而不敢言。”④雍正帝分析说:土司敢于恣肆,大率皆由汉奸指使。汉奸或缘事犯法避罪藏身,或积恶生奸依势横行,他们粗知文义,为不法土司主文办事,助虐逞强,无所不至,诚可痛恨。他于是要求:“嗣后督抚提镇宜严饬所属土官,爱恤土民,毋得肆为残暴,毋得滥行科派。”⑤雍正帝不能容忍土司地区的人民受到土司不公正的统治。 雍正帝对于土司看法的转变,与他追求社会治安、维护社会秩序有关。即位之初,他要求科道诸臣凡有所见应竭诚入告,不少给事中、监察御史奏请推行保甲制度,以维护地方社会秩序。雍正帝决心试行保甲,大约在雍正元年八月初五日至八月十四日之间,密谕督抚整饬营伍情弊、举行社仓备荒、设立保甲弭盗,提出用三年的时间推行保甲与社仓,反映了新皇帝教养治国的理念,即用社仓养民,用保甲(包含乡约)弭盗及管理人民。如湖广总督杨宗仁奏折说,他是在九月初三日钦奉密谕督抚设立社仓、保甲以及稽查省府、州、县、卫所设立官兵,其中有关保甲的内容是: 地方设立保甲,乃安民缉盗之第一良策,好府州县官亦有行之者。尔大吏不加奖励,不行者亦不见教诲,所以,怠惰偷安者,将此善政皆忽之不问。今尔督抚当劝勉府州县渐渐学行,不可急迫生事,三年成功不为缓也。⑥ 雍正朝推行保甲分为三个阶段。雍正元年八月至雍正四年(1726)七月三年间是第一阶段,从雍正元年九月开始,各地督抚不断上折向皇帝汇报推行保甲与社仓的情况。雍正四年八月至雍正五年(1727)八月一年间,是推行保甲的第二阶段。雍正四年七月,清廷正式公布了保甲条例。从雍正四年八月起的一年间,清廷要求各省通行保甲制度。雍正五年九月之后进入推行保甲的第三阶段。雍正帝鉴于保甲的完善需要时日,而徐徐责成官员,强调进一步落实保甲职责,于是保甲制度推行全国,普及社会。雍正朝的保甲制度主要形成于雍正四年、五年,各地推行保甲因地制宜,具有自己的地方特色。雍正朝保甲制度的普及,不仅对于清代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首次将国家权力有效深入县级以下基层社会,具有划时代意义。⑦ 正是在推行保甲的过程中,大规模实行改土归流。同时,不仅以保甲维护治安,清朝还依靠军队维护社会治安,即以驻防八旗、绿营控制地方,八旗驻扎于重要城市、军事要地以及交通线上,广大地区则依靠绿营维护。督抚是各省绿营兵的最高长官,提督各省是绿营兵的最高武官,有节制各镇之责。各省绿营的最高编制是镇,其长官为总兵。各镇总兵兼辖协、营,协以副将为长官,营则以参将、游击、都司、守备为长官。各协、营绿营兵除了留守协、营驻地为城防守外,其余被派到该协、营辖区内,划分汛地,分别防守,由千总、把总、外委千总、外委把总等率领分防驻守。各汛之内,除部分兵丁驻汛地防守外,大部分兵丁又被分派到汛防区域内各交通要道、山险要冲之处,设塘驻守。⑧绿营兵是清朝控制全国各地的重要工具,绿营对于基层社会的控制,主要是以汛塘划地设点,扼制道路,形成治安网络。汛塘与保甲是清代为保障社会治安主要采取的两种手段。 雍正初年推行保甲制缉盗,多民族聚居地区的地方官向雍正帝密奏,在临近土司地区盗匪猖獗,土司控制民众,地方社会秩序难以控制,对于土司统治不满。地方官反映的情况一是实情,二是因推行保甲使得问题彰显,这样在康熙朝本已存在的土司问题显露出来。 湖广土司较多,又是力行保甲的地区,有关土司与朝廷社会控制的矛盾突出。雍正二年六月总督杨宗仁奏报:本年四月内荆州府属与土司连界之远安县有匪类郭姓改名朱桃红,诡称法术能治疾病,捏造妖言名号。据他核查,郭姓并未招聚多人,况远安逼近土苗,更须俾知国法。他与巡抚饬各属力行保甲,彼此稽查。⑨八月,杨宗仁又专门上了奏请立法约束楚南苗瑶折。他提出,楚南有苗、瑶各州县,民瑶杂处之地甚多。苗、瑶有生熟之分,其稍纳瑶粮者为熟瑶,其不纳瑶粮者为生瑶。苗、瑶的破坏性很大,如湖南之永、宝、郴、靖等处皆有瑶人,峝数甚多不一,其类情性不伦,全不畏法,惟以抢夺为事。至永州之道州、永明等处,界连广西之富川等处,每粤地苗、瑶越境为非,或有边地光棍勾引生事,捉人勒赎,暗中分肥。又或土人雇瑶佣工,倘在主家物故,苗、瑶借端起衅,不与主家理论,潜入地方,不问谁家坟墓,掘冢取骸而去,便将情由书写一纸,置于竹筒,标插墓侧,名曰仇帖。被害之家执帖控官,地方官无法查拿凶瑶,令落雇苗之主家出银赎骸,相纵日久,野苗竟以此为利薮,近瑶百姓每被捉人抢夺,枕不安席,地方官弥缝粉饰,匿不报闻,恬不知怪,皆由平时防范无术,查察不严之故。因此,杨宗仁建议:“宜敕下督抚,令有猺、苗之各州县,将所属峝寨查明处所,亦照民例编设保甲,每峝寨设练总一名,寨长二名,择知法诚实者以充其役,以总其事,如有干犯,地方官著落练总、寨长拘拿,不致违抗。”⑩至于生苗、生瑶,则严防其出入,杜绝土棍勾通,“敕谕督抚令各州县查明伊等出入必由之路,设立塘汛,加紧查察守御,如两邑交界之处,彼此设汛,互相稽查”(11)。十月,杨宗仁向雍正帝报告说:边苗地方,督令各州县一体清编保甲,互相守望稽查,汛守严密,武弁不时游巡,间有苗性难驯,或挟隙伏草报仇行窃,一旦发觉即令文武协缉追擒。(12) 湖南巡抚王朝恩上任不久,十一月奏陈苗、瑶州县推行保甲。他指出:查苗、瑶原有生熟之分,熟者耕凿饮食与齐民不甚相远,但生性犷野,时有抢夺,贻害地方,究其根源,亦由近峝奸民勾引,或联结婚姻,或暗为主谋教唆构衅,不特同类相残,抑且捉人掘骸,流毒百姓。他建议:饬令有司严禁附近居民,不许与彼结亲并出入峝寨,致起祸端,违禁查解,尽法惩治,则苗、瑶无勾引之人自不敢于生事。查历来原设有土千百户,在总督衙门给发委牌管辖,亦各有寨长分理,似无庸再添练总名色,与齐民一体编查,徒滋纷扰。至于生苗、生瑶散处深岩密箐之中,言语、衣食不与民同,又以熟苗、熟瑶为耳目,时出边界作祟,不法之徒亦有串通熟苗、熟瑶,引线潜入彼地构衅为患者。王朝恩提出,生苗、生瑶出入之处现有附近镇协营汛分防弹压,因此“严饬苗、猺杂处州县实力奉行内地之保甲”。通过这两套系统,“加谨隘口之稽防,则民自为民,生熟苗瑶各以类聚,不致彼此勾引,内外酿祸”。雍正帝朱批称:“此奏甚得中而妥,与朕意甚合,严饬属员实力行之。”(13)雍正二年君臣就湖广推行保甲的讨论,使得雍正帝对于湖广地区土司与苗族、瑶族的情况有了了解,最终采取生熟苗瑶分别处置的办法,生苗、生瑶出入之处用镇协营汛分防弹压,苗、瑶杂处州县推行内地的保甲制。 此时雍正帝对于改土归流仍不赞成。雍正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他在广西巡抚李绂的奏折上批示:“土官相袭已久,若一旦无故夺其职守,改土为流,谁不惊疑?”(14)他希望封疆大吏审择中道而行。 云贵更是多民族聚居、土司众多的地区,雍正初年也在推行保甲。云南巡抚杨名时在雍正元年十二月接到设立保甲的谕旨,他奏报说:“于府州县各官进见时,宣播皇上弭盗安民德意,令其编立门牌,十家为甲,十甲为保,互相稽察,切戒其扰累小民,随宜措置。云南多彝猓,村寨零星散居,难以十家百家为限,只可就近联络互查,总以简易便民为主。”(15)云贵总督高其倬也报告了编保甲的情形。(16)云南布政使李卫报告了省界接壤地区多民族杂居,疆界彼此不清,难于管理。他说:湖南之于贵州广西,广西之于云南,云南之于四川,广东之于福建,地处边远,汉苗杂居,其间往往有地数百里、千余里并未明隶某省管辖,即当年绘舆图之钦差亦不曾深入其地,遗漏不可胜数,平居无事,两省皆置之度外,一旦匪类窃发,有争杀抢掠之事,则两省互相推诿,倘其中可以取利,则两省文武官代为之争,甚非体统,更可患者,其地既为可黔可楚之地,则其民即为非黔非楚之民,保甲不得而编,汛兵不得而防,钱粮不得而征,奸恶以是为盘踞之窟,盗贼以是为逋外之薮,“以致幅员之内竟有教化不及之地,刑政莫加之民”(17)。即言之,贵州与湖南交接地区并未纳入到朝廷的保甲、汛兵控制之内。 上述资料表明,雍正初年在推行保甲、汛塘以控制地方社会的过程中,雍正君臣将未能直接控制湖广、云贵等南方地区土司作为严重的问题提出,土司所在地区的争杀抢掠成为缉盗的对象。由于土司的存在,缉盗事权不一也是面临的突出问题。如何处置土司,成为雍正君臣非常关心的问题。 二 从贵州长寨事件看改土归流起因 面对贵州的土司问题,雍正帝指示云贵地方官剿抚并用,治理当地严重的秩序失控问题。雍正三年(1725)二月初十日云贵总督高其倬、贵州巡抚毛文铨、提督赵坤等接到皇帝谕旨:黔地诸苗仲苗最为不法,仲苗及红黑诸苗与其有事而剿抚,不如未事而筹划。要求一二年间,内地之兵民与向化之苗倮皆畏威怀德,感激思奋。谕旨的核心是要求地方官未雨绸缪,对于为恶土司先以招抚,继以剿捕。(18) 值得注意的是,雍正三年四月云南将威远土州改土归流。雍正三年正月二十六日,云贵总督高其倬奏陈元、二两年历奉密谕暨折奏事件办理情形,讲到保甲说: 云南民杂猓夷,地多山箐,臣择蒙化、和曲、安宁、陆凉、赵州、昆明、太和、永平、浪穹、通海十府州县先令试行,行之有益,再令各州县照依其法,次第举行。今所行各属俱已举行,已比前少有约束,民亦无不便之处,俟至今年秋冬,臣再令未行各州县酌量举行。又元江、新平二处讨保之野贼虽已剿除,然彼地猓民染于故习,恐暗纠人众出外妄为,臣令元江、新平将各村寨仿保甲之意,编开人户口数,令地方官于九、十、十一、十二等月不时巡查。如出外之人多,即是讨保,务行根究,以杜奸宄。至贵州沿大路村寨及各州县,俱已行令地方官编立,现俱举行保甲。至于苗寨不便举行,只在文员尽心拊循,武员加意振勉,自可消弭抢劫。臣惟一意于整顿属员,以期安辑地方耳。(19) 该折所讲云南、贵州推行保甲消弭苗倮“讨保”,即成群外出抢劫之习。 此后,高其倬建议采取设立防汛、改土归流,治理云贵苗倮。他说:云南苗倮,平时踞元江、新平之间,官兵剿捕则遁入威远、普洱、茶山等处,广袤二三千里,难以控制。请将威远土州改土归流,设抚夷清饷同知一员、经历一员、盐井大使二员,于猛班设巡检一员,分理民事。再添设普威一营,置参将一员,驻扎普洱;守备二员,一驻威远,一驻茶山,千总四员,把总八员;兵丁一千二百名,分汛防守。此外,针对“猓夷有讨保之习,勒索银两,骚扰地方。请于九龙江口夷人出入之处,设立防汛,照山海关例给以印票,并将所属村寨编立里甲户口,以凭稽察。其夷人子弟有志读书者,准其于元江附考,元江府入学额数应加取二名。田亩照地肥瘠酌定额赋,土地可辟者见今开垦,照定例水田六年、旱田十年升科。至于土官方普二姓纠众骚扰,所有二姓土巡检承袭之处,应永远停止”(20)。兵部建议听从所请,得到了雍正帝的赞同。这是雍正朝第一次改土归流,所采取的措施,成为以后改土为流的先例。 雍正三年发生了长寨事件。云贵总督高其倬奏准,在贵州贵阳府广顺州仲家族村寨建立营房,增置防汛。当即在宗角盖造完毕,及至计划在长寨施工,该寨土舍(21)用大石头堵塞路口,不许清军建房进驻。署理贵州巡抚石礼哈、提督马会伯先后提出用兵要求,雍正帝认为二人所奏有理,然而担心他们难当此任,告诫他们不可轻举妄动;又怕石礼哈过于勇往直前,派何世璂为贵州巡抚。何世璂主张招抚,不见效验。三年冬,任命鄂尔泰为云南巡抚管云贵总督事,召高其倬回京,进一步了解云贵土司情况,并征询他的意见。高其倬主张征剿,雍正帝遂下旨询问鄂尔泰。雍正四年春,广顺土舍焚烧清军营房,鄂尔泰看到事态严重,四月请求用兵,雍正帝大加赞赏。鄂尔泰在长寨用兵中,深感土司难以控制,应筹措一劳永逸之法,九月他正式提出改土归流的建议,方法是计擒为上策,兵剿为下策;令自投献为上策,勒令投献为下策。对于投献者,收其田赋,稽其户口,仍量予养赡,授以职衔冠带终身,以示鼓励。他的改流策略,既要用兵,又不专恃武力,争取波及面小,尽量减少阻力,以便尽快奏效。雍正帝批准了鄂尔泰的建议,决定改土归流。(22) 因此,高其倬在长寨建房增置防汛引起土司抵抗,长寨事件是引起后来改土归流的导火索。鄂尔泰很快平定长寨,设立长寨厅(今长顺县)。长寨的用兵是雍正朝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开端。(23) 雍正四年十月,雍正帝授鄂尔泰云贵总督,加兵部尚书衔,又将广西从两广总督辖下划归云贵总督管理。五年十二月,雍正帝正式提出云南、贵州、四川、两广以及湖南、湖北的土司改土为流问题: 谕兵部:向来云贵川广以及楚省各土司,僻在边隅,肆为不法,扰害地方,剽掠行旅。且彼此互相仇杀,争夺不休,而于所辖苗蛮尤复任意残害,草菅民命,罪恶多端,不可悉数。是以朕命各省督抚等悉心筹画,可否令其改土归流,各遵王化。此朕念边地穷民皆吾赤子,欲令永除困苦,咸乐安全。并非以烟瘴荒陋之区,尚有土地人民之可利,因之开拓疆宇,增益版图,而为此举也。(24) 从雍正帝提出改土归流的理由来看,土司的问题在于破坏地方社会秩序,表现在剽掠行旅,彼此互相仇杀,草菅民命,认为改土归流可以使土司地区人民永除困苦,各遵王化。声明绝不是贪图土地人民,借此开拓疆宇,增益版图。这些理由以往常被作为雍正改土归流的原因,其实掩盖了雍正推行改土归流的直接原因。同时,也掩盖了土司问题很多情况下是地方官贪索造成的事实。王钟翰先生指出:“至若事件之起因,诬少数民族以劫杀、以抗命,不过借为口实。”(25)雍正六年(1728)十二月,雍正帝特授鄂尔泰为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总督。鄂尔泰受到雍正帝的充分信赖,大力推行改土归流。 由上可知,从贵州长寨事件看改土归流,起因于高其倬在长寨建房增置防汛引起土司抵抗。其他资料也可证明清朝针对土司设置汛塘的想法,如川陕总督岳钟琪奏称: 查普雄即梁山(凉山——引者注,下同)居云贵四川三省之中,横亘千余里。自汉唐以来,三省沿边一切土司敢于负固者,皆倚此为退藏之地,一经追捕,则携族遁入,莫可如何……将四川梁山收入内地,相其扼要,安设营汛,收其贡赋,以资兵饷。再招善于开垦之楚民,广推屯种,则不数年,居民稠密,势同内地,不特国势加增,即沿边各土司转皆腹里受制,将来改土归流,俱为顺易。(26) 岳钟琪将安设营汛作为控制土司的主要手段,为改土归流打下基础。在交通要路设置汛塘,符合雍正帝的想法。不过事实证明,在土司地区设置汛塘,会引起土司的不满与反对。 三 改土归流后行保甲、设汛塘可证其初衷 云南巡抚管云贵总督事鄂尔泰对西南土司用兵以及进行改土归流,同时推行保甲制度。雍正四年八月初六日,鄂尔泰上奏,言及保甲问题: 窃照流、土之分原以地属边徼,入版图未久,蛮烟瘴雾,穷岭绝壑之区,人迹罕到……然所以清盗之源者,莫善于保甲之法。臣屡与督臣杨名时、抚臣何世璂熟商酌议,拟立规条,行之两省,及阅邸钞,知荷蒙圣恩,著九卿详议具奏。臣等伏候奉旨,部行到日,当即颁行一体遵奉外,按保甲之法,旧以十户为率。云贵土苗杂处,户多畸零,保甲之不行多主此议。不知除生苗外,无论民彝,凡自三户起皆可编为一甲,其不及三户者令迁附近地方,毋许独住,则逐村清理,逐户稽查,责在乡保甲长。一遇有事,罚先及之。一家被盗,一村干连,乡保甲长不能觉察,左邻右舍不能救护,各皆酌拟,无所逃罪。此法一行,则盗贼来时,合村百姓鸣锣呐喊,互相守望,互相救护,即有凶狠之盗,不可敌当,而看其来踪,尾其去路,尽在跟寻访缉,应亦无所逃。(27) 雍正帝批示兵部、刑部、都察院各议具奏。鄂尔泰依据云贵土苗杂处、户多畸零的情形,为推行保甲而建言献策:“自三户起皆可编为一甲,其不及三户者令迁附近地方,毋许独住,则逐村清理,逐户稽查。”(28)同年底,内阁等衙门议核鄂尔泰疏言诸事,其中有:“清盗之源,莫善于保甲,云贵苗民杂处,户多畸零,将零户编甲,独户迁移附近以便稽查之处,行令该督悉心筹画,饬令该地方官善为奉行,安置得法。”(29)请求行令云南、贵州、四川、广西、湖南五省一并遵行,雍正帝从之。清廷要求在南方少数民族聚居区一体编查保甲,且鉴于少数民族居住分散的情况,采取缩小编甲规模的灵活措施。 在处置长寨苗人问题上,鄂尔泰的《长寨示稿》保留了有关保甲问题的记载。其内容是:“现委员遍谕苗民,各照祖宗姓氏,贯以本名,造报户口清册,编立保甲。”(30)雍正四年九月十九日,鄂尔泰提出具体的措施:“既先之以重兵弹压,即继之以清册稽查,按其户口,照汉民以行保甲;清其田亩,借赋役以为羁縻。不独户与户环相连保,并寨与寨互相甘结,则容一凶苗,而群苗为之获罪;隐一凶寨,而各寨为之靡宁,势不能不互相举首,交为盘查。”(31)鄂尔泰对西南土司用兵以及进行改土归流时,推行了保甲制度。雍正五年正月二十五日,鄂尔泰奏治理“顽苗”问题时提到:“况保甲之法已行,则乡保头人自应稽查,地方邻佑自应首告,使皆各有责成,违者并坐。”(32)三月,兵部议覆鄂尔泰疏奏经理长寨等仲苗事宜,其中有:“狆苗姓氏相同者多难于分别,应令各照祖姓造报户口清册,编立保甲,其不知本姓者代为立姓,以便稽察。”(33)帝从之。六月二十七日鄂尔泰说:“查生苗来归,应示羁縻以计长久,科粮务须从轻,户口定应清造,夷民半无姓氏,名多雷同,日后难以稽查,现在恐有重复,复经札致提臣,并饬知刘成谟、官禄等,再加查明,更定姓名,编立保甲,汇造清册,以凭具题报部。”(34)这些记载表明了当时实行保甲制度管理苗民的情形。 云贵改土归流地区继续推行保甲制度。雍正五年九月十六日,鄂尔泰奏称:“向经归顺各苗悉与汉民一体严立保甲并取具不敢容奸容贼甘结”(35),说明苗汉都实行保甲制。此后不断在新附苗民中间实行保甲,十二月十三日,鄂尔泰奏称安顺镇宁定番广顺等府州边界地方生苗皆愿内附,“已檄令文武各员附载版图,编入保甲,各加奖赏安插讫”(36)。六年十月二十日鄂尔泰又奏:“据镇远府知府方显呈报,分遣各土官、土舍以及效用人等分道前往招抚,随抚得清水江一带生苗共一十六寨,计一千五百九十户,男妇五千七百六十七名口,业经编立保甲,理合造册呈报。”(37)七年(1729)三月初三日,云贵乌蒙总兵刘起元奏陈地方改土归流事:“请照边地充发流徙之例,遇有缘事充发之犯,仰请发乌安插,取其地方官收管,编入保甲,与民一例输差。”(38)雍正帝批示廷臣详议。七月,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奏:“贵州高耀等寨生苗秾狆等俱向化输诚,陆续投见提臣杨天纵……今将认纳粮赋数目造具清册,各寨户口编入保甲,永为良民。”(39)鄂尔泰又疏报:“都匀各寨苗民输诚纳赋,编入保甲。”(40)雍正帝命下部知之,并说:“都匀各寨苗民向化投诚,认纳粮赋,编入保甲永为良民,甚属可嘉。”(41)闰七月,鄂尔泰奏报:“黔省边境生苗剿抚兼施,俱已向化投诚,认纳钱粮,听编保甲,愿为圣世良民”(42)。贵州少数民族编入保甲完毕。九月十九日,鄂尔泰针对御史龚健扬所奏设立乡官的建议,认为多此一举,举例说:“如遍行保甲,则原有户口门牌,细开名数,并记簿稽察之例。”(43)指出保甲制度实行以来已较为完善。八年(1730)五月二十六日,鄂尔泰奏请添设云南分巡迤东道管理地方事宜,说:“至于劝农课田,勘河查路,稽察保甲,严拿匪类,宣讲《圣谕广训》,晓谕《大义觉迷录》,俱令不时督察。”(44)其口吻视稽查保甲为已有之事。 清廷在改土归流地区普遍设立保甲。有的地方是十户立一头人,十头人立一寨长。又在黔东南正式设立古州、台拱、清江、都江、丹江、八寨等六厅,分属黎平、镇远、都匀三府。(45)雍正帝在土司地区推行保甲的设想得以实现。 清朝统治力量进入土司地方以后,安营设汛,建立军事据点。雍正年间,在黔东南新附苗区共设置9个营,29个汛,78个塘,驻兵六千多名,随后又增加到一万五千名。另一方面,派驻流官,建立地方政权。这些新设流官有:雍正四年,设长寨同知;六年设八寨同知、丹江通判;七年设古州同知、都匀府理苗同知、都匀通判、镇远府理苗同知、黎平府理苗同知;八年设清江同知;九年设都江通判;十年设归化通判;十一年设清江通判、台拱同知;等等。雍正帝在土司地区设置汛塘的设想也得以实现。 学者对清代绿营汛塘的设置过程有过研究,证明汛塘作为一种制度在云南大多数地区应继清顺治十六年(1659)废关哨之后建立起来,汛塘分布情况较大改变发生在雍正年间。随着改土归流的进行,清政府对改土归流地区派驻了绿营兵。“雍正时期云南以分汛防守的绿营兵有了较大增长,达到20780名,占当时云南绿营兵总数47980名的43%,较康熙二十年三藩之乱平定后云南分置于汛塘的绿营兵13795名增加了6985名。”(46)同时,云南腹里发达地区绿营兵额的下降和边疆地区的绿营官兵分布数的上扬,成为这一时期云南绿营兵分布的最大变化,“标志着封建王朝对云南的统治已由传统的以腹里中心区向全省各地扩展,中央王朝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大大增强”(47)。 清军添设营汛,扩大了驻防。新设的镇协有,云南的乌蒙镇、昭通雄威镇及普洱元威镇,贵州的古州镇、台拱镇,广西的右江镇,湖广则增添了龙顺协、永绥协。 清朝通过设置保甲、汛塘,有效地控制了基层社会。具体情况如湖广地区,湖广总督迈柱密陈永顺、保靖、桑植三处改土归流善后措施:“其建设营制,缘地方广阔,必声息联络相通,分布管辖,乃资弹压。”(48)具体如“六里地方幅员千有余里,层峦叠嶂,大箐深林,其中苗巢约计不下二百寨,自十户以至百十户不等,合计则顽苗不下五六万之众。开辟之初,必须安设官兵,少则不足以资弹压,多则钱粮又复浩繁。”(49)镇营之下则分汛设防。再如云贵乌蒙地区,“兹蒙改土设镇安兵,所有营制官兵统辖几宜以及汛守设防处所,久蒙督臣鄂尔泰裁画题定,足称星罗棋布矣”(50)。同时乌蒙地区还推行了保甲制:“嗣后应请于乌治之东南西北设为四乡,将现在各土目名色削去,尽数编入乡甲之内。另择其彝人中忠厚诚实者充当乡约、保长,以资约束,务使斯民尽属流管,赋役不由彼出,使华风日炽,而彝俗亦可渐消。”(51)由此可见,清延安营设汛,建立军事据点。 西南改土归流后,少数民族苗人等亦被要求薙发,四川永宁协副将张瑛条奏改土归流事宜中有“已归流之土民宜从国制”(52)一条,建议归流百姓“宜令剃头改装,分设里长甲首,令百姓轮流充当”(53)。云贵总督鄂尔泰说当时投诚各寨及土民都有数千人自愿剃头,并认为“抚夷之法,须以汉化夷,以夷治夷”(54)。这反映了改土归流实现国家认同的目的。 四 结语 综上所述,当我们利用大量的雍正朝朱批奏折史料考察改土归流问题时,发现了改土归流与推行保甲、缉盗、设置汛塘的直接关系,看到改土归流是在雍正初年新政改革的背景下出现的。如果要深入认识雍正朝的改土归流,应该深入了解雍正朝以及清史。以往众多的研究首先从理论出发,套用社会进化、集权有利的模式看待改土归流,将历史问题简单化,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即使从长期的观点来看,改土归流有一定程度的历史必然性,然而雍正朝改土归流的起因确实在于该朝历史的偶然性,我们看到的是国家权力、皇帝意志对于地方社会的干预,而不是地方社会的自变。固定理论模式很难说明历史的复杂性,这就是历史学对于社会科学理论的制约,历史学的特性即在于此。 ①刘桂林《近十年来雍正及其时代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4期)介绍了改土归流问题;贾霄锋《二十多年来土司制度研究综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4期)的第四部分是“有关改土归流的研究”;秦中应《建国以来关于“改土归流”问题研究综述》(《边疆经济与文化》2005年第6期)也有涉及。 ②常建华:《确立统治与形成秩序:清顺治康熙时期对南方土司的处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2012年号,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1年。 ③《清世宗实录》卷三,雍正元年正月辛巳朔,《清实录》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第70页。按:清人记载少数民族族称使用“犬”字偏旁多有侮辱性,如猺、獞、狆、猓等,本文引文依旧,以存当时真实情况。但是转述清朝官员所言少数民族族称时,则改写“人”字等偏旁,使用瑶、僮(壮)、仲、倮等字,以示尊重少数民族。 ④《清世宗实录》卷二○,雍正二年五月辛酉,《清实录》第7册,第326页。 ⑤《清世宗实录》卷二○,雍正二年五月辛酉,《清实录》第7册,第326页。 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以下简称《汇编》)第4册,第121号《湖广总督杨宗仁奏覆历奉密谕遵办情形折》,雍正二年十二月初十日,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61页。 ⑦常建华:《雍正朝保甲制度的推行——以奏折为中心的考察》,《故宫学刊》总第10辑,北京,故宫出版社,2013年。 ⑧秦树才:《清代云南绿营兵研究——以汛塘为中心》,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页。 ⑨《汇编》第3册,第162号《湖广总督杨宗仁奏陈力行保甲稽查匪类并缴朱旨折》,雍正二年六月二十五日,第242页。 ⑩《汇编》第3册,第296号《湖广总督杨宗仁奏请立法约束楚南苗瑶折》,雍正二年八月初四日,第401页。 (11)《汇编》第3册,第296号《湖广总督杨宗仁奏请立法约束楚南苗瑶折》,雍正二年八月初四日,第401页。 (12)《汇编》第3册,第652号《湖广总督杨宗仁奏覆安仁知县田仁亏空库银一案等事折》,雍正二年十月二十日,第855页。 (13)《汇编》第3册,第717号《湖南巡抚王朝恩奏陈苗猺州县推行保甲折》,雍正二年十一月初四日,第928页。 (14)《朱批谕旨》卷二二上,朱批李绂奏折,《钦定四库全书荟要》,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影印本,2005年,第2册,第386页。 (15)《汇编》第4册,第8号《云南巡抚杨名时奏覆两年内奉到密谕逐一办理情形折》,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第14页。 (16)《汇编》第4册,第289号《云贵总督高其倬奏陈雍正元二两年历奉密谕暨折奏事件办理情形折》,雍正三年正月二十六日,第364页。 (17)《汇编》第4册,第357号《云南布政使李卫奏陈筹画海防省界暨密折防弊等事折》,雍正三年二月十二日,第444页。 (18)《汇编》第4册,第397号《贵州提督赵坤奏钦遵上谕整饬苗务情形折》,雍正三年二月二十三日,第496页。 (19)《汇编》第4册,第289号《云贵总督高其倬奏陈雍正元二两年历奉密谕暨折奏事件办理情形折》,雍正三年正月二十六日,第364—365页。 (20)《清世宗实录》卷三一,雍正三年四月乙未,《清实录》第7册,第482页。 (21)管理少数民族村寨的头目,见李世愉《清代土司制度论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89页。 (22)冯尔康:《雍正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33—336页。王钟翰:《雍正改土归流始末》,《清史新考》,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05—206页。 (23)冯尔康:《雍正传》,第336页。 (24)《清世宗实录》卷六四,雍正五年十二月己亥,《清实录》第7册,第986—987页。 (25)王钟翰:《雍正改土归流始末》,《清史新考》,第197页。 (26)《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6辑,川陕总督岳钟琪《奏报添设营汛折》,雍正四年十月十七日,台北,“故宫博物院”印行,1978年,第754页。 (27)《汇编》第7册,第603号《管云贵总督事鄂尔泰奏陈宜重流官职守宜严土司考成以靖边地管见折》,雍正四年八月初六日,第851—852页。 (28)《朱批谕旨》卷一二五之二,朱批鄂尔泰奏折,第6册,第43页。 (29)《清世宗实录》卷五一,雍正四年十二月戊寅,《清实录》第7册,第772页。 (30)《汇编》第8册,第507号《云贵总督鄂尔泰奏报审讯抗阻官兵建营仲苗暨川贩汉奸情由折》附件,第701页。 (31)《汇编》第8册,第84号《云南巡抚鄂尔泰奏遵旨剿办不法苗人折》,第112页。 (32)《朱批谕旨》卷一二五之三,朱批鄂尔泰奏折,第6册,第77页。 (33)《清世宗实录》卷五四,雍正五年三月甲寅,《清实录》第7册,第827页。 (34)《朱批谕旨》卷一二五之四,朱批鄂尔泰奏折,第6册,第130页。 (35)《朱批谕旨》卷一二五之五,朱批鄂尔泰奏折,第6册,第149页。 (36)《朱批谕旨》卷一二五之五,朱批鄂尔泰奏折,第6册,第173页。 (37)《朱批谕旨》卷一二五之八,朱批鄂尔泰奏折,第6册,第286页。 (38)《汇编》第14册,第592号《云贵乌蒙总兵刘起元奏陈地方政务管见九条折》,雍正七年三月初三日,第780页。 (3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起居注册》雍正七年七月初三日,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4册,第2933页。 (40)《清世宗实录》卷八三,雍正七年七月戊午,《清实录》第8册,第110页。 (41)《雍正朝起居注册》雍正七年七月十五日,第4册,第2956页。 (42)《雍正朝起居注册》雍正七年闰七月初七日,第4册,第3001页。 (43)《朱批谕旨》卷一二五之十二,朱批鄂尔泰奏折,第6册,第411页。 (44)《汇编》第18册,第573号《云南总督鄂尔泰奏请添设云南分巡迤东道管理地方事宜并以元江知府迟维玺补授折》,雍正八年五月二十六日,第774页。 (45)张捷夫:《关于雍正西南改土归流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第5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77页。关于改土归流后设置保甲,王钟翰先生指出:“惟封建统治之策,莫善于保甲,而旧以十户为率。”鄂尔泰以云、贵土苗杂处,户多畸零,倡议三户可编一甲。(王钟翰:《雍正改土归流始末》,《清史新考》,第216页)李世愉先生也指出清廷“在所有改流地区推行保甲制度”。(李世愉:《清雍正朝改土归流善后措施初探》,《民族研究》1984年第3期) (46)秦树才:《清代云南绿营兵研究——以汛塘为中心》,第128页。按:增加的绿营兵名数误为“6685”,径改。 (47)秦树才:《清代云南绿营兵研究——以汛塘为中心》,第129页。 (48)《汇编》第14册,第79号《湖广总督迈柱密陈永顺、保靖、桑植三处改土归流善后事折》,雍正六年十二月初二日,第107页。 (49)《汇编》第14册,第80号《湖广总督迈柱等奏覆不宜急于开辟六里红苗地方情由折》,雍正六年十二月初二日,第108页。 (50)《汇编》第14册,第592号《云贵乌蒙总兵刘起元奏陈地方政务管见九条折》,雍正七年三月初三日,第776页。 (51)《汇编》第14册,第592号《云贵乌蒙总兵刘起元奏陈地方政务管见九条折》,雍正七年三月初三日,第778页。 (52)《朱批谕旨》卷一二五之三,朱批鄂尔泰奏折,第6册,第91页。 (53)《朱批谕旨》卷一二五之三,朱批鄂尔泰奏折,第6册,第91页。 (54)《朱批谕旨》卷一二五之三,朱批鄂尔泰奏折,第6册,第91页。标签:雍正论文; 改土归流论文; 鄂尔泰论文; 清朝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贵州民族论文; 历史论文; 高其倬论文; 绿营兵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