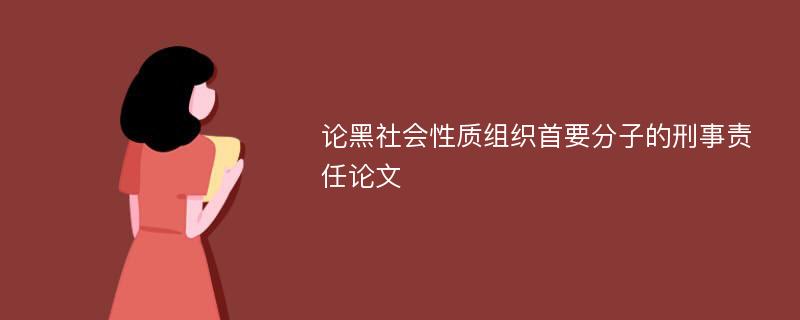
论黑社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的刑事责任
陈 梅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梧州学院 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广西 梧州 543000)
摘 要: 黑社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的刑事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认定不一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刑法总则第二十六条规定虚置的问题;二是对黑社会性质组织所犯的全部罪行认定逻辑不精细问题。黑社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的处罚在德日、英美刑法理论中都有较大的争议,其中共谋共同正犯理论、正犯背后的正犯者理论以及共谋犯理论是相对主流的学说,这些学说在我国的语境下既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也提示了在实现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目的时,应当坚守刑法保障人权核心价值的要求。确定黑社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的刑事责任范围需要注意其罪过的边界以及其组织、领导行为的认定。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的刑事责任程度需要注意“从严处罚”原则与“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的协调,并应在具体的情节中考虑首要分子的责任程度,而不是一概对其追究“主犯”的最重的刑事责任。
关键词: 黑社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刑事责任
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一直是严重危害社会正常秩序、损害人民群众安全感的恶性犯罪。扫黑除恶工作中,如何依法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既关乎到能否有力打击震慑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又关乎是否严格依法办案,确保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对黑社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的惩治,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着认定不统一的问题。尤其是对黑社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并没有实际参与,甚至没有具体组织、策划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的犯罪,能否归责给黑社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无论在实务界还是理论界都有很大争议。明确黑社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的刑事责任,即是在理论上对共同犯罪相关理论的进一步探究,也有助于为司法实践提供理论指导,解决“同案不同判”问题,强化依法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力度。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我法国刑法总则第二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可知,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首要分子,应按照其组织、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全部罪行处罚。虽然刑法第二十六条、第九十七条规定的表述有所不同,但这只不过因为首要分子不仅包括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还包括聚众犯罪中的首要分子,出于用语的精确性,导致了表述中的细微差异。真正成为问题的是:如何认定“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对于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来说,即为如何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全部罪行?
对此,有学者于2014年进行了一定范围的实证研究,发现司法实践中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全部罪行”的认定不一现象较为突出。还有学者从个案角度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发现同一黑社会性质组织中存在多个首要分子的情况下,各首要分子的刑事责任范围并不完全相同等问题。[1]这一问题是否仍旧存在呢?笔者通过对近两年有关于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裁判文书进行搜集、分析,发现司法实践中对黑社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刑事责任的认定仍然存在着标准不够明确、统一的问题。这一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司法实践中对刑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虚置的问题。在本文所搜集的近两年的相关裁判文中,存在着部分司法判决并未在判决书中运用刑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处罚规则,而是将黑社会性质组织所犯的各罪行打散、还原至各个具体犯罪人处,重新组合成各共同犯罪,再以一般共同犯罪的基本原理认定各项罪行主体。其逻辑思路大致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事实→各犯罪、违法行为的犯罪、违法事实→认定组织、领导者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对其具体组织策划、指示以及参与实施的相关犯罪认定构成相应犯罪;认定参加者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对其具体实施的犯罪认定构成相应犯罪,并对是否构成共同犯罪予以说明。有学者就指出:“《刑法》第26条‘集团犯的全部罪行’的规定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被消解,即该规定在‘涉黑’犯罪的司法实践中事实上被排除适用。”[1]为此,该学者主张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以“个人罪行”替代“集团罪行”。但此种观点并不符合我国刑法的明文规定,也与从严惩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刑事政策不相符合。并不能因为司法实践中有这样的现象,就轻易动摇刑法既有的规定。理论要为实践服务,不仅仅只体现在为实践中即存的现象进行合理性说明,更重要的是需对实践中的现象进行理性化、规范化的反思,并构建或完善相应的理论,更好地指导实践。
二是对黑社会性质组织所犯的全部罪行认定逻辑不精细问题。司法实践中还有一种做法是,在判决中对刑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予以明确并适用。但在适用的过程中,部分判决存在着逻辑环节缺失的问题。在对黑社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以组织所犯的全部罪行追究刑事责任时,应当遵照的逻辑思路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事实→各犯罪、违法行为的犯罪事实→犯罪、违法行为的犯罪、违法事实属于/不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所犯→首要分子按黑社会性质组织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参加者按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这其中,非常关键的逻辑环扣在于犯罪是否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所犯的认定,但在部分判决中,这一环节的认定被略过。例如,在(2014)鄂刑初字第00129号刑事判决中,法院认为“关于被告人蒋某是否构成故意伤害罪、聚众斗殴罪,被告人邹某某是否构成寻衅滋事罪的问题。经查,被告人蒋某、邹某某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上述三起犯罪,但二人是黑社会组织的组织、领导者,不管其是否知晓或者直接指使,均按照组织所犯的全部罪行定罪处罚。”① 案例来源为北大法宝网:http://www.pkulaw.cn/case/pfnl_a25051f3312b07f3214b072cdb866569354298a6c3d55814bd fb.html,2018-07-07. 又如,在(2015)郑刑一终字第241号刑事判决中,法院认为:“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领导者即温某某1、张某某2应当按照其所组织、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所犯的全部罪行进行处罚,即二人应当对2014年4月之后组织成员所犯全部强迫交易罪负责。”② 案例来源为北大法宝网:http://www.pkulaw.cn/case/pfnl_a25051f3312b07f3440743bb00a9e263bbc189e5e3e69f9abdfb.html,2018-07-07. 组织成员所犯的罪行就一定等同于组织所犯的罪行吗?这一问题的当然不是必然的,为此,就不能省略对组织成员所犯罪行是否为组织所犯罪行的判断环节。
孙子认为:“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在篮球场上,优势往往掌握在拥有主动权的一方。想要战胜对手,就应当让对方跟着自己的节奏和打法走。他认为“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画地而守之,乖其所之也。”在篮球场上,也应当善于通过隐藏实力和技战术的变化来迷惑对手,调动对手。使对方疏于设防,疲于奔命并暴露弱点,从而“以利动之,以卒待之”。
上述问题说明,司法实践中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刑事责任的认定仍较为混乱,理论界对这一问题也还仍处于争论当中。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黑社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的处罚依据出发,探清其理论根基。需要注意的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并非一般的犯罪集团,更不是普通的共同犯罪,其自身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处罚上的特殊性,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降格为普通的共同犯罪,适用一般共同犯罪的理论显然违背了立法本意,也不符合当前的社会现实环境需要。为此,对黑社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刑事责任的研究既要从共同犯罪的基础理论中进行深入探索,又要注意到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本身不同于一般共同犯罪的特质,及因此可能会对传统共同犯罪理论带来的必要突破。
试验所使用的设备为:AGS-X10KN拉伸机进行相容性试验有两个目的:一是将标准橡胶试样与润滑剂进行静态浸泡试验,以测试橡胶试样硬度、体积及拉伸性能等特性的变化,得到在不同环境下,不同润滑剂对橡胶密封材料性能的影响规律;二是提供经润滑油浸泡过的O型圈,以分析O型圈不同特性的变化对气缸工作性能的影响。本次相容性试验的橡胶材料有两种类型,分别为标准哑铃状橡胶试样及O型橡胶圈。由于试验气缸中所使用的O型圈材料均为丁腈橡胶,因此相容性试验中的橡胶材料也选用丁腈橡胶。根据相容性试验标准以及可靠性试验标准,每组试验的橡胶试样包括3个标准哑铃状试样以及5个O型圈。
二、黑社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的处罚依据
黑社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首先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如果其同时参与、实施了其他犯罪,按照一般共同犯罪的理论,对其参与、实施的犯罪要承担刑事责任已经有很成熟的理论依据。问题在于,当黑社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并没有实施实行行为时,其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应在多大范围内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这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形:一是黑社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具体组织、策划、指挥,由其他成员实施了犯罪;二是黑社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没有具体组织、策划、指挥,但事前知情并默许组织成员实施了犯罪;三是黑社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没有组织、策划、指挥,事前不知情,组织成员实施了犯罪。在上述几种情形下,黑社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都没有实际分担组织成员的犯罪实行行为,其是否要承担刑事责任,甚至是承担主犯的刑事责任,因为根据我国刑法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是主犯。这就需要在理论上探析在共同犯罪中,只是进行了组织、策划,未实际实施实行行为的人承担责任的方式及其依据。
(一)德日学说之考察
在德日刑法中,由于采用的是正犯与共犯相分离分离的体系,要将并未实施符合构成要件行为的犯罪的组织、策划者作为正犯处理,与其以“构成要件为中心”构建起来的传统正犯理论体系相违背,但为了惩治性质恶劣的犯罪组织、策划者,日本刑法理论发展出共谋共同正犯理论,德国刑法则发展出正犯背后的正犯理论。这两种理论都是对传统正犯认定标准——实施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进行的突破,以达到将犯罪的组织、策划者作为正犯处罚的目的。
1.共谋共同正犯理论
德国并没有类似于日本的共谋共同正犯理论,其解决实行犯的“幕后人”的刑事责任问题通过的是“正犯背后的正犯者”(也被翻译为实行人背后的实行人)理论,即控制犯罪理论。根据罗克辛教授的观点,幕后人可以在三种情况下,并不直接插手犯罪事件,但可以控制这个事件:一是人们能够强迫实施人;二是人们能够欺骗实施人;第三则是罗克辛提出的新的想法——命令国家机器。国家机器在没有强制与欺骗的情况下,也要确保命令得到实施,因为这种机器本身就保障了执行。这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实施犯罪的人在国家机器的组织框架下如同螺丝钉一样是可替换的。典型的判例如1994年的柏林墙案。在这个案件的判决中,前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防卫委员会”的成员,被判定是杀害柏林墙附近“共和国逃亡者”的间接实行人。虽然是柏林墙附近的边防士兵开枪射杀了“共和国逃亡者”,并在柏林墙附近埋设炸弹导致了逃亡者的大面积伤亡,但边防士兵是执行“国家安全防卫委员会”的命令。虽然,在德国这种“正犯背后的正犯者”理论也受到了理论界的一些批评,但在司法实务界,这种理论的适用逐渐从利用国家机器控制实行人,扩展至其他的领域。在《联邦最高法院刑事判例集中》,第五审判委员会认为:“一个被这样理解的间接实行人,不仅仅是出现在滥用国家权力的场合,而且在类似黑社会组织犯罪的情况下,也要考虑。”[2]42这就表明,在黑社会组织犯罪的情形下,也存在有利用组织权力的情形,组织、领导者即处于正犯背后的正犯者地位。
虽然有批评者对共谋共同正犯理论进行了抨击,但在解释集团犯罪首要分子刑事责任的问题上,共谋共同正犯理论还是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尤其是松村格教授将系统论引入共谋共同正犯理论中,进行了深入论述。① 具体论述可见童德华. 正犯的基本问题[J]. 中国法学,2004,(4):65-70. 松村格教授的观点看到了共同正犯与单独正犯的共同性,都是构成了系统性的责任主体,只不过是系统的构成要素有所差异。这一观点即较好地说明了犯罪集团组织、领导者的性质及处罚的依据,同时也对其处罚的边界有一定的提示作用。
2.正犯背后的正犯者理论
共谋共同正犯理论因在日本的司法判例上有所运用和体现,该理论的研究在日本较为流行,学者们基于不同的立论提出了共同意思主体说、间接正犯类似说、行为支配说、实质正犯说等具体的理论。同时,由于日本刑法第六十条明文规定:“两人以上共同实行犯罪的,都是正犯”,即明确要求共同正犯的构成要求有“实行”,为此,共谋共同正犯理论绕不开的问题在于“共谋”与“实行”如何画上等号。共同意思主体说从集体责任的角度,认为共谋即已经使得各个行为人形成了共同的意思主体,主要这个主体中有人实施了实行行为,即等同于该意思主体全体实施了实行行为。而间接正犯类似说、行为支配说、实质正犯说等理论则从个人责任的角度,根据共谋者的“共谋”所起到的作用,试图将“共谋”等于“实行”。共谋共同正犯理论在日本是十分有争议的,批评者也不在少数。但由于司法实践的立场,加之支持者们的不懈努力,该理论在日本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强。
那段时间,陈清经常给我打电话,询问身体反应情况。起先我没有一点生理反应,也没有恶心、嗜酸等早孕反应。幸运的是,手术二十多天后,妊娠反应出现了,而且反应非常强烈。恶心,呕吐,吃下的都被吐了出来,一点胃口都没有。但为了给胎儿增加营养,又不得不吃,这样吃了吐、吐了吃,痛苦不堪。
(二)英美刑法共谋犯理论
在英美刑法中,共谋犯用以表示只要共谋人参与了共谋,并不要求直接参与犯罪的实行行为,便可以认定的一种犯罪。设立和处罚共谋犯罪主要基于如下两个目标:“一是打击集团犯罪带来的危险。经过共谋的犯罪是多个人共同实施的犯罪,各个共谋者会在犯罪过程中相互分工和配合,从而提高犯罪的社会程度和成功几率……二是将犯罪消灭在萌芽状态。法律惩罚‘犯罪共谋’的目的在于把危险的有组织犯罪扼杀在萌芽状态,即惩罚共同犯罪的‘预备行为’,甚至是‘前预备行为’。”[3]227此外,从程序上来说,由于组织犯罪内部结构的复杂性,共谋的规定可以使得检方在面对庞大的犯罪组织起诉时更具便利性,从而获得程序上的功利性。
共谋属于英美刑法中的一种不完整犯罪,并且距离真正的犯罪行为还有一段的距离,但将共谋本身即作为犯罪,表现出英美刑法中的实用主义,同时也反映了组织犯罪打击的难度与复杂性。而黑社会性质首要分子的刑事责任,在共谋即已经是犯罪的情况下,组织、策划但未具体实施的行为也当然不能逃避刑罚的处罚。
(三)我国语境下的思考
我国的共同犯罪体系与德日、英美的共同犯罪体系都不相同,在我国刑法总则中并没有“共犯”“共谋犯”的概念,而是根据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同时根据分工又划分出了教唆犯。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也明确规定了“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是主犯”,这就使得对黑社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的组织、策划、领导行为本身具有了主犯的可罚性立法根据,而无需在理论上像德国、日本那样小心翼翼地在与立法冲突的情况下对组织、共谋者的正犯性进行论证。但是,有立法上的根据并不表示在理论上就不需要探究,实践中的问题往往就来自于理论上的混沌。
首先,在黑社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具体组织、策划、指挥,由其他成员实施了犯罪的情况下,黑社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可罚的主客观基础都是较为明显的,运用一般的组织犯原理即可以充分说明其可罚性基础。主观上首要分子的具体组织、策划、指挥反映了其主观故意,并与具体实施的组织成员形成了共同的犯罪故意。客观上首要分子虽没有直接参与实施,但其对犯罪事实具有显然的支配和制约关系,其将实施者的实行行为当做自己的实行行为达到实现犯罪的目的,这与设计组织代码编入智能机器人去实施犯罪,在组织、策划者责任的角度上来说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别。
在个人责任原则的要求下,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首要分子对组织成员实施的犯罪至少要有总体的组织、领导,如果组织成员的行为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私自行动,显然不能将此归咎于组织的首要分子。但如何认定“总体的组织、领导”呢?还是应当在黑社会性质组织这一组织体特性的基础上进行。即组织的首要分子对整个组织的领导、指挥,制定的纪律、要求等,都是首要分子总体组织、领导行为的体现。这即包括了对成员实施犯罪行为的总体组织和领导,也包括首要分子为了维持组织持续存在而展开的组织、领导活动。
编辑出版学学科的制度化没有达到根深蒂固的程度,加上体系重构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不可抗阻,因此重构的阻力是可以克服的。学科体系结构是描述一个学科体系构成的基本逻辑层级,是一种框架性描述,结构化的学科体系的优点在于可以根据学科逻辑起点知识的变迁规律与外界对知识的现实需求与时俱进的进行调整,一条线索是知识的变迁演进,一条线索是知识的规训与权利。从结构层面看,学科体系建构可秉持“三三”原则——三个方面、三个维度,即体系上可以大致划分为知识体系、学科课程体系、人才培养体系三个方面;话语生产又分为知识生产、规则生产和价值生产三个维度。
哈哈,自从妈妈生了弟弟之后,我们家又出现了一件大喜事——我家的机器人小白和我一样,也有了一个小弟弟,他的弟弟叫小谷。
黑社会性质组织是具有特殊组织体的犯罪集团,其严密性、危害性远远大于组织结构随意和松散的普通犯罪集团。尤其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控制性”特性,表明在特定行业和领域内,替代了国家所维持和主导的合法秩序,甚至形成了足以与国家法律合法的暴力机器(法律的强制执行力)相抵抗的能力,这种能力已经远远超越了个人合意体的普通犯罪集团,更是普通共同犯罪所不能比拟的。而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打击,不能不考虑这种特殊的组织特性。在德、日刑法以及英美刑法中都考虑到了有组织犯罪的特殊组织系统特性,即使是批评共谋共同正犯或正犯背后的正犯者理论的学者,也会认为将这些理论运用至有组织犯罪是无可厚非的。甚至很多国家针对有组织犯罪的特性,专门制定单行法对其进行打击。如美国的《有组织犯罪控制法》、德国的《防止非法毒品交易和其他形式的有组织犯罪法》、日本的《暴力团对策法》等等。
在日本就有这样的刑事判例。日本最高法院最近通过了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成员包括首领同时同地被逮捕时,其首领的刑事责任为共谋共同正犯(共同正犯的一种)责任的决定。具体来说: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成员开车转移、持有武器来保护他们的首领,这种安全保镖被称为持枪保镖(SWAT,来源于美国总统的警卫这个短语)。这些保镖保护他们的首领是他们自己的责任,也就是说,并没有其首领明确的要求。因此,当他们因为持有武器被逮捕时,其首领不会被惩罚。日本最高法院近来决定对其首领按持有武器的共谋共同正犯来处罚。虽然有组织犯罪集团的首领从未明确要求这种持有武器的保护。尽管如此,他仍然因为共谋而有罪。根据共谋共同正犯的刑法理论,只有当一个共谋共同正犯真正开始实施犯罪时,共谋共同正犯的刑事责任才成立。在持枪保镖案件中,首领作为共谋共同正犯被惩罚,尽管他与持枪保镖间并没有明显的共谋。有组织犯罪集团的首领和成员间固有的关系和成员需要在特定地点和特定的时间保护首领的客观情况,被用来作为证明默示同意存在的证据。虽然下级法院的判决有不同的倾向:一种同意承认首领共谋共同正犯的责任,另一种持反对态度。但有日本学者认为,“承认首领的共谋共同正犯责任很重要,它使逮捕和惩罚有组织犯罪集团的首领成为可能,而且可以使共谋共同正犯的理论得以发展”。[7]113-114
三、黑社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刑事责任的范围
黑社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刑事责任的范围,主要是为了解决其要为哪些组织成员实施的犯罪行为负责的问题。正如上文所述,在首要分子具体参与实施、进行了具体地组织、策划、领导的犯罪行为的情况下,首要分子对这些罪行负责是毫无疑问的,即使是普通的共同犯罪中,主犯也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而当黑社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没有具体组织、策划、指挥,但事前知情并默许组织成员实施了犯罪,以及黑社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没有组织、策划、指挥,事前不知情,组织成员实施了犯罪的情况下,黑社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仍然有可能要对罪行负责。之所以说“可能”负责,表明要在特定的条件下负责,在特定的范围内负责,而不是所有组织成员实施的犯罪都由首要分子负责。
图中可以看出,机动过程中,该拉杆受到明显的拉压载荷作用,通过舵机作用,引起舵面上偏和下偏,与实际飞行情况一致。
这个条件在原则上即为必须遵守现代刑法之基石的主观责任原则与个人责任原则。前者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刑法所规定的故意或过失以及期待可能性,后者要求行为人只对自己的行为及结果承担责任。但在犯罪集团中,主观责任原则与个人责任原则的要求相对缓和一些,即只需要对具体犯罪有总体策划、指挥即可。黑社会性质组织作为犯罪集团的高级别形式,自然也可以运用这一原理,甚至在个人责任原则及主观责任原则上可以做更为抽象的解读。但这样做难免又会使得认定的标准模糊化,怎么认定“总体的、概括的故意”,如何理解“总体策划、指挥”?这是确定黑社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刑事责任范围的关键所在。
德国司法判例中,还尝试在“经济企业的活动中产生的责任问题,也这样解决。”罗克辛教授认为这样就走的太远,因为“在这里,通常缺少在组中才具有的实施人的可替代性。这种可替代性在由其实现的犯罪性行为构成方面,已经在法律上消除了。这样一种法消除性(仅)存在于国家犯罪、恐怖主义犯罪与有组织犯罪的情况下。”[2]43但这从侧面也表明,有组织犯罪中实施人也因为组织的特殊性而具有可替代性,从而进一步论证出了有组织犯罪人可适用利用国家机器控制实行人的理论原理。
(一)黑社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的罪过边界
黑社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对组织成员的犯罪行为首先要有预见可能性,如果首要分子无论如何不可能预见到组织成员会实施某种犯罪,则无需对此负责。需要注意的是,首要分子的概括故意并不一定要以明示的方式明确表示出来,只要组织成员在长期的组织违法犯罪活动中,掌握了首要分子的总体的犯罪意图,即使首要分子对在此总体的犯罪意图下具体实施的犯罪行为并不清楚具体细节,也不影响首要分子对此罪行的负责。
所谓概括的故意,是不确定故意的一种,一般指的是事例群的法现象。最初将概括的故意体系化的是德国学者韦伯,概括故意的认定包括认识因素及意志因素两个部分,在认识因素的角度,行为人只对犯罪结果的发生有明确的认识,但“结果发生的对象不特定、侵害的程度不确定,即对象的数量以及哪个对象的发生结果不确定时,就是概括的故意”[6]105-105,意味着对行为人对这些因素的认识是不确定的,但如果行为人无论如何不可能认识到行为会导致危害结果,则已经超出了概括故意认识的边界。在意志因素的角度,学界有希望说和放任说的不同观点,笔者认为虽然行为人对犯罪的结果发生有明确的认识,但这种认识实质上也只是一种“极大可能性会发生”的认识,只有当结果真的出现时,才能说对结果发生有了明确的认识。因为任何犯罪结果的发生,都并不只依赖于行为人的主观,还需要客观条件以及因果关系的连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差错都有可能导致犯罪结果的不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完全可能出于预见到了特定结果而在内心放任该结果的不确定的具体形态,如程度、对象等。
要上传你的最佳作品,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在标题中注明“寻觅红色”挑战,将作品发送到wangc@gaozhimage.com,挑战将于2018年1月15日结束,获胜者将收到刊登你作品的杂志。投稿意味着你同意杂志在“寻觅红色”比赛中刊发你的作品,图片版权和署名权仍由参赛者所有。获胜者将收到一本杂志,上面刊有你的获奖照片!
黑社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的罪过边界指的是其总体性、概括的故意的边界,虽然并不要求其对组织成员的犯罪行为有明确的故意,但至少需要有概括的故意。这就需要从认识因素及意志因素两个方面角度进行认定。
为此,在上述两种情形下,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首要分子仍然有追究刑事责任的可能性,其可罚性依据就在于组织本身。“有组织犯罪所显示的却是一种群体性的社会恶势力,在这种犯罪组织中,组织成员不再是孤立无援的个人,而是强大的组织力量、组织纪律、组织措施提供支持。”[4]37组织成员与组织首要分子之间并不是互相独立、松散的关系,而是通过组织体紧密联系于首要分子周围,共同成为组织体的一个部分,只要组织成员实施的犯罪能归结为组织体的犯罪,组织的首要分子就应当为其负责。至于在什么情况下组织成员实施的犯罪属于组织本身的犯罪,这涉及到的便是刑事责任范围的问题,对此将在下文进行详述。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当团藤重光教授于1983年以学术泰斗身份担任最高裁判所法官后,“改变了以前强烈反对共谋共同正犯的立场……致力于防止判例中共谋共同正犯范围的扩大。”[5]110这也从侧面给了我们研究黑社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刑事责任的重要提示,即不能因为打击犯罪的需要而盲目扩张首要分子的刑事责任范围,仍然要在实现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目的中,坚守刑法保障人权的核心价值。
要就组织成员的犯罪行为对组织首要分子追究责任,首先就应当确定该组织成员的行为是否符合组织的意志(首要分子的意志),只有在符合组织的意志的情况下,成员的行为才会被吸收成为组织的行为,从而使得首要分子对其负责。而符合组织的意志,首要分子必须对行为的结果有认识,且至少放任这一结果的发生,但并不要求所有细节全部吻合,只要求在总体上与组织的目标、要求一致即可,即使是默示的目标也可以认定为组织的意志。
(二)黑社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组织、领导行为的认定
其次,在黑社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没有具体组织、策划、指挥,但事前知情并默许组织成员实施了犯罪,以及黑社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没有组织、策划、指挥,事前不知情,组织成员实施了犯罪的情况下,按照一般的共同犯罪理论难以追究首要分子的刑事责任,这也是为什么在司法实践中,司法者往往会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打散,重新组合成各个共同犯罪追究责任。要么就是盲目套用我国刑法总则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将组织成员实施的犯罪全部归责到首要分子处。这实际上是没有认识到黑社会性质组织与一般犯罪集团以及一般共同犯罪的差异。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的《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以及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发布的《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中,都对哪些情形应当认定为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进行了规定。这些规定的情形中,除了组织者、领导者直接组织、策划、指挥、参与实施的,其余都表现出组织成员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组织性,而这种组织性正是来自于首要分子对整个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总体领导。存在问题的是,根据两个司法解释,为了组织的利益实施的犯罪,也应当被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这是否违背了个人责任原则以及主观责任呢?当组织成员的犯罪行为是为了维护组织的利益,但并不符合组织首要分子所代表的组织的要求时,是不是还是要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呢?毕竟组织成员自认为是为了维护组织的利益,但这种认识并不一定符合组织的领导要求。例如某一组织刚成立的时候,组织者、领导者就立下帮规“只谋财不害命”,在这一总体的组织和领导下,成员积极开展非法敛财活动。但其中某一成员,好大喜功,为了打击竞争对手,树立组织的威信,将某竞争“帮派”的头目枪杀了。此时,由于组织成员的行为已经超出了组织、领导者的领导范围,就不应当再对组织、领导者追责。但如果组织虽然不认可部分成员的行为,但是对于组织成员的行为效果予以继承和利用,该违法犯罪行为就应当被认定为组织的行为。
根据表5中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可以得知GDPL、LGAS、LENERGY三个变量的原始序列均不平稳,但是当通过差分处理,序列都变平稳,即可以建立协整模型。
总结来看,黑社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与单个犯罪主体及普通的共同犯罪主体在责任范围上是有较大差异的。由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组织性特征,其首要分子基于其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和领导,其承担的责任范围不仅仅是自己直接实施并具体组织、策划的犯罪。当其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时,其个人犯罪意志、目标等已经渗透进组织当中,通过组织的系统性自我运转,组织成员实施的符合组织意志、目标的具体犯罪已经不再需要首要分子“亲力亲为”地策划与实施。但这些犯罪仍旧是首要分子犯罪意思的体现,也是首要分子总体领导、组织行为的具体化,其仍然要对其负责。只有完全超出其认识范围以外,组织成员脱离组织私自实施的犯罪,首要分子才能不对此负责。
四、黑社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的刑事责任的程度
黑社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按照组织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但并不意味着在每一个犯罪中首要分子都应当作为主犯承担最重的刑事责任。虽然根据我国刑法第26条规定,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是主犯,但对该条款还是应当结合罪刑相适应的原则进行分析。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主犯、从犯的区分应当根据的是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进行的划分,在共同犯罪中其主要作用的是主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的则是从犯。但我国刑法第二十六条关于组织、领导集团进行犯罪活动是主犯的规定,实质上是根据行为人的分工认定的主犯,这就与根据作用认定主犯的标准有所出入,这也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认定了黑社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是主犯的前提下,又认为其在组织的某一个犯罪中不是主犯的矛盾局面。笔者认为,我国刑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主要有以下基层含义,一是揭示组织、领导活动本身的可罚性,其可以等价于实行行为,甚至可能在社会危害性及人身危险性上高于实行行为。二是解决犯罪集团组织者、领导者的刑事责任范围问题。即组织者、领导者是犯罪集团中的主犯,对整个集团实施的犯罪要承担主犯的责任。但是在具体的量刑上,还是应当根据首要分子在各具体犯罪中所起到的实际作用、具体的各种情节来进行量刑,而不能一律对首要分子在所有具体犯罪中都依照主犯的量刑规则施以最重的刑罚。尤其是在我国本身规定了组织、领导、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而黑社会性质组织成立本身就包含了实施违反犯罪活动的特征的情况下,确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首要分子的刑事责任范围,应当避免量刑重复评价的问题。
徐进步还没来得及把狡辩的话说出口,仓库外传来一片“乌拉”之声。他们一齐跑到仓库门口,朝七连那边看去,只见队形已经散乱开了,女知青们围成一团,男知青们往空中抛帽子。
(一)黑社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的量刑原则
黑社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的量刑原则,除了需遵守基础性的罪刑相适应原则以外,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从严处罚原则与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的平衡。
要着力解决面临的特殊困难。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学校大多地处边远,地广人稀、交通不便、情况各异,存在许多特殊困难,应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的《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明确要求:“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要依法从严惩处”。从严惩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是“宽严相继”的刑事政策中“以严济宽”的具体体现,也符合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一般规律。我国自古就有“擒贼先擒王”的经验,在剿灭黑社会性质组织工作中,如果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被抓获,该组织往往会自动解散,不再有笼络组织继续存在的精神核心,我国法传统文化中的“造意为首”也是由此而来。然而,在从严处罚黑社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的过程中,存在着是否违背了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的问题。
禁止重复评价原则指的是对同一侵害事实不能多次进行重复评价的原则。德国刑法典第四十六条“量刑的基本原则”规定:“属于法定构成要件特征的情节,在量刑时不予考虑。”这是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在德国刑法典中的体现。虽然该原则并未在我国宪法、刑法中有明文记载,但其与罪行法定原则、罪行相适应原则等原则一样,都是现代刑法的基础性原则,应当成为定罪、量刑活动的指导性原则。在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存在是符合该罪构成要件必不可少的情节,而要成立黑社会性质组织,必须要具备“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特征。这就表明,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在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中已经进行了一次评价,从而在首要分子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时,已经附带对此情节进行了评价。但根据我国刑法分则的规定,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罪又有其他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根据刑法总则的规定,组织受要分子按组织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这就可能出现重复评价的问题。要避免重复评价,就必须在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或其他犯罪的量刑中,对相应具体罪行只评价一次,从而使得组织首要分子的量刑似乎“轻缓”了不少,这又似乎与“从严处罚”的要求相矛盾。
笔者认为其实这二者并不冲突。“从严处罚”的前提是“依法”,即要从严处罚,更要依照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具体规定从严处罚,从严处罚并不是没有边界和限度。对于重复评价的问题,主要也还是出现在组织首要分子并未实际实施,也没有具体组织、策划的情况,组织成员自行在组织的总体目标下实施犯罪的情况中。如果组织的首要分子自己本身参与了组织的具体犯罪,就该具体犯罪负责并不违反禁止重复评级原则。而当组织的首要分子并没有参与到具体的犯罪中去,而是基于组织本身的系统性出现了的组织成员的犯罪,组织的首要分子在对组织的存在已经承担了刑事责任的情况下,对该具体的犯罪至少不应当一概以“主犯”论处,而应当考虑具体的情节,及其具体在犯罪中起的作用进行判断。
大多数该类化合物在正离子模式下的质谱响应好于负离子,高能碰撞下逐步失去CO(相对分子质量28),且伴随CO2(相对分子质量44)的丢失;苯环上的CH3、CH3O等取代基也易形成碎片离子;此外,蒽醌苷类化合物则易发生苷键断裂而失去糖苷配基[33]。本品中共鉴定出10种醌类化合物,分别为丹参酮IIB、丹参新醌A、羟基丹参酮IIA、1-β-羟基隐丹参酮、大黄素、二氢丹参酮I、丹参酮V、丹参隐螺内酯、隐丹参酮和丹参酮IIA。
(二)黑社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的量刑情节分析
有实务界的学者指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首要分子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一般是主犯,但并不意味着在所有具体犯罪中,其都是主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首要分子在量刑上也并不必然就是最重的,还是需要根据具体情形以及其在具体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来判断。”[8]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在此基础上,有必要对具体影响首要分子量刑的情节进行探讨。
一是组织成员与组织之间的关系紧密度。正如前文所述,之所以在首要分子没有参与,也没有具体组织、策划、领导组织成员实施犯罪时,仍要对组织成员的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是由于其对组织体本身的作用导致了犯罪的发生。而组织成员与组织之间的关系越紧密,组织成员自觉维护组织利益、维护组织首要分子的可能就越大,组织首要分子对其组织成员实施犯罪行为的预见性就越高,同时也表明组织首要分子对组织的控制力度越大,此时其应承担的责任程度也就越大。但是否一定会超过具体实行行为者的刑事责任程度还不能轻易做肯定的回答。如果组织成员的行为及意志完全与组织融为一体,此时首要分子对其的控制力是相当大的,或许首要分子可以辩称在某次具体犯罪中并没有下达明确的犯罪指示,但出于其对组织、对组织成员的支配,已经足以推动组织成员自觉实施犯罪,此时完全可以对首要分子追究重于具体实施者的刑事责任。但若组织成员仍有较大的自由空间,对组织的依附程度并不高,此时首要分子的刑事责任就不应当高于具体犯罪事实者所承担的刑事责任程度。
二是组织成员实施犯罪时的客观情形。组织成员私下自行事实犯罪可能出于各种各样的客观情形,在这些情形中,只有该情形是有先例的、有惯例的,或者符合一般人可以预见的组织成员会事实犯罪的情形,此时的首要分子所承担的责任至少可以等同于具体实施者的刑事责任。但在突发异常情况下,首要分子的犯罪意图以及组织的意志尚未来的及以明示或默示地方式进行表达,组织成员自行实施的犯罪行为,即使得到了首要分子的事后追认,对该犯罪不宜认定首要分子的刑事责任重于具体实施者的刑事责任。
三是当组织内有多个首要分子时,应区分各个首要分子的刑事责任范围及程度。不少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并不是单独一人处于组织结构“金字塔”的顶端,而是出现多层级的现象。此时处于同一层级的组织、领导者对对方所犯的罪行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而是应当在各自组织、控制的范围内自行承担责任。
参考文献:
[1]秦宗川. 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全部罪行”的认定[J]. 中国刑事法杂志,2014,(5):39-49.
[2]克劳斯·罗克辛. 德国刑法学总论(第2卷)[M]. 王世洲,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3]刘源,吴波. 外国刑法学专题研究[M].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
[4]谢勇,王燕飞. 有组织犯罪研究[M]. 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
[5]陈家林. 共同正犯研究[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6]苏惠渔. 刑法学[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7]京藤哲久. 日本黑社会犯罪的控制和预防[A]. 周长军,于改之. 实体与程序打黑的国际经验与中国课题[C]. 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
[8]周光权. 论量刑上的禁止不利评价原则[J]. 政治与法律,2013,(1):109-116.
On the Criminal Liability of Ringleaders of Underworld Organizations
Chen Mei
(School of Criminal Justice,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School of Law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Wuzhou University, Wuzhou 543000,China)
Abstract: The criminal liability of the ringleaders of underworld organizations is inconsistent in judicial practice,which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wo aspects: one is the problem of false provisions in article 26 of the general provisions of criminal law and the other is that the identification logic of all crimes committed by underworld organizations is not precise. The punishment of ringleaders of underworld organizations is controversial in German, Japanese, British and American criminal law theories, among which the theory of common principal criminals, the principal criminals behind the principal criminals and the conspiracy theory are relatively the mainstream theories. These theories have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in the context of China, and also suggest that the core value of human rights guaranteed by criminal law should be adhered to when the purpose of fighting gangland organized crimes is realized. To determine the scope of criminal liability of ringleaders of underworld organizations need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boundary of their crimes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ir organizations and leaders.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strict punishment" and "prohibition of repeated evaluation principle" in determining the criminal liability degree of ringleaders of underworld organizations and the degree of liability of ringleaders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specific circumstances rather than the most serious criminal liability of all the "ringleaders".
Key words: underworld organizations; ringleaders; criminal liability
中图分类号: DF6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3745(2019)04 - 0068 - 09
收稿日期: 2019-06-14
作者简介: 陈梅(1987—),女,湖南怀化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法学博士生,梧州学院讲师,从事刑法学研究。
责任编辑:林 衍
标签:黑社会性质组织论文; 首要分子论文; 刑事责任论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论文; 梧州学院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