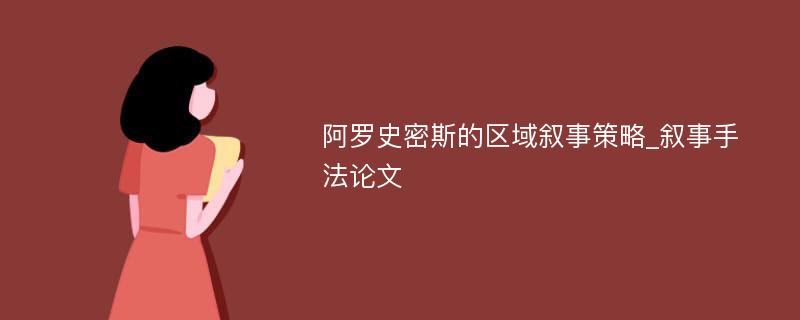
《阿罗史密斯》的解辖域化叙事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密斯论文,策略论文,解辖域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阿罗史密斯》(Arrowsmith,1925)是美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1885-1951)的重要作品之一。长期以来,批评家们忽略了刘易斯作品叙事所呈现的一个美利坚民族文化主题——“集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于一体”的矛盾的文化特征,“逃逸”是这种文化特征的起源方式和表现形式,美利坚民族主要就是由以英国为主的欧洲各国的逃逸人员组成的。①长期以来,研究者对这种主题的忽略,导致对刘易斯作品重要的叙事形式的忽略——由逃逸导致的断裂-连接-发展的多元叙事线条。美国作家迈克尔·卡门在其专著《自相矛盾的民族——美国文化的起源》中指出,美国民族的一个典型特征是:“你必须同时拥有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卡门:217)刘易斯作品的叙事就是对这一民族文化特征的生动阐释。
刘易斯的《阿罗史密斯》运用了传统的全知叙述模式,但其全知叙述模式具有与传统不同的特点。刘易斯非常出色地发挥了传统全知叙事给予叙述者之客观可靠的优势,使得其文本所建立的道德标准及所显示的对社会之犀利批判获得了读者广泛的认可,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文化影响。同时,刘易斯又避免了全知叙述模式中权威性的中介眼光、说教味太浓、作品缺乏逼真感和戏剧性等缺陷,赋予了他的叙述者一种超越传统的特质——一种“多元”的特质,在文本中建构了连接-发展-断裂-连接的多元叙述线条,而不是传统小说中的完整的叙事线条。这种独特的叙事技巧与“集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于一体”的文化特征之“逃逸”的表现形式巧妙地嵌合在一起,让刘易斯的作品具有了一种不同于其它小说之“现代现实主义”的叙事特征,使得叙述者在小说虚构的世界里能挥洒自如地编织着美国多元文化的历史画卷,尽量不受叙事文体的限制,达到作者反叛的文化叙事目的。
以前的研究一致认为,刘易斯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而未知现代现实主义是刘易斯作品所体现的一种独特的叙事特征。通过分析,我们认为,首先,刘易斯通过“多元”的全知叙述者叙述所创造的作品不但具有反映社会现实的真实性、客观性等现实主义文学最重要的因素;其次,所呈现的强烈反叛传统、标新立异的精神、突出的自我意识也包含了现代主义的某些内核;另外,作品开放的形式、叙述视角的转换、消解深度的描写、事件的拼贴组合方式、强烈的反讽、断裂的线性结构等却又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因此,我们把刘易斯的这种多元叙述者所创造的集合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特征的这种文体称为“现代现实主义”。
这种现代现实主义叙事风格在刘易斯作品中的表现形式并不是完全相同的,连接-发展-断裂-连接的多元叙述线条是其基本特点也是刘易斯多部小说的共同特点,但是多元叙述线条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中,又演绎出了各自独特的叙事特征,本文要讨论的就是刘易斯所创造的现代现实主义叙事风格的表现形式之一——解辖域化的叙事策略在其小说《阿罗史密斯》的民族文化叙事中的体现。
相对于刘易斯前两部小说《大街》和《巴比特》中平凡的主人公来说,阿罗史密斯是个英雄,他有着崇高的理想,为了科学研究,可以置一切功名利禄于不顾。他这种忠于科学、献身科学的思想有一个形成过程。这是刘易斯四部杰作中唯一一部具有明显的情节变化,主人公有个长大成长(尽管小说主要还是从大学时候开始详述)、性格有所变化和成熟的过程的一部小说。②这部小说一问世,像前两部一样,刘易斯又获得了巨大成功。但这次与前两次相比,反对的声音明显减少,评论界的反响比较一致。詹姆斯·赫切森论述道:“《阿罗史密斯》平息了长期以来批评刘易斯缺乏‘精神的禀赋’的声音。在美国和英国的批评家都一致判断,《阿罗史密斯》是刘易斯最好的小说。几乎所有的评论家都注意到这部小说比《大街》和《巴比特》有更强有力的和更深刻的审美观。例如,《文学评论》(Literary Review)说‘小说所体现的人性比科学更闪亮’;《大西洋书鉴》(The Atlantic Bookshelf)宣称刘易斯‘不再是最高级的爵士乐的作曲家了。他已经显示是一位艺术家,忠诚的、强大的和有克制力的。’”(Hutchisson:122)
像前两部打破文学神话,开创小说新主题一样,《阿罗史密斯》又为美国小说带来了一个科学理想主义的全新的主题。对此,一向对刘易斯反感的马克·斯高勒也肯定了这一事实。(刘易斯,后记:560)查尔斯E.罗森博格非常赞赏《阿罗史密斯》,罗森博格说是弥漫于社会的妥协空气驱赶阿罗史密斯最后离开他的妻子、孩子和纽约的实验室,他对社会及其要求的拒绝并不就是像有些批评家所说的“长不大的浪漫主义”,是刘易斯想要描述其伟大性而认为其存在于美国社会的不可能性所导致的合乎逻辑的结果。(Rosenberg:50)罗伯特M.拉福特和马丁·赖特也对《阿罗史密斯》表示赞赏,但提出了和罗森博格不同的看法。拉福特认为对理想的追求和幻灭的体验是《阿罗史密斯》的中心。(Lovett:32-34)赖特认为《阿罗史密斯》的主题表现为:“美国人生活中的骗子、挥霍者和伪善者把人从最好的最纯洁的工作中赶走,他的唯一救赎是退却。”(Light:57)由此,他认为阿罗史密斯是个堂吉诃德式的英雄,最后退至山林是败笔,是不明知的处理,是长不大的孩子气行为。而马瑞林M.赫勒博格则极力贬斥《阿罗史密斯》的艺术性,对刘易斯给予了完全的否定,认为刘易斯创造的人物阿罗史密斯是不堪一击的“纸娃娃”。(Helleberg:29-36)
从赫勒博格的观点看来,他显然无法接受刘易斯对医疗界和科学界某些机构和官员的嘲讽和批评。但我们认为,那些现象非常真实,刘易斯也只是通过艺术创作,让那些现象呈现在读者面前,仅此而已。可却引来赫勒博格这类批评家的如此不满,这恰恰从另一侧面说明刘易斯的艺术水平高超,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刺伤了某些读者的自尊心。
我们认为,阿罗史密斯最后退至山林不是理想的幻灭,他也不是堂吉诃德式的英雄,更不是纸娃娃,他是美国民族精神的现代传承者。他对理想的追求过程,可以说是放弃和逃逸的过程,是世俗利益和科学理想之间的不得已的选择,是贪求眼前个人的实利、失去个人思想的自由,还是坚持探求真理、着眼全人类的疾苦是经常摆在阿罗史密斯面前的两难问题。而每次,阿罗史密斯无一例外地做出了继续求索真理的选择,也就是逃跑。但我们认为,他的逃跑不是向世俗利益妥协的标志,不是懦弱,而是正直诚实的人格基础上对权势利益的一种鄙视,对科学真理的一种挚爱和执着。
刘易斯把马丁·阿罗史密斯化作了理想的象征——美国拓荒精神的现代化身,就像谢尔登·诺曼·格雷布斯坦所说的,“这在刘易斯看来是我们本国传统中最有活力的传统。”(格雷布斯坦:82)在《大街》的开头,刘易斯曾把这种精神象征性地附丽在了具有叛逆思想的卡萝尔身上。卡萝尔部分地传承了这种血脉,进行了一些不成功的抗争。刘易斯肯定是不满意的,但那是人物性格的发展使然,刘易斯只能服从这种创作规律。在《阿罗史密斯》的开头,有一个独立的小叙事,叙写一位十四岁的小姑娘赶着马车,载着病弱的父亲和穿着破烂的幼小弟妹,穿过森林和沼泽,摇摇晃晃向着遥远的西部坚定地前行。叙述者告诉我们,这就是马丁·阿罗史密斯的曾祖母。刘易斯再一次把这种光荣的开拓精神传递给了他的人物,想让这种他所崇敬的民族核心精神得到完全的展示,这一次他做到了。并且把祖辈们飘洋过海追求自由和财富的开拓精神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境界,与时俱进地把祖辈们着力于自身生存、物质财富和信仰自由的追求上升到了对尖端知识、科学精神和人格自由的追求,是一种对真理执着追求的无畏精神。我们说刘易斯呈现的这种主题元素才代表了人类文明的真正进步,而不应深陷在文明进步所带来的浮华繁荣的金钱堆里不能自拔。
这样一位正面人物的塑造,是极易流于形式化和表面化的,特别是对于全知模式的叙述者来说,也是极易使小说陷入说教式的、枯燥乏味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局面的。但刘易斯的《阿罗史密斯》避免了这一切不利后果,显示了其高超的叙事艺术技巧。《阿罗史密斯》的全知叙述者用解辖域化的叙事艺术,用批判-赞美、逃逸-追求、舍弃-获取、断裂-连接的多元叙述线条串起了阿罗史密斯跌宕起伏的平凡而伟大的生命乐章。
细读原文,刘易斯的胃口不可谓不大,他的主人公阿罗史密斯身上流淌着世界各民族人民的血液:
马丁是“典型的纯盎格鲁——萨克逊血统的美国人”,这就意味着他是德国人、法国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也许还有一点西班牙人的结合体;不难想象,他具有少许“犹太人”那样的混合血缘,大量的是英国人的血缘,而英国人本身是原始的不列颠人、凯尔特人、腓尼基人、罗马人、日耳曼人、丹麦人和瑞典人的结合体。(刘易斯:2)
刘易斯的视野和胸襟非常开阔,叙述者的这一阐释使我们一开始就看到阿罗史密斯这一拓荒精神的传承者身上具有的民族多元性特征。他的曾祖母十四岁时肩负起了全家生计的重任,坚定地奔向西去的进程,而阿罗史密斯在十四岁时,表现出了对医学的强烈兴趣,成了他家邻居维克森医生的义务助手,在其指导下,阅读《格雷氏解剖学》,决定了以后要从医的志向。并记下了维克森医生的反复叮嘱:一定要学好基础科学,在上医学院之前要上大学预科。于是,阿罗史密斯在专科毕业后,才进入温尼麦克医学院。在这里,他成了德国籍细菌学教授戈特利布的得意弟子,显示了在细菌实验科学研究方面的某种天分和执著。实验室里解剖豚鼠,辨认炭疽杆菌等令常人恶心的枯燥乏味的工作,却使阿罗史密斯产生了非常美妙的感觉。“对马丁来说,这些日子具有一种令人十分愉快的特色;有着一场激烈的曲棍球比赛的那种热情,草原一般的明朗,美妙乐曲似的迷惑人的力量,还有一种创世的感觉。”(刘易斯:44)这段描述是一段多声部的话语,它是人物阿罗史密斯内心愉悦的心声,也是叙述者的概述之声,更是隐含作者的赞美之声。这赞美之声又是文学家刘易斯与医学科学家克鲁夫的双声部融合。刘易斯聘请克瑞夫做他的助手,认证涉及医学学术上的细节,但作为科学家的克瑞夫对科学的认识和态度不可能不影响刘易斯。赫切森经过仔细研究就认为,克瑞夫对刘易斯写作《阿罗史密斯》有很大的作用,没有他的帮助、建议和他的思想和科学观,《阿罗史密斯》可能就会大不一样。(Hutchisson:103)
我们可以从上面的引述中读出科学家克瑞夫所体验过的真切感受,但此段引述也更有可能还融合了刘易斯从他的医生父亲和哥哥那听到的话语。无论多少原因,给我们的感觉是这是一个充满灵感和想象的灵魂对所崇拜和痴迷的科学事业的非常真切而符合实情的感言。再看另一场景的描述,万籁俱静,医学生阿罗史密斯还在实验室里,寻找引起昏睡病的原因:
他在研究老鼠身上的锥体虫③——这是一种有八根分支的瓣形体,染上了多色的亚甲基蓝,其紫色的细胞核,蓝色的细胞,纤细的鞭毛,是一簇像水仙花一样娇美的微生物。他很激动,也有点得意,他给细菌染色染得十分漂亮,而要给瓣形体染色却不破坏它的花瓣体形态是不容易的。(刘易斯:44)
这里,我们看到,在令常人惊恐和讨厌的染病老鼠身上的病菌,在阿罗史密斯的眼里却成了娇美的水仙花,这是医学生阿罗史密斯在从事细菌研究工作时的真切情感体验。我们说这时的叙述者更像一个科学家,作为读者的我们相信,去掉科学研究者爱屋及乌的情感美化因素,在显微镜下,锥体虫的形状肯定与兰花的形状有某种相似之处,而不是与其它的什么鲜花有相似的形状,而作为非专业的人员是不可能把科学与文学结合得如此和谐美妙、绘声绘色的。因此,我们认为,《阿罗史密斯》的全知叙述者的身份具备一名医学工作者的专业素质,这与刘易斯在找到克瑞夫做助手后才开始这部小说创作的实情是吻合的,这同时也说明刘易斯对待文学创作是非常细致严谨的,有一种文学创作的科学态度,这也是他的作品总是那么生动逼真的一个重要原因。反之,如果刘易斯的作品不那么现实却胜似现实的真实,就会减弱对社会的批判性,也不会招致那么多“爱国”人士的诋毁之声。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判断出,刘易斯作品显示出的对社会的强烈批判性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力于他作品所体现的真实性甚至于科学性所给予的非凡力量。
我们观察叙述者对待进行科学技术研究的态度,我们说上面那两段引文既是阿罗史密斯的真实感受,也是叙述者的评价。可以看出叙述者对待阿罗史密斯在科学技术研究上的出色表现是非常欣赏的,叙述者是一个理解科学工作者、懂得科学、热爱科学并尊重科学的医学专家。那么,作品的伦理标准就很明确了:它一反当时以赢利为目的的社会时尚和标准,建立了自己崇尚科学,致力于解除全人类疾苦的崇高目标。致力这种目标的科学家最基本的品质要求是对待科学研究要有耐心、爱心,要能忍受孤独、要能淡泊名利,岂非纸娃娃式的人物能肩负的重任。此外,上述引文也从另一侧面反应了生活的某些真谛,某种人性真实的一面。像阿罗史密斯及他的导师戈特利布这类科学家耐寂寞、忍孤独、淡名利地追求科学真理,并不是什么被迫的行为,是他们主动为之,他们乐此不疲,享受着身心的最大幸福和快乐,也获得了精神和灵魂的最大自由。他们是普通的人,追求着自己的快乐和自由;他们又是不平凡的人,从事着揭开自然的奥秘、解除人类疾苦的使命。这决不是堂吉诃德式的英雄,堂吉诃德式的英雄把个人建功立业的名誉摆在首位,其次是其方式的不可行性和不切实际性。而阿罗史密斯则是脚踏实地在走着科学研究的道路,经过了漫长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的学习和培训,然后是实验室长年累月的无以计数的精心实验和精确演算,还有对相关各学科的专业知识不断深入的研习。可以说阿罗史密斯这样的科学家是现代科学的开路先锋,绝非堂吉诃德式的幻想者和莽撞者。
叙述者对马丁是赞美的、欣赏的,但与《巴比特》的全知叙述者是巴比特的化身不同,《阿罗史密斯》的叙述者并不是马丁的化身,他是独立的。他除了向读者报道阿罗史密斯的情况,他还用其他人物的声音向读者报道其他人的情况。安格斯·杜尔是阿罗史密斯的同学,他的功课很好,他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做一个高薪的出色外科医生。在实验室上完戈特利布的细菌学课后,叙述者报道了杜尔边走边对另一个同学说的话:
安格斯·杜尔对一个代伽马会友说:“戈特利布是实验室里一个老而无用的家伙;他没有什么想象力;他株守在这里,而不出去见世面享受战斗的乐趣。当然他的手很灵巧。他有极好的技术。他本来可能是一个第一流的外科医生,每年赚五万美元。实际上,我想他每年最多不超过四千!”(刘易斯:42)
这与阿罗史密斯的声音完全不同,但叙述者并没有对杜尔所说的话做任何评论,更没有因欣赏阿罗史密斯而贬斥杜尔,只是做了一个忠实的报道者。在这里,从杜尔的视角,读者看到了另一个戈特利布。戈特利布在阿罗史密斯的眼里,是了不起的科学家,是他崇拜和热爱的偶像。而在杜尔的眼里,却是个老而无用的家伙,为什么无用呢?因为他穷。杜尔也承认戈特利布的本事,但却鄙视他,为什么?因为他本可以用自己的技术去赚取高额薪酬,过上比现在好得多的生活。杜尔的话很有力量,他在用社会上流行的、认可的成功标准来评价戈特利布,可以说不是偏见,因为它代表了大多数人的观点。叙述者不直接进行评论也是很在理的,他如果说杜尔的话错了,反而是没理了,因为那违背了大家认可的道理。由于没有叙述者的评价,只能由读者自己去判断杜尔对戈特利布的判断了,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看法。以实用主义为目的、以赢利为成功标志的读者肯定会赞同杜尔的看法。然而,作为读者,我们明白,叙述者其实是不赞赏杜尔对戈特利布的评价的。通过对阿罗史密斯沉醉于实验室工作的乐趣的描述与杜尔对戈特利布株守实验室的鄙视的话语的描述的对比,叙述者其实是开启了赞美-批评的叙述之流,呈现了不同的世界观,拉开了赞美-批评之间的张力所呈现的局部的不稳定,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作品的伦理标准。其后的叙述进程就通过断裂-连接的多元叙述线条来表现逃逸-追求、舍弃-获取之间的得与失的赞美和批评,解决人物与社会冲突之间的张力,以获得局部的稳定。
在医学院,除了学习知识之外,阿罗史密斯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认识了戈特利布,受到了戈特利布的实证主义科学观的影响;二是认识了文静、坚忍、朴实的西部姑娘利奥拉,并娶她为妻。这是位无论他做什么,都会永远默默地支持他的妻子。安格斯·杜尔曾这样评价过阿罗史密斯的爱情:“一个聪颖的年轻小伙子,竟然与一个不能提高他社会地位的姑娘结成伴侣,世界上竟然还有马丁与利奥拉之间的这种男女爱情。”(刘易斯:96)从杜尔的评论中,我们可以判断,阿罗史密斯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很不成熟的,单纯的,也是脆弱的,与社会的流行规则不相适宜,这也预示了他的这种伦理观在社会上必定会碰壁。由此,个人与社会的冲突烽烟四起。
果然如此,阿罗史密斯医学院毕业并在泽尼斯一家综合医院担任二年实习医生后,在利奥拉的家乡惠西法尼亚做了一名乡镇医生,但他不善于让别人了解自己,做事过于耿直认真,把同行甚至病人都给得罪了。于是,他远走高飞,离开了惠西法尼亚镇,应聘来到诺梯拉斯市,给公共卫生局长阿尔穆斯·皮克博当助手,并在皮克博高升后接任代理局长。阿罗史密斯想在这里一展宏图,但是,当他认真地实施有利于市民们卫生健康的措施时,又触犯了好些开业医生和一些企业团体的利益,他们开始联合起来散布各种于他不利的谣言,并上诉要求市政府免除他的职务。而阿罗史密斯在这种社会习俗的强大阵势面前,他的能力是不堪一击的,只是他的另一种能力,他的真才实学总是有人欣赏,让他能找到安身立命的地方。无论在哪里,阿罗史密斯总是利用一切条件,抓住一些空隙时间,因陋就简地对他的细菌做些研究,然后写成论文在刊物上发表。这次,阿罗史密斯又离开诺梯拉斯,来到芝加哥的郎斯菲尔德私人高级诊所担任病理医生。该诊所是由一些医学专家组成的私人组织,由他们共同投资,分享赢利,安格斯·杜尔现在已是这个著名诊所的主要成员之一。在来芝加哥的路上,经历了这几次惨败,阿罗史密斯不想再看到实验室和公共卫生部门了,打算就呆在郎斯菲尔德诊所,后半辈子就做个营利集团的医生,赚一切可能赚到的钱。阿罗史密斯希望自己能明智地做到这一点,安安静静地呆了一段时间过后,他的心忍不住又被他的细菌实验吸引住了,想多少搞一点链球菌溶血素的研究。然而诊所只希望他搞点实际的研究,他觉得很为难。眼看着冲突又起,正在这时,他的关于链球菌溶血素的论文在《传染病》杂志上发表了。他把论文的复印件交给了郎斯菲尔德和安格斯,以为他们会因此有点高兴,而放松对他的限制,但他们不感兴趣。他也寄了一份给纽约麦格克生物研究所的戈特利布。戈特利布给阿罗史密斯回了信,认为这篇论文很说明了一些问题,向这位昔日的爱徒发出了热情邀请,希望阿罗史密斯能去他所在的研究所做细菌学研究工作。于是,放弃了做个赚钱医生的想法,阿罗史密斯来到了戈特利布身边,作为一名专职人员开始了他的研究工作。来到分配给他的实验室,阿罗史密斯顿时感到踏实了,他想到再也不会有皮克博或郎斯菲尔德突然闯进来,把他拖出去向大众做解释、搞鼓吹和宣扬了,因而他满心欢喜,认为终于可以自由自在地工作了。
从温尼麦克医学院到麦格克研究所,从表面上看来叙述者让阿罗史密斯一次次扮演了失败者的角色,由此导致有些批评家如马丁·赖特的“退却是阿罗史密斯的唯一救赎”、罗伯特M.拉福特的“对理想的追求和幻灭的体验是《阿罗史密斯》的中心”的结论。④但我们认为,潜文本下,叙述者其实是用断裂-连接的叙述线条在演绎着逃逸-追求这一民族文化进程的脉络。阿罗史密斯的一次次逃逸,另一方面也是他的一次次壮大,在舍弃的同时,是更大的收获,这是人物的成长过程。阿罗史密斯是一个英雄,但首先更是一个普通人,他诚实、正直、聪颖、机敏、坚韧、不拘常规,富于想象力、活力和激情,渴望并富有创造性的开展工作的能力。但是他也有不少弱点,过于单纯急躁,不善表白,忽略沟通或缺少沟通技巧,缺少圆滑变通。他虽然从小就对医学、对生物学感兴趣,但并不像他的同学安格斯一样事业目标非常明确。在医学院三年级时由于表现出色担任戈特利布实验室的助手期间,他曾因医学功课和实验室工作的繁忙、想念利奥拉而产生的孤独寂寞而一度变得异常紧张脆弱,在工作出现差错遭到戈特利布的批评时,竟然扭头而去。事后他也拒绝向戈特利布认错,从此很长一段时间离开了戈特利布,直到来麦格克研究所工作,才回到戈特利布身边,坚定了科学理想主义的信仰,明确了自己科学研究的目标。
叙述者就是利用断裂-连接-发展的多元叙述线条呈现阿罗史密斯通过逃逸的方式来反省自己和自己前一段的生活,厘清自己的生活道路,对自己与社会组合的某个编码系统进行“解辖域化”。这是理想主义的召唤,也是性格中些许的实用主义成分产生的作用:逃逸此地,不必斗个你死我活,鱼死网破,退一步海阔天空。通过对上一情节的解语境化,叙述者最主要的是用“逃逸”来解决叙述进程中的局部冲突,表现人物思想上产生的“断裂、创新和新认知”的认识过程,这是刘易斯现代现实主义手法的典型显现,也是互文性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之文化研究理论的一个主要特征。⑤随着人物新认知的出现,随即就是新的追求,这强烈地表明阿罗史密斯的退却不是阿罗史密斯的失败,是他与社会某个编码系统的组合出了问题,随着与这个编码系统的断裂,由逃逸而获得了新的追求机会,连接了新的编码系统的组合,新的更有利于理想实现的机会。
詹姆逊认为最重要的解辖域化就是:“德勒兹和伽塔里称作资本主义公理的东西破解了(decode)旧的前资本主义的编码系统(coding),将其‘释放’出来以建构新的更具功能性的组合。这个新术语产生的共鸣可以用目前流行的一个更轻浮、甚至更成功的媒体术语‘解语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来衡量;它恰好意味着从原有语境中攫取的任何东西都可以在新的区域和环境中被‘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但解辖域化要比那绝对得多。”(詹姆逊:360)从詹姆逊的阐述可以看出,“解辖域化”就意味着断裂,对旧的不合时宜的东西的抛弃,逃向更有利的区域,通过“连接”,建构新的作用更大的组合,一个展示新的社会风情的粘性平面——社会大舞台。如阿罗史密斯从惠西法尼亚村到诺梯拉斯市公共卫生局,从公共卫生局到芝加哥高级私人诊所,再到纽约麦格克研究所,他的每一次逃逸都连接了另一个社会舞台,建构了一个作用更大的组合。也就是说阿罗史密斯从导致退却的行为中得到了锻炼,获得了经验,这是他的宝贵财富,断裂-连接的逃跑-追求过程,也是阿罗史密斯积累财富和转移财富、寻求更大发展壮大的过程。因此,阿罗史密斯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强大,更加坚定,对自己能力和兴趣的认识更加深刻,离成长为一个坚强的科学理想主义英雄也就更近了一步。
由此,我们看到,从断裂-连接-发展的叙述结构中,叙述者逐步建构了一个真实、可信、丰满的英雄人物形象,一个极具个性化的人物形象。四部杰作中,唯有《阿罗史密斯》得到了批评界相对一致的认可,被授予普利策奖,但也唯有这部作品没有获得当时著名文学批评家H.L.门肯的钟爱,他倒非常欣赏《阿罗史密斯》中最受讽刺的人物公共卫生官员皮克博——一个不学无术、但却能大张旗鼓地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的吹鼓手,认为他是《阿罗史密斯》中迷人的巴比特,美国各地都可看见他的身影。他认为阿罗史密斯一个重要的失误是:他是个个性化的人物,不具有典型性,他不是一个合适的美国人。(Bloom:2)门肯的言外之意是阿罗史密斯不是大众化的形象人物,这种人物在美国太少。门肯说得确实没错,这种人物在美国太少,戈特利布也是这么认为的。他在学生中发现了阿罗史密斯,夜深时站到埋头做实验的阿罗史密斯身边说道:“好极了!你手艺不错。啊,科学里有一种艺术——只是对少数人才有。你们美国人,你们这么多的人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想法。可是你们对这种美妙而又单调的长期努力没有耐性。……五年中我一次也没得到懂得技艺、懂得精确性、也许还具有某种对假说的巨大想象力的学生。我想你也许具有这些品质。”(刘易斯:45-46)门肯的埋怨从另一侧面理解,又是对刘易斯艺术成就的极大赞扬,这一点也足以反驳批评界有关刘易斯的小说人物简单化、类型化的观点。它说明刘易斯不但能生动逼真地刻画巴比特似的典型人物形象,也能成功地塑造丰满逼真的阿罗史密斯似的个性化人物形象。
门肯坦言阿罗史密斯这样的人在美国很少见,戈特利布在五年中才能发现一个像马丁·阿罗史密斯这样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品质的学生,刘易斯写作初始的目的也志在写一位“对一切生命有无限影响的医生”。(格雷布斯坦:84)而阿罗史密斯也不负众望,他用发现的噬菌体拯救了西印度群岛圣休伯特岛上染上鼠疫的无数生命。这个小岛虽然属于英属殖民地,但人们心中似乎没有多少国界的概念,居民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这是很有全球化多元文化的象征意义的。此外,叙述者安排德国籍犹太人戈特利布做阿罗史密斯的科学引路人,阿罗史密斯后来在麦格克研究所所取得的每一步成功都凝聚了戈特利布的心血。另外,是瑞典籍预防医学家桑德利厄斯帮助阿罗史密斯在圣休伯特与鼠疫作战,并为此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与阿罗史密斯的爱妻利奥拉一起长眠在这座热带岛屿上。这种人物关系上的叙事结构组合蕴含着作者内心的一种超越国界的文化视野,再联系作品第一章开始时叙述者给予阿罗史密斯身上所流淌的多民族血脉,我们说,阿罗史密斯身上的国界也已经被解辖域化了,他的科学理想主义已经破碎了疆界的辖域,刻上了世界多元文化的烙印。
综上所述,小说《阿罗史密斯》纵向的断裂-连接-发展的线性叙事进程演绎的是阿罗史密斯对自己与美国社会医疗机构的组合之解辖域化,是阿罗史密斯成长为一个坚定不移的科学理想主义者的磨炼历程;横向的人物关系的叙事结构的组合蕴含的则是一种解辖域化的全球视野。由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关于全球化,《阿罗史密斯》的可靠叙述者已成功地通过这纵横交错的叙事结构,帮助作者在他的文学创作实践中先行一步。阿罗史密斯为了不受干扰,宁愿抛弃眼前的功名利禄,退至山林也要坚持全力以赴地进行科学实验,这种实事求是,百折不挠的求索精神无疑就是当年科学家诺贝尔先生及所有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真实写照。小说以马丁·阿罗史密斯和特里·威克特躺在荒林小湖中的小船上而结束,在文本的潜流中,佛蒙特荒林小船已和当年“科学疯子”诺贝尔湖上飘荡的实验小船交接在了一起。诺贝尔奖也是没有国界的,刘易斯先生在自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把自己跨越国界、放眼世界的文化视野附注在了拓荒精神的传承者、世界各民族人民的儿子、科学家阿罗史密斯身上,把民族传统追求物质财富的拓荒精神提升到了对科学求是精神的追求高度,最后升华到多民族人民共同探索拯救全人类生命疾苦的境界。《阿罗史密斯》解辖域化的艺术手法所呈现的这种全球化的多元文化元素也是长期以来为批评界所忽略的一个重要主题,它为辛克莱·刘易斯这部小说的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注释:
①关于美国“集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于一体”的文化特征及其“逃逸”的表现形式,请参见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语言大学杨海鸥博士论文《辛克莱·刘易斯小说的文化叙事研究》中的详细论述。
②本文所指的辛克莱·刘易斯的四部杰作分别是:《大街》、《巴比特》、《阿罗史密斯》和《埃尔默·甘特利》。
③锥体虫是引起昏睡病的一种原虫,非常难以对付,非洲的一些村庄里,百分之五十的人患这种病,毫不例外是要致命的。参见Sinclair Lewis,Arrowsmith.New York:Harcourt,Brace and Company.1925.
④参见Martin Light,"The Ambivalence towards Romance," Mordern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Sinclair Lewis's Arrowsmith.Ed.Harold Bloom.New York:Chelsea House Publishers.1988.p.57.Robert Morss Lovett,"An Interpreter of American Life," Sinclair Lewis: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Ed.Mark Schorer.Prentice-Hall,Inc.1962,P32-33.
⑤参见由王逢振主编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文化研究和政治意识》的第356页。詹姆逊认为他能够为一种尚未成型的正统的马克思式现代主义理论作出两点贡献,其中一点是一个辨证的悖论,“即作为现代主义的现实主义,或从根本上作为现代性之组成部分的那一种现实主义,因此要求用传统上描写现代主义本身的一些方式来描写之:如断裂,创新,新认知的出现,等等。”可以说詹姆逊的这种现代主义的现实主义在某些方面揭示了刘易斯的现代现实主义的特点,只是刘易斯的现代现实主义除了具备詹姆逊的现代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内涵外,还包含有詹姆逊的现代主义的现实主义所没有的后现代主义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