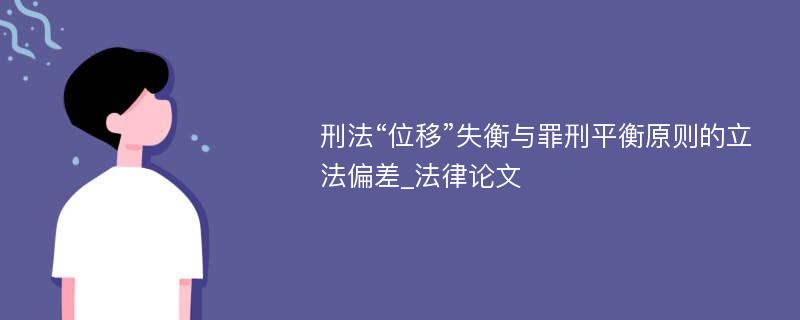
刑法“位移”中的不平衡及克服——罪刑均衡原则的立法背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位移论文,刑法论文,不平衡论文,原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24.1
文献标识吗:A
我国现行刑法出台之前,刑法学界曾存在着“大改”,还是“小改”之争。结果是,立法者基于“注意保持法律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的指导思想,[1]采纳了“小改”的方案。但同时立法者又怀着“修订出一部统一的、比较完备的刑法典”[2]的意图。在此情况下,刑法修改意味着既存的多元刑法规范体系(即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三种渊源并立存在)内发生一次规模较大的“位移”现象。具体来说,其一,自1981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陆续制定、公布、施行的20多个单行刑法,根据情况或迳行编入或修改后编入刑法典;其二,民事、经济、行政法律中130多条刑事法律条款被修改后纳入刑法典。也就是说,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中的刑法规范被“位移”入刑法典。显然,此种“位移”因欠缺法典编纂的整体和全局观念,(注:从法理学而言,法规整理可分为法律汇编和法典编纂两种形式,前者着眼于技术性处理,后者更强调规范的再设置。1997年的刑法修订,即不属于法律汇编,因为其存在“小改”;也不属于法典编纂,因为其缺乏全局整体观。借用地理学之概念,其可称之为刑法“位移”,因为地壳板块在位移过程中,在整体稳定的前提下发生部分变化。)势必造成法典内在的不平衡。在此,笔者拟以1997年刑法典分则若干罪状的设置为例加以佐证,并就不平衡现象的生成及克服加以探讨。
一、刑法“位移”中的不平衡的表现
现行《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刑法学界将其概括为“罪刑均衡原则”,[3](P76)也有将其概括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4]。罪刑均衡原则在刑法典中被确立后,首先就应在刑事立法中加以兑现,从而为罪刑均衡在司法活动中的实施提供制度保障。现行刑法吸收了大部分单行刑法、附属刑法中的刑法规范,从刑法的整体来看,其中,若干刑法分则条文的纳入,显然背离了罪刑均衡原则,从而引发出内在的不平衡。具体来说:
(一)《刑法》第140条叙明罪状中“销售金额”要素引发的不平衡(注:犯罪构成要件要素是犯罪构成要件的下属范畴(参见肖中华:《犯罪构成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1999年印,第20页)。)
例如,1993年7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1993年《决定》)第1条规定:“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违法所得数额2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以并处罚金”,在“位移”入刑法典时被修改为,“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罚金”(第140条)。其中,“违法所得数额”,被修改为了“销售金额”。从形式上说,此种修改是基于以下原因:
其一,消除“两高”对“违法所得”的不同理解。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决定〉若干问题的解释》(1995年1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审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刑事案件如何认定“违法所得数额”的批复》(1995年7月6日),将“违法所得数额”解释为“非法获利额”,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立案标准的规定》(1993年12月1日)将“违法所得数额”解释为“销售收入”。
其二,与计算“违法所得数额”相比,计算“销售金额”相对来说更为容易并且如果以非法的销售收入扣除成本,或者以非法的实际收入计算“违法所得”,实际上等于给犯罪分子“开工资”。[5]
其三,将扣除成本的所谓“违法所得数额”作为犯罪构成要件,与其他相关的犯罪也不协调。从实质上说,“销售金额”比“违法所得数额”更能体现或说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等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特别是在“违法所得数额”与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数额之间不一致的情况下,若将“违法所得数额”作为犯罪构成要件,显然未能真正把握犯罪的本质在于行为侵犯了合法权益,而不在于行为人获得利益”。[6]由此可见,立法者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中的构成要件要素“违法所得数额”修改为“销售金额”,显得更科学和合理,应予以肯定。
但是,立法者并未立足刑法整体的观念对性质类似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其他罪的构成要件要素“违法所得数额”作出统一修改。例如,1994年7月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的决定》第1条之规定:“以营利为目的,有下列侵犯著作权情形之一,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单处或者并处罚金,……”,在被“位移”入刑法典(即第217条)时却只字未改,刑法第218条也未将“违法所得数额”改为“销售金额”。显然,《刑法》第140条修改“违法所得数额”的原因同样存在于《刑法》第217条之中。前者作出改动,后者原封不动,势必造成这个罪横向之间的不平衡。上述两个条文关于“违法所得数额”的规定,改为“销售金额”就更为合适,因为对这两个条文规定的犯罪而言,“销售金额”的大小是完全与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成正比的,“违法所得数额”的大小与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一定成正比关系。
(二)《刑法》第358条第3款简单罪状中“协助组织卖淫”要素引发的不平衡
1991年9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1条之规定“组织他人卖淫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1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协助组织他人卖淫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1万元以下罚金”和第2条之规定“强迫他人卖淫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1万元以下罚金”,在“位移”入刑法典时被合并为“组织他人卖淫或者强迫他人卖淫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协助组织他人卖淫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刑法》第358条)。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1997年11月9日)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的罪名的意见》的规定,《刑法》第358条第3款设置了一个独立的罪名“协助组织卖淫罪”。其中,协助是指在组织他人卖淫活动中起辅助作用,也即在组织者的指使、操纵和雇佣下,为组织者完成组织他人卖淫行为提供便利条件,通常表现为:①以招工为名帮助组织者招募、诱骗他人卖淫;②为组织他人卖淫的犯罪分子充当“皮条客”,四处勾引嫖客、牵线搭桥;③为组织者充当保镖,为其看家护院,望门把风;④为组织者充当管帐人,收支卖淫活动的收入,等等。显然,按照共同犯罪理解,第3款规定的协助组织他人卖淫行为,其实就是第1款“组织他人卖淫罪”的帮助犯,即我国刑法中的从犯。立法机关将非实行行为即帮助行为予以独立罪名化,一方面,会在司法中产生不利影响,因为在有些情况下,协助与被协助之间关系十分难以区分,如果作为共同犯罪处理,不需要作细致区分,从而可避免因区分不当而发生定性的错误;同时,独立罪名化割裂了与组织卖淫罪的联系,从而失去处罚上的比照对象,从而导致量刑失衡的后果。[3](P579-580)另一方面,也引发刑法典中的内在不平衡。因为,组织卖淫罪并非犯罪的特殊形态。
首先,从组织行为来看,《刑法》第120条“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第294条第1款“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第306条第1款“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第300条第2款“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利用迷信致人死亡罪”、第317条第1款“组织越狱罪”、第318条“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第333条第1款“非法组织卖血罪”、第364条第2款“组织播放淫秽音像制品罪”、第365条“组织淫秽表演罪”等中都包含组织行为,但立法者在上述罪名之下并未再将非实行行为中帮助行为予以独立罪名化。
其次,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来看,组织卖淫罪侵犯的法益是社会风俗;从刑法分则体系来看,社会风俗并非比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命权、健康权等法益更重要。因此协助组织卖淫的行为社会危害严重性也并不比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人身权利罪中大部分共同犯罪形态中的帮助犯严重。因此,其也并不需要专门予以独立罪名化,以表征立法者的严厉的否定性评价。
再次,从《刑法》第358条第1款的规定来看,立法者将1991年《决定》第1条“组织卖淫罪”和第2条“强迫卖淫罪”予以合并,同时规定了相同的法定刑档次。此种多罪名一条文规定的合理性暂且不论,至少可以发现,立法者已认为组织卖淫罪与强迫卖淫罪的社会危害性大体相当。因此,单独将协助组织卖淫予以独立罪名化,而不同时将协助强迫卖淫予以独立罪名化,势必造成同一条文内的不协调。
最后,从刑法的总分则关系来看,《刑法》第27条已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总则条文普遍适用于刑法分则条文,因此,《刑法》第358条第3款通过设置独立罪名而排斥《刑法》总则第27条的适用,并无必要,反而可能徒增司法的麻烦,进而导致定性不当与量刑失衡的结果。
(三)刑法第326条引证罪状中“违法犯罪分子”要素引发的不平衡
1991年9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8条之规定:“旅馆业、饮食服务业、文化娱乐业、出租汽车业等单位的负责人和职工,在公安机关查处卖淫、嫖娼活动时,隐瞒情况或者为违法犯罪分子通风报信的,依照刑法第162条的规定处罚”,在“位移”入刑法典时被修改为“旅馆业、饮食服务业、文化娱乐业、出租汽车业等单位的人员,在公安机关查处卖淫、嫖娼活动时,为违法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情节严重的,依照本法第310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显然,《刑法》第362条将1991年《决定》第8条“依照……规定处罚”改为“依照……规定定罪处罚”,已表明第632条没有设立独立的罪名。但是,该罪状中的“违法犯罪分子”要素显然不能与第310条之规定相协调。《刑法》第310条第1款规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显然,《刑法》第310条“包庇罪”的犯罪对象必须是“犯罪的人”,而《刑法》第362条中的“违法犯罪分子”则可作出两种解释:其一,狭义解释,即指“犯罪分子”;其二,广义解释,即指违法分子(一般违法)和犯罪分子(严重违法),其中狭义解释则难以与《刑法》第362条中的“情节严重”的综合性要件相协调,广义解释则难以与《刑法》第310条的“犯罪的人”相协调。
(四)《刑法》第414条叙明罪状中“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犯罪行为”要素引发的不平衡
1993年7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第10条第1款之规定:“负有追究责任的国家工作人员对有本决定所列犯罪行为的企业事业单位或者个人,不履行法律规定的追究职责的,根据不同情况依照刑法第188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在“位移”入刑法典时被修改为“对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负有追究责任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不履行法律规定的追究职责,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按照“两高”有关刑法分则罪名的解释,第414条设置了独立的罪名“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显然,该罪状中“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要素的类型化和特定化,也会引发刑法典内在的不平衡。除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外,社会现实中尚存在其他种类犯罪行为,其中部分犯罪行为也可能是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义务去追究的对象,但是唯独将“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予以独立罪名化,而不将放纵其他犯罪行为予以独立罪名化,显然,有损于刑法的整体内在平衡。
(五)《刑法》第311条叙明罪状中“间谍犯罪行为”要素引发的不平衡
1993年2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26条之规定:“明知他人有间谍犯罪行为,在国家安全机关向其调查有关情况,收集有关证据时,拒绝提供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分,或者由国家安全机关处15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的,比照刑法第162条规定处罚”,在“位移”入刑法典之后,成为独立的罪名“拒绝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罪”,并有相应的法定刑。“间谍犯罪行为”的具体含义与“反革命罪”类罪的修改密切相关。原《刑法》第97条规定:“进行下列间谍或者资敌行为之一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一)为敌人窃取、刺探、提供情报的;(二)供给敌人武器军火或者其他军用物资的;(三)参加特务、间谍组织或者接受敌人派遣任务的。”刑法学界曾对该条所设的罪名存在“两罪名说”:[7](一)、(三)项的间谍罪和(二)项的资敌罪和“三罪名说”[8]——(一)、(三)项的间谍罪、特务罪和(二)项的资敌罪。显然,两者的分歧在于特务及特务组织能否被扩大解释入间谍及间谍组织,同时也就会影响到间谍行为的具体内涵。《刑法》第110条规定:“有下列间谍行为之一,危害国家安全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一)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的;(二)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的”。其中,第(一)项沿用了《国家安全法》第4条第(二)项的规定,不再具体区分间谍与特务、间谍组织与特务组织,第(二)项则渊源于《刑法》第100条“反革命破坏罪”的第(四)项。而原《刑法》第97条第(一)项则被《刑法》第111条独立罪名“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予以涵括。
基于上述间谍犯罪的较大修改,刑法学界对第311条中的“间谍犯罪行为”存在不同观点。有人认为,其仅指《刑法》第110条规定的间谍罪;[8]有人认为,除间谍罪外,还应包括第111条规定的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9]。显然,前种观点可以由新刑法条文作为依据,后种观点可以从刑事立法史的角度寻找理由。间谍犯罪的内涵的不同理解除会影响《刑法》第311条与相关条文的协调外,“间谍犯罪行为”作为“拒绝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罪”的要素类型化、特定化,也会引发刑法典内在的不平衡。设置本罪的目的是为保障国家安全机关对间谍犯罪的侦查诉讼活动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此立法精神是应予肯定的。但是在刑法未专门设立“拒不作证罪”的前提下,立法者只通过第311条专门将拒绝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的行为予以犯罪化,而不同时将拒绝提供其他比间谍犯罪更为严重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如背叛国家罪、分裂国家罪、武装叛乱、暴乱罪、颠覆国家政权罪等)证据的行为予以犯罪化,显然会破坏刑法整体的内在平衡。
二、“位移”不平衡的克服
根据法理学的观点,一个国家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法律部门而形成的有机联系的整体,被称之为法律体系[10]。法律体系是大系统,各部门则是小系统。大系统的功能的有效发挥,离不开小系统的有序平衡与协调统一。刑事法律作为法律体系中的“保障法”,内在的平衡与整体协调自然会直接影响到刑事法的保障功能的发挥,进而也关系到整个法律体系的运作效率和功能发挥。
在1997年刑法修订过程中,立法者确立了“制订一部统一的、比较完备的刑法典”的指导思想。因而,刑法典内在平衡就直接反映着整个刑事法规范体系的有序协调状态。(注:在此需指出,刑法规范的单一渊源体制也只存在相对较短的一段时间,1997年刑法典施行后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颁布了单行刑法《关于惩治外汇犯罪的补充规定》,同时在《证券法》中设置了附属刑法规范。这样,在刑法规范的多元渊源体制之下,刑法规范体系的有序状态则不仅仅反映在刑法典的内在平衡,也依赖于各种刑法规范渊源之间的外在平衡。)从总体而言,1997年刑法典无论在价值观念的转换,还是在立法技术的提升;无论是刑法基本原则的确立等宏观问题,还是具体罪状的设置等微观问题,都值得肯定。但是,刑法修改反映出来的问题与不足也依然存在,在此不作深入探讨。
前述若干条文引发的刑法典内在不平衡,就表明刑法典未能采取“法典编篡”方式,并立足于整体的观念对全部现存的刑法规范加以重新设置所造成的局限。上述条文在未被“位移”入刑法典之前,单从既有渊源来看,其本身都有一定的语境(context)合理性。例如,《刑法》第311条“拒绝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罪”罪名在《国家安全法》中是比照原《刑法》第162条处罚,独立罪名的设置显然可弥补刑事诉讼法中有关证人作证义务规范欠缺法律后果的缺陷,从而确保国家安全机关对间谍犯罪的侦查活动的顺利进行;《刑法》第414条中的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的行为在1993年《决定》中是依照或者比照原《刑法》第187条处罚,显然可以强化对伪劣商品犯罪的刑事惩治功能;《刑法》第358条第3款的“协助组织卖淫的行为”在1991年《决定》中作为第1条第1款“组织卖淫罪”之后的第2款,在“强迫组织罪”没有被合并而是独立存在(即《决定》第2条)的前提下,至少可排除刑法在将组织卖淫罪与强迫卖淫罪合并规定的情形中所引发的条文款与款之间的不协调。但是,上述条文被“位移”入刑法典之后,立足于刑法典的整体层面,先前的语境合理性就不存在,反而引发出了内在的不平衡。总之,上述条文的简单“位移”所引发的内在不平衡,至少可以表明1997年刑法修改所采纳的“小改”方案留下了深层的后遗症。
同时,在法典必须维持相对稳定性以确保法律权威,此种不平衡在相对长时期未能通过刑法创制(包括废、改、立)活动加以纠正的前提下,将始终存在于“纸面上的法律”中;同时,多少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影响着司法活动。“法是需要解释的,法在解释中存在并在解释中发展”,[3](P718)“法是为实现自我(sich verwirklichen)而存在的,法的实现(verwirklichung)就是法的生命,才是真实的,法的实现就是法的自身。如果法不能实现,只是单单存在于法规中、存在于纸上,那就只是虚幻的法,是空洞的语言。相反,如果法是实现了的东西,即使在法规中不存在,即使人民和法律学都没有意识到它,它也是法”[11](P354)(耶林语)。因此,纸面上的法律的不平衡,必须借助于司法者在司法解释中的主观能动活动尽量加以纠正,使不平衡在“行动中的法律”上最大程度的恢复平衡。例如,针对《刑法》第217条、第218条关于“违法所得数额”的规定与第140条“销售金额”的规定不协调,司法者在确认第217条和第218条之犯罪的本质是侵犯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可以通过承认刑法用语的相对性的手段将第217条和第218条的“违法所得数额”解释为第140条的“销售金额”(注:在此需指出,作此种解释,并不意味着应当将刑法中的“违法所得数额”均解释为“销售金额”。其中,只有司法者在确认某罪的本质类似于《刑法》第140条属于“侵犯合法权益”的前提下,才能将“违法所得数额”解释为“销售金额”。显然,这就要求司法者发挥更大的主观能动性(参见张明楷:《刑法第140条“销售金额”的展开》,载《清华法律评论》(第二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6页)。),从而可以克服两者之间的不平衡并使之达到协调统一。当然,针对其中部分“先天的”结构性内在不平衡(注:相对于因社会各种生活关系的变迁而引起的法典的不平衡而言,刑法“位移”中因缺乏全局整体观念而造成的不平衡 ,属于“先天性”和“结构的”不平衡,相反,前者则属于“后天性”、“进化的”不平衡。借用法律泼洞之“原始漏洞与后发漏洞”划分观点(参见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258页),其可被称之为“原始不平衡”和“后发不平衡”,前者指法律制定之当时即已存在的不平衡,后者指法律制定当时不存在,后因情事变更而发生的不平衡。),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解铃还需系铃人,也就是说,刑法创制(包括废、改、立)活动者是最终克服不平衡的途径。例如,《刑法》第311条可通过设立“拒不作证罪”来加以替代,《刑法》第358条第3款“协助组织卖淫罪”加以废止,《刑法》第326条可通过删除“情节严重”综合性要件加以协调,等等。
最后需指出,正如日本民法学者我妻荣论证的,“各个时代的全部法律体系,在一定时期的横断面上没有矛盾的体系是不存在的”。[11](P379)因此,立法者只能尽力在法典编纂过程中最大程度的将刑法总则中确立的三大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罪刑均衡原则、罪刑平等原则)加以兑现以减少“原始不平衡”,(注:从理论上而言,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既是立法原则,又是司法原则。在某种程度上说,立法上贯彻三大基本原则更为艰难,也更具有奠基功能。刑法“位移”中的不平衡其实就是未能具体兑现三大基本原则而呈现的结果。)至于最后不可避免而留下的部分矛盾和破绽(包括“后寻不平衡”),则只能由法学家的法学理论去缝补、司法者的司法活动去调和。“现实的法律秩序不是一件简单的合乎理性的事物,它是一个复杂的或多或少地不合理的事物”,[12]因此,法律人(包括所有关涉法律领域的人)应努力把理性加入进去,从而建构出最大程度的理性秩序。
收稿日期:2000-03-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