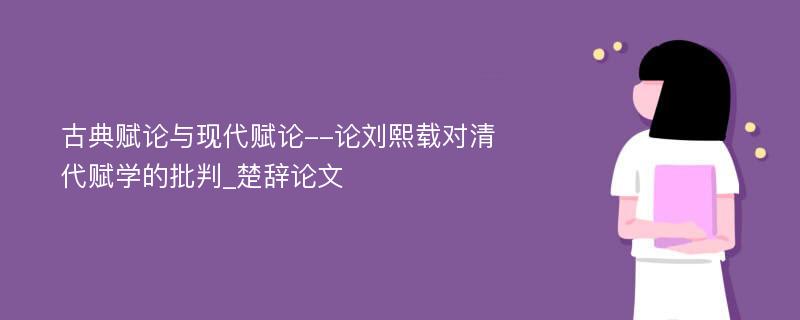
在古典赋论与近代赋论之间——论清人刘熙载的赋学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人论文,近代论文,批评论文,古典论文,刘熙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 2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194(2009)04-0064-05
《赋概》是刘熙载《艺概》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概·自叙》作于同治癸酉年(公元1873年),可知《艺概》成书于近代社会前期。因此,张少康先生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中肯定《艺概》“是近代时期总结和发展传统文论方面的最重要著作。”①《艺概》之《赋概》部分尤能体现出总结和发展传统文论的特点。然而,近代时期,新的科学的赋论体系也在萌生之中,因此研究刘熙载写成于近代时期的《赋概》及其对近现代赋学批评的影响又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一、刘熙载论赋之体
刘熙载谈文论艺有“举此以概乎彼,举少以概乎多”的特点,其论赋也有这样的特点。这一方面与刘熙载受传统诗话、词话的影响有关,一方面也与其治学方式有关。其《艺概·自叙》中说:“顾或谓艺之条绪綦繁,言艺者非至详不足以备道。虽然,欲极其详,详有极乎?若举此以概乎彼,举少以概乎多,亦何必殚竭无余,始足以明指要乎!是故,余平昔言艺,好言其概。”这不仅说明了《艺概》命名之由,也说明了刘熙载治学之特点。他对作家作品的评定,对艺术的本质特征及其内部规律的阐释,皆能举此以概乎彼,举少以概乎多,精炼概要,发人深省。刘熙载并无专论赋之体的专章,但我们仍可以从其文集的《赋概》部分看到这样一些论述:
班固言:“赋者,古诗之流”,其作《汉书·艺文志》,论孙卿、屈原赋有恻隐古诗之义。刘勰《诠赋》,谓赋为六义附庸。可知六义不备,非诗即非赋也。
诗为赋心,赋为诗体。诗言持,赋言铺,持约而铺博也。古诗人本合二义为一,至西汉以来,诗赋始各有专家。
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斯于千态万状,层见迭出者,吐无不畅,畅无或竭。《楚辞·招魂》云:“结撰至思,兰芳假些。人有所极,同心赋些。”曰“至”曰“极”,此皇甫士安《三都赋序》所谓“欲人不能加”也。
诗,持也,此义通之于赋。如陶渊明之《感士不遇》,持己也;李习之之《幽怀》,持世也。
刘熙载“诗言持”、“诗者,持也”之说源于刘勰《文心雕龙》,《文心雕龙·明诗》云:“诗者,持也,持人性情。”但刘熙载在其《持志塾言叙》中对“持”之义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他说:“孟子始言‘持志’,志之赖于持也久矣。持之义不一端,大要维持之欲其正也,操持之欲其久也。”②近代诗人、文论家王闿运在《湘绮楼论诗文体法》中也曾说:“诗,承也,持也;承人心性而持之,以风上化下,使感于无形,动于自然。”③因此刘熙载论赋为诗体,实是从诗心、赋心相通的角度出发,认为“诗为赋心,赋为诗体”,“古诗人本合二义为一”。这从荀子、屈原赋“有恻隐古诗之义”④的角度看,也有一定道理。因此,刘熙载在《赋概》开篇中即说:“班固言:‘赋者,古诗之流’,其作《汉书·艺文志》,论孙卿、屈原赋有恻隐古诗之义。”广义上说,诗心、赋心之说,谈的又是文心。刘勰《文心雕龙·序志》云:“夫文心也,言为文之用心也。”刘熙载作为刘勰之后通论各体文学创作的文论家,其对诗心、赋心的论述实际上继承了刘勰对文学创作主体之用心进行评判的特点。刘勰虽有“诗为乐心,声为乐体”⑤之说,但刘勰论赋时未谈赋心、诗心,因此刘熙载此论实是“扩前人所未发”。
刘熙载进而认为诗赋始各有专家是从西汉开始的,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近代学者章太炎在《国故论衡·辨诗》中谈到诗赋关系时,就曾以荀子《赋篇》为例,说明诗赋未离之时的情形:“屈原、孙卿诸家,为赋多名。孙卿以《赋》、《成相》分二篇,题号已别,然《赋篇》复有佹诗一章,诗与赋未离也。”⑥荀子虽是文学史上以赋名篇的第一人,但赋体文学发展为一代之文学,却是从西汉时期开始的。刘熙载既认为诗心赋心相通,又能够从文学和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到诗赋各有专家,同时指出赋与诗的区别,即“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他看到了赋的内容涵量非一般的诗所能相比的特点,揭示了赋体本质上的特点,他的这一精辟之论得到了现当代学者的一致认同。刘熙载从诗赋关系入手论赋之体的内容,深入精警、启人深思,对于我们从新的角度考察近现代文体分类中何以有人把赋归入诗歌一类是有启发作用的。
其次,刘熙载论骚赋关系也与论赋之体关系密切。刘熙载受宋元以来赋学批评上的祖骚宗汉说影响较深,他说“骚为赋之祖”⑦,也认为汉代存在辞赋通称的现象,其《赋概》云:“古者辞与赋通称。《史记·司马相如传》言‘景帝不好辞赋’,《汉书·扬雄传》‘赋莫深于《离骚》,辞莫丽于相如’,则辞亦为赋,赋亦为辞,明甚”;“《橘颂》品藻精至,在《九章》中尤纯乎赋体。《史记·屈原传》云:‘乃作怀沙之赋。’知此类皆可以赋统之”。刘熙载虽然认同辞赋通称,但汉赋与楚辞仍有明显的区别,因此在《赋概》中刘熙载又概言楚辞与汉赋的不同之处,《赋概》云:“《楚辞》尚神理,汉赋尚事实。然汉赋之最上者,机括必从《楚辞》得来。”刘熙载虽极推崇楚辞,但在比较中道出了汉赋所具有的特点,内涵非常深刻。这种骚赋通称和崇骚的倾向在近代赋论中比较普遍。近代学者刘师培也对骚赋关系发表了看法,认为骚体同赋体。他说:“观班《志》之分析诗赋。可以知诗歌之体,与赋不同,而骚体则同于赋体。”⑧无独有偶,刘师培《论文杂记》第四也曾论曰:“秦汉之世,赋体渐兴,溯其渊源,亦为《楚词》之别派。”⑨章太炎也说“然言赋者,多本屈原”,他认为汉世贾生、司马相如、枚乘、刘彻、东方朔、刘向等,“未有出屈、宋、唐、景外者也。”⑩可见刘熙载赋论宗骚的倾向既继承了清代古赋派的崇骚观,也在近代赋学批评中具有代表性。
二、刘熙载论赋之创作
刘熙载论赋之创作的内容较多,他论赋往往能融会贯通,“阐前人所已发,扩前人所未发”。(11)观其论赋之概要,着重从赋之创作主体、赋之立意、赋之艺术构思等几个方面论述。
刘熙载兼重创作主体即赋家的才学与人格。《赋概》中论赋与才学之关系时说:“赋兼才学。才,如《汉书·艺文志》论赋曰‘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北史·魏收传》曰‘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学,如扬雄谓‘能读赋千首,则善为之。’”他认为“故才弱者往往能为诗,不能为赋”;赋“言典致博,既异家人之语,故虽宏达之士,未见数数有作,何论隘胸襟、乏闻见者乎!”刘熙载对赋家之品格也非常重视。《赋概》云:“赋尚才不如尚品。或竭尽雕饰以夸世媚俗,非才有余,乃品不足也。徐、庾两家赋,所由卒未令人满志与!”刘熙载继承了我国古典文论文行并重的思想,重视作家的品格,强调赋家要有高尚的人格,尤不能“流连般乐”、“夸世媚俗”、“玩物丧志”。他说:“文不本于心性,有文之耻甚于无文”;“文,心学也。心当有余于文,不可使文余于心。”(12)
就赋之立意上,刘熙载认为“赋欲不朽,全在意胜”;“赋家主意定,则群意生。试观屈子辞中,忌己者如党人,悯己者如女媭、灵氛、巫咸,以及渔父别有崇尚,詹尹不置是非,皆由屈子先有主意,是以相形相对者,皆若沓然偕来,拱向注射耳。”刘熙载强调赋以意胜,但他认为这种意还需与己之情志相关,认为赋应有个人思想感情的表现,而不仅仅是对客观外物的模仿或如实记录。他举赋与谱录的区别时说:“赋与谱录不同。谱录惟取志物,而无情可言,无采可发,则如数他家之宝,无关己事。以赋体视之,孰为亲切且尊异耶?”刘熙载非常赞成宋代李仲蒙的说法即“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所以他又提出了情景相生以创作赋的理论:“在外者物色,在我者生意,二者相摩相荡而赋出焉。”并且说:“若与自家生意无相入处,则物色只成闲事,志士遑问及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他对赋中言情的重视,也与其诗心、赋心相通的观点有关。
在论创作的艺术构思上,刘熙载肯定创作过程中的想象和虚构。关于艺术想象,刘熙载推崇司马相如的赋作,他说:“相如一切文,皆善于架虚行危。其赋既会造出奇怪,又会撇入窅冥,所谓‘似不从人间来者’此也。至模山范水,犹其末事。”他认为:“赋以象物,按实肖象易,凭虚构象难。能构象,象乃生生不穷矣。唐释皎然以‘作用’论诗,可移之赋”;“赋之妙用,莫过于‘设’字诀,看古作家无中生有处可见。如设言值何时、处何地、遇何人之类,未易悉举”;虽虚构设辞难以一一举例,刘熙载仍以其“举少以概乎多”的方式,例举了前人之赋的创作,他说:“赋必合数章而后备,故《大言》、《小言》两赋,俱设为数人之语。准此意,则知赋用一人之语者,亦当以参伍错综出之。”又举张融《海赋》说明“赋须难有者尽有,更须难有者能有也”的创作观点。
三、刘熙载论赋之风格
刘熙载论赋之风格,尤重古赋之风格,他对古赋评价非常高,以至把古赋看成一种极理想化的天籁之作。他说“赋之尚古久矣”,并解释说,所谓“古”主要是“性情古,义古,字古,音节古,笔法古。”即从思想感情、主旨大义、用字、音韵、笔法等几个方面来看,古赋都有一种自然高古之美,古赋“调拗而谐,采淡而丽,情隐而显,势正而奇”。近代文论家唐才常也曾评雄深之西汉赋与藻丽之东汉赋云:“盖闻玉生于山,雕之则华缛;冰出于水,凿之则纷纶。惟不雕者完其太璞,惟不凿者顺其天真。是以西汉雄深,卓然典谟之制;东京藻丽,渐伤风骨之庳。”(13)这与刘熙载对古赋的推崇有异曲同工之妙。赋之古是与赋之骈化和律化相对而言的,所以刘熙载论古赋则说:“古赋意密体疏,俗赋体密意疏。”他认为由于俗赋隶事用典太多,以至其文气困踬不畅。刘熙载指出:“古赋难在意创获而语自然。或但执言之短长、声之高下求之,犹未免刻舟之见。”也就是说古赋以意格胜,而不像骈赋、律赋那样,刻意求句式之短长、音声之相和,而是自成天籁。
刘熙载推崇一种自然高古的风格,他论赋尤重高奇、重风骨、重意格。刘熙载以“奇崛”、“高奇”评淮南小山《招隐士》云:“‘诗人之优柔,骚人之清深’,后来难并矣。惟奇崛一境,虽亦诗骚之变,而尚有可广。此淮南《招隐士》所以作与?”“王无功谓薛收《白牛溪赋》‘韵趣高奇,词义旷远,嵯峨萧瑟,真不可言’。余谓赋之足当此评者盖不多有,前此其惟小山《招隐士》乎?”对枚乘《七发》,刘熙载则评以“雄奇之气”,《赋概》云:“相如之渊雅,邹阳、枚乘不及;然邹、枚雄奇之气,相如亦当辟谢。”对东汉及建安以后赋,刘熙载则重在评其风骨,评其意格,他说:“《楚辞》风骨高,西汉赋气息厚,建安乃欲由西汉而复于《楚辞》者。若其至与未至,所不论焉”;“建安名家之赋,气格遒上,意绪绵邈;骚人清深,此种尚延一线。后世不问意格若何,但于辞上争辩,赋与骚始异道矣。”这些论述不仅可以看出刘熙载宗骚以评赋的情结,同时,可以理解刘熙载论赋之风骨、意格的指向,他推崇楚辞之风,尤其推崇《离骚》的兼得风雅之致。因此刘熙载评赵壹之赋时,对其赋的风格显露不满,“未能如屈、贾之味余文外耳。”
刘熙载虽极推崇有风骨、气格的作品,但他也承认不同赋有不同的风格。他说:“屈子以后之作,志之清峻,莫如贾生《惜誓》;情之绵邈,莫如宋玉《悲秋》;骨之奇劲,莫如淮南《招隐士》”;“屈子之缠绵,枚叔、长卿之巨丽,渊明之高逸,宇宙间赋,归趣总不外此三种。”刘熙载在评赋的过程中,也看到不同人的赋有不同的风格,他说:“赋因人异。如荀卿《云赋》,言云者如彼,而屈子《云中君》亦云也,乃至宋玉《高唐赋》亦云也;晋杨父、陆机俱有《云赋》,其旨又各不同。以赋观人者,当于此著眼。”这种以赋观人,风格即人的观念既有孟子“知人论世”之意,也是风格即人的文学批评观的反映。
刘熙载论赋推重古赋的做法,在近代赋学批评史上也多有回响。1912年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序》中提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点,即“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14)王国维论赋即推古赋的代表——汉赋。章太炎也认为:“自屈宋以至鲍、谢,赋道既极,至于江淹、沈约,稍近凡俗。庾信之作,去古愈远……赋之亡盖先于诗,继隋而后,李白赋《明堂》、杜甫赋《三大礼》,诚欲为扬雄台隶,犹几弗及,世无作者,二家亦足以殿。自是赋遂泯绝。”(15)可见章太炎论赋也推崇汉魏而薄隋唐以后。近代学者姚华在其《论文后编》中则对律赋作品罕构名篇的原因作了分析,他说:“六代之际,相承递变,陆机、潘岳、谢庄、鲍照、庾信之属,酝酿陈篇,孕育新制,遂启唐风,更著功令,于是赋古今之目,较然分焉。今赋试于所司,亦曰律赋……自唐迄清,几一千年,或绳于场屋,或规矩于馆阁,其制益艰,其才弥局”;“律赋既行,古赋衰歇,格律拘束,不便驰驱,登高所能,复归于诗。于是李、杜歌行,元、白唱和,序事丛蔚,万物雄伟,小者十余韵,大者百余,皆用赋为诗,汉人所未有”;“清人律赋,往往有以五七言相间成篇者,或竟体七言,亦以为赋,虽出庾信,特律所不许,罕构名篇。”(16)姚华纵论赋史,其所论律赋之弊切中肯綮。以律赋取士造成赋体的衰落,这也是何以近代赋论家几乎均推重古赋的重要原因。
四、刘熙载论赋之鉴赏
刘熙载《赋概》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论赋之鉴赏的内容。刘熙载对赋的审美鉴赏虽有道德评价的趋势,但他论赋的独到之处并不在此,而是他运用了艺术理论中一些对应的概念、术语、范畴等,如文与质、真与伪、正与变、抑遏蔽掩与才颖渐露、丽与奇、幽深与显亮、拟效与本色、夷与险、精神与色相、思与辞等,对文学现象和赋家赋作进行了品评。“在我国古代文论中,辩证思想是屡见不鲜的,但像刘熙载在《艺概》中这样自觉地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辩证地来谈文论艺的,在过去文学批评史上并不多见。”(17)这种富于辩证精神的审美风格在晚清至民国的赋学批评史上也是比较有特色的。
刘熙载对赋的鉴赏是建立在感性认识和直觉思维的基础上的,但他又善于运用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概念、术语等,以相辅相成或相对相应的概念来立论。如他以“文与质”论荀卿赋与屈原赋的不同时说:“荀卿之赋直指,屈子之赋旁通。景以寄情,文以代质,旁通之妙。”这里的“文”指的是赋的形式和表现,“质”指的是赋的思想感情、内容、本质。因为荀子赋主要目的是说理,表现上有理胜其辞的特点,因此是“直指”。而屈原之赋善于以景寄情,感情的表现通过香草美人的表象所代替,也就是文以代质,富有文学性,所以刘熙载认为有“旁通之妙”。又如刘熙载说:“屈子之赋,贾生得其质,相如得其文,虽涂径各分,而无庸轩轾也。”其中的“文”与“质”仍不离本质与形式的内涵。古代文论中文质概念的运用比较普遍,如《文心雕龙》中文质概念的使用就不下几十处。但刘熙载却能形象地把这一概念运用于赋评中,取得了意在言外的艺术效果。至于刘熙载鉴评赋时所用的“思与辞”、“志与才”的概念,其内涵与他所用的文质概念的内涵也多有相通之处。
在对立概念的运用上,刘熙载还善于以表现方式的“隐与显”作为审美理想,他说:“骚之抑遏蔽掩,盖有得于《诗》、《书》之隐约,自宋玉《九辩》已不能继,以才颖渐露故也”;“言骚者取幽深,柳子厚谓‘参之《离骚》以致其幽’,苏老泉谓‘骚人清深’,是也。言赋者取显亮,王文考谓‘赋以物显’,陆士衡谓‘赋体物而浏亮’,是也。然二者正须相用,乃见解人。”刘熙载认为《离骚》“抑遏蔽掩”是继承《诗经》、《尚书》的隐约,实际上也就是说《离骚》在表现上具有委曲婉约、蕴藉含蓄的特点,而宋玉《九辩》的“才颖渐露”是指《九辩》主旨的表现上不再有蕴藉含蓄的特点,而是比较直露,作家逞辞倾向明显,这是艺术表现上隐与显的对举。而“言骚者取幽深”,“言赋者取显亮”是就骚与赋的艺术风格而论,这大体是承前人观点,但刘熙载认为“幽深”与“显亮”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虽然赋的表现方式可以昭明彰显,以增加作品的形象性,但赋以物显,赋中也应讲情景交融、事意贯通,避免作品的一览无余。所以刘熙载在《赋概》中又说:“《风》诗中赋事,往往兼寓比兴之意。钟嵘《诗品》所由竟以寓言写物为赋也。赋兼比兴,则以言内之实事,写言外之重旨。故古之君子,上下交接,不必有言也,以赋相示而已。不然,赋物必此物,其为用也几何!”这是极有见地的看法。王闿运在《湘绮楼论诗文体法》中曾说:“赋者,诗之一体,即今谜也,亦隐语,而使人谕谏。”(18)王闿运的论述,则从赋体探源的角度说明了赋作表现上“隐”与“显”的关系。
刘熙载不仅注意到文学鉴赏中对立概念、术语、范畴的应用,而且也常能指出对立概念、术语、范畴的转化。如在论赋之体的变化上,刘熙载认为《风》诗、《雅》诗和《离骚》可以正变论,他说:“变风变雅,变之正也;《离骚》亦变之正也。‘跪敷袵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屈子固不嫌自谓。”但他也能突破古典文论的正变论,提出了“真”与“伪”的概念。《赋概》中说:“赋当以真伪论,不当以正变论。正而伪,不如变而真。屈子之赋所由尚已。”刘熙载所谓屈子之赋的“变而真”,是指其表现形式上的异于《风》《雅》,但思想感情仍得《风》《雅》之精神。淮南王刘安叙《离骚传》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19),正可为刘熙载所论的“变而真”做进一步的注疏。在论赋之“理趣”与“理障”时,《赋概》云:“以老、庄、释氏之旨入赋,固非古义,然亦有理趣、理障之不同。如孙兴公《游天台山赋》云:‘骋神变之挥霍,忽出有而入无。’此理趣也。至云:‘悟遣有之不尽,觉涉无之有间。泯色空以合迹,忽即有而得玄。释二名之同出,消一无于三幡。’则落理障甚矣。”以此说明赋中有理趣之作,如果不能化理于景、融情于物,很容易落入理障。显然,刘熙载非常善于以形象化的例证来分析美学范畴对立概念之间的关系,具有极高的艺术鉴赏力。
刘熙载论文受到了传统《周易》哲学思想的影响。他曾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文,经纬天地者也,其道惟阴阳刚柔可以该之。”(20)《周易·说卦》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21)刘熙载认为经纬天地的文,其道也可以用阴阳刚柔来解释。因此在论赋的过程中也运用了这样一些可以相互对立,而又相应相成的极形象的概念、术语来鉴赏赋。这是刘熙载哲学思想上辩证精神的反映,也是刘熙载从理论上对近代赋学批评的重要贡献。当然,刘熙载论赋也有极通达之论,他在《赋概》的最后一则评论中说:“皇甫士安《三都赋序》曰:‘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刘彦和《诠赋》曰:‘拟诸形容,象其物宜。’余论赋则曰:‘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刘熙载论赋“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的态度,与其《昨非集·序》中所言“四十后乃始悔之。又后,则欲勿存之矣。既而思之:非与是,不容偏掩者也。是中有非,非中亦岂必无是”(22)的思辨有相通之处,其实都是富于辩证精神的反思,也表现出处于近代社会初期的学者科学求真的精神。
就刘熙载对中国赋学批评的贡献而言,目前赋学研究界已有人断言,“回顾中国赋学的历史,有‘三刘’的贡献甚大,分别是刘勰、刘熙载与刘师培。”(23)如果从对赋学思考的深度和理论体系的完整性上看,可以说刘熙载赋论直承以刘勰为代表的古典赋论并进而对近现代赋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40页。
②刘熙载:《刘熙载文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5页。
③舒芜等编:《近代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334页。
④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65页。
⑤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02页。
⑥章太炎:《国故论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86页。
⑦刘熙载:《刘熙载文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22页。
⑧刘师培:《论文杂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16页。
⑨刘师培:《论文杂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11页。
⑩章太炎:《国故论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91页。
(11)刘熙载:《刘熙载文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83页。
(12)刘熙载:《刘熙载文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75页。
(13)唐才常:《唐才常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00页。
(14)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15)章太炎:《国故论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91页。
(16)舒芜等编:《近代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659-660页。
(17)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612页。
(18)舒芜等编:《近代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334页。
(19)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9页。
(20)刘熙载:《刘熙载文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461页。
(21)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济南:齐鲁书社,1979年,第455页。
(22)刘熙载:《刘熙载文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09页。
(23)许结:《赋学:从晚清到民国——刘师培赋学批评简论》,《第七届国际辞赋研讨会论文集》,西北师大文学院,2007年,第48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