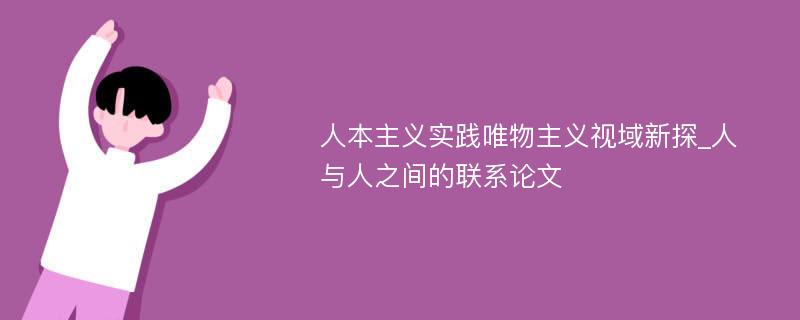
人学的实践唯物主义视界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主义论文,视界论文,人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西方人学思想史上,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人学显然具有独树一帜的个性,它既不同于传统的形而上学人学,也不同于后来的新康德主义、存在主义人学。马克思人学的独特视界是由它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在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中,准确地把握作为马克思人学思想基础的实践概念的内涵显得尤为重要。然而,毋庸讳言,近几年我国学术界在实践唯物主义的“共识”下,对马克思实践——人学内涵的理解显然已经产生了许多的分歧。在我看来,导致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不能对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几个维度之间的关系作准确地把握。不少学者单方面地抓住了马克思人学中的一个维度,并把它视为马克思人学的基础,其结果必然会导致无法正确地理解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人学的丰富内涵。
我认为,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在逻辑结构上是一种“三维结构”,它分别围绕着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的现实实践活动这三者来展开,这是一种类似长、宽、高三维座标的立体结构。任何孤立地从一种或者二种维度去对马克思人学思想的解释都将是片面的。下面我准备从马克思人学思想发展史的角度,结合对西方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的分析,来说明马克思人学思想的这种三维特性。
第一维:人与自然界的关系
马克思人学的实践唯物主义视界的标志不仅在于把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维度引入人学理论的研究之中,而且还在于对这一维度的内容在人学理论建构中的地位和价值作出了独特的、深层的把握。只要我们仔细地分析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发展史,理解这一点应当是不困维的。
在马克思理论活动的早期,如“博士论文”和“莱茵报”期间,马克思的人学是滞留在这一维度之外的,“主观性在它的直接承担者身上表现为他的生活和他的实践活动,表现为这样一种形式,通过此种形式他把单独的个人从实体性的规定性引到自身中的规定。”[①]这样的人学当然不可能具备实践唯物主义的“色彩”。
自“巴黎笔记”开始,马克思把“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的维度注入他的人学思考之中,“劳动”成了此时马克思人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尽管事实上马克思在“巴黎笔记”中的人学思想依然带有强烈的人本主义色彩,但这并不意味着就能抹杀把“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维度注入人学问题的研究对于马克思人学思想的成熟来说所具有的重要意义。马克思只是急于把理论诉诸于批判,所以未能真正地“消化”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在人的问题中的重要性,但他毕竟把仅仅在精神领域内游戏的“人”抛在了身后。
在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马克思找到了赋予“人对自然界的改造关系”真正的人学价值的理论立足点,即科学的实践观点。学术界有的同志认为《提纲》的第一条浓缩了整个《提纲》的精华,并以此为根据推论出马克思此时的“实践”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搞》时期的“劳动”概念之间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两者都是用来指称人类学意义上的、与人的主体性本质的发挥相联的劳动活动的。笔者不能赞同这种观点。在我看来,《提纲》中蕴含了下面三条不可分割的逻辑线索:人对外部环境的改造、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性、现实的实践活动,它们分别体现在《提纲》的第一、六、八条中。因此,《提纲》中的“实践”在内涵上远远超出“手稿”时期的“劳动”概念,并且,这两个概念之间还有本质上的不同,“实践”是个社会历史性的概念,而“手稿”时期的“劳动”只是一个人类学意义上的概念。因而,“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的维度在此时的马克思看来,只有与人与人的关系、现实的实践活动的维度紧密结合起来,才可能具有真正的人学价值。在这一思维视界上,人与人的关系便不再是关于人对自然界的改造行为的规范性设定,这种关系的改变不是听命于人的价值认知水平,而是受制于现实实践活动的发展。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这一点做了更加直接而清晰的论述,“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休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②]紧接着,马克思又作了如下的界定,“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③]人们的活动当然是指现实社会中具体的人的活动,因此,马克思这里实际上是把“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置于了由它自己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人的现实的实践活动”这三者构成的科学人学观的三维结构之中,这是对“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作出科学说明的保证。
从1847年《哲学的贫困》开始,马克思把他的实践唯物主义人学观凝炼成了一种科学的方法论,体现在具体的政治学、经济学等等研究中间。以经济学的研究为例,马克思集中探讨了由生产力、生产关系、物质生产活动这三个维度所构成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及其发展规律问题,其中,作为人类对外界自然界的改造能力之标志的生产力范畴当然是不可或缺的。“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④]“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⑤]。
现在我们来看看国外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的一些情况。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学者中,真正否定马克思人学思想中的这部分内容的,很少。他们大多保留人对自然界的改造这一理论环节,他们希望达到的只是在把人理解为个人或者在“合类性”的前提下把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人学人本主义化。真正希望否定这一理论环节的是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圈子之外的西方哲学家如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的“我们要把价值从一切现实的客观中分离出来”[⑥]道出了新康德主义在人的问题上的全部本性。认真地汲取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界在这一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是我们深刻地把握马克思人学的实践唯物主义视界的必要前提。
第二维:人与人的关系
我们还是从马克思人学思想发展的角度,来看看在这一维度上怎样的理解才算是真正代表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人学水平的思想。在理论活动的早期,马克思由于从精神自由的角度去理解人的特性,所以,从根本上说,他不重视并且就他当时的思想水平而言也无法理解人与人的关系的真实特性。譬如,在《博士论文》中,就像理解原子与原子之间的结合是“以外在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一样,马克思把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结合也理解为“无缘无故”的。
在《莱茵报》时期,从表面上看,马克思这时已经提出了“人民性”、“人民精神”等等概念,似乎他已经关注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其实不然,马克思这时关于人的主题思想仍然是个体的精神自由,他的理论指向无非是希望个体的精神能够像“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一样,挣脱“官方的色彩”,达到完全的自由。因此,这时的“人民”概念只是“个体”概念的无限膨胀而已,并不具有它自己的本质内容。
在《巴黎笔记》中,马克思认真地研究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从理论上说是应该能得出关于人与人的关系的正确结论的。然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迫切要求使他还没找到正确的批判方法就急于投入战斗,于是便不得不延用他以前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时的方法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此时经常提到“社会”、“类”等等概念,但他此时所理解的“社会”和“类”仅仅是一些个体凑在一起而已,它本身没有自己的特性,它的内容依然是个体的内容。马克思曾直接了当地指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这些个人是怎样的,这种社会联系本身就是怎样的。”[⑦]这种情况在理论上的反映就是马克思这时是通过“物”这个“窗口”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在他看来,作为人的生产活动的产物的“物”本来应当是对人的个性的确证,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不再是人的个性的“直接语言”了,而是成了“异化语言”,即“物”导致人与人之间产生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显然,马克思这时还没有从(生产)关系的“窗口”去得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的、科学的批判。在我看来,这是伦理的批判的一种必然,只要是基于伦理角度的批判,那么,其出发点必然是个性,即使你谈论再多的“类”或“社会”,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个体的“不再是无声的合类性”(卢卡奇语)而已。
即使在1844年的《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对人与人的关系的理解也不能说是完全清晰的。尽管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中,马克思已经明确地看到了利益关系的决定性,但尚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说明马克思对整个人类历史也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的。真正的转变发生在1845年3月的《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之中。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契机,纵观马克思1845年以前的思想发展,他始终认为,从市民社会出发必然会得出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结论,因为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人都是从市民社会出发的。而李斯特对自由竞争的市民社会的恐惧(关税保护主义的提出)则从反面启发了马克思,使他看到从市民社会出发的理论研究并不一定会得出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结果。这一转折是关键性的,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在评李斯特的这一手稿中对历史发展的现实剖析看出这一点。针对李斯特从纯人类学意义上把“劳动”美化为“促使头脑、胳膊和手从事生产”的观点,马克思说“谈论自由的、人的、社会的劳动,谈论没有私有财产的劳动,是一种最大的误解。”[⑧]“一种‘劳动组织’就是一种矛盾。这种能够获得劳动的最好的组织,就是现在的组织,就是自由竞争,就是所有它先前的似乎是‘社会的’组织的解体。”[⑨]这里的观点应当说是很清晰的,在把“劳动”理解为现实的社会物质活动的前提下,马克思已经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理解成了现实的社会关系,即使这种关系再“异化”也无妨。
在与这一手稿同时期所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对这一新思想有更直接的表述,“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⑩]马克思在这里明确地强调只有处于社会关系之中的人才是具有“现实性”的人,这是针对费尔巴哈,当然也是针对马克思自己的早期思想而言的。如果一般地说,人当然具有理想、伦理维度的特性,博学的马克思怎么可能不了解这一点?但问题在于,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领袖,马克思在反对了宗教神学和资产阶级“永恒真理”式的意识形态之后,他的理论阵地在哪儿?只有从现实的历史的人出发的思维方式才能证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暂时性和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马克思经过艰苦的理论摸索,努力想达到的理论目标就在于此。
跟上面的“第一维”的科学化过程一样,马克思对人与人的关系的正确认识也是建立在对另外二个维度的正确理解基础上的。马克思人学思想的这种三维立体特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更加详尽的阐述,“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11)“生产什么”是指人对自然界的改造能力,“怎样生产”是指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发展水平,这二个维度和“生产活动”的一致,便构成了达到科学水平的马克思透过物质生产这一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对人学问题的正确理解。
在此以后,马克思理论研究的对象尽管转移到了经济学等其它领域,但对人的问题的这一基本思维原则一直没有改变,“对人与人的关系”这一维度在人学问题中的地位的重视就更不必说了。《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始终围绕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生产关系。这便说明任何脱离这一维度去对马克思人学思想所作的解释都是不足取的。
西方和东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的绝大部分在这一问题上栽过跟头。出于意识形态或者用自己的理论注解马克思的需要,他们大多把马克思的科学人学观理解为基于人道主义的一种社会批判理论,“与许多存在主义者的思想一样,马克思的哲学也代表一种抗议,抗议人的异化,抗议人失去他自身,抗议人变成为物。这是一股反对西方工业化过程中人失去人性而变成自动机器这种现象的潮流。”(弗洛姆语)(12)“马克思已经超越了纯粹的哲学并创立了一种全面的批判社会理论”(马尔科维奇语)(13)。即使是自命为修正了早年理论错误的晚年卢卡奇也始终没法理解马克思理论中的批判性是怎么定位的,努力再三也还是把伦理上的“合目的性”和现实中的“因果性”视为马克思思想中并行的二条线索。基于上面的这种理解,他们或者把马克思的“人”理解为个人,如弗洛姆,“马克思的哲学……它的核心问题就是现实的个人的存在问题”;(14)或者把它理解为抽象的人类学意义上的类,如南斯拉夫“实践派”和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晚年卢卡奇从“不再是无声的合类性”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的“人”,认为自然界和人都具有“合类性”,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是“无声的”,后者是“不再是无声的”。(15)在对伦理学作哲学本体论论证的理论目的下,卢卡奇恐怕也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第三维:人的现实的实践活动
从对上面两个维度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从对人的内在价值的追求、伦理批判的活动还是对悬设的终极价值的实现的角度,都不能达成对马克思人学理论的正确理解,因为,“人的现实的实践活动”的维度是马克思人学思想内在结构的第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关于这一点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的证明是非常清晰的,在此不再详述。
为什么在马克思人学思想的结构中非要这一维度不可呢?弗尔巴哈和黑格尔在这一问题上的失败恐怕能说明这一点。跟其它青年黑格尔派分子不同,弗尔巴哈在思考人的问题时天才地面对了人与自然界、人与人的关系这两个领域,但是,由于他在理论的指导思想上并没有从对宗教神学的批判转移到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上来,因此,他没有把“人的现实的实践活动”的环节引入他的理论框架,这致使他在对上面两个领域的理解上也止步于前科学的水平。黑格尔也一样,尽管凭着辩证法的强劲力量,黑格尔把握到了人与自然界、人与人这两个领域的本质,但客观唯心主义的“神目”却阻碍了这一思想的表达和发挥,并且最后还不得不停留于半途而废的地步。在我看来,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无论是黑格尔还是费尔巴哈都没有真正摆脱18世纪自然主义思维方式的遗风。自然或者透过自然而表现出来的上帝是自己理论建构的最后支柱,这分别是18世纪的这种思维方式在费尔巴哈和黑格尔身上的体现。而我们知道,以现实实践为基础的思维方式恰恰是跟这种自然主义思维方式直接相背的。这是马克思在科学认识方法论上的超越,也是为什么只有他才能完成对人的科学把握的重要原因。
在对马克思人学思想这一维度的理解中,我们还要着重说明的是,为什么没有把人的价值追求的维度列入马克思人学的结构之中?我在这一问题上有以下两点基本看法:第一,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唯物史观)中是存在价值追求的维度的,正像许多学者所看到的,真理观和价值观在马克思那里是统一的。第二,但是问题是怎么统一?是像晚年卢卡奇理解的那样的外在统一呢,还是别的什么方式的统一?
马克思不是一个一般的人学家,他的人学思想并不指认关于人的所有问题。马克思是个历史——人学家,他关注的是历史活动中的人的特质。这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前提。近几年,国内学界的许多同志从实践的角度对马克思的思想作了新的理解,在学术进步方面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然而,其中也并非没有问题。在我看来,除了不多的几位学者之外,大多数人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无外乎有下面两类:第一,根本没有考虑人的价值追求的维度与马克思科学人学观的关系问题;第二,考虑到了这二者的关系,但找不到理解这种关系的方法。
这牵涉到对马克思的《关于弗尔巴哈的提纲》的一些段落的理解。在前三条提纲中,有些问题需要作完整的认识。譬如第一条,有些同志认为,费尔巴哈用“感性客体”取代了黑格尔的“思想客体”,马克思用“客观的活动”、“感性的活动”取代了费尔巴哈的“感性客体”,于是,马克思的“客观的活动”自然而然地就和人的思维问题远不可及了。在第二条中,有的同志也以“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16)这句话来宣布人的思维,即人与自己的意识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的“非法性”。于是,在考虑科学历史观和科学人学问题时便不需要考虑人的思维问题了。这种理解应当说是欠妥的。
马克思“提纲”的真正含义其实并非如此。第一条中,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仅仅因为费氏用直观的感性的客体取代了黑格尔能思的客体,而马克思用感性的活动取代了费氏的直观的客体,就断定马克思的“活动”跟人的思维(包括价值追求的向度)无缘了呢?这岂不是肯定了马克思和费尔巴哈是站在同一个思想水平上的了吗?第二条中,马克思其实讲得很明确,“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17)只要是具有“此岸性”的思维就有“现实性和力量”,这里哪有无原则地否认人的思维在历史中的作用的痕迹呢?在第三条中,“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8)这句话应理解为在实践中,人创造了新的环境,创造了新的社会关系,也创造了人的新的认识思维能力和价值追求水平。
上面对马克思“提纲”前三条的分析,实际上也回答了人的价值追求在马克思理论中的定位问题。马克思的思路是,只要是“此岸”的思维,只要是对“此岸”的价值的追求,在历史观中便有其地位和力量。“此岸”的价值追求不是空泛的抽象人道主义式的对人之价值的追求,而是处在社会关系(在阶级社会中是阶级关系)中的人的具体的历史性的价值的追求。马克思否定的是把整个人类历史看成是向一个悬设的终极价值回归的历程。上面这种历史性价值的追求在马克思的科学人学中当然是有重要地位的。再进一步,对这种价值的追求难道和人的现实的实践活动还是两个相互并列的东西吗?不。人们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整个实践活动本质上就是对人的具体的历史性价值的实现过程。
这便是我们没把人的价值追求的维度单独列入马克思人学思想之中去的原因。
以上是我对马克思人学思想的一点理解。最后,我还想强调的是,应当对马克思人学思想的“本文”内容和它在现时代的理论发展这二个问题作有限度的区分。对经典作家的思想在现实的背景之中进行理论的发展,这应当说是十分可取的,但这不应导致对经典作家思想本身的任何不切实际的阐释。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69页。
② ③ ⑩ (11) (16) (17)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页,第24页,第18页,第25页,第16页,第16页,第17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4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页。
⑥李凯尔特:《哲学体系》,图宾根,1921年,第113页。
⑦ ⑧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4~25页,第254页,第255页。
(12) (14)转引自《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第15页。
(13)参见《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与理论》,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
(15)《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42页。
标签: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实践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科学思维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社会论文; 卢卡奇论文; 科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