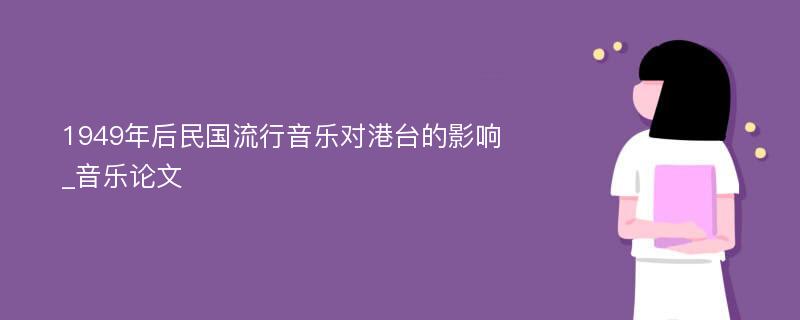
民国时期流行音乐对1949年后香港、台湾流行音乐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流行音乐论文,台湾论文,香港论文,年后论文,民国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时代的进步、视野的开阔和观念的渐变,越来越多的学者们开始以更具学理性的目光关注民国时期流行音乐和1949年后香港、台湾的流行音乐。由于研究兴趣使然,近年来笔者较关注上述二者的关系。在本文中,笔者将站在一个大陆学者的角度,努力挖掘民国流行音乐史的得失经验与“一国两制”①大背景下的港台流行音乐发展的关系,尤其是揭示后来流行音乐是否发扬光大了民国时期流行音乐的优秀传统、是否有意识地在避免重蹈历史上消极方面的覆辙。也就是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不论今日流行音乐界人士主观上是否承认,通过研究民国流行音乐史可以诠释今日流行音乐界许多看似无法找到答案的音乐现象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换句话说,在研究中笔者发现今日中国流行音乐界存在的诸多音乐现状恰好就是民国流行音乐史的一个变形,而变形恰恰就是历史的本质。鉴于此,本文将努力探寻民国时期流行音乐和1949年后两岸三地流行音乐之间的千丝万缕的“今昔渊源”。如果漠视这一点而孤立地研究民国流行音乐史,只会将研究的视野限定在一个相对狭小的范围之内。只有正视民国流行音乐史的“今昔渊源”,民国流行音乐的研究才有可能“更上一层楼”。
尽管民国“时代曲”②曾起过消极的作用,但这不应成为抹杀其历史积极性的理由。如果摘掉有色眼镜,我们不难发现“时代曲”中亦不乏一批包含暗喻、讽刺的优秀作品。其中,《讨厌的早晨》(电影《鸾凤和鸣》插曲,李隽青词、李七牛曲,周璇唱)和《三轮车上的小姐》(裘子野词、陈歌辛曲,云云唱)堪称“战时”和“战后”的经典之作,特别是后者甚至“受左派欢迎”③。“时代曲”在1949年后继续在港台被几代人传唱,两地的创作和体制均可见“民国”的影子,部分作品产生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歌曲本身,如《高山青》(电影《阿里山风云》主题曲,邓禹平词、张彻曲,张茜西唱)等。新中国成立后,大时代背景和审美理念的转变,使得“时代曲”无法在大陆找到立足之地。于是,一批颇负盛名的“时代曲”词曲作家、歌星、制作人等纷纷南下香港,先后促成了“大长城”、“百代”等唱片公司和“凤凰”、“邵氏兄弟”等电影公司在港的相继成立,重新开辟出“时代曲”的新天地。当然,“时代曲”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南移,它是随着时局动荡、人口迁徙,一步步地渗透进香港大众的文化生活中的。此时随着“国民政府”败退台湾,登岛的百余万大陆人口的精神需求在呼唤着“民国时代曲”,于是“海港派”(上海、香港的流行音乐)国语时代曲成了岛上“大陆人”慰藉乡愁的精神食粮。事实证明,民国时代曲之所以能够在1949年后传入港台并于30年后重返大陆,盖因两岸三地之间有着血浓于水的亲缘关系。香港尽管百年来一直受到英国的殖民统计,但居住于此的市民却是地道的广东人,底蕴深厚的岭南文化决定了港人在接受南下的时代曲时不会有太大障碍,更何况50—60年代粤语流行曲还处于襁褓之中。由于意识形态方面原因,台湾流行音乐起步要早于香港④,1949年后因当局“戒严文化”曾一度滞后于香港,后又与香港交相辉映,并与之一道携手席卷大陆。尽管自1988年8月⑤以来海峡两岸专业音乐界的交流逐步加强,但大陆受众了解台湾音乐信息最多的还是流行音乐。
社会环境
民国流行音乐滥觞于“五四”后期,辉煌于抗战、战后时期。滥觞期间,它目睹了思想的碰撞、白话文的推广和有声电影的崛起;辉煌期间,它和整个民族共同经历了八年抗战、三年内战,甚至连四年“孤岛”岁月也没有阻止它前进的脚步。与其他国家的流行音乐不同,民国流行音乐涌现、发达于社会转型之时。比起同时代的专业音乐,它好像有着更为顽强的生命力,政治的角逐、外敌的入侵似乎都没有从根本上将其摧垮,当然它也必须为自己“生不逢时”和常常“被利用”而付出代价。后来的香港、台湾之所以在70、80年代能够拥有自己的“粤语流行歌曲”、“中国现代民歌”,和两地跻身于“亚洲四小龙”不无关系,再次显示出社会转型对流行音乐创作“井喷”的影响之大。
和其他国家流行音乐相似的是,民国流行音乐的成长同样离不开现代科技的发展和依托。民国时期,收音机和留声机这两个当时较新颖的传播媒介极大地推动了时代曲的风靡,其影响之深、传播之广丝毫不逊色于此前的“学堂乐歌”,以至于张爱玲不得不感慨:“中国的流行歌曲,从前因为大家有‘小妹妹’狂,歌星都把喉咙逼得尖而扁,无线电扩音机里的《桃花江》听上去只是‘价啊价,叽价价叽家啊价……’外国人常常骇异地问中国女人的声音怎么是这样的。”⑥鲁迅也不得不忍受“《十八摸》……男嗓子的上低音(barytone)的歌声,觉得很自然,比绞死猫儿似的《毛毛雨》要好得天差地远。”⑦尽管鲁迅、张爱玲还没有喊出“打倒黎明晖”⑧的口号,但显然他们对《毛毛雨》、《桃花江》、《妹妹我爱你》等“时代曲”的印象不甚良好。二人之所以对当时的“黎派音乐”有着如是的感官印象,应该和此时的唱片灌录技术、录音设备有一定的关系。笔者相信,如果让黎明晖、周璇等歌星在今天的录音棚里灌录CD唱片,鲁迅、张爱玲这两位大家定会得出截然不同的新论。与民国时期相比,50—60年代的香港流行音乐因“邵氏兄弟”电影公司、“丽的”有线电视和商业电台的推波助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邵氏兄弟”秉承民国上海时代曲的一大特征—使流行歌曲能够乘着电影的翅膀飞得更高、传得更远。民国的流行音乐和电影音乐始终呈“支声复调”状向前发展,二者之间常常相互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前者大大扩大了电影的受众面,使得原本只关注“音乐”的受众逐渐加入到电影“粉丝”的队伍中来;后者成为继电台、唱片后流行音乐加快传播步伐的又一现代传媒,让一些原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的歌星一夜之间摇身变为万众瞩目的歌、影双栖的明星。尤其是在“后黎锦晖时代”(1937—1949年),二者携手并进,共同掀起了民国流行音乐、电影音乐的第二次高潮。此时“有线电视”却是一个新现象,是对民国流行音乐的一大突破,再一次强调了一个真理——流行音乐总是伴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亦步亦趋。而“商业电台”则是民国时期上海流行音乐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白先勇的一句“家家‘月圆花好’,户户‘凤凰于飞’”⑨非常形象地勾勒了一幅民国时期时代曲通过商业电台充斥于上海市民生活的图景,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流行音乐在第二个高峰时的盛况。尤其是60年代LP唱片的面世,更是在技术上延长了黑胶唱片单面灌录音乐的时间,使得香港百代在此间推出系列民国时期国语时代曲专辑成为可能。
无论是民国流行音乐,还是港台流行音乐,其孕育的温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产生地均为带有殖民地色彩的、开放的国际化大都市,如民国时期租界林立的上海,以及英国统治下的香港、日本占领下的台湾。自鸦片战争后,至新中国成立前,上海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西方殖民者在中国的聚集中心,其中也包括在民国时期纷纷来沪淘金、避难的西方专业演奏家和爵士乐师——“洋琴鬼”⑩。在此群体中,以来自菲律宾的舞厅乐师、俄罗斯沙皇时代宫廷乐师影响最大,他们基本占据了当时上海的主流歌舞厅以及唱片公司的舞台,为民国时期上海流行音乐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国立音专”于1927年落户上海。尽管当时和之后的诸“学院派”人士对“民国时代曲”和“港台流行音乐”嗤之以鼻,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民国时期乃至后来的港台流行音乐创作队伍中不乏“国立音专”的毕业生和肄业生,如冼星海、贺绿汀、刘雪庵、张昊、林声翕、黄飞然、黄贻钧、刘如曾、王福龄、周蓝萍等。即使是非该校校友的流行音乐作曲家,也有一部分直接或间接地受过该校乐雨新风的洗礼,如聂耳、綦湘棠等。从50—60年代香港人能够接受非自己方言文化的国语时代曲到70年代粤语流行曲被西方媒体称之为“Cantopop”,就不难看出香港在延续着民国时期的上海开放、多元的一面。而早在“日据时期”,台湾就有了自己的流行歌曲,如邓雨贤作曲的《望春风》(李临秋词)、《雨夜花》(廖汉臣词)等,但这些作品大都充斥着“哀怨之调”(11),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殖民地的烙印。直到“光复”后的一段时期内,在台产流行音乐中仍不难寻觅这种殖民伤痕。
坚持贵在创新,是民国流行音乐能够在“十里洋场”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时代曲”涌现之前,上海市民的娱乐主要局限于欣赏说唱、戏曲。然而当他们第一次通过电台和留声机听到用白话文而非文言文、用“国语”而非上海话、用“本嗓”而非耳熟能详的戏曲唱腔演唱的“时代曲”,却能毫无排斥地去张开双臂拥抱之,表现出海派创作者和受众群体“敢为天下先”的胆识和气魄。此外,上海人紧跟时代潮流的特点在民国时期流行歌曲创作中亦是不难见到,如“战后”的一曲《夫妻相骂》(李隽青词、姚敏曲,姚敏、吴莺音、逸敏唱)。该曲中有一句歌词——“这样的女人简直是原子弹”,而此时距美国人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刚过数日。由此可见,战后的时代曲着实体现了上海人在“与时俱进”方面的积极进取和海纳百川。随着“时代曲”的南下,善于与生活、时尚紧密相连的传统也逐步渗入到后来的港台流行音乐创作之中,直至80、90年代。1986年、1990年,台湾的李宗盛、刘铮分别推出了他们的首张个人专辑——《生命中的精灵》和《到底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前者和后者中的《老兵卖冰》(李安修词、蔡宗政曲,刘铮唱)均以口语化的语言,揭示了平民生活中平凡小人物的心态和生活处境,令当时的台湾乐坛耳目一新。
民国流行音乐之所以自诞生之日起就常常陷入被众多“学院派”人士和“进步人士”诟病的尴尬,除了其风花雪月的内容和“生不逢时”的出身外,批评者和诘难者多易忽略一个客观事实——“娱乐”是流行音乐的主要功能之一。早在1941年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Adorno)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在《论流行音乐》一文中指出:“另一方面,娱乐不仅是流行音乐的先决条件,而且是流行音乐的产物。”(On the other hand,distraction is not only a presupposition but also a product of popular music.)(12)遗憾的是,不论是民国时期,还是今天,依然有一部分“学院派”人士没有意识到“理解流行音乐须遵循耳听为实的原则。因为流行音乐有着自己的凝听习惯”(Understanding popular music means obeying such commands for listening.Popular music commands its own listening habits)(13),以至于经常拿着衡量交响乐、艺术歌曲的标准来审视流行音乐。这一点在大陆表现尤甚。作为民国时期上海娱乐业的支柱之一,舞厅、夜总会除了雇佣洛平(Lobing Samson)等“洋琴鬼”乐队和杰米·金(Jimmy King)、黄飞然等华人乐队,还催生了《别走得那么快》(狐步,Foxtrot)、《夜来香》(伦巴,Rhumba)、《春之舞曲》(圆舞曲,Waltz)和《人海飘航》(探戈,Tango)等一批带有浓郁舞曲风的“时代曲”。诸舞曲风格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出现,一方面是因为此时“时代曲”的作者们都希望能够为自己的歌曲寻找到适宜的来自欧美的不同风格的舞曲载体;另一方面也是为迎合当时舞厅林立的“十里洋场”对此类歌、舞一体的作品之市场需求,甚至有一部分作品就是为某些舞厅驻场歌手而量身定做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民国时期流行音乐曾一度掀起了如是舞曲风的“时代曲”创作浪潮,歌、舞相得益彰,饱耳福者和流连忘返的舞客在此类作品中各取所需、各享其乐,从一个侧面加速推动了民国时期流行音乐的发展进程。然而,由于意识形态迥异、时代步伐变化、地域文化差距等原因,1949年后两岸三地似乎再也没有重现如是舞曲风的流行歌曲创作浪潮。
创作传承
由于黎锦晖首先出于推广白话文的目的而开辟出一条新路——开创“时代曲”,因而民国“时代曲”大部分采用了“白话体与文言体并存的歌词”。(14)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地域的变化,1949年后香港、台湾流行歌曲的歌词创作仅部分继承了民国“时代曲”的衣钵——几乎摈弃了“文言体”、进一步发扬光大了“白话体”。尤其是到了70年代末以后,更是将“白话”拓展为“口语”和“俚语”,着实与民国时期文绉绉的词风相去甚远。伴随着沪人来港的还有其上海时期的合作者——菲律宾的“洋琴鬼”。因是时大陆流行音乐土壤的失调,一部分菲律宾“洋琴鬼”们不得不做出南下的选择,并逐步完成了从“洋琴鬼”到“香槟”(15)的身份转换,其无形中已然成为衔接民国时期上海时代曲和1949年后香港时代曲的纽带,基本实现了两地、两个时代的“无缝接轨”。值得一提的是,“香槟”在香港流行音乐界的影响直至今日依然存在,并保持着一定的艺术生命力,如鲍比达(Chris Babida)、戴乐民(Romeo Diaz)等。“香槟”和姚敏、李厚襄等南下作曲家们共同将国语时代曲带进香港这个陌生、崭新的世界,引领着50—60年代香港流行音乐的大步前行,以至于还吸引了黎锦光、严折西等部分滞留上海的时代曲作曲家屡屡间接地参与香港时代曲的创作。此举多少传达出两个信息:一方面说明此时香港已然取代了上海在民国时期流行音乐中心和基地的地位,另一方面反映出此时在上海“固守家园”的一批昔日时代曲的骁将们之无奈和望“港”兴叹。抵港后的姚敏因其曾任歌手和作曲家的经历,较能知人善用,遂成为香港流行音乐、电影音乐的领军人物,在重用姚莉、李丽华、白光、逸敏、张露等“老”歌星的同时,积极培养了葛兰、潘秀琼、静婷、刘韵等一批“新人”。用今天的话说,姚敏既是一位作曲家,同时又是一位“创作型”歌星。姚敏去世后,粤语流行曲虽已初露锋芒,但人们时不时在其中仍能捕捉到70年代前国语时代曲的影子,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涌现出一批根据前国语时代曲重新填词的粤语流行曲。
歌曲之所以比器乐更容易接受和传播,是因为它有歌词——这个文学拐杖。歌词的存在,使得受众在欣赏歌曲时有了理解上的依据,流行歌曲自然也不例外。无论是民国时期、1949年后的港台,还是今天的大陆,大部分流行歌曲的词作者都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情歌”。其中,以民国时期尤为普遍,堪称“无郎不成歌、无妹不落词”,如周璇唱的《候郎曲》、白虹唱的《郎是春日风》、张帆唱的《唱不完的郎》等。特别是1944年涌现出的将两首电影插曲《红歌女》(电影《鸾凤和鸣》插曲,李隽青词、梁乐音曲,周璇唱)、《歌女忙》(电影《鸾凤和鸣》插曲,李隽青词、严工上曲,周璇唱)合二为一的一首流行歌曲——《红歌女忙》,更是堪称民国“情歌”的集大成者。在此歌中,词作者巧妙地将早已广泛流传的六首歌曲的曲名、关键词镶嵌于该曲的歌词里,一方面使得歌曲显得更加俏皮、有趣,另一方面流露出词作者欲通过该曲对此前的诸经典流行歌曲作一小结的意图。在涉及的六首歌曲中,除了《卖糖歌》(电影《万古流芳》插曲,李隽青词、梁乐音曲,李香兰唱)以外,其他五首作品——《采槟榔》(殷忆秋词、黎锦光曲,周璇唱)、《四季歌》(电影《马路天使》插曲,田汉词、贺绿汀编曲,周璇唱)、《疯狂世界》(电影《渔家女》插曲,李隽青词、李七牛曲,周璇唱)、《卖相思》(包乙词、嘉玉曲,姚莉唱)和《郎是风儿姐是浪》(黎锦光词曲,周璇唱)均为情歌,无不于字里行间流淌着“郎”、“妹”、“情”、“爱”之字眼。尤其是当歌者周璇唱到“周璇的疯狂”和“李香兰的卖糖”这两句时,似乎更是于不经意间暗示着这两位歌星在当年歌坛的领军地位,虽然这其中也不排除该电影的制作方“华影”(伪“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有商业炒作之嫌。每听此歌时,笔者都不禁感慨民国后期流行音乐创作高峰令今人难以望其项背的情境。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的无数作品证明:爱情主题似乎没有地域、年代的界限,已然成为流行歌曲创作的一个永恒主题。究其原因,笔者以为“商品属性”是其主要根源。作为一个面向以市民阶层为主体的大众体裁,流行音乐不得不将主要精力投掷于“风花雪月”、“郎情妾意”的题材,而此题材的局限性决定了它必须以“浅吟低唱”、“怜香惜玉”的方式去表情达意。“爱情”,对于中国流行音乐而言就像是一个“胎记”,是与生俱来的、挥之不去的,不论是民国时期的上海和台湾,还是50—60年代的香港,也不论是改革开放后的大陆,还是今日之两岸三地,统统难掩此“胎记”。换言之,这是中国流行音乐在长期的发展中不得不遵循的一个生存法则。另外,“远离政治”也是流行歌曲倾向爱情题材的重要原因之一。此现象在“孤岛”时期的上海表现得尤其明显,在“回归”前的香港、“解禁”前的台湾则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说民国时期部分优秀“时代曲”已达到了“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的社会影响力也不为过。原因何在?除歌词贴近大众外,旋律素材来自于中国的民歌小调亦有很大的关系。中国流行歌曲自诞生之日起就与民歌结下了不解之缘,常见的有“民歌”和“新民歌”两类。前者主要由民歌改编而来,基本保留了原民歌的骨干音和结构,如贺绿汀的《天涯歌女》对江南民歌《知心客》的改编,黎锦光的《采槟榔》对湖南花鼓戏“双川调”的改编,姚敏的《十里洋场》对陕北民歌《五哥放羊》的改编等。后者的笔触并不指向某一首具体民歌,而是在更高的层面上去刻意追求民歌的某些地域特征和意境之美,如黎锦晖的《毛毛雨》、严华的《月圆花好》、陈歌辛的《小小洞房》等。这种将民谣、小调等传统音乐“流行歌曲化”的做法,不论是在民国时期、1949年后的港台,还是在流行音乐占据半壁江山的今日,都不失为一种屡战屡胜的创作手法。与今日大陆将歌曲明确分为“流行歌曲”、“艺术歌曲”、“民歌”几类不同,民国时期和50—60年代的港台却没有如是分类,只有一个较笼统的称呼——“时代曲”。但由于词曲作家和歌星的教育背景、个人风格、美学追求的不同,最终便出现了“时代曲”的“艺术歌曲化”现象,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跨界”现象。由此可见,“跨界”现象由来已久,其源头完全可以追溯至民国。在“跨界”作曲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民国时期上海的刘雪庵、陈歌辛、黎锦光,50—60年代香港的姚敏、李厚襄、叶纯之、林声翕、王福龄,70—80年代台湾的李泰祥、刘家昌、古月,90年代以来大陆的徐沛东、赵季平、叶小钢、三宝等。在“跨界”歌星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民国时期的李香兰、吴莺音、云云(屈云云)、欧阳飞莺,50—60年代香港的葛兰、潘秀琼、方逸华、静婷(席静婷),70—80年代台湾的邓丽君、齐豫、蔡琴,90年代以来大陆的宋祖英、谭晶、姚贝娜、曹芙嘉等。
流行音乐是伴随着近代工业文明和城市现代化的发展而亦步亦趋的,故自然具备工业化大生产的一些特征,如专业化分工日益明确。此特征在民国就已初露端倪。民国时期,大部分歌星相互之间保持着壁垒森严的界限,即每个人基本上只活跃于一个相对固定的领域内,于是便有了“电影歌星”、“唱片歌星”、“舞厅歌星”和“播音歌星”等。当然,由于少部分多才多艺的歌星具备了相当的市场号召力,故也会出现在两至三个领域交叉活跃的歌星。如周璇、李香兰早期都是活跃于播音领域、后期主要活跃于电影和唱片两个领域;而姚莉在上海的早期也是活跃于播音领域、后期主要活跃于舞厅和唱片两个领域,在香港时期则完全成为电影“幕后代唱”和唱片歌星。二度创作如此,一度创作领域亦如此。当一部分未能熟练掌握配器技术的“时代曲”作曲家完成其第一步工作——“旋律”后,便委托时任百代公司乐队指挥的阿隆·阿甫夏洛穆夫(16)和刘雪庵、贺绿汀(17)等“学院派”作曲家来继续完成配器工作,最终交由歌星演唱或录音。为了最大限度赋予趣味性、增强商业性,民国时期的部分“时代曲”在配器上会有意无意地运用“拼贴”古典音乐片段的手法,从而获得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如黎锦光的《讨厌的早晨》和陈歌辛的《可爱的早晨》在曲首均借用了格里格的《皮尔金特组曲》之《晨曲》片段,陈歌辛的《恋之火》挪用了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NO.1)片段,等等。此三首作品都适可而止地运用了“拼贴”手法,表现出此间中国流行音乐作曲家在努力探索、大胆尝试,以期从更生活化、更耳熟能详的旋律中找到帮助自己作品成功的契机,尽管如是“拼贴”还停留在较浅显的“整合”而非“风格拼贴”。抵港后,姚敏、李厚襄等人秉承了上海时期的创作模式,基本将配器工作交由葛士培(Vic Cristobal)、雷德活(Ray Del Val)等“香槟”。由此可见,自民国起“洋琴鬼”——“外援”(主要是编曲、演奏人才)现象就已现于上海的流行音乐创作领域,此惯性随着“时代曲”的南下而延伸至香港时期的“香槟”。究其缘由,一是因为民国时期的上海为“十里洋场”,租界里“洋人”甚多,浓厚的“洋人”气息必然要呼唤与之相匹配的“上层建筑”的存在,而包括舞厅、夜总会乐师和“工部局管弦乐队”在内的“外援”音乐人才的加盟,自然顺理成章地满足了此文化需求。二是对于当时尚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流行音乐而言,人才(尤其是编曲、演奏)匮乏是最为突出的问题,而“外援”力量的乘虚而入则从根本上保证了是时上海“时代曲”编配的“洋味十足”和爵士风格的“原汁原味”。1949年后,香港再度延续了这种“外援”的惯性,似乎也是一件意料之中的事。
明星制度
民国流行音乐事业之所以能够起步于“黎锦晖时代”(1927—1936年)、辉煌于“后黎锦晖时代”,与其“明星制度”的建立不无关系。是时,黎明晖、王人美、周璇等明星的影、歌双栖,“明月”、“梅花”等民营歌舞团(社)和“明星”、“联华”等电影公司所属各类训练班对旗下歌舞人才的培养,“百代”、“胜利”、“大中华”等唱片公司对歌星的包装、宣传,均在逐步完善民国的“明星制”。体制的初创和词曲作家的披荆斩棘,最终使得一流水准歌星的诞生成为可能。诸歌星以一个群体的面貌大踏步地登上了历史舞台,在掀起民国流行音乐高潮的同时,亦提前让香港、台湾地区的受众听到了来自祖国上海的声音,为此后的人才南下做了有力的铺垫。
1949年后,随着“时代曲”人才的南下,上海原有的一套明星制度也随之抵港。此时的香港遗弃了“黎锦晖时代”歌舞团(社)的模式,基本沿用了“后黎锦晖时代”的“影、歌双栖”和电影“幕后代唱”的体制。对于姚莉、白光、张露等“老”歌星而言,南下无非就是将歌唱的舞台由上海转移到了香港,除了适度考虑香港受众对西方流行音乐的关注外,大体上仍继续其原上海时期的风格和路线。由于客观原因,周璇、吴莺音等人滞留上海,使得南下香港的明星阵容相比民国时期稍显薄弱,这就为50、60年代的葛兰、静婷、刘韵、崔萍、潘秀琼等新一代歌星的诞生埋下了伏笔。其中,以葛兰较令人瞩目。在港崭露头角后,葛兰经姚敏、綦湘棠、服部良一(18)、李隽青诸上海时期“时代曲”大家为其量身创作,留下了至今仍堪称经典的《曼波女郎》、《空中小姐》、《野玫瑰之恋》等电影和《说不出的快活》、《台湾小调》、《我爱恰恰》等流行歌曲。特别是上述三部歌舞电影,以合计18首插曲和载歌载舞的冲击力,奠定了葛兰的50—60年代香港流行歌坛代表性歌星的历史地位,使她在一定程度上足以与40年代初期的周璇相媲美。与葛兰不同,同时期的静婷属于“幕后代唱”型歌星,尤其是在《貂蝉》、《江山美人》、《梁山伯与祝英台》等“黄梅调电影”中成功地演绎了“黄梅调时代曲”,从而成为50—60年代香港国语时代曲的又一个领军新秀。1963年台湾的邓丽君在“中华电台”歌曲比赛中荣获冠军,翻唱的就是香港黄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插曲《访英台》(李隽青词,周兰萍曲)。由此可见,此时香港的“黄梅调时代曲”在台湾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之所以说黎锦晖是中国流行音乐的开创者,既指其开中国流行音乐创作的先河,又指其适时推出了明星制度。后来90年代初涌现于香港歌坛的“四大天王”——张学友、刘德华、黎明、郭富城和“女四大天王”——王菲、叶倩文、林忆莲、周慧敏的称谓,便有模仿民国歌舞表演“四大天王”(19)——黎锦晖主持下的“明月社”的黎莉莉、薛玲仙、胡笳、王人美之嫌。今日两岸三地流行音乐界都将举办演唱会作为衡量一名歌星演唱实力和商业价值的尺子,殊不知此传统亦是由来已久。其源头可从1945年3—7月在上海举办的6场“歌唱会”追溯。其间,周璇、白光、龚秋霞、白虹、李香兰、欧阳飞莺、云云等歌星相继在上海举办了自己的“歌唱会”——即今日的“演唱会”。其中,既有“商演”,如周璇的“三天歌唱会共售四百余万元”、“盈余相当可观,周璇名利双收”;(20)也有“义演”,如白光的“独唱会”是为“防涝运动”而“募集基金”。(21)既有今天的“个唱”——“个人演唱会”,如“开得最成功的”(22)李香兰的“歌唱会”;也有多人参与的“歌唱会”,如龚秋霞、胡蓉蓉的“歌唱舞蹈大会”和周璇、白光、白虹等人的“仲夏音乐歌唱会”。诸“歌唱会”引起了当时上海媒体的关注,受到了影迷、歌迷、“白迷”(白光的歌迷、影迷)等受众的追捧,再加上严俊、白杨、秦鹏章、服部良一、陈歌辛等业内人士和“上海交响乐团”(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的参与、助阵,最终形成了“一九四五年是歌唱会年”(23)的公众印象,令人感觉不出此时的上海还陷于“黎明前的黑暗”。
尽管音乐是听觉的艺术,但我们还得承认流行音乐由于其特殊性而不得不成为对视觉效果也有所追求的大众文化。“男要俊,女要俏”是自民国以来“时代曲”的固有传统,这也是为什么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严华、白云等男歌星“娘娘腔”较严重的原因之一。直到今天,两岸三地依然存在着若干带有“娘娘腔”的男歌星,看来这颗种子在民国时期就已埋下。当然,事物的发展也不总是绝对的。1988年台湾歌星赵传以一曲《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引起华语流行音乐界的关注。他和民国时期的韩兰根,70—80年代台湾的凤飞飞、香港的卢冠廷,以及近年来大陆的韩红一样,都是明星制度中的个案,不具备代表性。
今日受众对每年岁末“排行榜”的风起云涌早已习以为常了,流行音乐的商品属性决定了它已然是词曲作者、歌星、唱片公司在过去一年里“业绩”的风向标。其实,“排行榜”在民国时期亦早已有之。类似的歌星竞选活动可追溯至1934年由上海《大晚报》举办的“三大播音歌星竞选”活动。该报纸从是年5月2日至6月14日,每日通过“专栏”刊登参选歌星、播音团体的演唱歌曲、播音时间和得票数字等信息,有效地调动起了读者、受众、诸播音团体和歌星的积极性,大有一番掀起民国流行音乐新高潮的趋势,其当时受关注程度似乎不逊色于70年代后台湾的“金韵奖”(“金韵奖青年歌谣演唱大赛”的简称)、香港的“十大中文金曲评选”和80年代后大陆的“青歌赛”(“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的简称)。尤其是此次“三大播音歌星竞选”的最终结果,以其较客观的标准和公信力,将白虹、周璇、汪曼杰等102位歌星载入史册,既肯定了已然成为大家的歌星,也关注到了颇有发展潜力的新星,堪称民国时期流行音乐界的一次盛事。(24)
从民国第一位歌星——黎明晖起,就已逐步产生了“偶像效应”(25)。张爱玲笔下的“中国的流行歌曲,从前因为大家有‘小妹妹’狂”(26),和黎明晖当时“短发赤脚,短衣短裙”(27)的“小妹妹形象”不无关系。从此以后,歌星和影星的衣着、照片、绯闻等消息铺天盖地地现于《歌星画报》、《明星画报》和《咖啡味》等演艺、娱乐期刊杂志,成为上海市民茶余饭后的谈资。由此可见,追捧偶像、特别是年轻人的“追星”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论是港台,还是内地。80年代中期香港的追星族中就出现过“芳迷珠迷联群结党对垒”(28)的现象。此现象在当今“超女”李宇春的“粉丝”——“玉米”和其他歌星的“粉丝”之间也曾发生过。该现象一方面说明了流行音乐的“大众性”和歌星的社会号召力,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其劣根性,这也是“学院派”人士对其不耻的主要原因之一。客观地讲,由“偶像效应”而引起“追星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然“梦想成真”是其主要原因之一,这早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一曲成名”、“一夜走红”是流行音乐界自民国以来一直存在的现象,也成为几代追随者踏入此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了更好地帮助歌星扬长避短,词、曲作家有时需要为某个歌星量体裁衣式地创作,即由一、二度创作形成“固定搭档”。中国的流行音乐词曲作家为歌星量身定做地创作自民国起就已有之。此传统最大限度地缩小了二度创作和一度创作之间的间隙,以其公认的艺术效果和成功的商业效应赢得了几代流行音乐创作队伍的青睐,并一直发扬光大至今日,虽然有时作曲家不得不委曲求全地让步于有着一定艺术局限性的歌星。此“固定搭档”模式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存在于两岸三地的流行音乐创作中,如民国时期的上海组合——20年代的黎锦晖、黎明晖父女,30—40年代的李厚襄和周璇;香港的“铁三角”组合——50—60年代的陈蝶衣、姚敏和姚莉,70—80年代的黄霑、顾嘉辉和罗文;台湾的“铁三角”组合——60年代的琼瑶、古月(左宏元)和凤飞飞;新时期的北京组合——80年代后的王酩和李谷一、谷建芬和毛阿敏,90年代以来的叶小钢和朱桦、三宝和沙宝亮等。“时代曲”之所以能够造就一批又一批的歌星、掀起一次又一次的高潮,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与国语电影唇齿相依”(29)。“唇齿相依”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非常客观地道出了自民国以来电影音乐和流行音乐的相互依存、共生共荣的并行发展关系。自“黎锦晖时代”起,就有了将流行歌曲植入电影之中的创作模式。此模式也影响到了1949年后的香港和台湾、80年代以来内地的流行音乐与电影音乐创作,并于70年代逐步拓展到电视剧音乐创作领域,使得“流行音乐”和“影视音乐”这对大众音乐姊妹艺术始终保持着齐头并进的发展势头,进而取得了双赢的积极效果。
结语
1949年后,两岸三地因政治制度的不同而形成了流行音乐的差异。其中,内地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时代曲”被统统斥责为“靡靡之音”、“黄色音乐”,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香港因其属性而能够容纳“时代曲”,并于不久后逐步衍生出港产流行音乐——“粤语流行曲”;台湾因与内地“本是同根生”(30),顺理成章地延续了民国“时代曲”的生命,并于80年代末放飞出自己的声音。如果将80年代末台湾“解禁”前整个两岸三地的流行音乐比作一条龙的话,那么当时的发展态势是:香港是龙头、台湾是龙身、内地则是龙尾。然而随着台湾“解禁”和两岸交流不断向纵深挺进、香港回归的倒计时和内地的进一步开放,两岸三地流行音乐发展的排序似乎恰恰颠倒了过来。这是30年前的人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其足以说明——历史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当然,内地的“后来者居上”也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其“反向输出”(31)由来已久。内地向香港的“反向输出”既包括创作“反向输出”,如80年代末李海鹰在内地创作的“刘欢版”、90年初由香港传遍海外的“吕方版”的《弯弯的月亮》和80年代末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在台湾的“被引进”,也包括人才“反向输出”,如生于内地于80年代末登上香港歌坛的王菲、黎明等。台湾1987年7月的解除“戒严”、1988年1月的解除“报禁”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流行音乐创作的一次飞跃。这和民国流行音乐崛起于五四时期、新时期内地流行音乐的奔流颇为相似:此三个时空环境都秉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新思想、新观念、新作品和新人的涌现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温床。
1997年香港回归后,随着香港和内地的交流日益增多,香港的流行歌坛出现了“国语时代曲又有冒起的现象”(32)。或许这就是历史的轮回。半个世纪后,因为香港和内地关系的巨变,国语时代曲再度重回到香港流行音乐的舞台中心,虽然未能实现一统天下的历史局面。这是姚敏、李厚襄、黄沾、顾嘉辉等人当时难以预料的。表面上看,这不过是中国流行音乐发展历程中的一个偶然现象,但如果我们将其放置于20世纪滚滚向前的中国历史大潮当中的话,它似乎又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因为历史就是这样,常常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也正因为此,一部分关注它的后人和学者恰恰就是于诸“偶然现象”中发现了、享受到历史的无穷魅力。尽管我们不得不承认香港、台湾的流行音乐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对内地的流行音乐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但我们仍然要面对一个客观事实——包括香港、台湾在内的整个华语流行音乐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对世界流行音乐产生重大影响的“大家”和“大作”。除了极个别作品外,港台流行音乐始终没有远播海外。造成此状况的原因比较复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作为一个面积约1104平方公里、人口刚过700万的“弹丸之地”和面积约3.6万平方公里、有着2228万人口的海岛,香港、台湾在文化艺术领域(电影除外)的建设始终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以与其在物质建设领域相媲美。这既是香港、台湾流行音乐的不足,也是中国流行音乐的遗憾。就此而言,香港、台湾流行歌坛的某些颇有影响作品的传播还不如民国时期上海时代曲的代表作——《玫瑰,玫瑰我爱你》(电影《天涯歌女》插曲,吴村词、林枚曲,姚莉唱)。内地现在又何尝不是?
21世纪的中国流行音乐——任重而道远!
注释:
①从某种程度上说,民国时期的上海(尤其是“租界”)也具有“一国两制”的特征,因而民国流行音乐便自然而然地染上了“殖民地”色彩。
②民国时期乃至五六十年代的港台均习惯将“流行歌曲”称之为“时代曲”,故本文将这两个名词通用。
③水晶《流行歌曲沧桑记》,(台北)大地出版社1985年版,第66页。
④沈冬《音乐台北——建城百年的历史回响》,《音乐艺术》2006年第1期,第102页。
⑤1988年8月8日—12日,海峡两岸“中国作曲家座谈会”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举行。这是两岸专业音乐界四十年来的首次聚会,被吴祖强誉为“在我国现代音乐史具有历史性意义”。参见《吴祖强撰文畅叙四十年来的首次聚会》,《音乐世界》1988年第11期,第41—42页。
⑥张爱玲《谈音乐》,《张爱玲散文全编》,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页。
⑦鲁迅《阿金》,《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03页。
⑧李德钊《省府推行音乐教育之主旨》,《音乐教育》1933年第1卷第2期,第15页。
⑨白先勇《上海童年》,《姹紫嫣红开遍》,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⑩当时上海人将在上海舞厅、夜总会、唱片公司谋生的来自菲律宾、俄罗斯等国的外国乐师统称之为“洋琴鬼”。参见水晶《流行歌曲沧桑记》,大地出版社1985年版,第166页。
(11)许常惠《中国新音乐史:台湾篇(1945—1985)》,刘靖之编《中国新音乐史论集(1946—1976)》,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1990年版,第222页。
(12)Theodor W.Adorno(with the assistance of George Simpson),“On Popular Music”,Simon Frith and Andrew Goodwin On Record,New York:Pantheon Books(1990), p.311.
(13)同注(12),第309页。
(14)王丽慧《从唐宋词到当代流行歌曲》,复旦大学2007届博士学位论文,第153页。
(15)即“香”港的菲律“宾”人。参见黄霑《粤语流行曲的发展与兴衰:香港流行音乐研究(1949—1997)》,香港大学2003届博士学位论文,第132页。
(16)亦译成“夏亚夫”(Aaron Avshalomov,1894—1965),美籍俄国作曲家。据歌星龚秋霞的丈夫、电影导演胡心灵回忆,“百代公司的和声大部分是他配的”。参见水晶《流行歌曲沧桑记》,第261页。
(17)据胡心灵回忆:“百代公司的和声”当时除了阿隆·阿甫夏洛穆夫外,“刘雪庵、贺绿汀这些学院派的人可以勉强配一点。”参见水晶《流行歌曲沧桑记》,第262页。
(18)上海“孤岛”时期较活跃的日本作曲家,其中文名字叫夏瑞龄,代表作为《苏州夜曲》、《说不出的快活》等。
(19)岳尚《明月社的四大天王》,《中国电视戏曲》1995年第4期,第32—33页。
(20)吴剑《何日君再来——流行歌曲沧桑史话(1927—1949)》,北方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35页。
(21)同注(20),第37页。
(22)郑德仁口述。《音乐人生:寻访中国第一支爵士乐队》,2009年9月18日网易论坛http://bbs.local.163.com/ bbs/localsh/151865244.html.
(23)同注(20),第42页。
(24)同注(20),第23—27页。
(25)据王人美回忆:黎明晖“在二十年代的上海,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曾经有人给她写信,信封上既不写地址,也不写姓名,只画个短头发的姑娘头像,她居然能收到。”参见王人美(口述)《我的成名与不幸——王人美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41页。
(26)同注⑥。
(27)王人美(口述)《我的成名与不幸——王人美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45页。
(28)同注(15),第78页。
(29)余少华《乐犹如此》,国际演艺评论家协会(香港分会)2005年版,第196页。
(30)梁茂春《让音乐史研究更全面——关于台湾、香港音乐研究》,《音乐艺术》2007年第2期,第65页。
(31)同注(15),第170页。
(32)梁宝耳《香港的流行音乐》,朱瑞冰主编《香港音乐发展概论》,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371页。
标签:音乐论文; 民国论文; 周璇论文; 香港流行音乐论文; 流行音乐论文; 流行音乐风格论文; 香港论文; 艺术论文; 台湾论文; 鸾凤和鸣论文; 毛毛雨论文; 流行歌曲论文; 民谣论文; 女歌手论文;
